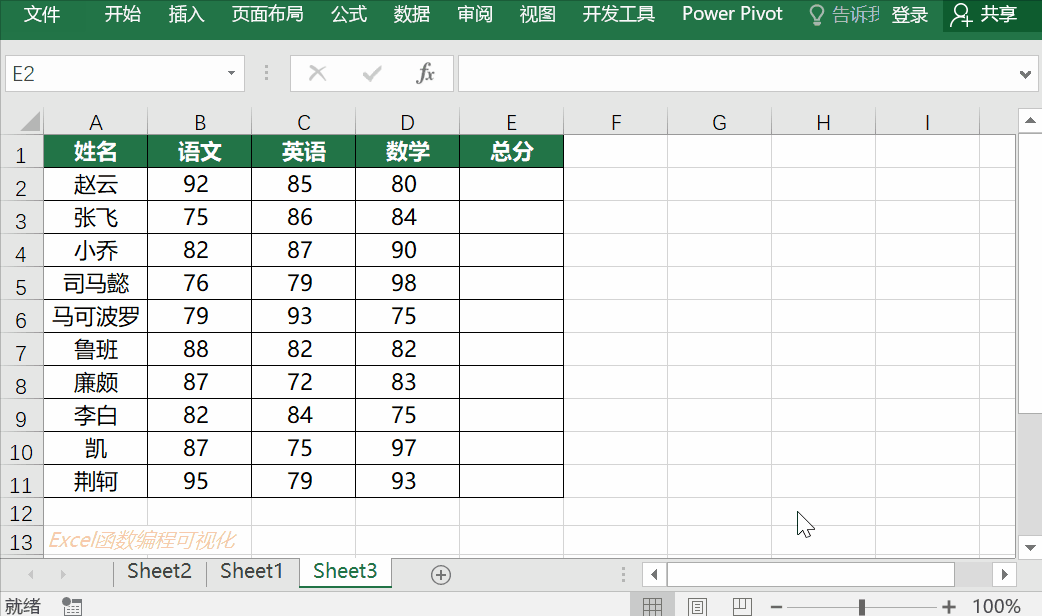第七章迷茫(第六章边缘人)
第六章 边缘人我们在考察了家庭政治中的礼义和委屈之后,还要进一步来看,这种正义观念对每个人意味着什么义者,宜也家庭生活若能做到因礼成义,就要让每个人各得其所,现在小编就来说说关于第七章迷茫?下面内容希望能帮助到你,我们来一起看看吧!

第七章迷茫
第六章 边缘人
我们在考察了家庭政治中的礼义和委屈之后,还要进一步来看,这种正义观念对每个人意味着什么。义者,宜也。家庭生活若能做到因礼成义,就要让每个人各得其所。
那么,人人各得其所是什么意思呢?简单说来,就是让每个人实现其人格的价值,按照一个人应有的方式过日子,使他在更完全的意义上成为一个人。如何成为一个人,我们在第二章已经简略谈到了。首先,在家庭生活中过日子,是人格的最基本要求,可概括为“以家成人”;因为赌气自杀,是通过赌气来实现自己的人格价值,可以概括为“以气成人”;为了面子而自杀,则是通过挣面子这种外在方式,实现人格价值,可以概括为“以面成人”;而通过想清楚过日子的道理,按照礼义,在日常的过日子中实现人格,则是“以理成人”。我们在第三部分会分别讨论对人格的这四种理解。在本章,我们就首先来看,当地人如何理解一些边缘人的自杀。
6.1 疾病
研究边缘人的自杀,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在中国的自杀者当中,精神疾病究竟意味着什么。研究者发现,中国的自杀人群中有大约63%的人患有精神疾病。这个数字虽然不如西方国家的90%以上那么高,但毕竟超过了半数,也不能算很低了。因此,我们不能简单地说中国的自杀者有无精神疾病,而要深入到精神疾病的文化意义。
我们在第一章已经看到,在西方精神医学中,自杀一般被认为是精神疾病导致的;在《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第四版)》(DSM-IV)中,有无自杀意念,甚至被当做判断有无抑郁症的指证之一。而在孟陬,我却看到,精神疾病患者的自杀,往往被当成自杀的例外。在一般人的眼中,多数自杀不是精神疾病导致的;即使这些自杀者患有精神疾病,他们的自杀也往往不被当做精神疾病的一个结果。要理解当地文化对自杀与精神疾病关系的看法,我们首先要考察几个典型的精神疾病患者的自杀能力。
我在田野研究中遇到过好几个有明显精神疾病的自杀个案,但总是难以了解他们的详细情况。我的受访者往往对这样的个案不感兴趣,甚至也推测我不会对他们感兴趣。当我问起这样的自杀来,他们会说:“那不算,是个疯子。”比如,兰皋的一位向导向我讲了一个叫求美的女孩的自杀,告诉我,她是因为被一个男人勾引,后来又遭到父母的责备而喝农药死的,随后我又问他,村里还有没有别的自杀个案。他想了想说:“也有,可是不像求美这一个字这么有教育意义。比如,我的表弟就喝药死了。可他是个傻子,不算。”(参见6.3)
同样,武都的一个人跟我讲了好几个个案后,儿乎忘了他亲弟弟就是自杀死的。我问起他来,他说:“那不算自杀,他疯。”(参见6.3)娘娘庙村的一个年轻人有明显的抑郁症,而人们也找不到别的什么原因导致了他的自杀。他的一个朋友就对我说:“他自杀是因为抑郁症。”他的言下之意是,他没什么可说的,因为是抑郁症,而不是什么更重要的原因导致了他的自杀,因而我就可以不必研究他了。
人们并不是毫无医学常识。农民们知道精神疾病有时候会导致自杀。但他们认为,这些自杀不是典型的自杀。当我说我要研究自杀的时候,他们就认为,我只研究那些有点社会原因、有教育意义的自杀。那才是典型的自杀。
当然,人们在谈到典型的自杀时,也可能说:“她忒受罪了,差不多都疯了,所以自杀。”“他自杀前变疯了。”这些自杀者在自杀前往往表现出精神疾病的症状,但人们不认为这些病是他们自杀的最终原因,而是认为,那些导致他们得病的因素,才是自杀的真正原因。疾病和自杀,都是这个原因造成的结果。
我们在考察葛曼的自杀时谈到了,像“小姐”这样的边缘人的自杀,也被认为不算自杀。她们的自杀,也不值得研究。研究者们不断指出,中国文化与基督教文化的一个区别就在于,自杀往往被赋予积极意义。〔1〕自杀是勇敢的反抗,自杀者往往是好强的烈性人。疯子、傻子、“小姐”等边缘人没有完整的人格,所以,人们不认为他们的自杀是因为勇敢和人格价值。在很多情况下,某些人虽然患有精神疾病,但他们的自杀并不是这种精神疾病导致的,他们自杀的实际原因和动机与别人没什么不同,但他们的自杀还是被赋予了不同的意义,不被当成典型的自杀。所以,当我采访的村民说他们的自杀不算什么的时候,他们的意思是,虽然这些人自杀了,但他们的自杀并没有社会意义和积极因素。
孟陬民间关于精神疾病的词汇有“魔怔”、“傻”、“疯”等。其中,“魔怔”的含义最轻。其含义本来是邪魔附体导致的行为不正常。现在,人们若是说谁魔怔,那一般就是指,此人行为奇怪,但还没有完全变成疯子或傻子。医学上诊断的抑郁症,就常常被称为“魔怔”。
“傻子”和“疯子”是对有精神障碍者的一般说法,而两者并不相同。傻子是智力迟钝的人,疯子是精神错乱、胡言乱语、行为躁狂的人。在一些村子,我偶尔会看到一些精神不正常的人在街上游逛,一时并不容易区分,他们究竟是傻子,还是疯子。当地人有时候也并不区分这两个称呼,甚至把光棍和乞丐也称为疯子或傻子。
6.2 魔怔
一家媳妇若是自杀了,我一般比较难从她婆家的人那里得到准确信息,因为他们总会回避自家的责任。但武都村的玉英的情况却不是这样。我在问起玉英的小叔子,他嫂子为什么自杀时,他很爽快地讲了起来。因为玉英明显有些魔怔,她的丈夫似乎可以不负责任。他说:
“一开始,俺嫂子老是不高兴,说她不想活了。我跟她聊起天来,她总说活着没意思。她老是说:‘我就是想跑到地里去好好哭一顿。’那时候我有个错误的看法,我觉着她因为跟俺哥关系不好,才会这么想。俺哥的脾气是不好,他们老是吵架。后来,她找医生看了看,医生说,她得的是更年期综合症。我这才明白,她这个状态不是因为跟俺哥的关系,是因为她的病。
“她在得这病以前,老跟俺哥吵。她出身好,家里边富,她爹还是个挺有名的书法家,字写得好。俺这个嫂子也聪明,爱交往人,特别能干,知书达理。她也非常好强,别人比她强了就不行,她就得想办法超过别人。可是俺们这个家庭不一样,是一般人家。俺哥上过学,可是念的书也有限,又不怎么能干。俺嫂子跟俺哥不投脾气,就觉得俺哥没什么能耐。俺哥干活也一般,挣不了多少钱来,俺嫂子就老嫌他不好好干活。他们也常为这个吵架。俺哥那个脾气,一急起来就摔东西。为这个,至少摔坏过两口锅,好几张桌子。我好几次亲眼见他为这个掀桌子。
“自打那个医生说她有病以后,俺哥就不怎么跟她吵了。医生跟俺哥说,老吵架对她身体不好。俺哥知道了她有病,就想方设法不刺激她。可她还是好不了,总是特别烦。虽然俺哥因为她这病容忍她,她的状况还是越来越不好,睡不着吃不香。我有时候就问她:‘你为什么不欢喜呀?’她说:‘活着不如死了好。你不觉着死了比活着好得多吗?’你听,这是正常人说的话吗?
“从医生说她有病后,过了半年,她就吃安眠药了。那天晚上,俺哥不在家,在地里干活呢,我也在地里干活。那是麦熟的时候了,地里活多。因为那一段俺嫂子老是说死呀死的,俺哥不敢把她一个人留在家里。可是地里有那么多活,他也不能不收麦子呀。俺嫂子睡着得特别晚,得有十二点了。俺哥看着她睡着了,觉着不会有危险了,就去地里干活了。快早晨了,他才回来,俺嫂子就已经吃了安眠药半天了。那天我也是早晨才回的家,有人就跑来跟我说:‘忙去你哥院里。’我知道出事了,忙到他这院里,俺嫂子早死了。她那年46岁。”
他讲完之后,我问:“你嫂子是个怎么样的人?平常事她都能想得开吗?”他说:“俺嫂子上过学,是个聪明人,也不死心眼子。一般的事她都想得开。”我又问:“那她这回怎么想不开了呢?”他笑着说:“她有病啊。再聪明的人也会得病啊。她是挺能干的,那也架不住生病呀。一开始我觉得她这状态是因为老跟俺哥吵架,后来我发现我不对了。”
玉英的小叔子几次强调,他当初认为嫂子的状况是因为和他哥的吵架是错了。我想让他解释一下为什么认为自己当初错了:“你怎么就认为自己原来的想法不对呢?”他说:“俺们知道她生那个病以后,我就意识到,她的这种状态不是因为吵架,是因为生病。”
我又问:“那你认为她的病和吵架没关系吗?”他说:“有时候我也觉得生病和心理状态有关系。像前几天,我生病了,一跟朋友们聊天,就不觉着难受了。说上几个钟头的话,我也不觉着累。要不然,我站上几分钟就受不了。她这病当然跟吵架有点关系,要不俺哥知道她这病以后就不跟她嚷嚷了呢。”
虽然他承认,夫妻之间的吵闹还是和玉英的病有关系,但他从未认为,那所谓的“更年期综合症”会是吵闹的一个结果。他用自己的感受来描述这一关系,好像她的病只是有点心理症状的肌体疾病,只要她处在一个较好的环境里,病情就会缓解一些。
但从我的被访者所描述的情况来看,很可能是夫妻之间的关系导致了玉英的抑郁状态。别的村民们也认为,玉英后来的状态应该就是夫妻的频繁吵架造成的。即使我的被访者,一开始也是这么认为的。但在医生做出那个诊断之后,他却完全改变了先前的看法。我问他为什么这么聪明的人还会有想不开的时候,他的回答是,即使是聪明人也会生病。他谈起这种心理障碍来,就好像在讲一种无法通过“想开”克服的生理疾病似的。
凯博文教授曾经谈到,中医喜欢用生理概念来描述心理疾病。〔2〕而这正是玉英的小叔子所做的。由于医生的诊断,他认为导致玉英变得魔怔和不满的,不是家庭争吵,而是某种生理性的变异。
玉英的丈夫后来不再和玉英吵了,因为她有病。这并不是因为他认为争吵导致了疾病,而是因为他觉得争吵会恶化她的病情。换言之,他已经把玉英看做了一个与正常人不同的病人,将她排除在了正常的家庭生活之外。
我不敢断言,玉英小叔子究竟是真的认为争吵没有导致玉英的疾病,还是仅仅想减轻他哥哥的责任。但玉英的病确实成了她丈夫的一个借口。疾病彻底改变了人们看待她的状况和自杀的角度。这病使人们把她当成了一个不正常的人,把她排除出了正常的家庭生活,于是,她的自杀就不再是对丈夫的反抗,而是疾病导致的自然结果。疾病与我们在第五章看到的神秘解释起到了非常类似的作用。
凯博文认为,精神疾病的躯体化可以帮助中国人获得政治上的安全。在20世纪70年代那样的政治环境中,把精神疾病理解为躯体性的,而不是当做政治性的反抗,就可以避免政治上的麻烦。而在家庭政治中,躯体化同样帮助全家避免了家庭纠纷。虽然玉英的抑郁和自杀好像都是家庭矛盾导致的,但医生的诊断却使她的自杀减弱了这层意义,好像和典型的自杀不同,不是出于反抗的目的。
这使我想到了田野研究中经常遇到的一个问题:社会原因导致的精神疾病和完全病理性的精神疾病的意义有何区别?颇有几个人是因为家庭原因导致的精神失常。比如,渐离的一个媳妇青云因为和婆婆有激烈的冲突,而变得魔怔了,总说自己能看到鬼,还喝过农药。娘娘庙村的一个媳妇愁予的丈夫是个混混,整天打她,后来丈夫还坐了监狱,她也变得疯疯癫癫的,结果喝农药自杀。虽然这样的自杀明显和精神疾病有关,但人们在谈到这些案例时,还是会说,家庭矛盾是导致自杀的原因,而精神疾病不过是间接的原因而已。
他们会把精神疾病当做家庭矛盾的一个结果,自杀是同一原因的另一个结果,而不是精神疾病的结果。于是,这些自杀者都被当做典型的自杀,反映了自杀者出于委屈的反抗。玉英的小叔子虽然一再强调她的自杀是疾病引起的,但其他村民,特别是玉英的娘家人,却完全不这么看。他们虽然也并不否认玉英确实有病,但并不认为这病就可以掩盖玉英丈夫的责任,如果她丈夫好一点,玉英就根本不会得这样的病。
人们往往觉得,有病理性的或遗传性的精神障碍的人的自杀,更多是疾病造成的。但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自杀也并不只是一个医学问题。我们可以再看一下茹蕙的例子。
茹蕙是七坡村一个40多岁的妇女,有两个女儿、一个儿子,在1999年上吊身亡。娘娘庙镇的医生告诉我,她有明显的精神障碍。
茹蕙的一个亲戚说,她的母亲和两个哥哥都有精神病。她娘家村的人都知道茹蕙的母亲精神病很严重,她总是跑到街上去胡言乱语。她大哥也病得很厉害,在18岁自缢而死。她的二哥起初没有发病。但他在中学毕业后找到了一份工作,因为过分高兴而一下子变疯了。不过他后来治好了,没有再犯病。
刚结婚的时候,茹蕙也没有什么异常。她不言不语的,老实文静,和街坊邻居相处得很好。但是,她在生了一个孩子之后就变了。她不会像自己的母亲和哥哥那样到处乱跑,而是胡思乱想。发生什么小事,她都会琢磨上半天。比如,有一次她的耕牛掉到水坑里淹死了。这在农村里不是什么稀奇事,谁也不会太当一回事。但是茹蕙没完没了地想这事,好像无法承受这个损失。连续一个多月她都难以释怀。她的公公婆婆觉得她不对劲了,就相互告诫说:“不管她要什么,咱们都尽量满足她。”过了几个月,她情绪稳定了一些。
他们后来分了家。茹蕙和她丈夫到另外一个院里住去了。据人们说,这倒不是因为茹蕙和公婆处不好,而是因为她对一些小事太较真了,所以就容易和人们发生冲突。但这些冲突一般都不大。
茹蕙并不是随时都这样,但隔一段就会严重一些,那时候就会和丈夫因为很多小事吵架。比如他们在地里干活的时候,经常就会因为怎么干活争起来。茹蕙要是想用什么法子,就一定要丈夫听她的。她丈夫的脾气也不大好,经常受不了她这态度。但他还是努力满足茹蕙的要求。
大约在茹蕙死之前两个月,她得了胆囊炎。她到娘娘庙镇医院里去,医生说那不是什么严重的病,就给她开了一个方子。但茹蕙总是认为自己得了特别重的病,不相信娘娘庙镇的医生。她坚持要去更好的医院,于是走了县里甚至市里的好几家大医院,得到的诊断都是一样的。茹蕙总以为她丈夫和儿子在骗她。她的小姑子跟我说:“有一次是我跟她去的医院。回来的路上,我叫她到我家去吃晌和饭。她在我家央求我说:‘俺儿子现在15岁了,我也没有什么怕的了。你们怎么就不能跟我说实话呢?要是这病治不好了,咱们也不用到处去找好医生了。你跟我说,医生到底是跟你怎么说的?什么我都能承受。’”
凡是茹蕙想要的东西,她丈夫和儿子都尽量满足,但这一次,人们实在没有什么可以告诉她的了。
关于她的死,七坡村人有比较流行的一个说法:在她自杀前两天,茹蕙突然说,他们看的那个黑白电视不好。她丈夫和儿子立刻就上县城去买了一台彩电回来。那天晚上他们一起看这台彩电,茹蕙又说:“这台电视忒小。”第二天,她丈夫和儿子又去了一趟县城,给她换了一台大彩电。一个村民对我说:“他们把电视抬回来,茹蕙好像满意了,什么也没说。两天以后的晚上,老两口坐着看电视,他们的小闺女在另外一个屋里,他们儿子出去了。茹蕙的男的靠着被摞打了个盹。他一睁眼,看不见茹蕙了。他到处找,最后发现,他媳妇在门洞子里上了吊了,那时候已经死了。”
我最早从七坡村的一个村民那里听说茹蕙的故事,后来采访了她的小姑子和她娘家的亲戚。她娘家的亲戚告诉了我她家的情况,说:“茹蕙不像她娘和她哥那么严重,可是也偶尔魔魔怔怔的。”这是我一个重要的向导,曾经给我提供了很多自杀的线索,但在我没有特意问起茹蕙的时候,她从未提到过这件事。她说:“她这个你问不出来什么,那不算自杀。她一家人都魔怔。”
我在孟陬遇到的疑难病症患者不止这一例。比如在龙堂村,一个女人秋兰得了肾炎,却认为自己得了不治之症,疑心了半年多,上吊死了。她和丈夫关系很好,丈夫据说颇有些怕老婆。而因为她家里从来没人精神有过问题,她以前也没有魔怔过,所以谁都不认为她那是有病。人们还是说,她的自杀仅仅是因为想不开。但由于她和丈夫实在没有什么过节,更多的人就说她是遇见鬼了。她是在野地里一个小破屋里上吊的,所以一开始谁也找不到她。
据说,她向儿子托梦,告诉他自己在哪里,大家就找到了她的尸体。在兰皋,一个总是头疼的人目前总是怀疑自己得了脑瘤。在他的一个叔叔出殡之后,目成用孝袍把自己吊死了。人们都认为他不可能魔怔了。他的口袋里有一封遗书,上面写的都是人们如何继承他的财产。于是人们说,一个有病的人不会写这么清楚的遗书。大家怀疑他还是因为家事自杀的。他此前和妻子没有什么矛盾,但人们还是觉得,应该是他妻子的坏脾气导致了他的死。
与秋兰和目成相比,茹蕙的病未必更重。虽然娘娘庙镇的医生说她确实有病,但人们大多不是根据医生的诊断做出判断的。他们的主要根据是,茹蕙娘家好多人有病。
七坡村的人都说,她家里没有多少严重冲突,他们的争吵是家家都有的那种小的误会和口角。因此,她的自杀不该有别的原因。但在和她小姑子进一步谈了一次以后,我认为事情恐怕要更复杂些。
虽然茹蕙确实和公婆没有严重冲突,但他们的关系并不好。她小姑子说:“俺嫂子忒敏感了,俺娘受不了她。他们知道她有病,千方百计满足她的要求,可还是过不到一块去。忒不方便了,这才分的家。分家之后,俺哥住得离俺爹他们特别远,两家都不怎么来往了。”茹蕙的公婆虽然尽量容忍茹蕙,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关系好。因为茹蕙的病,人们自然会尽量不招惹她,以免她过于敏感;但长期这样下去,老人们都受不了。在别人家看来很普通的小事,在茹蕙看来可能就会变得特别敏感。老两口之所以对茹蕙如此宽容,并不是因为他们关系特别好,而是因为他们无法把她当成一个正常的儿媳妇来看待。换言之,她不被当成家庭的正常成员,而是一个应该特别注意的病人。这才是他们分家的真正原因。
茹蕙和她丈夫之间的关系也与此类似。她丈夫的脾气也并不好,但他还是尽量满足她的要求,听她的话。他会尽可能容忍她那些地方,但这并不说明他们的关系好。像关于电视机的那个事,丈夫和儿子确实满足了茹蕙的过分要求,但那是因为担心她犯病,而不是因为他们对她特别好。而茹蕙的小姑子也告诉我,其实这件事并不像人们传说得那么离奇:
“他们家里是有一台黑白电视,他们早就准备买一台彩电了。那一天,俺哥跟俺侄子买了台彩电。他们买回家,那台电视画面不好,俺嫂子就唠叨了几句。他们又去换了一台大点的,效果好多了。他们看了一晚上电视,就睡觉了。第二天早上,俺哥发现俺嫂子找不着了,就琢磨,她怎么起得这么早呢?他就往外走,在门洞里发现俺嫂子吊在那儿,死了。”
她还谈到,茹蕙死前还有一件事让她不高兴:“她上吊前几天,她闺女上段庄的天主教堂去了。俺嫂子知道以后,跟她闹了一顿。她上吊的时候,她们这事还没有完呢。这也许是她上吊的一个原因。”我在《麦芒上的圣言》里谈到,当地农村一些人对天主教徒有成见,所以家长大多不愿让孩子去天主教堂。〔3〕茹蕙因为此事和女儿生气,是可以理解的。
茹蕙家里有很多麻烦事,有很多原因可能会促使她自杀。我当然不是说,她没有精神疾病,或她的自杀不是疾病引起的。上面说的这些事,看来都不足以导致她的自杀。最可能的原因,还是她的疾病。但我关心的是,为什么人们把她的自杀归结为精神疾病,但在秋兰和目成的例子里就不这么做。茹蕙与另外两个人的区别在于,人们已经把她明确认做了精神病患者,她娘家人的病尤其使人们这样认为。而秋兰和目成一直被当成正常人,过正常的日子。虽然他们怀疑自己有病也有很长时间了,但人们还是不认为是精神疾病导致了他们的自杀。
在当地人的观念中,魔怔的人处在正常人和疯子之间。一方面,他们还有相对正常的家庭生活;但另一方面,他们又常常不被当成正常的家庭成员。他们的自杀有可能是家庭矛盾导致的,也有可能是精神障碍导致的。如果人们把他们当成正常人,他们就不会认为这些自杀是精神障碍导致的;如果人们把他们当成魔怔的人,精神疾病就成了他们自杀的主要原因。而由于魔怔的人的地位较有弹性,人们也可能从不同角度看待他们的自杀。因为大家把玉英和茹蕙当成了魔怔的人,她们的家庭矛盾就显得不重要了。她们的自杀也被当成非典型的自杀,是由精神疾病引起的,而不是由委屈导致的反抗行为。
6.3 癫狂
我在6.1谈到,兰皋的向导对我讲了求美的故事后,不大愿意谈他自己的表弟的自杀,因为那是个傻子。我求他还是讲一下,他就简单地讲了这个过程:
“我那个表弟超远是个傻子。你要是第一次见他跟他说话,会觉着他挺知事、挺精神的。他跟你打招呼说话,都挺好的,可是你要再往下说,就不行了。他都20多岁了,还是不会干活,整天什么也不做,就知道吃。他白天到处跑,疯玩。附近几个村里都知道俺们村有这么个傻子。谁也不把他当人。他有时候在公路上骑着一辆车子,看见一个俊点的闺女就追人家,跟人家喊。有一天,他又跟我说些个没用的话。当时有好多人呢,他又那么冒傻气,我看不下去了,就扇了他一巴掌。他回到家就喝了药死了。他娘跟他姨也都是傻子。”
虽然超远表哥的叙述非常简略,我们也足以看出,超远的自杀并不是他的病导致的。他虽然很傻,总是做些糊涂事,但他自杀也是因为委屈,和别人没什么不同。当我的向导微笑着讲到他自己如何打了超远耳光,然后他又如何喝农药自尽时,我感到非常惊讶。而他最后指出超远的母亲和姨也是傻子,是为了强调超远确实是个傻子,这个个案实在没什么可研究的。他这么简单地讲完此事,并不是在描述一个个案,而只是向我指出,此事是多么没有研究价值。
但这个村里的另外一个人告诉了我更多关于超远的事:“虽然他有点傻,但超远还是种地干活的。每到麦收的时候,他不像别人那样,把粮食都存起来。他把收来的麦子到处乱放,满院子都是。过不了多少日子,老鼠就给他吃没了。他没吃的了,就得去打点零工挣钱,比如帮大队里干干活什么的。他有了钱也不过日子,都用来喝了玩了。”
超远不藏粮食和乱花钱确实是不过日子,但这并不能证明他在智力上是个傻子。兰皋另外一个人说:“超远的爹可和他不一样,是个聪明人,比一般人都聪明。可惜,他娶了个傻媳妇,从此也就不好好过日子了。爹娘都不管超远,他得不到什么管教,也就变成傻子了。超远的爹死得早,他娘出门了。超远必须得挣钱自个过。”超远的姥姥家是西堂村的,滋兰和我说过她家的情况。她说:“我忒知道她了。超远的姥姥就是个傻子,找的西堂的婆家。超远的姥爷就因为娶了个傻媳妇失望了,不好好过,到处靠人。超远的姥姥知道了,一气之下就回了娘家。超远的娘是老大,有一个妹妹一个弟弟。仨孩子都在西堂长大的,爹娘都不管他们。两个闺女都傻,可是男孩不傻。”
根据这些人的说法,超远的姥姥是这个家族中的第一个傻子。她的两个女儿和一个外孙也都是傻子。那么,超远之所以傻,首先是因为遗传。但无论他还是他的母亲和姨,先天失教是导致他们傻的重要原因。因为没有得到教育,超远从小不懂得怎么过日子,这一点更使人们觉得他是傻子了。
超远的娘虽然也智力迟钝,但她还是结了婚,生了几个孩子。超远却没有结婚,也就不能过正常日子。他虽然也干活,但人们都“不把他当个人”。于是,他的表哥可以当着那么多人的面打他耳光,好像他不知道丢脸似的。即使在超远因为这一耳光自杀之后,人们也不认为他的表哥负有多大责任。他自己在讲这个故事的时候,甚至在轻松地微笑。
这倒未必是因为超远的表哥多么残酷,而是因为他认为超远就不该享受正常人的尊严。对于像超远这样的边缘人,谁也不该为他的死负责,也没有谁替他追究。人们可以逗他们,取笑他们,向他们咆哮,羞辱他们,而都不必负什么责任。如果这样的人生气了,人们不过一笑了之。有人说:“人们就把他们当小孩一样逗。”这些边缘人确实和小孩很像。他们和小孩一样,不结婚,没有成为一家之长,从而不是完整意义上的人。在社会意义上,他们被排除出了正常人的范围。有些宽厚的村民说,超远要是受到正常的教育,就未必是个傻子了。因为无法通过教育长大成人,超远仿佛永远是个孩子,被人们也永远当成孩子来看待。当然,我们现在已经很难假设,他的傻究竟只是因为没有教育而不会过日子,还是真的有生理性的原因。
有个村民更详细地讲了他自杀那天的经过:“有一回,超远和另外几个年轻人给村委会干了点活。村委会的一个干部是超远的表哥,给他们发钱。他这个表哥知道,超远一旦拿了钱,很快就会花完,根本不会用来过日子。他就说:‘我给你拿着这钱。等到浇地或是买化肥的时候,我再把钱给你,你用在正地方。要不,我怕你一下就花光了。’他这个表哥是好意,怕他浪费钱。可是超远不懂这个。他看别人都拿了钱了,自个拿不着,就不干了,跟他表哥嚷起来了。他这个表哥急了,嫌他不识好人心,就扇了他一巴掌。超远气哼哼地回家去,就喝了药死了。”
在这个讲法里,超远的表哥反而不像他自己说得那么残忍。一方面,他知道超远的毛病,怕他乱花钱;但另一方面,他也挺关心超远的生活,希望帮他过得好一点。超远不理解他的一番好意,反而和他嚷嚷,他才打了超远一巴掌。
我们在葛曼的故事(参见4.1)里已经看到,边缘人虽然社会地位很低,遭受歧视,但他们并不是没有常人的情感。葛曼虽然是个“小姐”,人们不把她当正常人看,但她因为遭到人们的歧视,无法与石磊结婚,还是会受到伤害。而超远的表哥在谈到求美为什么自杀时评论说:“坏人也有尊严呀。”不仅坏人有尊严,傻子和疯子也有尊严。他们自杀,就是因为他们希望被当做正常人看待。换言之,导致他们自杀的,是关于人格的一个悖谬。要求被当正常人看待,是一个最基本的心理要求;不被当正常人看待,当然会让人感到委屈;但从当地社会的角度来看,人格却是有条件的,只有结了婚,有正常家庭,过正常日子的人,才算得上完整意义的人。
我们可以通过四荒的故事来进一步看这个悖谬。我在6.1已经谈到,武都有个人在介绍了几个自杀个案之后,几乎忘了他的亲弟弟就是自杀而死的。他的弟弟就是四荒,患有精神分裂症,于1990年自杀。
我所采访的,是四荒的三哥。他的大哥也有很严重的精神病,在四荒死之前几年失踪了。他三哥,也就是我采访的那个哥哥,有个儿子患有很严重的抑郁症,被他父亲锁在家里。因此,他的家庭也是有精神病史的。
四荒年轻的时候并没有任何患病的迹象,因而也结了婚。在18岁他参了军。他是在部队里的时候犯的病,犯病后被送回了武都。他哥哥这样讲他的状况:“一般情况下,人们看不出来他疯。他能在地里干活,就是干得不忒好。他隔一段会犯一回病,就在街上来回走,念念叨叨的,总是叉着两只胳膊,低着个头子。一般是在春天,他容易犯病。”
因为四荒的这个病,他媳妇经常抱怨。一个村民说:“他要是早就犯病,也就不可能结婚了。他老早就结了婚,生了俩闺女,这才去参军。他从部队上回来以后,又生了个儿子,现在有18岁了。四荒在地里干活的时候干得不好,他媳妇老唠叨。有一天,他们又在地里一块干活,他媳妇又嫌他干活笨,说得挺厉害。四荒受不了了,回家就喝药死了。”
表面上看,四荒自杀的原因是和他妻子的争吵,而这也和我们看到的很多典型自杀没多大区别。他的自杀,应该就是对他妻子的责备的反抗。当然,他妻子也总是抱怨不公。人们说:“她没想到自个的男的会变成这样。跟这么个疯子怎么过日子呢?”我们在超远的故事里已经看到,超远的姥爷就是因为娶了个傻媳妇而开始靠人的,他父亲也因为媳妇傻,不好好过日子了。四荒的妻子也应该和他们一样,感到了挫败和命运的耍弄。当然,有精神病的人没有主动做什么对不起自己的亲人的事,他们似乎对这种不公无法负责。但那些与精神病人结了婚的人,又该向谁抱怨自己的委屈呢?
一个村民告诉我:“在四荒死后,他二哥就老是帮着四荒的媳妇干活。他60多岁了,是个老光棍。按照风俗,哥哥的媳妇要是守了寡,可以嫁给她小叔子,但一般不能嫁给大伯子。所以,这个女的就没嫁给四荒的二哥,可是老跟他一块干活,就跟两口子似的。四荒的儿子特别不高兴,觉着他娘不该这么做。”
但另一个村民告诉我,四荒的媳妇不是在四荒死后才和他二哥那么好的。早在四荒活着的时候,他就怀疑他二哥和他媳妇靠着:“四荒还没死的时候,就老说他媳妇和他二哥靠着,常为这个嚷嚷。有一回,他跑到他二哥院里去,砍了他二哥一菜刀。他二哥伤得可不轻,流了一地的血。”有人把四荒这次行凶当做他的疾病的一个表现。四荒的一个女邻居对我说:“他忒多疑了。有一回他跟我说:‘你知道她嫁给谁了吗?’我知道他是说他媳妇呢,就说:‘她嫁的是你。’‘不对,’他特别认真地跟我说,‘她嫁给你了。’也许得这病的人都这么着吧?俺一个亲戚也常这么说话。”
村民们不能确证,四荒的媳妇在他活着的时候是不是就和他二哥靠着了,但他们都知道四荒经常这么怀疑,而且在四荒死后,两个人的关系差不多公开了。他们解释说:“四荒是个疯子,也不能干活,他媳妇干不完地里那活。当然这个哥就帮帮她了。”不管这个怀疑是不是对的,我们基本上可以肯定,四荒的疑心也是他与妻子关系恶化的重要原因。
四荒和超远不同,是在结婚生子之后才变得不正常的。于是,他和他妻子都觉得自己很委屈。人们谈起这个案子来,有时候对四荒同情多些,有时候对他妻子同情多些。一方面,他妻子无辜地与一个疯子过日子,当然是不公;但另一方面,要把四荒完全不当正常人看,不仅让他妻子可以随意指责他,而且还自由地去和别人好,也是不公平的。两个人似乎都有一些道德资本。人们可以理解,四荒的自杀,是对他妻子的一种反抗;而另一方面,因为他是个疯子,他们又认为这样一个疯子不会过日子的基本技能,是没资格反抗的。虽然很多人还是对他颇为同情,但即使他三哥也不把他的死当成典型的自杀。
6.4 综论
本章是我们讨论人格问题的第一章。我们首先从边缘人谈起,通过他们尝试理解自杀与精神疾病之间的关系,并由此进入对人格的思考。
在中国自杀状况的相关统计数字出来之后,颇有人认为,中国自杀者当中之所以没有那么多精神病患者,是因为中国人不愿意看心理医生或是缺乏医学知识,其实有很多精神病患者并没有统计进来。但我们在这一章看到,农民们并不像学者们想象得那样无知。根本原因,还在于背后的文化观念。
一个受现代精神医学影响太深的人或许很难接受我们所说的,精神病人的自杀不被当成自杀这种讲法。但这并不是只有当代中国才有的现象。我们在第一章已经谈到过,在英国现代早期,虽然法律规定要惩罚自杀者的尸体,但因精神病自杀的人是例外。可见,即使在欧洲,有精神疾病的自杀也曾被当成非常典型的自杀。当然,精神病患者的自杀被排除在外的原因是不一样的。在现代早期的英国,精神病患者的自杀被认为是无意识的,因而不算犯罪;而在当代中国,精神病患者的自杀之所以不被当做典型的,是因为他们不被当成正常的人。
只有身心正常,能过正常日子的人,才有资格自杀。根本问题,还在于如何理解人性。在16世纪的英国,自我保存被当做基本人性,有意违背这一人性的,就是违背了自然法;但无意杀死自己的,并没有违背自然法的目的,所以是无罪的。而中国人并不从这个角度理解人性。在他们看来,只有有能力并认真过日子的人,才是正常人。这种正常人的一个特点就在于,他们会处在复杂的家庭政治中,有可能用自杀来面对家中的权力游戏。而精神病患者没有这个可能。
疯子、傻子、“小姐”、乞丐、光棍等都被认为没有完整的人格,因而被排除出了正常人的社会群体之外。人们认为,他们的自杀不算自杀。不仅那些确实因为精神疾病引起的自杀不算自杀,而且这些边缘人因为家庭原因的自杀,也被认为不算典型的自杀。这一现象呼应了我们在本书第二章所谈到的,对人格的社会性理解,即:一个正常人,首先是能正常过日子的人,也就是能建立和管理自己的家庭的人。像康娱这样的人虽然还是不认真过日子(参见4.2),但他毕竟是个正常人,有一个自己的家庭。人们只能从道德上批评他不过日子,却不能像对待疯子、傻子那样欺负他。
边缘人被排除于正常人之外,不能过正常日子,因而就没有资格自杀。由此可以反观自杀的意义。虽然我并不同意把中国文化中的自杀简单说成积极的讲法(这是典型的以基督教文明的标准来衡量中国文化),但我们可以看到,虽然自杀毕竟是悲剧,却不是人人都有资格去演的悲剧,而是只有过正常日子的人才配演的悲剧。我们在第二部分所描述的几个自杀个案,除了葛曼的之外,都是典型的自杀。那些自杀者的生活虽然都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但他们过的日子都是正常人的日子。他们能够自杀,能够因为自己的委屈和反抗得到人们的批评或同情,已经使他们同不配自杀的疯子区别了开来。在孟陬人的理解中,自杀是正常人的一种特权,因为自杀往往包含着对人格价值的正面追求。
,免责声明:本文仅代表文章作者的个人观点,与本站无关。其原创性、真实性以及文中陈述文字和内容未经本站证实,对本文以及其中全部或者部分内容文字的真实性、完整性和原创性本站不作任何保证或承诺,请读者仅作参考,并自行核实相关内容。文章投诉邮箱:anhduc.ph@yahoo.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