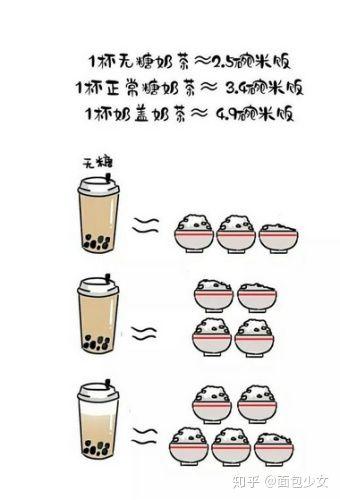关于银川的28个秘密你知道几个(老银川忆老银川)
“人老了容易怀旧”,这句老话过去对我来讲并没有什么感觉,现在我也老了,这种感觉离我越来越近。怀旧的思绪时时缠绕在我的心头。
我1949年生于银川西关,如今的凤凰碑附近。儿童时就在西门这一片玩耍,到少年时玩耍的范围大了些,大概范围南到南城墙拐子(相当于现在的南熏路口);北至北城墙拐子(相当于现在的中山公园西北角处);东城门楼太远,几乎不去那里。除此之外,西边最远也只是到唐徕渠栢上。

小时候的我也就是在这么大的范围玩的最多。如今我已是66岁的老人了,尽管中间有段时间离开了这里,但我的家终究还是在西关。换句话说,以凤凰碑为中心,南北一线三公里,东西不足1公里的范围,便称得上是我的故土了。
退休之后,茶余饭后的我,一次又一次在我而是玩过的地方散步。消失的西门城楼,护城壕沟,古老的城墙,源源长流的唐徕渠,以及渠栢上那长满疥疤的沙枣树。每每看到这些熟悉的情景,往事一幕幕的游荡于脑际,久久挥之不去。
银川的城门楼子,最熟悉的就算是西门了,那是它显得高大雄伟。清晨的傍晚,成群的灰燕在城门楼上空盘旋俯冲。蝙蝠就比她们飞的低很多,大人们教给我们一个绝招:脱下鞋子,抛向空中,蝙蝠就会钻进去,连同鞋子一并落下。这种特殊的技巧百试不爽,抓住蝙蝠,这个家伙长的贼头贼脑,面似老鼠,嘴像豺狼,牙齿锋利,两颗黑豆大小的眼睛闪着贼光。一不小心就会被它狠咬一口,不光得见红,疼痛也是钻心的。我们用细绳子将它的爪子和翅膀交叉拴住,在手上来回把玩,如果这家伙生命力顽强,可以坚持到我们的兴趣淡化,它也就会得到放生。在城墙根“打尖”(一种游戏,将长约10厘米的木棍两端削尖,用板子抽打到远处,对方用物接住。这种游戏在当年的银川很盛行,直至1969年开始消失),是玩的最多的游戏了,那个地方地面开阔,也不容易把“尖”打倒房顶上去,也不容易伤着人,一玩起来往往就忘记了回家,忘记了吃饭,为此不知道挨过多少次责骂。往西的唐徕渠上,到了七八月,渠水特别大,岸边上长着草,两侧长有柳树、榆树、沙枣树。有的沙枣树满身疙瘩,树皮粗糙扎手。渠栢上的沙土比较松软,长满甘草、苦豆子草。夏天的沙子还烫脚丫子。到处乱窜的四脚蛇有些令人发怵。常年的风沙从西侧涌到唐徕渠栢上,东侧成了斜坡,所以玩沙子的条件比较好。由于风沙常年不歇息,唐来渠的东西两边形成了银川特色的“沙滩”,至今在北京路北侧还有个沙滩清真寺。那时的渠栢两侧与农田之间常年积水,形成了一块块盐碱沼泽之地,低处的老坟被水浸泡塌陷,腐烂的棺材板翘出来,对我们来讲是既好奇又害怕。渠栢下的坟头比较多,加上那些奇怪的沙枣树、烂草滩,基本就形成了我们心中的“禁地”,一般情况下,不敢靠近。
沿着城墙根四周,既有环城路,又有空白地。用大青砖外包的城墙,中间是夯土。城墙下宽上窄,呈梯形。利用破损的豁口可以爬到城墙顶上玩。城墙顶上大约有2米多宽,也是杂草丛生。哪些被风吹断的干草团随风滚动,被人们捡回去当柴火烧。城墙根下的砖,不知被谁挖掉抽走,有好几处被人掏成猫耳洞,外边挂一个草帘子、破麻袋遮风挡雨,那些无家可归的人就蜗居在里面。那个时候,无论是城市的豪门大宅,还是贫民大杂院,都是旱厕,当年叫茅房,条件简陋到有的连屋顶都没有。粪便的清理全靠人力,用粪车拉走,运到城郊,找个空地进行晾干。城墙根也成了“晒大粪”的理想场所,时间长了,形成了特殊的市场——“粪市”。拾粪者们将大粪拍成粪饼,晒干后码成塔,用草帘子盖好,等待瓜农、菜农来买。就是这种纯天然的农家肥,在那个时候也有人作假,有的拾粪者会将池塘里的淤泥掺杂在大粪中,以“次”充“好”。当然,有作假的,自然也有打假的,有经验的菜农为了保证买来肥料的质量,会将粪饼掰开闻上一闻。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这种特殊的市场,特殊的商品,特殊的鉴别真伪的方法,在现在看来,还真是很有“味道”。城墙根下的粪市四面都有,一到天热的时候,城墙根的粪市味道就特别浓,我常常能看到那些居住在猫耳洞的穷人以及拾粪者就在粪市中间吃饭喝水,我们经过时往往是跑的最快的时候。现在想来,只要能填饱肚子,臭不臭的,大家真的无法顾及了。

粪市边上就是环城路了,实际上就是一条土路。下雨后泥泞不堪,车轮碾出的泥形成了一道道坎,太阳一晒,又干又硬。车走上去咯吱作响,人走上去稍不注意就崴脚。被踩碎的土渣厚的可以漫过鞋帮,一遇到风天,则尘土飞扬,卷起的尘土遮天蔽日,令人睁不开眼睛。我们无论是在城墙根下玩,还是路过这里。有两怕,一怕味道“浓郁”的粪市,二怕尘土飞扬的环城路,这也让我们一般不敢来这里玩。
北塔,一直是想去玩玩的地方,在北城墙根玩的时候,就总会想去北塔那里转转。然而感觉她实在太远了。北塔四周,除了有凌乱的农户外,尽是芦草洼,蒲草湖还有盐碱滩。荒草滩上连个像样的路都没有,当然也忌惮家长的责备,所以总是“望塔兴叹”。
路旁边就是一条水沟。这水沟就是西门楼子下的护城河延伸而来的。它从哪里发源,又到哪里结束,我们都不知道。水沟两边的野草开满各色的小花,吱吱叫的蚂蚱,水中的青蛙,盘旋的蜻蜓,成群游弋的小鱼都是点缀景色的一员。圆片状的浮萍贴在水面,小蜻蜓像个船夫一样蹲在上面,顺水流摆的水草宛如水蛇在水下摆舞。要不是有这些好玩的,好看的,我们也不到这里玩,毕竟这还是离家很远的地方。

那个时候,可以玩的东西真的实在太少。实在没地方玩的时候,就从城墙的豁口翻进去,跑到里面玩。有时候偷桑葚,像个小狗一样从墙洞钻进去,又被人像贼一样的撵出来。每次都是灰头土脸的。城墙里面并不是现在公园里面那样美,那时的中山公园叫“西马营”。城墙内的四周很大的一片,不是破旧的平房就是水坑、荒地。破砖头烂瓦片什么都有,一点不像城市的样子。只有进到解放街、中山街、玉皇阁街、步行街、新华街这个地段后,才有城市的味道。例如从西塔向西向南到城墙那些地方,有平房、农家小菜园、羊圈牛圈的独门独户,这些人尽管住在城墙内,却像是农户,我们也不知道他们到底算不算“城里人”。那里总是不乏野狗、野猫、野兔子之类的小动物,我们也去找过蘑菇,抓过小鱼,但总体来讲还是比较脏,所以我也只去过一两次。
后来,考入银川一中的我,不像儿时那么胆小了。星期天就四处乱跑,几乎把儿时没去过的地方都跑了个遍。那个时候,老城给我最大的印象就是湖很多。北门以西,玉皇阁以北,南到银川师范学校,西到公园荷花塘,这一片就有三四处面积不小的蒲草湖。东门三中旁边,南门清真寺西边,以及现在的十六小,富宁街西侧,南边的温州商城,一直到唐徕渠畔,到处都是大小不一的湖。至于城外四周更不必说了,到处是湖,芦苇、蒲草、水塘比比皆是。大小湖泊的数字,是所谓的七十二连湖远远不能涵盖的。
每天各家各户的炊烟袅袅升起,伴随着牛车的铃铛悠扬,再加上犬吠鸡鸣还有枝头小鸟的叽叽喳喳,这幅画面会让你真的置身在画卷里的田野乡村中。我喜欢在这种环境中去摘样子像极了香肠的蒲草,或者去抓绿头蜻蜓。湖面清澈的可以看到水中的小鱼,还经常有一些叫不上名字的小水鸟。现在想一想,如果那时有城市污水排放管道,又有今天这样日聚成吨的生活垃圾,那湖水可能真的只能在画里了。所以,银川塞上湖城的美誉,并非空穴来风。这一点我们这一代人深有感触。

如果有幸能登上西塔,四下瞭望银川城。纵横的街巷就像沟壑一样把民房分隔成一排排一片片的旱地一样。因为那时的房顶全部是草泥抹的,被太阳晒干后,灰白色的泥顶子遮挡住了城市的土地。一桩桩黑烟囱,一堆堆乱柴破木头星星点点堆放在房顶上。下雨天到处泥泞不堪,尤其是大杂院零散住户,根本没有可进出的硬化路面。铺上炉渣,垫上砖头,还是会不小心踩一脚新鲜泥巴。那时候我就经常梦想,什么时候能走上不沾泥土、不淌水的路就好了。

第一次在大街上逛,还是我五岁那年。父亲推个榔头车,上面搭个毛口袋要去买碳。一大早就出发,到了铁匠街又说先去给车轮打个箍子。铁匠街两边有十多座砖砌泥糊的铁匠炉,小徒弟坐个小凳子拉风箱,师傅在旁边边烧铁件边捶打。路边有小树,拴着驴、牛,地上放着赶车人带来的草料,牲口边吃边拉,整条街上充斥着打铁声、烟火味、驴粪味,要不是父亲给我奖了块麦芽糖哄着我,我可等不了那么长时间。打铁师傅的汗水从额头滴到肚皮上,扯下肩头的毛巾一擦了之。擦过的脸、肚皮还是黑色的。不过我们这些脏孩子似乎也习惯了,没觉得有什么。
到了碳坊(文化街北侧的尙勇巷),卖碳的店家把煤块和沫子一起铲到铁槽里过磅时,我和父亲撑开口袋,倒煤的同时喷我们一脸炭黑,我也不敢吱声。不过在场的所有人都是黑的,所以倒也无所谓了。回来的时候,车上啦了百十来斤的碳,榔头车子在疙疙瘩瘩的路上实在不好走。解放街是最好的路了,也还是用粘土、石灰和碎石子混合碾压而成的。晴天遇风起灰,雨天洼处积水。我帮助父亲在后面推车,走到南王爷大街(民族南街)附近,父亲想借机剃头,顺便洗个脸。在一个剃头挑子前,迎着铜脸盆里的热水,父亲剃了个大光头,接着顶上那个烂草帽向回走。到了天主堂实在走不动了,就干脆坐在路边休息。大街上卖瓜瓜糖、面糖、粘牙糖、三角皮糖、冰糖人、糖葫芦、切糕、牛头肉、羊杂碎的叫卖声不断。我的最大心愿是能买个面糖或者豆板糖。至于牛头肉、羊杂碎还有切糕什么的,那是大人们才吃得起的“大餐”,我想都不敢想。父亲掏了二角钱给我,我买了一块面糖,才花了8分钱,又用两分钱买了一块孙悟空模样冰糖人,剩下的一角钱我贼兮兮的放在了自己的口袋。
面糖容易散,不好拿,吃不好还容易呛鼻子,所以我决定先把它消灭掉。冰糖人这种耐吃的东西,我留在嘴里嘬了很久,一直坚持到家门口,都舍不得咬碎它。
大约到了红旗剧院那地方,我们碰到了一个老汉赶着牛车回家。车上坐着老奶奶、小媳妇还有一个小子。父亲好像和人家认识,从他们的对话中我能听出,他们也是趁着好天气来“逛城”来了,顺便来打点酱油,买点花布面料、针头线脑什么的。他们住在离城十多里的乡下,每隔几个月才来一次进行“大采购”。
这一天,我太累了,回去什么都不想做,两腿酸痛的像不是自己的一样。那个时候没有电灯,家家户户用的是煤油灯,条件差一点的还用的是香油灯。黄豆大小的灯头微微闪着亮光,透过窗纸的光亮和漫天的繁星,在漆黑的夜里仿佛也只能起到萤火虫的作用。外面除了狗叫声,晚上基本没有其他动静。人们睡的很早,要求也不高,有个热炕头就很舒服。我最讨厌的是每一天黎明,外面的牛车铃铛声、鸡鸣狗叫声还有清真寺的敲梆子声,这些声音总把我从热被窝中吵醒。
少年时的我,仅有一次当过“土豪”,大手大脚的花了一次钱。那是个“六一儿童节”,我身上带了一元五角,这点钱是我平时挖野菜、卖甘草换来的“血汗钱”,加上母亲给的五角钱,让我瞬间觉得腰杆都挺直了。在中山公园的“少年之家”里,我看着每本2分钱的小人书,吃着一毛钱的奶油冰棍还觉得不够,又吃了3个3分钱的糖水冰棍。5分钱的汽水我喝了4瓶,一毛钱一盘的凉粉一口气吃了3盘。加上家里带来的两个馍馍,这一天我从早晨10点吃到下午5点,身上的钱还没有花完。这次“豪华短途旅游”在60年后的今天在我的脑海里依旧清晰。现在仍然可以吃到那些街边的各种糖,我也可以吃到当年大人们专属的牛头肉羊杂碎,只是再也没有那年的味道。

今年春节后的一天,天气很好,我吃过饭后,再次踏上我走了多少年的路,踏上已经加了盖板的当年的壕沟,当年的龙须沟,现在两旁已经做了绿化,成了供人们漫步的林荫小道。唐徕公园里那几棵歪歪斜斜的老沙枣树,已经将她的树根深深的扎进了土里,干枯的枝条上仍然能生出绿芽,结出小沙枣。它就像一个饱经风霜的老人那样,在耄耋之年仍在哺育后代。它在这里屹立了这么多年,见证着银川人的变化,见证着银川的变化。园林部门授予的“市树”的美称,当之无愧。
塞上江南,塞上湖城已是家喻户晓的美誉,甚至已经名扬海外了。这里的人们,都在不知不觉的变老,城市也日渐靓丽。每当我上坟奠念我故去的父亲时,那种孝心未尽悔恨交织的心情时时煎熬在心,我为父母早早的离开美丽的故土而遗憾,为他们在世时,我们后辈的过错而揪心。在我还有能力提笔之际,我把点滴旧事讲给儿女,把对父亲的怀念留给自己。怎样对待家庭?怎样对待人生?也许是个永远探究不尽的话题。
注:文章是我家老爷子3年前有感而发的,老人家不会打字,我发出来给老银川们分享一下,文章虽比不上专业写手,但也是诚意满满,愿老爷子健康长寿。
,
免责声明:本文仅代表文章作者的个人观点,与本站无关。其原创性、真实性以及文中陈述文字和内容未经本站证实,对本文以及其中全部或者部分内容文字的真实性、完整性和原创性本站不作任何保证或承诺,请读者仅作参考,并自行核实相关内容。文章投诉邮箱:anhduc.ph@yahoo.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