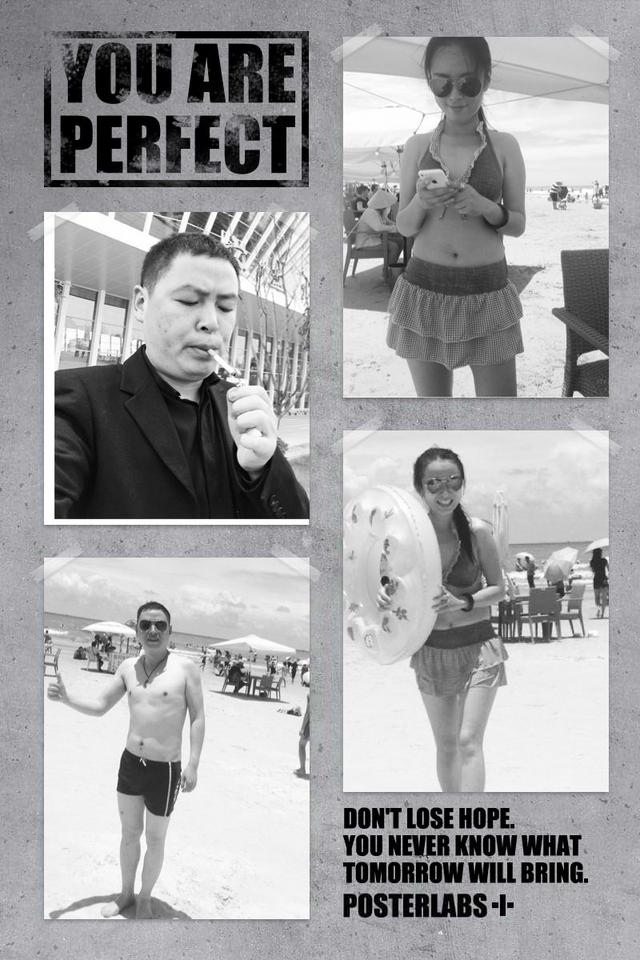陈望道的诗学观(陈望道的诗学观)
刘晓旭 复旦大学档案馆馆员
陈望道存世文章中,文学作品极少,小说和散文仅有6篇,而新诗则有22首,大部分创作于1921年。作为新文化运动的旗手,陈望道同其他当时的进步知识分子一样,试图从语言文学方面探索出一条教育、拯救国民的道路。20世纪20年代前期,陈望道编辑《民国日报·觉悟》,关注中外诗坛的动向,在该报上多次讨论关于新诗韵律的问题;20年代后期,陈望道执教于复旦大学、上海大学等高校,写作《修辞学发凡》,其中也体现了其诗学思想。用陈望道的话说,就是为了“证明新文学并非是江湖卖浆者流的市语,所有美质实与旧文学相迩而能跨上了一步”(陈望道致柳亚子信)。同时,这一时期陈望道与刘大白的行履轨迹大面积重合,二人交往频繁,就新文学各方面尤其是诗歌方面有深入而广泛的交流和探索。这样的探索贯穿了陈望道这10年间的几乎所有作品,从陈望道的诗学观中,可以窥见其在新文化运动中的主张与贡献。
弱化形式律,推崇内容律
陈望道最早明确提及新诗韵律问题是《谈韵律》(署名晓风)一文,发表于1921年5月18日的《民国日报·觉悟》,此时距离他3月时写作的第一首新诗《送吴先忧女士欧游》已近两个月。他在开篇写道:“诗是心弦上弹出的音乐,是情感、情绪底音乐的表白,当然该有——是有韵律。”接着,他提出了韵律的形式大致可以分为平仄律、叶韵律、音数律、内容律四类,他把前三类称为形式律、口律,把后一种称为内容律、心律。陈望道认为形式律是“因袭的韵律”,即从旧体格律诗沿袭来的韵律,反对强调新诗一定要重形式律的观点。他热烈推崇内容律,认为这是“诗人个性产生的韵律”,倡议新诗的作者和读者都要“拥抱这内容律底灵魂”。

“我们两人都抱奢望,一思证明新文学并非是江湖卖浆者流的市语,所有美质实与旧文学相迩而能跨上了一步;一思证明新文学系旧文学衰退后的新兴精神。”——陈望道1942年6月致柳亚子的信(上图)这样写道。
此前,宗白华在《新诗略谈》中提出作诗须要兼顾“形”和“质”。田汉也认为诗就是“以音律的形式写出来而诉之情绪的文学”(《诗人与劳动》),认为“有音律”和“诉之情绪”缺一不可。陈望道的这篇《谈韵律》,第一次提出了“形式律”与“内容律”的概念,把新诗的内容律置于形式律之上。刘大白读了陈望道的文章后,写就《读晓风君底〈谈韵律〉》,盛赞了陈望道此文打破了“偶像”的“诗是断断不可以无韵”的说法,并补充提出内容律可以通过与读者共鸣来影响形式律,使形式律由无形变为有形的存在。
陈望道的这一诗律观念,很可能来自高山林次郎的《新体诗底今日》,陈望道1920年8月将它译出,发表在《民国日报·觉悟》上。文中有两个主要观点:一是诗歌中“浓厚的意思”比“调子”更加重要;二是诗人的创作要能与读者产生共鸣。前者即《谈韵律》一文所推崇的内容律,后者即《谈韵律》中提倡的作者和读者要共同拥抱内容律。
陈望道对内容律的推崇表现在他对形式律的刻意弱化、对“因袭”的警惕。陈望道在为刘大白《旧梦》诗集写的序言中明确点出:“我今更要,为不曾会识大白的朋友们称述的,是大白这几年摆脱因袭的努力……他最憎恨自己因袭的经历,尝把彼,比之猛兽,尝对我叹息于摆脱不能尽净……他曾因不肯炫示旧藏的缘故,至于被人说为‘一知半解’了,他也安然受辱。”“学无本源,一知半解”是“一师风潮”时,浙江省教育厅文件中对陈望道、刘大白、夏丏尊、李次九等人的评价。刘大白旧学功底极深厚,但他下定决心作新诗后,便不再写旧体诗文。陈望道对刘大白摆脱因袭的描述,何尝不是他自己一直在努力的方向?他在新诗创作中用西方的意象,如《主微笑着》中用“主”“爱神”等词汇,描写恋人发誓言等场景;用西方典故,如《耶路撒冷众女子呵》即用《圣经》的背景,诗后还详细注解了各典故代表的含义;不在小诗中用韵,如三首《小诗》均不用韵,而用反问、感叹来串起情感的起伏。
至于读者如何与作者共同拥抱内容律?陈望道没有展开论述,但他多次描述了自己与诗人共鸣的阅读体验。在陈望道的新诗创作实践中,也表现出了“为了与读者共鸣”的倾向。譬如他第一首新诗《送吴先忧女士欧游》中叙写了“一师风潮”中的自己与吴女士,抒发老大无成的个人感慨。后来,这样极为个人化的经历体验逐渐从陈望道的诗作中淡去,他更多是从一个小场景、小事件入手去写普遍的感情,如《远处箫声》《无钱的姐姐》《西泠路上所见》等。与《送吴先忧女士欧游》形成强烈对比的是为外祖母去世而作的《您竟去了吗》,陈望道在诗中没有叙写任何与外祖母相处的事件,而把外祖母作为一个普遍的慈母形象,抒发痛心追念之情。
这样的倾向同样也体现在刘大白的诗作中。陈望道与刘大白不仅在诗律观和创作意图上一致,在新诗创作中也同气相求,如二人都为安庆“六二学潮”写下《为什么》;1921年6月14日陈望道发表《罢了》感慨制度扼杀了爱,三天后,刘大白也在杭州写下《罢了》参与讨论;二人还唱和了三首《黄金》谈论金钱与人的关系。陈望道对刘大白的新诗也是推崇备至,他在《修辞学发凡》引用的例证中仅有四首新诗,其中有两首(《泪痕》《旧梦》)是刘大白的作品。(另外两首是鲁迅的《我的失恋》、裴多菲的《勇敢的约翰》)因而,刘大白的诗作、诗论,亦可作为印证陈望道诗律观念的参照。
提倡女性的、自由的诗
陈望道对日本诗坛的关注不仅限于翻译关于新诗的理论性文章,他还曾以“春华女士”为笔名特意介绍了两位日本女作家,一位是二十岁的高群逸枝,另一位仅七岁(未提姓名)。陈望道两次摘录高群逸枝诗集《放浪者底诗》中的《日月之上》:“你坐在洪水之上,/神耶和华;/我坐在日月之上,/诗人逸枝。”(《东方文坛因青年女作家而起的旋涡》)热情地赞颂她能够从惨淡无比的生活中“这样地抬起头来”,“真教道学先生看了气死呢!”(《东方文坛两种珍异的诗集》)1921年7月,陈望道看了刘大白十岁女儿的四行小诗,“觉得很有意义”,也遂在《民国日报·觉悟》上刊登了出来。
1922年,刘大白在为查猛济选编的《抒情小诗集》作的序中指出此集的缺陷在于“女性底作品太少”,希望“男女之情,两性间双方平均地抒发出来”,号召“中国现代的女性新诗人”“一齐起来抽迸那久郁深藏的情苗啊!”陈望道以“春华女士”为笔名推崇女性作家富有生命力的创作,以“春华女士”署名创作了7首新诗,显然也是有意为之。
在《修辞学发凡》所举的例证中,也能窥见陈望道对女诗人的偏向。在《修辞学发凡》的初版后记中,陈望道说:“大白先生是对于本书的经历最熟,期望最大的……复叠的新设,便是因为他热烈地提议我才搜集材料写的。”陈望道提到的“复叠”这一节中关于“叠字”的用例材料,第一个便是宋代女诗人李清照的《声声慢》:“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陈望道从修辞角度笼统地介绍了叠字的长处。《修辞学发凡》中还援引了李清照《凤凰台上忆吹箫》《如梦令》、王微《如梦令》、苏伯玉妻《盘中诗》、苏蕙《璇玑图》、萧淑兰《菩萨蛮》等女性诗作的例子。
陈望道还追求诗歌内容表达的自由。1921年12月,陈望道和刘大白在新诗中讨论人际交往与金钱的关系,共写了三首《黄金》,被某君(不知姓名)说“我不赞成诗含议论”。十几天后,陈望道在《民国日报·觉悟》的《文艺漫谈》栏目发表《诗与文体》短文,探讨可用于新诗中的写作手法,认为说明和议论也可以入诗,他说:“解释与议论其实也未尝不可抒情……例如解释人生,议论人生,或解释议论别的而意在于解释议论人生的解释与议论,难道也不可以做诗么?因此我以为新诗尽可不限文体。”
从这三首《黄金》的创作来看,刘大白第一首《黄金》从诘问本来赤裸的人为何分出了冤亲友敌起笔,引出是“黄金”将本来赤裸的人变了,“铸就了任何人间底锁链”“垒起了人和人间底障壁”,最后抒发自己对黄金的厌弃之情,定要磨灭了黄金,才能显出人生底色。陈望道的《黄金——读〈黄金〉赠吾友大白先生》(署名平沙)则纯用议论的方式,反驳刘大白认为是黄金“垒起了人和人间底障壁”的观点。刘大白再作《黄金——答吾友平沙先生》,以议论入诗,与陈望道辩论。后两首的观点论证都显单薄无依托,不如第一首达意自然。大概因为这是次不大成功的尝试,陈望道为“议论可以入诗”的观点辩护说:“诗并不以文体而生好歹。所有好歹应该从别处去找差别。”(《诗与文体》)
陈望道还以对话入诗。他把与邵力子的两句对话写成诗《花瓣》——“伊底花瓣落在你底袖上了/把彼夹在《伦理学底根本问题》中罢!”在诗后记载了本事,说这是无意间觅得的颇有意义的诗句。另一首《言词底旨味》也是如此,诗中写了两位男青年对女性照片的态度、言语及自己对男青年话外之音的鄙弃。
从《黄金》《花瓣》《言词底旨味》三个例子可看出,陈望道对新诗内容的探索来自他对现实社会公共问题的关注,知识分子们讨论的热点话题、社会新闻、社会现象都能成为他写新诗的“本事”和“话头”。这从他对艺术的态度也可以得到印证:“艺术自身的目的是什么……是美吗?善吗?真吗?不是的……艺术的目的都与社会有关系的。艺术为社会而存在,不是为自己。”(《艺术与社会》)“为要将艺术从这寂寞中救出,只有一条路……这条路就是出了象牙之塔,走进平民队里,制作出‘平民艺术’来的路。”(《平民艺术和平民的艺术》)陈望道的新诗不单纯追求诗美,也不单纯记录片段的个人感受,他倡导女性作诗、作关注女性的诗,以议论、解释、对话入诗,都是为了传播思想,把新诗作为文字载体的尝试。1921年之后,陈望道的主要精力从启蒙民众转向高校教育,这也解释了为什么1921年之后他的新诗创作越来越少,直至1927年在他所执教的复旦大学所办的《复旦旬刊》上发表最后一首新诗。
诗的生命与口语化
陈望道倡导语言的革新,主张推广白话文、废除文言文,用新式标点,用口语甚至方言写文章。在《对于白话文的讨论(二)》一文中,他说:“我们固然也承认白话文是普及教育的利器,我们却更侧重白话文是新文艺的工具。”点出了他对白话文应用的两面——其一是普及教育,其二是用作新文艺的语言形式。
陈望道口中的新文艺的一大目的,是让人成为“有生命的”人。他在《“两个心”与“无心”》中感慨当下人们随波逐流:“从不曾见生命上有星火燃着,从不曾见胸膛上有什么主义底襟饰缀着,从不曾见眼帘上有果敢的光波流出……无心呵,真无心呵!”陈望道介绍爱尔兰文艺复兴时期的两大诗人——叶芝和拉塞尔之余,特意推出剧作家辛格,却不谈论他的戏剧,而着重论他的诗,说他“对于诗所做的工夫不是在自己,是在他感化许多人”,“他其实不是诗人,乃是一位诗的先知……他的大意以为徒然把寻常生活放在诗里,像从前诗人所为,这不是诗。诗所需的是生命的最强健的东西。”可谓借赞赏辛格,推出自己的诗歌理念。陈望道在自己的新诗中也热情讴歌“生命的声音”:
一切从生命的,从生命底核心喷发的,从生命底核心喷发了仍然有着生命的声音。
从这声音
我才见着人底色彩,听到人底节奏,嗅出人底芳香。
从这声音,
我才相信“真”于人间信有之,“美”在人间不曾绝。
我感着彼等在寻觅心的故乡,
在礼拜着灵的殿堂中全知全能的
——知情能感的神灵,
在诅咒着一切的虚伪,一切的愚蠢,一切的倾轧,一切只有感觉而无灵感,而无全灵魂的洪水以前的生物!(《人的声音》)
陈望道这一时期的杂文也充斥着“爱”“生命”“真”“灵魂”等字眼,可以说,新诗对于陈望道而言,就是唤醒更多人的“生命感”。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诗的内涵被他一再扩大,并不断尝试其他诗人忽略的部分。在题材选择上,他偏好选取易引发讨论的热点问题;在表达方式上,他大量引入议论来阐发道理;在诗歌形态上,他把因袭守旧的、没有生命的如文言句法、五七言、押韵等全部舍弃——这固然也是其他新诗创作者如郑振铎、宗白华等人所尝试的,但陈望道的态度更加决绝,以至于连文言中“美”的那部分也一律不要。在《对于白话文的讨论》中,有读者来信问邵力子:“现在既有了白话,那旧式的文言,是不是可以废掉不用呢?”陈望道代为答复道:“请你认明我们是主张从今以后一律公用白话文。”并在“从今以后一律”六个字上加了着重点。
陈望道并非不通旧学,只是决意从事新文化事业后,便与旧文化决裂。刘大白去世后,陈望道写作《大白先生的不死之处》,言及“大白先生一生最可使人纪念”的第一条,便是“公而忘私”:“大白先生的旧文学实际比他的新文学好得多。他于诗词、歌赋、八股、策论乃至楹联、尺牍,几乎没有一样不精。但他从参加文学革命以后,就不肯把这些东西拿出来发表。有些浅薄的人,看他只写些白话诗文,竟说他‘一知半解’。他也宁愿受‘一知半解’的讥评,不肯乘机献出些古色古香来给他们看看。”这点是陈望道与刘大白一致的追求,陈望道在给柳亚子的信中说:“我们两人(按,指陈望道自己与刘大白),都是立誓不做文言文,甘愿受人说是不通文言文的人。”正因为两人这契合的诗学观念,也因为陈望道比刘大白在摆脱因袭上走得更彻底,刘大白将未付梓的《旧梦》诗集交给新诗写作水平不如自己的小友陈望道来删削。
在陈望道看来,与因袭守旧相反的,是有生命的、由真性情中流出的、无虚伪矫饰的。对于诗来说,就是用当时人们的口语写成的歌谣。在《修辞学发凡》的例证中,陈望道大量引用口语歌谣,包括《诗经》《楚辞》、汉魏乐府诗、宋词、元杂剧,以及未经文人雅化的俗曲、童谣等,几乎不引格律诗。陈望道大力推崇这些有生命的诗的语言,把这些以往被忽视的作品提高到与经典的《礼记》《论语》《孟子》《左传》《史记》、韩愈文并列的地位上,一起作为讲解汉语修辞的语料。
值得一提的是,《修辞学发凡》的例证中,除经典、歌谣、白话小说和散文之外,还有大量的诗话随笔,绝大部分是宋代的。陈望道甚至还翻译了日本经济史学家加藤繁《宋代都市的发达》一文,与他其他译作的题材相去甚远。陈望道对宋代的异常关注同样可从刘大白的论述中找到答案:“赵宋一代,我们不能不认为它为白话作品于文学领域中大启封疆的一个特异时期。”(《旧诗新话》)陈望道在《文学与体制》一文中也提到自己对“随笔”的偏爱:“我想自古庄子起至最近金圣叹止的一类文章,集而统之,编成一部书:□□随笔。我们要知道,随笔是感情的连络,其他文章是逻辑的连络。”
陈望道不以诗歌创作鸣世且存世作品极少,他的诗学观念——提出形式律与内容律的概念,重视内容律、要求摆脱形式律的束缚,反对因袭旧体诗的要素,重视读者与作者的共鸣;提倡女性写诗、诗写女性,引议论、说明的写作手法入诗,在诗中表现、探讨社会问题;强调诗要凸显人的生命感,提倡鲜活的、口语化的诗——为新诗文体的发展作出了有益探索,也为我们全面理解陈望道在新文化运动中的贡献提供了新的视角。
《光明日报》( 2021年11月22日13版)
来源: 光明网-《光明日报》
,免责声明:本文仅代表文章作者的个人观点,与本站无关。其原创性、真实性以及文中陈述文字和内容未经本站证实,对本文以及其中全部或者部分内容文字的真实性、完整性和原创性本站不作任何保证或承诺,请读者仅作参考,并自行核实相关内容。文章投诉邮箱:anhduc.ph@yahoo.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