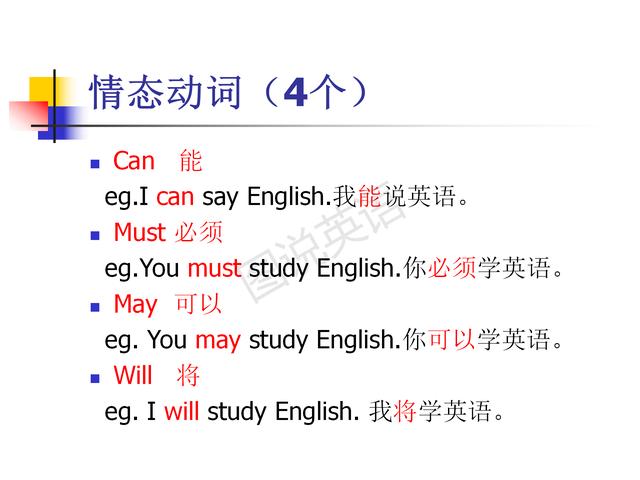曹德旺才是真的慈善家(曹德旺九年前就做到了)
导语
公益机构运行如何公开透明,捐赠物资分发如何高效、精准,机构运行是否精减高效,都是公益机构公信力的来源。而这些要求在九年前曹德旺的一次捐款中,都已经完美的做到了。早在 2011 年,曹德旺要求捐款给中国扶贫基金会的 2 亿元,要精准发放到五个省区市 5820 个自然村近 10 万贫困户手上,错误率要低于 1%。更苛刻的是基金管理费只有 3%,远低于国内 7%-8% 的水平!最终这样的低运行费高精准度的捐赠要求,是怎么在他要求下做到的?

福耀玻璃集团董事长曹德旺
2 亿元善款,6 个月时间,发到五个省区市的 5820 个自然村的近 10 万人手里,每人 2000 元,该怎么发?云南省寻甸县扶贫办工作人员张海波第一次感觉到,发钱也是件苦差事。「在寻甸发放了 1500 万,已经很头疼了。」张海波指的是「曹德旺曹晖 2 亿元扶贫善款项目」。2010 年 5 月 4 日,福建福耀玻璃集团董事长曹德旺与中国扶贫基金会签署捐赠协议,曹德旺、曹晖父子向西南五省区市旱灾区贫困农户捐赠 2 亿元善款。数额受人瞩目,却附加了不少条件。按曹德旺要求,中国扶贫基金会必须在半年内将 2 亿元善款以每户 2000 元的标准发放到滇、桂、渝、黔、川五省区市的近 10 万农户手中,管理费不超过 3%,差错率不得超过 1%,否则按超出部分的 30 倍进行赔偿。因此,这个项目也被赋予了「史上最苛刻捐款」的称号。然而当曹德旺提出这几项条件,并要写入合同时,中国扶贫基金会秘书长王行最的第一反应是:这活儿,接了。
管理费之争

事实上,曹德旺与中国扶贫基金会的合作并非一蹴而就。西南大旱后,曹德旺决定向灾区捐款两个亿。他起初想给灾民发粮食,考虑到粮食的运输问题以及可能带来哄抬当地粮价的风险,便决定发现金。曹得旺甚至派出调研团队,对项目的可行性及成本进行了评估和测算。「我正愁项目交给谁,中国扶贫基金会就找上门了。」但谈判并不顺利。曹德旺回忆,光管理费就谈了半个月。「我测算过,2 亿善款的运营成本在 200 万左右。但他们提出要 2000 万。」
王行最向曹德旺解释说,基金会必须争取管理费略有盈余,才能确保机构的可持续发展。但曹德旺不这么想:「基金会本来就是非营利组织,是做好事的,赚钱干什么?」中国基金会的管理费基本分为行政福利费、筹资推广费和项目执行费三个部分。按政策规定,管理费不超过 10%,几年来中国扶贫基金会平均提取的管理费比例约为 7%-8%。
王行最曾关注国外基金会的管理费运作,发现管理费只有 7%,但国外是把筹资推广和项目执行费用计入项目成本,所以管理费看似不高,但实际在 20% 到 30% 之间。最终,双方敲定管理费为 600 万元。此前,媒体报道中 3% 的管理费,是通过 600 万倒推回去的。尽管觉得苛刻,王行最也想以此案为例,证明中国扶贫基金会有这个管理能力,「从世界范围来说,3% 的管理费绝对是高效率的。」最苛刻条款不止于此。
曹得旺要求于受益人有两个标准:不能给当官的;不能给有钱的,差错率要控制在 1% 以内。曹德旺还不忘加上惩罚原则:若误差超过 1%,即按超出部分的 30 倍予以赔偿,最高赔偿额不超过 600 万。「曹先生很『仁慈』,」王行最笑着说,「如果 2 亿元里,有 100 万『瞄不准』,我就要赔他 3000 万,但他最多只收 600 万,很宽宏大量了。」在王行最 15 年扶贫工作中,从来没有人提出过差错率 1% 的标准。在国家的扶贫政策里,也没有相应规定。
即便在公益事业发达的国家,也没有这样的差错率标准。「我们是要和活生生的人打交道,加上地域、风俗等因素,1% 的差错要求已经非常高了。」事实上,王行最的担心并非多余,在项目实施中,情况远比他想象得复杂。不过,曹德旺不这么想。刚从博鳌论坛回到福州,他略显疲惫。「1% 差错率是根据质量管理的概率角度提出的。事情做细些就不会错,还能防止被人冒领。」

「苛刻」条款造就「苛刻」程序
2 亿元善款逐户发放,没有任何先例可供参考,扶贫基金会为此专门成立了「2 亿办公室」,受捐助的五省区市也分别设立省级项目协调小组和项目县执行办公室,并签署基金会、省、县三方协议,若最终未达到曹德旺的要求,省、县两级也要承担连带责任。
事实上,严苛的捐款条件带来的问题还真不少。首先,确定援助对象就是巨大的难题。扶贫基金会原计划在五个受灾省区市各选择一个县援助,但各省都希望多分到几个名额,云南甚至将十几个县的灾情全部列出来上报。不得已,基金会要求被推荐的县必须满足国家级贫困县、受灾较为严重、得到外部的援助最少等三个条件。在此基础上,确定了 17 个援助县。基金会原来希望推荐的方式,确定项目村,可是担心放权给县里可能出现「寻租空间」,为此,他们专门请该县农业等相关部门的工作人员按照受灾程度,依次列出需要资助村子,经多方讨论,最终由基金会确定了 5000 多个自然村的名单。最麻烦的是下一步。曹德旺要求,「不能发给当官的,不能发给有钱的」,但在排除了「当官的」和「有钱的」之外,又将谁定为援助对象呢?尽管国家规定农村年人均纯收入低于 1196 元的家庭为贫困户,然而大部分贫困县仅有行政村级的年人均纯收入数据,没有统计到户,特别是缺乏 2009 年的数据。
而逐户统计、核实农户收入构成和开支在实际操作中又是不现实的。中国扶贫基金会项目执行部部长桓靖说,苦思冥想后,基金会决定采用「排除法」来确定受援对象,将曹德旺要求的「当官的」、「有钱的」细化,制定了可谓最为严苛的十五条「筛选标准」,规定:两代以内直系血亲有副科级 (含) 以上干部的;配偶、子女中有公职人员的 (包括公办教师、医生);家庭成员中有村委会干部、村医、兽医的;房屋为二层以上砖混结构的;房屋装修档次明显高于本村平均水平的;有子女自费出国留学等情况的家庭,不能列入资助范围。受资助人名单需在全村公示,没有异议后方能确定。依靠这个严苛的筛选标准,基金会终于选定了他们认为有资格接受资助的近 10 万受援人。
但这不是结束。为了达到低于 1% 的差错率标准,无奈之下,基金会只好用了个笨办法:派出志愿者,逐户核实。与此同时,在各村张贴海报,提供投诉电话,接受举报。曾专门接听投诉电话的张海波说,他每天至少要接几十个电话。「举报和投诉电话的调查取证过程的成本很高,但我们都会严肃处理。」桓靖说,取消资格后的空缺,会用候选递补。核实的过程并不顺利。因为工作经费有限以及交通不便,志愿者们多乘摩托车或步行前往项目村,有时要在村中过夜,先后有 30 多名志愿者出现过伤病。项目还引发了不少摩擦。寻甸县某项目村的一次核查中,志愿者被不具受益资质的村民包围,要求得到资助。村民们甚至手持斧头恐吓村长。
桓靖说,他能理解村民的心情,「两千块钱在当地要攒两三年,没受资助的肯定会有不满。但我们只能向村民讲清楚,这规矩是捐钱老板定的。」善款最后以直接存入农户的独立个人存折的方式交付。与存折同时交给农户的,还有一封公开信,再次提醒农户:钱属于个人支配,若村干部要求上交,可随时举报。曹德旺在项目实施中曾赴云南进行实地考察。看到灾民拿到善款,他颇为欣慰:「现场跟我想象的一样,很折磨人,他们太需要帮助了。」
「我连感谢都不用说」

2010 年 11 月,2 亿扶贫善款项目基本完成。在历时半年的执行过程中,中国扶贫基金会投入 50 余人,组织 500 余名大学生志愿者和 20 名社会志愿者,调动五省区市扶贫办、17 个项目县和县扶贫办等部门领导干部、120 个项目乡镇领导干部、765 个行政村和 5820 个自然村的村干部,参与人数过万。与此同时,由中国人民大学非营利组织研究所组成的评估团队对 9 个项目乡镇,22 个行政村,39 个自然村的 1252 户进行入户调研,在长达 217 页的评估报告中,对项目进行了综合评估。其中,数据显示,缺损比例为 0.85%,低于捐方 1% 的标准,达到曹德旺的要求。同时,农户都在 2010 年 11 月 30 日前足额收到善款,也符合捐款方半年期限的时间条件。
在评估会上,有专家指出,该项目的标准化设计流程机制、瞄准机制、透明机制与纠错机制可以复制,值得借鉴,而其 1% 的差错率、3% 管理费和 30 倍赔付条款则无法复制。也有专家指出,这个项目的差错率低于 5% 已算完美。曹德旺对此不以为然:「专家是从书本里钻出来的,企业家是干出来的。为什么不能复制呢?专家书读得太多了。」
3% 的管理费也曾是大家议论的焦点。该项目执行中,工作经费较为紧张。张海波还记得,拨到寻甸扶贫办的项目经费只有 3 万元,连复印 7275 户受益农户的资料都捉襟见肘,只能让乡镇分担。王行最说,基金会按每户 2 元和 5 元的标准,分别补贴省、级两级,其他费用都是地方政府承担了,事有凑巧,项目执行期正是旱灾期间,地方政府正好有救灾预算。
曹德旺对此有自己的观点和角度:「基层干部拿着国家的工资就是给老百姓办事的,所以,我连感谢都不用说。之前大家都说难办,但不是办得很好吗?」他顿了顿,一字一字地强调:「事在人为啊!」扶贫基金会计算,如果把地方的成本算加进来,粗略估计管理费超过 6%。「但这个项目做下来,总共花了 600 万多一点,因为那两个亿还有些利息,所以基本持平。」王行最还记得,项目结束后,曹得旺对他说,基金会这次没赚到钱,但会带来很大的社会效益。
有问责,才有公信力

毋庸置疑,中国扶贫基金会与曹德旺签署的 2 亿元捐赠执行合同,是中国迄今为止问责公益最大的对赌协议。繁重而琐碎的工作让扶贫基金会连续半年超负荷运转,但王行最对曹德旺的问责精神极为感佩:「关注、跟踪善款的用途和效果,才是负责任的捐赠人。」王行最坦言,中国公益需要企业捐款,但在公益领域尚无独立、高效的监管和评估机构的情况下,也需要捐赠企业的问责,形成问责与响应问责的互动。他认为,这也是这个项目更大的意义所在。对于投身慈善多年的曹德旺来说,虽然选择问责是第一次,但此前多数项目,他的钱也都「花得很明白」。
「比如,让我捐条路,他们修,我来找监理,验收合格后我才会给钱。」曹德旺不止一次告诉媒体,他不相信任何人,只相信制度和逻辑。对于他来说,这 2 亿元捐款也是个试验。4 月 13 日,福耀玻璃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布公告,曹德旺将其家族持有的 3 亿股福耀玻璃股票捐赠给了河仁慈善基金会。这家基金会是曹德旺于 2007 年提出申请的,直到去年年底才获批成立。虽然目前没有捐赠股权的政策支撑,可曹德旺并不在乎。在他看来,自己的股票升值空间巨大,卖掉可惜。
「不管是捐现金还是股票,慈善是财富再分配的手段,我想告诉有钱人,要把钱捐出来,因为贫富差距长期拉大,对国家、百姓、企业家都是不利的。」至今已捐出 52 个亿的曹德旺说从未有过慈善计划,只要口袋里有钱就捐:「厦门大学跟我谈了两三年,从几千万增加到一个亿,今年分红有钱了,就再给他们捐两个亿。」对于河仁基金会的运营,曹德旺决定要当「甩手掌柜」,建立起较为完善的制度,并无条件接受媒体和社会的监督。曹德旺深谙制度的重要性:「只要建立起公开透明的管理制度,就没人敢轻举妄动,基金会也会变得有公信力。」
事实上,公信力也是王行最看重的。在他看来,公信力可以细化为执行力和透明度,而透明度又包括了对捐赠人、受益人和社会的透明,以及公益机构执行的过程透明和结果透明。「一些公益机构不是不想透明,而是没有专业的执行队伍和系统流程,不具备透明的条件,或者只能做到结果透明,无法展现过程。」这也是老生常谈的问题。
王行最分析说,中国公益机构发展时间短,政策法律不健全,不少公益机构是从政府体制下衍生出来的,带有强烈的行政化色彩,专业人员极少。「都是退下来的老干部发挥余热,你让他怎么专业化。」他反问道。曹德旺则认为中国慈善的症结在于:准入门槛太高,监管不利。他的解决办法很简单,不管官办民办,都纳入社会监管体系,允许媒体监督。公信力是慈善机构的生命,也是生存的基础。王行最说,他接下曹德旺这 2 亿元的项目,也是想证明「中国这个行业里有优秀的、值得信赖的组织」。在中国扶贫基金会「2 亿扶贫善款」表彰大会上,曹德旺戴上了少数民族灾民回赠的头饰:「得到灾民的肯定让我很激动。这个项目也说明,公益机构有了公信力,百姓才会信任你。」
我们焦虑的是:谁才是善待我们爱心的人?
中国人民不缺乏爱心,缺乏的是善待这份爱心的人!从路边骗乞的假乞丐,到水滴筹线下拉人头,再到郭美美……人们在心痛自己爱心被践踏的同时,焦虑的是在国家有难、困难群体求助时,什么才是可信任的渠道,我们要怎么做才能把我们的爱心真正传递到位?毕竟每人在信息搜集、传递,到接触到受助方力量都是有限的。
曹德旺用他的管理经验给出了一个解决方案:3% 管理费、1% 缺损率、30 倍赔偿最高不超过 600 万、6 个月、10 万人……这一系列的数据不是行政命令,更不是拍脑袋想出来的,是曹德旺从实际的企业管理中得出的精确数据,用企业运行的精细化管理来推进我们的社会管理,这样才能让有限的社会资源物尽其用。30 倍赔偿追责、不发给当官的、不发给有钱的,在细化工作回应社会关切之后,让公益机构真正拥有公信力!
*内容源:中国新闻周刊
免责声明:本文仅代表文章作者的个人观点,与本站无关。其原创性、真实性以及文中陈述文字和内容未经本站证实,对本文以及其中全部或者部分内容文字的真实性、完整性和原创性本站不作任何保证或承诺,请读者仅作参考,并自行核实相关内容。文章投诉邮箱:anhduc.ph@yahoo.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