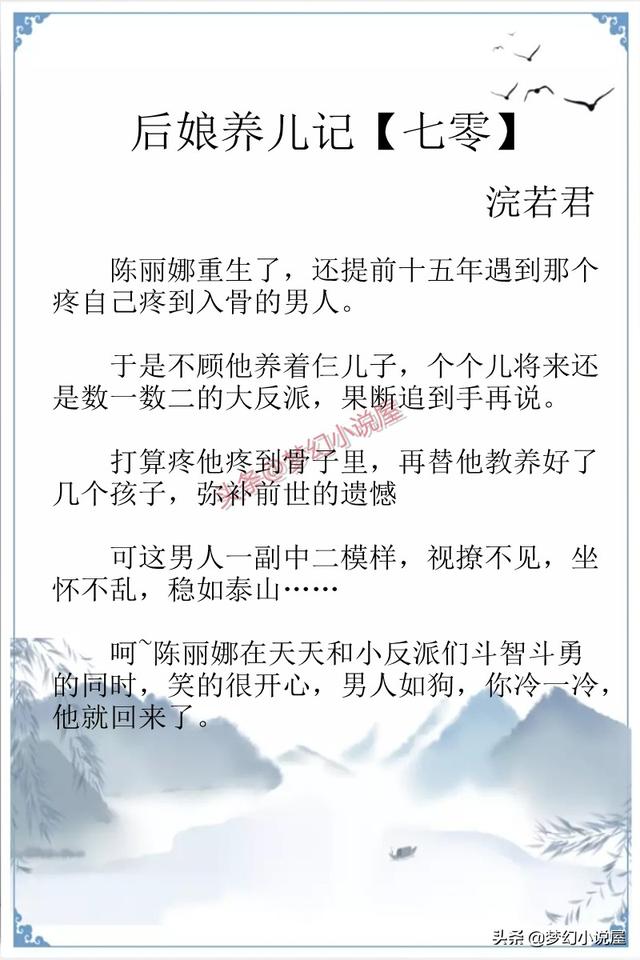张亚雄花儿(张亚雄与花儿集)
文/沈明永
来源:黄河三峡文艺

沈明永 甘肃省永靖县人,60后,毕业于西北师大中文系,爱好文史,创作了大量诗歌、散文,曾在《中华诗词》《甘肃日报》等报刊发表文学作品近百篇(首)。参与编纂《永靖史话》《蒋步颖诗词选》等文史著作多部。
张亚雄(1910-1990),笔名亚子,男,汉族,甘肃榆中连塔乡人,出生平民家庭。幼时在其家乡上私塾,稍长,考入榆中县高级小学。二十年代入兰州一中,1931年毕业于北平私立平民大学新闻系。其后在西北一直从事新闻工作,历任记者、编辑、主笔等职务。

(中为张亚雄先生,左为作者)
上世纪二十年代初,“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将胡适及著名文人周作人等在文艺研究方面积在全国掀起了一个极提倡搜集民歌、研究民歌的高潮。他们创办《歌谣周刊》,其中在该刊82期上刊登了著名地质学家袁复礼先生写的《甘肃的歌谣--花儿》的文章,揭开了研究“花儿”的序幕。这时,“花儿”作为“山歌”第一次进入了专家学者的视野。当时,张亚雄先生在兰州一中读书,他的国文老师,就是中共甘肃省特支书记张一悟,看他爱好写诗,曾多次对他说:“诗歌,必须从民歌中汲取养料。‘花儿’是你必须搜集和研究的。”其后,他在北平上平民大学新闻系时,创办该系的著名新闻家、《京报》社长邵飘萍先生和先后任系主任的徐凌霄、王小隐等报界名流时时在课堂上鼓励同学们搜集、研究民歌。并且,他们在不同场合分别多次鼓励张亚雄说:“花儿’是世界上最好的民歌,哪一种民歌都比不上它,你是西北人,身在宝山要识宝,希望你在‘花儿’这块处女地上耕耘,必有收获。”于是,他的第一篇“花儿”论文《“花儿”序》,就是由徐凌霄先生审定,二十年代末在北京发表。
三十年代初,他大学毕业后回到西北,利用职务之便深入三陇(甘、青、宁),广泛地与“花儿”爱好者联系。据他自己统计,前后他联系的学生、牧童、小工、车夫、脚户、水手、农民等计365人。他在1948年版的增版自序中坦言:“编纂过程实际上是一种集体的工作,……从一首歌词的抄录,到一地民俗风土的记载,到一个语词的注释,到一个土语方言的书写,都是经过反复的斟酌推敲,决不是率尔落笔的。当时我对于这些投稿和面谈的人物,都有姓名的记载,可惜在空袭频繁的山城重庆,把全部名单给遗失了,现在只记得总人数是三百六十五人,正因为恰恰是一年的天数,所以记在心里,永远没有忘记。”提供材料的除以上一些人外,在同一版的“引言”里,还多次提到民族学家牙含章,亡友于立亭,语言学家、诗人谢润甫等的大名。特别是谢润甫对他帮助最大,他不仅为《花儿集》作前言和民俗注释,还为1948年版的《花儿集》写过《〈花儿集〉校补叙言》。
谢润甫,名国泽,字润甫,甘肃临潭县人,作家、诗人、语言学家。他不但是一个“花儿”歌迷,而且是我国最早研究“花儿”的专家之一,“五四”时期,在北京发表《西北地区特殊民歌花儿》的学术论文。1937年-1939年任永靖县县长。张亚雄便多次写信给谢润甫,希望他给提供“花儿”素材,而谢也不辜负朋友之托,在案牍劳形之余,走乡穿户,广泛采录“花儿”,当他第一次接到谢采自永靖的“花儿”后,认为永靖“花儿”涉及了生活的各个方面,题材丰富,风格豪放,语言朴素、率直。能抒发各种不同类型的情感。而且永靖花儿的“长令”拖腔长,节奏明快,刚健激越,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另外,永靖花儿曲调随歌词而变,用北乡方言歌唱,具有浓郁的地方气息,在歌唱中完全能体会到农村妇女深沉、细腻、真挚的感情和男人诚实勇敢而又刚烈的性格。于是他便决定以临夏的北乡为中心,对“花儿”进行采录和研究。而谢润甫先生在自己采录“花儿”的同时,也积极地动员和号召在永靖文学上的同僚及学生、商人、脚户等,积极给《西北民国日报》投“花儿”歌词稿件。就这样,张亚雄便“坐地征花”,先后在永靖收集了二千多首“花儿”。其后,他如法炮制,不断扩大范围,在临洮、康乐、岷县等地进行收集、采录一千多首。于是,他便对其去粗取精,分类编目,精选了六百余首,加以注解和整理,于1940年写成《花儿集》一书。
当他将自己多年的心血付梓出版时,“七·七事变”爆发。接着作者离开西北原野,日夜惊魂,奔赴战时的陪都重庆。就在战火纷飞、辗转迁徙的旅程中,生命从弹灰里捡起,而把苦心搜集的“花儿”小心翼翼地带在身边,一路护持,始终没有散失。他决心将“花儿”付梓出版,以了自己的心愿。可当他把书稿交到出版社时,出版当局认为,“花儿”是山歌野俗之类的东西,难上大雅之堂,不予出版。于是,他找到了自己的老朋友,时任国民党办公厅主任的贺耀祖先生,经贺多次斡旋,最后《花儿集》被送到了国民党政治部设计委员会,进行再审查。此时,郭沫若先生任政治部第三厅厅长,郭老看了《花儿集》之后,以艺术家的独具慧眼,认为“花儿”是世界上最优美且很少见的民歌,应给予支持。于是在众多友人的关心下,《花儿集》终于在1940年元月22日,在重庆出版。刚一出版,便引起了各方注意。先有兰州宋炳琳先生的一篇文章,详细介绍《花儿集》,不久,重庆各大报纸也紧随其后,展开了一场有关民歌的大讨论,红火一时。此时正值国难当头,民族危亡,张亚雄编纂的花儿,特别是其中的《抗战少年12首》,用民歌的形式,激励人们抗战到底,当时在社会上产生了巨大的影响。1944年初到1947年4月的三年多时间,张亚雄在青海西宁。在这片“花儿”的故乡,他如鱼得水,利用空闲时间,奔走于田间地头、河畔田野,手拿采录本向当地老百姓请教,并将一些优美的“花儿”抄录下来。1948年秋,当《花儿集》在兰州再版时,又加进去了青海“花儿”的内容,使之更加充实、完整。
1949年以后,天地翻覆,旗帜变幻,江山易主,张亚雄准备第三次出版《花儿集》时,他被打成国民党“特嫌”,身陷囵圄,夙遭悯凶,他的人生顿时陷入了低谷。此时,他便对自己的爱妻说:“我已入狱,不知什么时候才能出来,你赶快回安徽娘家。你还年轻,今后的路还很漫长。”他的妻子不但没有离他而去,而是以拣破烂为生,用所得的一点收入,买来食物,送到监狱,每天铁窗对话,用一颗心温暖着另一颗心,并鼓励他要坚强地活下去。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演绎了一出真心的人间爱情佳话。
直到粉碎“四人帮”以后,先生才从监狱蹒跚走出。摘除“特嫌″荆冠,落实政策,并被纳为甘肃省政协委员,重任甘肃省文化馆馆员。先生此时想要重拾“花儿”,继续研究,可因几十年的折腾,特别是十年“浩劫”,手头资料荡然无存,想得到一本解放前出版的《花儿集》,庶几大海捞针,跑遍省内各图书馆,查无踪影,写信向全国各大图书馆求助,也一无所获,心中的失落和无奈无法言说。1981年,甘肃省第二届文代会召开,这次会上张亚雄先生遇到了平凉农民作家戴笠人,令张先生没有想到的是,戴笠人就把一本1948年版的《花儿集》亲手送给了他。说起这本《花儿集》,也有一段不平凡的经历:解放前夕,戴笠人在宁夏马鸿魁部当一名小班长,他的战友马尔力爱好“花儿”,用每月两角五分钱的津贴积攒了三元大洋,平时舍不得花,一天在街头书摊上上看到《花儿集》,便买了下来。两人在训练间隙常拿此书学唱“花儿”。马尕力在一次战斗中牺牲后,这本子被戴笠人带回故乡,从此他也爱上了“花儿”,并研究起了民间文艺。“文革”开始后,老戴因传唱“花儿”和这本《花儿集》遭到批斗,并抄家搜书。老戴在这本书的封底上写了遗嘱:“孩子们记住,此书得之于1949年的宁夏,三块大洋购来。咱家藏书几千本可以毁,惟我手稿与此书藏地下,乃你母之功。以后我不在世,挖出后当好好珍藏,如不愿读,可捐给文史馆。此乃珍贵文献。1956年被人借去,费了不少周折才复得,勿轻于人观。1972年2月20日。”老戴把《花儿集》和他的手稿装进塑料袋,放进腌菜罐,埋在了地下。还编了十首《花儿》,边唱边埋:“正是杏花的二月天,花儿们霜杀的可怜;枝断叶落(者)骨朵儿蔫,蜜蜂儿空恋者杆杆。”…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笔者负笈兰州,在友人的介绍下,认识了张亚雄老先生。此时,张先生已年近八旬,然精神矍铄,长冉拂胸。据张老先生讲,他刚刚失去了老伴,现在与女儿住在一起。先生除了经常参加省政协会议等社会活动外,就是继续研究“花儿”,写文史资料。同时,他给我们赠送了1986年9月由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发行的第三版《花儿集》。以后,每到周末,笔者常约一、二位同学到先生寓所,听他给我们讲如何写作,如何采访,讲解放前西北政坛轶事,文坛掌故。

《花儿集》总是以张亚雄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花儿集》作为第一部有关花儿研究和集锦的专著,所起的承前启后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是现代“花儿”研究的第一块碑石。《花儿集》从初版到今天将近70年了。在这几十年的岁月中,它对研究花儿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和古典花儿歌词,开创了搜集、研究花儿的先河。今后他无疑也将起着无可估量的推动作用,尽管《花儿集》的花儿是解放前传唱的花儿,但对今天的花儿研究者来说,仍是最好的蓝本。它不仅为研究者们提供了大量的宝贵资料,而且他那重视于花儿本来面目的求实精神也是值得研究者们学习的。
张亚雄先生一生在新闻、文艺评论、散文等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花儿集》仅仅是他众多成果中的一部分。只可惜,他在时局动荡的年代,因背负莫须有的罪名而被消耗掉了许多大好时光。现在,经他作为采录“花儿”地的永靖县,被联合国科教文组织于2004年10月确定为“民歌考察采录地”。这也算是给他的一个为了弘扬“花儿”艺术价值,不懈努力,终于能使“花儿”成为现在中华民族艺术院中一棵深受国内外、尤其是广大文化艺术工作者喜爱和青睐的艳丽奇葩,最好的告慰吧。
,免责声明:本文仅代表文章作者的个人观点,与本站无关。其原创性、真实性以及文中陈述文字和内容未经本站证实,对本文以及其中全部或者部分内容文字的真实性、完整性和原创性本站不作任何保证或承诺,请读者仅作参考,并自行核实相关内容。文章投诉邮箱:anhduc.ph@yahoo.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