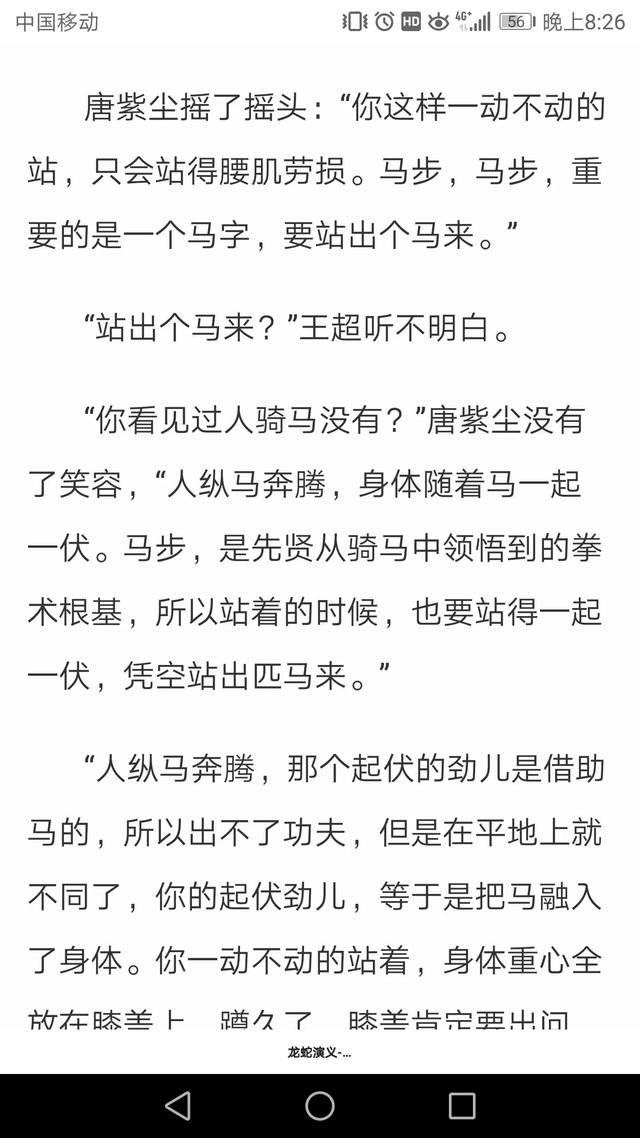相声演员王声简历及个人资料(观众如今进剧场不是听相声)

最早知道王声老师是通过东东枪的微博,枪总说青年相声演员王声长得像老年林语堂。那时,他和苗阜老师还没有上北京春晚说《满腹经纶》,大部分人还不知道他。2014年和王声老师认识,这些年平时偶尔聊上几句。
这轮访谈我提出采访他和苗阜老师,他说主要是苗老师比较忙不好“逮”。经过一段时间等待、确认,最终我专程飞到西安就在青曲社剧场采访了他们,上午苗阜老师,下午王声老师。
印象里中文系毕业的王声老师总是文质彬彬,平时爱看书,相声表演也带有很明显的文气。不过当天上午苗阜老师就说,其实王声是个坏脾气,到下午王声老师也说自己是有名的酸脸,台上那些人哪个他都骂过。
下午在西安鼓楼旁的青曲社剧场见到王声老师的时候,他正坐在下面看年轻演员们排练新作品,运动衫,手拿折扇。演员演完他走上前去,和众人交代哪里不对。
随后两个小时的访谈时间里,王声老师轻松中带着严肃,尤其说到相声抄袭问题时慷慨陈词,说出自己早已考虑成熟的想法。访谈中他的措词是有些特别的,时不时显出中文系的底子,提到罗素说的话,鲁迅说的话,这在我采访的这些演员中是绝无仅有的。
到最后在我本子上写留言的环节,王声老师拿起笔说自己的字可不好看,另外还得琢磨琢磨最近见到的有意思的话。这时候我问他,你们《这不是我的》里您那句“那我也不必骄傲啊”是怎么来的?王老师小眼睛一眯:哎,就写这句。

王声接受采访中。张望志拍摄
王声访谈录
王声:1982年生,陕西铜川人。6岁获得陕西省“秦都杯”少儿幽默大赛一等奖。毕业于陕西师范大学中文系,2007年跟随郑文喜学习相声表演,后拜郑文喜为师。2007年和搭档苗阜创办陕西青年曲艺社,常年坚持在小剧场演出,陕西青年曲艺社后改名青曲社。2014年,和苗阜在北京春晚表演相声《满腹经纶》,2015年两人在央视春晚表演相声《这不是我的》。代表作品包括,《满腹经纶》、《杯酒人生》、《礼仪漫谈》、《这不是我的》、《大话方言》等。
采访时间:2019年4月26日

王声接受采访中。张望志拍摄
“越多高学历进入相声行业越好,这是事实”问:这是你们青曲社的相声园子,您说书是在哪个地方?
王声:从这儿往那边过俩街口,那儿还有一个青曲社园子,不大点儿一个场子,观众五六十人。
问:是每周说书?
王声:每天都有,我每周说两天。

王声表演评书
问:您说书是从小喜欢。
王声:对。我说相声是爱好。
问:现在肯定不是爱好了,是专业演员。苗阜老师说,2014年大年初一的晚上北京卫视春晚一播完,微博转发量激增,您是不是也从那一刻感觉出来,从此不一样了?
王声:这个……
问:或者这么说,如果没有这一幕,你们就在陕西一直说,是不是也觉得可以了?
王声:2014年刚有知名度的时候,大家刚知道西安有这么一个团体,有人这样说相声。我没有您说的那种马上就能怎么样的心态,现在想想当时就是兴奋,对于演员来说那种刺激是不一样的。谁还没点儿自负呢?我说了这么些年相声,我这些东西还是可以。

2019年,苗阜、王声表演相声。杨明拍摄
问:苗阜老师说到你们其实在《歪批山海经》之外的作品上也下了很大功夫,但没想到最后因为这个作品火了,这说明演员被大部分人认识有时候有一定的偶然性。
王声:演员被广大观众熟知,在社会上拥有知名度,是一个命运的具体体现。这说得悬了一点儿,不过真是无形的手不知道怎么拨弄了一下。当然当年那些努力还是基础,但这只手什么时候把谁拎出来,谁心里都没准儿。不可能有人算好我今天到哪步,明天到哪步,后天到哪步,哪天我就红了。
问:但您小时候就红啊。
王声:咳。
问:其实您小时候那次获奖并不是表演相声,而是说笑话讲故事对吗?
王声:我们陕西有一位艺术家叫石国庆,就是王木犊,我们小时候他是最火的,磁带最多。所以我就学他,叫独角戏。我最早在大家面前一是讲故事,再一个就是学王木犊。

王木犊,陕西独角戏和喜剧演员
问:拿金奖那是一个全省的比赛对吧?
王声:秦都杯陕西省少儿幽默大赛。那次仿学的就是王木犊,那时候陕西大批孩子学他。他那种形式比谐剧少一点儿道具,比单口相声和评书跳入跳出和复杂程度要弱一点儿,故事形式和人物区分没有那么复杂。
问:不是“故事大王”,因为那会儿还是有很多讲故事比赛的。
王声:方言的成分大,用方言区分人物。
问:那时候您对相声的关注不如对评书的关注多是吧?
王声:我看我评书门师父田先生(田连元)表演是通过电视,听相声是通过磁带,很少听广播,有几盘相声磁带我翻来覆去听,牛群、冯巩、师胜杰、笑林、李国盛。大概就是1987年到1989年那段儿。
问:正好赶上八十年代相声中兴的一个阶段。
王声:对。反而到中学之后我开始会玩儿半导体,就开始大量听评书,上小学的时候听评书就是电视上那几部,包括后来的《电视书场》。
问:汪文华老师主持。那您那时候表演还是以表演评书居多对吗?
王声:那会儿我就一个人,一个是表演故事,学校要求讲一些典型人物的事迹,赖宁、雷锋、焦裕禄。前些天说评书的时候我还讲,赖宁的故事我现在还记得,赖宁救火当天晚上看的电视剧叫《再向虎山行》,还给家留了一个条儿,然后奔山火就去了。还讲雷锋的故事,那情节都是带扣儿的。
问:您拜郑文喜先生已经是2007年。
王声:不是,我跟我师父认识是2007年,那时候还没有拜。
问:那在这之前您说评书是跟谁学的?
王声:我6岁拿奖之后,家里人就认为可以培养一下。那时候我家在铜川,地方小,人也少,大家互相知根知底,当时田先生在全国最火,就说要找田先生。
问:还找到啦?
王声:没有,那时候哪有那么方便,不可能啊。联系不上,大家哈哈一乐就过去了。后来一上学学业一重,家里人就不拿这当回事了。另外我学习成绩又不好。
问:学习不好还考陕西师大?后来好的。
王声:反正那时候不好,这事儿就搁置了。没承想30年之后,我把当年这件事办成了。我评书拜到田先生这儿。

田连元与袁阔成。牛群拍摄
问:是哪年拜的?
王声:去年10月2号,在沈阳拜的,这也是我的一个夙愿完成。所以我是2009年有的相声门户,拜郑文喜先生,他也是那年去世的。

王声相声门的师父郑文喜
问:那时候说评书有意模仿过田连元先生吗?
王声:没有。我自从接触艺术以来很少模仿谁,包括相声,我没有动过这个脑子,我知道我学不像。而且田先生的艺术特点太难学了,他的帅,在舞台上那种挥洒,那种气度,不是一般人学得了的。
问:电视评书他是第一人对吧?
王声:现在定的就是他,有人出来讲我哪年哪年也说过,基本可以忽略不计。他是舞台表演和评书结合最早的,最好的。
问:而且他把评书和幽默结合得也非常好,还表演过很多小笑话。
王声:对。当时还不单是他一个人,还有一些评书演员都改小段儿,把相声小段儿改为评书演,《曲苑杂坛》那会儿田先生说过很多。
问:包括舞台故事那个。
王声:对,《舞台轶事》,“保险丝都打断啦!”他演得绘声绘色,给大家留下很深刻的印象。
问:您上的是陕西师大中文系,在学校的时候你们就有一个大学生说相声的松散组织是吗?
王声:毕业之后才有,我在学校的时候基本没碰上过一块儿说相声的人,能聊相声的人都很少。
问:大学四年没怎么说过?
王声:迎新晚会的时候说过一回评书,然后就没有什么了。我在学校的话剧社搞过话剧,相声方面没有什么志同道合的人。
问:看来这种气氛还是比不上北京的学校,比如东东枪他们的贸大。
王声:跟北京、天津没法比,基本没有这种氛围。
问:毕业之后最早把相声作为什么?爱好?
王声:爱好。我碰上几个说相声的人,他们在师大搞了一次相声演出,我们平时演话剧也在那个舞台上演。他们那次演出要么就是两块钱门票,要么就是不要票,反正晚上我就去看,有几个看着还真是不赖。那时候德云社刚刚在全国把相声的风掀起来,我这个人“杵窝子”,轻易不跟人主动交流,但我还是过去问了,你们几个是什么时候开始演相声的。他们说是最近,我说我也喜欢相声,咱们能不能一起活动。互相留电话,过几天一起排练,就这样开始了。
问:就不怎么赢利是吗?
王声:不赢利。压根儿就不赢利。
问:就在各大学演出。
王声:也别各大学,也没几个大学愿意让你去。当年申请一个大学场地比现在更严,一层一层往上报,一层一层往下批。
问:那就是说,当时相声当不了饭吃。
王声:不可能当饭吃。
问:毕业之后您是从事过一些工作的是吧?
王声:是,已经开始糊口了。
问:后来您和苗阜老师你们先是组建陕西青年曲艺社,再后来就是青曲社。您在相声圈属于高学历。
王声:没有没有。相声圈的高学历现在多的呀,过江之鲫。
问:您怎么看这些年更为高学历的人进入相声行业?比如李寅飞,还有上海交大博士夫妇。
王声:这个行业怎么啦?说相声就是个工作,现在我们国家做工作不分三六九等了吧?没有说这工作是下九流不允许干,时传祥先生那会儿不就平反了吗?它是个工作,能挣钱,有固定的演出场所,那就允许有人干。说一个人以前是研究导弹的,他不愿意干导弹了他愿意干这个,你就批评他你怎么不干导弹,导弹多高尚?
问:说明相声能养活人了。
王声:相声早就能养活人,而且一直能养活人。养活不了的人是不适合干这个的人,跟学历高低没有关系。说相声你的“相声学历”得高,艺术功底得深厚,让观众能够听你才行。
问:高学历对于演员创作相声,相对来说是不是更为有利?
王声:说悬一点儿,你的知识底蕴越深厚,他们爱说的“三观”越正常,就更容易对事物进行正常分辨。
问:以前的老先生常讲不说糊涂相声,学历稍高一些的演员进入相声行业,是不是有利于不说或少说糊涂相声?
王声:读书识字的人不一定不说糊涂相声。糊涂两个字涵盖面很广,你对表演节奏的把握不清晰,这就叫你糊涂,还不只是词句上的事儿,是一个节目的把控程度你达到没达到。在行业内一个人不说糊涂相声,其实挺难的,说明你已经上台阶了。我师父郑文喜先生是我接触最多的老先生,他经常说那谁谁是好说相声的,一辈子不说糊涂相声。
问:是一个很高的评价。
王声:就是夸这个人是好样儿的。你听高德明的录音,“咱们的嘴里没有倒音怯字”,他对这个是感到自豪的。这和学历高低没有关系,是你对这个艺术的认知程度问题,当然越多高学历进入相声行业越好,这是不可辩驳的一个事实。
“观众就是花300块钱进剧场说相声来了”问:你们俩说文哏相声居多,你们俩的文哏作品和苏文茂先生、马三立先生他们的文哏作品有什么不同?
王声:第一,我们对文哏这个概念必须先厘清一下。有的节目属于文哏,像苏先生后期就以表演文哏作品为主,马先生除了个别活之外,其他作品不是我们理解的文哏,《似曾相识的人》、《十点钟开始》……
问:《买猴》也不是文哏。
王声:这都不是文哏,这都是天津特有的塑造小人物的作品,可不可以归到文哏里面,可以,但严格区分不是文哏相声。马三立先生被广大人民群众所熟知的相声,也不是文哏作品。苏先生是大家设立的文哏相声的标准,文哏是什么,看苏文茂就可以。我和苗阜老师表演的很多节目其实属于子母哏作品,只是加入了一些带有文化色彩的元素而已,从表演方式到节目归类很多不能归到文哏中去。当然后来大家对文哏的界限放宽了,长时间以来也没人这么说相声,其实这不算是文哏。
问:正好您说到子母哏,如今年轻相声演员好像越来越愿意说子母哏作品,捧哏也总想露一手儿。
王声:我没有向老先生求证过,我没有这个胆量,但我自己认为,说学逗唱,就是建国以后给相声定的四门基本功课,这个“逗”就是子母哏。
问:哦?
王声:对,两个人得逗起来,你逗我一句,我逗你一句。
问:是这样的吗?
王声:一家之言嘛。现在年轻人爱这么呈现,不过他们很多人呈现出来也不叫子母哏,其实就是斗嘴,子母哏也有三翻四抖。有些人吐槽《满腹经纶》说它没有铺垫,是直接翻的,但是直接翻也有技巧和手段,不像现在有些节目就是为了斗而斗。

2019年,苗阜、王声表演相声。本文作者拍摄
问:过去居多的那种逗哏捧哏老少配,现在是不是真的不合适了?
王声:现在的相声节奏肯定是比过去快,但还是有个艺术功底问题,真要能达到过去苏文茂、朱相臣那种表演状态,老少配肯定还是合适。你现在听人家录音还是会乐,谁不乐以后就别听相声了,请去旁边休息看看别的节目,现在娱乐方式这么多。人叫人千声不语,货叫人点首自来,我们必须拿出东西来。有的观众说我不爱看你这个我就爱看那个,对不起我来不了。
问:那您怎么看迎合观众这件事?
王声:观众不需要你迎合他,没有观众说你必须迎合我。
问:比如他就要听那种皮儿薄馅儿大的相声。
王声:有啊,需求肯定是五花八门,罗素讲话,参差多态乃世界之福。都得有才行,这叫一路宴席款待一路宾朋,没有人规定相声必须得这样,也没有人规定必须得那样,你爱听谁听谁,爱听什么听什么,市场多元多态,这才叫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没有说谁不对,或者说谁就是对的。艺术水平的道儿就划在那儿,到这个级别你就演这个级别的节目。
问:你们过去在小剧场演得多,来的观众少,而且相对来说略懂相声的人多,一旦你们成名之后走入大剧场,观众多而杂,是不是就要说不太一样的相声了?
王声:演法不一样,表演手段不一样。王文林先生来我跟他聊天儿他就说,小剧场几十人你轻松着使就行,到了上千人大剧场你就得放得开一点儿,不这样观众看不见咱们。
问:这是表演手法不同,不是内容上往俗里说。
王声:这个说法我不知道是谁提出来的,我就说,演员不能把观众摒弃在自己的范围之外。就说我这样的年轻演员,咳,我怎么还是年轻演员我都过36岁了,国家都不拿我当年轻人了,就说八零后、九零后的演员,生活范围太小了。像姜昆先生、马季先生当年他们走街串巷,我不是说撂地啊,那真的是深入生活,工厂农村哪儿都去过,接触生活的面非常广。我们团的孩子反思过,他们过的就是眼前这50米的日子,生活范围小,可选择的人物和故事题材就少,而你同龄人也一样,不过是他眼前的50米,你去了解他,他来了解你,时代的故事就这样编织而成。不要想观众,他可能喜欢听这个,你以为是这样不一定就是这样。柴静那本书有一点写得非常好……
问:《看见》。
王声:对,她写到陈虻还在世的时候,陈虻编片子跟一个编导说,你这片子不行,得改,编导问为什么 ,陈虻说他认为观众看不懂。编导说,你看懂了没有?陈虻说,看懂了。编导说,人家观众比你差哪儿了呢?这个话问得很好啊,演员你总觉得我说的这个他们会不会不懂不喜欢,你看低了观众也不行。
问:就是说你得相信观众的接受力。
王声:对,艺术创造是第三方完成的。相声舞台上演员是甲乙,但艺术是在观众身上完成的,你一定要让他成为你的同伴,你要让他和你形成交流。当然现在也有一些乱象,互动有些过了。
问:现在有些观众进剧场,把和演员互动当成最大享受。
王声:这说得太委婉了,其实就是花300块钱说相声来了。
问:这会是一个方向吗?还是只是这段时期的一种乱象?
王声:说是乱象,也是太捧他们了,还到不了“象”的程度。
问:你们俩也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吧?
王声:有。今年在杭州演出,观众们和我们你一句我一句地完成了当晚最后一个作品。我在台上“弹压”过几次地面,观众不领受我的意思。斯德哥尔摩症候群啊,观众亢奋起来之后很难压抑住,越说越觉得好玩、过瘾。你说不行我们这表演节奏乱了,你跟他说不了这个,只能说是自己经师不到学艺不高,艺术能力不够强。

2019年,苗阜、王声表演相声。杨明拍摄
问:以前的老先生们是不是也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也没有办法问,他们遇到这么情况怎么处理?
王声:老先生遇到剧场杂乱的情况,我师父跟我讲过,就是照样按照自己的节奏说,不能理他们,越理越坏。
问:苏文茂先生和王佩元老师在山东演过一场,台下等毛阿敏出场就一直乱喊乱叫,苏先生照样一字不落地说。到后台王佩元一问,他就说,只许他不听,不许我不说。
王声:这和演员性格有关系。苏先生年轻时火的时候,他要在台上闹起来,谁都勒不住他,您听那录音,他跟赵佩茹说《窦公训女》的时候,那个苏文茂和后来的苏文茂可是俩人,他什么剧场情况没见过?但他和佩元先生搭的时候头发都白了,我还在乎你们这样闹腾吗?
问:我想苏先生面临的情况和现在不同的地方在于,那是观众不喜欢你,现在是观众太喜欢你了,我喜欢你,演员就更不好去冒犯他们。
王声:观众认为是和台上进行了良好的互动,只能说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艺术的特点,可能这个时代的观众对艺术的理解就是这样的,也可能是演员的引导有问题,与市场大势的变化也有关系,反正现在已经变成这个样子,这是个新课题。您说这个太对了,观众不听你有办法没有?有。田先生经常跟我讲,金声伯在苏州还是上海演出接摇滚乐,他接演评话,后头是张国荣,小桌子一搬,观众在台下还嗨着呢,金先生上台一拍木头说,再喊,都死人了你们都不知道吗?出人命了,还喊吗?十几岁大姑娘剥得赤条条地扔在烂泥塘里死了,这事儿你们不知道吗?这个事儿要破案,还得到开封府。
问:先垫话儿。
王声:你这不就领住了吗?这是手段。不过现在的情况,是观众要求你在台上跟他说话。我们这儿有位演员演完一段之后说,刚才是我们新创作的一个节目,接下来演一段传统节目。台下观众说话了,哎,说一个我会的。你这怎么弄?过去也有观众词儿比你还熟,但他不说,他只是坐底下听着你。时代变了。
“师胜杰先生点醒我,不要冲昏头脑”问:说一下你们2014年北京春晚上的《满腹经纶》。其实你们最早里面的方言都是陕西话,上春晚才加入河南话和唐山话对吧?
王声:唐山话是到北京之后,我们觉得得接接北京和河北一带的地气儿,就捡着比较顺嘴的怯口说了一下。

2014年北京春晚上,苗阜、王声表演《满腹经纶》
问:而且给你们还改了个名字。
王声:这名字改得好。我对活的名字总是不太在意,过去老先生使传统活哪有名字,有名字还刨活。
问:当时您能感觉出一夜之间的那种变化吗?
王声:《满腹经纶》之前,我和苗阜在全国演过几个地方,在重庆、成都,在你们河北的秦皇岛,有人认为这个活不赖。我干爹李立山先生来西安看完之后就鼓励我们,我最好的朋友、现在已经去世的张德武先生,他一直在北京推荐我们,没有他推荐,立山先生不会到西安来看。立山先生看完之后就说,你们应该走出去看一看,守在这个地方太小了,所以那年我们就走了几个地方。演完之后我就说,我们这个艺术不敢说好,但我们有自己的特色,所以后来《满腹经纶》就出来了。不过师胜杰先生说过我们,他说看《满腹经纶》的影响,你们的艺术其实到不了现在这么大的名气。师先生病重的时候我去上海看他,看完他要送我们出来,拿一把拢子在那儿梳头,我说我来吧,他说你不知道我头发这个方向,他跟我说,你要记住啊爷们儿,你们这个好处是时代给的,按你们本身的艺术到不了现在这么大的名气,要注意,要努力,要谦虚。他这是点醒我,不要冲昏头脑。

苗阜、王声与病中的师胜杰
问:《满腹经纶》受到这么热烈的欢迎,你们有没有想过接住自己的问题?姜昆老师说他当年总怕接不住自己。
王声:多年以后再重谈这个问题,所谓接住接不住,当年我是危机感很强的,《满腹经纶》这样的活好不好搁一边儿,从我们俩角度说想再创作出这样的一个作品来,难度比较大。它基于前几年我们磨合成的默契程度和对此类包袱儿的掌握程度,拿另一种形式演绎这个节目是不可能的,类似这样的活没有了。它是我们俩能掌握的这类技巧的集中体现,所以那就只能改范儿,换手段。姜先生跟我讲,他第一个节目演一个唱的,第二个节目就得演一个说的。所以我们也得换范儿,但是换范儿对于一个年轻演员来说难度极大。你得脱胎换骨,让人感觉不一样了。
问:其实第二年央视春晚上你们的《这不是我的》,是换了范儿的。而且在你们演出之前媒体也有宣传,对你们来说,这个节目的表演风格有很大变化。你们平时论说型作品多,《这不是我的》这样叙事性的少一点儿,最终是有遗憾在里面对吗?
王声:这个节目实在很难,拿到题目的时候就知道它不会太好,第一跟春晚气氛不合适,第二跟我们被大家熟知的演出状态不匹配。

2015年春晚,苗阜王声表演相声《这不是我的》
问:相声演员也有人设,不符合人设的表演观众不容易信你。
王声:拿我们行话说,这个节目我们不把杆儿,使不上劲,摸不着脉。而且这种题材说轻不是,说重也不是。
问:注定会有遗憾。
王声:是一种煎熬。
问:已经不是1988年《巧立名目》那个时代了。
王声:立山先生讲话,你们都说《巧立名目》之后,《巧立名目》是什么你们弄明白了吗?
问: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
王声:就是说,那是在一个什么局面之下,什么样的人演的节目,现在距离那时候过去30年,还能不能再出一个《巧立名目》?能不能达到那样的艺术高度?
问:但当时的媒体确实把两者联系起来了。
王声:说句不好听的,其实是媒体的臆想吧。
问:那就是说,演员对哪一类作品拿手,就应该一直走自己这一路?
王声:业内有一个不好公之于众的说法。当年迎秋剧场的上座率不高,高凤山、王学义、王世臣、王长友这老几位去找侯宝林大师,说四哥,我们一块儿演吧。侯大师的爱人雅兰老师跟他们说,宝林就别去了,宝林把杆活就16块,老露也不值钱,偶尔去一下给你们帮帮场可以,不能常演。那么大的艺术大师,那不是也知道自己有短板吗?我们这样的虾兵蟹将,那不可能啊。演员的成长也有明显的时间层级,几十岁到几十岁有一个过程,你不能让一个30岁的人达到50岁人的艺术成就,谁要说能达到那是疯了。
“苗老师和我是截然相反的两种人”问:你们提出“陕派相声”的口号已经有几年,这些年也到全国各地与演员们有切磋,你们后来在表演上有没有有意吸收其他地方相声表演的一些经验和手法?
王声:必也正名乎,先谈名词解释,陕派相声这个词儿是怎么来的呢?是鄙人给起的。当年《华商报》和青曲社搞大剧场演出,要找新闻爆点,这您懂啊,我说来,我给你起个名字叫陕派相声。谁都没想当一代宗师,以后让别人给我们把香上上,不是,这就是一个宣传口号,大家没有必要对一个名字这么纠结和刻意。

王声接受采访中。张望志拍摄
问:但你们总是有你们的特色嘛。
王声:您说这个对,但特色和特点不代表就能成一个派别,特色和特点是演员个人的,不是说一批演员都这样,还达不到那种普及程度和广泛程度。青曲社每一个演员的表演特点都很明显,但还没有到派的层面。津味相声带有小市民的特色,那么多活都是小市民吗?那不可能。再有您刚才说有没有借鉴其他地方表演风格的问题,相声永远是互通的,我当年想搞一个全国各地相声在陕西的交流和演变这样一个研究。现在也一样,只不过现在更方便了,不用到当地,把视频打开看一眼就明白。世界都打通了,巴黎圣母院那儿刚烧中国就开始哀悼,哪儿还有界限和壁垒啊?
问:说一下你们俩,苗阜老师社会职务比较多,他的性格和处事风格和您是互补的。
王声:互补搁一边儿,我们是截然相反的两种人,他那种生活方式我绝对来不了,我的生活方式他也来不了。成年人的合作到最后不都是压抑自己本性,拿出方便跟人接触的一面进行合作吗?任何工作都是一样,不仅说相声的这样。您带一个摄影师一起采访,不也是一种合作吗?关键相声在这方面被放得比较大,尤其现在的年轻观众把两个演员的行为归类越来越细化,对此产生无穷遐想和探索。
问:观众总是想当然认为台上两个人配合默契,台下也应该形影不离。
王声:说相声确实需要磨合时间长一些,我和苗阜磨合了将近十年时间,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也不用对活,来了稍微一说就可以演。
问:那你们的新作品呢?
王声:新作品得对。
问:现在新作品是您写得多还是苗阜老师多?
王声:我们写活很少一字一句地全写出来,有一个意图之后就整理一下,拿出来两个人研究哪些地方可以加,哪些地方可以减,找时间对一遍,对完之后把这个版本用文字落下来,然后针对文字不断修剪。
问:所以很难说哪个作品就是谁写的。
王声:我不知道别的创作者什么样,相声这个东西我觉得到最后完成,绝对不是出于一个人之手,肯定要博采众长,经过无数次压场,起码二三十次、四五十次的表演,别的人提意见,这才能成。一个人写一个往舞台上一拿就成了,不可能。
问:八十年代知识型作品曾经很流行,刘伟、冯巩以及马云路、刘际都说过这样的作品,当今时代还需要这样的作品吗?你们的《满腹经纶》有一点点像此类作品,但又有比较强的娱乐性。
王声:首先不要想传达知识,这不是你的责任,但你必须知道你作品中用的这几个东西是什么,得准确,这是你是素材。鲁迅说“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观众一听还有这个事儿,脑洞开得比较清奇,他回去翻一下书,等于我们也起到一点作用。你说你准备今天在这40分钟里讲一本中国文学史,那你勒死他他也讲不了,而且也没人听。
问:刚才也说到人设的问题,演员表演风格的问题,有没有人说过你们的表演风格相对比较单一?
王声:不是有没有,是一直有人说。现在能看到的在媒体上流传的我们的表演,基本都是这个样子,有时候我们出去录像人家要的也是这种风格,其他的风格没来剧场看过的人不知道。
问:其实还有很多样式。
王声:这么说吧,如果只会这几手的话到不了今儿。
问:那怎么能让更多的形式也传出去,这跟媒体的要求有关系吗?
王声:你不能苛求电视台,电视台就要你这么个元素,你说你怎么办?你说我们这个段子有四番儿,你有八番儿他也不理你,他只要你这两番儿。按理说现在自媒体发达,人人拿起手机就可以拍,但我认为这都不是真正了解相声的途径,真正的途径就是剧场。我还是比较老派地认为,走进剧场看相声是最直观的,看到的是最像相声的相声,在抖音上看到的不是。
问:比如就在这个剧场观众一直拍、一直录做直播,你们会拦着吗?
王声:按照我们的规定是严禁录音录像,他要是偷偷录十秒、二十秒你也管不了他。哪怕你为了让观众熟知,也不应该让人在这里直接录。
“《着急》是我最喜欢的相声作品之一”问:演出视频上网也牵扯到抄袭的问题,现在相声抄袭几乎没有成本,受此影响有些人就不写新活了,这是现在一个比较突出的现象。
王声:问到点子上了。我作为中国曲艺家协会行业风气和道德建设委员会的委员,来谈一谈这个事儿。抄袭事件由三方构成,作者、首演演员和抄袭演员。从作者角度讲,抄袭是对作者的极大不尊重,演员用了人家的活给人家钱,这是天经地义的。你看到一个活不错,在未弄清作者是谁以及付款方式之前,任何人不要演,如果最后一查这活是侯宝林写的,那我演了吧。这要靠自觉,我们不能把不自觉的都枪毙,国家没有那么多枪。演员这个自觉和社会普遍的法规遵从是一样的,得逐步养成,因为这个行业松散了很长时间。第二,首演演员对这个作品有普及和宣传的义务,演完之后不管好与不好,得对外告知是谁写的。如果演员在剧场演出没有时间说,主持人可以替你说,你也可以在自媒体上说。第三就是抄袭演员,他需要尊重首演演员,需要尊重作者,还要尊重相声行业。这三方聚到一起还必须说一点,都不要保守。作者说我这个活得压箱底,不能给别人,这不行。郑小山先生(王声的师大爷,苗阜的师父,2019年6月24日去世)当年跟我说过,有什么赶紧来问我,仨包袱儿俩垫话儿带不到坟里去,这是老先生的觉悟。相声行业核心已经越缩越小,当然外延现在越来越大,老先生越走越少,年轻演员断代越来越明显,到我们这一代全国真正能站在舞台表演的就那么些人。现在都说相声火,火的是抖音上,真正的从业者很少,所以不要保守,大家一定要进行有效的交流,让大量作品流通起来。一个演员每年演20个新活,留下两句话就行。当年原建邦先生跟我讲,不要认为你写一个活就能成一个活,你写一个活留下一个包袱儿,你坚持十年就有一个新活了。所以第一行业自觉自律,第二不要保守。
问:看来您已经有一个比较系统的想法。
王声:办法我没有,认知我到了。办法得“食肉者”去想,我们有建议权无监督权。
问:现在吃相声这碗饭的多,但真正发挥创造力的少。李菁老师说,很多年轻演员一直说传统作品,他认为传统作品是小时候学习相声和年老之后养老用的,年轻时候就应该发挥创造力创作新作品。
王声:这方面我和李菁也聊过,但演员要靠新活挣钱需要过程,生产过程比较慢。第二,很多年轻演员写新活能力达不到,最关键是新活不是拿出一个就能让人承认。大家都应该动起来,全都开始写,一批一批出作品,慢慢就成气候。传统活现在开发过度被用滥,是因为目前这拨相声兴起就是靠传统活,你返回头再演过去的新活照样能出效果,就看有没有人干。
问: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中前期,是相声的一个中兴阶段,那么多新演员,那么多新作品,但把传统也抛弃了很多。
王声:说抛弃不准确,也保留了一大部分。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艺术,那个时代的风潮就是那样,吉他相声,穿西服说清新的相声,那是各种各样的元素集合到一起构成的。不能说它抛弃了传统,如果完全抛弃就不算相声了。
问:我看大逗相声他们在改一些八十年代的经典作品。
王声:我们也在大量地改。
问:您觉得这是一个路子吗?
王声:不是路子的问题,八十年代的活到现在也是传统活了,那些作品为什么就不能翻演啊?
问:很多年前,我曾经作为相声观众代表跟央视春晚语言类编导聊意见建议,赵福玉老师也在,我当时就说为什么不能改一个《着急》新版,新时代人们着急的事情不一样了。
王声:《着急》是我最喜欢的相声作品之一。这个活我改过一版,但改得不成熟至今还没有演过。梁左先生写这个东西太好了,理路清晰。什么是经典作品?就是留下之后任何一个时代看都不过时,值得反复琢磨反复听反复看,梁左先生的好多作品都是这样。典范中的典范,一个是《着急》,一个是牛群的《威胁》。这些传统作品都可以翻演,演不好是能力问题,演不演是态度问题。
“相声还得回归最原始状态,就俩人站这儿说”问:都说现在全国那么多小剧场,一看节目单大同小异。
王声:打不完的“灯谜”,学不完的“聋哑”。不过大家也得宽容一点,因为常态演出对演员和节目的消耗非常大,一个演员可以做到一个月不翻头,俩月不翻,半年不翻,但一个剧场开多少年?就算两年不翻头,第三年你是不是还得翻?
问:对于你们的商演来说,节奏还是可以的是吗?
王声:还算正常吧。
问:还是有时间去创作作品。
王声:有时间去打磨一下。
问:说一下苗老师吧,他也评价您来着。
王声:他也吐槽我来着是吧?

2019年,苗阜、王声表演相声。杨明拍摄
问:他一个劲儿夸您。
王声:我可不敢说省领导什么坏话。
问:他现在也不像有段时间似的,动不动在微博上来两句惊人之语。
王声:可能是现在酒喝少了。
问:您一直算是比较淡定,跟年轻演员说活的时候,有时候会急吗?
王声:急呀,我是有名的酸脸。刚才台上那些人哪个没让我骂过?其实我性格比较暴躁,我是一个偏急性子的人。

2019年4月,王声在剧场指导演员排练。本文作者拍摄
问:伪装得比较好。
王声:因为知道自己有这种缺点,所以得装着点儿,我也得练练涵养性。
问:评价一下苗老师的业务吧。
王声:没有什么可评价的,全国这么多青年相声演员,能到他这个程度的没有几个。
问:他的表演总是那么火爆,充满精气神儿,你们叫“卖”。
王声:你没见过他师父,郑小山先生演出就是这个样儿,在台上比较冲,形成了一种自我表演方式,一进入表演状态就兴奋,怎么演都顺手。
问:您是一开始跟他合作就感觉很搭,还是也要经历一个过程?
王声:演员得磨。从2006年开始,一直到2011年、2012年才慢慢默契起来。
问:面对一个表演比较火爆的逗哏,捧哏演员如何既能完成任务,又不让人感觉他故意抢戏?
王声:这个得设计,俩人不设计上去就平铺着说,一辈子也说不出来。
问:现在有一个词儿说捧哏要“造反”。
王声:捧哏要“造反”不是今儿,冯巩就“造反”了,牛群和冯巩合作,冯巩永远是抖包袱儿那个人。
问:但是我们小时候看不觉得很突兀。
王声:两个人很合适,节目效果也能达到,这就行了。
问:对,还有贾冀光、魏兰柱合说《华山群英》,包袱儿也都在捧哏那儿。贾冀光老师说,包袱儿适合在谁那儿就给谁。
王声:对呀,他俩演过双簧,魏兰柱先生一使相,那谁也干不过他呀。
问:你们俩这种情况少,突出到捧哏这里的作品……
王声:没有。我本身不喜欢这种所谓的“倒三七”的活。我师父教给我说捧哏该怎么演,我就按他教我的演,其实我现在有些地方已经很过火了,我师父如果在的话他就得生气。
问:有些时候,观众是希望看到老老实实的捧哏造一些小“反”的。
王声:我觉得这是现在相声演出中形成的一种逆反式心态,是剧场演出中形成的一种不好的习气,它会破坏演出节奏,对节目是有伤害的。这一段儿你们过瘾了,那它到最后奔“底”去的时候怎么办呢?
问:正好说到“底”,过去来说底一般来说是一段相声的大包袱儿。
王声:必须得大。
问:但现在来说,很多时候观众是那种感觉,啊?这就完啦?谢幕啦?
王声:赵佩茹先生讲过,他讲张寿臣老说过,底都使不响你算什么说相声的?但是现在很多底不响。
问:很多时候逗哏一直强调一句话,重复一句话,这句话基本就是底了,《这不是我的》也是这样。没有超出观众预期,这样就不会太响。
王声:我也很尴尬。
问:这和现在的相声手法是不是有直接关系?很多作品比较零碎,各部分之间形不成渐进关系,所以到最后没有办法归到一个足够大的底。比如当年《虎口遐想》讲的是一个完整事件,到最后大家都拎着裤子没法握手,那就是超乎观众预期啊。
王声:现在还是艺术程度不够,把握程度不够。一个相声是为底服务的,你连底都使不响你算干嘛吃的?
问:有点儿像平庸的电影。
王声:对,高潮都没有,你看的是《地球最后的夜晚》。
问:自始至终是平的,长镜头。
王声:你在艺术院线可以。相声缺乏有力的底,还是创作者能力不强。包括我们也是一样,底使不响就是前头没弄明白,糊涂相声。
问:按照现在这种发展状态,娱乐化也好,互动性增强也好,您感觉将来的相声在表演上会不会发生大的变化?
王声:要我说,相声到最后还得回归到最原始状态,就是俩人站这儿说,站这儿唱,连那种大规模跑动最后都得慢慢烟消云散。相声就是这么一种艺术,大家想怎么变怎么变……
问:别叫相声了。
王声:你是别的艺术形式,你成立一个别的门派。你再火,人民大会堂演完观众不愿意走让你留三天继续说,那是另一种表演形式,跟我们没有关系。你可以在台上说,我借鉴了很多相声的表演手法,这是你有良心。这个世界上所有搞喜剧的离不开三翻四抖,谁要能离开那你是一代宗师。当年说相声那些老先生都是人精。
问:那对于有可能发生的变化,您是乐观还是悲观的?
王声:不乐观,不悲观。金斗叔跟我说过一句,爷们儿,这个世界上永远是倒霉的推着走运的走,走运的永远不知道自己要走运了。什么意思呢?否极泰来,物极必反,你总想我们这艺术怎么这样了,不要着急,亢龙有悔,潜龙勿用,这永远是一个交叉演变的过程。
问:希望是这样。有一个说法是外行最终决定了一种艺术,比如京剧之于昆曲。
王声:永远是外行决定艺术。我就问您一句,京剧还在不在?昆曲还有吧?
问:但是昆曲现在就是不如京剧火呀。
王声:别着急呀,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艺术风向,我都不替我闺女着急。在北京我跟很多人聊,他们都说您真乐观,我说不乐观咱也没办法,因为目前这个相声世界就是这样一个世界,每天看得我心惊胆战。
问:真像侯先生担心的。
王声:还不是侯先生担心,现在有的表演都有伤风化了,这并不是相声能不能说好的问题。

王声接受采访中。张望志拍摄
注:除特别标注外,文中图片均来自网络
——end——
,免责声明:本文仅代表文章作者的个人观点,与本站无关。其原创性、真实性以及文中陈述文字和内容未经本站证实,对本文以及其中全部或者部分内容文字的真实性、完整性和原创性本站不作任何保证或承诺,请读者仅作参考,并自行核实相关内容。文章投诉邮箱:anhduc.ph@yahoo.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