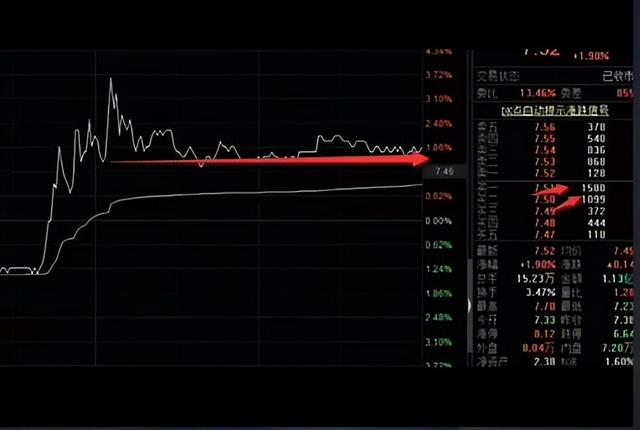人类语言与动物交流的区别(人跟动物交流的特殊语言文化)
如果你家里养了宠物,大概能理解人与动物之间有专门的交流“语言”,这实际上是老祖宗传下来的。以土地为生的时代,人与牲口、家禽的交流比之现在可丰富多了,不仅仅是生活经验,还是一种独特的语言文化。

曹延召 | 文
对牛弹琴不行
但可以跟牛说话
有道是“人有人言,兽有兽语”,人和动物在没有共同语言的沟通下,其实也可以通过特殊的“语言”进行沟通,有时候“对牛弹琴”行不通,但对牛说话还真是管用。
在农村老家,家家户户总养着那么一群鸡鸭狗鹅,狗子猫子数量不多,起个小黑、小花什么的倒是可以,喂食时候扯着嗓子一叫,小东西撒着欢儿就跑到你跟前了,但是要是养着一群猪、一群羊、一群鸡,那岂不要翻着《起名大全》来起名,喂食时候挨个来点名召唤?
其实,在农村无论是谁家,每种动物都有他们自己通用的名字,呼唤它们的时候也有通用的语言。

夕阳西下,常见鸡皮鹤首的老太端着半笸箩秕麦子站在屋前,嘴里“咕咕咕”地一叫,在门外林间草丛打野的鸡儿像一堆滚动的肉球般一窝蜂地就冲进院子。
老太用左手把笸箩架在腰间,右手从笸箩里抓起一把秕麦撒向鸡群,近处的鸡儿挤成一团了,就赶紧向远处再撒一把,一边喂食,一边在嘴里数着“哟、俩、仨、四柔、五窝——”。
在农村老家,家家户户都要养几头猪,一来剩饭剩菜免得倒掉浪费,二来到年底了不用再花钱去割肉,三来没有能力外出打工的妇女老人也能挣个零花钱。
打记事起,家里猪圈里年年都要养几头猪,每顿做饭时候,也要顺带着馇一些猪食。

干红薯秧子、花生秧子吹成的“糠”、玉蜀黍进“一风吹”吹成的“料”,两瓢糠一瓢料,在盆子里搅拌均匀,做饭时候多添几瓢水,水开时候先舀出来几瓢把猪食给烫着,然后再往锅里搅面水做人吃的稀饭或是糊涂。
等人吃完饭,猪食也馇的差不多了,再把锅里吃剩的糊涂连同刷锅水一起,跟猪食搅拌均匀了端到猪圈去,“啰啰啰”一叫,原本睡意正酣的几头肥猪争先恐后地就向猪食槽奔来,几个脑袋挤到一起头也不抬地竞相抢食吃。
老黄牛踏实好说话
老犟驴任性耍脾气
在没有机械化的农耕时代,家里养头牛也是必不可少的。
人与牛的交流不像是鸡和猪多在喂食时候交流,似乎在耕田工作的时候交流更多,语言也更为复杂。
麦罢或是秋收过后,爷爷就背着犁子牵着牛下地了,牛嘴巴上罩一个“牛笼嘴”防止牛打野啃青,牛脖子上架上一个人字形的“牛销头”方便受力,撇绳、袂绳、炮杆等一套耕地的装备连接完毕,爷爷对着红铜烟锅猛吸几口,而后在犁子上一磕烟灰,别在腰间就开始耕地了。
左手扶着犁子,右手攥着扎鞭,嘴里“嗷”一声吆喝,那头老牛就会意地迈力前行了,老牛发力、铁犁驻土,在老牛和爷爷走过的地方翻起的是一地泛着油光的沃土。

一塍地有好几百米长,中间难免会有拉偏的地方,万一犁子拉偏了,需要牛向右边走就吆喝“大大”或者“大大着”;需要牛往左边走,就吆喝“咧咧”;需要站住停下,就喊“喔”;需要牛往后退,就喊“哨”。
这些个与牛交流的语言,不仅爷爷会,在农村的每一个“把式”也都会,不仅光我们家的牛听得懂,老家那片的耕牛也都听得懂,换了把式换了牛,只要你谙熟这些语言,耕田耙地都没有问题。
踏实的老黄牛用语言可以轻松驾驭,但是万一碰到了“老犟驴”咋办?
面对“老犟驴”即便是有通用的语言,驾驭起来还是够费劲的。
卖豆腐的二爷爷家就养着一头黑色的老叫驴,老驴拉磨是常事,每天午后,歇晌起来的二爷爷把泡泛了的豆子拎进磨坊,拉驴上套就开始磨豆腐了。

老叫驴眼睛上罩着“驴碍眼”,“对儿”一声吆喝,叫驴拉着磨盘就开始转动了,一般情况下老驴还是比较敬业的,但偶尔也会耍滑偷懒,若是长时间没有听到二爷爷那经典的咳嗽声,老驴也会准确地判断二爷爷多是不在磨坊里,就会停下来偷懒片刻。
等二爷爷推门进来,一看老叫驴歇了活儿,拿起门后的笤帚就往驴屁股上夯,一边夯一边骂“你个鳖孙,还怪会偷懒咧!”
挨了打的驴身子一挺,石磨又开始轰隆隆转动了。
挨了打的驴子多半时候比较听话,但也有任性耍脾气的时候。

二爷爷的笤帚前脚放下,后脚老驴就又停下来了,“哗啦啦”一泡尿就浇在了磨道上,趁着二爷爷去灶膛底下掏灰垫尿的功夫,老驴可以趁机休息一会儿,可结果是驴尿刚拿土灰给垫上,老驴的尾巴一撅,一串的驴屎蛋儿欢快地在磨道里滚开了,似乎在宣泄着对这份工作的不满。
“老驴上磨道,不屙它就尿”,面对这老驴常用的伎俩,二爷爷多半不再斥骂,轻轻走过来在驴脸上拍打两下,用商量的语气跟它说:“好好哩,拉了了,有渣吃!”
说来也怪,那老驴通人性似地再也不拉不尿,一口气就把一盆豆子给磨完了,二爷爷也守信用地舀一瓢豆渣来给驴吃。
其实,在老家,逢年过节有乡亲需要借磨坊磨豆腐,也多半会把豆渣留下来作为对主家和老驴的感谢。
因为牲畜
人与人之间也有了特殊语言
在中原农村,人和动物用特有的“语言”进行交流不是啥稀奇事,但有时候人和人之间明明有通用语言可以用来沟通,却偏偏不用,非要整出另外一种交流的“语言”来,而且这种特殊的交流语言也多半是和牲畜有关。
这种因为交易牲畜而产生的特殊语言,老家称之为“行户话”,是一种只在袖筒里比划而不用嘴说的语言。

记得小时候,每次跟爷爷一起去庙会上“赶绳”(卖牲口),就有行户围过来,卖羊的时候他们拦腰将羊抱起来估估斤两,卖牛的时候他们凑上前,掰开牛嘴看看牛的牙口,然后再把爷爷的手拉进他的袖筒里,用手指头捏个价格,这叫“搭价”或者“佯绳”。
搭价往往是卖家的一个试探性价格,就是想测测自己家的牲口究竟值多钱,所以,没有赶过几次不同的庙会、没有经过三四轮行户的“搭价”、“佯绳”,卖家是不会轻易将牲口卖出的。
同样,很多买家也是心存顾虑,要买的牲口究竟有多大年龄,买回去的牲口有没有力气干活?他们也要寻找一个靠谱的人来帮忙识货,于是,行户的作用就开始充分凸显了。

他们通晓市场行情,他们识得牲口秉性,他们奔走于买主与卖主之间,巧言介绍,多方说和,反复在袖筒里以摸指来讨价还价,促使双方最终达成交易。
农耕时代,我们的先祖在与动物们的交流中创造了独有的交流语言,经济时代,在市场交易中人与人之间又形成了奇特的无声语言,然而,这些独特的语言交流方式正在时间长河中日渐消逝。
当机械化时代来临,当农村的大片土地都被流转,大批的农村人都住进了林立的高楼,一头扎进钢筋水泥的笼子里,邻里之间难得有一句话语的交流;当信息时代来临,当手机霸占了我们的生活,朋友之间在微信上聊得火热,到了一起却默然无语……
不是我们的话语变少了,而是时代跟环境让人类的语言功能退化,那些传承千载的语言文化也随之被遗忘在回忆里。
(图片来自网络)
豫记版权作品,转载请微信80276821,或者微博私信“豫记”,投稿请发邮件至yujimedia@163.com
豫记,全球河南人的精神食粮!
,免责声明:本文仅代表文章作者的个人观点,与本站无关。其原创性、真实性以及文中陈述文字和内容未经本站证实,对本文以及其中全部或者部分内容文字的真实性、完整性和原创性本站不作任何保证或承诺,请读者仅作参考,并自行核实相关内容。文章投诉邮箱:anhduc.ph@yahoo.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