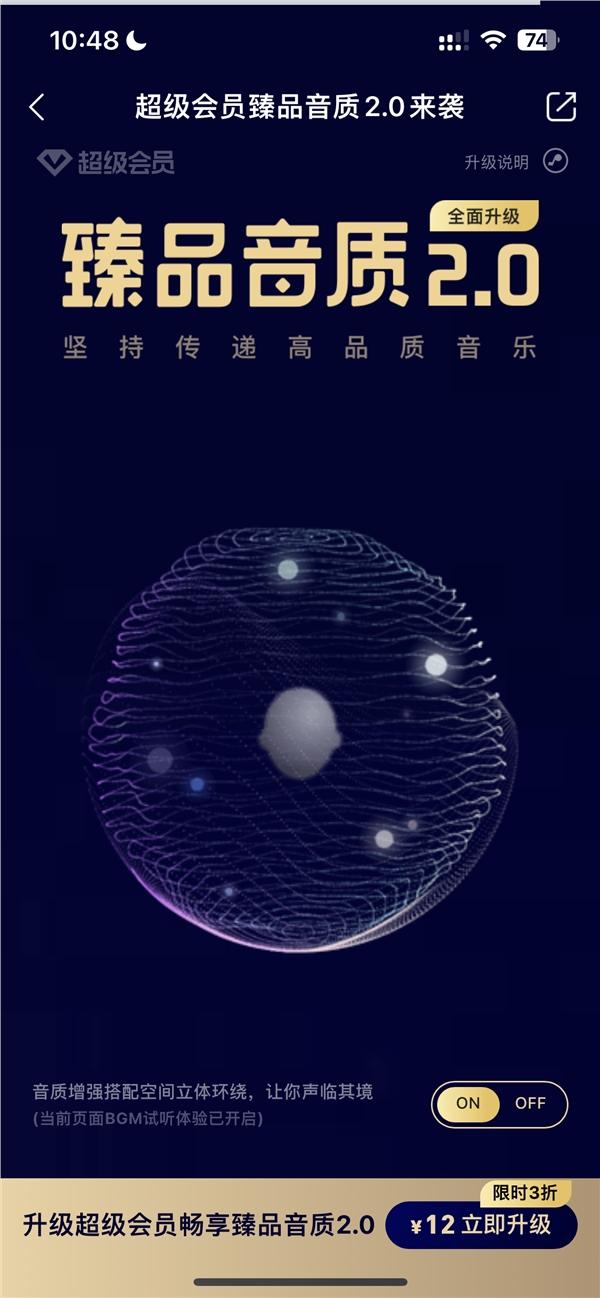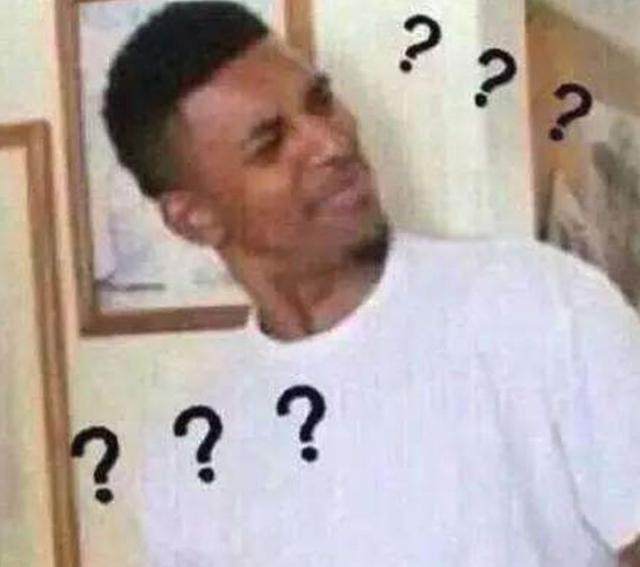大航海后世界发现了什么(欧洲大航海时代先驱伽马花两年远航亚洲)

瓦斯科·达伽马

瓦斯科·达伽马和他受上帝眷顾的船队
“为什么宗教战争的爆发,会渗透到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这是奈杰尔·克利夫(Nigel Cliff)的根本问题。为此,他写了一本关于瓦斯科·达伽马的书。
听上去这两件事情风马牛不相及。500多年前的葡萄牙航海家,和今日世界的宗教战争与恐怖事件,会有什么关系?
从2001年美国“9·11”事件以来,马德里、莫斯科、伦敦、巴黎这些原本象征着西方世界繁荣发达的大都市,陆续在突发新闻中与宗教狂热分子制造的血案联系起来。人类不同族群之间的伤害,促使奈杰尔·克利夫思考如今遍布世界的宗教矛盾究竟从哪里开端,又在哪里转折。
“我意识到我们是被拉回到了一场古代冲突中,而关于那场冲突,我们集体丧失了记忆。”在2012年出版的《最后的十字军东征》序言中,克利夫写道,“所谓的进步是胜利者自我陶醉的故事;失败者的记忆却经久不灭。某些当代伊斯兰教徒认为,他们的目标不是与西方和平共处,而是要斗个你死我活,用他们的话说,梁子早在500年前就结下了。”
在以西方视角为主的现代文明史中,从1497年7月8日葡萄牙人出航、史无前例跨越印度洋并抵达印度,到1499年7月10日第一艘帆船回到里斯本,这整整两年杳无音讯的远航探险,把历史永远地分为两半。之前是黑暗漫长的中世纪,之后则是光辉荣耀的现代。之所以“黑暗”,因为伊斯兰教势力总的来说压制着基督教势力;而之所以“光辉”,则因为欧洲的基督徒第一次绕过中东和北非的穆斯林世界,直接与富裕的东方接触,从此开始殖民时代的原始资本积累。
“作为一个英国人,我很想搞清楚欧洲究竟做了什么,双方过去都做了什么,那时候大家是如何看待彼此的。这是我写这本书的重要原因。”
在研究了大量文献资料之后,克利夫把达伽马的航海探险与中世纪长达200年的十字军东征联系在一起。他认为,达伽马去印度洋的探险与十字军那8次东征有某种共同之处。在罗马天主教教皇准许下,西欧封建领主组织军队对地中海东岸的国家发动战争,是宗教动机把“侵略”变成了“收复失地”;而15世纪末的伟大远航所开启的野蛮殖民时代,也因“找寻失落的基督同伴国家”这样冠冕堂皇的理由得到正名。
所以,克利夫把这本讲述达伽马发现亚洲航线的书,命名为“最后的十字军东征”,因为达伽马实际上完成了当初十字军东征没有完成的任务——他们终于开启了基督教国家掌控全世界的新时代。
关于达伽马的好故事
众所周知,在达伽马之前,意大利人克里斯托弗·哥伦布已经先行出航了。他肩负着西班牙君主的期望向西远航,第三次横跨了大西洋之后抵达美洲——可当时迫切希望找到通向神秘东方之路的欧洲人,根本就没想过世界上居然还有新大陆。所以从某种程度来说,哥伦布的发现是个“伟大的错误”。
两位探险家的目标一致,都是寻找通往亚洲的航线,但长期以来,哥伦布那个伟大的错误却一直令瓦斯科·达伽马的成就黯然失色。“不过对我来说最重要的一点是,与哥伦布不同,达伽马真的如同出发时所想的那样到达了印度。在哥伦布发现美洲之后几十年里,其实大家心中的世界地理概念还都是模糊的,以为必须要穿过美洲才能到达亚洲。”
克利夫选择书写这段历史,首先因为达伽马是个有趣的人物——投入航海事业之前,他完全是个无名小卒,但他具有某些非凡的首领特质,比如绝对的忠诚、对信仰的虔诚,以及最为可贵的,航海家、探险家必备的勇气,“特别像海盗”。
这次探险的整个航程极富戏剧性。“像真正的史诗一样,人们花了两年时间与大海搏斗,与家乡失去联系,唯一的依靠就是基督教信仰,有时会连续三个月在视野里看不到任何陆地的影子;当他们进入印度洋,情况变得更糟,没人做过这些事情,既没有地图,也没有任何已知信息。他们遇到的异域文化可能出现各种情况,有些人很友善,有些人则凶险。”克利夫说,“人类主动地跑到未曾去过的地方,经受重重考验,这件事本身就是个很好的故事。”
为了写作这本书,克利夫跑遍伦敦的博物馆、图书馆,还特别去研究过哥伦布当年出海时驾驶的航船。“当然我还读了大量航海教程,那些书就像是用外语写的,几乎每一个船上的小动作都会有个专属的术语。毕竟我写书是为了给大众读者看,所以必须搞清楚所有的细节,尽可能地避免出现晦涩难懂的词语。”
他两次去葡萄牙,每次待上几个星期,又花了一个半月重走达伽马当年的征途:从南非开始沿着非洲东海岸向北旅行,经过莫桑比克、坦桑尼亚、肯尼亚,横跨印度洋到达印度南部的喀拉拉邦,然后继续往北直到缅甸东北部的克钦邦。
如果不是亲自去过那些地方,他觉得自己很难写出几百年前发生在那里的探险故事。“我想去亲眼看看印度洋上的日落。”他说,“而在现场我感到尤为震惊的是,从海面看上去,非洲大陆是多么的不起眼——就是天边那么狭窄的一条深绿色而已,向两边无限延展出去,什么山脉地势起伏都完全看不出来。”
越是以现代人的状态身临其境,就越发敬佩当年航海家之壮勇。没有地图,没有航海图,航船都靠风帆作为动力,偶然出现的洋流、大风随时会扰乱航线。那些船又那么小,只能搭载30~100名船员,甚至与半个多世纪前下西洋的郑和舰队比都相形见绌。
叙述性非虚构写作
克利夫在这本书的创作中使用了一种特殊的写作方式。他说,传统的英国历史写作,一般只分两类:严肃历史学术著作或流行历史小说。而他的风格“介于二者之间”。
“一方面,我当然希望自己的历史写作能变得流行,不是只给学者们看,而是让更多大众读者接触到。但是另一方面,为了写作而做的那些调查研究是严肃的,跟我准备写一本学术著作的研究方法没什么差别。”他说,这种来自美国的文体,准确的叫法是“叙述性非虚构文学”,即基于事实来写作,但同时需要借助虚构文学创作中的某些文字技巧。
事实上,在收集完材料、做完调研之后,最难的部分才刚刚开始:如何把历史事实材料雕琢出引人入胜的故事。这个环节所需要调用的能力与虚构小说创造不相上下。“写的时候必须非常小心,不要创造事实。这其实非常困难。因为在完成一本书的过程中,作者常常与书里的人物朝夕相处两三年之久,他们遇到某类情况会做出怎样的反应、对某件事会做出怎样的评论,你知道得一清二楚,却不能写出来,因为那都是没有被史料记载过的。”
这种谨慎的态度贯穿全书。所以读者不会看到达伽马在遇险时产生怎样的心理活动,也不会看到欧洲人与印度人具体的对话内容,一切都严格依据被学界证实过历史真实性的记录文献。克利夫认为,一旦开始表达作者个人的感受、想法,那就意味着开始虚构写作了。所以即便是作出假设,也需要保证自己传达出来的意思是经得起学术推敲的。
但作者的价值观还是不可避免地会体现在写作中。在《最后的十字军东征》里,克利夫就在精心编排的历史事实当中埋设了自己对葡萄牙人的批评态度:当“伟大航路”被开拓出来之后,达伽马后面的两次重访,对异族施加了极其野蛮而血腥的暴力。这些行为与航海探险的勇气交织并列,构成了一种历史的真实。
“15世纪末,军队会在占领敌人的城市时用屠城来示威或庆贺,这有点像是欧洲世界通行的潜规则。那的确是个野蛮的时代,可是达伽马把这种态度带去了东方,因此而造成某种黑暗的后果。”克利夫说,“葡萄牙试图在东方寻找基督教同伴,试图寻找那个谜一般的‘亚洲基督教大国’。许多欧洲人真心相信关于祭祀王约翰的故事,说他的王国拥有欧洲三倍的人口。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段旅程是因为无知才成功的。假如他们事先接触过哪怕一位来自亚洲的基督徒,可能就不会去那里。”

《最后的十字军东征:瓦斯科·达伽马的壮丽远航》
【英】奈杰尔·克利夫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甲骨文2017年5月版
对话奈杰尔·克利夫
现实是如此的疯狂,比虚构更胜一筹
第一财经:为什么书名要叫“最后的十字军东征”?
克利夫:开始我发现了这个很好的角色、很好的故事,然后是这个故事背后更为深远的意义。达伽马的旅程将世界分为截然不同的两个。在英语世界其实他的知名度不如哥伦布,可是他至少是哥伦布发现美洲那个故事的另外一个侧面。
在那之前,伊斯兰势力要大于基督教势力,他们控制着葡萄牙、西班牙和北非,还有土耳其,是世界上最为富裕的地区之一。因为他们掌握着从中国、印度运送香料货物到西方去的命脉。达伽马开创性地绕过伊斯兰地区,直接到达亚洲,这样就省去了中间商环节,进而让欧洲人意识到控制全球贸易是件举足轻重的事情。那是欧洲开始增强全球势力的源头。
当年的十字军东征是罗马教会集结成批的基督教国家军队向耶路撒冷进发,这个过程持续了近200年。可是那之后,东征并没有完全停止,时不时还会出现一些号召和响应,其中包括海上船队,他们到红海、印度洋,阻断伊斯兰地区的贸易命脉。葡萄牙当时是个非常正统的天主教国家,并且与隔壁的西班牙始终处于激烈的竞争关系中,于是两者争先恐后以教皇的名义进行海上东征。所以远航的宗教背景其实至关重要,可以让这些国家向教皇证明自己做了对的事情。
第一财经:现在人们普遍把地理大发现的动机理解为单纯地寻求财富,宗教在其中到底占有多重的分量?
克利夫:当那些水手在海上航行的时候,常常会发出这样的祈祷:是上帝带来顺风助力我们完成使命,上帝鼓起了远航的风帆,上帝派来了洋流拖垮敌人……如果你读葡萄牙君主留下的文字,他会把自己认作是上帝的棋子,受到上帝的旨意要把基督教传播到全世界去。当然,你也可以认为这些都是借口,实际上他们就是想要钱。
可是,单纯认为“他们探险的目的只是为了更有钱”,这个想法本身是属于现代的。因为在那个时代,你真的很难把一个国家财富的多少与他们的宗教生活分开来讨论,就好像你无法将国王、教会与国家分开讨论一样。国富民强,他们会认为是上帝对人们虔诚的奖励。反之亦然。
第一财经:这段历史是否有助于我们理解当今世界的宗教矛盾?
克利夫:如果一切矛盾都只是金钱问题,就会省事很多,是不是?人类的宗教矛盾太复杂了。这段历史故事会提醒我们,当今社会的宗教冲突其实由来已久,双方纠缠了十几个世纪。部分原因是基督教与伊斯兰教总是在争夺同一片土地,而且这个问题也不会在短期内得到解决。
我们虽然处于现代社会,更加文明,但是冲突的某些模式与历史上并无二致。达伽马之所以开始这段旅程,有个很具体的目标,就是打破伊斯兰教国家在中国、印度等地的贸易垄断,这与当今社会的经济战争极为相似。
不过在我心底里,写这本书还抱着一个期待,就是我希望了解作为欧洲人,我们曾经的行为是什么样的,世界上其他地区的人是怎样看待我们的。写书的时候我会与非洲、印度的人们谈论这个话题,他们看待历史的视角与我们习惯的大不一样。
第一财经:欧洲人开启地理大发现前后不到20年,相比于十字军东征的200年,怎样看待这两者之间的对比?
克利夫:准备工作很长,而突破时间很短。这件事最好玩的地方在于,欧洲那么多有实力的大国想着远航去非洲想了这么久,最后居然是小小的葡萄牙干成了这件事。从近一些的地方开始,一点点地走得更远,不同的船长、不同的国王,之后所有人都要沿着他们开发的路线前进。一点点地坚持,最后成就了巨大的梦想,这一点非常令人赞叹。最后到达东非、横穿印度洋,几乎就是在两三年之内的事情,的确很快。
无论他们之后在亚洲做了什么,你终究还是无法否认他们的勇气。那么小的船,我是说真的,在几十年前中国明朝的船只也曾经到访过印度,那可是巨大的体量。有种说法是,如果中国当时决定要把印度洋纳入自己控制下,那么葡萄牙绝对没有机会。可是中国放弃了,以至于让欧洲的小船能够乘虚而入。
,免责声明:本文仅代表文章作者的个人观点,与本站无关。其原创性、真实性以及文中陈述文字和内容未经本站证实,对本文以及其中全部或者部分内容文字的真实性、完整性和原创性本站不作任何保证或承诺,请读者仅作参考,并自行核实相关内容。文章投诉邮箱:anhduc.ph@yahoo.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