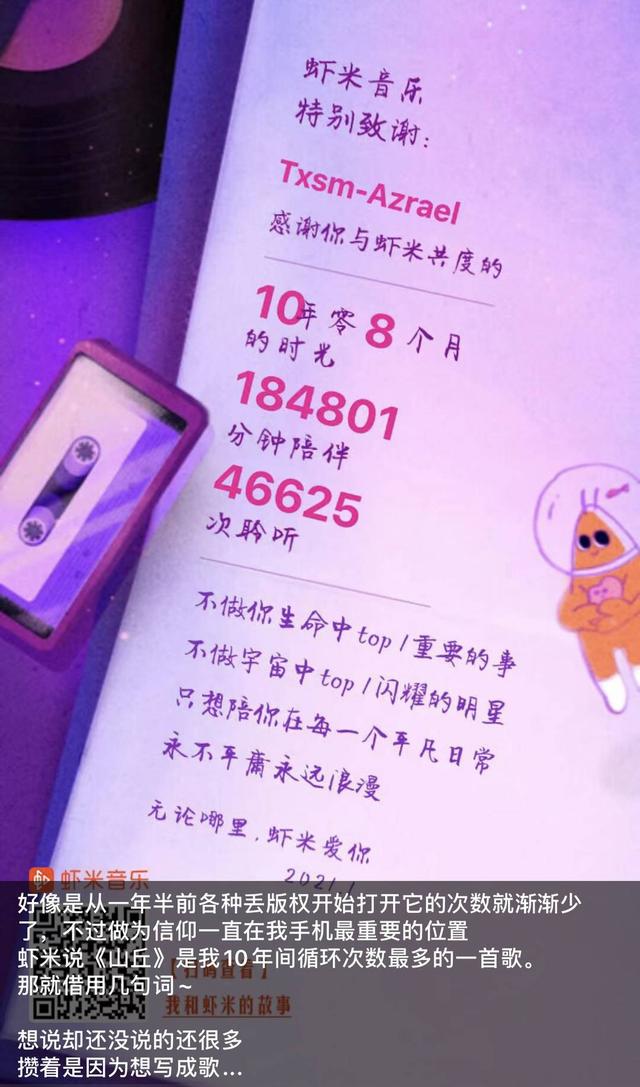真正的桃李满天下(真正的桃李满天下)

探析金铁霖声乐教学理论体系中的少数民族声乐教学
盛梅
一、前言
2013年11月28日,中国著名声乐教育家金铁霖先生从教50周年学术音乐会在中国音乐学院举行了新闻发布会。12月6日,金铁霖众多优秀的弟子,包括宋祖英、阎维文、戴玉强、郁钧剑、董文华、张也等优秀歌唱家,齐聚中国音乐学院国音堂,用各自优异的演唱,展示金教授50年来的教学成果。回顾金铁霖教授50年的教学生涯,金教授始终坚持洋为中用、古为今用的开放式教学理念,探索中国民族声乐表演风格的科学化道路,在学术方面并不断深化、拓展,为中国民族声乐的发展和繁荣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在日新月异的今天,音乐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局面下,歌唱艺术也与时俱进,不断蜕变,获得了新的成就,当然也遇到新的问题。伴随着中国民族声乐教学的发展和深入,金铁霖教授并没有停歇,始终对系列的学术、实践问题进行着深入的思考,对少数民族声乐教学的思考就是其中重要的内容之一。本文在回顾金铁霖教授50年的教学成果的同时,深入系统地探讨金铁霖教授近年来对于少数民族声乐教育的尝试和探索,并且在此基础之上,以新的视角更为深入地理解金教授所提出的中国声乐的内涵和外延。
二、少数民族声乐教学
中国是多民族国家,56个不同的民族中,很多都保持着独特的歌唱特色,这些特色是中国声乐领域中重要的组成部分。20世纪30年代,留学德国的著名音乐学家王光祈先生在论文《东方民族之音乐》中提出世界音乐的三大音乐体系:中国乐系、希腊乐系、波斯—阿拉伯乐系。基于比较音乐学的全球视野,我们看到中国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包含了三大音乐体系的国家。这一点很大程度上归功于中国民族的多样性。因此,中国的少数民族音乐具有明显的丰富性,这不仅体现在音乐乐制方面,更体现在丰富的表演体系中。中国的55个少数民族的音乐孕育着多种歌唱风格和唱法,从苗族的飞歌到侗族的大歌,从蒙古族的长调到维吾尔族的木卡姆,从朝鲜族的民谣到回族的花儿,从藏族《格萨尔王传》到达斡尔族的山歌扎恩达勒,大江南北丰富的演唱风格使得中国的音乐文化别样灿烂。通过不同风格的演唱,我们也发现了中国声乐表演体系的多样性。在中国音乐作品所汇聚的长河中,很多少数民族歌唱特点与音乐风格也体现在中国当代的声乐作品创作之中,比如彰显蒙古族风格的《牧民歌唱毛主席》、塔吉克族风格的《花儿为什么这样红》等。少数民族音乐丰富的表现方式、多样的演唱内容,在当今音乐社会中得到了全方位的关注,这一点体现出当代社会的多元性和包容性。但是,与受欢迎程度形成反差的是,我们对于少数民族声乐实践方面的探索却还处于起始阶段。我们必须承认,以往对于少数民族音乐文化的关注,更多集中于音乐理论、音乐文化等宏观方面。但就这一方面而言,我们的研究也并不彻底,关注的内容也非常有限。而更为薄弱的是,我们无法真正站在声乐表演的基础之上,思考如何在保持少数民族声乐特色的前提下,提高声乐的科学性,使少数民族声乐获得全面、系统的发展,成为中国声乐体系中最为灿烂的组成部分。
针对这一学术问题,近些年来,金铁霖教授展开了深入的思考,并且在实践教学中不断尝试解决相应的问题。回顾中国声乐发展历程,尤其是在新中国建立以后,涌现出一大批优秀少数民族声乐人才,包括才旦卓玛、德德玛、克里木等。优秀人才背后是声乐教育家的卓越工作和辛勤奉献。新中国成立以来,许多著名的声乐教育家对少数民族声乐教学做出了很多的尝试,包括上海音乐学院的王品素老师在内的一批教师培养了大量少数民族歌唱家。这不仅使少数民族声乐成为中国声乐领域的一支生力军,而且通过少数民族歌手的演绎,增进了中国各民族人民之间的交流和理解。自21世纪以来,少数民族音乐在规模和质量方面得到更全面的发展,更多的少数民族歌手出现在大众面前。金铁霖教授的课堂之上,也迎来更多的少数民族声乐学生,其中包括了维吾尔族、蒙古族等不同民族的学生。在教学的过程中,金老师发现,虽然少数民族的歌唱非常具有自我的风格特色,但是在发声方法方面依然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一)自然阶段
自然阶段是所有技能学习的第一个阶段,是纯天然的状态。这种状态淳朴、简单,如同大自然天然的产物,更多体现出演唱者自身条件以及基础特点。这个阶段虽然是歌手的本真状态,能够更清晰地展现民族地域风格,但是,特定风格也会带来一些不科学的演唱方式。这种演唱方式虽然能够获得相应的声音特色效果,但是有时候可能会不利于嗓音的健康,也可能影响演唱者的歌唱寿命。虽然特点鲜明美丽,但也暗藏和积累了很多问题,当问题积重难返时,很可能葬送歌手的艺术生命。很多少数民族学员长期处于这个阶段,但对自身歌唱的发展阶段并没有清晰的认识,有时候更不愿意面对问题并积极调整。从系统论的观点来看,自然阶段中歌唱者没有经过科学系统的训练,歌唱处于自身条件的自然状态,歌唱的风格也大多是模仿别人。[1]少数民族学员长期形成的习惯唱法,里面保留了不同民族歌唱特点,比如维吾尔族歌唱者的歌声常常使用声音的前靠后的快速交替轮换来展现其特色,蒙古长调中经常会出现蒙古族马头琴的颤音的特殊技巧,藏族歌手则特别以喉音来进行装饰,丰富自己的声腔。[2]碰到多种多样的特色演唱方式,金铁霖教授第一步并非不分青红皂白地改变,而是尊重不同民族的习惯,并且从最接近演唱者的唱法开始入手,逐步调整歌唱者的技巧。金教授在对自己的教学体系进行总结时,特别强调:民族化的音乐语言主要是指二度创作的过程中,无论从音色、语言、情感表现等各个方面都要符合本民族的音乐语言习惯、风格和思想情感表现要求以及审美原则,体现我们对中华美的独特认识和感受。[3]这一阶段重点也包括了解决声乐和歌词的关系,在一种相对自然的演唱方式中展现不同演唱者自身的特点。从语言学的角度,中国语言可以分为五大语系,即汉藏语系、阿尔泰语系、南岛语系、南亚语系以及印欧语系,不同的语系又可以细分为语族以及语支,种类非常繁多。在声乐的教学中,教师既要保持少数民族在歌唱语言的发音方面的特点,又要讲究语言中的吐字归韵,符合五音(唇、齿、牙、舌、喉)、四呼 (开、齐、撮、合)的重要规律。
(二)不自然阶段
通过大量基础训练,逐步调节民歌的自然唱法与科学的发声体系之间的矛盾。这一阶段可能会使演唱者不适应,有可能出现演唱能力退步的现象,也会造成学习者心理方面的问题。但是,有经验的教师会很好地进行引导,快速地帮助歌唱者度过这个阶段。此阶段中歌唱的所有机能都在不断地调整,可以说是处于一种动态之中,包括呼吸方式、位置的选择、咬字的特点、民族风格旋律的润腔要领,以及其他方面的内容都在不断地寻找更为协调的状态。这一阶段也是三个阶段中最为关键的阶段,很有可能是持续时间最长的一个阶段。本阶段问题解决的好坏程度,直接影响到歌唱者未来的发展。但是教学者和学习者心中一定要明确,这一阶段虽然痛苦,但是是必须经历的过程。调整阶段是艰辛的,很有可能在多种方法中来回反复,总是无法明确科学的发声方式。学生在这一阶段也会在心理方面发生一些变化,很有可能由于心态的不稳定更加影响歌唱的状态。因此,我们要正视这个阶段的问题,这一阶段也是老师教学的关键阶段。苗族歌唱家宋祖英在博士论文中就针对这一阶段谈到了自己学习和教学的体会:在学习的调整阶段,教师和学生的耳朵是法宝,因为所有发声正确与否都需要通过声音的感知来鉴别。不仅如此,耳朵还要能够找到问题所在,进行及时的调整。[4]通过长期、正确的训练,悟性好、认真刻苦的学生将逐步达到基本的演唱要求,进入相对自如的演唱境地。此时的演唱建立在科学的方法之上,不仅不会抹杀自我条件的优势,更会达到以往无法企及的演唱能力。金铁霖教授谈到在维吾尔族学生艾米拉的教学实践中,根据学员的特点,先后运用了“前中大支点”和“开贴”唱法。在不断地调整和尝试之后,最后定位到“开贴”唱法,以此方式通过科学的训练,逐步引导学生体会正确的发声方式,再加上学生的努力领悟与刻苦练习,使学生的演唱水平有了很大的进步。[5]可见,这一阶段非常关键,是声乐训练中最为重要的分水岭。在金铁霖教授科学理性的训练中,学生能够突破自己的坏习惯,在保留原有少数民族演唱风格的基础上,显现出更高层次的歌唱能力。
(三)科学自然阶段
在教师和学生共同努力之后,学生能够运用科学的发声方法,轻松、自然地演唱,通过提高而重新获得本真状态,即如同老子所提倡的“常德不离,复归于婴儿”(《老子·二十八章》)的境界。在声音训练逐渐到位的同时,也要注重情、味、表、养、象等几个方面的内容。可以说,虽然学生在歌唱方面逐渐通过科学的方法找到了自我风格,但我们对一名歌唱演员的培养还远没有结束。优秀的学员会在个人修养、作品理解等多方面不断完善自己。当然这种提高是点滴的,也是普通歌唱者向歌唱家发展的必经之路。作为少数民族声乐学生,尤其要注意在掌握科学歌唱方法之后,更加大胆地表现自己本民族的风格。斯大林论民族性时,总结了民族所特有的共同的根本的特性,即每一个民族,不论大小,都有其本质上的特点,即只属于该民族而为其他民族所没有的特殊性。[6]民族性是人类音乐文化中最为重要的话题之一,尤其是在包含了音乐和歌词的声乐领域,民族风格更加明显。因为,声乐离不开语言,而语言正是不同民族彰显自我风格的重要内容。这一阶段的演唱是在科学自然阶段基础上的风格展现,表现本民族的音乐应该更加游刃有余,而不是摒弃自己的民族风格,或者使民族风格受到扭曲。金教授也注意到,少数民族歌唱者不仅体现出强烈的自我民族风格,也同样会展现自己个人的风格特点。每个学生也会根据不同的作品需要,不同人物性格的需要调整自己的演唱方式。不仅如此,演唱者还需要根据不同的演出方式的要求,做出一些调整。可以说,科学的演唱体系是在不断变化中完善的,体系本身也具有开放性。宋祖英曾深有体会地谈到自己演唱的经历,她在出演《赤道雨》中,演唱《望月》,运用的是“全通道下支点”,这种方式能够使各个音区声音平衡;2009年在美国肯尼迪艺术中心举办独唱音乐会时,她运用“下支点”全身唱的方式,使声音更为宽厚,气息流畅,吐字也更为清楚;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闭幕式的时候,她演唱《爱的火焰》,使用的是“中下支点”全身唱的方式,这是为了追求更多美声的色彩,并与多明戈演唱风格相协调。[7]不同的演唱内容配合不同的声乐技巧,演唱者个人也在不断地学习实践中获得了丰富的经验。由此可见,经过科学系统的训练,从个性演唱到掌握共性特点,再到展现更高层次的个性,能使一个歌唱学习者逐步走向成熟的歌唱家。尤其是少数民族的学习者,不仅能够在更高的层面和更科学的唱法中表现自己民族的音乐,也可以掌握很多国内外经典音乐作品,表现不同文化的音乐风格。学员演唱水平不断提高,风格不断拓展,自信心等综合能力都有很大的进步,歌唱事业的道路也会越走越宽。
三、结语:从少数民族声乐教学到“中国声乐”的建设
金铁霖教授从实践出发,在当今多元文化并存、多民族共同繁荣的局面中,思考少数民族声乐的教学特点,并且运用多年形成的、科学的歌唱理论体系,帮助众多少数民族歌手完善了歌唱方式,拓展了歌唱的能力,丰富了演唱的曲目。通过对个体教学的思考,金铁霖教授也逐步将目光放到声乐教学的未来发展中,并且进一步思考中国民族声乐的发展路向问题。2011年12月11日,在第五届全国民族声乐论坛上,金铁霖教授在题为《中国民族声乐发展的新阶段》的发言中提出了自己的想法。金教授首先对中国民族声乐在几十年中取得的巨大成就表示非常赞赏,但也提出自己在不断思考民族声乐的发展现状和未来。金铁霖教授认为提及民族声乐会给人一种印象,即汉族民歌。这当然无法涵盖包含着56个民族的中国音乐文化的现状。中国是世界上音乐形态最多样的国家,很多民族的音乐文化相互之间的差异非常大,不能简单一概而论。金铁霖教授在指出以往声乐观念中的一些误区之后提出“中国声乐”的概念,他认为这个命名具有更强的包容性,相对于我国目前的声乐形式而言更科学、更恰当。[8]从民族到中国,应该说是以世界的眼光、国际化交流的要求重新定义我们以往的声乐领域。由此可见“中国声乐”的提出,全面考虑了中国多民族音乐文化丰富性的特点,从更高层次着眼,体现出科学发展的眼光,具有更强的学术前瞻性。能够得到如此的见解,与金铁霖教授对少数民族声乐教学实践的不断思考是密不可分的。可以说,金教授从少数民族的声乐教学中反思了国家层面的声乐发展课题。在此基础上,当代的声乐教育者应该思考如何进一步地挖掘少数民族声乐教学的内容,如何引导中国声乐教学的进一步发展。当然,金教授也提到,女声多、男声少以及不同音域类型发展不平衡也同样是未来建设中国声乐所面临的重要课题。任何事物的发展总是生于忧患,死于安乐,问题意识是我们前进的动力。我们也希望所有中国声乐领域的同仁,精诚合作,共同面对所有学术问题,让我们的歌唱事业的道路越走越宽,让中国声乐成为世界音乐文化中瑰丽的奇葩。
注释
[1]参见金铁霖、邹爱舒:《金铁霖声乐教学艺术》,30页,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2008。
[2]参见郭建民、郭兆龙、赵世兰:《中国民族声乐教学艺术的变奏曲——王品素与金铁霖》,载《音乐生活》,2010(1),17页。
[3]参见金铁霖、邹爱舒:《金铁霖声乐教学艺术》,23页,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2008。
[4]参见宋祖英:《我对金铁霖民族声乐教学理论体系的探索与实践》,中国音乐学院博士论文,26页,2012。
[5]参见金铁霖:《中国民族声乐发展的新阶段》,《乐府新声(沈阳音乐学院学报)》,6页,2011(4)。
[6]参见杨淇:《艺术学概论》,355页,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
[7]参见宋祖英:《我对金铁霖民族声乐教学理论体系的探索与实践》,中国音乐学院博士论文,29页,2012。
[8]参见金铁霖:《中国民族声乐发展的新阶段》,载《乐府新声(沈阳音乐学院学报)》, 2011(4),7页。
,免责声明:本文仅代表文章作者的个人观点,与本站无关。其原创性、真实性以及文中陈述文字和内容未经本站证实,对本文以及其中全部或者部分内容文字的真实性、完整性和原创性本站不作任何保证或承诺,请读者仅作参考,并自行核实相关内容。文章投诉邮箱:anhduc.ph@yahoo.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