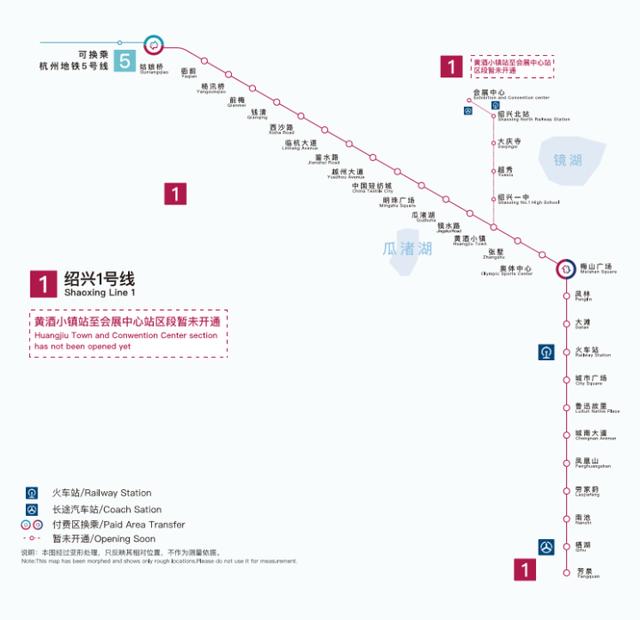老舍写的书(老舍的信)
文 | 俞竹筠

今年是老舍先生逝世56周年,我翻出2007年2月11日《扬州晚报·解密新闻》登的整版拙笔,感慨万千。作为对老舍先生的一种深切缅怀,越读越思念。在我的一生中,老舍先生对我的鼓励时时激励着我,让我刻刻铭记要做一个真正的作家,必须接地气,虽然我早已不是那个做文学梦的少年了。(《扬州晚报》记者东东当年的旁记与老舍先生公子舒乙的复信附后。)
那是1956年的暮春。杨柳依依,绿草如茵。正是南宋词人李清照所说“绿肥红瘦”的季节。一天下午,我正在教室里伏案自习,突然,有人从我身后猛拍我的肩膀,大声地说:
“喂!传达室有你的信,是老舍——写的!”
这声音犹如炸雷,惊动四邻:
“啊,什么?老舍的信?!”
“老舍怎么给他写信?”
众人议论纷纷,大家拥着我一起来到学校传达室的门前,那四面八方的各地来信都整整齐齐地竖在收发室玻璃窗前。我四下扫射,目光一下子集中在一封杏黄色的牛皮信封上,只见从右到左醒目地竖写着3行苍劲有力的钢笔字:

笔者的示意图
“寿宝”是我当时的用名,上大学后才改为俞竹筠。信封上的这19个字,珠联璧合,一看便知出自名家之手。先生落款未写地址,只书“老舍”,难怪大家那么肯定地说是老舍的信。沸沸扬扬,想保密是保不住的。我那班好管闲事的同学都急切地想看看信里老舍写了些什么,一时你争我夺,我怕将信撕破,急得直喊。
“别抢了!别抢了!噢,别拆!别拆!”
也不知道信是怎么回到我手里的。我珍惜得像护身符似的贴在胸前,仍在大家拥护下回到教室。不知谁递过来一把小刀,我小心翼翼地划开口子,抽出一张又白又薄的道林纸,不等我阅读,一些同学已凑上身来朗声念道:
寿宝同学:
来函敬悉。近因会议频繁,工作较忙,迟复颇歉!
大作阅后,已转请《北京文艺》编辑部帮助修改,不日当有回音。
您想当作家,甚慰。
一个文艺工作者要想写出点好东西,必须深入到工农兵群众中去,虚心学习,拜他们为师,要仔细观察他们的一言一行,体验他们的喜怒哀乐,与他们同呼吸,共命运。这样,才能创作出有血有肉的人物,写出群众喜闻乐见的作品。
俗说:“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只要您一步一个脚印,沿着这条路走下去,相信您的愿望一定能够实现。
上述意见,谨供参考。
顺颂
时绥
老 舍
1956年4月24日
先生的这番话,刻骨铭心,五十六年来,我时时忆起,一直没有忘记。
我自幼爱好文学,喜欢弄文吟诗,别人把写作看成负担,我却引为乐趣。当时,我还是个16岁的花季少年。我的作文常被语文教师当成范文评讲,偶尔也在《少年文艺》、《萌芽》杂志上发表点诗文,在校园里众星捧月算得上小有名气。
我这不知天多高地多厚的牛犊怎会想起和鼎鼎大名的大文豪老舍先生通起信来?
缘皆出自先生“京味”十足的不朽作品。
我自小爱读先生的小说、话剧。那《骆驼祥子》中拉了一辈子洋车的祥子;那《四世同堂》中不甘屈辱投河而死的老爷子祁天佑;那栩栩如生的程疯子、二妞子;那一幅幅波澜起伏的生活画卷常常地打动了我,我为先生高超的写作技巧拍案叫绝,曾在日记中万分激动地写道:“中国作家数老舍先生第一人!”
正是带着无比崇敬之情,我冒昧地通过《北京文艺》给老舍先生写了信,还附上一篇既非小说又非散文的习作,请这位文学泰斗指点。
想不到老舍先生毫无大作家的架子,不但给我这乳臭未干的毛孩子回了信,还认乎其真地阅读我的“大作”,并传授其创作经验。先生回信措词谦和,使用“敬悉”、“颇歉”、“您”,结尾甚至用“顺颂时绥”,实令我诚惶诚恐,汗颜不已。先生是当代名人,其时除担任北京市文联主席、《北京文艺》主编外,还兼了一大堆社会职务,工作繁忙可想而知;百忙中抽空给我这无名小辈回信,耐心地读了我那不成样子的拙文,还请《北京文艺》的编辑帮中学生修改作文,这种诚恳待人、爱护晚辈的作风是我始料未及的。老舍先生有世界一流的传世作品,他所说的创作道路上的至理名言,不单是讲给我听的,也是对爱好文学的青少年的关怀与厚望,多么可敬可爱的老舍先生,不愧是人民的艺术家。
后来,《北京文艺》的编辑真的寄回了我那篇原文,圈圈改改不知多少处,还附了一封关于修改意见的长信。我将原文重又润色一番,工工整整抄了一遍,投给《萌芽》。不久,收到编辑部录用通知,又过了一些日子,收到样刊。我一口气读完那散发着油墨香气的铅字,乐得心花怒放。我的同学亦争睹为快,抢着阅读。兴奋之余,我突然想起什么,在收到稿费后,买了几瓶黄瓜乳等“扬州酱菜”,装进木盒,寄给老舍先生品尝。谁知,先生来信批评道:
京城酱菜有买,何劳千里馈赠?你是新中国的高中生,别学那套请客送礼……
老舍先生呀老舍先生,我可没有这种想法呀!扬州酱菜,京城固然有卖,那可是我千里送鹅毛,一片心意啊!再说你和《北京文艺》的编辑为我修改文章,应该共享劳动成果嘛!我想这么说这么辩,想想还是没有这么说这么辩。文学泰斗能如此直言不讳地教诲你,你想听还听不到,想得还得不到哩!不过,先生的那封信,我再也不敢摸,再也不敢读了。一看见它,就好象做错了事似的,愧汗自责,我也羞于让别人看到,下不了面子。偷偷地藏在一边,不知所踪。又过了好些时,我忽然收到先生的回礼,那是一本奥斯特洛夫斯基著作《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仍然被那班同学抢在手中传来传去。几十年后,看过那本书的田君还记得扉页有老舍先生的题字:“赠 俞寿宝阅。老舍 57年春”。
此后,我继续给老舍先生写信,又收到过先生三封亲笔信,信中都是殷切希望我多读名著多写笔记,或是谆谆教导我集思广益,打好基础,扎扎实实地闯过语言关;还有一信是劝告我不要急于求成,文章写好后要多读,多修改,还给我讲了北宋文学家王安石对“春风又绿江南岸”的“绿”字改了又改的典故。
老舍先生的那5封信我一直珍藏在身边。58年高中毕业后,我上了南京师范学院(今南师大),大学毕业后我被分配到江苏如皋的一所乡村中学任教。时光虽一年年地流逝,环境虽一处处地变迁,但先生的信一直跟我跑东奔西。
1966年那年的冬天来得特别早,11月中旬当地就下了一场雪。本地的红卫兵也高举着“革命到底”、“造反有理”的大旗,一批批进京接受检阅,又一批批的回来煽风点火,砸烂一切。我所在的乡村不算偏僻,任教的中学也难以逃过暴风骤雨的洗礼。老舍先生与我通信的故事在当地广为流传,何以瞒得住红卫兵小将的“火眼金睛”,小将们从北京回来后对我严词训斥:
“老舍是反动学术权威,已经跳湖自杀了!你要老实交代与他的所有来往!把他的黑信交出来!”
刹时,铺天盖地的大字报从我宿舍门上一直贴到床上,就差贴在我身上。他们的小头头一次次勒令我交出老舍的信。
噢,小将们,你们不了解老舍,不知道他才是真正的爱国作家,人民艺术家!你们怎能造出这种谣言,说他自杀了呢!我不相信,不相信!我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将先生的几封信珍藏了这么多年,豁出性命也不能把信交到你们手里!
我编出种种理由,一会儿说信没了,一会儿说已经烧了,就不承认信还在我身边。小将们看我“顽固不化”,革命行动也就升级:从“闭门思过”到关进“牛棚”里。我死顶着一直不松口,巴望着暴风雨过后就可保住那些信。不料,有人告密,说在窗孔里窥视我在翻皮箱。结果,不但藏在皮箱夹层里的5封信统统被搜了出来。连那本老舍先生送的书也偷走了。小将们扭住我的双臂,一边狂呼乱叫,一边将先生的信一封封撕得漫天飞舞,那洁白的纸片随风荡漾,久久才落回地面。寒风怒号,飞雪溅泪,我声嘶力竭地抢天呼地:信哪……书哇……。
在那样扭曲人性的疯狂年代里,象我这样的无名之辈除了忍耐别无他法。我努力回忆先生每封信中的每一句话,准备有朝一日条件许可时就逐字逐句地默写出来。可惜除了第一封信外,当时我那痛苦得近乎麻木的大脑只能忆起其它4封信的只言片语了。
悠悠岁月,斗转星移。一转眼几十年过去了。1987年底,我赴京开会,在王府井新华书店里买到了《老舍之死》这本书。在这之前,我在报刊上也陆续读过许多缅怀老舍先生的文章,但一直不太清楚先生离世的具体情况。读完这本书才第一次知道,先生于1966年8月24日因不堪忍受侮辱与迫害,抱着“士可杀不可辱”的气慨,前效屈原大夫,后学祁老爷子,怀抱《骆驼祥子》手稿,一头栽进北京的太平湖……1968年诺贝尔文学奖评选,老舍先生位居5名候选人中的第一名。后来,瑞典驻中国大使馆了解到老舍死了,按诺贝尔文学奖不颁发给死者的规定,换成日本作家川端康成。中国作家难得的一次诺贝尔文学奖失之交臂,令人扼腕叹息。
老舍先生去世五十五年,我一直牢记他的教诲,按他56年4月24日给我的第一封信中的话去做,退休后,仍笔耕不辍,收获颇丰。
附旁记:昨天(2007.2.10),记者就40多年前老舍先生与高中生俞寿宝(现名俞竹筠,即《四十多年前与老舍先生的几次通信》一文作者)通信一事,向俞寿宝的高中同班同学朱庆森教授进行了采访。朱教授现为扬州大学农学院农学系博士生导师。他说,老舍先生给俞寿宝写信这件事是完全真实的。当时我们正在念高一。我们班是3班,五八届。班上有5个同学写作很好,文学水平高。除了寿宝外,还有一名姓华的同学,一名姓吴的同学,另外两人我记不清了。在他们5人中,寿宝的语文最好。老舍先生给他写的信,班上的同学也都看过。我们整个五八届都把这件事作为一件美好的事情来传颂。我们当时的班主任谈志成老师教生物,很重视这件事,把信在班上读了。 记者 东东
舒乙先生复信:
竹筠先生:收到信,两份报,谢谢!
喜读《四十多年前与老舍先生的几次通信》非常非常好,是很重要的回忆,再次谢谢您!您在文章中写得很清楚了,我没有什么问题,只是表示感谢和敬意。
祝好!
舒 乙
2007.4.13
,免责声明:本文仅代表文章作者的个人观点,与本站无关。其原创性、真实性以及文中陈述文字和内容未经本站证实,对本文以及其中全部或者部分内容文字的真实性、完整性和原创性本站不作任何保证或承诺,请读者仅作参考,并自行核实相关内容。文章投诉邮箱:anhduc.ph@yahoo.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