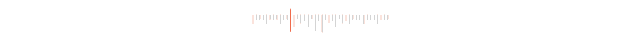硬汉演员吴京安(我是演员 不是明星)

谁是吴京安?
六月一个晴朗的下午,在西安一个酒店五楼的酒廊,老远就看见一个长得像兵马俑的大高个儿一边招手,一边喊:“你们都来了,咋不早告诉我?”。
害怕有的人听不到,他还又加大说话的分贝:“打个电话我就过来了,在这儿瞎等干什么”。
他就是吴京安。未见其人,先闻其声。
他慢慢走近,算说算笑,眼睛都快笑没了,整张脸也因此变得柔和。此刻的他,不像兵马俑了,更像是老城墙根儿下坐着的关中老头儿。
62岁的吴京安身上还有肌肉,这暗示着他应该经常健身。一米八的个头,笔直而瘦削。
破洞牛仔裤,酷跑球鞋,加上一顶白色棒帽,这些街头元素穿在他的身上,变得又潮又有态度。胸口的项链和胳膊上的手环,以及又硬又直的腰杆,显示出他的沧桑与个性。这不禁旁边的女记者满足地赞叹:比电视上还帅!
眼前这个穿衣说话都很新潮的人,全没有艺术家的那种端着的拽劲儿,你很难把他同他塑造过的角色联想在一起。

这是《初心》里的那个雄纠纠少将军野茫茫老农民甘祖昌吗?
这是《天下粮田》里为了大清国苍生的粮仓,而穷其情感殚精竭虑的刘统勋吗?
这是二十多年前,播遍了祖国大地,这两年还在不断重播的《红旗渠》里面的男主角修持的突击队长孙二旺吗?
那个拖着一条残腿,穿着一个铁靴子,在朝堂之上舌战的他。
那个面对诸多腐败大臣一个人孤单,奋力的企图,用自己的血肉之躯支撑江山的一角的他。
那个在“梅花奖”、“金鹰奖”……各大颁奖晚会上光彩夺目、一身正气的他。

和这个可爱、时尚、酷炫的他叠加在在一起。让我们一步一步走近,一点一点看清这个带着三秦大地的风、背着秦岭脊梁的西北男儿。
这是一个有着极好修养的人。自信而谦和:“我不是一个要面子的人,我可是能听进去别人意见”。
相比有礼貌,一个更准确的描述应该是,与吴京安相处,让人感到很舒服。没有人提到过他勃然大怒的样子,甚至很少说重话。然而在谈吐中,还是能捕捉到他身上深沉的文化基因。
作为演员的吴京安曾经出现在尤小刚、高希希、欧阳奋强、冯小宁、尚敬、李保平……的电视剧之中,也出现在《七七事变》、《领袖1935》这样的电影之中。这些导演包括了从第三代到第六代的所有代际,包括了电影界、电视界和话剧界;这些作品的题材纵贯古今、横跨中外,从类型片到艺术片,从正剧、喜剧到悲剧。
从领袖到农民、从军人到古人…….这些角色无论从年龄、身份、地位,还是年代、城乡、职业等等方面,都反差极大、相距甚远;但这一切并不妨碍人们迅速辨认出“吴京安”这一强大的演员主体。他的光芒足够耀眼,甚至大部分时候盖过了导演和作品本身,当然,也包括角色本身。
看吴京安所演的各种角色,你需要首先破除身份、地位、年代、城乡、职业、年龄等等所造成的表面上的藩篱,深入到骨子里、血液里,你会辨认出一个永恒不变的吴京安,正如酒永远是酒,而白开水永远是白开水。
决定这种成色的,不仅是剧本和导演,而是吴京安身上所具有的特殊的天赋,和军人气质,以及一种对角色的身体和精神深处的敏感和解放,经过吴京安个人的吸收和反射,构成了他廓鲜明的“角色光谱”。
在光谱的一端,是被黑太阳照得通体透明、顶天立地的“白嘉轩”;另一端,是历史上被认为最具争议的人物“蒋介石”……
这些形态各异的角色的人物特点,吴京安总能赋予他们恰到好处自尊和愤怒。
现在谈起演过的角色,吴京安总是眉飞色舞、神采奕奕。能感到他的内心,对“表演”是有欲望的。

双面吴京安
出生在陕西的吴京安,生活中有着西北男儿特有的生冷蹭倔,大大咧咧又真性情,跟后辈说话,从不玩假大空的那一套:“哥哥我要不说真话,我就不是吴京安”。
文娱圈资深评论人谭飞将1990年代之前的中国影视业比作“史前时代”——“银幕上全是人民艺术家,不沾一点商业性质。等到90年代初,一切才慢慢变化。
身为塑造“银幕上人民艺术家”专业户的吴京安,私下接地气程度令人惊讶。他不谈那些宏大词语,年轻时候就不谈,现在更不谈了。他投身到了时代洪流之中。他找到属于自己的角色。接受一切好的和坏的事,拥抱变化。和喜欢的人在一起工作、生活。他表示很享受。

“吴京安本来也不是什么红遍大江南北的人,走在街上没有多少人认识我,经常有人拉住我说,你是演那个谁谁谁的,叫不出来名字,现在的年代都是举头望明月,低头看手机,谁看我呢。”。
记者最初他听到吴京安本人说出这句时,浑身一激灵,居然还有人这么说自己。
有次,吴京安在同福家道的门口坐公车,要投币,他没零钱,傻里傻气的他拿着纸币就要投,被司机拦下。司机认出了他,说:“哟,吴老师,您还坐公共汽车呢?快上来,快上来!”
吴京安总算刷了次脸,享受了一次名人效应.
生活中的吴京安,是个实打实的新新人类。
买菜做饭,写诗健身喝酒。在62岁的年龄,没有什么是不能尝试的。
吴京安笔直的坐在沙发上,两个多小时的采访,他没有蜷缩过一下。这大概会让不熟悉的人觉得他不随性,实际上这只是参军留下的后遗症。他说自己:“是一个真性情的人”。
生活中简单、纯粹的吴京安,与外界想象的高傲和难接近相距甚远。他把造成误解的原因归咎于大部分人没有机会像我们这样面对面接触。
尽管如此,他也觉得没什么所谓了。活自己的,别人怎么看有什么关系。
别看吴京安说得云淡风轻。即便是现在,他也会经常沉浸在自己所饰演的角色里。“如果你将自己角色长到心里,入骨入血入魂,那就会面临两个不易,首先代入到角色中不容易,其次结束之后从角色中剥离也非易事”。
每每剧组杀青,满身疲惫的吴京安回到家,都会两眼发直的坐在客厅。叫他都都叫不应。这大概就是演员和明星的区别了。他们在画魂,明星是画皮。除了演戏他还会参与一些幕后和创作上的工作:“我虽然不是一个960万平方公里都有人认识的演员,但我一定是一个用功、用心、用情的演员。”
经典电影《海上钢琴师》中的男主角1900吹小号时说:“一个人活在这个世上,能活出一段好的故事,有倾诉的对象,那么他就是一个幸福的人”。
吴京安把这句经典台词说给了帮他装修的设计师。他说:“我未来的倾诉对象就是即将形成的水泥,钉子,砖头,木头,灯……我想让来我家的人一进来,就老知道吴京安的爱好。吴兴安的经理吴京安的性格,习惯,以及情怀”。
吴京安说到这里的时你能从他脸上捕捉到有一丝丝的得意。因为他现在拥有了这样一个空间。一个代表了生活中的空间。不是那种奢华的金光闪闪一定要有名家字画彰显品位的那种。
红五角星、皮影、陕北的炕、剪纸、七十年代的用钩针钩的沙发的,旁边摆放的是父辈的照片、一连二排排长的办公室,一样的一个军,一个小军队的一个东西,有一些弹药箱与东西……这些都是吴宅里别致的风景。
吴京安问记者:“你看,我家好玩吧?”
作为一个中年人,他活得一点也不沉重,非常鲜活。他一直保持着一种积极向上的幽默感和正能量。
他像大海里跳出来的红日,让你感到他的光芒温暖和力量。

以前是为演戏活,现在驱动吴京安的是什么?
不是那些宏大的词汇,也不是一蔬一饭,是对生活的热爱和对未知事物的好奇心,是不做就不做,做我就要把他做好的DNA,是传递幸福和快乐的多巴胺。
“不累吗”?
“累啊,累了就带家人去旅行,放松一下,停一停。电充满了,再继续出发呗”。
《白鹿原》与吴京安
2020年年初,一个短视频在全国刷屏。这个短视频就是由吴京安主演的话剧《白鹿原》选段,“子霖兄弟、子霖子兄弟,你就这样走了,走得好啊”,吴京安深情的白嘉轩的台词,眼里饱含泪水。旁边儿有人弹着琵琶、悠扬琴声加上吴京安深沉的朗诵。尽管没有舞台和背景,你依然能感受到白嘉轩在他的表演下,具有的那种非凡的激情和活力。这个视频堪称史上的经典。
时间拨回到2016年,陈忠实患舌癌去世。
白鹿原上,苍穹之下,先生的背影越走越远。
第二轮《白鹿原》话剧在人民剧院首演,逢陈忠实头七。演出前三天,公开了一张大剧照,所有演职人员转身谢幕,三鞠躬,令所有人为之动容。
肖云儒像话剧中白嘉轩的扮演者吴京安转达陈忠实的长女陈黎力对该剧的评价:“学院版的白鹿被真正读懂了原著。满满的正能量,情不自禁的让人热泪盈眶”。

《白鹿原》对吴京安来讲,意义非同小可:“我太喜欢了”。能够饰演白嘉轩,这对吴京安本人来说,也是巨大的滋养。
话剧剧本一打开,第一句:“白嘉轩引以为豪壮的是一生里娶了七房女人。”
“咣——”。
幕一黑,七个仙女披红跪在舞台上。
吴京安从原上下来一个一个拥抱她们,最后,他问:“你是”?
“我是仙草”,然后大戏开始。
一个舞蹈,用了三分钟把六个媳妇略去。剩下一个仙草跟他过日子。
话剧演完,观众们齐刷刷地喊出“吴京安”的名字。所有演员把手中的鲜花送给舞台中央的他,大幕在掌声中徐徐落下。
话剧《白鹿原》里面有一句词:“共产主义就是那只神奇的白鹿”。
这句话不是吴京安自己的杜撰。属于陈忠实小说里的东西。。是白灵和鹿兆鹏两人的对话。
吴京安把它用在戏里,用成像诗一样表达出来。
如今娱乐圈的土壤已不同于吴京安出道的年代。土壤变了就长不出一样的禾苗。当经纪公司像打造明星一样来包装新生代的演员时,吴京安还是吴京安。
不仅是因为这个人,还有这里面贯穿的态度、价值观念、理性追求、好好说话的欲望和透着的那股对艺术追求的执着劲儿。
就像五年前,他在《白鹿原》的节目单上写着的那几个字:原上的理想、青春和梦。
每当说起这些,一向乐天派的吴京安总是心情复杂。惊讶,哀伤,又隐约能感到艺术家本身的力量。
不由得想起陈忠实老师说的:“自信平生无愧事,死后方敢对青天”。
今年的春天来得很艰难,冬天赶走得不容易
——对话吴京安
每个人对社会、对病毒的思考都在情感里波动
记者:疫情期间,隔离的状态对您的生活、心境一定有很多的影响,可以跟我们分享您的心情和感悟吗?
吴京安:我应该和大家一样,疫情期间一直以家庭为“战斗堡垒”,老老实实呆在北京家里,哪儿也没去。从1月19号离开西安,到5月9号,整整4个月没出过小区门。这是4个月以来头一次坐飞机回到了故土西安,我的家乡。
我必须说,新冠肺炎给我带来的恐慌、焦虑、内心的不安是存在的,而且似乎产生了对生活前景的迷茫,不知道未来是什么样的状态。这种情况下,我能做的就是在家里待一段时间。
但等到第二阶段,看到倾全国之力奔赴湖北武汉的时候,尤其是全国的医学界、医疗界大批的90后赶去,我的心境是不同的。
还记得当时我看过一张照片,一个2岁多的孩子隔着玻璃,可能是感染了,玻璃外面有一个护士全副武装,背过身来,不忍心看孩子。那个画面对我冲击很大,顿时心里就特别不是滋味。那时候我对病毒的认识和现在我们坐在这聊天,完全是两种心态。
记者:看过您对陕西九姑娘剃发的评价,您曾说:“这些光头的女娃,是最美的星星!”当时是怎样的情绪状态,让您想要对这件事发声?
吴京安:当时看到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院九个孩子奔赴武汉之后,为了防止交叉感染以及行动方便,主动剪去了自己的美丽秀发,成光葫芦了,我当时看了照片和视频后,心深深被触动。
我是一个军人,当了40多年的兵,十八岁离开西安。我个人认为她们这种对自己青春美丽的牺牲和战场上牺牲生命是一个道理。当时我心里就有几句话特别想诵读出来,后来就创作了《九姑娘剃发上阵》,也有叫《热干面里长安辣》。
让我特别欣慰的是,2月12号左右晚上6点钟发出,40分钟后,陕西医疗队通过我的朋友找到我,在微信上和我说:“谢谢您吴老师,我们看到了眼睛湿湿的,有人惦念着我们。”
我是一个部队文艺工作者,说了几句发自内心的话,前方的医护人员有感应,我内心真的特别欣慰。这个微信留言转过来之后,我总想做点啥,老在家里光做饭、收拾屋子也不行,于是我陆陆续续读了邓康延的诗作,他曾是《凤凰周刊》、《深圳青年》的主编,做了很多文化教育上的善事,拍了很多纪录片,也是个诗人,是一位才华横溢的老兄。他写了《黄鹤楼》、《筑一道哭墙》,和我合作写了解封后的三首诗。
记者:《娃,回家咧,咥面》也达到了“现象级”的收听率,收到了很多听众的点赞、留言。您是用陕西话诵读的,大家就觉得很接地气,《娃,回家咧,咥面》的创作初衷是否跟您与西安的感情有关系?
吴京安:孩子们回家,用我们北方习俗那要“长接短送”,用面条把孩子们接回来。我母亲是烟台人,我在西安长到18岁,我每次离开西安的时候,妈妈在的话,都会包一顿饺子。我一直在琢磨第一首诵读里面最后一句,热干面里长安辣。所以我说:娃,回家咧,咥面。
等到春天疫情出现转机的时候,渐渐医疗队往回撤,看到武汉人歌颂陕西团队,用了一个词,“勤劳勇敢”。想到杜甫《兵车行》里那句“况复秦兵耐苦战。”我们三秦大地上的这支医疗队表现得那是相当英勇,和全国其他医疗队一样。
这时候我觉得我这个文艺老兵,干了一件应该干的事情。至于陕西话,其实当时,大家在表现方式上提出过各种各样的解读,但无论如何我觉得,作为三秦大地子孙后代的我,感谢这片土地,也最能用陕西话表达我的心情。
记者:您当初在朗诵《逆行者是移动的山》时,为了给主创团队传高质量的朗诵视频,听说是一家三口齐上阵,用三部手机反复录制了5个多小时,将最佳的朗诵状态呈现给天津观众。当时主办方评价说:吴京安正是全体演职人员的缩影,展现了文艺界的担当作为,让文艺真正发挥能量。这是您的初心吗?
吴京安:无论如何,在这个特殊时期,心里面肯定不是轻松的,是沉甸甸的,当听到疫情好转了之后,也不是一个简单的胜利或喜悦能表达出来的。
跟我合作《娃,回家咧,咥面》的音乐人曹阳20多岁,非常有才华,合作很多年了,刚开始我说不要配乐,他却坚持,说“吴老师,就用你《白鹿原》的音乐”。我连着读了4个晚上,录了不下12遍,我认为一个作品,无论是影视、戏剧,还是朗诵也好,它一定带有第一自我的内心表达,固然是文字表达情感,也需要表演者的动情演绎,是需要情感的。
这段文字,其实初稿时,局限于九个姑娘,后来听了建议,觉得不能只局限于个人,希望走远一点,于是有了“九只春雁、九十九只九百九”“九百九十九个大老碗,圪蹴在白鹿原”,作品里面多了深沉、沉重,多了人生不易的悲叹和悲鸣,这是需要的,尤其是在这个时候。我觉得保持自己独立的思考是最重要的。
今年的春天来得很艰难,冬天赶走得不容易,尽管大自然的花依然盛开,雪依然在下,温度渐渐回升到了春天的温暖,但是人们内心情感发生了变化。因为这场病毒,不仅是中国的敌人,也是全球人类的敌人。每个人对社会、对病毒、对未来、对当下的思考都在情感里波动。
记者:听说您有天在家中炒菜时,差点把锅铲给扔掉,因为想出一句好词。写诗对您而言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
吴京安:我是个演员,我在意每一次的情感表达,从降生的第一声啼哭,告诉世界,我来了,我饿了,我要吃,每个人都需要表达情感。
汶川大地震的时候,我和徐帆主演了一部剧叫《贫富人生》,并在中央电视台“爱让我们在一起”晚会上募款,去了不少演艺界人士。剧组也在默哀,我收工回家的路上,听到车里苏芮很老的那首《亲爱的小孩》,心里很难受,回家就写了一首诗,叫《天堂鸟》。后来北京日报见报了,我生平第一次得到了200块的文字稿费,还获得了抗震诗二等奖。北京音乐厅演出时,张家声老师疑惑真是我写的吗?他说写得不错。
我一直认为。有感而发,情感波动想表达的时候,没有舞台,你可能想把它变成文字,通过自己的声音传递给更多人。这次疫情情况更特殊,剧场艺术天塌地陷般地受到停滞,大家都不能出去,前两天高晓松搞的两场线上音乐会,我看了也很感动,大家都在尽自己的力量表达。
记者:疫情发展到如今,很多人对自己的人生有了新的规划和感悟,对于尘世的很多复杂和纠结都放下了,您呢?
吴京安:在没有出现疫苗的病毒面前,所有人无能为力。疫情改变了人们对生命的珍视程度,在生命此岸走到彼岸终结的路途中,人们发现有些东西可以扔掉了,还有些东西可能更珍惜了。对于总提的“舍得”二字,舍什么得什么,大家认识得可能更具象一些了。而且在生命的质感上,有了更清晰的方向感。
比如在我未来20年直到82岁,我绝不会只是一个演员的工作了,干点自己爱干的事,让自己心里敞亮点、能好好享受生活的事情。就像我曾诵读过的:我们就坐在鹅黄的油菜花田,把花儿一朵一朵地数,把日子一分一秒地过……
但其实,世界上没有义无反顾的事,也没有我非得如此不可的事情。是因为我们需要了,医生的医德就是救死扶伤,南丁格尔的精神在任何一个护士身上都存在。然而真到了让你往前冲的时候,这是职业带来的责任。
我挺喜欢一个人逛街买东西,但这次疫情发生,我感觉自己喜欢看的电影没了,国内外的好戏也看不成了,有时候我想到死亡、想到人类消失、想到特别具体的事,在我的生命中做不到了。我越想越恐惧,有时候吓得一晚上睡不着觉。
谁不怕死?所以有些人才伟大。在2月4号,第一批医护人员是坐着绿皮车去的,谁都不知道病毒长什么样子,不知道前景如何。所以你这个问题提得很好,人活的要快乐,但不要自私,要活得有我,也要活得无我。
记者:对您个人来说,这次疫情对您的生活是否产生了很大的冲击?
吴京安:我本来厨艺就不错,经过这三个月,厨艺又精进了。我在家里种地,种了4种,小白菜、生菜都吃了,辣椒没种出来,还有一院子的花,挺好。我就觉得你有时候要把这种不利当成有利因素来看,这次时隔这么久,再和家人一同吃饭,这对自己的思考、自己的行为、未来的选择肯定有这样那样的调整。从没有和家人在家朝夕相处这么长的时间。也有碰碗摔盆儿、鸡毛蒜皮的小争执,也有在群里晒我拿手菜梅菜扣肉的快乐,虽然后来也疲了,但这就是生活。疫情避之不及,就把它当作对日常生活的再思考吧。
我的父亲母亲:多做些陪伴不留遗憾
记者:您的家庭和您的演艺环境其实离得不近,是什么样的生活背景造就了今天的您?
吴京安:我的名字叫京安。我父母是在北京有的我,在西安糖坊街二院生的。所以我觉得想要表达对这方水土的感情,陕西方言说起来给劲儿得很。
1958年我父亲在北京基建局当局长,支援大西北时,因为是西安人,他就来到了陕西省基本经济计划建设委员会(陕计委)当主任。9月28号我生在西安,在计委那个院子里我住到了1963年,大概是5岁。我还能依稀记得小时候在院里够槐花,家里好像住了三间平房。后来父亲调到了西北建筑工程管理局(西管局)当党委书记,后来叫建工五局,现在叫陕建集团。我前段时间收拾老房子,当年周恩来下的任命书我都把它珍藏起来了。父亲1933年参加革命,是旧社会出来的高中生,他的学校在北大街十字路口西南边一个最早的市政府家属院。前十五六年那个院里有一块黑匾,像石碑一样,题着“中山中学”,父亲还带我去看过那块牌匾。
父亲后来在抗大当教员。我对父亲很崇拜,父亲幽默睿智。我小时候听他作报告,乌压压一堆人在旧祠堂里,他不拿稿子站着就滔滔不绝。他书看得多,家里一堆线装书。父亲拿给8岁的我看东汉、西汉故事,白话的《资治通鉴》,我哪里看得懂(笑)。
父亲的言行对我有影响,晚年离休,他总爱研究《人民日报》、《参考消息》,对社会问题看得非常透彻,因为有文化,思考问题很敏锐,逻辑缜密。但他从没刻意地教我说你应该怎么去做。
父亲44岁有我,我44岁,父亲离去。因在家中行五,最小,所以父亲赐我乳名“小娃” 。这一叫,便是44年,叫的我心里是满满的快乐。在父亲膝下,我永远是长不大的“娃”。镜头里露脸多了,父亲为之骄傲。他不光自己夸自己的娃,还会在晨练的革命公园,对其它的战友说:“我家小娃的戏,你们看了么”,“看了吴老,演的好”。父亲像钓鱼一样会反问:“真的好吗,我看演技不怎么样,比赵丹、兰马、崔巍差得多。”“好着哪,吴老。”“真好?”父亲会又问,“真好吴老。”父亲乐了。把跟着的姐姐笑死了,就为让别人说自己的娃演的好。从别人嘴里说出赞美的感叹!那一天他都腰杆直直的,古城墙下,走路像风,笑声朗朗一串。中午都会多饮几盅。父亲是我心中最酷的男人。我永远是父快乐的“小娃”。
我的性格像母亲。我母亲十六岁入党,1942年参加革命,母亲没读多少书,老区扫盲班识得字,在革命队伍里打仗、行军、学习,后来在陕西省建筑设计院任副院长,手下领导了一大批知识分子,他们都非常尊重她,称她为“张大姐”。母亲有人格魅力,行得正、心中有良心。
记者:3月疫情期间央视又重播了《初心》,这部剧已经被央视重播二十多次了,剧中您主演的甘祖昌,把将军与农民演得浑然天成,在您成功塑造的诸多军人角色中,有没有嫁接进去父辈留下的独特烙印?
吴京安:当时导演宋业明找到我,我说:这角色一定接。我还说:这个角色只有我来演。感谢导演让我在最想扮演一个角色的时候,没有与“甘祖昌”失之交臂,与他相遇,与他拥抱。
刚播完《初心》那几天,我的情绪依然被困在戏里,沉浸其中。因为创造这类角色的经历,对我而言也不多。在我演过的角色中,唯独这个角色是前期是雄赳赳少将军,后期是野茫茫的老农民。
小时候他常给我讲中国共产党的故事,所以与其说是我在演甘祖昌,实际上是在告慰父亲,还父亲之灵魂。父亲去世已经十多年了,我依稀记得他戎装的样子,他给我的那种感觉,甚至后来在演甘祖昌老年时戴着草帽的一些细节,也是照父亲的形象来演的。我是个军人,也是军人的后代,对军人有着深厚情结,从小对中国共产党建党史上的英雄都很崇拜,也很熟悉那些英雄的故事。
记者:听说您只要不拍戏,就会和家人在一起享受天伦之乐,对您而言,现在最重要的是家庭对吗?
吴京安:我每次从西安走的时候,永远买下午2、3点的航班,一定要在家吃完中饭再出发,而桌上也总是有一盘荠菜馅饺子。在母亲走后的一段时间,每当我吃饺子、芋头这些,我就难过。母亲生前就爱吃芋头。
我常常回忆起小时候的事,感受到的是父亲的坚韧,和母亲对孩子的爱。记得小时候母亲想我了,想把我接到身边,我清楚地记得大风雪天,我坐在卡车上,身旁是个大汽油桶,晃荡着,去合阳农场看妈妈,坐了很久很久。母亲一见到我就开始哭了,抱着一身汽油味儿的我。我那时候10岁,她40多岁。每个礼拜从干校回来,周末提着个绿饭罐,去东大街白云张饺子馆买饺子馅,回来给我们包,包好看我们吃完又走了。每次回想起来,我都真真切切感受到母爱的温暖。
我小时候会唱的第一首歌不是中国歌,是苏联红军歌曲,共青团之歌,这是妈妈经常唱的。那时候母亲很厉害,抗战时期妇救会主任。她有大海一般的胸怀,豪爽能喝酒。还很幽默,我有一次忙得三天没打电话,再打电话过去,她就说“我找报纸登寻人启事了,儿子不要妈妈了。你要再不来电话,我就满街贴寻人启事了。”
记者:您怎么看待陪伴这件事?
吴京安:母亲92岁去世。人一走,我们才会觉得做儿女的一生陪伴父母的时间太少了。我现在常和女儿说,除了必要的工作,常在家待一待。所以我现在有一个原则,只要我不拍戏,我不放弃任何一次和家人在一起相处的机会。不是说对未来悲观,只是都要走到这一步,多做些陪伴不留遗憾。
我特别庆幸自己从父母前辈学习到了一些精神,那种从共产党建党时期为践行理想淬炼而出的信念、从小耳濡目染第一代共产党人的故事,父亲和我讲瞿秋白,讲他的《多余的话》,讲述那代人的理想信念,瞿秋白是我最佩服的在共产党里的人物。而母亲给了我血统基因里的耿直豪爽。我生在这样的家庭里,我是幸福的。
我与女儿的故事:我爸很牛,炒个菜都能写出诗!
记者:听闻您的女儿在外企上班,但没人知道您是她父亲,是这样吗?
吴京安:女儿现在在外企工作挺好,单位同事也不知道她爸是谁,就算有小道消息,她也从来不理会,不暴露她爸是一个演员。
我在北京演出,她也从来不给同事去说捧场。之前她在英国南安普敦大学读了8年金融,她妈妈在她的成长中更重要,我年轻时拍戏很忙,经常没空陪她,但是她很懂事,总是向她妈夸我,“我爸很牛吧,炒个菜都能写出诗!”(笑)。
现在我住郊区,她住在上班附近,我平常对她的关心就在吃饭睡觉这些琐事上,每次她周末回家,我都会准备上一大盘红烧肉、牛肉、饺子冷冻上,让她带回去。
有件事我还挺感动的,就是我出车祸不久,她来照顾我,说:“躺在床上啥也别干,我能养活得了你”。
我以前很少过问她的工作状态,她也难得主动告诉我她的工作情况,我很欣慰她有很强的工作能力。
我女儿每天拿着ipad看书,我也很看重阅读,书是离不开的,哪怕只是一张报纸。这个时代要看要学的东西太多了,我经常有无力感,无力改变生活,改变孩子,因为她成人了,有自己的生活方式。
记者:您的孩子并没有像很多演艺同行一样,子承父业,这是您的选择还是她的选择?
吴京安:我不想让女儿走演员这条路,她在表演上其实也有天赋,前几年在公司联欢上出演了一个相声段子,我看了录像,表演松弛,声音上好。演员这一行,人们对于一夜成名这个事做的梦太多,而且觉得来的那么容易。这里面有太多偶然的因素了。所以随着我年纪渐渐大了之后,即使我演了一辈子的第一主角,也要接受一个巨大的现实,我从C位退到A位,甚至D位,但是我要看谁站在C位。
我女儿自己在国外读书的时候,最终选择了金融。我同行的孩子很多都学了传媒,干着演艺工作。我仍然为我女儿现在的选择感到非常骄傲,她在国内、在美国、澳洲、日本拿过不少奖,在北京带着一支优秀青年团队。作为下一代,我只期望她从爷爷奶奶、姥爷姥姥身上的优良品质中继承那些真诚、不骄奢、不虚伪,活得干净纯粹,保持人格的独立性。
她不趋炎附势,有时候我话说得多一点,她还批评我。这样是好的,一代人对一代的否定,这是时代往前走的一大步。她说你不该这样,我要是你我会这样做……你看,这种探讨多好。
话剧《白鹿原》是我的生命之作:我的人生底色就是对戏剧的痴迷
记者:您对学院版话剧《白鹿原》的感情极深,我们也认为这是一次极其经典的演绎,其内里究竟有何魅力?
吴京安:我只干过一次导演,就是学院版《白鹿原》。我虽然挂在第四编剧,但是我干的是导演、主演和编剧的活,挺不容易的,一个人像扛着一个演出公司,用几十年积攒下来的人脉资源带着这个戏演了70多场。走了北京、天津、南京、兰州、太原、南昌、泸州、内江、福州等。我在泸州那场演出之前,打了5个月的电话,把人家感动了。
朋友问我,你为什么对《白鹿原》那么上心,我只说一句话:“生命之作,这是我的命,我能不上心么?”我在人民剧院排演时,忙到上蹿下跳,后台光线太黑,意外摔下去了,整个皮全开了。二话没说,接着演。
第二轮在西安人民剧院头场演出,恰逢陈老师头七,演出前两天,卸完幕后,全体演员转身面向白鹿原,这时陈老师巨幅画像从天幕上缓缓落下,演出者和观众一起,向陈老师三鞠躬。台上台下,泪雨滂沱……当晚,肖云儒老师转来陈忠实老师长女陈黎丽发来了信息:“我们家五十余口人看了学院版《白鹿原》,满满的正能量,编导者真正读懂了原著,情不自禁地让人热泪盈眶……”
别人对于我演的白嘉轩的评价我就不过多说了,我觉得一部作品要给观众一些新的东西,戏剧的魅力在于创作地推陈出新,在一分一秒里不断向前滚动。
我的人生底色就是对戏剧的痴迷、对《白鹿原》的痴迷。我看国外的戏,一堆好戏,我忽然觉得我出演的《白鹿原》是那么幼稚,那么单刀直入,没有去繁就简,也没有人家多元化的内涵。
我不是导演,我站在舞台上只能演白嘉轩,什么都不用管。但当我是导演,在观众席的中间时,我要控制全场整台演出,我在侧台看别人演的戏,谁这段词演得不好,我就把我拄的拐杖扔到台上,就想指着喊:“戏怎么能这么排?”骂完我晚上再请孩子们吃宵夜,我说“孩子,你们不应该是这水平啊”!我对自己的要求也是这样,排得不好我自己下来检讨。但这个过程是快乐的,这就是剧场演出艺术的魅力,在舞台上能感受到一个演员的尊严。
记者:角色万千,为什么这么想演白嘉轩?
吴京安:这是我的土地!这是深埋着我的妈妈、我的父亲的土地……我离开西安许多年了,在外面时间越长我就越想念西安。我非常渴望演一部关中戏,最想演的角色就是白嘉轩。所以我主动要求不要任何报酬,只要让我演白嘉轩就行。能在西安用话剧的形式诠释陈忠实先生的巨著,用我自己的方式回报生我、养我的故乡,我多年的梦圆了!
就我个人而言,我对舞台、对剧中人物和土地的那份难以割舍的痴迷,除了体现在已演遍全国的《红旗谱》中,更源自一个陕西娃的乡愁。我希望在甲子之年用当年自己叩开艺术大门的形式来回报家乡。
记者:您与陈忠实老师有怎样的接触?
吴京安:我和陈忠实老师近距离接触过一次,我拍《白鹿原》的时候,陈老师已经病了。我是在一个朋友孩子的婚礼上见到他的,当时高建群、贾平凹都在,我过去敬了一杯酒,陈老还说看过我的戏。
最近疫情期间,我又在看《白鹿原》原著,爱不释手,记不清看了多少遍了。我还买了陈忠实一系列的书,都翻了看了,很多也还没琢磨透。我觉得这些作品浩瀚无比,是秦岭,是渭河,是骊山,是整个三秦大地的风雪雷雨。写得是真好。
在原上的青年依然是那么罕见地追着自己的理想,鹿兆鹏、白灵……那是怎样美妙的时刻,万家康乐、五谷丰登.....那是一段历史,孩子们到最后还是把自己的信念和肉体一起埋到了土里。
记者:您怎么看待白嘉轩?
吴京安:剧中的白嘉轩是恪守祖训的决绝之人,有着西北汉子的生冷倔,唯一的柔情给了女儿白灵。白嘉轩是一个符号,是历史老人,更是一个碑文,但我要让他喘息才能有那种原上的味道。陈忠实特别希望后人解读时能够走出他,而不是沉浸在苦闷、挣扎和绝望中。所以台词里有这样的话:要想在这原上活人,心上就得插得住一把刀。当女儿白灵死后跟父亲说:“这不是梦。”白嘉轩说道:“这咋就不是个梦呢。 ”
舞台对我而言是不离不弃的最美好空间
记者:《红旗谱》巡演那次,出了车祸,当时大家都很关心您的健康,但很快,您就又演出了,表演对您而言意味着什么?
吴京安:我出车祸之后的第一场演出,我自费买了很多票答谢老师、战友、同学、医生,因为在生死线上,大家对我都格外关心。谢幕的时候,舞台中间把我推出来,那一瞬间哗的一下掉泪了,我哭了。
所以我不会放弃舞台,坚持健身也是为了有个好体魄,舞台没有体力不行,我在演《抉择》的时候,有场大戏要把我放在两层半楼高的平台上上去,底下30多个战士在跑圈,看着晃啊。台上看的都是台下功夫,所以我会一直坚持。
我演了这么多主旋律作品,共产党、军人、农民形象都深入人心了。在和舞台导演交流时,我说特别想演理查三世、李尔王,渴望在外国戏剧文学名著里再锤炼一下自己。现在老是在原创剧本里纠缠,用在排练上的时间是说剧本时间的五分之一,还经常和编剧吵起来。
我今年计划是和北京演艺集团排一个《独自温柔》,导演说我把男主角改成陕西人了,就觉得我说陕西话有魅力、又幽默。
舞台是个什么东西呢?它需要一定的技巧,就如李玉和的词“喝了这碗酒,什么样的酒全能对付。”
记者:您说过对待观众始终要保持谦卑学习的态度,亲近人民群众,从社会各个切面演绎人生百味。您怎么看待别人对您艺术家的评价,您认为演员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
吴京安:我是在鬼门关走过一遭的人,《红旗谱》巡演车祸后,到病房看我的有卖菜的老魏,我很感动。
他过去老问我:“吴老师你还买菜呢?”
我说:“我怎么不买菜?谁说演员不买菜?我还常坐地铁去买菜,大家都举头看明月,低头看手机,没人认出我。”
我觉得这太正常不过了,普通人生活干好了,你才能在荧幕上、舞台上塑造好一个普通人,可是不敢离大众太远,不能把自己束之高阁,好像把自己放在一个所谓艺术家的阁楼里面。
近五年来,我主演了4台话剧,《红旗谱》、《白鹿原》、《天下粮田》、《抉择》。我突然又回到了起点,我是从话剧团出来的。戏剧的魅力是真刀真枪见功夫的,耍的就是演员的本体,一览无余地展示在观众跟前。
我演《红旗谱》时,有次陈道明来看戏,我也不知道。恰巧那天我在舞台演出中腿上的绑带松了,我按照经验,很自然地坐了下来,边说词边把它系好。这于剧本是小差错,但也无妨,生活的常态不就是这样吗?最高的技巧就是无技巧、了无痕迹。导演死在演员身上,演员死在角色里。演出结束,道明请吃宵夜,却提起了这事儿,他说“京安我看出来了,朱老种这个角色长在你心里了”。
为什么《权利的游戏》那么好看?我是“权游迷”,因为它不像是在演戏,像在生活,它构置出来的场景、演员的一举一动,你会觉得那么有魅力和特点。
记者:会不会出演自己并不喜爱的角色?
吴京安:这世界上工作的人70%都是在干自己不爱干的事情,多少人能在自己爱干的事情上获得一定的薪酬呢?我做演员是干着自己爱干的事,这是一种幸运。在热爱中还能养家糊口,哪里不好?不过要保持自己的独立性,要去拍自己爱的戏,有些东西是不能拍的。我有时候觉得当艺术为了生活的锅碗瓢盆创作时,出来的东西没有意义。
我不是个艺术家,我只是个演员。最好的称谓就是演员吴京安,没有那么多艺术家,我既没有艺术家的情怀,也没有艺术家的情操。我首先是一个军人,其次才是一个文艺工作者。我也演不了那些烂角色,一人千面是不可能的。
记者:近些年来,很多流量明星出炉,他们有年轻人的支持和鼓励,但也有很多被诟病的地方,比如演技、比如敬业问题等等,您怎么看待演艺圈里的这种新现象?
吴京安:其实很多青年演员的表演能力不错,他们点子多,有创意。对于青年演员是否敬业的问题上,我没有发言权,因为我没有碰到过不负责任的流量明星,可能我所在的剧团还是很严谨,不会有什么不称职的演员被选进来吧。但是对一个作品的创作态度,每个演员确实是不一样的,这不是前浪、后浪的事。我们年轻的时候,得到一个角色都是珍惜得不得了。希望青年演员们不忘初心,坚持热爱。
对陕西文化的理解:但愿那些汉唐风骨能遗存在自己身上
记者:作为乡党,您对陕西是一种怎样难以割舍的情谊?
吴京安:西安是十三朝古都,我是真心希望这座城市的每一处,不要丢了古人的气度和风范。在2000年时我曾在首都剧场出演莫言的一个小剧场话剧《霸王别姬》,我演项羽有一句台词:“秦国虽好,不是我的家,我要回江东打鱼。”我觉得一个城市里人的性格,应该有点文化的承袭,带着秦遗风骨。
陕西文人邓康延身上就有古风古韵的文人气息,作品有秦人之风,《大秦帝国》的歌词“端起关中一碗面,搅拌天下做粮仓。”写得多棒、多豪迈啊!骨子里是个爷们儿,豪爽,这就是我愿意看到的陕西人。
我在京城待了40年整,我媳妇也是陕西人。好多人打趣说我长得就像兵马俑,我也开心,我微信名就一直是“大秦老吴”,(哈哈)但愿那些汉唐风骨能遗存在自己身上。
年轻时候我到处演出,去过好多地方,保持着“愣娃精神”哪里有演出就往哪里冲,我觉得这可能也是西安人应该保有的精神风貌吧。
,
免责声明:本文仅代表文章作者的个人观点,与本站无关。其原创性、真实性以及文中陈述文字和内容未经本站证实,对本文以及其中全部或者部分内容文字的真实性、完整性和原创性本站不作任何保证或承诺,请读者仅作参考,并自行核实相关内容。文章投诉邮箱:anhduc.ph@yahoo.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