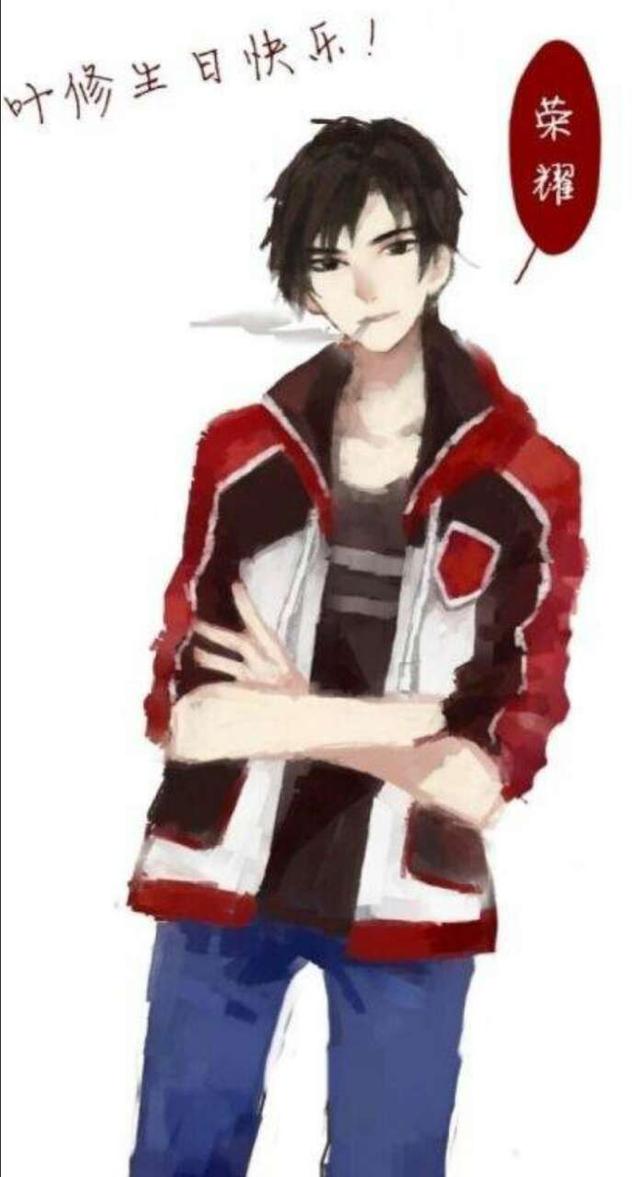傣族上海知青 知青往事傣族边寨足迹
1969年,这一年春城的暮冬初春时节似乎很长、很冷。
父母因隔离审查都不能回家。父亲被送去昭通农村劳动,母亲也被迫要求一步不能离开学校。家中只有哥哥、我和弟弟、妹妹,哥哥就成为这个家的“顶梁柱”了。哥哥默默地为出行做着准备,同时也为我准备好了被褥、蚊帐、脸盆、口缸以及打背包用的油布、背包带等物品。1月31日,哥哥出发去陇川县插队落户,是昆明市第一批上山下山的知青。

2月6日,是昆三中第二批赴陇川县插队的学生出发的日子。天还没亮我就起床了,弟弟帮着我打好背包。我背起背包、拎着衣物袋匆匆赶往学校。在迈出家门的瞬间,我突然感觉到脑子一片空白,没有了方向——我这是要去往哪里?片刻后我记起了我要去学校,只是没有和弟弟、妹妹说句道别的话,也来不及再看一眼曾经温馨的家。
我这一走,家里只有未成年的弟弟、妹妹了…!我心中呼唤着:爸爸您知道吗,您的女儿今天就要出门远行啦!我不知道您被送去昭通农村是不是也像我一样是插队落户?妈妈您也许知道我和哥哥是去陇川插队,您不能回家为我送行, 但我明白,此时您一定在为我、为哥哥、为您的学生祈祷和祝福!
来到学校,看到陆续集中的同行同学,朦胧中我仿佛意识到了什么:不管千里之外的陇川是什么样,不管未来的知青生活怎么样,我已经踏在这条路上了。
2月11日下午,经过六天的昼行夜宿,我们乘坐的解放牌大卡车抵达陇川县章凤区入境防疫检查站。按规定全部人员下车,走过浸着石灰水的通道,然后才能上车再继续前行。就在这短短几分钟时间,哥哥和他的几个同学突然出现在检查站,哥哥找到我忙说:“我在章凤区芒拉乡顺满社,已经上报了兄妹关系,你也可以来顺满……”,来不及多说我就上车了,哥哥还在后面追着喊:“章凤——芒拉——顺满……”,哥哥的突然出现让我又惊又喜,我真不知道他怎么打听到我们到达章凤检查站的时间?又在这里等了多久?当我们车队到达城子——县革委(县政府)所在地时,太阳已经落山了。按照哥哥说的,我办好了相关手续,便和我们高六八五班的同学告别,去到哥哥插队落户的芒拉乡。
芒拉乡是章凤区下辖的傣族乡,其顺满寨、芒丙寨、芒拉寨、贺门寨等村寨均分布在国境线上,有的地方,田埂就是国界。把高三的学生安置在芒拉,可能就是考虑到它地处边境的特殊地理位置吧。
顺满社是高十三班知青的一个安置点,我到时,顺满知青点什么都有了:宿舍、床铺、厨房、锅瓢碗盏、柴米油盐,我的“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知青生活也就从这里开始了。
我明白,既然是来边疆农村插队,当然干农活是“第一要务”。从第二天起,我每天按时起床,和傣族社员一起下地。
傣族社员干活时男女是分开的,这季节男社员去干砍龙竹、修建房舍等重活,女社员干的活就轻多了,比如整整沟渠,挖挖旱地等。记得在昆明期间,学校每年也都要组织我们学生到附近郊区“支农”,但那时只不过是“体验”而已,而现在却是实实在在的干活了——挣工分养活自己。好在傣族社员非常热情:傣族的农具我们不会用他们会手把手教,担子不会挑他们会边说边示范,沟渠整不好他们会再整,干一会儿就会招呼我们歇歇。
劳动过程中,我们还聊着天,他们喜欢要我们知青侃侃城里的“奇闻异事”,而我们知青则好奇于傣族的“奇风异俗”,田间时不时伴随有浅浅的笑声。很快,我就融入顺满大集体中成了其中一员了。
时下是春季,算是当地农闲时节,白天干活的时间不长,没觉得有多累,和傣族社员有说有笑也快乐着,还觉得时间挺快,只是到了晚上躺在床上,或当浓浓黑夜的异常寂静袭来让人害怕,或当晚风从竹篱笆墙的缝隙透进感觉寒冷时,就会辗转难眠甚至直到天亮。此时昆明、家人、同学……便一一跃入脑海、一幕一幕在眼前重现……。昆明啊,我生长的地方,何时再能回到你身边?
4月7日中午11点左右,我们收工回家准备吃午饭,哥哥所在班的郭班长找到我,神情紧张地说:“你哥病了,肚子疼,你赶紧去看看”!我不容分说疾步跨进男生宿舍,只见哥哥躺在床上,脸色煞白,欲说无语,那是因为疼的!
这是怎么啦?哥哥可是家里乃至他班上身体最棒的呀!我惊恐着茫然不知所措!就在床边的宰弄(傣族大哥)正为哥哥刮着痧时,哥哥的同班同学姐李(傣族都这么称呼我们)突然制止并说:“什么都不能做,什么药都不能吃,赶紧送医院”!这时大家才从慌乱中醒过神来,七手八脚把宿舍门板拆下来作担架,十多位男生顾不上吃饭,抬起担架就往章凤医院赶!
顺满离章凤十多公里,知青们一路不停在小跑,我脑子一片空白,一边哭一边和姐李紧跟其后。到达医院时,早已等候着的李医生立刻就在走道上伏下身子开始进行检查,这时我看到哥哥腹部硬得像一块铁板!“胃穿孔”!李医生说完,迅速抓起电话向县革委汇报,对方显然听不懂“胃穿孔”,李医生大喊:“就是胃上有个窟窿”!尔后无奈慢慢放下了电话,顿时,医院走道一片寂静,气氛更加紧张,所有人的眼睛都紧盯着李医生……。
李医生是“文革”中毕业于第三军医大学的高材生,和同学汪医生是夫妻。在那个年代,他俩被分配到云南,到保山,到德宏,直至到了章凤区医院,李医生外科见长,其爱人是内科医生。李医生报告的是:一昆明知青得了胃穿孔,必须马上手术治疗,按理应立即送往芒市州医院,或者陇川弄巴农场医院,然而章凤医院唯一的救护车正在昆明修理!转院不可能,病人病情越来越危急,章凤医院设备简陋,从未做过这样的手术!怎么办?只见李医生紧锁眉头思索片刻,咬了咬嘴唇后抬起头果断地说:“救人要紧,马上手术!”
顿时医院一片忙碌,术前准备紧张而有序地进行:赶紧去把在地里被监督劳动的麻醉师(原章凤医院院长)叫回;护士小王立即收拾手术室、准备手术器械,并通知知青赶紧组织献血……。就在这时,突然听到哥哥艰难断续地说:“一定…一定…不要让…同学输血……他们…路还长…长……”,我走过去靠近他耳边轻轻地说:“哥,听医生的……”。
得知要献血,远近的知青从四面八方纷纷赶到医院,几十号知青竟然只有三人是“O”型血,我也排除在外,那三名知青就在章凤街上饭馆吃点东西,等着输血。
手术在当天下午开始了。我后来才了解,像我哥的病情,若在昆明,“胃大部切除术”是首选。但当时李医生果断选择了“胃修补术”,这样手术出血会少些,时间会短些。然而,意外还是发生了——脊椎麻醉时麻醉打漏导致术中麻醉失效!“冬眠灵!”李医生指示护士,然而仅有的一支冬眠灵不能支持到手术结束。
此时,在李医生的指导下,知青们四人一组,紧紧压住哥哥的手、脚不让动弹,几分钟就得换一组人。时间仿佛凝固了!哥哥同班同学姐吴不停地念着:“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郭班长几次让我进手术室,一会儿说:“开始缝合了”,一会儿又说:“缝到最后一层了”,而我始终挪不动脚步……。
哥哥就这样坚强地、坚强地挺着,终于坚持到手术结束,回到病房了。李医生白天查房,晚上也来病房问问情况。他用两个大玻璃瓶,自制成手动“胃肠减压器”。护士小王遵医嘱,打针、送药,翻转减压器,汪医生也常到病房看望哥哥。我就一直吃住在上章凤社知青点,陪着哥哥煎熬地度过术后的护理期。
手术当天晚上,我去章凤邮局给表姐打长途电话,请她转告弟弟,寄些营养品来。当打开弟弟寄来的包裹,我又喜又惊!包裹是用竹片钉的盒子,里面装满了鸡蛋粉、猪油、腊肉等,哥哥太需要它了,但不明白弟弟又是从哪儿弄到这些的?!
哥哥得以“起死回生”,是章凤医院的李医生及汪医生、小王护士等顶着压力,担着风险,在没有输血的情况下顺利地成功完成了手术;是高十三班的同学们、上章凤寨和城子朋生寨的知青们全力以赴帮助我哥哥胜利闯过了生死难关!是他们的共同努力救回了我哥哥,为我、为我们家撑起了一片天!我永远感谢他们!
当年六月,云南省知青慰问团来到芒拉慰问时了解到哥哥的情况,经多方努力,当年七月哥哥获准回昆明接受进一步治疗。回昆后哥哥仍与那位医术精湛、以救死扶伤为己任的好医生——李书儁一直在保持着联系。现在,李医生一家都已生活在美国。
哥哥得救了,能回昆明康复疗养了。我心中的阴霾消散了,天空晴朗了,阳光又灿烂了!
1969年7、8月间,哥哥班的4位女同学带着我和另一男生的妹妹小张,还有初中的小缪一起重新组成一个清一色的女知青户,离开顺满寨转移到芒拉乡贺门寨落户。这次我们女知青转移是芒拉乡乡长贺保(傣族干部)支持下完成的。
贺保乡长比我们大几岁,早先曾到云南民族学院学习、培训,他汉话讲得好,常到知青户串门,帮助知青解决困难,他多次串门后发现像顺满这样的知青大户人数多且条件有限,确实不适合农耕生活,同意知青户调整为小户。

资料图片来源网络
贺门寨的傣族乡亲十分热情,听说知青到了纷纷出来欢迎。老社长安排我们住进了一家普通的傣家住宅(原主人离境去了缅甸),住宅包括有竹楼、堂屋、厨房、院子,几位宰弄(大哥)为我们整修住房,他们砍来大大小小的竹子加固房梁,换好房顶的茅草;又按我们汉族的习惯,将竹楼改为平房,并在房间里用竹子造出了七张床。
毕朗(大嫂)、小卜少(小姑娘)帮着从田里运来沙土,送来牛粪,毕朗挽起袖子,将沙土、牛粪用水和好,然后就将这种“建筑材料”给住房地面、厨房地面、灶台都涂上一层,毕朗指着“建筑材料”开心地告诉我们:傣族都这样做,糊上它,地面不仅易干、光滑,还防潮呢。
很快,我们的新家就建好了,还很整洁、靓丽哦。稍后,我走出房间在我们新家小院里转转时,惊喜地发现院子里有芒果、牛肚子果(菠萝蜜)、缅桃、李子、野柠檬等果树,还发现有两排(宽度约2米、高度约1.2米为“一排”)柴火,显然是贺门社傣族乡亲提前为我们准备好的,他们考虑得太周到了!
芒拉雨季5月份就已开始了。天空时时下着雨,清晨随着寨子里第一声铓锣的敲响,栽秧就拉开了序幕。傣族流传一种说法:男人不能栽秧,栽了也长不活,所以对我们女社员来说栽秧算是最苦的农活,每一块水田的秧苗都得是毕朗、女知青、小卜少们一株一株栽下去。
社里共有一百多箩田呢,一箩田即为一箩(30公斤)的种子撒下后育出的秧苗所栽的水田的面积。也许因为栽秧确实苦、确实累,栽完一块田直起腰来,回头一看还有“一眼望不到边”的水田时,总会感叹:唉,社里的水田真是太多太多了!
这个季节出工总是很早,若去远处的水田,得走半小时甚至更长时间。每天听见铓锣声,或者听见另一知青户男知青的歌声,我们就起床,每个人还要带上篾帽、披上塔衫(当地一种类似蓑衣的雨具)、穿上人字拖鞋有时甚至是赤着脚就出工栽秧去了。
其实男社员、男知青比我们更辛苦,当铓锣敲响或歌声唱起时他们就已经骑着水牛下田干活了,他们要在我们这些女社员到达之前犁好、耙好几块田。
开始下田栽秧我们都觉得很新鲜,当我们模仿毕朗他们姿势和动作把秧往下栽时,脚不知怎么移动,手不知怎么分秧,一颗颗数着秧苗往泥水里栽,那动作堪比插棍棍。看到我们手脚不知怎么协调配合、动作如此笨拙可笑,毕朗们便亲切但又略显羞怯地教我们,一边讲述栽秧的动作要领一边做出示范。
我们也一边琢磨一边模仿,很快我们也就学会了基本动作,掌握了步骤、得了要领,手也利索了,和脚的协调配合也“默契”了,没过一两天我们就能把秧栽得又快又好。到后来,我们还和毕朗们比赛,谁栽得慢,就会被“关”在水田里,每当这时大伙就会吆喝着发出阵阵笑声。
栽秧是累,但在田间吃午饭则是一大乐事。我们知青和傣族一样,每天留一人在家做饭,做好后便和一群毕朗一起送饭到田间,饭一到,社长就发令休息、吃饭。社长总能找到一块较大的地方,铺上芭蕉叶,各家把饭、菜搁在芭蕉叶上,大伙围着吃,我们把它叫“打平伙”。这时,我们不只是吃自己的黄瓜、青菜,还能吃上傣家的鱼干、牛干巴、烤肉、芭蕉、菠萝、酸笋了。每每吃着这些可口饭菜的时候,我都觉得是一种“享受”,不仅仅是肚子饿了,仿佛还有妈妈的味道……。
连续栽几天秧,我们全都真的腰酸了、腿疼了。对于没有经过这种磨练的城里女孩,傣族老社长很是心疼,也早已想好了用拔秧来为我们调节,也就是让我们知青户每天轮流一人去拔秧。
拔秧这活虽不重,但却是个技术活。要保证质量,特别要注意的是不能像割草那样把秧苗拔断,而是要把“根”留住,所以这个活儿一般是由有经验的咩巴(大妈)来干。
轮到我去拔秧的那天,心里一阵高兴,刚走到旱秧地里,咩巴们都热情地招呼我,邻居咩巴牙相劳(人名)递给我一小竹凳,让我坐在她旁边。这种小竹凳其实就是一节大的竹筒,把相对的两面削平,其中一面留一个把手。一坐下,我就动手干起来。没想到,拔下一把秧,一多半都是断根的。我不知所措,牙相劳咩巴却呵呵笑了。她没有责备,而是手把手地教我,还边说边示范,其实我没能太听懂她说什么,但看明白了。我认真学着老人家的动作,一手一手地拔,一把一把地捆,咩巴看着会心地笑着点点头表示肯定,我心里也充满了成功的喜悦!
秋天是旱季也是收获的季节,收稻子那就更快乐了。清晨,我们迎着轻轻薄薄的水雾,踏在洒满露珠的小道上,无垠的田野,翻滚着金色的波浪,满眼丰收的景象。太阳露头,微风徐徐,缭缭云雾渐渐散去,全寨男女老少怀着丰收的喜悦,开始了一天的劳作。
一到田里大家就忙着割稻子,只听见镰刀嚓嚓声此起彼伏,不一会一块块稻田的谷子就被放倒了。接近中午,太阳威力越来越大,大家都憋着劲尽量多割稻子,以便摊开在田里好在阳光强烈的时段多晒晒。不知是汗水,还是稻穗上的芒,刺得我脸上、手上、手臂上生疼,真想到树荫下躲一躲,歇一歇。但看着大伙都不停地干,我也坚持着,直到各家的饭送到田间。
午饭后稍作休息,下午的活就是捆稻子、垛稻子。傣族捆稻子不用绳子,而是用篾条。学会用篾条后,觉得跟绳子一样好用,甚至比绳子还好用。捆好的稻子必须堆垛,垛稻子很累但也很有趣。先将捆好的稻子用扁担挑到肩上,然后沿着竹梯走上去,把一捆捆稻子垛成垛。挑着担子走竹梯就像是走“独木桥”,垛堆的越高,梯子也就越陡,走上去越困难。
垛子一般有2米左右高,挑着担子走上去真有点像耍“杂技” 呢。其实这也不难,刚开始有点害怕,多练多走几次就行。我们女知青都能挑着30多公斤的稻子,一口气上到垛子最顶端。当然那个累只有自己知道。但也有好事啊,老社长会事先安排几个宰弄去地里挖地瓜“犒劳”我们,地瓜一到,大家就一哄而上抢起来,边抢边吃边说边笑,那又甜又解渴的大地瓜和那开心场景至今难忘。
年终分红,我们知青也能分到一年的口粮。社里给我们弄了个屯粮的围子,竹编的一张大篱笆,在房间中间围成一个直径约1米5,高约1米3 的围子,再用篾条固定好。这样屯粮既透风,又防鼠,还方便取用翻晒。毕朗们耐心地教我们:挑担子——不用绳子,而是用扁担每一头直接穿1个箩筐。开始挑起担子都摇摇晃晃不会走路;
碾谷子——自己把谷子挑到水碾坊,社里有专人负责把谷子碾成米;簸米——用簸箕把米糠簸出去,而米保留在簸箕里,这个技术活得学一阵呢。从栽秧→收稻谷→储存稻谷→碾成大米→做好米饭全过程真的不容易,“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啊!
顺满、贺门、芒丙等凡是我到过的寨子,不,应该说整个傣族地区,处处能感受到傣家的安详、和谐以及民风的淳朴、善良。傣族乡亲的优良品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让我明白了很多做人的道理,终身受益。
傣家寨子里,家家户户从不上锁,房门都是向外开的,只用一根一尺多长的小竹棍,在门里横置就行了,为的是防止猪、狗、鸡窜进家去。我们知青家的门当然也是这样,“入乡随俗”从未有过担心,从未感到不安全,也从未丢失过东西,真的是“夜不闭户”哦!
牛粪对傣族来说是不可或缺的。晚上烤火用它,打地、平灶台用它,驱赶蚊虫用它,听说做酸扒菜还用得着它。在寨子里,收集牛粪就是常事,谁见到谁就随手捡一小树枝或小棍插上,别人就不会去动它,谁认的谁取走。真的是“路不拾遗”哦!
寨子里的水井都有遮风避雨的顶棚,打水的竹筒是公用的,每个人取水都自觉等候,从不会发生争吵,井里的水非常干净,没有任何杂物。大家这么爱护它,水井虽历经年年岁岁,而井水始终保持着清澈、甘甜!
“入厕”对于我们知青来说是一个必须要解决的大问题,而傣族是不用厕所的,但是他们尊重知青的习惯。为建厕所,社里帮我们砍来竹子、挑来茅草。这样在我们宅院后面一个简易实用厕所建好了,大大方便了我们知青。
厕所建好了后,每天收工后我们都会给“自留地”里的茄子、辣椒、番茄、南瓜施上了有机肥。这时也在附近“自留地”干活的毕朗、宰弄们,会和我们用傣、汉夹杂的语言交流对话:“命(臭)呐,命滴滴,金豪(吃饭)不香啦”“菜哩哩(好)哦”说完都笑了,爽朗的笑声传递着对我们知青的理解和宽容。要知道,这些做法对他们是有悖民风民俗的,而他们却如此理解和宽容。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和贺门寨的乡亲越来越熟,越来越亲。白天,我们会去傣家串门,往往能吃到甜甜的芒果、牛肚子果,还有又咸又辣的李子、酸琶果。可能是没有嫁接的缘故,李子很酸,这时毕朗把李子用刀一拍,撒上盐、干辣椒拌着吃,很爽口,还可清凉解暑呢;
看毕朗织布也不失为一种享受,只要听见织机“咣——当,咣——当”的声响和织梭来回穿梭,你就能看到色彩斑斓并带有各种栩栩如生花纹图案的布就慢慢从织机里吐出来啦。早先傣家乡亲们独具特色的服饰布料基本都是由这种织布机织出的。尽管傣族现在用的布料大都可以去百货公司买到,但这种织布的传统方式还一直保留着。
小卜少也喜欢来我们知青家玩耍,听我们唱歌、聊天,谈笑风生,好不热闹。记得有一天,一位男生带着相机来了,大家决定每人照一张“傣族相”,于是小卜少们就张罗起来,跑出跑进,好不兴奋,把她们漂亮的傣族衣服找来,帮着我们穿衣,戴头饰——把一辫编好的缠着红头绳的头发辫盘在头上,让我们挑着傣族的箩筐,大家说着、笑着、闹着,一个接一个照相。从那张带着微笑的照片看自己,我已比当初来芒拉乡时明显的胖多了。
在贺门寨,我们的劳动、生活基本上就是这样周而复始近三年,由开始的迷茫不习惯到后来适应着快乐着。
1971年11月,昆明冶金机械厂到外五县招工,我也在被招收之列,这意味着我要回城了。离别之前,隔壁邻居毕朗——板(人名),专门去洋人街买了好多吃的,她要为我饯行。盛情难却,我如约去了。撒苤、烤鱼、干巴、凉粉、竹筒饭、还有我叫不出名的野菜,好不丰盛。这顿饭板自己没怎么吃,总是叫我吃,而且还非得看着我吃下去。
板的左手带有残疾,听说是生小孩时感染导致的,孩子不幸也没了,公公婆婆相继去世、丈夫也出走了。
板一生坎坷,平时话不多,却乐于助人,和她相处就像是一家人过日子:差什么针呀、线呀随时去她家拿,想吃的只要她家有了就可任意去摘;当我们需要猪油、猪肉等当地没有又不熟悉哪里能买时,她就主动不辞辛苦帮忙到缅甸洋人街那边采购。
最高兴的是过年在她家舂糍粑,她把蒸熟的糯米饭放在石臼里,我们站在大木槌的后端,有节奏地一下一下用力踩下去,她在石臼旁掌着,踩一下,她手上蘸点油翻一次,直到把每一粒米饭舂成黏黏的泥(这是技巧活,双方配合不好就会砸伤手),然后趁热捏成饼状,这时就可以吃了,或者待晾凉了再用芭蕉叶包好,以便保存一段较长时间。
就这样,我们七、八个人一起舂的舂,捏的捏,笑语喧哗,好一派过年的喜庆气氛——它赛过一桌丰盛的过年饭菜,融合傣族乡亲和我们知青的浓浓深情,让我们远在边疆的知青春节也过得有滋有味。
芒拉乡地肥水美,物产丰富,风调雨顺;傣族乡亲勤劳智慧、纯朴热情、善良好客。这块美丽富饶的土地眷顾着与她和谐相处的傣族兄弟姐妹,也眷顾着远道而来的昆明知青!当年在人生道路上失去方向、迷茫徘徊、十分无助的我有幸来到芒拉傣族村寨,来到傣族乡亲中间,平安度过了人生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

近三年的知青生活对人生而言不算长,时至今日,已经近半个世纪了,但我常常思绪飞跃、穿越时空,眼前一幕幕重现着和傣族乡亲朝夕相处的日子。我知道,那就是我对傣族乡亲的思念牵挂、不了情缘!
啊,芒拉,是你用博大的胸怀拥抱着我、呵护着我;是你用纯真的热忱、质朴的品格感染着我、温暖着我;是你用特有的聪明才智哺育着我,丰富着我......。芒拉,我的第二故乡,我的家——一个温馨、永生难忘的家!
作者:吕伟华 (本文来源知青情缘,编辑:刘乐亮)
,免责声明:本文仅代表文章作者的个人观点,与本站无关。其原创性、真实性以及文中陈述文字和内容未经本站证实,对本文以及其中全部或者部分内容文字的真实性、完整性和原创性本站不作任何保证或承诺,请读者仅作参考,并自行核实相关内容。文章投诉邮箱:anhduc.ph@yahoo.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