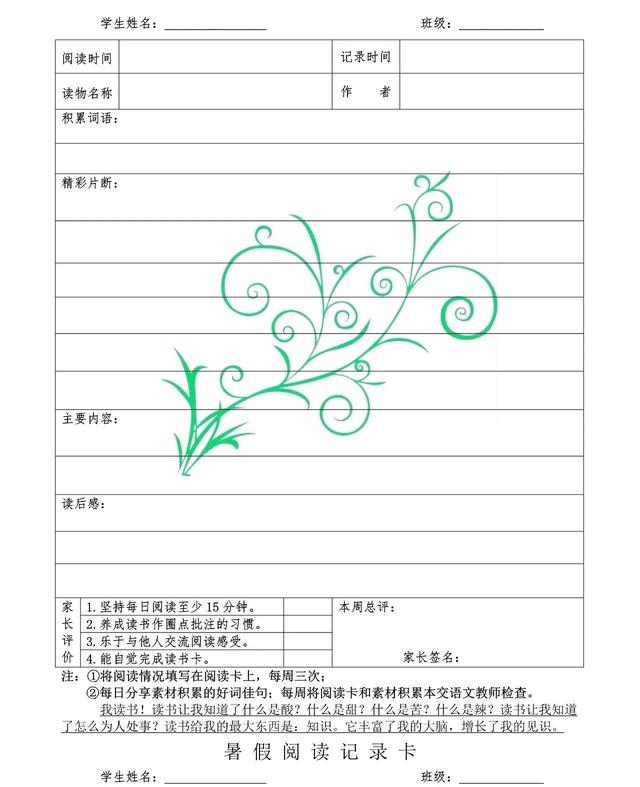俄罗斯人到底多爱读书(究竟是什么让乌克兰人不同于俄罗斯人)

《欧洲之门:乌克兰2000年史》
[美]浦洛基 著
曾毅 译
中信出版社出版
乌克兰,地处欧亚大草原西缘文明的断层线上,诞生于东方和西方相遇之处,许多个世纪以来都是通往欧洲的门户。当战争和冲突到来,关闭的欧洲之门成为阻挡东来或西来侵略者的屏障,而当欧洲之门开启,乌克兰就成为连接欧洲与亚洲、东方与西方的枢纽。
直到今日,乌克兰仍是东西方力量冲突的焦点。若不理解两千年以来塑造东欧的复杂力量,就看不清当前牵动世界的动荡。哈佛大学乌克兰研究院院长浦洛基以同情的理解,写下欧洲之门所经历、所见证的两千年,为理解东方与西方的过去、现在和未来,补足了拼图上缺失的一块。
>>书摘
将乌克兰人视为俄罗斯民族之一部分的观点可以上溯至近代俄罗斯民族孕育并诞生于“俄罗斯(而非罗斯)万城之母”基辅的起源神话。1674 年首次出版的《略要》(那部由寻求莫斯科沙皇庇护的修士们编撰的俄罗斯历史“教科书”)第一次在俄罗斯提出了这一神话,并加以传播。在帝国时代的大部分时间里,乌克兰人都被视为“小俄罗斯人”。这种视角容忍乌克兰民间文化和口头方言的存在,却不允许它成为高级文化或近代文学。1917 年革命之后,乌克兰人开始被承认为一个文化意义上(而非政治意义上)的独特民族,这对“小俄罗斯人” 视角形成了挑战。然而,2014年发生的危机却基于“俄罗斯世界”理念。对乌克兰人而言,这与苏联时代的做法相比也是一种倒退。对未来“新俄罗斯”民族建构的设想,没有在更广泛的俄罗斯民族内部为一个独立的乌克兰族群留出空间。这很难说是一种漠视或一种因战争热度导致的偏颇。

《马匹残骸前的奥列格》,维克托·瓦斯涅佐夫(Viktor Vasnetsov)作于 1899 年。诺夫哥罗德的奥列格(?-912),是古罗斯人(瓦良格人)王公,诺夫哥罗德的第二位大公,也被视为基辅的第一位大公
苏联解体以来,俄罗斯民族建构道路的重心发生了转移,转向这样一种观念:创造一个单一而非分散的俄罗斯族,并以俄语及俄罗斯文化为基础联合各东斯拉夫民族。乌克兰则成为这种模式在俄罗斯联邦以外的第一个试验场。
这种新的俄罗斯身份认同模式强调俄罗斯民族的不可分割性,与俄语和俄罗斯文化紧密相关,由此对乌克兰的民族建构事业构成了重大挑战。从19世纪诞生之初开始,乌克兰民族建构事业就将乌克兰语和乌克兰文化视为自己的核心,但它也从一开始就允许其他语言和其他文化的使用。被许多人视为乌克兰民族精神之父的塔拉斯·舍甫琴科的俄语作品即可作为这一点的例证。双语主义和多元文化主义早已成为后苏联时代乌克兰的准则,将来自不同族群和宗教背景的人纳入乌克兰民族的范畴。这对俄乌纷争的过程产生了直接的影响:与克里姆林宫所期待的不同,俄罗斯的举动未能得到俄军直接控制地区(指克里米亚和顿巴斯部分地区)之外俄罗斯族居民的支持。
根据声誉卓著的基辅社会学国际研究所提供的数据,俄罗斯族占乌克兰总人口的17%,而调查对象中仅有5%的人认为自己只是俄罗斯人,其余则认为自己既是俄罗斯人,也是乌克兰人。

《罗曼接待教皇的使臣》,尼古拉·涅夫耶夫(Nikolai Nevrev)作于 1875 年。罗曼·姆斯季斯拉维奇(约 1152—1205),加利西亚 – 沃里尼亚王公,1205 年在与波兰人的战斗中身亡。在那之前数年,继承了沃里尼亚公国的罗曼取得了邻国加利西亚的权力,成为基辅以西全部罗斯国土的统治者
乌克兰在历史中成为一个统一的国家,却又因过去的文化边界和政治边界所造成的诸多地区分界线而陷入分裂。乌克兰中部稀树草原和南部干草原之间的分界线成了北方农业地区与南方蕴含丰富矿藏的草原上各中心城市之间的一条多孔边界。东西方基督教世界的分界线在17-18世纪间推至第聂伯河,随后又后撤到加利西亚,令人回忆起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哈布斯堡帝国和俄罗斯帝国之间的国界。在从前属于哈布斯堡帝国的地区中,加利西亚有别于曾大部受匈牙利人统治的外喀尔巴阡和前摩尔达维亚公国省份布科维纳。在从前俄罗斯帝国的地盘上,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归于波兰的沃里尼亚与20世纪大部分时间里都属于苏联的波多里亚不同。此外,曾由波兰统治的第聂伯河右岸地区与曾属于哥萨克国的左岸地区之间存在差别,而哥萨克人地区与18-19世纪间俄罗斯帝国在集权化过程中所殖民的地区也有所不同。这些地区上的各种边界又共同构成日常生活中更喜欢说乌克兰语和更喜欢说俄语的人群之间的分界线。
实际上,乌克兰的地方主义比上文中的描述更为复杂。前哥萨克国占据的传统哥萨克地区和斯洛博达乌克兰之间存在着差异,而南乌克兰省份米科拉伊夫在族群构成、语言使用和投票行为等方面与克里米亚更是迥然不同。然而,尽管存在以上各种差异,乌克兰各地区彼此之间仍然紧密相连。这是因为上述诸多边界尽管在历史上曾十分清晰,却几乎不可能在今天重新建立起来。今天人们看到的是一张由各种语言、文化、经济和政治交会地区连成的网络。它将各个不同地区连缀在一起,让这个国家保持统一。在现实中很难找到一条将克里米亚同与之相邻的南乌克兰各地区分隔开来的清晰文化边界,而顿巴斯与其他东部地区之间的关系也是如此。

《卢布林联合》,扬·马泰伊科(Jan Matejko)作于 1859 年。14 世纪末,乌克兰地区被并入波兰王国和立陶宛大公国,这两个国家的双边关系开始决定乌克兰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1569 年,两国达成卢布林联合,波兰 - 立陶宛联邦由此诞生,大部分乌克兰领土被归于波兰,白俄罗斯地区则留给了立陶宛。这是近代乌克兰版图形成的开端
对俄乌冲突的这种理解深深植根于俄罗斯文化和俄罗斯知识传统当中。尽管我们很难设想一个将俄罗斯对欧洲文化的参与排除在外的近代俄罗斯历史,但同样真实的是:许多世纪以来,俄罗斯要么与西方隔绝,要么与中欧和西欧国家发生冲突。哪一套历史经验最能够定义俄罗斯与西方之间爱恨交织的关系呢?俄罗斯知识界中西化派和亲斯拉夫派之间的争论旷日持久,始于19世纪。这场争论将两种观点对立起来:一种将俄罗斯视为欧洲的一部分;另一种则视俄罗斯为一种负有世界责任的独特文明。当下,亲斯拉夫派和反西方派的继承者们在这场争论中占了上风。
对乌克兰而言,其独立主张则从来都有一种亲西方的色彩,这是乌克兰历史经验的产物:作为一个国家,乌克兰正位于东西方分界线上。这是东正教与天主教的分界线,是中欧帝国和亚欧大陆帝国的分界线,也是这些帝国的不同政治实践和社会实践之间的分界线。这种地处几大文化空间交界地带的状况让乌克兰成为一个接触区,在这里持不同信念的乌克兰人可以学会共存。这种状况也催生了各种地区分界,使之为当下冲突的参与各方所利用。乌克兰向来以其社会的文化混合性著称,近来更是因为这种混合性而备受推崇。然而,在面临一场“混合战”之际,一个民族在保持统一的前提下到底能承受多大程度的混合性?这是当下的俄乌冲突将要回答的一个重要问题。
(节选自该书《结语:历史的意义》)
作者:浦洛基
编辑:金久超
,免责声明:本文仅代表文章作者的个人观点,与本站无关。其原创性、真实性以及文中陈述文字和内容未经本站证实,对本文以及其中全部或者部分内容文字的真实性、完整性和原创性本站不作任何保证或承诺,请读者仅作参考,并自行核实相关内容。文章投诉邮箱:anhduc.ph@yahoo.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