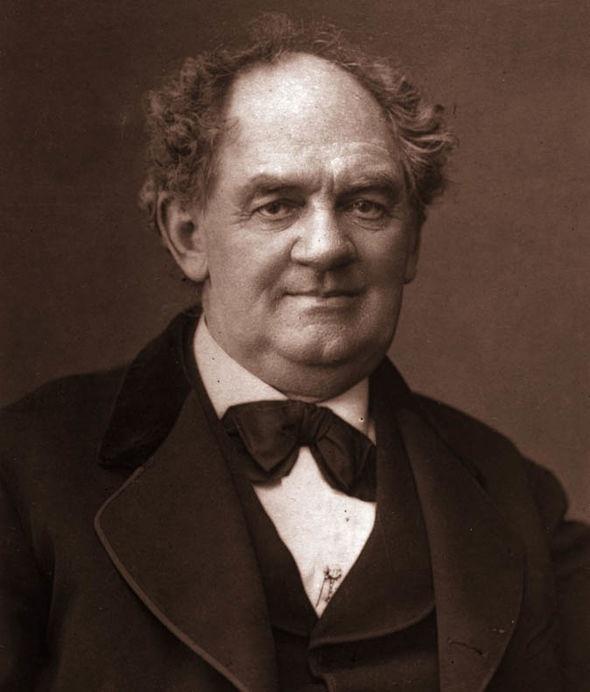我和我的家乡同时上映的电影(我和我的家乡是一部没有拍完的电影)
今年的国庆假期,颇有些把失去的年补回来的感觉,多部电影轮番上映。
不过,今年国庆档最好的电影,反而不是之前被寄予厚望的《夺冠》和《姜子牙》,而是一部有些主旋律的《我和我的家乡》,目前票房已经超过了姜子牙。

无论网络舆论,还是街头巷尾,叫好声都不绝于耳,清爽的观影体验令人禁不住点赞。
其中的独立单元《最后一课》,还顺便带火了淳安那所流光溢彩的乡村小学。

电影的主题简单而隽永,正如片名那样直白,讲的就是家乡的故事:
张北京为了给表舅治病,精心策划了一场“医保诈骗案”;为了给痴呆失忆的父亲治病,儿子伙同村里人演绎了一段历史;
黄大宝心系旧爱,谋算了一起UFO事件;第一书记马亮隐瞒妻子,虚构了一幕幕俄罗斯的景观;乔树林为了还账,一路讹言谎语却被轻易揭穿。

在这些戏剧性的主题下,农村骤然巨变的图景正在打开,这是新时代的农民,也是新时代的生活。
从内容上说,电影基本是合格的,中国人的故土情结,到这几十年中国对于乡村的建设,该说的点都说到了,中间的泪点与笑点纷至沓来。
有些不喜欢这部电影的,说它太假,是宣传,但其实,这部电影里面的几个故事,都有其现实的原型。
而且,电影因为篇幅所限,有些内容浅尝辄止。
但在现实中,这一个个故事背后是整个中国几十年建设的风风雨雨,里面有心酸,有泪水,也有欢乐。

电影最出彩的单元,莫过于《最后一课》,范师傅再次贡献了他的影帝级演技。

故事是大抵是这样的,在瑞士某大学教国画的范老师,突然患了老年痴呆,记忆停留在了92年,要想帮助他恢复,就必须回到当年的场景。
老范当年是乡村支教教师,于是,儿子赶紧带老范回国,回到当初去支教的那个村子,希望村民们帮帮他。

可如今的村落已经是天翻地覆,早不是过去那番破落模样,怎么办呢?
好心的村民们决定给范老师演一出戏,帮他恢复记忆。
村支书把村民召集到一起,找到一所茅草屋,当做当年的教室,请一群小朋友,扮演92年的学生。
范老师站上讲台,镜头移到过去,那时,有个小朋友喜欢画画,可没有颜料,范老师就冒着大雨从老远揣着颜料给他带回来。

小朋友画的是一所五彩斑斓的学校,没想到,很多年后,范老师真的看到了这所学校,记忆闪电般回来。
这段最亮眼的《最后一课》,取材自真实经历,范老师的现实原型是方老师。

1988年8月,方老师调到了淳安的枫树岭乡中心小学。
这个乡村在崇山峻岭之中,所以一直以来的建设就相对较为缓慢,哪怕是92年,很多乡村的基础设施还是跟不上时代,晚上野猪来拱门,睡觉老鼠从脸上掠过,方老师的支教经历比电影更离奇。
大山里的很多孩子,父母外出打工,留守儿童日子苦,病了要垫付医药费,开学要垫付学杂费,有的还要给学生补贴伙食费,晚上想爹妈的孩子,方老师还要抱着哄着睡。

后来,方老师辛苦教育的这批孩子,都长大成材,走上了不同岗位,他们中有校长,有村支书,有企业老板,有干部,有军人。
很多人不理解,为什么电影里都92年了,乡村看上去还像是五六十年代的?
这就得说道这个故事背后的淳安县了。
在五十年代,淳安县发生了一件影响当地所有人命运的大事。
彼时,中国刚刚解放,河山一片狼藉,工业基础基本为零,国家领导人眉头紧锁。
尤其是电力,作为工业最发达的城市,上海的全部电力仅有30万千瓦,而整个浙江,竟然才4.1万千瓦。
1956年,新安江水电站被列入了国家“一五”计划。如果水电站上马,每年能平均发电18亿度,相当于当时14个浙江省的发电容量。

但这里建水库的最大难题,不是技术,是移民,蓄水会让水位上涨,原来居住在这里的居民就需要搬走了。
1954年5月24日上午,新中国第一大水利工程的移民拉开了序幕。
几十万淳安人,浩浩荡荡出走,他们经历了外迁,回流,再外迁,或有序或无序,前前后后进行了十六年。
在《国家特别行动:新安江大移民——迟到五十年的报告》一书里,作者童禅福记下了这段沉痛的历史。
1959年4月15日,这一天,童禅福所在的全村人必须全部移走,不该带的东西都不要带。
移民搬迁叫“洗脚上船”,如同行军,因为他们要像战士一样带上被褥衣服就走。

新安江上一千多只木船白帆飘动,公路上移民大篷车穿梭往来,携儿带女、肩挑背扛的移民们,来去匆匆。
水库原计划1960年截流蓄水,1961年发电,施工期限5年。
当时,美国普列斯托滩水电站也在修建,中国人正提出和美国比速度,需要划提前20个月发电。这样一来,已经无序的移民工作更加雪上加霜。
而且,这批人正赶上大跃进和三年困难时期,有些安置工作地方政府做得也很差。
1959年,有的移民对安置地不满意,也有被血吸虫吓坏了了,偷偷回到淳安,掀起了一波回流浪潮。

到1967年,回去的人有两万人,他们在水库周围搭起了茅棚,到了晚上,星星点点的土油灯和煤油灯布满了水库四周。
不愿意搬迁的村民,水位一上涨,就往山上搬,搬家没几日,水又涨上来了,再往更高的地方搬,这山搬那山,一年搬好几次。
他们住窝棚,种非法地,没有一分钱移民费,最后沦为“黑户口”。
这种来回倒腾造成了不少悲剧。

童禅福还在大学读书,家人却跟着乡里乡亲搬迁到江西。
第二年,母亲因为肝硬化去世了,不料61天以后,父亲被吸血虫折磨,也撒手人寰。
移民们的家搬了一次又一次,大多去了江西,有的甚至去了新疆石河子。
少小离家老大回,日久他乡即故乡。很多人自那次离别后,再回去时,已是白发苍苍。
童禅福去调查的时候,遇到的移民几乎都说:“我们不怪政府,只怪自己遇上的时代不好,移民高潮时正碰上大跃进,而后又连着三年困难时期。”

可他们为国家做出的牺牲,国家没有忘记。
假如没有当初的移民,中国就没有一个重要的大坝,华东工业就没有充足的电力,生产不出供应全国的生活必需品,中国现代工业的起步也无从谈起。
或者更确切点说,在整个新中国的工业化进程中,没有帝国主义靠侵略掠夺来的原始积累,我们只能从自己的牙缝里省一点扣一点,那一代每一个中国人,都为新中国的工业化做出了巨大的牺牲。
所以到了新时期,针对性的扶贫工作要坚持做到底。
人民牺牲自己换来的中国的工业化,现在必须反过来造福人民的生活。
经过多年的扶贫,淳安终于否极泰来,曾经的新安江水库,如今摇身一变成为了“天下第一秀水”,成了最时髦的旅游景区。
一栋栋高楼拔地而起,湖光山色映入眼帘,千岛湖的令人心驰神往,引得游客纷纷打卡驻足。

电影中那座小学是真实存在的,名字叫富文乡中心小学。
青山翠谷,丛林掩映间,有一座糖果色的小城堡,层层叠叠,绚烂夺目,是孩子们梦幻之地。

现在,全国有43.5万名优秀干部,到贫困村和基层党组织薄弱涣散村担任第一书记,有277.8万名干部驻村帮扶。
湖南十八洞村,扶贫工作队一山一水勘实地、挨家挨户访实情,引导年轻人搞乡村旅游、中老年人养牛羊、留守妇女做传统苗绣、村集体成立矿泉水厂……短短几年,昔日苗寨旧貌换了新颜。

贵州南部的罗甸,年平均气温接近20℃,是得天独厚的“天然温室”。依托自身独特的资源禀赋,主攻菜、果、药等优势产业,从贫困山区变成生态示范基地.
过去的山区,往往能看到这样的情景,夫妻俩耕种两亩地勉强维持生活,家里儿女上学往返要翻山越岭几个小时。
要知道,七年前的2013年初,中国还有一亿两千多万贫困人口。
到今天,已所剩无几。
周恩来总理当初在视察新安江水库的时候,亲眼见识过不少人吃的苦,受的委屈,周总理曾对他们说过:你们付出了很多,国家不会忘记你们的。
这个承诺,中国做到了。

葛优演的《北京好人》故事,是另一个比较出彩的小故事。
故事里淳朴而不善言辞的二舅,是过去漂流于医保体系之外中国普通农民的缩影。
张大爷(葛优饰)给表舅冒用医保卡引发的笑料堪称全场最佳,但欢乐背后的时代悲剧色彩也最为浓烈。

试想,如果没有张大爷这个热心肠的北京亲戚一顿折腾,没有钱就不看病的老农民表舅,是不是就在甲状腺癌带来的呼吸、吞咽痛苦中继续煎熬下去,不敢去做手术,而完全没意识到自己也能享受医保报销?
其实在新农合政策刚刚推出的时候,比起不知道政策的表舅,很多贫困地区的农民即便知道政策,也抱之以不信任态度,需要村干部进行不断开导,才在疑虑中参保。有些甚至是在罹患癌症之后,才对拒缴医保后悔不迭。
不知道,不信任,不会用,新农合普及推广中的种种问题,的的确确是过去医疗保障缺位造成的意识真空。
为什么?
因为我们新中国的农村医保体系,在开局很不错的情况下,中间却走过一段时间的弯路,一度甚至到了快让人失去信任的地步。

建国之初,中国积贫积弱,连吃饱都成问题,农村更是缺医少药得厉害。医疗资源实在欠缺,新中国只能就地取材,在农村培训了一大批基层医疗人员——赤脚医生。
尽管医术落后、药材稀缺、报酬微薄,但这是中国农民几千年来头一次享受到了国家制度层面的医疗保障。
1968年,当时中国最具影响力的《红旗》杂志发表了一篇《从“赤脚医生”的成长看医学教育革命的方向》,介绍了上海市川沙县江镇公社的全国首位赤脚女医生王桂珍的事迹。

随着《人民日报》、《文汇报》等各大报纸的纷纷转载,连毛主席也在文在眉头上批示:赤脚医生就是好!
之后便有了“要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六二六”讲话指示。

于是,全国大队 (村)一级正式设立了“赤脚医生”,赤脚医生人数最高到了150万 ,正式建立起了农村合作医疗制度。
农民每人每年交一元钱,每次五分钱挂号费,就能得到基本医疗,被世界卫生组织誉为“发展中国家解决卫生经费的问题的唯一范例”。
赤脚医生们上午参加生产队劳动,下午才在合作医疗工作,不给薪酬,只记工分,相当于半个农民。
在宣传画里,赤脚医生的形象干脆就是一手扛着锄头、一手背着卫生箱,以半农半医的方式奔波于田间地头。

诚然,以现代医学标准,没有系统性训练的“赤脚医生”很难称得上合格。
但那时候的“赤脚医生”还是完成了足以名垂青史的两大成就:
大大降低了中国各种传染病特别是血吸虫病的感染率。
大大减少了婴儿和孕产妇的死亡率。

但同时,问题也不少。
由于缺乏全面的医学知识与相应的检测设备,赤脚医生们对大病、重病大多数时候只能建议转院,能治疗的主要是一些头疼脑热、跌打损伤、接生、包扎等紧急医疗救助什么的。
药品更是缺,往往是自己采挖、播种的草药外加少量的西药,有时候甚至是靠“一根银针治百病”。
当时整个国家资源都有限,为了提升医疗水平,国家想了很多办法。
1969年,上海中医学院、浙江中医院等集体编著了《赤脚医生手册》,将精深奥妙的医学知识化繁为简,从感冒咳嗽到心血管、血吸虫,浅显直白地向所有农村普及了99%常见病的中西医诊断治疗方法,至少挽救了上亿农民的性命,被译成了多国文字,至今仍旧在一些落后国家发挥着重要作用。

国家在努力,一边种地一边看病的赤脚医生们也没有闲着。
1974年9月,来自辽宁开原县的一位大队(村)赤脚医生牟浩就给《新医学》杂志写读者信,希望经常刊登“赤脚医生病例讨论”,从而在缺医少药、资料不全的情况下进行更好的自学与交流机会,尽可能地提高医术。

但赤脚医生的合作医疗制度建立在农村公社制度上,改革开放之后,医疗市场化改革却再也没有了赤脚医生的位置了。
原本属于其职责范围内的计划免疫、爱国卫生、改水改厕等基层卫生医疗网络也因此土崩瓦解。
"中国赤脚医生之父"、1966年第一个搞农村合作医疗的湖北长阳人覃祥官,曾经管理了500亩草药田。
在70年代末,由于集体土地包产到户,药田也被分走,药也很快被刨光改种了粮食。

一位领导还对他当面嘲讽道:老覃啊,我看你的“农村合作医疗”也是个极左的东西,要批判!
不去考虑实际情况,只看左和右,在一厢情愿下,从此医疗问题被架上了市场化的快车道,在金钱迷雾中磕磕绊绊地摸索前行。
面对动辄数万、数十万的医疗费用,多年来,中国农民们唯一的指望就是凑钱看病,借遍了亲戚邻里借不到,就只能静静地看着病魔一点点蚕食自己的身体与家庭的幸福。
过去几十年,太多太多的因癌症家困人亡的悲剧,让整整一代遭遇病魔的农民陷入孤立无援,以至于被逼得铤而走险(比如影片中的冒用医保卡以及《我不是药神》中的买走私药),甚至动摇了大家对医保制度的信心。

《北京好人》故事最后,表舅的医保卡被亮出,一切辛酸一扫而空,只剩下这爷俩的调侃和搞笑。
那是因为交够了学费之后,国家又重新花大力气整治,把我们丢失的东西捡了回来。
2009年以来,中央财政投入600多亿元,支持4万多个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建设和化解历史债务。
这条路还没有完全走通,还在路上,但我们希望的是,“病不要命钱要命”的喊声,能随着时间的流逝越来越少。千万个家庭不再会因一场疾病而支离破碎,也不因几万块钱而重回贫穷。
3《回乡之路》这个故事里,邓超主演的乔树林费尽心思、厚着脸皮也要黏着带货直播网红同学,希望她推销自己的沙地苹果,为的就是实现当年老师留下的治沙遗愿。
如果说医改走了一段时间的弯路,那么在治沙这个千年工程上,国家一直坚定地走在了正确的道路上。

剧情细节这里就不剧透了,但这里要重点说的是,虽然《回乡之路》写的主要是两个已经开创事业的成功(破产)商人回馈故乡的故事,但在故事结局时,大屏幕上出现了治沙英雄和团体,在一闪而过的镜头里,女子民兵治沙连显得尤为特别。
而这里的民兵治沙,是治沙过程中的绝对主力,背景就在毛乌素沙漠。
毛乌素沙漠横跨陕蒙宁,总面积约4.22万平方公里,是中国四大沙地之一,也是京津地区重要的风沙源。
上世纪50年代统计,榆林流沙高达860万亩,林木覆盖率仅为0.9%,年入黄河沙量为5.13亿吨。
过去,位于毛乌素沙地的陕西榆林风沙肆虐、草木不生、颗粒无收,当地人民群众生活艰难,纷纷远走他乡,连榆林城都曾被迫三次南迁。

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以“植树造林,绿化祖国”为口号,大规模的生态治理在这里展开。
当地领导人喊出了“榆林不治沙,不造林,就到不了共产主义”的口号,实行“国造国有,社造社有,房屋前后归个人”的政策,并且各级地方政府带头冲在治沙第一线,竭尽全力调动人们的治沙热情。
1974年,54位只有18岁的女子民兵积极响应“植树造林,绿化祖国”的号召,成立了女子治沙连,在榆林补浪河一驻扎就是四十五年。


沙漠生活本来就极其艰苦,更何况她们的目的是与沙漠对着干。
当地一种植物叫牛腥秧子草,会快速腐蚀皮肤。由于缺医少药,一旦感染,这些年轻的姑娘就按照当地土方,用自己尿下来的尿去洗手消毒,才治好溃烂的手。
第一代队员席永翠在日记里写道:
“黄风呼呼不见天,黄沙漫漫不见边,从小没有离开过爹妈的小女子们,心里越发慌的住不下,想家哭鼻子,吃,没有副食,每天白开水,高粱加青稞面馍。”
治沙连有一个规矩,只要结婚了就可以离开,但席永翠偏偏为此三次推迟了婚期。
如今治沙连第14任连长席彩娥,是席永翠的侄孙女。一代代女兵坚守沙地,一代代下来累计治理了14000多亩荒漠,才有了今天毛乌素沙漠的绿翠成荫。


改革开放后,这种政策进一步进化为承包制,进一步明确了责任与权利,实现了谁治理、谁受益,多治理多受益,鼓励科技人员搞治沙技术开发、进行沙地综合利用。
结果是治沙和扶贫搞到了一起,一口气把两个问题都解决了。
1984年初,国家鼓励个人承包治沙,住在陕西省榆林市靖边县东坑镇毛团村的郭成旺就是其中之一。
回忆当年,对于治沙的初衷,他提到了一个最最简单的需求:没柴烧饭。
“当时我们那里谁家都没有柴,也没有树,做饭烧柴就成了当地人生活中最大的困难。”

承包一万亩沙地后,最大的问题是如何把每天把几百株树苗运进沙地深处。
由于当时没通公路,郭成旺就把之前栽下的沙柳枝砍下来,当柴火发给村民们当工资,让他们帮忙运树、种树。
一直持续到90年代,随着树林增多,当地人做饭才不愁柴火。
2010年,通往沙地公路开通,彻底终结了人工搬树苗的历史,成为了毛乌素治沙的阶段性成功之年。

如今,郭成旺家养了20头奶牛、150只山羊。再加上国家拨付的公益林生态补偿金,全家一年收入也翻了几番,没有造好的树木资源,这些都是养不起来的。
在电影里,我们看到了个人的治沙奋斗,看到了个人意志的坚持,但其实,人类面对恶劣的自然环境,第一个想法就是迁徙,这是千百年来共同的生活方式,也是最市场化的方法。
面对几乎不可能逆转的荒漠化,如果没有中国一代代治沙人逆天而行,以革命般的热诚,用肉身顶在沙暴,治沙扶贫绝对不会成功。
这一代代治沙人,才是真正的英雄。

在故事《神笔马亮》里,提到了一个地方,列宾美术学院。
列宾是巡回展览画派的旗帜,是批判现实主义的泰斗,他画《伏尔加河上的纤夫》,他画《查波罗什人复信土耳其苏丹》,都在尽情描述劳动人民的力量和革命者的不屈斗争。

新中国70年的故事也是这样,靠自己的双手,一步步实现愿望,最开始是“站起来”,后来是“吃得饱”,再后来是“能说话”。
在波澜壮阔的这70年里,新中国的这些故事从来都是传奇而浪漫的,只是此前很少有人把他们搬上银幕而已。
我们告别了吸血虫,借问瘟君欲何往,纸船明烛照天烧;我们告别了黄沙万里,新栽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渡玉关 ;我们告别了千沟万壑,万里神州,天堑变通途。
《我和我的家乡》虽然还有不少问题,有一些像是为了完成任务的生硬的部分,但总算是把“讲好中国故事”开了一个头,虽然离“讲得精彩”还有很远的距离,但比起有高超的技术却讲了一个外国故事内核的电影来说,这部电影显然更容易打动观众。
中国的艺术也应该这样,不要虚头巴脑,不要白左横行,该热烈就热烈,该浪漫就浪漫,该悲怆就悲怆。
你可以写实,也可以写意,但它的主体一定属于劳动人民的,是有时代风貌的,是过去与现在一脉相承的。
人民为了一个宏大的愿景,吃得苦,耐得劳,“唤醒了沉睡的高山,让那河流改变了模样。”
这就是属于中国人民的传奇。
,免责声明:本文仅代表文章作者的个人观点,与本站无关。其原创性、真实性以及文中陈述文字和内容未经本站证实,对本文以及其中全部或者部分内容文字的真实性、完整性和原创性本站不作任何保证或承诺,请读者仅作参考,并自行核实相关内容。文章投诉邮箱:anhduc.ph@yahoo.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