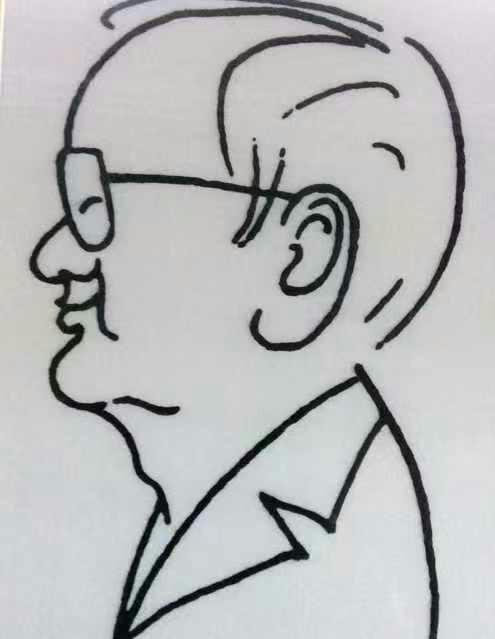再探牛岭村领略不一样的岭南故事(本土原创华安骡仔岭)
说起“骡仔岭”,在下田,在古时的华丰(茶烘)、仙都(宜招)、安溪一带是颇有名气的不少70岁以上者及其上辈,都曾在此来来往往过,“骡仔岭”承载着他们许多难忘的记忆,我来为大家科普一下关于再探牛岭村领略不一样的岭南故事?以下内容希望对你有帮助!

再探牛岭村领略不一样的岭南故事
说起“骡仔岭”,在下田,在古时的华丰(茶烘)、仙都(宜招)、安溪一带是颇有名气的。不少70岁以上者及其上辈,都曾在此来来往往过,“骡仔岭”承载着他们许多难忘的记忆。
岁月荏苒。如今,“骡仔岭”的故事,只能在《志》书、在民间口传中略知一二。
一、古道上的“骡仔岭”
“骡仔岭”的闽南话叫法音相同,在书写时有“李仔岭”、“离仔岭”、“吕仔岭”、“锣仔岭”等之异,但意思一样,既是指一段山路名,又是指一个自然村名。
其实,“骡仔岭”还是古时古道上的一段路名,这在民间,几乎没人了解,笔者亦然。
公元2010年5月的一天,笔者于厦门图书馆查阅漳州史籍,在翻阅《漳州市志》时,无意中在第333页读到一段文字:
“清乾隆巜漳州府志》载:‘揭鸿岭(汉称葵岗岭,今为金沙岭),去城西北四十里。汉唐时,西北向长安故道,由安溪大田以行’。”又称“揭鸿岭古道”。
此道的路线及路况,同一页中作了如下注明。
路况:该古道沿途崇山峻岭,人烟稀少,为中原地区通达漳州的捿径,是唐代漳州朝京孔道……。在漳州境内180多里。
路线走向:从古漳州城北门出发,旱路经乌石(今石亭),逾揭鸿岭,至华安汰内,路沿北溪上溯,至新圩岭兜,爬九龙岭扺华丰;再由华丰越"骡仔岭",向安溪、大田北行,经沙村(今沙县),抵延平(今南平)与中原入闽大路衔接。至长安(今西安)。
这段记载,不仅明确的告诉世人,“骡仔岭”是“揭鸿岭”古道上的一段路名,历史悠久;而且标准称呼是"骡"仔岭而非其它,这也让民间知道了另一含义的“骡仔岭”。
至于为何是骡子的“骡”呢?是否如民间传的,古时此段山路,有“骡子”队帮人驮货物过大岭因而得名。仅是口传,无证可考。
该古道在华安境内120多里,其中在下田境内约15里,即,从现在“石门坑”社对面山的山下,上“骡仔岭”,越烘炉格,下烘炉岭,穿小官田大路脚后山横路,过官田格,再下“罗房”大岭。
值得一提是,清乾隆朝,良村有一支黄氏迁徙江西上饶广丰,走的就是这条古道。
二、年代久远的“骡仔岭”
山川本无名,是人类的活动才赋予或雅或俗之名。那么,这个“骡仔岭”是在什么年代开始叫起呢? 这不是一言两语能说清楚的。
如果据史载解读,“骡仔岭”出现远早于下田开埠,而且距今太遥远了。至于具体哪个年代出现,真不好确定。
“府志”载:它曾是“汉唐漳州进京孔道”。那,汉朝末年是公元220年,而唐朝元年是公元618年,折中计算,距今有1500年以上了。那时,不用说下田,就连漳州最早的县置龙溪县都没出现呢。
从另一史料也可佐证,古道名远早于自然村名。谱籍载,汉族人大规模迁徙华安,大都始于明朝初期。所以,华安县潭口之内(旧称“潭内”),现在所能见到的各姓族谱,始祖大都是源于明洪武的不同年份。良村黄氏始于明洪武二十三年公元1390年。当然,之前华安境内也有人类居住活动,极少,是闽越族人,部分少数民族族群。
所以,有证据表明,“骡仔岭”并非是有人迁徙此地定居后,给起的地名。
那么,会不会是古道上的“驿”或“铺”之名呢?
据史载,古代中国的交通,都是各种古道。其中,把连通帝都“长安”的古道称为“孔道”,相当于今天讲的国道。
早在秦、汉之际,古道上供人歇脚之地称为“亭”,“亭者,停也”。还有“长亭”、“短亭”之分,依距离长短而定,“长亭”设有“亭长” 。史载,汉高祖刘邦在未起事前,曾是一位“亭长”。
唐代,在孔道沿线,每隔几十里设驿,旧称“驿站”,供公职人员休息或换马之用。有没有一种可能,唐代时期,“骤仔岭”作为孔道必经之段,是否是个“驿站”由官方命名的呢?这尚未查到史据文字佐证,只是一种假设。
到了宋朝,经济繁荣,富甲世界。朝庭诏令,把古道上的“驿站”改为“铺”或“庵”。史载:“随铺立庵,命僧主之,以待过客”。规定,30华里设一“铺或庵”,并配有专人管“铺”,将以前专为公职人员服务的“驿站”,改成为所有来往行人提供服务,这利民之举深受欢迎并得到执行。到明隆庆元年公元1567年,漳州境内置91个铺,布局更为合理。
那,会不会是孔道上的一个“铺”或“庵”,由当时地方政府命名“骡仔岭”作为地理符号呢?
这也仅仅是据史的推测。
所以,“骡仔岭”的名称是在什么年代正式出现,尚无定论,但其历史悠久,远早于下田开埠是肯定的。尽管如此,“骡仔岭”成为“揭鸿岭”古道上一段的地理符号,载入史籍,则是有据可查的。
三、明、清时期的"骡仔岭
古道越千年。历史上的“骡仔岭”,曾经人来人往,人挑肩扛,货物通达。现只能在史籍里和民间口传中,追寻古道上曾有过的生机与繁忙。
据万历《漳州府志》、《闽南史》载,明隆庆元年公元1567年始,朝庭解除禁海令。仅用十年时间,漳州实际上掌控了当时全国对外贸易,漳州月港成为全国海上贸易中心,因而也成为海外商品输入中国的中心。
为加强朝庭的管控,在明万历四年公元1576年,朝庭在漳州府专设“盐运同知”一职,驻扎于漳州北溪柳江营(江东桥),正五品,知府的副手。专掌地方盐、粮、河工、水利等事务,换言之,专管江河运输。
当时漳州成为全国最富裕地区,漳州城也以富裕文明之名,誉满全国。这一盛况,延续了近百年。其繁荣辐射到漳州周边地区,可以想象,当时漳州河道运输之繁忙,于是,特设专职伺之。
到了清朝,漳州月港衰退,式微。但由于清朝是全国人口爆增时期,全国从上一亿到突破四亿人口,均在清朝。随人口快速增长,货物需求量猛增,给各地运输带来源源不断的货物。
当时,北溪是连接华安、漳平、龙岩、安溪等地区的主要物资通道。
据民间传说,那时九龙江上,舟楫穿流不息,水路运输繁忙。各种物资从月港溯北溪而上,抵达华安新圩岭兜码头,卸货后走陆路,经古道、山路,运往各地,“骡仔岭”成为历史上最有生机也最繁忙的路段,一年四季,挑夫们三五成群,穿梭于“骡仔岭”。
尤为秋冬两季,该路段日夜都有络绎不绝的挑夫队伍经过。夜,来自各地挑夫,各自举着火把,担着木炭、瓷器等等大宗山货赶往码头装船,再挑回食盐、布匹等各种生活必需品。正因为此,全长约6里的“骡仔岭”路段,历史上曾建有三座凉亭,分别是山脚下的“大凉亭”,中段的“观音亭”,接近山顶上的“中凉亭”。均为土木建筑。
“大凉亭”近40平米,含左右各一间歇息房。大亭的大房间有专人设铺,供应粥饭,为过往行人提供方便。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国家建设需大量木炭,此亭曾住过一支烧炭队伍,有近30人。
“观音亭”在骡仔岭段中间,不足8平米,摆有观音雕像和简易供桌。据传,当时此路段常有虎祸,偶尔也有匪患。商人们担心货物遭袭受损,募捐筑之,以求平安。
“中凉亭”已经接近岭顶,有10平米左右,处在骡仔岭自然村与烘炉格之间,专供行人歇息擦汗换衣之用。大、中凉亭由谁筹筑,已无考。
由此可见,明清时期的“骡仔岭”段,是繁忙又充满生机的。民间的传说是有渊源的。
四、近代的“骡仔岭”
“骡仔岭”段繁忙景象,延续至民国时期。
现在人很难想象,在山高林密的偏远大山里,民国十六年公元1928年,“骡仔岭”自然村曾开设过客栈,还有裁缝铺,服务过往行人和周边百姓,店主是位黄氏先民,从抱古的上平山迁徙来的。可见,当时此段古道并不落寞。经营好几年后,因遭土匪抢劫而关闭。此先民就是从广电退休、现居大燕村后坂的黄荣木之祖父。
到公元1961年,此道仍是安溪、仙都通往华安县城的最便捿的道路。每逢圩日,挑着各种货物的赶集者,搭乘火车者,川流不息。
话说,公元1957年初夏的一天,时任华安县政府副县长的卢亚来(后,任过漳州市市长,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已故),率人前往仙都下乡检查,也走过此道。一行人走到骡仔岭,见有户人家施粥水,便入屋休息,卢副县长一边喝水一边与户主聊天,他听得懂方言但不大会说。
户主讲:此段道路约有5里多长,山高岭陡,都是石阶沿山而上,行人费力,尤为挑担的人,就是大冬天,只穿单衣,个个都满头大汗,走到这里差不多一半路。在这备些开水、草药茶,稀粥汤和咸杨梅,供行人休息解渴。茶水免费,稀粥汤随客便,愿给就收,只收一分钱,没给也不索要。因时常忙于农事,无空看顾,大都凭行人自觉自愿。除正月初一初二外,天天有备,逢仙都或茶烘圩日,多备一些。
卢副县长饶有兴趣,转头叫随行人问户主,哪一样最受欢迎?
这一问,户主板着指头,如数家珍:青草茶水,预防中暑,夏天才有备;喝粥汤的,大都是从安溪远道来的挑担人,他们多自备熟地瓜、熟芋头或熟地瓜丝捏成一小团一小团的,没配粥汤难吞下肚;挑担人,开水是必添加的,大都是用麻竹切一节加工成的“竹筒”;咸杨梅,挑担人个个会吃几粒,有些挑担人会顺带几粒继续赶路。俗话说:“人缺盐分会软脚”。吃咸杨梅,补充体内盐份,有助体力恢复。因此,每年端午节前夕,都要上山摘几担野杨梅,大约有二百五十斤。户主用手指指着厅边继续说:把这十来个瓷瓮腌满,才能保证一年之需。咸杨梅算是最受欢迎吧。
这时,卢副县长才发现,角落里有一块小木板,一行字已模糊不清,走近细看才认出:茶水免费,粥汤自愿,只收一分钱。
卢副县长被大山里质朴村民的行为所感动。他叫随行人员取来纸笔,写完后交给户主,请他每二个月到华丰的县粮食局粮店领取十斤米和一斤油。
户主不识字,听不懂卢副县长讲什么。随行人员解释后,户主仅憨厚笑笑。感谢话也没说。心里嘀咕,这张纸管用?
隔些日子,在邻居催促下,户主乘赶集日去县城,经人指点找着粮店,就进去试试看,果然管用,取回纸条一看,上面多出一个红色条印,好生奇怪。但此后再也没去领过。
有人问他:怎么不去再领呢?户主称纸条找不到了。而私下与亲戚讲:这小事做这么久,是自己愿意,就图给人一个方便。那是公家的米和油,我是个山民,怎么好意思再去领呀。
那位户主早已故去,卢副县长手书的纸条也难览踪影,但亲民的县长,质朴的山里人,朴素的农民语言,至今,仍在华安乡间传为佳话。
在公元1959年,随最后一户迁居外地,“骡仔岭”自然村消失。但她作为曾经的古道:“骡仔岭”段还在,光滑的石阶正默默地诉说着千年过往的故事,也收藏着散落在下田境内古道上的奇闻轶事,历史风烟,等待有心人去探究,去挖掘,把悠悠的古道文化继续传唱!
参考资料:
1《漳州府志》万历版。卷26风士志风俗考第3页。2,《漳州市志》,第333页。漳州市地方志编委会。3,《闽南史》作者,徐晓望。4,《华安县志》,华安县地方志编委会。5《陈氏族谱》咸丰年手稿。6,《黄氏族谱》清乾隆二十三年公元1758年,黄长出手稿。
导报讯(通讯员 黄明周 记者 张雄敏)
感谢黄明周供稿
,免责声明:本文仅代表文章作者的个人观点,与本站无关。其原创性、真实性以及文中陈述文字和内容未经本站证实,对本文以及其中全部或者部分内容文字的真实性、完整性和原创性本站不作任何保证或承诺,请读者仅作参考,并自行核实相关内容。文章投诉邮箱:anhduc.ph@yahoo.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