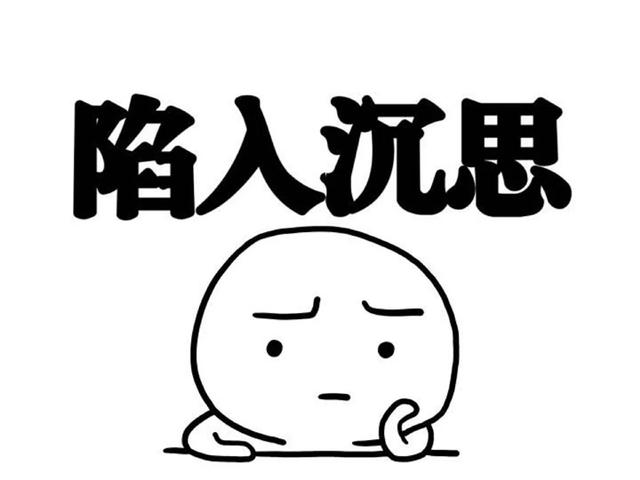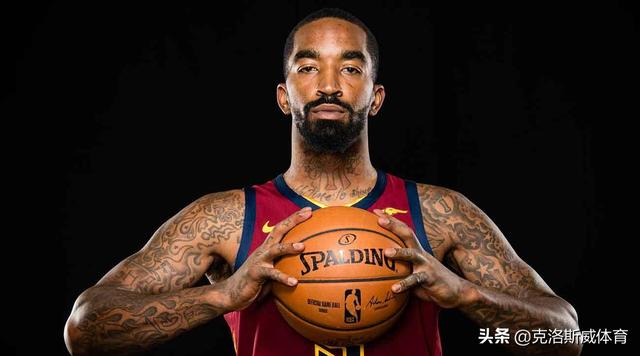晋祠晋阳湖公园(期待回来的水世界)
大唐天宝十三载(754年),春天,盛世还在继续。没有谁会想到,一年后,眼前的花团锦簇就将凋零于安史之乱的狼烟。
53岁的李白也不例外。游历完幽州、魏州(两州均属今河北境内),他折入山西。在晋阳(属今太原晋源),他买舟南下。彼时,作为黄河第二大支流的汾河,水量之丰沛远超今日。波涛滚滚之上,晋阳与绛、蒲诸州(今山西新绛、永济)甚至长安之间的帆影摇曳不绝。或许是船头的浪花,飞珠溅玉,勾动了回忆。李白想起了十九年前宴游晋阳的往事,写下长诗《忆旧游寄谯郡元参军》:“时时出向城西曲,晋祠流水碧如玉。浮舟弄水箫鼓鸣,微波龙鳞莎草绿……”他忘不了晋祠。
那个时候,唐叔虞是晋祠主祀的神明。唐叔虞本名姬虞,乃西周武王的三子、成王的胞弟。幼年某天,他和成王玩耍。成王捡起一片桐树叶子,比作当时分封爵土的凭证——圭,说:“吾以此封汝”。摄政的周公闻知,认为“天子无戏言”。于是,古唐国(今山西临汾翼城、曲沃一带)被分封到姬虞名下。自此,姬虞又称唐叔虞。后其子改国号“唐”为“晋”,累世兼并征讨,鼎盛期囊括今山西全境和河南、河北、陕西、内蒙的一部分。其国祚绵延600余年,至“三家分晋”,方寿终正寝。虽然晋国覆亡,但不知何时创立的唐叔虞祠,屡兴屡废,时至今日,敷演为蔚然大观的建筑群——晋祠。

晋祠中的水镜台是唱戏酬神的戏台。 (庞勉/图)
悬瓮山下
知道晋祠,是在初中上学时。梁衡先生的散文《晋祠》,像一粒种子,埋进我的心底。一埋,三十多年。直到两年前,新冠疫情略微平淡的时候,才破土而出。2020年七八月间,趁差事之便,我去了那里。
与梁衡先生“出太原西南行五十里”不同,我是出汾阳东北行高速公路140余里抵达晋祠的。这个行止,无意中与另一位梁先生——建筑学家梁思成及夫人林徽因的有些雷同。1934年暑假,梁、林赴汾阳预查古建。他俩探访古建有个习惯,多对名胜——尤其像晋祠这样“历来为出名的名胜”——怀疑:“因为最是名胜容易遭重修乃至于重建的大毁坏,原有建筑故最难得保存……直至赴汾的公共汽车上了一个小小山坡,绕着晋祠的背后过去时”,他俩“才惊异的抓住车窗,望着那一角正殿的侧影,爱不忍释。相信晋祠虽成名胜却仍为古迹无疑。”一个多月后,预查结束。返程中,梁、林尽管“心力俱疲”,携带“种种行李什物,诸多不便”,却“因那一角殿宇常在心目中,无论如何不肯失之交臂”,遂于路过晋祠时,“下了那挤到水泄不通的公共汽车……”
下了“网约车”,我的情况不比梁、林好多少。大背包里塞满了从汾阳搜罗来的图书,打算寄存,没承想,到得有点早,寄存处、景区连门都没开。只好背着,随几名当地人,走厕所旁一条花木掩映的小道,“偷偷”溜入景区。进去后,才发现林荫下、草坪上、湿地边都有人晨练。一打听,明白了:原来现在的晋祠景区像一个俄罗斯套娃。外面一大圈为晋祠公园,不收费,供市民休闲。真正的“名胜”晋祠,称为晋祠博物馆,得往里再走几里路。
路一直上坡,蜿蜒曲折且旁逸斜出。我似乎置身于一座小径不断分岔的大花园,动辄“迷途知返”,倒回重走。好在,透过林木挤出的缝隙,不时能望见远处晴空下的一抹青山——悬瓮山。那是个大坐标,朝着走,没有错。
悬瓮山又名县雍山、结绌山,属山西西部的吕梁山支脉。其1200米的海拔,看上去并不高大,盖因我脚下是黄土高原东缘的山西高原,平均海拔达800多米。关于悬瓮山的得名,明末顾祖禹在《读史方舆纪要》中说:“山腹有巨石如瓮”;清末刘大鹏在《晋祠志》中进一步认为“其石高悬”。可惜的是,宋真宗咸平年间的一场地震摧毁了巨石。近年来,又冒出一个新说法,认为悬瓮山为石灰岩地质,“悬瓮”系山体溶洞内的钟乳石。
先秦奇书《山海经》最早记载了悬瓮山。“其上多玉,其下多铜,其兽多闾麋,其鸟多白翟、白䳑。晋水出焉”的描述,给它涂抹了一笔魔幻神秘的色彩。而晋祠,确凿记载始自北魏地理学家郦道元编撰的《水经注》,“际山枕水,有唐叔虞祠……于晋川之中,最为胜处。”

一只鸟正好飞过大殿上方。 (庞勉/图)
智伯溪与李唐龙兴
当我汗流浃背,跨过晋祠博物馆(下称晋祠)大门,一瞬间,如同穿越爱因斯坦的“虫洞”掉进了遥远的古代。“左右杂树交荫,希见曦景”,这1500多年前的文字依然生动概括了我的初见。未等定神,洋洋洒洒参差广布的楼台亭阁又迫不及待地奔至眼底,竟有应接不暇之感。此般感受,不独有我。博闻强识的梁、林也认为晋祠“过于初时的期望……那一种说不出的美丽辉映的大花园”,使他们“惊喜愉悦”。
在一株虬枝盘曲的唐槐下,我注意到不远处有两道石砌护栏,走过去,低头发现沟底镶嵌的水流,纤细柔弱。对照手中导览图,我看见了它的名字——智伯溪。如果没有史志的记载,我简直不敢想象它曾经的水势浩大。春秋末期,晋国正卿智伯率韩、魏伐赵,见赵氏固守晋阳,便开渠筑堰,引悬瓮山下的晋水,围灌晋阳。城破在即,赵氏以唇亡齿寒之词,偷偷说服了韩、魏。晋哀公四年(前453年)三月,韩、魏倒戈,赵军掘开堰堤,大水反噬了智军。智伯兵败身死,晋国势成三分,中国历史由此递进战国。这就是有名的“晋阳之战”。后人将“助战”的渠水称作智伯溪,自东汉起“踵其旧迹”,重加疏浚,用于灌溉。北宋范仲淹赋诗云:“神哉叔虞庙,地胜出佳泉……千家溉禾稻,满目江乡田。”
范仲淹拜谒晋祠的时间,在庆历四年(1044年)夏天。作为主管陕西、河东路(今山西大部)军政的宣抚使,他的目的,就是为了饱受旱魃之苦的苍生求雨。可见,彼时的唐叔虞已司掌“行云布雨之责”。
无独有偶,时间再上溯四百二十七年的话,同样在晋祠,同样在夏天,另一场求雨则掀开了一个王朝的序幕。大业十三年(617年),隋朝大乱,唐国公李渊在其子李世民的劝谏下准备起兵。与此同时,隋炀帝亲信王威、高君雅觉出异样,想骗李渊到晋祠求雨,伺机诛杀。不料,风声走漏。李世民抢先下手,清除王、高。最终,李渊前来拜祭唐叔虞,名虽求雨,实则“用竭诚心,以祈嘉福”。在他看来,自己反隋无异于武王伐纣。是年七月李渊举义晋阳;翌年五月称帝长安。二十九年后,也就是贞观二十年(646年),李世民重游晋祠,触景生情,写下《晋祠之铭并序》,勒石树碑(下称唐碑)于晋阳城内。宋太宗赵光义亲征北汉时,将其都晋阳夷为平地。此碑侥幸逃脱水火之劫,移入晋祠。

匾额是晋祠的一大观。 (庞勉/图)
智伯溪左岸的贞观宝翰亭,就是唐碑“藏身之处”。入内,我竟看到仿若“孖生”的两通大碑并肩而立,3米多高、1米多宽。根据碑额图形,我判断右为“原版”,雕螭首一对;左为清乾隆年间担心“原版”风化的“复刻”,雕二龙戏珠。
亭外,西北隅,朱墙折绕的唐叔虞祠高耸于一摞台阶上。或因避讳之故,其山门匾额仅书贴金篆字“唐叔祠”。这是一座两进庭院,别有清幽。跨进享堂,14位泥塑乐伎手持箫笛笙钹分列左右。我卸下背包,轻轻地,生怕打断了她们的演奏。伫足观赏之际,偶一扭脖,瞥见那头,大殿内,唐叔虞神像也在端坐聆听……

唐叔虞祠 (庞勉/图)
实际上,“唐叔祠”已非唐朝旧迹,而是元代遗存。不只外观迥异于唐碑形容的“金阙九层,玉楼千仞”,连位置、朝向也发生了更迁:从中轴线的西端挪至中轴线的北侧,从坐西朝东改为坐北朝南。
晋祠的中轴线
中轴线一般强调南北贯通,讲究东西对称。北京故宫、曲阜孔庙莫不如此。但晋祠不同,它的中轴线呈东西走向,与西南流向东北的智伯溪相交于会仙桥。
献殿,顾名思义,献祭之殿。前身系北宋构筑的均福堂,于金世宗大定八年(1168年)重建。这座单檐歇山顶建筑,高约10米,面阔三间,进深二间。“四周均无墙壁,当心间前后辟门,其余各间在坚厚的槛墙之上安直棂栅栏,如《营造法式》小木作中之叉子”,梁、林接着指出献殿的“梁架,只是简单的四椽栿上放一层平梁,梁身简单轻巧,不弱不费,故能经久不坏。”这般设计,依我看来,与其说献殿是一座殿堂,倒不如说是一座放大版的凉亭,通风、采光都极好。
凉风习习,光影迷离,恍惚中,戴着南洋帽的梁思成和蓝衣白裤的林徽因谈笑着经过身旁。顺着他们的指尖,我看到了鱼沼飞梁。

飞梁下的鱼沼 (庞勉/图)
沼者,池也;“鱼在于沼”,鱼沼也。梁者,桥也;“架虚为桥”,飞梁也。疑似实景的记载最早见诸《水经注》,“蓄以为沼……水侧有凉亭,结飞梁于水上”。但郦氏所指,究竟是不是鱼沼飞梁,学界仍有争论。
不管怎么说,等我踏上四五级台阶,走到鱼沼飞梁的十字路口,不,是“十字桥口”时,才发现,原来飞梁并非一架桥的跨越,而是两架桥的相遇。东西为正桥,平板式,长约20米,宽约5米;南北为翼桥,斜坡式,比正桥略短稍窄。可惜背包装的不是无人机,否则,我定能拍下飞梁若白鸟点水般的风采……鱼沼内的锦鲤似乎猜透了我的心思,成群结队,从许多八棱形小石柱间游来……这些石柱仍如梁、林当年的描述“上端微卷杀如殿宇之柱,柱上有普拍枋相交,其上置斗,斗上施十字栱相交,以承梁或额。”如此水中立石柱,上置斗栱,再架梁、铺板、立栏的桥梁,“即古所谓石柱桥也”。十年后,梁思成在四川宜宾李庄写完《中国建筑史》。书中,关于飞梁,他写到:“此式石柱桥,在古画中偶见,实物则仅此一孤例,洵为可贵。”那个时候,他不知道,飞梁的桥板已由木料换成石料。再往后,又改铺方砖,安装了汉白玉桥栏。
一个多月来,萦绕梁、林脑海里的“魁伟的殿顶,雄大的斗栱,深远的出檐”总算展露出真容。趁天光明亮,梁、林赶紧支起三角架,开始拍照考察,否则错过去太原的末班车,晚上就只能露宿或住店了。“大殿,重檐歇山顶,面阔七间进深六间……在布置上,至为奇特。殿身五间,副阶周匝。但是前廊之深为两间……异常空敞,在我们尚属初见。斗栱的分配,至为疏朗……在下昂的形式及用法上,这里又是一种未曾得见的奇例……这种做法与正定龙兴寺摩尼殿斗栱极相似,至于其豪放生动,似较之尤胜……斗栱彩画与《营造法式》卷三十四‘五彩遍装’者极相似。虽属后世重装,当是古法……”

梁思成在晋祠大殿前廊处拍摄照片。 (庞勉供图/图)
让梁、林不住赞叹“奇特、初见、奇例、尤胜、古法”的大殿,就是和鱼沼飞梁同时落成的圣母殿。圣母殿确系北宋遗构无疑,但具体年代,说法不一。从梁、林判断“结构法及外形姿势……较《营造法式》所订的做法的确更古拙豪放”来看,肯定早于《营造法式》开始编撰的绍圣四年(1097年),极可能在宋仁宗年间(1023年-1060年)。
圣母殿的创建,使得唐叔虞祠迁离了中轴线终端,“屈居”到如今的位置。熙宁十年(1077年),求雨越来越灵验的圣母被封为“昭济圣母”、政和元年(1111年)加封为“显灵昭济圣母”……
应龙、蟠龙、蛟龙、螭龙……八条龙,从北宋腾云驾雾而来,又各自抱紧一根檐柱留连不去,这就是“缠龙柱”——今世仅存的能够印证《营造法式》所记的木制雕龙。走进前廊时,群龙依然身姿奇矫,冲我跃跃欲试。左右4米高的镇殿将军,曾经反出朝歌的方相、方弼兄弟,也只怒目圆睁,不发一言。
大殿深处,神龛正中,圣母凤冠霞帔,趺坐凤椅,两旁环立42尊内侍彩塑。其中,宦官像5尊,著男服的女官像4尊,侍女像33尊。从仪态、服饰、手持器物,不难看出,这群内侍正遵照北宋后宫的六尚制度,小心伺候着圣母的饮食起居。对此,现代雕塑大师刘开渠评价到:“站在这些雕像中间,不但能看见她们轻巧的动作,还像听见了她们清脆的笑声,快乐的言谈,或不乐意的小小地讽言讽语,清楚的了解她们彼此间的思想感情关系;这是……令人难忘的抒情的美的境界……”
那么,尊享荣华的圣母是谁?主流说法有二:一说是姜子牙之女、周武王之妻、周成王及唐叔虞之母邑姜;因后世天子祭拜国君唐叔虞,于礼制不合,晋祠遂改祀邑姜。一说是宋仁宗的养母、垂帘听政11载的太后、太原人刘娥,即电视剧《清平乐》里面的大娘娘。
除了圣母,大殿还“埋”有一个秘密。那就是其下方石基包裹着一处泉眼——圣母泉。1953年,鱼沼飞梁翻修,人们发现微温、晶莹的泉水通过古老的人工暗渠,哗哗注入沼内。
像这样的泉眼,据方志记载,在过去,晋祠多达百余处,几乎每座屋宇、庭院都有清泉脉脉、水井幽幽。用梁衡先生的话说,“怕这几百间建筑都是在水上漂着的吧!”究其原因,与悬瓮山特殊的地质构造有关。悬瓮山地处由三条大断层形成的石灰岩三级阶梯,中间的台阶受地质动力作用最强,生成裂隙。这些裂隙长期受地下水的侵蚀、溶解,不断扩大发育为溶洞。这些溶洞宛如地下水库,靠汾河水和大气降水的补给,水位持续上升,直至涌出地表,形成晋祠数目众多的泉或井。除圣母泉外,以难老、善利两泉最为有名。北齐文宣帝高洋(550年—559年在位)于晋祠“大起楼观,穿筑池塘”之时,两泉已赫然列入扩建名单。
去善利泉的途中,我被一株苍龙横卧般的古木吸引。凑近,始知是快三千岁的周柏。北宋欧阳修游览晋祠时,周柏仍为站姿。清道光年间,周柏忽然南倾,幸被另一株古柏扛住,才未砸中大殿。1929年,冯玉祥到太原劝阎锡山反蒋。住晋祠期间,借周柏明志:“大树苍苍数千载,虽然倾斜成大观。饱经世界冷暖事,能耐风霜不畏寒。”

倾倒的周柏 (庞勉/图)
周柏再往北,便是善利泉。泉上有亭,八角攒尖顶,为明嘉靖年间重建。亭内有匾,曰“善利”,典出《老子》:“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尽管知道1972年善利、圣母两泉就已干涸,但我仍和很多游客一样,在围栏外面蹲下来,希冀黑乎乎的泉眼能在俯看的刹那出现奇迹。
1993年,智伯溪的源头、与善利泉南北对应的难老泉也彻底断了流。这眼寓意青春永在的泉水,终于不敌狂伐山林、滥采煤层、过度抽水导致的水系补给衰竭。人们只得埋设管道,用自来水灌满鱼沼,“复活”难老泉,维系水母楼、不系舟、真趣亭等处的流水景观。这一年,距梁思成先生作出“(晋祠)为井垣名胜,清泉出之”的评价不到50年,距吴伯箫先生发表散文《难老泉》32年……
出了晋祠,我再次坐上一台网约车。开车师傅是本地人,他对我说,这些年关了许多小煤矿,效果不错,让村里的泉眼又出了水。等你下次来,也许能看到真正的难老泉了。
庞勉
,免责声明:本文仅代表文章作者的个人观点,与本站无关。其原创性、真实性以及文中陈述文字和内容未经本站证实,对本文以及其中全部或者部分内容文字的真实性、完整性和原创性本站不作任何保证或承诺,请读者仅作参考,并自行核实相关内容。文章投诉邮箱:anhduc.ph@yahoo.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