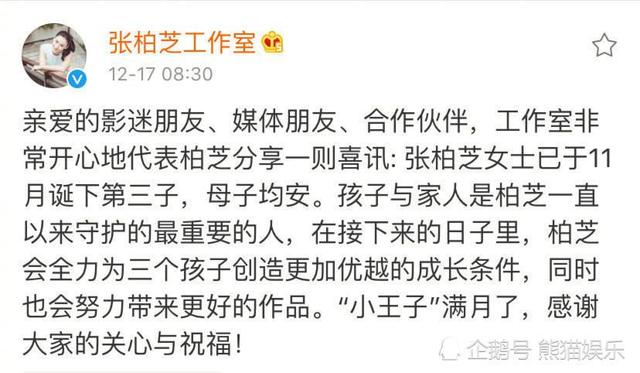现在的大夫还是以前的大夫(既不姓白也不是大夫的白大夫)

【小说界】
既不姓白也不是大夫的白大夫
文‖韩素彩 图‖网络
白大夫既不姓白也不是大夫。
白大夫姓牛叫顺顺。顺顺二十岁时,已抽成了重眼双皮儿,白净子儿,细高挑的大小伙。到了春心萌动谈婚论嫁讨媳妇的年龄,他那个深谙世道的寡居娘,并不在他面前提他的婚姻大事,只顾侧歪着小脚舀碗水一摇一摇地往锅里添水做饭,看似心不在焉,实际是旁敲侧击劝他打消这个念头说:大麦不熟,哪有小麦先熟的理儿。顺顺知道哥哥不娶,是下雨天打伞——淋不到他,就收了心。现在嫂嫂到家三年了,他今年二十九,眼看着翻过年就三十了,婚事还无着落,顺顺就整日心灰意冷蔫蔫的没了精神。冬日里,上工时他衣帽不整,邋里邋遢,懒洋洋地躲在堰旮旯里晒太阳。
队长老崔是个急性子,又是个热心肠。夏天就他热,冬天就他不怕冷,伏天里,他把一把把儿摩挲得黄中泛红闪着幽幽亮光的芭蕉扇往后裤腰一别,敞着怀疾步走起路来,后背呼呼张着风,衣服被撑得鼓鼓的,像背了一个乌龟盖。冬天穿件黑色褪旧弯着袖筒子的撅肚小棉袄,依旧敞着怀,他背着手撅哧撅哧走起路来,脚底生风一溜烟。他看见顺顺躺在那儿就来了气,大声骂:你不缺胳膊少腿儿,年青力壮不干活,躺在那儿仰球晒蛋偷啥懒哩。顺顺懒洋洋地笑着说:叔,不是提不起来劲嘛。老崔拿眼瞪他一会儿,若有所思,噎着脖子不再吭声。

第二天上工前,队长老崔在饭市上开个社员会,他用手抻抻褪旧撅肚棉袄前襟上的褶皱,以表严肃,他掐着腰,摇着头,声若洪钟似的大声宣布说,经队委会研究决定,以后牛顺顺是咱生产队的记工员兼经济保管,还是咱生产队的保健员。那年月生产队的一个小职务就了不得,何况现在顺顺一下子有了三个职务,顺顺精神是焕然一新,一下子春风得意马蹄疾起来。
先说说这三种职务,那时候大集体人人是脸朝黄土背朝天,四下汗流冒狼烟,每天是上工下工,上工干活挣一分工分都能分一份口粮,人人靠工分吃饭,记工员可是一个不可小觑的职务。生产队的经济保管也是生产队里的一个重要角色,尽管生产队有的只是买槡叉、农具、牛笼头那几个数得过来的钱,但毕竟是个官。保健员的整个家当就是大队发个带红十字的棕红色药箱,里面装着人丹、薄荷片、十滴水等防暑药和包扎伤口用的胶布、纱布、碘酒、消炎粉、小镊子、小剪子。保健员的工作就是伏天里田间地头劳动中谁热的受不了了,发几片人丹,薄荷片降降暑。在田里干活谁擦破了点皮,划破了口,保健员拿个小镊子捏一小疙瘩药棉沾点碘酒在伤口上轻轻抹一抹,伤口流血了,上点消炎粉,用一小片纱布一盖,刺啦撕一绺胶布一沾就妥。

顺顺的老表是个复员军人,他死乞白赖地求他表哥借给他一身旧军装,又去找村里被割过资本主义尾巴的老剃头匠剃了个时兴的小平头。顺顺一下子改头换面,每天穿着多少人羡慕的绿军装,屁股上挎一串明晃晃的钢钥匙,顺顺走起路来故意把腿伸得直直的使脚板重重落下,屁股就一颤一颤的把钥匙震得哗啷哗啷地响。每天上工了,顺顺穿着洗濯得干干净净,在枕头下压得展挂挂的那身绿军装,背着板板正正的药箱子,精神头十足地巡回在生产队的田间地头。放工了,顺顺从袋子里掏出卷了边的记工本,往地头一蹲,很严肃地用手指一下一下把卷边的纸捋平,然后就笑微微的,认认真真地开始一笔一划,在每个人的名下记工分,众人喜笑颜开,众星捧月般围着他,顺顺甭提多神气了。
时气来时不由人,风吹草帽扣鹌鹑。顺顺上任没几天,村里的崔坡田外号叫棉花碓碓的媒筋,来给顺顺说媒。啥是棉花碓碓,就是人特会说,黑里能说成白的,白里能说成黑的,有榷死人不偿命的本事。顺顺自然不敢怠慢,常言说成不成,酒两瓶。顺顺买了酒,整个下酒菜,崔队长作了陪,推杯换盏,吆五喝六,晕晕乎乎中事情就说定了。

崔坡田给顺顺说的是西边王庄王里快家的老闺女王香芙,王里快身强力壮,孔武有力,是个大力士,每天除了干地里活挣工分,家里的大小事交由老婆甄讲玖操持。王里快的老婆甄讲玖一辈子就生一个闺女王香芙,王香芙长得三月桃花面,二月风摆杨柳腰。甄讲玖说闺女长得好,就是个享福的相得找个当干部的,即便不是干部也得是个吃商品粮的工作人,女儿的婚事甄讲玖把关把得紧,任凭说媒的踏破门槛磨破嘴皮,她觉得男方不合适,叫闺女呆在奁中不让轻易飞出去。甄讲玖帮女儿左挑又捡看花了眼,一转眼女儿过了三十岁的门。她女儿的婚事在三里五村也成了出了名的不好管,说媒的也望而止步,从此她家门庭就开始冷落。如今看见大名鼎鼎的崔坡田,甄讲玖乐呵呵的赶紧让座倒茶格外热情。
崔坡田进了王里快的家,从上到下看着利利索索的甄讲玖,她穿着浆洗得干干净净的有襟白褂子,头发梳理的纹丝不乱在脑后打个鬏,用宽宽的半圆形黑塑料卡子卡成个好看的髻,穿条黑色的阔脚裤,隐隐的遮着放了的半大脚。屋里屋外拾掇得干干净净,连厨房里冒的淡淡炊烟也是素净的。崔坡田心里说甄讲玖呀真是真讲究。

崔坡田在王里快家堂屋当门八仙桌旁落下坐,小呷一口茶,轻轻放下碗,讪讪笑两声,就往正题上说。我今儿给咱闺女说的是俺庄上的牛顺顺,牛顺顺不但人长得重眼双皮儿,白净子儿,细高挑模样没包谈,在俺生产队是记工员兼经济保管还是医生一挑三,不是有句话大小是个官儿,强似卖水烟儿,现在顺顺年纪轻轻的可是一挑三,前头的路可是宽着哩。崔坡田说完最后一句话端端地坐在那儿并不扭脸,只是觑眼看一下王里快和甄讲玖。王里快弯着身子坐在一边矮凳上慢慢抽着自己卷的粗烟卷不说话,甄讲玖身子坐的很直,双手搭在膝盖上,听崔坡田开口说顺顺长得好,崔坡田说这话她并不往心里放,她心里轻轻飘飘地想又不是干部也不是吃商品粮的人,但听崔坡田说顺顺一挑三,不免动了心。她看似心不在焉地问这孩子多大了。顺顺属狗的今年二十九,崔坡田见甄讲玖问心说有门就赶紧笑着回。
甄讲玖一听脸一沉,双手松松地在膝上轻轻一捏说,狗咬鸡,绕天飞,不中,她俩大象不合。崔坡田又讪讪笑了两下说,老嫂子,不是还有句俗话说,外狗不咬家鸡吗,没啥忌讳的,顺顺人又那么好,将来俩人能和和睦睦的过上好日子儿的。

甄讲玖被崔坡田说动了心,说我就这一个闺女,我明天得先去看看。崔坡田双手在腿上轻轻一拍很高兴地说,儿女的婚姻是大事,老嫂子自然得先去看看了,说定了,我就先回了。
崔坡田回来一屁股坐在顺顺家小椅子上,很自得地把身子往后一仰,顺顺笑着赶紧端茶递烟。崔坡田说这事有门,闺女她娘是个细致人,那个是真讲究,说明天来家看看。
顺顺的娘一听,鞋里长草荒了脚,她侧歪着小脚在屋里走了几步,身子软软地往墩上一坐,一脸无措地用手捏着衣裳襟,说他叔你也知,咱家是东打西旮旯,除了俩大缸空荡荡啥也冇,人家娘是个讲究人,来一看那会能成亲戚?崔坡田大嘴一咧嘿嘿笑出了声,说活人还能叫尿憋死,你叫顺顺去问崔队长先借二十斤蜀黍二十斤麦。把你家俩大缸往当门两门后一放,底下垫些糠,把借来的粮食放上面。再去把你大媳妇床上的铺盖背来铺到咱顺顺床上,再去东家借桌子,西家借凳子,我再去把俺小孩他舅那辆永久牌自行车推来放到咱屋里。嘿嘿,崔坡田又笑了笑说,这不就都铺摆好了。顺顺不好意思地说,叔,那会中,那不是坑人哩。

崔坡田眼一瞪,你说的,你小子还要不要媳妇了,现在是给那竹竿样,先通一节说一节,等娶到家了,女人不都是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嫁根扁担抱着走,到那时媳妇就是煮熟的鸭子想飞也飞不了了。顺顺和他娘虽觉这样做有点不妥,但俩人讨媳妇心切,也就依崔坡田说的办。
第二天,顺顺去集上割了一块肉,顺顺母亲在灶台上用文火炖了一只鸡,炖鸡肉的香味从灶屋里一股一股急不可耐地往院里窜。上午半晌时,甄讲玖被顺顺一家人恭恭敬敬地迎进了门,顺顺家打扫得干干净净的院里飘着醇厚的肉香味,顺顺春光满面甜甜地问了甄讲玖一声伯母好,甄讲玖看见重眼双皮儿,白净子儿,细高挑的顺顺很是满意,觉得崔坡田说的话不假,进了屋在上座坐好,接过了顺顺递过来放了糖的茶,在低头喝茶时,她不动声色地拿眼在屋里四处巡睃。她看到屋里缸里有粮食,床上有新铺盖,屋里有摆设,还有一辆永久牌自行车,心里悬着的那颗心也落了地儿。喝罢了茶,她直起身往后轻轻地抿抿纹丝不乱的发,摆出一副很明事理的高姿态,高兴地对顺顺娘说,真早晚新社会都兴婚姻自主,只要俩孩子愿意我冇啥。

顺顺和王香芙俩人见了面,他俩一个是潘安貌一个是羞花容,俩人彼此情又投意又合,王香芙接了见面礼,接下来的日子里,顺顺和王香芙俩人换了表记,王香芙的七大妗子八大姨来吃过了订婚席,婚事就定下了。三月后顺顺高高兴兴地把王香芙娶进了门。
甄讲玖对女儿这桩婚事很是满意,虽说顺顺不是吃商品粮的工作人,但顺顺一挑三的大名,也给爱虚荣的甄讲玖长了脸,挽回了想攀高枝落了空的面子。
办完婚事的第二天,甄讲玖连日的劳累,心口痛的旧病犯了,往常痛的时候,她总是忍着不出声,这次犯心口痛的老病,她躺在床上一叠声的呻吟着哼个不停,女儿的婚事是她一手操办的,女婿是个医生,她很颐指气使地派那个不管事的丈夫王里快,快去叫医生女婿来给她医。王里快不敢怠慢,速速前往。
顺顺看见泰山老岳丈到来,唯恐怠慢,赶紧恭恭敬敬地搬凳、敬烟、递茶。等泰山老岳丈说明来意,顺顺白净子儿的脸腾地一下子红到了颡根,手足无措的傻站在那儿不知说什么好,还是顺顺娘杵着小脚一侧歪一侧歪从灶屋出来,边走边用围裙啪啪绰着身上的灰,三言两语帮他解了围。

顺顺娘十分关切地说,老哥哥,老嫂子心口痛可是有老病根的,俺村牛得手老中医治老陈病是他的拿手戏,他下药是百打百中。扭脸对顺顺说,你还不快去请牛医生给你娘看病去。顺顺愣过神来,赶紧借坡下驴,疾步跑出去去请牛医生。
甄讲玖知道了顺顺的底细,觉得这次是被崔坡田忽悠着吃亏吃大了,她在人前人后夸顺顺是医生时,仰着脸嘴角挂着笑那种得意劲,会被街坊邻居茶余饭后当笑料说来说去的。说她挑女婿,今挑明拣还不是挑个瞎眼,她越想越气,气的肚子涨涨的。她忽地从床上坐起来,拍桌捶凳尖着腔用指头朝空捣着骂崔坡田,啥狗屁崔坡田,就是个名副其实的吹破天,还说是医生,呸,榷死人不偿命,把俺一个如花似玉的好闺女送到穷坑里。呜呜……
晚上,王香芙从娘家回来,她深感受骗,她躺在床上蒙着头,抽抽噎呜呜地哭,嘤嘤地哭。

闪闪烁烁的灯光里,顺顺心疼地听着王香芙的哭声,自知理亏,他惭愧地坐在床沿,手足无措的使劲搓揉着大腿帮子,觉得劝也编不出合适的劝词,不劝又不忍。最后他蹲在地上大大的眼里落下了泪,顺顺说,是俺对不起你,还都不是因为穷,才这样办的,事到如今,你要嫌俺穷,我把你送回去吧。王香芙听了气不打一处来,噎着了哭,忽地掀开被子,伸手抓起枕头狠狠砸向顺顺,嘴里大声说,你是雪蛋擦包(包是方言屁股的意思)——屁话,啥时候了你还装好人,穷就穷吧,那还装什么医生,你啥病也不会治,就是个白大夫。顺顺听王香芙说穷就穷吧这句听似嗔道人的话里有一种情的味道,刚才那颗凉下去的心立刻又热乎起来。他张嘴刚想为自己辩解,说他不是有意要骗她的,是村里人把背药箱的人都称呼为医生。窗外几个听房的半大撅,听到王香芙说出白大夫三个字,憋不着忒儿地笑出了声,脚步嗵嗵地散去了。屋里顺顺开始低眉顺眼,软语温存地劝慰新娘子说,就算不是医生,家里还穷,老人们不是说穷不生根,福不长苗吗?我有的是力气,能吃苦,保准不叫你受委屈。顺顺再也想不出合适的劝慰新娘子的话,他想起了街上的标语,就说,大干快上,在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路上,我们的日子会慢慢好起来的。王香芙被顺顺这句文绉绉的话,一下子逗得嗤地笑出了声,她又抓个枕头朝顺顺身上砸来。

第二天顺顺背着药箱子,拿着记工本,还有经济保管抽屉上那串明晃晃的钥匙,去崔队长家。崔队长正皱着眉坐在他家门限上,低头咝咝地地抽着烟,他看见顺顺就笑了,顺顺倒不好意思起来,顺顺郑重地说,叔,我给你交差,咱生产队还有王顺顺、刘顺顺……需要你操心呢。崔队长啃啃嗽了两声,扔掉了燃到指根的烟蒂,站起来,抬起手,弯弯的棉袄袖筒子呼呼带着风,照顺顺肩上咚咚榷两下,嘿嘿地笑了笑说,好好干,别对不起自己的女人。
几十年后,恩恩爱爱的顺顺和王香芙的三个儿女都已结婚成家,顺顺和王香芙是子孙满堂,安享天伦。头发花白的王香芙头发梳的溜溜光,穿一身好看的花衣裳,面容慈祥,神情怡然轻轻地摇着扇,和几个老妇人在路边树荫下乘凉,精神矍铄乐呵呵的顺顺和几个老人在树荫下玩纸牌,笑声、争执声一浪高过一浪。
路上悠哉悠哉走过来俩头发花白的老人,其中一个大声说,老嫂子,白大夫呢?看病去了。王香芙笑着骂道,啊,可不是,你娘有病了快请他去看,他的手可高那。那人并不气恼,只是哈哈地一笑而过。

【作者简介】韩素彩,农民,禹州市顺店镇大韩村人,禹州市作协会员,一个热爱家乡,喜欢文字的人。
1、本文由作者授权发表,文责作者自负,如有侵权,请通知本今日头条号立即删除。本文作者观点不代表本今日头条号立场。
2、文图无关。文中图片来自网络,版权归原摄影者或原制作者所有,在此表示诚挚的感谢。本文所用图片如有侵权,请通知本公众平台立即删除。
3、“老家许昌”版权作品,转载或投稿请发邮件至hnxc126@126.com 。
爱许昌老家,看“老家许昌”。 老家许昌,情怀、温度、味道!
本文为头条号作者原创。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免责声明:本文仅代表文章作者的个人观点,与本站无关。其原创性、真实性以及文中陈述文字和内容未经本站证实,对本文以及其中全部或者部分内容文字的真实性、完整性和原创性本站不作任何保证或承诺,请读者仅作参考,并自行核实相关内容。文章投诉邮箱:anhduc.ph@yahoo.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