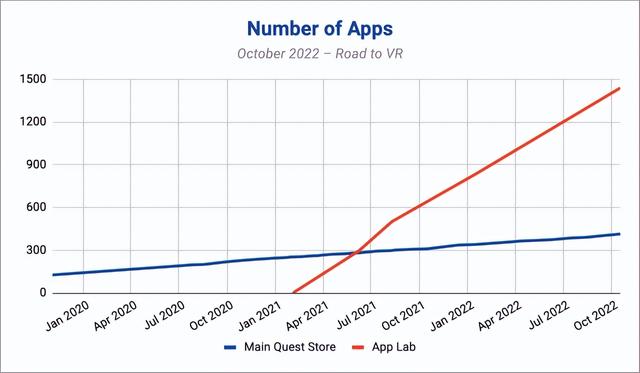她依然要为革命战斗到最后一刻(一场只完成了一半的革命)
“她”字走入大众视野,至今不到100年,我来为大家科普一下关于她依然要为革命战斗到最后一刻?以下内容希望对你有帮助!

她依然要为革命战斗到最后一刻
“她”字走入大众视野,至今不到100年。
在南朝梁太学士顾野王的《玉篇》中,曾收入“她”字,是“姐”或“毑”(音如姐,母亲的意思,汉代许慎《说文解字》中称,蜀地呼母为姐)的异写,以后渐次湮灭无闻。到1918年左右,当“她”字重新被提出时,几乎所有主张者都不知道还有这段前史。
黄兴涛先生在其杰出论文《“她”字的文化史:女性新代词与认同研究》(以下简称《“她”》)中,对“她”的历史进行了细致的梳理,在“她”如何战胜“伊”等问题的钩沉上,尤显精彩。
然而,“她”字在字形上虽然有所“革命”,在字音上却没有变化,刘半农、周作人等学者曾主张“她”应读如“坨”,以示区分,但未能普及。作为结果,“她”只在字面上取得了独立地位,在日常语言中,依然与他、它含混不分,而这个剥离之路为什么被中断,其实是一个相当有趣的话题,甚至从中可以窥见近百年来“革命”在本土文化中的变异。
刘半农不是“她”字之父
在黄兴涛先生的《“她”》文中,提出“她”字始于翻译需要,一方面,在广州海关的英文教材中,已出现了近似的主张,另一方面,初期倡导者普遍指出英文中的“She”无法对译的问题。
解决方案不外乎三种:
一是采用日文方法,标注为“他女”(女字字号略小),这样可以不用铸造新字,周作人、叶圣陶等人曾是热心的实践者,但一篇文章中字体忽大忽小,且两字读成一字,实在太别扭,所以后来周、叶转向支持“她”字。
二是从白话报纸和小说中直接借用“伊”字,在江浙口语中,“伊”虽然兼指男女,但后期基本成为女性专用,鲁迅先生等一大批作家都拥护这种做法,鲁迅先生使用“她”字还要晚于周作人,后因几名“鸳鸯蝴蝶派”中间作家坚决否定“她”,导致不少进步作家接受了“她”,但事实上,“鸳鸯蝴蝶派”中也有很多人早就放弃“伊”了。
三是另造新字,后人多误以为是刘半农发明的“她”字,理由是他写有诗歌名篇《教我如何不想她》,但这首诗写于1920年,此前康白情等人已经使用了“她”字(康白情于1919年5月20日《晨报》第7版上发表的《北京学生界男女交际的先声》一文中,两次使用“她”,1920年2月俞平伯在《新潮》杂志上发表的《狗和褒章》一文使用将近40个“她”,同年俞平伯发表了《别她》一诗,均先于《教我如何不想她》)。
鲁迅先生曾说,刘半农在北大课堂中提倡过“她”字,但从史料看,他是接受了别人的观点后加以推广而已,并非“她”字的发明者。但在提倡使用“她”字上,刘半农用力甚多,特别是他的《“她”字问题》一文发表,赢得巨大社会反响,以后《教我如何不想她》广泛传播,使“她”进一步流行开来。
在今天看来,与英文无法对译根本不是什么大问题,可在“她”问世的初期,这却是一个相当硬的理由。可见,“她”字诞生在一个对自身语言高度自卑的氛围中,如果当时人们英语足够好,这个借口很可能会被拆穿。
为什么“她”字要闹革命
值得关注的是:“她”字为什么诞生在1910年代,既不更早,也不更晚?应该说,这与时代心理的变迁息息相关。
甲午战败后,白话报纸激增,到晚清时已达140多种,堪称是一次“白话文运动”,这为后来的“新文化运动”做了充分的铺垫,可当时却并没有出现“她”字,作家们主要使用的是“伊”,可见,是否使用“她”字并不影响交流,在“她”字背后,不仅是使用是否方便之争,还是文化地标之争,只有当社会整体紧张程度超越临界点,“她”字才真正找到了创生与流布的土壤。而这个土壤,就是“杀死父亲”的情结。
从心理层面看,人类的服从需要理由,而父权是天然的培育所。在古代,东西方的统治者对此都有异常清醒的认知,都会利用公权力来鼓励尊重父亲,孝不仅是传统中国的核心价值,也是古代西方的重要价值。毕竟,父亲是无法选择的,他有足够的暴力来维持一个家庭的等级秩序,这是成为臣民的入门培训,当你不得不爱你的父亲时,你就已经做好了接纳暴政的心理准备。
这就是为什么,革命往往会以“杀死父亲”为开始,因为一个人只有在心理上杀死了父亲,并将自己与父亲的关系彻底剥离开来,才有可能获得打破旧秩序的勇气,革命才拥有了她最坚定的儿女。否定父权作为标准的社会动员技术,从法国,到俄国,再到中国,一脉相承。
然而,“父爱”是现实存在的,一旦被否定,就会给人带来巨大的心理真空,需要新的价值来填补,这就为“同伴爱”的神话铺平了道路。因为相同的价值观,陌生人成为兄弟,不惜为此付出生命,在这个“同伴爱”的天空下,没有欺骗、世故、推诿、隐忍等“父爱”的缺点,却有价值至上、彼此忠诚、绝不苟且的浪漫,有了这样的替代品,“杀死父亲”也就不再那么艰难。
在这个心理置换的过程中,“男女爱”作为“同伴爱”的辅翼,往往会得到推崇,于是,革命才会有如此多余的情怀,率先投射到书面语言中,为“伊”转向“她”创造了契机。“革命加浪漫”给不谙世事的年轻人们勾勒出一个现实的乌托邦,从而最大化地激发出他们的创造力与牺牲精神。女人以为这将解放自己,男人以为这将自我实现,可结果却出人意料。
正如著名作家阿西娅·吉巴尔在《房间里的阿尔及利亚女人》中描写的那样,在谋求国家独立的过程中,阿尔及利亚女人们付出了巨大的牺牲,可当胜利到来后,她们身上的枷锁反而变得更加沉重,革命在不知不觉间背叛了她们。
其实,道理很简单,革命从未承诺过个体的尊严与价值,它是用否定的方式来重新定义自我的,否定现实秩序,对于重重压力下的女性们有巨大的诱惑力,可新秩序会如何,只有一张美丽的蓝图。现实的问题是:每次失序以及每次秩序重建,对于弱者可能都是一次莫大的伤害,可能都会成为一次对她们的公开抢劫。
历史往往由对个体的背叛写成,“她”的文化史自然也无法幸免。
就这样一步步走向极端
“杀死父亲”是一个曲折、遮蔽的过程。
以“法国大革命”为例,长期以来,我们误以为启蒙作们家的创作曾极大地推动了历史的进程,可事实上,在当时的畅销书排行榜中,《社会契约论》《法意》《波斯人信札》《爱弥尔》等名著根本无法排入前十名,只有卢梭的一本书曾位居第九,而真正把持榜单的都是黄色小说。
为逃避出版检查,当时普遍的做法是将启蒙书籍拆成散页,分别装订在色情图书内,换言之,如果你不是好色者,几乎得不到启蒙的机会,而阅读一本好书的代价是,至少要看3-4本下流小说才行。
我们以为攻占巴士底狱的是觉醒者和战士,但事实上,他们都是色情小说读者,他们一边沉浸在下流的描写中,一边走上街头,并顺手推翻了专制制度。
色情小说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力量?因为它是一种反叛,是对父权的无言对抗,它能给人以僭越的快感,毕竟,在性的层面上,所有人都是平等的。
色情是权威的腐蚀剂,在色情小说中,路易十六和他的夫人不断成为主角,特别是路易十六的夫人,被描写成色情狂,甚至连亲属、老人、孩子都不放过,这样的人还有当“国母”的资格吗?而路易十六视而不见,他还有当父亲的资格吗?对这样愚昧和失德的父母,难道还要继续服从不成?
砍下路易十六的头后,人们疯狂地冲上断头台,痛饮他的血,并互相议论着:为什么有点咸?这让革命政府极为尴尬,他们不想被世界嘲笑为野蛮人,在路易十六受戮一周年后,就是否举办庆祝仪式,高层发生了激烈的争论。最终,游行还是举行了,并且砍了四个罪犯的脑袋,以让人们重温曾经的狂欢。
类似的历程在中国近代史中同样存在,而这与“她”字生根发芽,乃至被大众接受的过程,几乎是完全同步的。
而最奇妙的,莫过于《红楼梦》的重新阐释。《红楼梦》问世后,虽然影响极大,但未被主流认可,长期背负着“诲淫”的名声。然而,戊戌变法失败后,《红楼梦》地位陡升。梁启超远避日本后,力主“文学救亡”,畅言要在诗界、文界、小说界中搞“三界革命”,梁启超们写了大量诋毁慈禧太后的文章,很多是色情小说。而到辛亥革命时期,陈悦说:“《石头记》一书,虽为小说,然其涵义,乃具有大政治家、大哲学家、大理想家之学说,而合于大同之旨。谓为东方《民约论》(指卢梭的《社会契约论》)。”认为贾宝玉“不怨”“不骄”“不忮”“不谄”“能爱”“不淫”“不怒”“不恋”,“纵观始终,可以为共和国民,可以为共和国务员,可以为共和议员,可以为共和大总统矣。”从此,《红楼梦》由世情小说陡升为政治小说。
让贾宝玉当总统,虽是陈悦一家极端的说法,但体现了当时革命者的普遍心态,他们之所以与贾宝玉“心有戚戚”,因为贾宝玉也有一个糟糕的父亲,他也向往“同伴爱”“神圣的友谊”,而他与林黛玉的爱情更是建构在“志同道合”的基础上,这是多少年轻革命者的心中向往?正是从这时开始,宝、黛形象渐渐变成了反封建战士
翻开“五四”前后的中国文学,有太多糟糕的父亲,他们要么如华老栓那样愚昧,要么如周朴园那样狡诈,要么如方遯翁那么腐朽,要么如吴老太爷那样封闭……在阶级性大于人性的借口下,父亲压榨、出卖、欺骗儿子几乎成了母题,不断被翻出新的花样,而在父亲们诸多的共罪中,破坏婚姻自由、制造爱情悲剧成了必有之旨。打倒父亲,保卫爱情,曾是太多青年人的荷尔蒙。
被背叛的“她”
然而,后来的事实却大大出乎人们的意料。
如果说,革命前人们所想象的未来,是一个更自由、人性充分解放的社会,可结果却相当令人意外:我们反而进入了一个空前的性禁忌社会中,人的生理不再完全属于自己,还要承担社会责任。在道德洁癖的秩序下,女性遭遇了更多禁忌,这与革命的初衷似乎背道而驰,可事实上,这又完全契合于革命的逻辑中。
革命建构在否定的基础上,不得不以虚构的平等为前提,但现实是,这个平等并不现实存在,人的天赋、文化、背景、机遇等天然存有差异,我们既不可能向美貌收税,也不可能平分好运气,正是由于对这个虚拟平等的恐慌感,使革命不断制造出继续革命的借口,而女人试图“成为女人”,本身就是对平等的否定,以承担国家、社会责任的名义,女性被拉入到革命进程中,而革命试图把她们改造成非女人。
面对否定与颠覆,社会中层本来是重要的稳定器,他们本应承担起捍卫并传递传统与文化的责任,可他们为何没能阻挡局面的变化呢?
可以看到,虽然在书面语中的“她”剥离过程中,学者们充当了主力,几乎所有名教授、名作家都参与到争论中,然而,在口语“她”的剥离中,只有周作人等少数人有所主张,绝大多数学者漠然视之。
这背后有两方面原因:一是传统士人阶层与社会脱节,他们互不关心,自说自话,中层本是链接上下层的力量,但明清两代残酷专制,使社会各阶层彼此孤立,信息只能在小圈子里流通;二是近代精英文化屡受冲击,传统士人的自信被彻底摧毁,他们无力领导社会,反而特别想融入到“人民群众”中,向后者“学习”。
其实,即使主张使用“她”的学者中,又有多少人真的是站在“女性的发现”的立场上呢?思想开放如鲁迅,亦不能超越世俗偏见,他多次对张竞生大加嘲讽,并说:“张竞生的主张要实现,大约当在25世纪。”
因为,那一代中国知识人生于忧患,成于焦虑,他们急于从西方文化中找到解药,无法静下心来系统地学习,这种功利心态使他们的知识不系统、认识偏肤浅。鲁迅崇尚自由,却反对自由主义,胡适高呼实用主义,却错误理解了杜威的思想,达尔文明确提出不同意将生物学的进化论引入社会学领域,可他却成了中国人眼中的思想家,严复主张系统学习西方文化,可他的《天演论》却突破了赫胥黎的原文,完全在谈自己的观点……
现实的压力使他们在介绍西方文化的同时,却又在误会、歪曲、否定西方文化,西方文明是在其本土环境中博弈而形成的,截取其只言片语,硬性移植过来,必然丧失其原有的生命力,成了只有形式没有灵魂的空架子。可以看到,当时绝大多数留学西方的中国学人在学术上的成绩无法超越其师,可知他们已陷入了集体性的惶惑中,无力自拔。
书面的“她”作为变革成果被继承了下来,而口语的“她”则还没有扎下自己的根。从参与,到边缘化,再到遭遇背叛,女性在文化上、精神上乃至社会地位上,离真正平等还遥遥无期,而当一个社会连这个基础层面的平等还无法实现,则更多的道义诉求难免被虚化、被延宕、被忽略。
其实,百年来上下求索而迷失初心的,又何止是一个“她”字。
,免责声明:本文仅代表文章作者的个人观点,与本站无关。其原创性、真实性以及文中陈述文字和内容未经本站证实,对本文以及其中全部或者部分内容文字的真实性、完整性和原创性本站不作任何保证或承诺,请读者仅作参考,并自行核实相关内容。文章投诉邮箱:anhduc.ph@yahoo.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