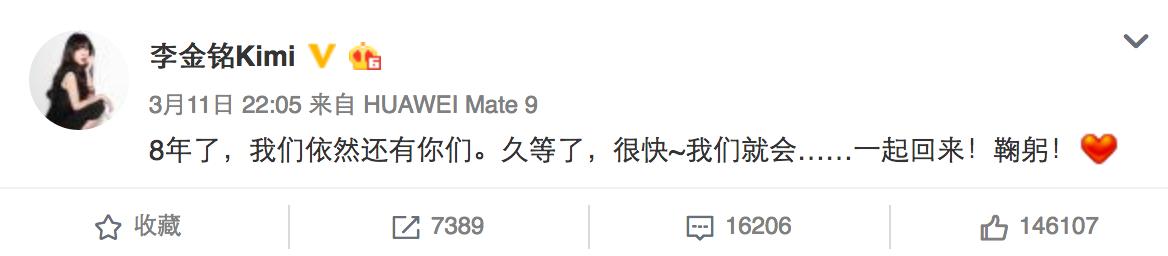马尔克斯和哪一位文风相近(想写马尔克斯没写到的爱情)
从1982年走进《收获》到现在,四十年了,程永新是中国文学现场最密切的见证者。如今已是《收获》杂志主编的他推出了写进文学史的“先锋专号”,经手发表了《活着》《妻妾成群》等名作。
其实程永新也写小说。“职业编辑”和“业余作家”是他给自己的定位。他的《到处都在下雪》是马原眼里“毫无疑问的杰作”,《穿旗袍的姨妈》被余华形容为“简洁而博大”,只是后来越写越少,几近停笔。直到2020年春节,突然到来的一段不能出门的日子,他把计划退休后要写的故事提前写了出来,这便有了最近结集出版的《若只初见》。

所有被损害、被斩断的记忆都会留下痕迹
程永新曾经认识一个“小芳”。那是在并不遥远的1976年。那一年,他高中刚刚毕业,他的母亲带着他去浙江东阳的娘家。长途汽车几经辗转后,一架木制的独轮车把他们带到了一个沪语叫“华程里”的地方。
差不多40年后,他确定“华程里”实际上是厦程里。这个村子在会稽山脉南麓东白山的脚下。当他对“小芳”朦朦胧胧的情谊被发现后,他先是被反对他的姨妈和舅舅们“软禁”在老屋,最后,干脆被送上独轮车,送出了村子,返回上海。
在那个年代,可能许多人都有个让人念念不忘的“小芳”。后来,程永新回忆起那段经历时,曾感慨“所有被损害、被斩断的记忆都会留下痕迹”,那段记忆给他留下的痕迹,是他最初的笔名“里程”,这个笔名,是他对青春期的纪念。
知名作家和批评家程德培,也是程永新的好友,在其评论程永新小说的文章《近身的美学与遥远的时光》中,引用了法国作家罗兰·巴特的一个观点“小说就是不敢说出自己名字的传记”。看到文章后,程永新认为巴特的这句话“很精彩”。程永新也很认同获得过诺贝尔奖的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所说的“小说都是从回忆出发”。
对“小芳”的记忆,在他的一篇叫《他乡》的短篇中可以看到踪影。他的同名中篇集《若只初见》,则有他其他回忆的影子。
“女王教会我如何换位观察世俗与禁忌的关系”
《若只初见》中的人物“大师兄”,程德培认出其原型是他们共同的一位兄长似的朋友。《若只初见》的“我”是大学毕业后分配到出版社,而作者是大学毕业后分配到《收获》杂志社。小说讲述的是“我”和“青青”的故事。小说中的“青青”有三个,其中一个,和“我”没什么关系,另两个,一个是古筝女王,一个是女教师。
古筝女王是一号女主角,经常在一家星级酒店的大堂吧演奏古筝,有时候,她直接被称呼为“女王”。女王似是情场高手,在和“我”的感情中出没自如。和女王一对照,“我”就是情场小白。女王是其和“我”的关系的主宰者,作为王,她甚至丝毫不顾及“我”的感受。例如,他们在某个活动中接触到了一个导演,女王首先问“我”是否会一直对她好,得到肯定的答案后,说了让“我”脑袋一下炸了的一句话:“你要对我好的话,就让我和他谈一场恋爱。”
女教师青青,是位业余诗人,她是在女王从“我”的世界里消失的那段时间出现的,在女王重新出现前,离开“我”去日本寻找她的归宿去了。女王短暂重现后,很快又不知所终。这时,第三个青青亮相了,她是“我”的一个朋友的妻子,和“我”没任何瓜葛的这个青青后来去九华山出家了。
小说接近尾声时,“我”从女王闺密那里获知了女王重病的消息,但因为不想看到女王被岁月和疾病双重摧残的惨样而没去医院看望,闺蜜以为“我”是记恨女王,实际上“我”不仅不恨,甚至还感谢女王让“我”思考了之前不会思考的问题:“是女王教会我如何换位观察世俗与禁忌的关系,如何真实地面对自己。”
《若只初见》主体故事发生的时间虽然没有明写,但从小说中歌厅里流行的《你看你看月亮的脸》来看,故事主要发生在1990年代。
清华大学讲授美学及大众文化评说的肖鹰曾在《阿姐鼓与90年代文化》中分析了1990年代的中国:“改革的深化,打破了已经根深蒂固的个体对集体或国家的稳定的依赖感,取而代之的是必须自足自力的‘个人’观念。另一方面,面向世界的开放,把一个无限的世界天地推到人们的面前,面对这个无限的天地,个人所获得的自由和他所面临的失落,是等值的。”
这也是小说《若只初见》发生的时代背景。小说中写到“我”为香港回归而撰写纪录片剧本,1990年代程永新曾担任过纪录片《上海建筑百年》的主创,“我”的虚虚实实,让人有理由认为《若只初见》从某种程度上折射出了程永新这一代知识分子对人、对人性的思考。
无疑,女王是一个塑造得非常生动、让人印象非常深刻的人物,她有着很多的欲念,游离于伦理规则之外,不满足于一个爱人。她爱得很自由、很主动且很大胆——她视男主角“我”为精神按摩师,可以与之彻夜长谈;她直白地表达,渴望与第一次见面的导演谈场恋爱;她甚至视爱情为战争,执拗想得到年长导师的爱。
即使是当下,女王都很难获得较多的理解,非常可贵的是,程永新并未站在道德的角度对其有任何批评,相反,他在女王第一次“出场”时,安排了名曲《广陵散》。《广陵散》的旋律是激昂、慷慨的,它的出现也为女王不顾一切进行的情感冒险奏响了序曲。

对话
“我想把人性最隐秘的东西写出来”
“女性获得自由的境界难度更高”
潇湘晨报:在你的后记里面,看到你写到特朗斯特罗姆的诗集,你对他的关注是什么时候开始的?
程永新:我早年的时候,大学时期也写过一点诗歌,写得不好,但是也写过,对诗歌一直比较关注。特朗斯特罗姆的诗我特别喜欢。他写得不多,一生就200多首,可是他每一首都值得你一读再读。有一些你可能一开始还读不懂,但是慢慢地你就发觉他太厉害了,在现代诗歌里面,他真是一个大师级别的人。
潇湘晨报:从特郎斯特罗姆谈起来,主要是想问问他有没有影响你的写作?比如说他写得很少,你做编辑做了40年,但自己创作也比较少,是不是他在这方面对你有一些影响?
程永新:影响肯定是有的,你喜欢他就难免会受到他的影响。他对意象的运用,他思考问题的高度和深刻性,我做他的学生都不配。他的诗歌有好多是要慢慢消化的。我觉得中国的写作者没有完全消化他诗歌中的精髓。就我个人创作比较少,还是因为比较懒散,然后也不够专注。
潇湘晨报:你说的懒散,是不是对自己有很高的要求?
程永新:和要求肯定有关系。但是上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诱惑也比较多。我去拍过电视片,做过话剧制片人,然后也请了一年的创作假,也下海做过生意。后来发觉自己根本不是经商的材料,慢慢就放弃了。在游游荡荡中,实际上就把时间都浪费掉了。后来自己给自己做了比较准确的定位,静下心来做编辑。回过头来发觉,我的好朋友作家们坚持写作,有了很好的成就,生活也比一般人要过得好。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巨大的讽刺。
潇湘晨报:其实这也说明我们这个社会还是认可好的文本的,有好的文本,价值还是能够得到体现。
程永新:是的。这些年脑子里酝酿的东西蛮多的,但始终没写。前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我关在家里每天就是不停地看稿子。稿子看完了,我就尝试着把脑子里的一些念头写出来,比如青城山,比如邓丽君。邓丽君的资料我收集了很多,疫情之前,我还专门去了一趟清迈,去看她住过的酒店。有一个当年为邓丽君服务的服务生,我专门去跟他聊天。之前是想退休了就把它写出来,但是疫情一来,就把想法提前了。

潇湘晨报:关于从商的经历,你说是浪费了,实际上那段经验也变成了你的写作素材。
程永新:因为小说和诗歌,都是表达跟人性相关的东西。一是对人性的挖掘,一是人跟时代的关系。比如《若只初见》里面的女性,跟上世纪90年代有关。但是我用力的地方是超越这个时代,把人性最隐秘的东西写出来。
女性的命运,也是我写这篇小说时考虑得比较多的。她们的情感,她们的理想,还有人性的表露,都受到很大的束缚。社会中的不合理,对男性女性都一样。但是女性更不容易,让她获得一种自由的境界难度更高。
潇湘晨报:《若只初见》主人公说“抛开伦理,从另一个角度看,女王也许是人类探索自身命运的一个殉道者”,把她当殉道者看,这种观念是怎样形成的?
程永新:其实还是对生活的观察吧。比如说婚姻关系、爱情关系,都带着这个时代的印记。我们的社会有好多禁忌,它束缚女性,也限制和规范男性。所以我就想塑造一个形象,为了她的追求,付出了很多。这个人物不是凭空捏造的,生活当中确实存在。
另外,《霍乱时期的爱情》是我非常喜欢的一本书。马尔克斯写这本书的时候,有一个目标,想穷尽人类爱情的模样,我就想写一篇在他的范围之外的。这就是文学有意思的地方,也是文学的意义。各个历史时期都有有关爱情的名著出现,但是每个时代都还可以不停地写下去。对人性、对情感复杂性的探讨,永无止境。文学最有意思的地方,就是不停地研究探讨人的问题,人的生存问题、人的情感问题、人性的复杂。这也是我写小说时考虑比较多的。
潇湘晨报:《若只初见》,这四个字透露着一丝惋惜,是这样吗?
程永新:这篇小说原来在《江南》发表的时候,我跟主编钟求是商量这篇小说的名字时,这个名字一下就击中了我。
除了你说的惋惜之外,这个题目我特别想表达的,其实不仅是情感、情谊,还有人和人相处的伦理,等等。比如说我们一群上个世纪80年代过来的好朋友,走着走着可能就散了。这种伤感也有。它是蛮复杂的,但也恰恰是我要的。
传统作家要写的东西,我们尽可能要把它省略掉
潇湘晨报:你做编辑做这么多年,先锋的、通俗的,各种风格都接触过,为什么你会选择用很简洁、很平实的风格来写?
程永新:时代不同了。我过去写东西,会用比较多的形容词。现在必须承认,因为新媒体的出现,阅读趣味和阅读习惯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人们在阅读小说的时候,更喜欢比较准确、简洁、直击人心的作品。你去看石黑一雄的《请别让我走》,他写一个克隆人,一个长篇小说,场面处理、细节处理都非常简洁,它跟这个时代是相呼应的。
潇湘晨报:我个人非常喜欢你的一点,是你舍得舍弃一些东西,包括一些可能会很精彩的内容,让读者去自己去补充,特别是《风的形状》这篇,最能够体现这一点。
程永新:我们这次青年专号上发了一篇《盛年的情人》,是一个叫夏麦的年轻作者写的。她也是写一个爱情故事,她是学理工科的,她的思维就是点到为止。读者很聪明的,你点一点他全明白。现在思维的习惯、阅读的习惯、写作的习惯都在变化。传统作家不会去写的东西,现在的作家可能就会把触角伸到那个地方;传统作家要写的东西,现在的作家又尽可能要把它省略掉。这就是小说的一种变化,一种取舍。就像电影导演一样,拍的镜头很丰富,但是选取哪些镜头组合成我的最终目标,这个就很有讲究了。我不一定处理得很好,但是我想这应该是我们去追求的一个目标和方向。
潇湘晨报:《风的形状》感觉像悬疑题材,实际上讲述的还是时代背景对人的影响。这么一个宏大主题你用悬疑来包装和展示,是一种怎样的考虑?
程永新:这篇小说有点奇怪。上世纪90年代初我写过一个短篇,写完以后,我给苏童看,他看了以后意见说得很委婉,那个小说后来发在《雨花》上面。发表以后我发现这个故事没有写完,但是怎么重新建构,我一直在思考。这个故事写到建筑,我拍过一个纪录片叫《上海建筑百年》,我是总编剧和总策划。我们当初拍的那些建筑现在都没了,都拆掉了。从建筑里面我领悟到艺术的相通性,怎么让这个小说呈现时代、人性以及建筑的美学。这是我的一种尝试。
收在这本书里面的5篇小说,我想写出5篇风格完全不同的小说。所以《风的形状》就带了一点悬疑,一点凶杀。因为经常有好多作家朋友送我书,看了一篇,再看第二篇,第二篇和第一篇没什么区别的时候,我就没兴趣了,就不想看了。所以我集子里面,我努力地想做到每一篇风格都区别非常大,是试试自己是不是能写不同类型的小说,把我当编辑接触的那么多作家的作品文稿的一些思考和感受,在我的小说里体现出来。
潇湘晨报记者刘建勇 实习生赵婷 文佩锋
新闻线索爆料通道:应用市场下载“晨视频”客户端,进入“晨意帮忙”专题;或拨打晨视频新闻热线0731-85571188。
,免责声明:本文仅代表文章作者的个人观点,与本站无关。其原创性、真实性以及文中陈述文字和内容未经本站证实,对本文以及其中全部或者部分内容文字的真实性、完整性和原创性本站不作任何保证或承诺,请读者仅作参考,并自行核实相关内容。文章投诉邮箱:anhduc.ph@yahoo.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