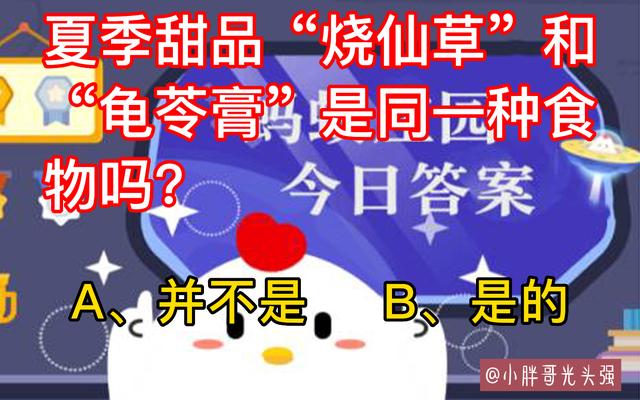我只取一朵 我只取上面艳丽的花朵

文 / 曾芷筠、林怡秀;文中人物摄影/李盈静;网站大图摄影:沈志煒Tezuka Shin剧照提供/光点影业;摄影/蔡正泰
2012年收到《聂隐娘》开镜记者会的通知,当时不少人带着「侯孝贤拍武侠片了?」的疑问,经历长达两年、拍拍停停的拍摄期,展现在眼前的《聂隐娘》脱开了武侠小说中的奇幻与速度感,拉回真实的地面,使其中的人物皆成为有血肉之人。拍摄武侠的想法,早在他大学时期读《唐人小说》时就已经植下。读过剧本的人也许会诧异,导演为何将许多交待剧情的画面剪尽?但对侯孝贤而言,「影像的魅力」包括了影像本身、人物的行为和所有种种,铺实角色关系的基础远比在镜头前的「演出」更为重要。这部以女性角度出发的武侠片,原著内容不过1700多字,却在电影中展开了一个无有同类的孤绝世界,并连结着侯孝贤过往的经历与养成。从小开始在城隍庙口「行走江湖」的侯孝贤,又如何思考唐代女性刺客的武侠世界?
看完《聂隐娘》后,很多人在讨论武侠电影类型,但舒淇饰演的聂隐娘本身的「侠」的特质很有意思,是介于侠女与刺客之间,您自己如何看待「侠」这件事?
侯孝贤(以下简称侯):侠其实各种形式都有,只要是见义勇为的义举,或是抛开私人因素、为了公益,对社会有利的事,你去做,这就叫侠。这跟刺客是两件事。像《刺客列传》里的刺客有时具有政治目的,孟子说「杀一独夫可救千百人,则杀之」。独夫就是暴君,会影响很多人。那么,侠的概念就是仗义直言,全世界都有,比如法国的三剑客。
我从小学五年级开始看武侠小说,因为我哥哥喜欢看,我负责去租,一租就是一整套。我和哥哥看的速度很快,两个弟弟跟不上,所以他们都没看,看不了多久很快就看完了。没书可看,只好等新书。以前的租书店是骑楼底下用门板搭成的书摊,用铁链锁起来,像明星咖啡屋楼下周梦蝶的旧书摊。后来,开始看黑社会侦探小说,像费蒙《职业凶手》系列。男孩子喜欢看的书都看完了,就开始看言情小说,像郭良蕙、金杏枝、孟瑶……琼瑶反而是后来高中才看的。念初中后,发现图书馆有很多书,由教育部统一购买,我记得有套书封面是灰黄底、黑色边框,中间写著书名,什么《基督山恩仇记》、《鲁宾逊漂流记》、《咆啸山庄》,后来还发现有《鲁宾逊家庭漂流记》,看了一堆,什么都想看。
但我不是只看书,每天在城隍庙附近,一群人打架、赌博。赌博是赌什么呢?我可以无聊到跟欧巴桑赌四色牌,过年时赌骰子「三六仔」,还有「十二生肖」,牌长长的,折成两半,一边包着纸,上面写着十二生肖,如果押中就一赔二,三块钱都是你的,这个数目以那时来讲很大了。更早则是玩尪仔标、弹珠、报钱……我小学时就在赌,那时候很厉害,领了压岁钱,从过年开始赌,持续两、三个月。赌博必须要很专注,我很会赢,每次都赌很久,常赌到我弟来叫我吃饭。他一叫,我如果没有撤手,一定开始输。念头一有干扰,或是空档中摸摸自己赢了多少钱,念头动一下,立刻开始输,百试不厌。后来我看一个美国赌徒写的书,他的说法也一样,一干扰就没了,你应该马上撤手。
因为从小赌博、看书、打架,在公园,跟别的地方来的人一起赌,赌了就会起冲突,冲突就会打架,通常都是因为不甘愿。打赢了,他们来找我;打输了,换我们过去找他(笑)。初中时,地方角头约在公园比拼,附近有凤山医院,晚上乌漆抹黑、没人,河水和桥过去就是大东国小。我记得我跟朋友「落咕」去大东国小探听,回来报告说没看到人,其实他们都躲在桥底下。那时候都拿刀,我们那挂人有人家里是铁工厂,那是黄金水「阿水仔」的家,偷偷打武士刀,打得很粗糙,短短的武士刀装在一截铁管上。半夜打的时候「锵!」一声,都是火花。因为他们突袭,我们退到街上,年纪比较小的就捡砖头,劈哩啪啦砸。以前这种打法都没事,顶多受伤。
我记得,城隍庙前面出去分成三条路,两旁又分成好几条,四通八达的巷子围绕一个广场。所以警察根本抓不到人,一下就全跑掉了。左边出去,有家大山戏院,还有凤山、东南亚、南台三家戏院,有名的是「军中乐园」,就是豆子(钮承泽)拍的那种,因为附近有步校、炮兵学校、卫武营部队,很多军人在那边,油水也最多,那边的帮派叫「十五郎」。长大后参与愈来愈多,高三时就去逛士官俱乐部,跟朋友四、五个人玩撞球,我就在旁边丢球玩。那时小鬼少年常被士官骂,我们就去外面找砖头砸,把玻璃门砸破,砸了就跑。警察(我们叫刑事)都知道我们,有时站在路边,他们会骑脚踏车过来噜你,我们回说「我又没怎么样!」他就一副恨不得把你们全抓走的样子。
高三时,我成绩一蹋糊涂,是不可能毕业的,上英文课都在睡觉,被留校察看。那年去台南成功大学考联考,到了别人地盘,台南那边的就来找我报仇。他低我一年级,以前转学来省凤过,跟我们也有冲突,看到我就挥手叫人来。他也蛮狠,曾经带着刀直接到我班上来,我一个人跟他到学校后面,把刀丢了,用拳头打,打完握握手就走了。那时书包里都放着大型的手指虎,自己用铁做,每天四处晃荡。
记得有次,我帮一个黄埔眷村的朋友寻仇,把计程车的保险杆拆下来打,打完后去他家,他妈妈是校长,知道我父亲,因为我父亲是县政府合作社主任。我爸在我初中时过世,但他们提到我父亲,都很尊敬,因为他做人很正直。这些《童年往事》里都有。我母亲去世后,有人欠尾会钱没缴,我跟隔壁洗衣店借了山口摩托车,载衣服的那种,跟两个城隍庙的朋友去收这条钱。一进去客厅,只放着一张行军床,很穷,外省欧巴桑出来,认出我们,我说了声「没事」,就走了。
从小到大看那么多书,经历这么些事,自己不知道什么时候养成的。假如没有看武侠小说,我可能不会这样,觉得自己好像可以帮人、可以干嘛。这是慢慢养成的,拍「侠」,基本上也是这个意思,《聂隐娘》也是这样。
图:《刺客聂隐娘》剧照。
电影中的刺客特质强调孤独,说「一个人,没有同类」,又与「青鸾舞镜」的意象有关。但您小时候大多是一群人?城隍庙与各族群帮派,好像也形成一种「江湖」。
侯:江湖就是世俗、社会,以前的武侠小说太多帮派,大江南北、丐帮少林武当峨嵋,好像每天都这些人在穿梭来去。其实以前的社会没有到这种程度,我感觉有点过头,所以我不会那样拍,而是建构一个刺客的故事。
唐朝安史乱后是绥阳围城,我们设计道姑的师父从绥阳围城中被救出来,里面人吃人、父母吃孩子,光景很惨。 《资治通鉴》中,土波(吐蕃)围攻,皇帝逃难,双胞胎公主嘉诚、嘉信被带到道家寺庙里,师父的观念就是要杀独夫以救天下。那时道教比佛教兴盛,皇族退出都会进入道教寺庙,跟日本很像。
裴铏所作的《聂隐娘》原著中,道姑本与皇族无关,据说双胞胎公主的设定来自阿城的建议,在电影中,这样的设定有一种双重、一体两面的感觉。为何这样设定?
侯:双胞胎一个是道姑,一个是嘉诚公主;一个进入道教,一个嫁到魏博。聂隐娘从小脾气非常拗,但就是很喜欢嘉诚公主,从小让她带着,跟田季安是青梅竹马。春天时,他们会去郊外一起做游玩、踢球,像这种细节建构了很多,但写了都没办法拍。嘉诚公主降嫁,没有小孩,领养了田续庶出的小孩田季安,收为养子。洺州刺史元谊带着一万军队投奔魏博,田季安虽是庶出,但需要势力,正好跟元谊的女儿联姻,牺牲了聂隐娘。
设定成双胞胎,才有可能带走聂隐娘,比较有说服力。本来剧本里写她固执到底,像亚斯伯格症,根本无法应付,最好只好请嘉信公主把她带走,因为她长得跟嘉诚公主一模一样。在田季安成年行冠礼(女子是及笄礼)这年被带走。电影虽然没有拍,但观众可以感觉到。我把人物的线索、底下的恩怨情仇全部接起来,都没拍,但底是全部建构好的。
图:道姑/嘉信公主与聂隐娘
图:道姑派聂隐娘刺杀田季安
您在访谈中提到有拍了一场双胞胎公主争论的戏,后来剪掉了?
侯:现在很容易拍一人分饰两角,但我嫌太啰嗦了,其实所有东西我们都拍了,但我感觉解释太多没味道,就想说剪掉好了,看不懂没关系。这下面的底子很厚,没有底子是做不到的,虽然都拍了,但我只取上面部分艳丽的花朵,所以电影会有一种氛围。
原著中有很奇幻的情节,比如聂隐娘投靠新主人、会法术等等,但是电影不只写实,也拍出了唐朝中央与地方的政治张力,以及情感上的政治关系。
侯:因为你拍那个谁相信啊(笑)!而且拍那个很难,我比较喜欢前半段聂隐娘被道姑带走的部分,讲了受训的过程。原著后面的情节包括看到磨镜少年,立刻说要嫁他;晚上聂隐娘在外面练习刺杀动物、杀人,父亲也不敢多问;还有可以把尸体化成黄水的化骨粉。还有更奇幻的,因为刘昌裔会算,所以聂隐娘服了他,这是什么道理?我看不懂。
电影中呈现的人际政治非常有趣也复杂。比如田季安主张与中央对立,田兴主张与朝廷和平相处,道姑与聂隐娘也是一样的。但田兴被贬谪后应该就没有威胁,为何元配夫人要派人去追杀他?且田季安与元配夫人的立场应该是相近的?
侯:田兴是聂隐娘的舅舅,父亲聂锋(倪大红饰)是押衙,就像宪兵队队长。 《资治通鉴》里写到,田季安把邱绛贬到尉县,半途派人把他活埋,以前很多这种事。田兴被贬后,田季安知道他有危险,就派聂锋护送他。
田季安的大老婆为了巩固势力,会铲除异己。双胞胎公主争执那场戏有谈到,其实道姑原本要刺杀田续,就是田季安的父亲。 《资治通鉴》记载,田续死时,手握长刀,脸呈惊怖状,因为他杀了堂兄一家才取得政权,这都有过去,跟嘉诚、嘉信公主都有关连。她们的争论是,当初嘉信公主来刺杀,被嘉诚公主挡了下来。这些人物关系、来源、历史都是有建构好的。
电影开头,画面从黑白变成彩色,声音是树叶摇曳声渐渐变大,像是暗示聂隐娘的情绪波动,让人联想到黑泽明《罗生门》。黑白到彩色之间的转折有其意涵或是技术考量?
侯:那就像是个序场,独立出来揭开序幕,讲一个刺客杀不了人的故事。另外,那个搭景用黑白会比较统一,不会有干扰,否则用彩色还要调光。那场戏呈现了聂隐娘跟师父之间的关系。声音处理本来是为了拍聂隐娘在树上闭眼倾听,然后下去杀人,但这个细节很难。本来设定聂隐娘躲在院子,听到人声渐歇,知道时间到了,眼睛一睁就「哗!」一声下去。但第一天拍这场戏,我们那位小姐(舒淇)一下来就尖叫,她很拼,也不讲自己有惧高症,所以保留声音,画面上改成她直接从外面进来,两三下解决后就走了。
上左:躲在屋梁上;上右:倾听声音中
下图:观察屋内的动静
还有个镜头让人印象深刻,是聂隐娘躲在白纱后观察田季安与瑚姬。画面中隔着纱帐,一旁烛火摇曳。这个镜头其实是聂隐娘的主观镜头。您提过,镜头大致可分成导演的主观、导演的客观、人物的主观、人物的客观等四种镜头,但这个镜头其实很暧昧,究竟是谁在看?这意味着您在镜头视角使用上有些改变吗?
侯:基本上是现场拍摄的现实。我是所有的电影观念清楚后,利用这些观念来表达你要的。到了现场,你会抓到一些你要的东西,拍摄过程你会去catch一个方式,可以自我解释,只要自己通过就可以了,剪接时做最后定案。因此镜头本身会有一种魅力,不是主观客观的限制。拍摄现场我不管主观客观,只是感觉这个角度很好,剪接时才下最后决定。
像帕索里尼(Pier Paolo Pasolini)的《伊底帕斯王》,里面主、客观镜头很清楚,但现在需要像义大利新写实、法国新浪潮那样吗?其实也未必,因为他们都在打破这些限制,你有这个概念,在表达时会有一种魅力,可以有很多想像,最后还是回到影像的结构、自己的感觉去剪。如果没有这些概念,只是一直拍他们,好像导演是神,用俯视的角度,这也是一种。影像有趣的地方是可以怎么使用?全看个人喜欢,每个人的看法、角度不同。当你揣摩这可能是她的主观镜头,就会有你的想像,比如躲在纱帐后面,看他们到底会怎样。跳回客观也无所谓,也可以拍。有时候是从主观脱离到客观,但在剪接的时候,也许主观感觉不好,就改成用客观镜头。其实这都是最后剪接时才决定,画面味道如何,完全靠直觉。我不会被这些逻辑绑住,否则最后会变得很呆板。
电影最终还是要处理细节,包括人的状态、情感。这在国外很厉害的,因为演员表达、造型都很厉害,那种观念跟东方完全不一样,亚洲还是不太行。演员本身到底有没有办法自我解释,或是意识到人物的关系?我感觉还是很困难,而且很平面。台湾电影还是不够,不管是深入到学理结构上的,或是纯粹感觉的。所以,镜头使用、影像表达上还是不太一样,这是长年累积的文化,亚洲对艺术的涵养还是不够深邃。
对我来讲,我可以这样、那样拍,剪接时我再挑,自己感觉可以就可以,千万不要一板一眼,或是一定要主观、客观镜头。影像以好看、动人为原则,因为影像可以独立出来,它本身有种魅力,在剪接时我会一一琢磨。
用物质表达人物状态似乎是亚洲独有的美学,像美国、欧洲电影,重点在演员身上;您的电影中,例如《童年往事》中的邮票、《聂隐娘》中的纱帐与道姑身后的白雾山岚,都是在用物隐喻人物的情绪。这也许跟演员表达困难,或东方人比较内敛有关,您自己怎么看这些物质性的暗示?
侯:这是不自觉的,如果自觉就很惨。不自觉有个好处,什么地方有什么状态,你看了觉得新鲜,就会想拍。聂隐娘辞别师父的那个镜头,她站在山边,那座山有2800公尺高,底下是个很深的谷,远看对面的山形状很奇特,云就从下面呼呼地上来,看到云很自然就拍了,好像拍了两个镜头就OK了。所以,你是直接在现实中靠直觉捕捉,这感觉很过瘾。美国电影工业可以做到所有技术,包括演员、特效、摄影机运动,或几台摄影机同时拍摄;但我们不是,有时你设计了一个镜头,但演员做不到,干脆拿掉吧!没办法,所以变成现场的状态,你感觉很过瘾就拍。但事后回去看毛片,又感觉不行,这种情况也有。
所以,一定要在现场反应、反射,而不是按照分镜拍。我们以前只有一部机器,现在有两部,数位化后早该摆脱器材限制。台湾有时还是太想着戏剧、剧情,一天到晚在想戏剧性,反而影像的魅力、空间的味道没了,所以很难看,这是跟外国最大的差别。演员表演、电脑特效、临时演员在美国都是基本配备,所有东西都是安排设定好的,跟我们这种土法炼钢不同。没办法,电影工业不到,差太远了。
这次还是用胶片拍,拍完再过数位,这是我破天荒用最多胶片的一次,总共44万呎。以前因为胶片贵,一部片只有1万呎,日本制片厂还会在门口贴公告,让大家知道小津安二郎拍片到现在第几天、总共用了多少胶片,以前是这样的。
图:剧组工作照。
片中的台词混杂文言、口语,贵族与市井小民的词汇、口音又明显有差别,在语言与台词上您是怎么考证或设想的?
侯:以前怎么说话,谁也不知道。文言文是用写的,上朝时官员拿笏板,字是用刻的,所以要简洁清楚,不可能啰嗦。文言文是文,不是语言,在电影里还原腔调、语言也没意义。 《海上花》还可以用方言,方言有自己的特殊性,普通话是后来才有的,发音也是晚近才统一起来的。
电影中的讲话,我只是让它稍微文一点,朝廷上讲话与一般不同。田季安可以粗鲁,底下的官一定要文雅,使用非常简洁的语言,不像现在咿呜啊呀的。
谢海盟跟她老爸一样,记忆力特厉害,现场什么对不对,问她就知道。她研究唐朝的称谓,比如父亲叫「阿爸」,就是后来的闽南话。闽南话其实是古汉语,仔细想想,我们讲「失礼」,多文哪!我们听惯了觉得很口语、很台湾,其实不是。
您长年合作的编剧朱天文在电影完成后,在文章中提及,电影最后呈现的聂隐娘,已经跟一开始的构想不同,似乎从编剧到导演的构想有些落差,您怎么看?
侯:哦!本来就是这样子呀!任何在脑子里想像、讨论的,最后落实都会遭遇现实面,这是一定的。如果要完全按照最初的想像,只有美国啰!就像《骇客任务》那样,虚拟世界讲半天听不懂,一画出来全都懂了。
要呈现脑海中的想法,我拍摄时会尽量维持基调,但最后的选择还是在剪接的时候,没办法按照工程一步步来,光演员就做不到,台湾没有办法。不如放开交给演员,用直觉去捕捉现场的氛围。
圖:侯孝賢。(攝影/李盈靜)
【版权声明:此文刊于《放映週報》第522期“影人”专栏,原文链接:funscreen.tw/headline.asp?H_No=580#】,
免责声明:本文仅代表文章作者的个人观点,与本站无关。其原创性、真实性以及文中陈述文字和内容未经本站证实,对本文以及其中全部或者部分内容文字的真实性、完整性和原创性本站不作任何保证或承诺,请读者仅作参考,并自行核实相关内容。文章投诉邮箱:anhduc.ph@yahoo.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