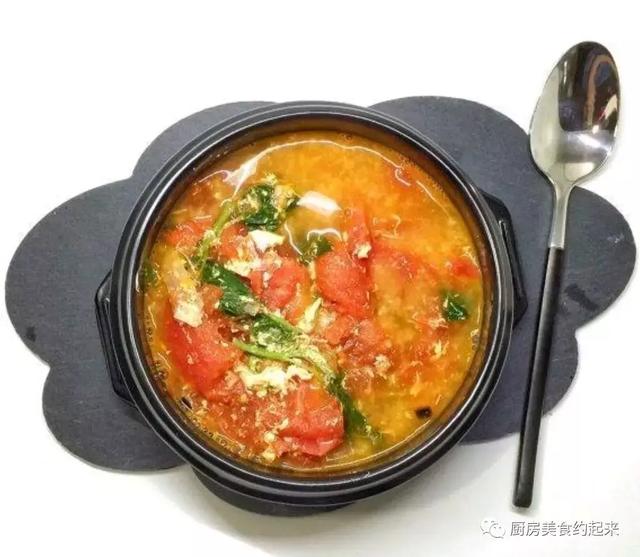童年的交通(儿时走过的五七道路)
记得那是1970年,我家当时住在抚顺北站新华大街一个好似日式或者俄式三层楼房的三楼(是那种有屋脊带瓦的),当时那个年代有个说法叫做下乡走“五七道路”,父亲也在走“五七道路”其列,之后我们全家带着家当也就随着父亲一路颠簸也没有记住坐了多久的车,就稀里糊涂搬到抚顺县章党公社新屯村依稀记得当时到新屯下乡的有五户人家,大队共计给盖了两排泥篦子草房,前排一家第二排四家,我家住在第二排的东边我家一进屋左边就是一个大锅台(这种锅台就能做饭,又能利用做饭火的热度加热大炕取暖),再往里走是两个南北大炕,西山墙有个小炕链接南北大炕,整个屋子没有间壁,完全是敞开那种,只要妈妈一做饭那是满屋蒸汽、烟气整个村子东、北、西三面环山,南临抚顺大伙房水库,分上屯和下屯,我家住在上屯上屯后山有个很高的山,山下有个军工厂,在山里挖了几条大山洞,是那种可以通小轨道的小火车,小时候去看过几次,可惜不让往里看,留下一点小遗憾下屯挨着大伙房水库边,村口有两个碑楼,相距能有四五米距离,外表灰色罩面,楼内还有碑文据父亲说此碑楼是由当时本地有个大土匪地痞张作相所建,张作相与马龙潭、吴俊升、冯德麟、汤玉麟、张景惠、孙烈臣、张作霖拜把兄弟,虽说此人为土匪,但当时对本地老百姓还是可以,也许为了积德或许其它原因,建了这两座碑楼,这个碑楼离水库边缘比较近,每年一到雨季水大时都会时都能蔓延到村头,离此碑楼不是太远因为我家祖坟还在这个村,所以我每年清明节都回去扫墓,年年都能目睹一下碑楼,至今保存尚好,现已经被文物单位保护起来了小山村的春季来临时被绿草和早春急忙绽放的花丛围绕,当漫山遍野的绿都茂盛起来时候,我们时常三五几个小伙伴去田野山间去采一些山野菜,有酸桨桨(发音)、猫爪子,应该有好多种山菜,但是小时候就记住这两个山菜的名字那时候孩子没有现在这么娇贵,刚到农村第二年七八岁就和当地农村小伙伴们戏耍着穿越山沟田间,因为那时候还不认识一些山野菜,我是基本跟着他们屁股后边一个一个识别各种山野菜,后来逐渐熟悉了,每次都会采一些山野菜喜悦的拿回家,妈妈看到非常高兴,因为这是我的劳动成果到了种地季节,我时常跟着妈妈去大队分给我家在后山的几分田地干活(我家是带着城市户口下乡,还吃城里的供应粮,所以分的很少一部分地),虽然很小干不上什么重活,但是时不时的也能帮妈妈打个下手,陪妈妈做个伴,也会体验那种不一样的乐趣,起码到了收获季节也会感觉到丰收的快感心情当时走“五七道路”的五家共有我这么大的男孩还有两个陈平、张勇,我们算是最铁的小伙伴,基本每天形影不离记得离我家东面不远处有条小河,垒了个小河坝,垒完之后河水能有半米深,到了盛夏季节,我们几个小伙伴都是光着屁股出溜一下扑倒水里,把那些在水中啄食游玩的鸭子、大鹅啊,统统哄跑,就被我们这些七八岁也不知道害羞光屁股小孩占领,在水中相互戏耍撩水打闹,玩的好一个热火朝天秋季是收获的季节,此时的农村到处都是打扬场面,看着大人们头裹毛巾使劲踏动脱粒机的踏板,让脱粒机棍子飞转,然后他们手里握着一小捆一小捆带谷子的稻穗往飞转的轮子送,瞬间天空弥漫着乌烟瘴气抽打谷子所带起的灰尘,金黄色的稻粒纷纷被打脱到地面,不多时地面上堆积起一片一片波浪式的颗粒谷子那时候还没有现在这么高的机械化程度,每一道造作工序都得农民亲手完成,真是每一个稻粒都是农民辛辛苦苦的汗滴换来的,正所谓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还有一种打扬是我那时非常喜欢跟着大人一起干的,就是黄豆打扬,事先找个平整干净的场子,清理地面上的石子,把晒干后豆夹的均匀铺开,再把牲口(马、驴、骡子都行)套上,后边牵引一个用青石表面刻成纹路的石磙子,然后赶着牲口来回转圈,在豆子上碾压,一圈一圈走啊,慢慢豆粒就从豆瓣中被挤压出来也许那时候在农村小孩没有什么好玩取乐的事,当时感觉挺好玩的,我就偶尔求打场的人让我帮着他赶一会牲口在豆子场上转圈,挺有乐呵的打场是个慢活,要来回翻弄地面上的豆荚,保证碾子压到所有的豆荚,这样提高出豆率有时候帮忙完,大人会奖励我些黄豆,这把我高兴坏了,屁颠屁颠跑回家,让妈妈炒黄豆,那个年代能吃上炒黄豆也是非常享受的呦一晃秋季收获忙碌完了,冬季也就悄悄来临了东北农村一般家家户户在快要在进入冬季时候去山里松树林下挠几立方松树枝,因为深秋的松树枝特别干燥,绝对是冬季家里烧火非常好的火引子,只要一根火柴,那松树枝就会腾腾的燃烧起来,火苗那个旺啊一会就把劈材点燃持续燃烧,这时候也就是妈妈开始做饭了,伴随菜饭熟了之后,屋里火炕温度也上来了,室内也就暖和了,这时也是躺在家里的火炕上特别舒服的时刻,适合的温度通过贴在火炕身体处传遍全身暖融融的,好美好幸福到了大雪纷纷的季节,农村的木爬犁可是派上用场了,最主要的是上山运输烧火用的树枝树杈,其次就是我们这些孩子冬快乐无比的娱乐项目当大雪覆盖漫山遍野时候,我曾随父亲去过山里砍劈材,记得爸爸把树枝、树杈砍下来或锯下来,然后把这些劈材一捆一捆的捆起来顺着堆满积雪的山沟往下拽,这样非常省劲,等把这些劈材全部拽下来,在一捆一捆固定的爬犁上,全部码好后,就看爸爸把一根绳子斜跨在肩膀上顺着山间小路就像革命的老黄牛一样拉着前行像一般人家一个冬天怎么也得准备七立八立劈材越冬做饭取暖,还的适当备一些苞米杆,这样一冬天就可以舒舒服服的过去了七十年代那时候的气候,一般在进入冬季一月份左右,山区地面上的雪就比较厚实了,这时候我们就三五成群的拽着爬犁登上我家西面的小山岭,当时和我最好的儿时伙伴一起来走“五七道路”来的陈平、张勇和当地农村家的小友,我们几个总是坐在一个爬犁上,顺着山坡往下放,用脚调整爬犁前行的方向,随着山坡的马路一路狂奔下去,速度真的挺快,当时也不知道害怕啊如果发生翻滚或者侧翻那是非常危险的,很容易造成身体伤害,也许就是因为那个年龄段不知道什么危险,所以才有很多刺激的快乐那个年代对于农村的孩子放爬犁绝对是冬天最愉快的游戏,一玩就是小半天,大部分都是造的满身雪和土尘,带着有点疲惫的身体拽着爬犁欢快回家,至于被父母挨说不挨说都不在考虑之内,反正那次都得挨说,但是心理偷偷的开心啊当时我家在农村条件比那些当地农民还是强点,因为我家还有城市供应粮食,大队还能分配一些粮食,所以那时候家里生活条件吃的还是稍有一点富余(当然也就苞米面富裕一些,细粮肯定不够吃),时常有些剩饭剩菜都倒进一个大缸里(有个俗称发音叫盖水缸),正是因为这些剩饭剩菜在加拌些苞米面,我家养了两年多的猪长的还算膘肥体壮达到二百多斤农村都有过年杀猪的习俗,在一九七二年春节前夕,我家决定杀一头猪过年,再给住在市区搭连的姥姥家送点年货依稀记得当时过来帮忙就有七八个人,农村可能都这样,谁家有个事,特别杀猪的好事,肯定不缺乏人手,再加上还有要请的人,最后我家弄了两桌猪肉全席宴,什么血肠、肥肠、排骨炖酸菜、肥肉片炖酸菜等等吧,当时可没有现在时令性蔬菜那时候不但是农村,就是城市家庭冬季的蔬菜无怪乎就白菜、酸菜、土豆、大萝卜、绿萝不、红萝卜这些可冬季存储的菜可怜啊这一顿胡吃海喝吃了不少我家的猪肉,年少的我看的好心疼啊因为那都是我妈妈辛辛苦苦一舀子一舀子盖水加饲料喂出来,几百天才长到二百多斤的猪,当然这是小孩的思维一晃农村生活的几年光景过去了,1972年开春之时,我洒泪送走了我的下乡儿时好友陈平,他随着他父亲落实回城计划回到湖南老家去了,我想这辈子我们一别,天各一方肯定再见不到了,现在偶尔还想起我的好友陈平过了不久,市里上级单位通知父亲可以回城了,也许当时国企比政府机关收入多些吧,我爸爸就选择去了国企化纤厂,而没有回到政府机关回城之时,我清晰记得从农村带走了两只鸭子,几只鸡,其中鸭子我起的名一个叫白脖、一个大麻鸭,鸡我只记住一只叫鼓鼓头,因为这几个家禽是我平时最喜欢的,也是我经常爱和它们追逐玩乐的,这几只家禽伴随我很多年,给我家下了很多鸭蛋鸡蛋,也算为我家生活的改善立下了汗马功劳随着厂子派来的搬家的嘎斯带箱的板车,虽然也就二三十公里的路程,在那时的公路实在太难行走,再加上车上都是物质足足颠簸了近两个小时,终于来到回城第一个居住地~章党,完成了两年多的农村生活时间流去的好快,再过几年我也就到了花甲之年我也像常人那样,经历人生必有的各个阶段,上学考学工作结婚生子,但是我的人生旅途相比父辈要坦途平顺很多,幸运很多慢慢的人生路总有让你难以忘却的回忆,特别是儿时对你触动最深的那种感觉,是那种心灵深处占有的情愫,时不时就会冒出来,让我回忆起儿时走过的“五七道路” ,今天小编就来说说关于童年的交通?下面更多详细答案一起来看看吧!

童年的交通
记得那是1970年,我家当时住在抚顺北站新华大街一个好似日式或者俄式三层楼房的三楼(是那种有屋脊带瓦的),当时那个年代有个说法叫做下乡走“五七道路”,父亲也在走“五七道路”其列,之后我们全家带着家当也就随着父亲一路颠簸也没有记住坐了多久的车,就稀里糊涂搬到抚顺县章党公社新屯村。依稀记得当时到新屯下乡的有五户人家,大队共计给盖了两排泥篦子草房,前排一家第二排四家,我家住在第二排的东边。我家一进屋左边就是一个大锅台(这种锅台就能做饭,又能利用做饭火的热度加热大炕取暖),再往里走是两个南北大炕,西山墙有个小炕链接南北大炕,整个屋子没有间壁,完全是敞开那种,只要妈妈一做饭那是满屋蒸汽、烟气。整个村子东、北、西三面环山,南临抚顺大伙房水库,分上屯和下屯,我家住在上屯。上屯后山有个很高的山,山下有个军工厂,在山里挖了几条大山洞,是那种可以通小轨道的小火车,小时候去看过几次,可惜不让往里看,留下一点小遗憾。下屯挨着大伙房水库边,村口有两个碑楼,相距能有四五米距离,外表灰色罩面,楼内还有碑文。据父亲说此碑楼是由当时本地有个大土匪地痞张作相所建,张作相与马龙潭、吴俊升、冯德麟、汤玉麟、张景惠、孙烈臣、张作霖拜把兄弟,虽说此人为土匪,但当时对本地老百姓还是可以,也许为了积德或许其它原因,建了这两座碑楼,这个碑楼离水库边缘比较近,每年一到雨季水大时都会时都能蔓延到村头,离此碑楼不是太远。因为我家祖坟还在这个村,所以我每年清明节都回去扫墓,年年都能目睹一下碑楼,至今保存尚好,现已经被文物单位保护起来了。小山村的春季来临时被绿草和早春急忙绽放的花丛围绕,当漫山遍野的绿都茂盛起来时候,我们时常三五几个小伙伴去田野山间去采一些山野菜,有酸桨桨(发音)、猫爪子,应该有好多种山菜,但是小时候就记住这两个山菜的名字。那时候孩子没有现在这么娇贵,刚到农村第二年七八岁就和当地农村小伙伴们戏耍着穿越山沟田间,因为那时候还不认识一些山野菜,我是基本跟着他们屁股后边一个一个识别各种山野菜,后来逐渐熟悉了,每次都会采一些山野菜喜悦的拿回家,妈妈看到非常高兴,因为这是我的劳动成果。到了种地季节,我时常跟着妈妈去大队分给我家在后山的几分田地干活(我家是带着城市户口下乡,还吃城里的供应粮,所以分的很少一部分地),虽然很小干不上什么重活,但是时不时的也能帮妈妈打个下手,陪妈妈做个伴,也会体验那种不一样的乐趣,起码到了收获季节也会感觉到丰收的快感心情。当时走“五七道路”的五家共有我这么大的男孩还有两个陈平、张勇,我们算是最铁的小伙伴,基本每天形影不离。记得离我家东面不远处有条小河,垒了个小河坝,垒完之后河水能有半米深,到了盛夏季节,我们几个小伙伴都是光着屁股出溜一下扑倒水里,把那些在水中啄食游玩的鸭子、大鹅啊,统统哄跑,就被我们这些七八岁也不知道害羞光屁股小孩占领,在水中相互戏耍撩水打闹,玩的好一个热火朝天。秋季是收获的季节,此时的农村到处都是打扬场面,看着大人们头裹毛巾使劲踏动脱粒机的踏板,让脱粒机棍子飞转,然后他们手里握着一小捆一小捆带谷子的稻穗往飞转的轮子送,瞬间天空弥漫着乌烟瘴气抽打谷子所带起的灰尘,金黄色的稻粒纷纷被打脱到地面,不多时地面上堆积起一片一片波浪式的颗粒谷子。那时候还没有现在这么高的机械化程度,每一道造作工序都得农民亲手完成,真是每一个稻粒都是农民辛辛苦苦的汗滴换来的,正所谓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还有一种打扬是我那时非常喜欢跟着大人一起干的,就是黄豆打扬,事先找个平整干净的场子,清理地面上的石子,把晒干后豆夹的均匀铺开,再把牲口(马、驴、骡子都行)套上,后边牵引一个用青石表面刻成纹路的石磙子,然后赶着牲口来回转圈,在豆子上碾压,一圈一圈走啊,慢慢豆粒就从豆瓣中被挤压出来。也许那时候在农村小孩没有什么好玩取乐的事,当时感觉挺好玩的,我就偶尔求打场的人让我帮着他赶一会牲口在豆子场上转圈,挺有乐呵的。打场是个慢活,要来回翻弄地面上的豆荚,保证碾子压到所有的豆荚,这样提高出豆率。有时候帮忙完,大人会奖励我些黄豆,这把我高兴坏了,屁颠屁颠跑回家,让妈妈炒黄豆,那个年代能吃上炒黄豆也是非常享受的呦!一晃秋季收获忙碌完了,冬季也就悄悄来临了。东北农村一般家家户户在快要在进入冬季时候去山里松树林下挠几立方松树枝,因为深秋的松树枝特别干燥,绝对是冬季家里烧火非常好的火引子,只要一根火柴,那松树枝就会腾腾的燃烧起来,火苗那个旺啊!一会就把劈材点燃持续燃烧,这时候也就是妈妈开始做饭了,伴随菜饭熟了之后,屋里火炕温度也上来了,室内也就暖和了,这时也是躺在家里的火炕上特别舒服的时刻,适合的温度通过贴在火炕身体处传遍全身暖融融的,好美好幸福。到了大雪纷纷的季节,农村的木爬犁可是派上用场了,最主要的是上山运输烧火用的树枝树杈,其次就是我们这些孩子冬快乐无比的娱乐项目。当大雪覆盖漫山遍野时候,我曾随父亲去过山里砍劈材,记得爸爸把树枝、树杈砍下来或锯下来,然后把这些劈材一捆一捆的捆起来顺着堆满积雪的山沟往下拽,这样非常省劲,等把这些劈材全部拽下来,在一捆一捆固定的爬犁上,全部码好后,就看爸爸把一根绳子斜跨在肩膀上顺着山间小路就像革命的老黄牛一样拉着前行。像一般人家一个冬天怎么也得准备七立八立劈材越冬做饭取暖,还的适当备一些苞米杆,这样一冬天就可以舒舒服服的过去了。七十年代那时候的气候,一般在进入冬季一月份左右,山区地面上的雪就比较厚实了,这时候我们就三五成群的拽着爬犁登上我家西面的小山岭,当时和我最好的儿时伙伴一起来走“五七道路”来的陈平、张勇和当地农村家的小友,我们几个总是坐在一个爬犁上,顺着山坡往下放,用脚调整爬犁前行的方向,随着山坡的马路一路狂奔下去,速度真的挺快,当时也不知道害怕啊!如果发生翻滚或者侧翻那是非常危险的,很容易造成身体伤害,也许就是因为那个年龄段不知道什么危险,所以才有很多刺激的快乐。那个年代对于农村的孩子放爬犁绝对是冬天最愉快的游戏,一玩就是小半天,大部分都是造的满身雪和土尘,带着有点疲惫的身体拽着爬犁欢快回家,至于被父母挨说不挨说都不在考虑之内,反正那次都得挨说,但是心理偷偷的开心啊!当时我家在农村条件比那些当地农民还是强点,因为我家还有城市供应粮食,大队还能分配一些粮食,所以那时候家里生活条件吃的还是稍有一点富余(当然也就苞米面富裕一些,细粮肯定不够吃),时常有些剩饭剩菜都倒进一个大缸里(有个俗称发音叫盖水缸),正是因为这些剩饭剩菜在加拌些苞米面,我家养了两年多的猪长的还算膘肥体壮达到二百多斤。农村都有过年杀猪的习俗,在一九七二年春节前夕,我家决定杀一头猪过年,再给住在市区搭连的姥姥家送点年货。依稀记得当时过来帮忙就有七八个人,农村可能都这样,谁家有个事,特别杀猪的好事,肯定不缺乏人手,再加上还有要请的人,最后我家弄了两桌猪肉全席宴,什么血肠、肥肠、排骨炖酸菜、肥肉片炖酸菜等等吧,当时可没有现在时令性蔬菜。那时候不但是农村,就是城市家庭冬季的蔬菜无怪乎就白菜、酸菜、土豆、大萝卜、绿萝不、红萝卜这些可冬季存储的菜。可怜啊!这一顿胡吃海喝吃了不少我家的猪肉,年少的我看的好心疼啊!因为那都是我妈妈辛辛苦苦一舀子一舀子盖水加饲料喂出来,几百天才长到二百多斤的猪,当然这是小孩的思维。一晃农村生活的几年光景过去了,1972年开春之时,我洒泪送走了我的下乡儿时好友陈平,他随着他父亲落实回城计划回到湖南老家去了,我想这辈子我们一别,天各一方肯定再见不到了,现在偶尔还想起我的好友陈平。过了不久,市里上级单位通知父亲可以回城了,也许当时国企比政府机关收入多些吧,我爸爸就选择去了国企化纤厂,而没有回到政府机关。回城之时,我清晰记得从农村带走了两只鸭子,几只鸡,其中鸭子我起的名一个叫白脖、一个大麻鸭,鸡我只记住一只叫鼓鼓头,因为这几个家禽是我平时最喜欢的,也是我经常爱和它们追逐玩乐的,这几只家禽伴随我很多年,给我家下了很多鸭蛋鸡蛋,也算为我家生活的改善立下了汗马功劳。随着厂子派来的搬家的嘎斯带箱的板车,虽然也就二三十公里的路程,在那时的公路实在太难行走,再加上车上都是物质足足颠簸了近两个小时,终于来到回城第一个居住地~章党,完成了两年多的农村生活。时间流去的好快,再过几年我也就到了花甲之年。我也像常人那样,经历人生必有的各个阶段,上学考学工作结婚生子,但是我的人生旅途相比父辈要坦途平顺很多,幸运很多。慢慢的人生路总有让你难以忘却的回忆,特别是儿时对你触动最深的那种感觉,是那种心灵深处占有的情愫,时不时就会冒出来,让我回忆起儿时走过的“五七道路”。
相信那个年代一定和我还有同样经历同龄人,也一样有触动心灵深处的那种情愫。
2021年2月23日
,免责声明:本文仅代表文章作者的个人观点,与本站无关。其原创性、真实性以及文中陈述文字和内容未经本站证实,对本文以及其中全部或者部分内容文字的真实性、完整性和原创性本站不作任何保证或承诺,请读者仅作参考,并自行核实相关内容。文章投诉邮箱:anhduc.ph@yahoo.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