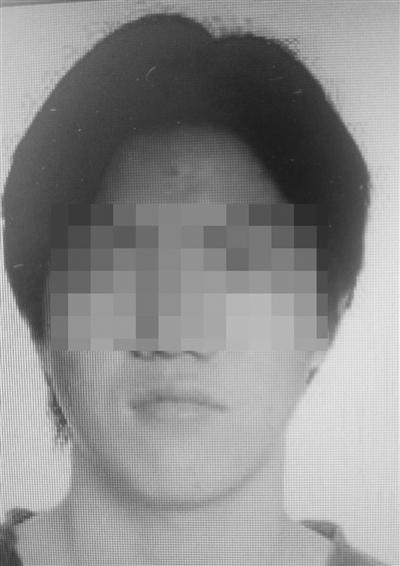清华梅贻琦奖学金是多少(先听岳南老师讲讲清华校长梅贻琦的故事)
小编注意到,2022年高考本科一批录取工作已经结束,大家都考取心仪的学校了吗?清华大学想必是许多学子心中的“白月光”,而说起清华,就不得不提到一位老校长,他就是“生斯长斯,吾爱吾庐”的梅贻琦。

梅贻琦
1962年5月19日,清华校长梅贻琦先生病逝于台大医院,享年七十三岁。当时的祭文用“天之将丧斯文”来追悼他,而教育界以“原子开新运,士林哭大师”来怀念他。梅贻琦去世后,被葬于新竹清华大学校园内,那片区域被取名为梅园。中国教育界一代名宿,连同一个伟大的灵魂,就此长眠于地下。
没人愿意倒梅(霉)梅贻琦生于天津,毕业于天津私立第一中学堂(南开中学前身),后考取庚子赔款留美生,赴美国伍斯特理工学院就读电机工程系,于1914年夏毕业,获电机工程学士学位。这年暑期,梅贻琦作别留美的同学好友,乘船归国。次年秋,受清华校长周诒春之邀,梅贻琦来到北京清华园出任物理教员。这便是他与清华师生结缘之始。
清华大学的前身是1911年北京郊外清华园内创办的清华学堂,继之是清华学校,再继之是1928年北伐之后挂牌的国立清华大学,直到1931年底,梅贻琦才继任清华大学校长。
自清华学堂创办到梅贻琦始任校长的二十年间,国家动荡,清华不安,校名三更,校长也更换了十个。其中,主校最久者为周诒春,任期四年五个月。较短者为温应星,此人毕业于西点军校炮兵科,归国后被奉系军阀张作霖派到清华当校长,是为武人主校之始。温应星和后来的吴南轩,任期皆不到两个月就退出舞台。短者为乔万选,是军阀阎锡山派的一个小军阀,刚进校门即被学生赶出,任期约为一分钟。最短者为罗忠诒,未出家门即被拒,任期几等于零。在校长被驱逐之后的许多个时期,清华处于群龙无首状态,一切事务得益于多年形成的惯性或校务委员会出面维持。
1931年“九一八”事变前的几个月,吴南轩校长被师生赶走,地质学家翁文灏出任清华代理校长。“九一八”事变后,翁文灏撂了挑子,清华又处于群龙无首状态。就在这个国家和民族以及学校最艰危的时候,正在美国担任留学生监督的梅贻琦奉召回国,出任国立清华大学校长。
其时,梅贻琦已在清华任教十六个年头。他从一个普通的物理教员升至系主任、教务长、代理校长、清华大学驻美国留学生监督,直至这时坐上校长的位子。

中年梅贻琦
清华校史研究者黄延复、钟秀斌在《一个时代的斯文》中说:“过去有一种传说,说梅出任清华校长,也是蒋介石亲自指挥的,由此还‘派出’许多‘演义’性的情节。其实这都是不确的。尽管蒋介石确曾亲自干预过清华事务,也亲自指派过清华校长(罗家伦、吴南轩,以及担任‘临时校长’的翁文灏),但梅出任清华校长却与蒋介石无干。当时梅贻琦还是个‘小人物’,在蒋介石那里根本挂不上号。引荐梅出任清华校长的,确有一个‘中枢人物’,那就是在1931年下半年接替蒋介石出任教育部长的前中法大学校长李书华。”
黄、钟二位先生所言大体不差。时值“九一八”事变爆发,全国学潮汹涌,清华学生会借机向教育部及最高当局发难,多次发表声明,宣称清华校长人选标准必须具备以下五个条件:一、无党派色彩;二、学识渊博;三、人格高尚;四、确能发展清华;五、声望素著。在学生胁迫与清华校内外声势压力下,南京政府鉴于国破家亡的危急形势,不敢轻易往清华派校长,以避免引起更大动荡与风潮。经反复物色权衡,他们终于把目标投向了远在大洋彼岸、悄无声息、蛰伏隐忍的梅贻琦。在得到梅的同意后,教育部部长李书华果断颁布了训令。自此,梅贻琦在历史的夹缝中脱颖而出,动荡不安的清华终于迎来了一位与众不同的校长,国立清华大学迎来了梅贻琦时代。
梅贻琦担任校长后,国难日重,学潮更加凶猛,威逼校长、教授之事时有发生,奇怪的是,校长梅贻琦不但没有在学潮中被驱赶,反而,激进分子在提出“打倒某某某”的口号或标语时,后边还要补上一句“拥护梅校长”。
自1931年上任,到1948年底被迫离开北平,梅贻琦任清华校长达十七年。这么长的时间里,梅贻琦一直深受师生拥护,对此,清华出身的钱思亮深有感怀地说:“那时期清华校长连年更迭,学校很不稳定,校长很少做得长久的,自从梅先生接掌以后,就一直安定下来,就只这件事在教育史上已是不朽。”
当有人问梅贻琦有何秘诀令学生如此敬佩爱戴时,他说:“大家倒这个,倒那个,就没有人愿意倒梅(霉)!”这当然是一句玩笑话,也是梅贻琦为之自豪之所在。梅校长之所以赢得师生的广泛敬重,自有他的过人之处,或者说内含玄机。
校长是为教授搬凳子的人我国早期的官办大学都是当衙门办的,无论是由京师大学堂演变的国立北京大学,还是由清华学堂演变的国立清华大学,甚至后来南京的国立中央大学,无不如是。
在梅贻琦上任之前,清华的衙门习气虽有不同程度的收敛,但仍残存不消。周诒春校长算是开明的校长,但仍保持衙门的一套:上午基本躺在床上抽烟不起床,若需要拟档或条例等,就传唤秘书来到床前,他一边吞云吐雾,一边断断续续说着,秘书一一记录,整理后传达全校。即便是北伐成功后的罗家伦接手清华后,也把教授看成是无职无权、随便开革扫除的过河卒子,梅贻琦都曾被他扫地出门,流放海外;清华国学院主任吴宓教授,对其做派都胆战心惊,小心谋划应对,唯恐也被扫地出门。清华早期的体育是很有名的,后来在马约翰教授带领下就更厉害了,但罗家伦认为体育一科的教头如马约翰、周更生等,就是一个低贱的体育教员,并下令革掉马约翰等人的“教授”帽子,且降低薪水,如同一般职员对待。不过,此事引起了清华师生的同情与愤怒,罗家伦也因此官僚做派很快被教授和学生联合赶出了清华园。
梅贻琦出任校长后,深刻吸取前十任校长被革职查办或被学生打跑的教训,风格大变,整个清华园面貌为之一新。他对清华教授一视同仁,唯才是举,绝不搞小圈子。此前梅贻琦被看作南开派的,有人认为他会重用南开出身的人,形成一个小团体,但他没有这样做。如此一来,清华再也没有圈子或派系存在了。
破除了圈子与派系,在个人利益方面,梅贻琦更是小心谨慎,绝不专权搞个人私利。他曾对自己的秘书说,如果有找我开后门办私事的,这类信件不必给我看,直接封存或扔进纸篓子便是。
梅贻琦公开说过“校长不过是率领职工给教授搬椅子凳子的”。这是自谦,也说明了他看待自己身份的态度和其治校理念。他把自己定位成一个为教授搬凳子的人,是因为他有一颗感恩、感激之心。他认为自己是庚款的受益者,能赴美国留学,是天之恩泽,所食之禄,是民之脂膏。他时常提醒自己:“尔所受者不是皇恩是天恩,尔所领者不是官费是民费。”因此,他学成回国服务清华,借这个平台培养后进,为国储才,则是报答国家与人民之恩。
此情此理,可通过梅贻琦自己的言论验证。如1941年4月底,值清华建校三十周年与抗战南渡昆明三周年纪念日,清华在昆明云南大学校园举行了校庆,梅贻琦作为大会主席,满含深情地说道:
母校成立,今年恰为三十周年。琦自一九零九年(宣统元年),应母校第一次留美考试,被派赴美,自此即与清华发生关系,即受清华之多方培植。三十二年来,从未间断,以谓“生斯长斯,吾爱吾庐”之喻,琦于清华,正复如之。
这就是梅贻琦给自己的身份与地位的定位,他把自己看成是受惠者、服务者、报恩者。在梅贻琦时代,清华就是一个研究学术、造就人才的高级学府,校长、师生是一体的,人格独立,各司其职,为一个共同目标而前进。这亦是梅贻琦开创的一个崭新风气。

梅贻琦书法作品
“教授治校”面对“校长治校”还是“教授治校”这个决定梅贻琦本人及清华前途命运的根本问题,梅贻琦选择“教授治校”。他抛开南京政府教育部制定的校长总揽人事大权的《规程》,重新按1926年曹云祥掌校、梅氏本人被选为教务长时,由清华教授会制定的《组织大纲》行事,即:评议会为最高权力机关,教授会担任制衡角色,校长为“王帽”,三者相互制衡监督。
在这之前和之后的梅贻琦,一直把自己当作京戏中王冠整齐、仪仗森严、端坐正中,其实并没多少戏份和唱段的“王帽”看待。这个制度一直坚持到1948年底,梅贻琦出走清华园,飞往南京的那一刻。
关于“教授治校”制度的实施是否出于梅贻琦的真心实意,经实践和教授们多年的观察来看,应是肯定的。梅贻琦对此也有过一段说明。那是1940年,清华校友在昆明为梅贻琦服务母校二十五周年召开庆祝会。会上,梅在答词中说:“诸位觉得一人在一个学校服务二十五年,应予鼓励。其实在清华服务达十年以上者,已有三四十人,十五年以上者,亦有一二十人,而马约翰先生且达二十六年之久。可见清华近些年之进展,不是而亦不能是一个人的缘故,是因为清华还有这很多位老同事,同心合力地去做,才有今日。现在给诸位说一个比喻,诸位大概都喜欢看京戏,京戏角里有一个角色,叫‘王帽’的,他每出场总是王冠齐整,仪仗森严,文武将官,前呼后拥,‘像煞有介事’。其实会看戏的绝不注意这正中端坐的‘王帽’。因为好戏——除了很少数的几出,如《打金枝》《上天台》,并不要他唱,他因为运气好,搭在一个好班子里,那么人家对这台戏叫好时,他亦觉得‘与有荣焉’而已。”
曾任清华法商学院院长的陈岱孙晚年亦解释过此事,说:“无论如何,梅在受任校长后接受了这一体制,并加以扶植……在理论上,教授会、评议会、校务会议、校长四者之间,在权限和意见上是可以发生矛盾的,但在实际上却没有发生过任何裂痕。校长是教授会、评议会、校务会议的主席,在会上梅总是倾听群众的意见,而与会的成员也十分尊重他的意见。”
这样的局面使学校的许多危机化为无形,亦让学校平安渡过许多难关。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或如朱自清所言:“在这个比较健全的组织里,同仁都能安心工作,乐意工作。他使同仁觉着学校是我们大家的,谁都有一份儿。”
“大家的,谁都有一份儿”,正是梅贻琦掌校后“大家”的共同认知和心声,也是力量集结的源泉和化险为夷、不断前行的催动力。正如清华历史系主任、后为联合国常驻代表的蒋廷黻所言:梅贻琦掌校后,清华“在他的领导下不再是个政治皮球,步上了正轨”。
当“教授治校”这块决定国立清华大学发展的柱石被梅贻琦赋予校内合法地位并夯实蹾牢后,清华这个在历史夹缝中闹腾了二十年的“政治皮球”,在正常的轨道上运行开来。

晚年梅贻琦
通识教育新理念1932年,清华大学规制已达四院十五个学系,设有航空研究所、机械工程系、电机工程系等。梅贻琦是清华“改大”的强力推进者,曾寄予清华特殊的期望和使命——“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也,有大师也”“我们理应把它办成一所世界上著名的学府”等流传于后世的名言警句,是梅贻琦于1931年底掌校第一天在清华大礼堂对全体师生讲的。之后,这些话也实实在在带来了清华的“黄金时代”。除了原有的陈寅恪、冯友兰、陈岱孙、叶企孙、叶公超、刘文典、潘光旦、吴宓、金岳霖、朱自清等大师,一群年轻的才子如陈梦家、吴晗、沈从文等纷纷云集清华园或西南联大,在当时的中国教育界形成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有了大师,继之就是如何培养和造就人才。而清华的通识教育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通识教育不是梅贻琦的发明,在他当校长之前就开始实行,一直难以落到实处。梅的南开同学张彭春在清华做教务长的时候,曾搞过类似的通识教育,但他失败了,且一败涂地,被校长曹云祥与几名教授合谋,逐出了清华园。梅贻琦掌校之后,通识教育才全面贯彻实施开来。这也是梅贻琦作为教育界巨头超前的理念在实践中的应用。
今天谈“通识教育”似乎很平常,但在梅贻琦时代,“通识教育”在清华开了先河,曾引起一阵很大的争论,喧嚣了大半年方才平息。
梅贻琦的理念很清楚,他主张:学生应先通后专,即“通识为本,专识为末”。新生入学第一年一律实施通才教育,第二年起进入各自专业领域。各学科分为必修和选修两种,成绩以学分计算,视学生能力定高低,各系毕业学生至少修满一百三十六个学分(体育除外),土木工程学系单列。如此改革的总目的是让学生有较大的选修空间,但各系学生毕业之前,须受该系之毕业考试,考试及格,方能毕业。
如今回望,清华出了那么多人才,是与梅贻琦倡导实施的“通识教育”分不开的,这也是“大师之大”“联大之大”的内在驱动力。
三个联大的不同命运西南联大虽由三所院校组成,但南开校长张伯苓与北大校长蒋梦麟不常在校,实际就是清华校长梅贻琦一人在撑持,他作为联大的常委会主席几乎贯穿了西南联大的始终。体力的劳苦不必提,精神上的劳苦也是可想而知的。西南联大之所以为“大”,与梅贻琦的“大”是分不开的。对于这一点,清华校友傅任敢曾有过一段精彩论述:
抗战起后,国内成立过好几所联合大学,可是除了西南联大一直联到胜利以后方才各自复校以外,其余全都中道夭折了。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倘若西南联大也如其他联大,因为意见不合,联不到底,那是中国教育界以至全中国国民多么重大的一件耻辱。外国人看不起中国人,说中国人是一盘散沙,是一个无组织的国家。倘若在那国难临头的时候,连智识最高的高等教育界都仍没有例外地联不拢来,一盘散沙之说岂不全盘证实,百口莫辩了吗?而其所予全体国民与下代青年的暗示又将是何等的恶劣与深远?我们又可以再想一下,为什么其他的联大通通联不下去,惟有西南联大能够联到底呢?这就与梅校长的大很有关系了。
傅氏所说的国内成立过“好几所联合大学”,主要指东南联大与西北联大。东南联大由时在上海的暨南大学为首,收拢上海、江浙一带几家专科学校师生,在福建建阳筹备国立联合大学,惜因诸方实力不一,合作困难,1943年6月2日,教育部指令东南联大文、理、商三学院并入暨南大学,法学院与艺术专修科并入英士大学,7月底所有移交工作全部结束,东南联大就此流产。
与西南联大几乎同时成立的西安临时大学,于1937年9月10日在西安开课,同年11月9日太原沦陷,日军沿同蒲路南下,西安告急并遭到敌机轰炸,临大教务长杨其昌与几位学生被炸死,师生处于极度危险境遇中。为避战乱与敌机轰炸,1938年3月,西安临时大学迁往陕南汉中城固及周边地区,4月改名为国立西北联合大学,领导体制与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一样,同为校务委员会制。国立西北联大开课不久,因校方高层几位常委以及教授之间意见不合,加之政局混乱,学生无法正常上课。7月,工学院单独设立,称西北工学院;农学院也单独设立,称西北农学院;教育学院改称为师范学院。1939年7月,国民政府教育部部长陈立夫发出指令,撤销国立西北联合大学,新成立西北大学、西北师范学院、西北工学院、西北医学院、西北农学院等五个独立国立院校。8月,西北联大正式撤销,存在时间为一年零四个月。

1939年,梅贻琦全家在昆明
对于西南、西北两个国立联合大学的差异与区别,冯友兰打过如此比喻:“梅贻琦说过,好比一个戏班,有一个班底子。联合大学的班底子是清华、北大、南开派出些名角共同演出。但是步骤都很协调,演出也很成功。当时还有一个西北联合大学,也是从北京迁去的几个学校联合起来而成的,设在陕西城固。但是它们内部经常有矛盾,闹别扭。蒋梦麟说,它们好比三个人穿两条裤子,互相牵扯,谁也走不动。”
这一形象的比喻得到了西南联大师生的普遍认同,西北联大就是在这样的历史景况和相互拉扯中被迫解散的。而西南联大在1937年至1946年间,凝聚并培育出了一大批精英,并产生了李政道、杨振宁这样斩获诺贝尔奖的杰出人物。
在昆明的西南联大之初,清华、北大、南开教职工和学生的人数比例是7∶5∶2,清华人多势众,又有庚款加持,自是最牛的一个组成部分。
这个时候,身为联大委员会主席的梅贻琦格外小心谨慎,竭力维持校内各阶层人事平衡的同时,最忌讳也最提心吊胆的就是清华在领导层人数上一家独大,或渐渐演变成一家独强甚而独霸,成为联大分裂的导火索。
联大开办之初,曾有北大教授向校长蒋梦麟提出,清华在校内高层的人数占比过多,理工科我们是甘拜下风,可文科我们并不弱,为什么不能领导群伦?文学院院长由清华的冯友兰担任,北大的汤用彤是哈佛毕业生,学问不比冯氏差,为什么不能当院长?如此等等,引来了清华与北大的矛盾与分歧。面对这一裂隙,梅贻琦尽量在联大秘书主任、教务长、总务长、建设长、训导长、图书馆长等“巨头”方面,搞三校兼顾,人事平衡,裂隙逐渐得以弥合。
据《西南联大校史》,从开列的校内高层名单看,三校基本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校务高层的“四长”及院长的比例也基本持平。如中文系主任分别是朱自清(清华)、罗常培(北大)、闻一多(清华)、杨振声(北大、清华、教育部)、罗庸(北大)。其他系如此前三校皆有设置,则错落程度与比例相似。若属一家独有或独大,如清华的工学院或外文系,则属清华专设或独强,系主任自全是清华的。也因这个缘由,就联大全部系主任比例看,清华还是高于北大与南开,这说明梅贻琦搞的平衡不是平均,该突出的还是要突出,因为当时清华无论在科系设置还是师生的人数上,确实是老大,北大、南开不能无理和任意挑战。
除了人事上的“误会”和分歧,还有经济上的差异与“误会”。当时清华师生间多少有一股“怨气”,认为自己有钱有人,何必与一个牛气哄哄的穷北大联合,我们自己单干不是更好?到了中后期,差点发生分裂。北大校长蒋梦麟在重庆向教育部部长陈立夫告状,说清华有钱不愿意掏出来与大家共享,表示要与清华决裂。为此事,陈立夫专门召梅贻琦到重庆磋商,梅认为蒋梦麟校长所述不是事实,当场与蒋争执起来,后来也有点感情用事地说,分开就分开,清华受够了,不怕,也愿意分开,云云。就在将要重演西北联大因不合而解散悲剧的最后一刻,陈立夫请示了蒋介石,蒋让陈立夫竭力劝说蒋梦麟与梅贻琦并捎话,大意是:抗战之初搞了三个联合大学,有两个已烟消云散了,如果西南联大再一解散,成何体统?如何向国人和外界交代?——这个话,也就是傅任敢前面所说的大体意思。
经蒋介石这么一指点,陈立夫从中说合,最终,梅贻琦同意从清华校款中拨出五十万元给北大,供北大自己的研究所使用。蒋梦麟见梅贻琦以大局为重,也就不再争执,联大各校继续合作下去,一直坚持到抗战结束。
西南联大正是有了梅贻琦这样一位具有高尚人格与博爱精神的掌舵人,才把三校的师生团结在一起,秉承着“刚毅坚卓”的精神,与民族共患难,为国家争未来,使联大诞生了一批又一批专业顶尖人才。真的是“群星璀璨,大师云集”,令世人叹为观止。
校长风范长存1939年春,抗战处于紧急关头,东南地区形势危急,广州的中山大学迁往云南澄江。清华校友、时任中山大学史学系教授的罗香林,于4月6日抵达昆明,借短暂休整空隙,前往联大拜谒老校长梅贻琦,并报告自己辗转的历程。
梅贻琦以乐观态度对罗说:“教书,诚然辛苦,但也还有喜乐。只要我们忍耐下去,环境总会好转的。”第二天上午,罗将起程去澄江,梅贻琦亲自前往旅店回访。当时梅身上带了一包冬天的衣服,说要顺便去典当,因为联大最近的薪水还没有发,只好先自典当周转。
许多年后,罗香林仍记得这一幕,并饱含感情地说:“这更使我感动到几乎流泪。梅先生主持这么庞大的学校,也还要以典当周转,这一方面固然显示时局的艰难,一方面更显示梅先生的高风亮节。”
罗香林所见这一情景,与梅贻琦五弟梅贻宝(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曾任流亡成都华西坝燕京大学代理校长)所见所闻尽管有所区别,但在体现生活之艰辛与气节上,有其相类之处。

梅贻宝
梅贻宝说:“三十四年(1945年)美国国务院约请燕京大学指派教授一人,赴美报聘。教授会议推举我去应邀。由成都起飞,道出昆明,在‘五哥’(梅贻琦)五嫂家住了一夜。校长住宅倒也罢了,只是人口多些,挤些,晚饭实在太简单了。当晚只见祖彦侄(梅贻琦儿子梅祖彦)闷闷不乐,迥异寻常。临睡给我搭了张行军床,借了条被,就设在‘五哥’书架前。他一面看学校公事,我们一面叙谈家常。我问到祖彦,‘五哥’才说,两天前跑警报,彦侄把一副眼镜连盒给跑丢了。家里无钱给他再配一副,而他没有眼镜就不能念书,故而父子都觉十分窘困。我素来服务于私立学校,大致比国立机关待遇好些,而家里多半有两份职务收入。亦曾听说‘五哥’在昆明主持联大,生活不宽裕,但未料到他们一贫至此。遐迩传闻的校长太太制卖定胜糕的佳话,大概就属于这个时期。”
为了赚点外快补贴师生们的拮据生活,梅贻琦在暑假带领学生组建服务社,卖掉了自己所有值钱的东西。有次召开师生大会迟到了,梅贻琦歉疚地解释:“我刚才在街上给我内人的糕点摊守摊,她去进货了,可她办事不利,我告诉她八点我有会,她七点半还没回来,我只好丢下摊,跑来了,不过,今天点心卖得特好,有钱挣啊!”同学们听罢纷纷拭泪,他们知道眼前这位梅校长为了办学变卖了值钱的家当,连师母都得去街上卖糕点。

梅贻琦和夫人韩咏华
梅贻琦曾说“生斯长斯,吾爱吾庐”,他将四十七年的精力投于清华教育事业,强调“德智体美群劳,诸育并进”,强调大学之目的有二:“一是研究学术,二是造就人才”。在他早年发表的《大学一解》中,前瞻性地提出“新民”的概念,强调健全人格的重要性。他强调“在通而不在专”,宣扬通才教育理念。诸多贡献,铸就今日两岸一流之学府,梅贻琦本人也被誉为“两岸清华永远的校长”。他在短暂的七十三年人生旅程中,施于清华乃至整个中国教育事业的恩泽,永为后人铭记、感怀。
(原文《永远的清华校长梅贻琦》刊于《名人传记》2022年第8期 文/岳南)
责编丨王苑 责校丨张静祎
排版丨王苑 审核丨杨彦玲
,免责声明:本文仅代表文章作者的个人观点,与本站无关。其原创性、真实性以及文中陈述文字和内容未经本站证实,对本文以及其中全部或者部分内容文字的真实性、完整性和原创性本站不作任何保证或承诺,请读者仅作参考,并自行核实相关内容。文章投诉邮箱:anhduc.ph@yahoo.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