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子文言文阅读(墨子英译本中文化负载词的变异)
本文原载《中外文化与文论》2016年第1期
转自:国际汉学研究与数据库建设

作者简介
聂韬,电子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四川大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博士,比利时天主教鲁汶大学博士联合培养,主要研究方向:先秦海外汉学研究、比较文学与跨文化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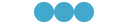
[摘要]:中国比较文学学派中一个重要的学术概念是“失语症”,而从上世纪二十年代开始,中国译者对《墨子》文本的英译过程,一直处于“失语症”的状态之下。本文通过中西方译者对《墨子》中“天”、“仁”、“义”、“上帝”这四大文化负载词的英译情况进行分析,并加入对《论语》 中承载了早期儒家文化的相同术语的英译情况进行比较,试图说明中国译者所受到的“他者文化”的影响,并不亚于具有西方文化主体身份的西方译者。在当下跨文化的学术环境下,中西交流与对话的机会越来越多,相反,译者的国别与主体文化身份对译本的影响越来越小,中国译者只有充分利用异质文化的互补性,对典籍的文本和文化背景的了解和理解上做出努力,才能走出一条摆脱“失语症”的必由之路。
[关键词]:文化负载词 失语症 义 上帝

曹顺庆先生曾在《中西比较诗学》中的附录《中国学派:比较文学第三阶段学科理论的建构》中说道,“中国学术一直是在西方强势话语之下生存的,中国学术的思维方式和话语言方式都和西方有着惊人的一致,也就是说,在西方强势话语之下,中国学术是去了言说自身的权利。”1这就是所谓的中国学术界的“失语症”。
将中国先秦文化典籍之一《墨子》进行英译的本质,是一场在异质文化下所进行的中西对话,译者对上下文语境的把握和文意的解读,皆是处于这个大文化环境之下。文化对话不仅仅涉及到翻译语言与本体语言之间的沟通与转换,它同时着重于语言背后的不同文化背景的译者和作者之间,在思想上的神交与融合。而在这个交流与融合的过程当中,文化负载词的变异情况无法避免。
本文是在承认异质文化差异性的基础下,针对《墨子》文本中几大重要文化负载词,“天”、“义”、“仁”、“上帝”的英译情况进行较为深入地考察,对中西方译者在译词选择上的异同进行分析、与《论语》中承载了早期儒家文化的相同术语的英译情况进行比较,讨论音译方式对于典籍翻译的优势与劣势,并论证,中国译者在这些文化负载词的翻译中,同样也出现了“失语症”现象,而这样的状况出现的原因之一,可能与西方传教士在中国发起的“基督术语本土化”的本色化运动有关。
一、基督之“天”与墨家之“天”:“天志”的英译变异
从1861年英国汉学家理雅格(James Legge)的《中国经典》(Chinese Classics)开始,《墨子》的英译活动到今天已经进行了一百五十多年,抛开《墨子》的研究者大量的《墨子》相关研究著述、论文中对《墨子》中部分章节、语句的翻译副产品不论2,截止2014年,在中西方流传的《墨子》英译本专著(包括节译本和全译本)一共有十余种3。从留美学者梅贻宝到美国汉学家华兹生(Burton Watson),再到二十一世纪中国翻译家王宏、汪榕培,美国墨学学者李绍崑,翻译家艾乔恩(Ian Johnston)、诺博诺克((John Knoblock)和王安国(Jeffrey Riegel),也就是说,在《墨子》的英译过程中,都有中西两种主体的文化身份在参与。
《墨子》中记载了一项墨家的极为重要的思想与主张,同时也是《墨子》中三个章节的标题,“天志”,即“天的意志”。文本记载了“天”在墨家文化中至高无上的地位以及赏贤罚暴的功能,而人必须要“尊天明鬼”。对于“天”的意向的英译,中西译者皆使用“Heaven”一词与其相对应,而“志”一般为“Intention”或“Will”,取译词的“意图”、“意志”之意。
由于中西译者对“天”所使用的译词相同,因而在这个部分,笔者并不会从译者的主体文化身份入手,而是着重讨论的是“天”与“Heaven”在中西异质文化下的变异性。如果对照《论语》的英译本,我们可以发现,译者对于“天”的英译并不是完全基于对《墨子》文本中此概念的理解。“天”的“Heaven”译法,很早就出现于西方译者、汉学家对先秦两汉儒家典籍如《论语》、《孟子》、《荀子》的翻译文本中。无论是早期的理雅格的《中国译本》,还是现当代白妙子夫妇(Bruce &Taeko Brooks),都将“Heaven”视作“天”的常用译法,值得一提的是,在安乐哲(Roger T.Ames)和罗思文(Henry Rosement)合著的《论语的哲学阐释》(The Analects of Confuius: A Philosophical Translation)的译本中,二人认为常用的“Heaven”译法,从中西比较哲学的范畴来说,此词“为之强加了若干中国文化没有的,源自耶稣-基督传统的意象”,是不可取的。他们认为,儒家世界中的“天”是人类社会话语系统中一个十分重要的元素,现实人文社会的盛行衰败同样会波及自然4。因此,这样“天”的意向,在英语中并没有与之相适应的术语,因此,罗斯文和安乐哲选择了用汉语拼音“tian”的音译方式进行翻译。
正如安乐哲所说,早期儒家典籍中的“天”并不是基督文化中上帝创世居住后的场所,而是尽心尽责地服务于子孙后代的祖先集合体,正如《尚书》所说,“天聪明,自我民聪明。”5“天人统一”,是我国传统文化中人与天的关系所在。
那么,墨家的“天”又呈现着怎样的特点?
墨家与儒家同为先秦显学,虽然作为早期儒家最大的反对者,但它思想依旧生成于夏、商、周的文化传承之中,尤其对于“天”这种在上古古籍中早已出现的文化意向。与《论语》一样,《墨子》文本中的“天”通常也是以神谕、反常的天气、异常的自然界现象等方式出现,与人类形成有效的沟通,这就是所谓的“天志”,或者是《墨子》文本中常出现的“天(之)意”。如前文所提到“非攻下”,“日妖宵出,雨血三朝,龙生于庙,犬哭于市”的描写就是“天”与人类社会沟通的具体表现。
为此,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就有一大部分中国学者对于墨子的“天鬼”思想与基督教的宗教思想进行了对比,而其中的典型当属1934年在中国第一基督教期刊《真光》上发表《站在基督教立场上来批评墨子宗教思想之得失》的镜高。文中,镜高在肯定墨家思想与基督教思想在宗教范畴上的共同点的同时,主要指出了它们之间的区别。他认为,墨家思想中的“天、鬼”并称是因为墨家的“天”是多元的,也就是说,墨子“既对天十分尊敬又祀奉鬼神”,而基督教除了独奉三位一体之神以外,虽亦认可天使、魔鬼和灵魂的存在,但绝不会将其看作神,予以崇拜,也就是说,天使、魔鬼和灵魂也和人类一样受到神、也就是“Heaven”的惩罚,而“墨子以其他鬼神亦能直接向人作威作福、或赏贤罚暴,则惑之甚也。”6
美国汉学家卢秀芬(Xiu Fenlu)也认为,墨家的“天”来说所体现出的异质文化下的变异性十分突出。2006年,美国汉学家卢秀芬(Xiu Fenlu)在她的《在比较的视野下理解墨子的道德观基础》(Understanding Mozi’s Foundations of Morality: 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一文中甚至认为,由于对于《墨子》中“天”一概念的误读,甚至直接影响到了西方汉学界对墨家思想道德基础的判断。7
然而,从另一个方面来说,若我们将《论语》与《墨子》文本中与“天”有关的相关论述进行比较,我们会发现,相对于《论语》中孔子对于“天”隐晦的、少有的描述,8墨子则是浓墨重彩地渲染了“天”至高无上的地位,甚至在“天志”篇章中得出了“义果自出天”,“顺天意者,义之法也”的结论。“天”的意向和效用在《墨子》的文本中得到了极大的扩张与发挥。那么,从对天的“至高无上”的地位与“义出于天”的概念上来说,相比儒家典籍中的“天”,《墨子》文本中的“天”或许更适合“Heaven”这个译词。这也是为何,近代墨学诞生后,无论是中国学者还是西方传教士、汉学家,都将墨家思想中可能出现的“宗教性元素”作为了墨学研究重点之一,而镜高与卢秀芬只是其中的两个中西学者的代表人物。
尽管墨家与儒家在论述“天”上的强弱程度有所区别,但从根本上来说,我们必须承认“天”的意向在中西异质文化下所呈现出的差异性是客观存在的。无论是在《论语》还是在《墨子》的文本翻译中,使用“Heaven”作为“天”的译词,势必会在译介的过程中造成文化过滤,很容易让西方读者用西方文化标准进行考量,得出与原文相离甚远的阅读结论,甚至会影响到译本为参考的哲学家、汉学家们对于墨家思想的误判和误解。
“天”作为先秦儒家、墨家,乃至整个中国传统文化流传中重要的术语和意象,映射到英译本时,无论选择怎样的译词,都必须是一个尽量规避术语变异所造成的文化误读的思考过程。安乐哲与罗斯文正是出于这样的考虑,才在《论语》中用音译的方式直接表示“tian”,笔者认为,在没有在英语语言体系中找到比“Heaven”更贴近的译词之前,“tian”的译法也可以出现在《墨子》英译本的正文之中,但是,采用这种翻译方案的前提条件是,译者有需要在绪论或附录中列出关键词表,阐释“天”在墨家思想中的具体表现与意向,并与西方宗教中的“Heaven”加以区别。
比较文学变异学的理论从根本上要求我们,在译介的过程中需要首先承认异质文化之间的差异性,《墨子》的英译中体现出这种差异性,主要来源于中英两种语言体系所承载中西两种思想体系的相互作用力,译者作为英译活动主体,对于原文本的解读、阐释和翻译,必须建立在这样的差异性之上。而音译加注释的翻译方法,虽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使用英语本身而呈现的变异性,但它并不适用于所有的术语翻译,它的存在,是在异质文化下,由于强行翻译特定术语会造成较大的文化变异现象所采取的过渡手段。如果音译的方式在译本中多次使用,所带来的阅读者理解成本过高、上下文语境断裂的问题也不容忽视。笔者也会在接下来的研究中继续探讨这样的翻译方式的优劣之处。
二、《墨子》“义”英译的称儒兼墨
英语世界中对于中国古代典籍的译介现状,依旧是以《论语》、《孟子》为代表的儒家典籍为主流,也就是说,儒家思想在当今西方所受到的关注程度、对西方汉学研究造成的影响,以及西方汉学家的参与程度,都要远远大于《墨子》和墨家文化。
前文已有所提及,最早对《墨子》进行译本式英译的理雅格对于“义”的译法贯穿了整部《中国经典》,即“righteousness”、“righteous”,同样的,理雅格也将《墨子》中的“义”使用了同样的译词9。于是,与“天”的英译一样,“义”在中西异质文化下出现了三个意象,即儒家的“义”、墨家的“义”、以及“righteousness”。我们同样以第一节中所使用的四译本为主要研究蓝本,先来看待在其他《墨子》英译本中的“义”。
“义”的概念在“墨家十论”的第一论“尚贤”篇章中已然出现,足显其重要的地位。墨子认为,“举贤”是“古者圣王之为政”,“尚贤上”中有言曰,“不义不富,不义不贵,不义不亲,不义不近。”10对于“不义”的英译,四个西方译者的译本中,华兹生延续了原文的否定形式,直接将“不义”译作“unrighteous”11,艾文贺与诺、王以及艾乔恩12的译本则将其译为“not righteous”13。
值得一提的是,在《墨子》文本中,“义”所身处的语境以及用法并不是完全一致的。“尚同上”里有言,“故者民始生,未有刑政之时,盖其语曰人异义。是以一人则一义,二人则二义,十人则十义。”14此处的“义”的用法与他处有所不同,“一人一义、十人则十义”的“义”,是不同的人对事不同的观点、行事准则或标准,它或对或错,正因为“义者兹众”,才会导致“天下之乱,若禽兽然。”因此,这样的“义”才需要“上同于天”,最终成为墨子所持的天下之“义”。
根据这样的理解,四位西方译者皆为其选择了其他译词。华兹生译为“view”,艾文贺采用了“norm”,艾乔恩与诺博洛克、王安国的版本则分别使用了“principle”和“standard”。译者们选择不同的译词以突显此“义”的不同之处,都是建立在对《墨子》文意以及上下文语境的正确把握之上。
而我们在这里所主要讨论的,是“万事莫贵于义”的“义”,四个西方译者都沿袭了理雅格用于《中国经典》中对儒家经典中的“义”的译法。那么,这是否代表着,儒家文化中的“义”的概念是否与墨家的“义”相同呢?
除了墨家以外,孔子在《论语》也将“义”视为一个极其重要的术语。孔子认为,“信进于义”,并将“仁、义、礼”作为早期学派的核心观念,《中庸》中有言:“义者,宜也,尊贤为大。”而后,儒家的“亚圣”提出了“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主张15,在孟子的思想体系中,“义”与“利”被塑造为两个完全对立的概念。
墨子在“贵义”篇中说道,“万事莫贵于义。”与孟子不同,墨家的“义”与“利”是相互依存的关系。“耕注”篇中,巫马子与墨子讨论什么是良宝的时候,墨子说道,“和氏璧”、“隋侯珠”都不能谓之为良宝,因为它们不能利人,而义可以利人,故曰,“义天下之良宝也。”在被墨学界普遍认为是后期墨家所著的“墨经”篇章的“经说下”中,“义,利也”的定义更是让后期墨家的“义利观”得到了高度的统一。
除了墨家的“义利观”以外,在“义”的具体表现中,墨家有时会直接与儒家形成冲突,如“节葬下”中,墨子认为,儒家的“厚葬久丧”之举是“非仁非义,非孝子之事也”16,而儒家“厚葬久丧”正是由“亲亲尊贤”的“仁义”思想中衍生出的现实活动。
由此可见,尽管墨家与儒家都将“义”视为自家学说中重要的理念,但二者无论在“义”的内涵还是具体表现上都存在着很大的差异。
在理雅格使用了“righteous”作为儒家“义”的译词后,儒家典籍的英译经历了一百五十多年的发展,西方汉学家对于“义”的英译也随之经历了一系列的更迭。为了追溯流变,笔者同时查看了在儒学经典译介史上影响较广的辜鸿铭和艾文贺的《论语》译本。
《论语》中第一次出现“义”的地方是在“里仁”篇里,子曰:“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17辜鸿铭将“义”译为“what is right”18,艾文贺为使用了“right”19;在“卫灵公第十五”中,子曰,“君子以义为质”20,辜鸿铭将此处的“义”译为“right”21,艾文贺则使用了“rightness”22。从词源的角度来讲,虽然“rightness”与“righteous”皆衍生于“right”,三者都包含了“正确、公正、正义”等含义。但是“righteous”一词诞生后,多用于基督教、犹太教、伊斯兰教的教义之中,也就是说,“righteous”的“公正、正义”的意义来源于“上帝”(God ),决定于上帝。相较而言,“right”或“rightness”所散发的西方法制伦理的思想更为浓厚。
西方译者对于儒家经典中“义”翻译在安乐哲与罗斯文的译本中又有了新的改变。在中西异质文化下比较哲学的视域下,安、罗二人在译本中将《论语》文本中所出现的关键术语都出了新的释要,并选择了新的译词,如上一节论述的“天”(tian)、“仁”(由常用的“benevolence”或“goodness”,变为“authoritative person”),对于《论语》中“义”,安乐哲认为,无论是“right”、“morality”甚至是“righteousness”都是先前的译者按照西方的观念而贯彻的翻译方式,因此,安乐哲立足于《论语》文本中,并根据孔子对“义”的定义,“义者,宜也。”的定义,将其译为“appropriate”。23
在《墨子》的现已出版的英译本中,“righteous”的译法从理雅格的时代一直延续至今。一方面,若仅从儒家与墨家的思想区别上来看待,“righteous”一词或许适合《墨子》文本的论述。在前文笔者已经有所提及,墨子强调尊天明鬼,“天志”篇中有“义果自天出矣”的言论;从另一方面来说,“righteous”一词本身在西方宗教文明中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宗教术语。它源于《圣经》(《古兰经》、《托拉》),本意为“遵从上帝的意愿行事”(obey the will of God)。而西方宗教文明中的“上帝”,并不存在于墨家所身处的先秦文化背景中,中国古代文化中的“天”并不是西方的“天堂”(Heaven),也没有无所不能的“God”。《墨子》文本中的“天”尽管赏贤罚暴,公正无私,但并不是一个被人格化的意象,而是通过任命政权统治者“天子”作为祂在人间的代言人,通过神谕的方式与“天子”形成最直接的联系。因此,若从“义”与“righteous”在各自文化背景来进行审视,后者成为前者在《墨子》英译本中的代替,并不能涵盖在先秦文化背景主导下的文化话语的内涵,“righteous”的英译方式,依旧是在西方基督宗教文明的作用力下,《墨子》文本话语发生变异的结果。
《墨子》的英译本中,唯有艾乔恩的译本对“义”的英译进行了一定的考量。在艾乔恩的第一版《墨子》译本中,“义”的翻译依旧为“righteous”,24而在2013年的修订本中,艾乔恩将“义”的译词变更为拼音“yi”25,并在正文中第一次出现“义”的概念的“尚贤上”篇章里直接添加了“right act、righteous、duty”三个词语进行阐释。而“义”最先使用音译方式的是现代西方汉学家葛瑞汉,在他的《后期墨学科学、伦理与逻辑》(Later Mohist Logic, Ethics and Science.) 一书中,葛瑞汉对“墨经”中“义,利也”一句的翻译为,“To be yi (righteous/dutiful/moral)is to be benefit.”26
对“义”音译加注释的翻译方式恰好能够,葛瑞汉和艾乔恩在研究和翻译《墨子》文本的过程中都发现,仅仅使用“righteous”已经无法涵盖“义”在《墨子》一书的内涵,在进行初次的定义后,整个“墨学十论”中,相同语境下的“义”都统一用音译进行表示。
“万事莫贵于义。”27,从这些词在现代语法中的用法来看,我们或能根据将“墨家十论”分为三个部分;首先,“节葬”、“节用”、“非乐”、“非攻”等主张,是天下之人可以采用的正确的行事方式,“天志上”有言,“义者,善(言)政也”,“尚同”、“尚贤”则是明君可以采纳的治理天下的手段(right act);“尊天”(天志)、“明鬼”是在“天”进行赏贤罚暴强制手段下,君、臣、民都必须要遵行的义务(duty);而“兼爱”、“非命”则是人们能够贯彻的正确的道德标准(righteous)。
除了《墨子》的英译本,当前绝大多数的西方墨学研究成果依旧选择将“义”译为“righteous”。当然,也有部分西方汉学家如方可涛(Chris Fraser),他在功利主义(结果主义)的西方近世哲学观念的关照下,将墨子视为一个道德哲学家,因此,他选择将“义”译作“morality”(道德准则),与“righteous”所代表的宗教神学观念形成对比。28
然而,与“天”的翻译现状相似,梅贻宝、汪榕培、王宏、李绍崑等具有中国本土文化身份的译者们,皆在各自的《墨子》英译本中直接使用了“righteous”作为“义”的译词,这也是在译介领域中所体现出的中国译者犯下的“失语症”。
或许“righteous”的译法在《墨子》已经基本定型,或许中国译者借鉴了先前译本的翻译方式,并认为这是在表达对先前译者的学习与尊重的方式。然而,如果译者在“尊重”里却不自觉地陷入了“他者”的文化视域之中而不自知,甚至被西方文化的基督话语所吞噬,那么,无论译者原本的文化身份是什么,翻译文本中所展现的文化变异无法避免,“失语症”的出现更无法避免。
而采取音译加注释的翻译方式是西方译者在充分理解《墨子》文本的条件下所作出的尝试。承接上文的观点,笔者认为,这样的英译方式,可能能更适合于墨学研究者,首先,这样的翻译方式既能够保证研究者在研究过程中,最大程度地呈现尊重原文文本的谨慎与客观,其次,研究成果也具有将术语阐释完整、明晰的篇幅承担力,也就是说,研究者可以通过大量的语言来降低阅读者在理解上的风险。
然而,对于纯粹的译本来说,使用音译加注释的翻译方式,依旧存在读者理解成本依旧过高的问题。例如,艾乔恩在自己的最新译本中,面对《墨子》文本中的诸多关键术语,用音译进行英译的仅有“仁”与“义”两个术语,其余的依旧使用英语实词相对应;且译本中,尽管艾乔恩为阐释“义”的内涵而给出了三个不同的词语,然而,译本并没有为其提供更进一步的阐释空间,也就是说,身处异质文化背景下的西方读者对此后用拼音形式出现的“义”,都要进行一次单独的意义上的判断,这无疑提高了译本的难度。而笔者认为,也许译者在译本的绪言、章节的前言、抑或是附录中花费一定的篇幅对关键术语进行阐释的方式,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降低音译的翻译方式所带来的负面影响。
三、 同与不同:“仁”的英译变异
《墨子》文本中,“义”除了独立出现在墨子的论述中以外,还多以“仁义”的形式出现,在“仁义”中,与“义”相连接的另一个术语“仁”,与“义”相同,在《墨子》文本中的英译同样受到了儒家经典英译的影响。
《墨子》的英译本中,从理雅格到梅贻宝、华兹生,再到艾乔恩、王宏与汪榕培以及李绍崑的全译本,“仁”的翻译一直为“Benevolence”,“仁义”的译法为“Benevolence and Righteousness”。艾乔恩在2013年的修订本中,针对“仁”的英译处理,采取了“义”相同的音译加注释的方式,即在每一个篇章第一次出现“仁”或“仁义”之时,都直接使用拼音“ren”来表示,且在括号中加入“Loving、Kind、Humane、Benevolent”四个英语单词进行词义阐释,同理,在吼文中出现的所有“仁义”则统一用“ren and yi”29来表示。除此之外,诺博洛克与王安国的译本则将“仁”译为“Humane”,将“仁义”译为“Humane and Proper”。
“Benevolence”作为墨家“仁”译词,就如“Righteous”之于“义”一样,在这一百多年的英语世界《墨子》译介和研究里,一直沿用至今,鲜有学者对此种译法提出质疑。当代部分西方墨学研究者中可能对“仁”的译法有所商榷,在其研究作品中用音译的方式表示,也欠缺新的译法或翻译考虑。
墨家之“仁”的英译形态,与“兼爱”、“义”一样,最早出现在理雅格的《中国经典》之中,也就是说,无论是儒家之“仁”还是墨家之“仁”,理雅格都统一翻译为了“Benevolence”,然而,与《墨子》英译情况不同的是,“仁”作为儒家思想中的核心概念,经历了一个多世纪的发展后,与“义”的翻译相同,为数不少的西方儒学家、翻译者对儒家之“仁”的翻译存有与“Benevolence”所不同的方式与考虑,在这里,我们单看理雅格前后,国外汉学家、译者对于《论语》中的“仁”的思考以及相对应的译词选择。
在理雅格之前,儒家“仁”曾经被耶稣会和传教士译为“Piety and Mercy”、“universal love”、“make us love all men”等,而这样的诠释是早期的耶稣会士们企图让儒家的思想与基督教义取得一致,以达到基督教思想在中国更容易被接受和传播的目的。30而理雅格在《中国经典》中对于《论语》采取的严格遵照原文、传统经学诠释方式的翻译策略改变了早期耶稣会和传教士对于“仁”完全基督教化的诠释,这也让“Benevolence”在较长的一段时间内都成为了西方汉学家们研究《论语》时认可和使用的译法。
此后,英国汉学家翟林奈(Lionel Giles,1875-1958)在翻译《论语》时发现,“仁”在《论语》文本中,不同的上下文语境中可能表达了不同的意义,因此,他对《论语》中“仁”的译法并不固定,而是根据上下文语境,大致有“Virtue”、“Charity”、“goodness”几种翻译方式;31而同为英国汉学家的韦利(Arthur Warley)在自己的译本中,通过追溯“仁”的语义演变历史,同时结合《论语》中对“仁”不同的论述,最后得出结论,儒家“仁”的概念与道家的“道”一样,都具有一定的抽象性,也就是说,其意义很难用固定地一种描述品德的词汇所涵盖。为此,韦利选择选择了“Good”作为“仁”的译词,因为他认为,“Good”在英语词汇系统中,也可以看作是能够涵盖多种品德的意义的词语。32
当代汉学家安乐哲与罗斯文的《论语》英译本,二者的处理方式与“义”相同,都是在比较哲学的视域下重新诠释“仁”的概念,安乐哲认为,“无论是‘Benevolence’、‘Goodness’还是‘Humanity’,这些译词都无法完整地展现儒家之‘仁’所代表的精神层面和物质指向,儒家‘仁’的存在是让‘人’成为完整意义上的‘社会人’。”33在这样的考虑下,安乐哲同样认为“仁”在《论语》中词意不固定的现实,因而也很难在英语中寻找固定的“译词”。安乐哲创新性地将其翻译为“Authoritative Person”,说明有《论语》中的“仁”之人是一个社会公认的典范。34
最后是白氏夫妇的《论语译本》。白氏夫妇持有与翟林奈、韦林和安乐哲相似的观点,认为英语中并不存在相对应的字词可以完全囊括“仁”的含义,且“仁”在《论语》前后诸篇的论述中,意义不断的发生变法,因此,译者采取了音译加注释的方法进行诠释。35
那么,“墨家”之“仁”在《墨子》文本中的内涵和具体表现又是怎样的?
《墨子》中的“仁”虽然也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概念术语,但其地位却远远不如《论语》中的“仁”。在《墨子》尤其是“墨家十论”的篇章中,相较于“义”、“利”、“爱”等术语,“仁”一般不以独立的形式出现,要么作“仁者”。如“兼爱”篇与“非乐”篇章,都有这样的记载,“仁之事者,必求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将以为法乎天下”;又如“节葬下”,“仁者为天下度也。”
而通常情况下,“仁”会伴随着“义”同时出现在论述之中,即为“仁义”。例如“天志中”,“今天下之君子,中实将欲遵道利民,本察仁义之本,天之意不可不慎也”;“尚同中”与“尚同下”,“今天下王公大人士君子,中情将欲为仁义,求为上士”;“节葬下”,“厚葬久丧实不可以富贫众寡,……此非仁非义,非孝子之事也,……”
从引文中可见,《墨子》中“仁者”与“仁义”的出现,都处于基本相同的上下文语境下,也就是说,所谓“仁义”,是天下王公大人与士君子所必须贯彻的理念,只有通过“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才能够成为“仁者。”“仁义”思想的贯彻,“仁者”的塑造,与“国家百姓人民之利”的为政之法息息相关。“仁义”是欲从政、治天下之人所必须具备的品质,拥有这样品质,才是合格的“为政之人”。
“仁”在儒家思想中,是人在道德层面所期望达到的最高境界,也正因如此,在《论语》之中,“仁”的概念在孔子与其弟子们的对话之中得到了不同的道德诠释。因此,无论是“Benevolence”还是“Humane”,甚至是“Good”,这些词语所强调的是在精神层面价值观和品德、以及受其指导的人的行为举动,那么,它们倘若应用与儒家之“仁”的翻译,在《论语》的部分语境中还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对于墨家,尤其对于“墨家十论”的相关记载来说,这两种译法都是对墨家之“仁”所表现的政治理想的误读与曲解。由此来看,艾乔恩用于阐释“Ren”的四个英语单词,即“Loving、Kind、 Humane、Benevolence”,没有任何一个是接近墨家之“仁”的原意的。
若单纯地考虑“仁”在《墨子》文本中的内涵与具体论述方式,笔者认为,对于墨家的“仁者”与“仁义”,我们或许可以译为,“仁者”,“officers who benefit the world”,“仁义”译为,“political appeals”,这样的翻译方式或许与我们固有的“仁”的理念大相径庭,但是它却明确地告诉我们,以“利人、利天下”为基础的“墨家”之“仁”的英译,需要完全摆脱儒家主流文化的影响与束缚。
至于用拼音直接表示“仁”的翻译方式,笔者认为,与“义”一样,在纯粹的英译本中采用音译的方式并不可取,尤其是将“仁义”表示为“Ren and Yi ”的方式更会增加研读的迷惑性和难度。
西方译者对“义”、“仁”的翻译充分体现了《墨子》英译的现状。使用西方文化视域下的英语词汇,译词以及表达的意义更为符合异域阅读习惯,可能更有利于浸淫在西方文化圈中的读者们接触并不未占据中国主流话语权的《墨子》及其思想,并萌生兴趣。因此,文化负载词的变异,一定程度上有利于跨文化视域下中西交流渠道开启与拓展。诚然,为典籍中的关键术语选择最优的异域文化词,是一个极为艰难的过程,但也是英译本的必经之路,相较于西方汉学家、翻译家们对于《论语》关键术语的英译,艾乔恩、葛瑞汉、方可涛等人对“仁”、“义”的英译所体现的思考,中国的《墨子》译者依旧有很长的路要走。
四、 基督教的影响?——“上帝”的英译变异
在《墨子》的英译中,最能够体现出中国译者的“失语症”状态的,是对“上帝”一词的英译。
“非命上”中存有这样一段论述。墨子认为,持有“有命论”之人破坏了天下之义,“有义之人”需要拥有权力,而当墨子被“天下之士君子”问及为什么“有义之人”需居于上位时,墨子答曰,“义人在上,天下必治,上帝山川鬼神,必有干主,万民被其大利。”
此引文的特殊之处在于,出现了“上帝”一词。用当代人的眼光来看,我们很难用当下文化环境中对“上帝”的认知与《墨子》中的“上帝”联系起来,在当代汉语语义体系中,“上帝”在中国传统文化背景中的唯一意象已经产生了变化,也就是说,基督教中“God”的概念同样进入了“上帝”的语义系统之中。
在中国上古文献记载中“上帝”一词已经出现。《尚书·召诰》有言,“皇天上帝改厥元子兹大国殷之命。”《尚书·舜典》中同样有涉及到“上帝”的论述,“肆类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遍于群神。”我们会发现,后者与“非命中”里“上帝”出现的论述在用词方面极为相似,那么,《墨子》中的“上帝”一词也许来源于《舜典》,是在中国传统文化背景中所诞生的文化负载词。
在《墨子》诸多的校勘版本中,无论是毕沅的《墨子注》、孙诒让的《墨子间诂》还是吴毓江的《墨子校注》,都没有对《墨子》文本中所出现“上帝”一词做出任何的校注,这至少能够说明,在清末民初的《墨子》校勘者的眼中,“上帝”的内涵依旧是中国自古以来所固有的,没有任何需要额外校注的必要。“上帝”的含义,即如《诗经》记载的一样,“ 皇矣上帝,临下有赫, 监观四方,求民之莫”,“上帝”即是“最高的帝王”,能够主宰与监视天下的最高统治者,这样的意象,与西方基督文化中的“God”—“耶和华”并不能相提并论。
明代以后,利玛窦将天主教传入中国,也正是利玛窦将拉丁文中的“dues“与中国古语中的“上帝”联系了起来,让“上帝”的内涵与天主教中的最高人格神,“God”—“耶和华”直接相关联,强行将中西异质文化下的两个文化负载词进行了关联,当《墨子》的译者在面对《墨子》文本中的“上帝”一词时,出现了不一致的情况,为此,笔者分别选择了两个中国学者、两个西方学者的译本进行比较。
梅贻宝:Because when the righteous are in authority, the world will have order, God, hills and rivers, and the spirits will have their chief sacrifice, and the people will be visited by the great blessings therefore.36
汪榕培、王宏:When the righteous men are in authority, the world will have order, the God, hills and rivers, and ghosts and spirits will have worshipers to offer sacrifice to them, and the people will be greatly benefited.37
艾乔恩:If there are righteous men (yi men/2013Revision.)above, the world will certainly be well ordered. The supreme Lord and the ghosts and spirits of the mountains and rivers will certainly have someone to preside over[the sacrifices],so the ten thousand people will receive their great benefits.38
诺博洛克、王安国:When righteous men occupy positions of authority, the world is certain to be orderly; the supreme Sovereign, the spirits of mountains and streams, and ghosts and spirits to have worshipers to host their sacrifices; and the myriads of people to be benefited greatly.39
中国译者梅贻宝,以及汪榕培、王宏的译本中,“上帝”的英译为“God”,而采取此译词的还有中国学者李绍崑;然而,无论本文所引的艾乔恩、诺博洛克与王安国,甚至较早的译者,华兹生、葛瑞汉等人,都没有将“上帝”直译为“God”,艾乔恩译为“supreme Lord”、诺、王译为“supreme Sovereign”,尽管所选择的译词不同,但皆是遵循了“上帝”在中国传统文化背景下的本意进行英译。40
这里便出现了译者主体文化身份与译词选择的错位。如果我们说中国译者对“天”、“义”、“仁”的译词选择,可能是受到了先前西方译者的《墨子》英译本的影响,而非西方文化与理论的浸染的话,那么这条理由,并不适用于他们对“上帝”的英译。
我们可以提出一个问题,那就是,研究者是否能预设,相对于中方译者,西方译者的自我身份长期处于西方的文化视域之中,在面对他者文化下的翻译对象时,会比前者更容易出现文化的误读或者理解的偏差?因为通过“上帝”这一文化负载词的英译我们却发现,中国译者受到的“他者”文化的影响,远远比西方译者更大。
“上帝”在《墨子》文本中,不等同于西方文化“God”的意象是一个无法争辩的事实,抛开译者对《墨子》文本的钻研程度以及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了解程度不谈,我们或许可以推断,中国的译者们皆采取这样的译法,也许与近代以后,基督教在中国的影响力逐步扩大有关。
近代西方哲学、神学的思想进入近代中国并不是清末民初开始的,然而,随着清末中国主权、封建政治体制的迅速崩溃,西方政治理念与经济发展方式的迅速渗透,让基督教文化在中国的渗透也加快了脚步。
为了尽快在民众中普及,且尽量规避中国原有文化的抵御,传教士们所采取的其中一个做法,便是基督教的“本色化”运动。在形式上,传教士开始在中国修建大量的极度教堂,而在内容上,其中一个重要措施,就是“基督术语本土化”。也就是说,寻找中国传统文化中近似的、可被替代的文化负载词,通过译介,排挤它原有的内涵,使之成为基督思想在中国的专门用语,而“上帝”在当代中国的使用现状,无疑让其成为一个基督教的“本色”运动下成功的范例。
“基督术语本土化”的活动发生的地点在中国,因此,身处在此语境下的中国译者所受到的影响比西方的研究者和译者更为明显。也就是说,在利玛窦以后的传教士们成功地偷换概念“上帝”之后,对《墨子》的中国学者和翻译家们在翻译过程中根本无法在中西异质文化背景下去审视“上帝”一词的本来意象,这也让“God”在中方译者的《墨子》译本中形成了格外明显的术语变异现象。
相反,并未经历或受到基督教在中国的本土化运动影响的西方汉学家和翻译者们,在翻译中的过程中直接接触《墨子》的原文文本,而“上帝”与“God”在中国本土的紧密联系在西方译者的翻译过程中被极度地弱化了。
五、结语
通过上文的分析,我们发现,无论是“天”、“上帝”还是“仁”、“义”,这些术语的译法相对固定,在这背后或许有以下几方面原因,
第一,在西方宗教文化、或中国主流儒家文化的影响之下,译者、研究者很难在英语中找到相对应的词语作为术语的译词,如“天”和“Heaven”,“义”与“righteous”,学者或许都能够在研究或者翻译之中体会到中国古代的“天”与西方“Heaven”的文化差异之处,但是,怎样的英文词语才能够完全符合“天”的内涵以及背后隐藏的中国古典文化背景?部分译者所采用音译加注释的翻译方式,也是寻找未果后的折衷之举。
第二,相对于儒家经典的英译状况来说,《墨子》在英语世界的译介情况远远落后。这种落后,不仅仅体现在译介时间跨度的长短、译本的数量以及西方汉学家、翻译学家的参与数量,它还体现在已经出版的《墨子》译本中,译者对于术语变异情况的敏感程度和处理的轻重程度。如译者对《论语》中儒家之“仁”、儒家之“义”的英译,每一次新的译词,新的翻译方式的诞生,都是西方学者对《论语》所做出的又一次新的解读与突破,实实在在地推动着英语世界中儒家典籍译介与研究的发展历程。
更重要的是,《墨子》译本中,“天”、“上帝”等文化负载词的变异情况出现,并不受制于译者原有的文化身份,这也能够说明,中国译者也如中国当下的学术界一般,身处“失语”的状态之中。曹顺庆认为,“中国不仅在文艺理论研究上处于失语状态,而且在整个中国文化上和学术研究上(包括比较文学研究)都患上了严重的‘失语症’。”41诚然,西方汉学家作为文学交流的接收方,自身传统和文化背景为基础的文化身份对目标文本的创造性的接受过程中所造成的文学文本的变异,在其翻译文本上所造成的文化过滤与文化误读似乎更容易被学界所注意,然而,通过前文的分析我们能够看出,参与《墨子》英译的中国学者们,如汪榕培、王宏,李绍崑,甚至梅贻宝,在翻译过程中同样受到了西方哲学、神学理念的影响,西方译本中出现的文化负载词的变异情况,中国学者的译本中照样出现;西方译本中有所避免的,如上帝、有所改进的,如“仁”和“义”,中国学者却深受“他者”文化影响,却依旧没有任何警觉,中国学者一方面表现出对先秦文化典籍的不熟悉,另一方面也忽略了中国话语规则,而这正是《墨子》的中国译者所体现出的“失语症”。
笔者认为,每一个在跨文化视域下进行交流的参与者的文化身份都是在不停地变化的,因为参与者们需要在“自我身份”和“他者身份”的双重行为下不断取舍、建构,以求达到平衡。如赛义德所说,“‘自我身份’或者 ‘他者’身份决非静止的东西,而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人为建构的历史、社会、学术和政治过程,就像是一场牵涉到各个社会的不同个体和机构的竞赛。”42
《墨子》的英译本与诸多中国典籍的英译本一样,都是中西文明碰撞下的产物,因此,在中西异质文化的关照下,《墨子》的译者和越来越多的研墨者所面对的,是两种文化观念,两种语言的冲突与融合,对异质文化的理解、对原文本的解读并不会限制于国别、或者是与生俱来的文化背景。两种不同文化、不同语言之间在翻译过程中所表现的特征,是互证、互补,是需要译者和研究者对文化话语的变异有更加深刻的认识。在当下跨文化的学术环境下,中西交流与对话的机会越来越多,译者的国别与文化身份对译本的影响越来越小,中国译者只有充分利用异质文化的互补性,对典籍的文本和文化背景的了解和理解上做出努力,才能走出一条摆脱“失语症”的必由之路。

注释
1. 参见,曹顺庆,中国学派:比较文学第三阶段学科理论的建构. 中西比较诗学,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11页.
2. 1898年,荷兰的汉学家高延[Groot, J. J. M. de (Jan Jakob Maria)],在他的著作《中国的宗教系统》(The Religious System of China)一书中,对墨子的节葬思想进行简短地介绍,与儒家的葬礼形式进行对比,并翻译了墨子《节葬》一章。又如胡适、冯友兰在各自的博士论文中都针对自己所研究的《墨子》文本进行了翻译,美国汉学家、冯友兰的好友卜德(Derk Bodde)在冯的《中国哲学简史》时也翻译了“兼爱”、“天志”、“明鬼”等部分进行了翻译;1980年,李约瑟(Joseph Needham)也在他所著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中也翻译了“经”上和“经”下的部分片段参见,Groot, J. J. The Religion’s System of China.[M]. Leiden: Brill Academic Publishers,1892;Hu Shi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Logical Method in Ancient China. [M]. Shanghai: The Oriental Book Company, 1922;Fung,Y. A Comparative Study of Life Ideals[M]. Shanghai: The Commercial Press, LTD, 1925.;Fung,Y. A Short History of Chinese Philosophy[M]. edit by D.Boddle. New York: Macmilan, 1948.;李约瑟.科学技术史(第二卷)[M]上海:科技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3. 1922年德国汉学家阿尔弗雷德·佛尔克(Alfred Forke)所著,名为《社会伦理家墨子及其弟子之哲学论述》(Me Ti: Des Sozialethikers und seiner Schüler philosphische Werke)是唯一的德语全译本,除此之外,西方世界所流传的《墨子》译本都为英译。参见,Forke.A.Me Ti: Des Sozialethikers und seiner Schüler philosphische Werke. Berlin:Kommissionsverlag der Vereinigung wissenschaftlicher Verleger, 1922.
4. Roger T.Ames. and Henry Rosement,Jr. The Analects of Confuius: A Philosophical Translation.New York: The Random House Publishing Group. 1998.
5. Roger T.Ames. and Henry Rosement,Jr. The Analects of Confuius: A Philosophical Translation.New York: The Random House Publishing Group. 1998.
6. 镜高.站在基督教的立场上来批评墨子宗教思想知得失. [J].真光1934.第15-20页.
7. Lu,X. “Understanding Mozi’s Foundations of Morality: 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Asian Philosophy,2006, (16). p.88.
8. 在《论语》中,孔子对于“天”的描述极为克制,直接提及“天”地方一共有十二处,在其中孔子虽然承认“天”是拥有至高德行的存在,却并没有将其作为论述的重点,甚至为了让人们实行现实的仁德之行,而说出了诸如“子不语,怪,力,乱,神”的言语。
9. Legge,James,trans. The Chinese Classics. Rpt., Hong Kong: Hong Kong Unversity Press, 1960 p.78.
10. 孙诒让.墨子间诂.[M].孙以楷点校对. 北京:中华书局,2001.第43页.
11. Watson Burton, trans. Mo Tzu: Basic Writing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3. P.21.
12. 艾乔恩对于“义”的“righteous”的英译方式仅仅出现在他的第一版《墨子》英译本中,在2013年的版本中,艾乔恩改变了对“义”的英译方式,下文会有具体论述。
13. Ivanhoe, Philip J., and Bryan W.Van Norden, eds. Readings in Classical Chinese Philosophy. Indianapolis: Hackett Publishing Company, 2004.p.58; John Knoblock and Jeffery Riegel,Mozi. A Study and Translation of the Ethical and Political Writings.Institute of East Asia Studi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2013,p.84.
14. 孙诒让.墨子间诂.[M].孙以楷点校对. 北京:中华书局,2001.第78页.
15. [清]焦循撰.孟子正义.十三经清人注疏.沈文倬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7. 第38页.
16. [清]孙诒让.墨子间诂.[M].孙以楷点校对. 北京:中华书局,2001.第171页.
17. [魏]何晏著.[宋]刑昺疏.朱汉民整理.论语注疏.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0.第52页.
18. 辜鸿铭. 《论语》英译. The Discourses and Saying of Confucius.辜鸿铭文集. 海南:海南出版社,2000.第368页.
19. Ivanhoe, Philip J., and Bryan W.Van Norden, eds. Readings in Classical Chinese Philosophy. Indianapolis: Hackett Publishing Company, 2004.p.10
20. [魏]何晏著.[宋]刑昺疏.朱汉民整理.论语注疏.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0.第237页.
21. 辜鸿铭. 《论语》英译. The Discourses and Saying of Confucius.辜鸿铭文集. 海南:海南出版社,2000.第489页.
22. Ivanhoe, Philip J., and Bryan W.Van Norden, eds. Readings in Classical Chinese Philosophy. Indianapolis: Hackett Publishing Company, 2004. p.41.
23. [美]安乐哲,罗斯文.《论语》的哲学诠释. 余谨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第49-54页.
24. Ian Johnston, trans.The Mozi:A Complete Translation.Great Britain: Penguin Classics, 2010. p.57.
25. Ian Johnston, trans. Mo Zi: The Book of Master Mo.Great Britain: Penguin Classics, 2013.p.32.
26. Graham. A.C. Later Mohist Logic, Ethics and Science. Hong Kong: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1978.
27. 孙诒让.墨子间诂.[M].孙以楷点校对. 北京:中华书局,2001.第439页.
28. 详情参见,Defoort,Carine and Nicolas. Standaert, “The Mozi as an Evolving Text: Different Voices in Early Chinese Thought”, in Studies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Texts, Vol. 4, Leiden: Brill, 2013.pp.175-204.
29. 参见,Ian. Johnston Mo Zi. The Book of Master Mo.London: Penguin Classics. 2013.p78..
30. 详情参见,王琰.汉学视域中的《论语》英译研究.[M].上海:上海外语出版社.2012.第42-97页.
31. Giels, Lionel. The Sayings of Confucious: A New Translation of the Greater Part of the Confucian Analects. London: John Murray. 1907.
32. 参见Waley Arthur. The Analects of Confucious. London: George Allen & Unwin, 1938.
33. 参见Waley Arthur. The Analects of Confucious. London: George Allen & Unwin, 1938.
34. 参见Roger T.Ames. and Henry Rosement,Jr. The Analects of Confuius: A Philosophical Translation.New York: The Random House Publishing Group. 1998.
35. 参见 Brooks, E.Bruce and A. Taeko Brooks. The Original Analects: Sayings of Confucius and His Successor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8.
36. Mei Y.B. Motse,The Ethical and Political Works of Motse. London:Probsthain’s Oreintal Series, 1933.p.184.
37. 汪榕培,王宏. (英译)墨子. 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 2006.第277页.
38. Ian Johnston, trans.The Mozi: A Complete Translation.Great Britain: Penguin Classics, 2010.p.323.
39. John Knoblock and Jeffery Riegel, Mozi. A Study and Translation of the Ethical and Political Writings. Institute of East Asia Studi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2013.p.292.
40. Watson Burton, trans. Mo Tzu: Basic Writing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3.p.119.
41. 参见,曹顺庆,中国学派:比较文学第三阶段学科理论的建构. 中西比较诗学,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第211页.
42. [美]萨义德.东方学.王宇根译. 北京:三联书店,1997. 第426-427页.
,免责声明:本文仅代表文章作者的个人观点,与本站无关。其原创性、真实性以及文中陈述文字和内容未经本站证实,对本文以及其中全部或者部分内容文字的真实性、完整性和原创性本站不作任何保证或承诺,请读者仅作参考,并自行核实相关内容。文章投诉邮箱:anhduc.ph@yahoo.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