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秀丽画家(徐秀丽从刘燕瑾)
1945年8月,王林正在晋察冀边区总部所在地阜平上党校,对整风、学习情绪倦怠。组长批评他们生产情绪高于学习情绪,王林则赞成“不是生产情绪高了,而是学习情绪不够高”的说法。好在本来为期一年的学习因抗战胜利突然中断。他们是在8月11日晚间获知日本投降消息的,整个边府立即沸腾了,人们笑闹狂喊,点起漆黑夜晚最能代表狂欢心情的火把,有人从校部搬出一大捆烧火用的芦子,惹得工友追出。人们说都胜利了,还在乎这个,整个点着在场中跑圈,后又拆开闹。校部宣布马上进行甄别与鉴定,一周内结束。王林则担心“这一周我看也要赶不上时代了”。
在这样飞扬的心情中,已经36岁的王林又一次痛感非马上解决“老婆问题”不可。他既幻想不久的将来“到北京演真的李自成”时寻找往日恋人或者另觅良缘,又处处留意身边的乡村少女,还再次动了追求火线剧社名演员刘燕瑾的念头。他一向欣赏刘的艺术才华而不喜欢其外表,但这年9月的相见,却惊讶地发现刘“特别漂亮”。不过刘并未接受他的追求。
王林虽是火线剧社的首任社长,是该社许多上演剧目的剧本创作者,他却不知道,刘燕瑾正在焦急地等待她的恋人凌风(即后来的名导演凌子风)归来。即使他自己,恐怕也并没有准备好一场认真的恋爱。

中国女演员刘威葳在舞台表演《火线剧社女兵日记》
一
刘燕瑾1923年出生于北京,1938年到冀中参加火线剧社。1941年,根据地掀起排演中外经典戏剧的热潮,火线剧社准备上演曹禺的《日出》。但火线剧社平日所演多是反映时事宣传抗日的小戏,对排演《日出》这类“大戏”没有经验,所幸丁玲率领的“西北战地服务团”(西战团)此时正在晋察冀根据地活动,剧社便请来“刚从上海出来见过大世面”的凌风当导演。18岁的刘燕瑾出演“顾八奶奶”,无疑给凌风留下美好印象——凌晚年仍说刘是冀中“最漂亮的女演员”。
据王林、刘燕瑾的长子王端阳推测,刘凌二人最晚重逢于1943年1月晋察冀边区第一届参议会召开期间的阜平。3月,凌向刘表达了爱情;不久,刘也坠入爱河。1944年3月8日,因“西战团”即将去“很远很远的地方”也就是回延安,凌风突然表示要带刘燕瑾一起走。稍作犹豫之后,刘答应了他。这天晚上,她“兴奋得全睡不着。月亮把屋里照得非常亮,我看着窗格的花影慢慢的斜过去,斜过去”。但她知道,她无法决定自己的命运,她是一个党员,必须绝对服从组织。
刘燕瑾性格活泼,演技精湛,是一个带有明星光芒的女演员,追求者众多。但实际上,凌风是她真正的初恋,是“第一个自发的主动的自然的恋爱”。她忐忑不安,言行举止紧张而卤莽。凌风表白后的第二天:
满怀着极大的不安,忐忑的走到了家中,我的脸一进村就烧得通红了,像有一件什么事情将要临头,我也不知我是兴奋还是恐惧。但是到了家各处全是冷清清的,没有一个人,大家全背粮去了,我只有等待着,等着他们回来。
黄昏了,人们也全零星的走了回来,但是却没有人找我谈,指导员,社长,全像往常一样,只有我这心里头像有一条花毛虫在爬,在爬。小鬼从门外急促的进来了,我马上从炕上跳到地下,心扑扑的跳个不停,原来他是找的别人,我只好又暂时的安静下去。
天快黑了,我实在再也等待不住,一股劲的跑到了社部。当我一进院子,我立着了,我到底干什么来呢?我怎样讲呢?这些事先我全没有想到,现在当然也没机会来准备了。鼓了鼓气大胆的喊出了一声指导员。他出来了,和往常一样,我不能抑制自己了,我说出了我的话。他没有回答,因为他不知道有这一回事。没法,我只好又回去。
当天晚上凌风的到来使情况更为恶化。既没有经过组织手续,剧社也没有接到通知,他却贸然提出了带走刘燕瑾的要求。事情自然办不成。凌非常坚决,说一定要经过组织把刘调走。但刘燕瑾没有那么乐观。“西战团”与火线剧社性质不同,又不属于一个组织系统,再说,剧社人员本来就调动不易,她又是台柱子。
刘燕瑾在忐忑不安中等待着进一步的消息。3月10日,剧社开始整风,她心不在焉。她参加学习,但她觉得自己是个局外人,别人的发言一句也听不见。学习文件,很好,很合适,正好可以掩饰她的不安情绪。她的眼睛顺着行一个字一个字的看下去,心却飞到了“西战团”,“陪伴着他们行军,陪伴着他们谈笑,陪伴着垂头丧气精神痛苦的凌风”。她下地劳动,低头干活不休息。手掌磨起了泡,泡又磨破了,也不感觉得奇怪,更不感觉到痛。她像一个呆子似的跟着别人乱跑,没有思维,也没有灵感,剧社热烈的整风、学习、生产,对她没有丝毫刺激。她的一颗心都在凌风身上。
在深深的焦虑中,她炸着胆子又找了指导员。他很不满意,严厉批评了她,最后指导员说他也没有办法,只有等待组织上的决定。
不用等多久,13日,组织上就告诉她“不能走”。组织的理由有两条,第一,刘是党员,凌是群众;第二,火线剧社属于军队,“西战团”是群众团体。刘知道这是她无法抗拒的,她深深感叹:“组织纪律呀,打破了那迷人的噩梦!”
深陷于热恋中刘燕瑾无法自拔,感觉“天是黑的,地是黑的,交流的空气也是黑的”。她总觉得凌风会给她留下一封信,哪怕是几个字,写明了他的去处,可以使她安了心,从而作长期的等待。她并未等到这封信,但她还是决定等。“虽然我也知道这是一种可能很小的希望,我也曾受遍人们的讽刺、谩骂,可是我的心却无时不飞向那有他住着的遥远的地方,任何人的力量全拉不回了我的心,任何人的爱都使我难于接受。”
“西战团”于4月初离开晋察冀边区返回延安,刘燕瑾一直留意着这个团体的信息。6月1日,她终于从报纸上看到一则消息,又哭又笑,向大家报告:“西战团到延安了,在中央大礼堂演出《把眼光放远一点》”!《把眼光放远一点》正是冀中的剧啊,刘燕瑾饰演“二老婆”,很是入戏。
9月份,刘燕瑾的战友中有多人(包括火线剧社的两人)调往延安,她按捺不住,向组织提出了要求,并给凌风写了信。结果又一次陷于绝望的孤独里,感叹“月圆人不团圆”。
12月,她在整风运动中“总结清算了我从历史发展以来的一切男女关系,从思想上从具体事实上来找出它的根源、危害及结果”。她说她在几次恋爱中都违反了政治原则,因为对象全是非党员;她说她有高度的强烈的“自信心”,党不可教育的人,自信可以培养,党了解的落后分子,自信可以由自己的手来改造成为进步的;她甚至不可思议地把自己贬低为与敌人的“桃色间谍”类似的角色,认为“因为自己的一种轻浮的风骚的调情的作风、风度,扰乱了周围的男人,激动了他们情绪的不安与混乱”。
但即使这样“触及灵魂”的批判与忏悔,仍不能使她忘记凌风。1945年3月8日如期而至,看到“纪念三八大会”几个字,她感到“血液忽的一家伙冲到了脑顶”。她想起三百六十五天以前的那一天,想起那一天刮着大风沙的白日,尤其是起了上弦月的半阴的夜晚,她感觉“这悠长的岁月是用痛苦和悲哀充实起来的,这悠长的岁月是用眼泪所洗过的日子”。她强抑住心中的锐痛,全身心投入新剧的排练中。她刚获得根据地红色文艺代表作品之一《王秀鸾》的主角,体验生活,卖力劳动,外观已成为强壮能干的农妇,熟人直接叫她“王秀鸾”。她想让这样的强行压抑习惯成自然,好让心中的痛不那么尖锐。但周围的人们已经听不到过去无处不在的“大刘的笑”了。她则说自己“严肃了,对于过去一切的小资产阶级罗曼蒂克的幻想,一切不合实际的念头都应该置之高阁”。
正是在这样的场景下,王林觉得“还是追一下大刘为上策”。中间人传来刘燕瑾的回话,说对王林别的没有挑,就是嫌体力体格不是她所理想的,惟恐将来的夫妇生活不济。与此相关的即年龄问题。王林大她14岁,年龄和体能的差异是无可改变的事实,她如此回答,自然是不留余地。她关注着延安文艺工作者的动向。有人说延安的文艺工作队已经出发,不久将到华北各解放区,并说凌风也会到冀中来。刘燕瑾在殷殷期盼的同时,又怀着强烈的不安:如果他真的回来了,可是却带来了另外一个她,她该怎么办?
10月,刘燕瑾在固安的街上看见许多从遥远地方来的旅客,穿着破旧,精神疲倦。她在大街上不断问来人,从拼凑起来的隐隐约约的零星信息中确认他们是从延安和其他根据地来的,目标是东北。她希望不久会有那么一天,在相似的一群旅人中能看见她的朋友的归来。她从10月等到11月,“等待一个最大幸福的来临”。
11月10日,她终于等来了凌风的消息。这个消息却让她万箭穿心。
凌风在延安已经结婚!刘燕瑾竭力压抑住自己的情绪,当眼泪涌上眼圈的时候,一个转身又把它逼回去,嘴上说道“结就结吧!谁能管着谁呢?再说相隔这样远,我们又没海誓山盟过……”。她跟着剧社在霸县上汽车,又到新镇上船,一路沉默,直到在船舱里躺下,用大衣蒙住全身,才哭了出来。
1946年3月8日这个特殊的日子,刘燕瑾又一次记下了这场恋情带给自己的“悲哀与不幸”。
给她最后的打击来自凌风夫妻的一张合照。照片中的两个人甜蜜地微笑着,刘燕瑾深受刺激,“感觉他们在向我示威,在向我炫耀,是一个胜利者对于他的颓败的对手的骄傲的微笑啊,是一个对于战败者的鄙视而讽刺的微笑啊……”
她可能听说过,凌风的婚姻是“组织”安排,她没想到照片中的两人竟如此亲密。
受到“甜蜜暴击”的这一天,是1946年8月10日,两个月前,刘燕瑾已经与王林确定恋爱关系。8月24日,王刘二人成婚。
刘燕瑾与凌风的爱情不能圆满,确实有“组织”的原因,如果“组织”同意两人共赴延安,可能会有不一样的结局。但是,“组织”并不是导致他们关系变质的主因。如果曾经爱得痴狂的凌风如刘燕瑾一样选择等待,只需一年多,他们便可重逢。当然他们并不能预知需要等待多久,但无论如何,他等待的时间过于短暂了。时间和距离,从来都是深情的敌人,只不过战争年代的人们行事更加仓促而已。从根本上说,刘凌这段感情,不是败于“组织”,而是败于亘古而然的“人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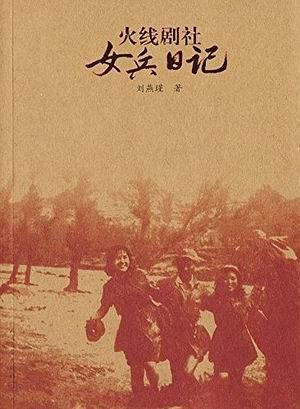
二
总有一些人,他们的婚恋过程特别曲折。不是因为他们轻忽这件事,恰恰相反,他们把婚恋看得太重、在人生中的意义太大,所以患得患失,难以成就;不是因为他们周围缺乏适当的对象,而是因为他们一直不能确定自己到底想要什么,对女性的欣赏趣味幼稚而固执,情商也往往低到难以正确判断对方的感受和想法。这样的人,现实生活中被称为“直男”。王林正是一个典型的“直男”。
“二八五团”(各根据地有大致类似的婚姻条件规定,28岁、5年党龄、团级干部即“二八五团”较有代表性)的组织纪律完全无法约束王林。他出生于1909年,革命资历深厚:1931年入党,曾担任青岛大学党支部书记——抗战时期冀中区重要领导之一黄敬就是他在此时介绍入党的;1935年参加一二九运动;1936年到东北军学兵队做地下工作,亲身经历了西安事变;1938年在冀中参加抗日战争,曾任冀中文建会副主任、火线剧社第一任社长、冀中文协主任等职,是冀中文化界的重要领导。
王林在文学创作上有相当高的成就:20世纪30年代初参加左翼文艺活动,出版小说《幽僻的村庄》受到沈从文赏识;抗日战争时期,他写下了大量小说和戏剧作品,其中长篇小说《腹地》是他在日寇扫荡的严酷环境下写下的壮美诗史;他还主持了多项重大文化活动——如影响很大的“冀中一日”征文。他与冀中军区司令员吕正操、党委书记黄敬、政治委员程子华、政治部主任孙志远等均交情甚笃。吕正操说他们几人相聚,总是谈笑风生,别有情致。吕还说他为人开朗,富有风趣,能接近群众,妇孺多识其名;王林长年累月走乡串户,熟悉地方风土,所知掌故最多,有冀中活字典、活地图之称。这样的经历、这样的个性、这样的工作环境和性质,都为他寻找理想伴侣提供了便利,但是,虽然其情史丰富而坎坷,其实在刘燕瑾之前,王林似乎还没有经历过一段真正投入而稳定的感情。
王林所梦想的女子,是“骄傲而美丽”。他不怕女人骄傲,只怕她们的骄傲仅只是外表的,一时的。至于“美丽”,他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完美主义者,对任何一点“不完美”——如嘴稍大,单眼皮之类都会介意。他最爱黄眼珠的姑娘——感觉好像有法兰西少女的诗和幻想!他最讨厌胖——胖子给他的印象永远不佳!
王林的情感经历颇为曲折。战前,他在北平有女友“仲英”,战争期间始终未通消息,他在日记中提及这位女友是在抗战胜利之后有可能再回北京的情形之下,可见他们并不具有牢固的感情基础;抗战初期追慕过较长时间的对象UL(王林日记中的代号,有些可以还原真名,但似乎没有必要还原),是一二0师战斗剧社的演员,并不在身边。1940年6月UL与王绝交,他随即转向H(可能即是“黄眼珠”的HS),觉得“她确实动人,她确实刺激了我这寂寞苦闷的心!”还说这是他唯一的春天,过了这春天,难见另一春天!但这段感情同样未得善终。1942年,因对LE失望,转而追求P(两人早有通信)。1943年初,经过两年多时断时续的通信交往,终于与P相见。传说中P极美,见面后却觉失望,以为不够美,但另一方面也认可P的美。不过P拒绝了王林的追求。抗战胜利,王林“光棍子心情乱飞”,更加乱了方寸。他一方面想象与“仲英”重逢的可能,或者“坚持一下”到大城市讨老婆,另一方面对身边的农村少女动情,先追求小嫣(或写成小然),再追求小馨(或写成小欣),仍然碰壁。
上述诸人中,只有LE对王林颇为主动,他们的关系也得到王林朋友孙犁等的认可。其他诸人大致属于王林一厢情愿。身材苗条、唇红齿白、神情高傲常常是低龄少女的特征,尤其是在严酷的战争环境下,具有这些特质的女孩更为低龄化。如追求过几年的UL,王林说“她太幼,但身段与鼻子,真是我幻想中的人物”。后期的两位农村少女都只有17岁。这种与实际颇为脱节的择偶观,害得他长期无法结束令其万分煎熬的单身生活。他的朋友对他“找对象”这件事有个评论,说他好像到电影院看电影,起初找个座,觉得不好。又找一个,还不好。后来才觉得以前找到的好,回去,可是已经被别人占了。最后只好坐个加凳。加凳不好,后来连加凳也没有了,只好立在太平门处看。这确是知人之言。王林认为这个比喻对他而言是深刻的,同时也是最辛酸的。
其实,如果仅仅追求外表,也不至于如此为难。他周围有些“速成”婚姻的例子。他的朋友史立德就“乘机观变,因势利导”,婚姻速战速决。某女士对史有好感,但又犹豫不决。史要她表白态度,她说:“让我们的关系自然发展下去不好吗?”史要她说痛快话,爱不爱他?她说:“事实的表现不很清楚的吗?”史要订婚,“何必这么急呢?”“我是这样急,急得等不得了!”“等我考虑考虑。”“考虑多久?”“三个月!”“不行!”“三天?”“不行!立刻答复!”“那么依着你!”“啊!这可是从你自己嘴里说出来的!”有位妇女干部旧历年刚结了婚,年后王林问她何政委是什么地方人,她说是陕西的,山西的?闹不甚清。王问其夫念“我”字是什么音,她苦笑着说:谁知道呢,我对他也没有什么印象!但王林是一个在根据地少见的具有纯粹文艺气质的人,外表只是他追求的表层,他的深层次追求,是艺术上的才华和共鸣。
从王林日记可见,他随时随地记录山川风景,故事人物,着意积累创作素材。作为有“冀中莫里哀”之称的戏剧家,他对周围人物尤其体察细致。他的日记中有从水塘中窜出追着他们要通行证的光屁股“中国新主人翁”,有魅力型群众领袖韩老祥、“大眼侯”等,有识字测验得第一但乱用新名词的老太婆,有筋肉紧张地努力学文化的老马伕……他对环境有着诗意的感受和描写能力。1940年5月4日五四纪念大会时,他和朋友躺在井台上的海棠树荫中,时而张林出来,他拉着提琴,声调缠绵。王林说“晋东南最叫我永要回忆的是海棠花和提琴”。说时一阵风过来,树上的白蕊纷纷而下。他具有艺术家的欣赏情趣,战争倥偬之间,仍然喜欢读经典名作,喜欢读充满美感的沈从文、朱光潜等人的作品。他说,“接受遗产,读古典作品,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愉快的。莫里哀时代距离这昝那么远,地域国度又大不相同,然而仍能叫读者感到栩栩如生。古典作品真乃人类性灵永恒不灭之光也。”他在战斗环境中读《大公报》上的文艺旧文,如沈从文的《湘行散记》,感觉别有情趣。沈从文是他在青岛大学读书时的老师,《湘行散记》写于1934年,文笔自然淳朴,流丽迷人,呈现的“湘西世界”忧伤而美丽,是有名的美文。他还自承受梁实秋的影响很不小,“由梁而朱光潜,于是资产阶级一套唯心论的艺术论,接受得真不少——当然其中未必都是反动的一部分,好的遗产也有。然而艺术与政治,非政治观点,人性观点,艺术自由观点却是直接从他们(那)儿学来的”。虽用的是批判的语调,欣赏和接受都是真实的。
更为重要的是,王林是一位具有独立思考意识和能力的真正的艺术家,具有环境和时代无法彻底化除的独立见解。1939年9月1日,他与梁斌谈起小说和剧本创作问题。他说:凡是主题和思想先行的作品,都必然走上宿命论的结局,因为故事有预定的框架,人物只能成为抽象思想的符号。“这虽然也可能是写实的,然而是宿命论的唯物论。”相反,如果以人物性格为主体展开故事,则可展示人的能动性,这样的创作符合“辩证唯物论”。总之,成功的小说和戏剧是人物性格决定故事的发展,而不是故事决定人物。这是对文学本质相当深刻的理解。他专注创作,不愿做其他工作;他设想即使在胜利之后,也选择像肖洛霍夫那样隐居乡间写作,而不是担任什么领导职务。他在敌寇的残酷扫荡中坚持不离冀中,以近距离观察和感受战争,记录下中华民族的伟大抗争。他在地道口和“堡垒户”土坑上写下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长篇小说《腹地》。根据地的文艺创作崇尚宣传动员功能,多短平快作品,写长篇不但不被倡导,且受批评和质疑。1940年,王林在太行山上写下长篇小说《平原上》,即受到批评。批评者说“写长篇不能配合政治现实,等你写完了,时代也早过去了。并且在写时,也妨碍了最迫切的应时文章”。认为长篇可以等胜利之后作为战后回忆从容写作。但王林不这么想。他从不怀疑中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将属于中华民族,却不敢幻想自己能在战火中幸存,所以“不能不早些把时代的光和音收在文字上!”
在对婚恋对象的选择上,王林固然属于“外貌协会”,但经过外貌这道门槛的拦截之后,立即便是对艺术气质和艺术潜质的考量。抗战胜利后他曾倾心过的两位乡村姑娘小嫣(小然)和小馨(小欣)——连名字都被他诗化了,他显然是“听音取字”,所以会有不同写法,而这两位姑娘更可能叫“小燕”和“小杏”——令他心动,但对小嫣,他在认识当天即赶去她的村庄,“再研究一下她在艺术上有何发展前途,是否艺术的低能儿?看她的身段、表情、体态、眉眼,至少能在话剧上发展。是否能在音乐上更有特长,今天即可研究出来。总之,她的声音也是圆润透明柔和的”;小馨是小学教师,这令王林满意,他迫不及待地让她读小说,学英语,练写作,并说她在艺术上一定会有成就。可见,长相美丽是他择偶的第一个条件,但并不意味着是最重要的条件。
王林“打光棍三十多年,永远梦想着像小说中似的有一个传奇般的恋爱”。但他的两条择偶标准,在彼时彼地,即使满意一条也难。他的长期单身,简直是“咎由自取”。王林对私生活严格自律,鄙弃“杯水主义”,这个表面上“顶快活”的中年人,内心却骚动得厉害,有时难以自制。1944年最后一夜,有老婆的团圆去了,王林“对明月发誓:出校后第一要搞老婆,打光棍太无价值”;“在这新民主主义社会中打光棍简直是可耻!简直是懦夫!简直是无用之辈,可耻!”
刘燕瑾和王林,这两个似乎不会选择对方的人,却在各自与别人来来回回擦肩又错过之后认定对方,并很快结为夫妇。
三
王林是火线剧社的社长,刘燕瑾是该社主要演员,他们当然很早便相识共事。但他们一直没有走进对方的心里。于刘燕瑾,这个活泼的女孩身边围绕着追求者,1944年后又因与凌风的恋情而遍体鳞伤,年长的领导王林不会是她的理想良人。于王林,他非常欣赏刘燕瑾的艺术才华,曾几度动过追求刘燕瑾的念头,但刘体态的“胖”(他在日记中有时称她为“胖刘”)却是他最为讨厌的女性外表特征,所以一直未下定决心。
刘燕瑾人称“大刘”,剧社同事编派的歌谣中描写她“大刘胖,头发薄”。她有个外号叫“二胖”,因为她有“两个凸出的松驰的甚至下垂的乳房”。刘本人虽为此而悲哀和悲观过,一度认为这是她生平中最大的遗憾。但当她提高觉悟后,认为从小资产阶级观点看来,这固然是一个不可弥补的缺陷,但是如果站在劳动阶级的观点看来,那么会更实际,因此便不以为意。在扮演王秀鸾期间,因卖力参加体力劳动,她比以前更粗壮了,体重比上年增加十斤,老百姓夸她“身大力不亏”。
刘燕瑾的“胖”是王林特别讨厌的,但她的艺术才华又对他构成无法忽略的吸引,因此,从王林一面说,难免陷于“天人交战”。
1944年5月22日,王林日记中说“刘燕瑾在《两方便》中的动作,饰老婆,动作极有节奏”。他应该动了追求的念头——其实此时刘燕瑾正陷于对凌风的刻骨相思中——但一方面害怕她将来更要胖,认为不如到新民主主义农村中找新民主主义少女更有趣,天真、单纯和朴实,另一方面又认为刘燕瑾这个天才也是很稀少的,失此机会,或将成终身遗恨。9月14日又看刘燕瑾演戏,说“刘燕瑾表演术真是好,风趣横生,我就是怕‘战胜’不了”。演出前,他溜到后台在熟人丛中与刘燕瑾乱谈了几句。16日夜晚,经过熟思,王林准备“对她下决心了”,说她忠厚而富于热情,“过去老讨厌她的胖是没有道理的”。他打算给她写信,要她帮忙抄个《前线》中的插曲,借以拉拢关系。
但从后来的日记可知,王林并未真正“下决心”,更没有行动。
1945年9月,在抗战胜利的喜悦中,王林与火线剧社诸人重逢。这一次,他感觉“大刘显得特别漂亮”,很后悔上一年有机会接近而自己则冷冷如也。王林虽又一次说不清自己到底是希望一个能上台的好演员,还是一个貌美性柔能给他抄抄文章的姑娘,但最终,“才华”压倒“美貌”,他决定“还是追一下大刘为上策”。不料遭到了拒绝。
王刘二人,彼此都不是对方的首选,都带有“退而求其次”的无可奈何。对刘燕瑾而言,凌风没有选择她,她只好另外选择,老干部王林是文艺内行,为人正派,性格幽默,是个不错的婚姻对象;对王林而言,他无法求得两全其美,最后舍表求里,折服于刘燕瑾的艺术才华。从后果看,这是一桩旗鼓相当相濡以沫的成功婚姻。王林后来的文名并不彰显,与他在冀中的地位和实力不相称,更有甚者,他“像写遗嘱那样”写成的《腹地》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第一部被批判的长篇小说,因其真实而生动地展现了根据地民众生活——包括“暴露黑暗”,被扣上“自然主义”的帽子。三十多年间,他不断地修改《腹地》,直到改得面目全非,而这时,时移世易,他的作品又一次与时代背道而驰。1985年王林身后面世的《腹地》新版让他的儿子“无法卒读”,而读完1949年老版后却受到极大震撼。这是文学史上一个带有悲剧性的故事,王林这位被评论者认为是“冀中抗战文学最有成就、最具代表性的作家”也被笼罩上了一层悲剧色调。
刘燕瑾显然是个好妻子,她也是个好演员——王林的艺术眼光不容置疑,在判断刘燕瑾艺术才华方面同样完全正确。她是冀中女演员中最出色的一位,而且艺术生命悠长,解放后出演过话剧《叶尔绍夫兄弟》《同甘共苦》,歌剧《白毛女》,电影《葡萄熟了的时候》《昆仑山上一棵草》《平原游击队》《活着》等,曾与于兰、郭兰英、葛优、巩俐等明星配戏。王刘夫妇还养育了两个富有艺术才华而且境界超越的儿子。
战争年代,青年云集,若对婚恋毫无规制,便难以形成严格纪律,无法凝聚强大战斗力。革命队伍中的婚恋,确实极大地受制于“组织”,组织不同意,肯定结不成婚。但从本文几位主人公的经历看,“组织”的作用也并非漫无边际。至少同样难以抗拒的还有人性:分离,移情别恋,感情的厚度不足以支撑长期等待,等等。
俗语云:“好看的皮囊千篇一律,有趣的灵魂万里挑一。”王刘二人最终选择了“灵魂伴侣”,携手共赴人生旅途。应该为他们庆幸。
参考文献
刘燕瑾:《火线剧社女兵日记》,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版。
王林:《王林文集》第5卷“抗战日记”》,解放军出版社2009年版。
王端阳:《母亲刘燕瑾和凌子风》,刘燕瑾《火线剧社女兵日记》附录。
王端阳:《父亲王林和他的<腹地>》,《名作欣赏》2016年第31期。
,免责声明:本文仅代表文章作者的个人观点,与本站无关。其原创性、真实性以及文中陈述文字和内容未经本站证实,对本文以及其中全部或者部分内容文字的真实性、完整性和原创性本站不作任何保证或承诺,请读者仅作参考,并自行核实相关内容。文章投诉邮箱:anhduc.ph@yahoo.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