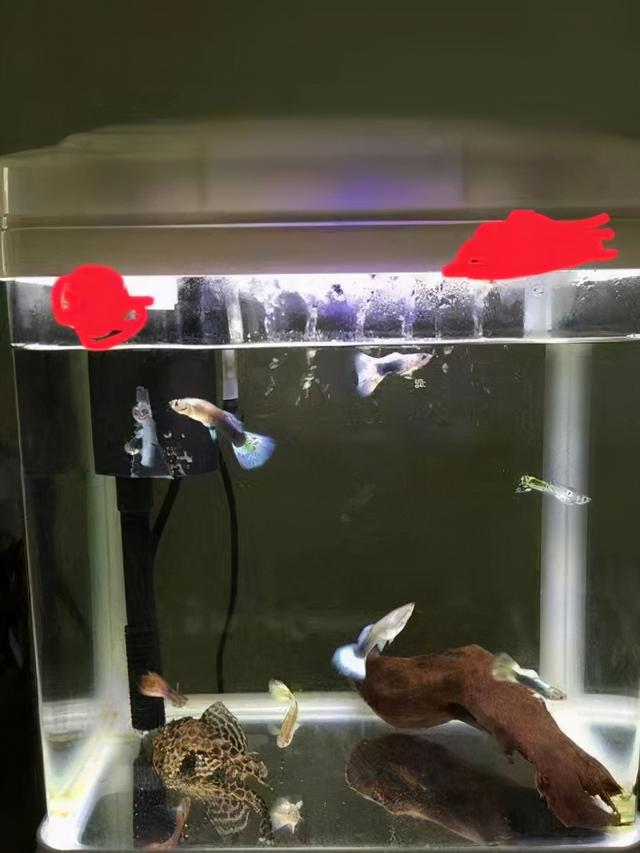中国陶器发展为瓷器的历史(世界许多地区都不约而同地发明和烧造了陶器)
本文刊载于《三联生活周刊》2019年第34期,原文标题《瓷之美:从形制到文脉》,严禁私自转载,侵权必究
没有哪一门艺术形式,如瓷器一般与人类的文明进程和日常生活如此息息相关。这让它有着强大而稳固的审美惯性,不只是在造型和装饰上,更是在人的情感依赖、成长记忆甚至文化族群的集体潜意识中。
文/贾冬婷

复原曜变天目的日本名匠长江惣吉在濑户工作室(张雷 摄)
美的魅惑
瓷器回到源头会是什么样子?
带着这样的疑问,我去看了一个名为“中国白”的展览。严格地说,这是一个当代艺术展,只是将材料限定为白瓷,其余从造型,到功能,再到观念,已经跟传统瓷器无关了。在这些出人意料的作品中,瓷泥从技术和实用中分离出来,仅仅成为艺术表达与个人认知的材料,反而赋予了它全新的生命形态。
某种意义上,这些作品打破了瓷器美学里中与西、传统与当代之间的割裂。比如韩国艺术家Taxoo Lee,他收集了景德镇明清两代被遗弃的陶瓷碎片,将这些古老的青花瓷片用作碗底,重新拼接上新的白瓷碗壁,变成一件缝合古今的艺术品。Taxoo Lee说,当他看到宋代的白色陶瓷碎片在被丢弃后堆成了一座巨大的山,他直观地感受到饱含生命力的文化冲击。这些微不足道的碎片无论年代多久远,都无法成为文化遗产,于是他想创造一种真正意义上的“重生”,以明确的接缝联系过去和现在,展示瓷的无限生命力。

韩国艺术家Taxoo Lee

Taxoo Lee收集了景德镇明清两代被遗弃的陶瓷碎片,做成一件缝合古今的艺术品“重生”
“其实‘中国白’不是一个材料概念,而是一个审美概念,同时也是时间概念、地域概念、族群概念、情感概念。它是中国对待白色陶瓷的丰富和诗意化的表达,也是东西方交流史中最具代表性的中国符号之一。”“中国白”大奖赛评委会主席、清华大学美术学院陶瓷系主任白明认为,这种白不追求纯粹的白,不追求无瑕的白,它追求类白、类玉,追求君子之德,追求简单中的丰富。定窑的白瓷也好,德化的白瓷也好,都是这种审美下的产物。在他看来,中国瓷器“南青北白”格局下的另一大类——青瓷,也是纯粹之中的万有,龙泉窑、汝窑、官窑的青瓷,还有唐代的秘色瓷,都属青瓷系列,但是却有截然不同的视觉感受。
十几年前,白明曾花了几年时间在景德镇研究传统制瓷工艺,最初是因为好奇是什么促使景德镇成为世界上唯一的千年窑火不断的城市。而当他深入传统的时候,也同时感到传统的强大魅惑,以及这种魅惑带来的双刃效果。
“一方面,不知不觉地被古代的技术和工艺感染。比如说瓷土是从山上挖来的,那么怎么把石头碾碎呢?借助了周围的环境,用水碓。随之而来的难题是,水碓是机械装置,作用力在一个点上,那个点的石头可以碾得很细,那么其他点呢?景德镇人很聪明,他们发明了一个可以替代人工拨弄石头的装置。最下面是大石板,石板上砌木头板。通过撞击,石板震动,传递给木板,木板又把外围的石头弹回去,不断会有小石头弹到中心位置。石板用的是大青板,因为最有力量,木板则是泡桐树做的,这种木头最具有弹性。而且,坑的下面一定要加一些松土,不能像水泥一样砌得很平,这样才能引发震动。这个装置非常了不起,它既不会被上面的力量砸碎,又能产生震动,而且完全是由经验而来的。这样的细节,当你体会到的时候,会觉得充满魅力。也正是这种技术上的独特性,带动了景德镇一直到今天,自《天工开物》记载起就没有什么改变。”
“这种魅力的另外一面,就是容易把人带走,会皈依这种技术。而随着你越来越熟练地去掌握技术,审美也会日复一日地跟它趋同了,所以景德镇周边大都是模仿传统的复古者。”白明认为,瓷器作为一个非常古老的艺术门类,已经形成了稳定持久的审美体系。这个体系非常强大,一方面瓷器得益于这种强大,维持了千年兴盛。另一方面,这个体系也非常泥古,某种意义上成为一种束缚。“还原一件宋代的青瓷,或者一件元代的青花,借助今天的技术仿制并不太难,但一个经典的样子不是传统。传统其实是一种审美,一种精神,核心是创新。”

清华大学美术学院陶瓷系主任白明(王旭华 摄)
相对于技术崇拜,或许我们更应该从文脉中去看传统瓷器。“从青白釉开始,制瓷的中心就移到了景德镇,高冷审美逐渐让位于更加朴素亲切的青白瓷。有了青白瓷,才有了200年后的青花瓷,青白釉下透亮的蓝,跟高温、跟景德镇独特的高岭土都有关。其后,景德镇的釉变更是让人目不暇接:青花流行后出来了釉里红,釉里红流行后有了高温颜色釉,高温颜色釉之后有了古彩,古彩之后有了粉彩,粉彩之后有了浅绛彩。”白明说,景德镇之所以千年窑火不断,就是因为几乎每一个100年,都会产生一个新的伟大的品种,否则不会走到今天。
尚玉
严格说来,中国并非是陶的国度,而是瓷的国度。一团泥经过千锤百炼,才诞生了震撼世界文明史的瓷文化。在瓷诞生以后,中国的大地上出现了各种不同的窑口、不同的材质、不同的烧制方式、不同的造型工艺,共同形成了迥异的审美规范。
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侯样祥指出,仍需深入研究的是,何以世界许多地区都不约而同地发明和烧造了陶器,但是瓷器的发明权却最终归属于中国?
以通常观点来看,瓷器有三个先决生成条件——瓷土、烧成温度和施釉,中国恰巧都满足了。侯样祥认为,这三个条件,其实中国都不具有唯一性优势。而将中国瓷器发展史放置到文化发展史中去分辨之后,便会意识到,“尚玉”,可能是中国人发明瓷器的外在文化因素。
侯样祥告诉我,考古发掘资料表明,至晚从河姆渡文化开始,“尚玉”文化已经在中国产生,并且开始流行起来。此后至今的7000多年里,形成了一部绵延不断的“尚玉”文化史,这在人类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究其原因,不外乎两个:一是作为“石之美”的玉,具有与生俱来的审美特征,这可以称作自然原因;二是人文原因,至晚从春秋战国时期开始,玉被儒家道德化、宗教化、政治化之后,便具有了深刻的思想性内涵。于是,一些耳熟能详的“尚玉”口语,如“古之君子必佩玉”“君子于玉比德焉”“君子无故玉不去身”等流行了起来。在中国古代社会,尚玉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文化风尚。
“在这种非常特殊的社会文化氛围中,面对陶窑窑壁或印纹硬陶等器物表面,偶尔又反复出现的局部美丽‘光泽’,中国人显然会更加敏感,绝不会只停留在‘窑汗’等粗浅的认识上,会自然而然地将它与美玉相联系。于是,尽管‘釉陶’可能并非中国人首先发明和使用,但中国人‘后来者居上’地在‘釉陶’的基础上发明了瓷和创烧了瓷器,是完全可能的。”侯样祥认为。
将瓷与玉直接相关联,甚至“以玉喻瓷”蔚然成风,在唐代已经出现。侯样祥梳理,唐代,茶圣陆羽在《茶经》中说“越窑类玉,邢窑似雪”,他故而认为“邢不如越”;诗人陆龟蒙在《茶瓯》诗中有“岂如珪璧姿,又有烟岚色”;两宋时期,文人苏东坡在《试院煎茶》诗中有“定州花瓷琢红玉”“分无玉碗捧蛾眉”;宋徽宗在《大观茶论》中有“盏色贵青黑,玉毫条达者为上”;南宋文人蒋祈在《陶记》里,更是直接用“饶玉”来称呼景德镇的青白瓷。到了明代,科学家宋应星在《天工开物》中认为“陶成雅器,有素肌玉骨之象”;文人高谦在《遵生八笺》中有:“茶盏惟宣窑坛盏为最,质厚白莹,样式古雅……宣窑印花白瓯,式样得中而莹然如玉。”侯样祥说,不可否认,在历史文献里,用于比喻瓷器的还有“千峰翠色”“烟岚色”“秋水澄”“春水”“绿云”“冰”“霜雪”“雨过天青”等,但是相比较而言,“类玉”仍然是形容瓷器最集中、最贴近、最具代表性的词汇。
在不同时期、不同风格的瓷器背后,“尚玉”也是一条潜藏的美学主线。侯样祥指出,至晚从唐代开始,伴随着瓷器“南青北白”大格局的最终形成,在文人文化中,瓷器“似玉”度的高低,已然成为衡量其审美性乃至思想性高低的重要尺度。代表性的如越窑秘色、邢窑透光白瓷、景德镇青白瓷、南宋官窑和龙泉窑的厚釉青瓷等,都突出体现了对美玉色泽和质地的追求。
原始青瓷出现于商州时期,属于由陶器向瓷器的过渡,早期釉色发灰、发黄,多是礼器和明器,造型多仿金属器。到了唐代中期时,青瓷经历了一次自我觉醒。越窑开始在造型上摆脱了青铜器和漆器的束缚,出现了大量的日用器皿,进入人们的日常生活,而且已经烧造出近乎完美的青色釉,成为当时的众窑之首。不仅陆羽推崇其为天下第一,陆龟蒙也写诗赞美:“九州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
所谓“南青北白”,与南方的青瓷遥相呼应的,是北方的白瓷。白瓷出现在北朝,晚于青瓷,唐代的邢窑标志着白瓷的成熟。如陆羽所说“越窑类玉,邢窑似雪”,“似雪”也是无奈的比喻,因为当时已经找不到另一种人造物品去形容白瓷了。定窑的白瓷不那么像玉,更像象牙,白中闪点黄,也是贵重的东西,被人喜爱。而明代德化的白瓷就像玉,被叫作猪油白、鹅绒白,如羊脂玉一般,独一无二。
故宫博物院器物部主任吕成龙告诉我,瓷器尚玉,主要体现在釉有玉质感,这是历代一直追求的。尤其以南宋官窑瓷器最为明显:“瓷器的釉是一层玻璃,上釉就是为了遮盖胎体。按说上一遍釉就可以了,但南宋官窑多次上釉。上一遍釉,在窑里低温烧,之后多次上釉,达五六次,再烧,现在我们能从根部看出一层一层的釉。釉越厚,玉质感越强。所以有些南宋官窑青瓷的釉比胎还厚,甚至超过胎体两三倍,就是为了追求玉质感。”吕成龙说,景德镇烧制的青白瓷也是一个代表,宋代就被称为“青白玉石”“假玉器”,到了明清时期也是一样,釉烧出来比较厚和润,青中闪白,白中闪青。李清照的《醉花阴》里有“玉枕纱橱”,这个玉枕不是真的玉做的枕头,就是青白瓷枕,“玉枕纱橱,半夜凉初透”。
文献记载,宋代汝窑以“玛瑙入釉”,想必也是为了要获得美玉的效果。陶瓷研究者、《宋瓷笔记》作者刘涛告诉我,汝瓷的釉,呈一种淡淡的蓝色,釉层比较薄,质地又很细腻,不是那种透明釉,是乳浊釉,所以能显出一种玉质感。不过,“玛瑙入釉”如今已经被神化了,好像釉中只有加入玛瑙,才会烧出富有玉质感的瓷器。其实,玛瑙就是纯粹的二氧化硅,同石英的成分相似。以玛瑙入釉,是完全可能的,但这样并不会产生什么特殊效果。最早仿烧汝瓷的朱文立曾告诉刘涛,他最初配釉时也曾用过玛瑙,但很快就放弃了,因为他发现玛瑙完全可用低成本的石英替代,而效果是一样的。
刘涛指出,古代瓷器仿玉主要在釉上下功夫,注重“以釉覆胎”,而相对轻视胎的改良。其结果往往是,瓷器虽有玉的光泽,却无玉的致密。他说,就仿玉的整体效果看,宋代景德镇的青白瓷是最为成功的。拿现代标准来衡量,也只有它最接近现代细瓷的标准。也是在青白瓷这一划时代品类的基础上,才出现了后来的元青花、明五彩、清粉彩。而即便是这些彩瓷,“莹润如玉”也一直是最高审美追求。

2019年,德国图林根州举办的一个东亚瓷器展(视觉中国供图)
美的两极:“芙蓉出水”与“错彩镂金”
中国的瓷器史,基本上是一部编年史。哪个朝代,出现了什么风格;哪个时期,诞生了哪件名器。但如果将它们古今并置,难免会产生各领风骚、难分伯仲之感。那么,如何去欣赏不同的瓷器呢?
“唐瓷看形,宋瓷看釉,元青花看画,明清青花看染。”已故古陶瓷学者刘新园曾总结出这一鉴赏要诀。刘涛解释,唐代瓷器多仿西域金属器、玻璃器等,中土固有器物中也融入胡风,所以造型有一种独特的美感。宋代是制瓷业大发展、大繁荣时期,瓷器品种丰富,花样繁多,在传统的青瓷、白瓷和黑釉瓷的基础上,又出现了南方青白瓷、汝窑天青、耀州窑橄榄青以及南宋官窑、龙泉窑的粉青之类厚釉青瓷等。宋瓷不仅重视釉色之美,更追求釉的质地之美。如黑釉瓷器已不再像过去那般单调,出现了兔毫、油滴、木叶、酱斑、玳瑁等富有美妙花纹和丰富质感的品种。元代青花瓷的最大成就在于它的绘画装饰。绘画题材和样稿有的直接取自当时的戏曲版画,画技也很高,已完全可与纸本绘画媲美。明清青花借鉴国画渲染技法,以达到“墨分五色”的效果,画面更富有层次和立体感。
刘涛认为,古瓷的看点还不止这些,每个时代都有能够代表这一时代风格的瓷器品种或工艺现象。比如宋金时期磁州窑类型瓷器的“化妆土艺术”,由于当时制瓷原料品质不高,胎质粗劣,为改善其外观,制瓷时往往在已成型的器坯上敷一层质地细腻的泥料,也就是化妆土,进而用剔、刻、划、镶嵌、彩绘等技法施加装饰,主要品种有剔刻花、珍珠地划花、白地黑花和红绿彩等。化妆土对装饰形式和美感往往有着直接的决定作用。像剔刻花装饰,往往就是利用化妆土和坯胎烧成后质地与颜色的不同,使花纹凸显出来;白地黑花装饰则需要在未干燥的化妆土上进行,这就如同在宣纸上作画,所以才会有纸本水墨的效果。可以说,没有化妆土,也就没有磁州窑风格的艺术。还有清代粉彩工艺,粉彩的出现导致景德镇釉上彩绘瓷器美感的变化,尽管这个可能不那么“正面”。粉彩出现于康熙晚期,是在五彩的基础上,受珐琅彩的直接影响而创制的釉上彩品种。由于最初多采用进口颜料,并吸取西洋画法,故又称“洋彩”。它的色彩较五彩更为丰富和艳丽,而且由于改变了五彩单线平涂的画法,采用渲染没骨技艺,画面也更具纸本绘画的效果。这样,粉彩很快就取代了五彩、珐琅彩的地位,成为釉上彩瓷的主流。景德镇釉上彩绘瓷器的装饰风格也为之一变,即由过去的浑厚刚健衍变为纤细柔丽。这一风格在雍正、乾隆制品上被表现得淋漓尽致,并化作一种工艺传统或审美定势,影响直至今天。
“在中国陶瓷史上,尽管各种风格层出不穷,但集大成者就是两类:一是宋代五大名窑,一是明清官窑,可谓双峰并峙,各领风骚。”吕成龙说,“从这些年的拍卖市场上看,两者也是难分伯仲。成交价最高的是北宋汝窑天青釉洗,2017年香港苏富比以2.943亿港元拍出,第二高的就是明成化斗彩鸡缸杯,2014年香港苏富比拍出2.8亿港元。”
宋瓷和明清瓷器双峰并峙的格局中,刘涛注意到一个有意味的现象:尽管明清瓷的技术和工艺水平远远超越了宋瓷,但在审美方面,明清瓷的声誉明显不如宋瓷那么广受推崇。他说,从文献上看,把古瓷作为珍玩来收藏和欣赏,并形成风气,是从明代开始的,“论窑器必曰柴汝官哥定”,即便是在彩瓷风行之际,宋瓷也深得文人雅士的珍爱。之后,宋瓷被进一步提纯和升华,成为高格调、高境界美的象征,并被抽象为一个堪与唐诗、宋词、元曲以及宋元山水画、明清园林等并列的“文化符号”。

明仇英《蕉阴清夏图》局部
陶瓷研究学者叶喆民就曾在其权威著作《中国陶瓷史纲要》中谈道:“宋代瓷器多以其淳朴秀美的造型,配以绚丽多彩的釉色,或变化万千的结晶、片纹而引人入胜,独步一时,至今仍称颂于世,令人叹为观止。可以说是将形态、色彩、纹理乃至光亮均调和得恰如其分,达到了科学技术与工艺美术表现的高峰。而后来的元、明、清瓷器则逐渐变成以绘画装饰为主体,多忽视前代以形态神韵为根本的特征。这一点或是宋瓷之所以驰誉中外无与伦比,为后人所不及的独到之处。”
为什么宋瓷审美更受人追捧?美学家宗白华先生认为,如钟嵘《诗品·中》中所写,“谢诗如芙蓉出水,颜诗如错采镂金”——“芙蓉出水”和“错采镂金”,可以说代表了中国美学史上两种不同的美学理想。宋瓷是“初发芙蓉,自然可爱”之美的一个代表,明清瓷则代表了“错采镂金,雕缋满眼”的美。宗白华指出,魏晋六朝是一个转变的关键,划分了两个阶段。从这个时候起,中国人的美感走到了一个新的方面,表现出一种美的理想,那就是认为“初发芙蓉”比之于“错采镂金”,是一种更高的美的境界。
刘涛分析,所谓“初发芙蓉”的美,与糅合儒道诸家强调委婉含蓄、温润和柔的“中和之美”有着直接的对应关系。也因此,芙蓉出水的美,不仅具有审美的价值,而且还具有伦理道德的价值,形成一种独特趣味和审美理想。即使在今天,它与许多中国人的审美心理仍保有一种深层的同构关系。这也就不难理解,在精英文化语境中,为什么“初发芙蓉”的宋瓷比“错采镂金”的明清瓷更受推崇了。
不过,刘涛说,这两种不同美感的关系也绝非尖锐对立、水火不容,而是一直互为周济与参融的。即使是在错彩镂金的形式中,也同样可以透出高雅的境界。比如清代中前期的某些五彩、珐琅彩和粉彩等官窑瓷器,顺合清初“归雅”之审美风尚,就具有清真雅正之美。
那么,从“芙蓉出水”到“错彩镂金”,这样两极的转折是怎么发生的呢?
刘涛说,一方面来自于工艺技术的推动。实际上,所谓一色明净、“初发芙蓉”的宋瓷之美,集中体现在那些原本就以质地、釉色取胜的单色釉瓷器上,如定窑白瓷,越窑、耀州窑、汝窑、南宋官窑、龙泉窑青瓷、景德镇青白瓷等,其实当时也有不少窑口展现出热衷装饰的倾向,只是囿于当时的工艺技术,彩绘装饰不能更全面更自由地得到发展。元、明之际是中国陶瓷发展的转折期,景德镇成为全国窑业中心,釉上彩的使用,釉里红的创世,特别是青花瓷器的异军突起,结束了瓷器以单色釉为主的历史,迎来了彩瓷飞跃发展的新局面。这一时期景德镇改进了瓷胎配方,加大了高岭土用量,从而烧制出精细的薄胎、脱胎瓷,这些优良的白瓷更容易与彩绘联姻,也出现了更加丰富、精致的彩瓷。
另一方面,明中晚期,瓷器鉴藏风气出现了明显的求变与转型,国外学者将这一时期称为“转型期”。刘涛分析,本来,明早期还是以赵宋为贵,青花、五彩在当时文人眼中是很俗气的东西,但到了嘉万年间,以成化斗彩为代表,被誉“为古今之冠”“价与古敌”。其地位的攀升,实际上也反映了当时文人趣味的变化,即“精工而雅”的美开始为文人所欣赏和推崇,而以往文人往往是排斥艺术的视觉美——感官愉悦的。
万历以来,大明江山已是摇摇欲坠,官窑烧造也因时局几近停废,而景德镇的商品瓷生产却在不断扩大的国内外市场的拉动下得以持续增长,并呈现出新的面貌。就装饰来看,题材多有新意,彩绘趋于细腻精工,特别是山水、花鸟以及戏曲人物等,别开生面。鉴藏风气与文人趣味的变化,士商阶层及精英文化与市民文化的合流,也使得晚明社会的文化样态更加多彩多姿和充满变数——文化中一切有趣的和无聊的东西都在这个时期的日常生活方式和艺术形态中得以折射或放大。
到了清代,尤其是康乾之世,瓷器已“无不盛备”,加之女真人的文物风俗与典章制度中本来就保留了较多的繁文缛礼,特别是在对外贸易和文化交往中更受到欧洲消费时尚的刺激,彩瓷装饰日趋繁丽。刘涛指出,包括制瓷在内的清代工艺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宫廷工艺的价值取向是“明尊卑,别贵贱”,将以“贵”为美的装饰风格推向极致,并影响到几乎整个工艺生态,这与两宋以及晚明时代由文人士大夫和民间艺人引领文化消费潮流的情况迥然不同。尤其是乾隆年间,更是将以“贵”为美的装饰风格推向极致,最大限度地追求材料的珍奇、工艺的精致和完美,这也让它日渐僵化并流于庸俗,异化为帝王权力意志包装的精致,走向了自己的反面。
刘涛认为,美与工艺的关系,有时是疏离的或相悖的。高超的工艺是双刃剑,它能创造美,也能毁灭美,当工艺一旦越过“合目的性”的界限,就容易走到美的反面。而且,一个普遍的艺术法则——艺术辩证法在这里同样适用:任何一种艺术形式和风格,当被推向无限的时候,或全部接受下来形成规范的时候,它的美便开始变异了。清代彩瓷“无不盛备”,精致的更精致,成熟的更成熟,这一方面反映出彩瓷工艺的高度发展,另一方面却也预示着这一工艺形式和风格行将走到尽头。

明《御花园赏玩图》局部
谁定义了瓷器审美?
在古代瓷器的研究前沿,近年来的视角已经发生了转向。北京故宫博物院器物部主任吕成龙告诉我,以前他们主要关注“看得见的东西”,瓷器摆在那,看是什么型、什么釉、什么彩、哪个窑的。现在更关注“看不见的东西”,即瓷器本身的历史土壤和文化内涵。
吕成龙说,对于故宫博物院来说,这些年主要是通过挖掘整理一些文献来联系当时的社会背景,特别是内务府造办处的《活计档》,就是记录清代宫廷造办处每天干了什么活、做了什么器物,包括珐琅作、玻璃作、玉器作,也包括瓷器作。景德镇御窑瓷器的制作,有大量详细的记载,都能跟实物对得上。《活计档》主要是从雍正时期开始的,一直到宣统,可惜之前的宫廷档案都没了,很可能是历史上宫廷着火给烧没了。《活计档》中也记载了皇帝怎么来修改器物的造型、怎么修改器物的釉色、落不落款等等,从中可以一窥雍正、乾隆等皇帝的审美,也可以看出帝王意旨是如何影响瓷器风尚的。
所谓“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各个朝代会形成各自不同的风格,都不是空穴来风,都与当时社会背景、帝王喜好有密切关系,这在清朝康熙、雍正、乾隆时期尤为明显。刘涛指出,三朝君主对瓷器都有特殊兴趣,而且直接干预瓷器制作,这在中国历代君主中可谓绝无仅有。他们常常亲自规定器物的造型、纹饰、色彩,先绘成画稿或制成木样,然后交督陶官依样烧制。三朝期间,以官窑瓷器为先导,景德镇窑业日益精进,如彩瓷品种更为丰富,除原有的青花、五彩、斗彩、素三彩等外,又新创了珐琅彩、粉彩、釉下三彩、墨彩等,颜色釉瓷器也是五彩纷陈,远胜前代。
“康熙时期刚刚经历过明末清初的战乱,康熙皇帝干了几件大事——智擒鳌拜,平定三藩,收复台湾,把清代的江山稳固了,整个社会有种活力,这一时期的瓷器也以挺拔硬朗为美。比如棒槌瓶,一看就是挺拔向上的感觉,线条硬朗,釉质也坚硬,我们形容‘紧皮亮釉’。就连瓷器上画的龙,都是不可一世、非常有气势的,这与康熙这一朝的大环境是有关系的。到了雍正时期,社会趋于稳定,瓷器的一大特点就是文雅精细。这也与雍正皇帝本人的审美趣味有很大关系,他45岁登基,年富力强,此前就发生过储位之争,但是他不露山露水,很低调,实际上隐藏得很深。所以这个时期的瓷器也不事张扬,造型小巧俊秀,曲线柔和,文人气息特别浓。到乾隆时期又不一样,清朝发展到鼎盛,乾隆皇帝好大喜功,喜欢卖弄技艺,所以瓷器上也开始追求装饰繁缛,造型复杂,怎么繁复怎么来。”吕成龙说。
而宋瓷“芙蓉出水”美感特征的形成,也离不开帝王的推动,最具代表性的是汝窑。作为御用瓷器,汝窑必定要符合帝王的口味。刘涛说,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有一幅《文会图》,该图传为徽宗所作,而今天专家认为,它更可能出自徽宗时宫廷画师之手。该图描绘了一群文士在宫廷庭园中聚会的情景,画面中心一张偌大的黑色方桌上,摆满水果、点心和成套的碗、碟、注子、盏等,文士们围席而坐,不远处石桌上有瑶琴一张、香炉一尊、琴谱数页,席前几个童仆正烹茶备酒,台面上也摆有茶盏和酒具,图的右上角是徽宗手书题图诗:“儒林华国古今同,吟咏飞毫醒醉中。多士作新知入彀,画图犹喜见文雄。”有专家认为,此为写实之作,图中每一位“文雄”都有来历,每一个细节都经得起推敲。刘涛也注意到了细节刻画的真实性,比如图中那些琳琅满目的各式器具都是高度写实的。它们多为瓷器,而且均为北宋末年即徽宗时代流行式样,并可根据不同形制与用途,将它们大致分为三类,即属于膳食器的碗、碟,用于饮酒的台盏、注碗、梅瓶,用于喝茶的托盏、茶末罐等。此外,图中的碗、盏、碟多为“扣器”,即以金、银或铜镶装器口的瓷器。“扣器”流行于宋代,出土的宋瓷特别是高档瓷器中多有所见。再经对图像观察辨识,多数瓷器呈淡青色调,接近汝窑青瓷釉色,加上形制上的比对会发现,这些瓷器是汝窑专为宫廷烧造的天青釉制品。比如注碗、台盏、梅瓶和作为食器的碗、碟等,都能在传世或出土的汝瓷中见到相同和近似的器物。特别是注碗,注子为塔形器盖,与景德镇青白瓷等相比,形制上更接近于汝窑青瓷。刘涛认为,《文会图》是一幅有政治寓意的作品,通过文人雅集这一传统题材,表现和赞美徽宗在广纳天下英才方面“跨越先代”的胸襟与气度,因而图中包括汝瓷在内的所有服用器玩都是经过精心选择和设计的,也都具有很强的象征性,充分显示出徽宗卓尔不凡的眼光和追求。由此再联系到汝窑“以玛瑙入釉”、不计工本的情况,有理由相信,造就出汝瓷独特美感的,正是宋徽宗。在这一点上,汝窑与后来的乾隆官窑也有些异曲同工。
汝窑独特的天青色,吕成龙认为也是受了宋徽宗影响。“为什么敲击的声音是砰砰的?要说瓷,其实它不够瓷,温度不太够,这属于一种生烧状态或者半生烧状态。为什么呢?当时的技术都没问题,就是因为追求天青色才故意这么烧制的。如果正烧,温度达到瓷化的程度,它的颜色就是豆绿色、豆青色,就不是天青色。烧出天青色,与宋徽宗的审美有密切关系。因为徽宗本身喜好艺术,他又是个道君,道家的审美是以静为依,以朴素为美,讲究不温不火。他认为,‘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为什么宋徽宗单独选择了汝窑宝丰清凉寺这个地方的这种青瓷?就是因为这里烧出来瓷器的颜色,被宋徽宗看到了。天青色有绿色之冷,蓝色之暖,介于两者之间,不温不火,非常符合徽宗皇帝在颜色上的审美。”
在宋代其他瓷器的烧造和选用上,也可以看出皇帝的取向。刘涛说,宋代经济繁荣却国势虚弱,为应付边患,自立国之初起朝廷就不断推行抑制奢侈消费的政策法令,这样也就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宫廷消费品生产的专断以及由此容易滋生的奢靡之风,两宋历朝皇室大都还是比较节俭的。宋哲宗本人“饮食皆陶器而已”,“一应华巧奢丽之物不得至于上前”。文献中还记有仁宗怒砸定州红瓷器的故事,是说一次仁宗到他的宠妃张贵妃住处,见到一件在当时比较珍稀的“定州红瓷器”,而当得知这件瓷器为臣僚所送时,仁宗一怒之下将其砸碎,也反映了仁宗对“奢丽之物”的排斥。
除了皇帝,文人士大夫也是引领瓷器风尚的重要阶层。刘涛说,尤其是宋代,推行文治之国策,从而产生了中国历史上一个最有文化修养、最富生活情趣的文人士大夫群体。宋代又是一个世俗生活精致化的时代,崇古之风盛行,文人士大夫所关怀的寻常事物中也浸入古人的风雅与情致,而这一切都深刻地影响到工艺产品的精神取向。如官窑、贡器及其他制作考究的青瓷、白瓷等,主要靠釉色取胜,追摹青铜器、银器、漆器、玉器和玻璃器的形制、颜色和质感。即使是热衷于装饰的普通民用瓷,受时风左右,也表现出一种美而不艳、华而不靡的美感。官窑和民窑分流与交融,民族化、本土化倾向更为突出,显现出“雅俗兼资、新旧参列”的特点。
这种由文人引领文化消费时尚的风气,在明代还曾出现过。刘涛指出,晚明文人推崇“精工之极,又有士气”的美,也就是“精工而雅”的美,境界也很高。宋元的名窑瓷器真正成为古董雅器而进入中国人的审美意识和日常生活,实际上就是从明代才开始的。当然,这些登堂入室的宋元名瓷也要符合“精工而雅”的标准。从《长物志》等晚明文人著述看,当时文人书房中的古瓷多为官窑、哥窑、定窑和龙泉等。
如果将视野再放大,站在思想史、文化史的角度看,瓷器风格的背后还有更广阔的国内和国际背景。刘涛说,比如宋代出现了一个特别的文化现象,即“中国”意识的凸显。由于契丹、女真和蒙古等异族政权的先后崛起,天下缩小为“中国”,四夷成了敌手,宋人的民族意识和“家国”观念不断增强。表现在瓷器上,与汉唐相比,宋瓷的民族化、中土化风格更为突出鲜明。从装饰上看,各种图案趋向简洁或写实,中土固有的龙、凤、鱼、鹤、鹿、鸳鸯、牡丹以及莲、菊、梅等吉祥纹样,经过宋人的提炼和推广,更具民族“集体表象”的意义而对后世产生深远的影响。
而在“南青北白”的单色釉主流审美下,元青花异军突起,显然是在元代的开放环境下,受到了伊斯兰文化的直接影响。刘涛指出,当时蒙古统治者倾心于伊斯兰文化,加之当时与阿拉伯地区的经贸往来十分频繁,大量接受外商订货,使得适应西亚市场需求的青花瓷器得以问世,这一品种因此多带有浓郁的伊斯兰情调。明初的文化政策是“沿汉唐之旧”,“文必秦汉,诗必盛唐”,雍容华贵之美受到提倡。其时花鸟画盛行,皆是追摹“汉唐以来名笔”,作风“妍丽生动,工致绝伦”。这一风气与“朝贡通商”而东渐的西亚文化交织,反映在瓷器装饰和造型上,呈现出鲜明的时代风貌。明中叶以降,城市经济发展迅猛,特别是富甲天下、人文荟萃的长江中下游地区,“士商相混”,风俗奢靡,绘画、书法、古董等成为流行的消费时尚,彩瓷也得到新的发展。
可以说,明清彩瓷的盛行,有其内在的必然逻辑——它是在西方文明崛起、世界海上贸易空前活跃以及经济全球化浪潮高涨的大背景下,各种内部及外来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刘涛指出,在摄影及其复制、传播技术尚未完善和普及之前,一切图像形式几乎都经历过精细化的发展阶段,而且它们之间彼此参融,交互影响。明清彩瓷朝着“精细图像”的方向发展,可说在一定阶段顺应并引领了世界文化交流融合的潮流。
如今,有“芙蓉出水”之美的宋瓷又重新受到追捧。似乎在世风奢靡的年代,宋瓷作为中国文化的一个符号,更能彰显一种文化理想和美学追求。不过,白明认为,这也是被一种审美惯性所笼罩,这个时代需要寻找新的认知:“从唐宋元明清各个朝代瓷器的不断更新中也可以看到,今天我们能称之为传统的,其实都是那个时代石破天惊的创造。”
(实习记者李秀莉、胡艺玮对本文亦有贡献)
,免责声明:本文仅代表文章作者的个人观点,与本站无关。其原创性、真实性以及文中陈述文字和内容未经本站证实,对本文以及其中全部或者部分内容文字的真实性、完整性和原创性本站不作任何保证或承诺,请读者仅作参考,并自行核实相关内容。文章投诉邮箱:anhduc.ph@yahoo.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