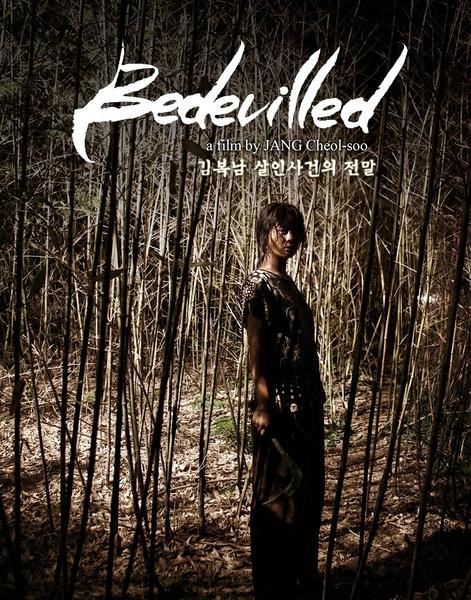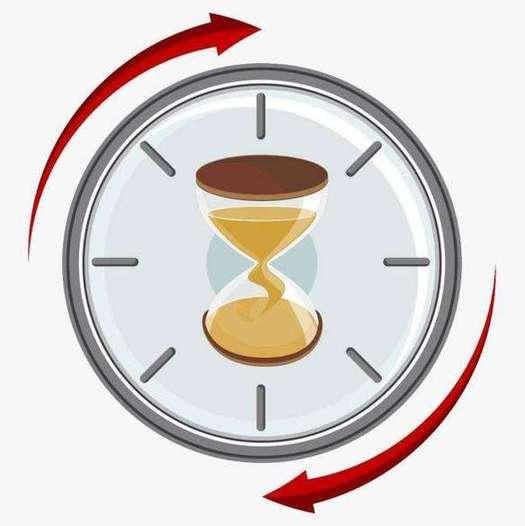他用生命给了她最后一次宠溺(那年他亲口许诺)
1从镇国候府回来的时候,下了雨,黑压压的天空,豌豆大的雨点,让人感到阵阵压抑和沉闷,我来为大家讲解一下关于他用生命给了她最后一次宠溺?跟着小编一起来看一看吧!

他用生命给了她最后一次宠溺
1
从镇国候府回来的时候,下了雨,黑压压的天空,豌豆大的雨点,让人感到阵阵压抑和沉闷。
沈遐龄刚刚坐上棕油马车,侍女离鸾就迫不可待地将汤婆子塞到她的怀里,“天气冷,您今天衣服穿得又这么单薄,赶紧暖暖身子吧。”
“你这是越发絮叨了,倒跟个嬷嬷一样,不知道的人还以为我沈遐龄是养了一个教养嬷嬷呢,只可惜着年纪对不上。”沈遐龄狭促地打趣道,接过汤婆子捂在怀里。离鸾又贴心地替她拢了拢白狐裘,戴好了昭君帽。
虽然车里早已经被四角摆放的金丝炭烧得暖洋洋的,沈遐龄也是浑身上下包裹得严严实实,可身体里还是又阵阵寒气涌动,让她不由自主地打了一个寒颤。
这是她十五岁上战场时中的寒毒。
由于当时没能得到及时的救治,毒入骨髓,最后只能无力回天,所以这些年,即便是烈日炎炎的盛夏,她也依然是手脚冰冷,浑身发冷。
“那大人您和镇国候谈得如何了?”
离鸾虽说现在是她的侍女,可从前,在战场上,却是她的副官,是名满北疆的巾帼英雄之一。即便后来和她一样退了下来,依然和她一样对北疆的安危念念不忘。
“致斋已经同意从江南那边调三百万两银过来,作为北疆的军费,北疆的兄弟们可以平平安安地渡过今年的冬天了。”沈遐龄的声音里是掩不住地兴奋。北疆苦寒,而朝廷已经好些年没有拨下丝毫银子了,若没有她四处奔波,筹措军费,每年都要死上不少人。
不是死于与胡人兵戈铁马的战争中,而是死于风雪交加的夜里,被冻死,被饿死,感染疾病而死。
她沈遐龄护不住天下人,可决不能让保家卫国的战士寒了心,更何况那些还是与她并肩作战的兄弟。
马车刚刚停到家门口,就有人淋着雨搬来了下车的木台阶,金丝楠木做的台阶,上面是由御物司的匠人雕刻的花纹,富丽堂皇,精致华美。内廷的饰物与它相比,只怕也要逊色三分。
沈遐龄扶着离鸾的手,缓缓下了马车,一抬头,就看到了挺直身子跪在门外的顾毓。
“他就这么一直跪着吗?”沈遐龄问身畔的侍卫。
“是的,今早您刚走不久,三皇子就来了,然后就直直跪在王府外,”侍卫风平浪静地回道,又微微压低了声音,轻声呢喃,“我们按照您的吩咐,没允许任何人踏出府半步。”
沈遐龄点点头,慢慢走到顾毓的身边,眼里带着些许悲悯的盛情,温柔地看着他,然后哆嗦着双手解下大氅,轻轻披到他的身上。
“起来吧,三殿下,我让离鸾送你回宫,阿父平生最讨厌被人胁迫,听我一句劝,无论您跪多久,阿父都不会允许二妹和您的婚事的,到头来,风湿发作,伤的还是您自己身子骨。”
顾毓的风湿,是在北疆,因违忤逆废太子吴王被罚在帐篷外跪了一天一夜落下的。那时正值冬天,冰天雪地,他又初到北疆,身子单薄,等沈遐龄从前线巡查归来,早已晕倒在雪地里。军医说,他这是寒气入骨,日后但凡阴雨天气,浑身都会疼痛不止,后来她虽为他寻遍各种名医,可依然无力回天。
往事如烟,物是人非,昔日意气风发的少年此刻却如同炸毛的狐狸,将沈遐龄的大氅一把打落在地,抬起头恶狠狠瞪着她,一双瑞凤眼尽是的怒火。
“究竟是你阿父不同意,还是你沈遐龄不同意?莫说这忠义王府,就是那王宫,那天下,只怕都是你沈遐龄说了算。”
“沈遐龄,你还是不是个君子,对不住你的是我,害你生不如死的也是我,你有什么事就冲我来啊,为难芳龄做什么?她只是一个无辜的女孩子。”
沈芳龄无辜,那自己就罪有应得吗?就因为她长了一张和沈芳龄七分相似的容颜,所以她就活该被当作替身,活该满腔痴情错付,活该把属于自己的一切对沈芳龄拱手相让吗?
沈遐龄心一紧,只觉得顾毓那张容颜格外刺眼,面带讥讽之色,居高临下地俯视着顾毓,“我若真要害你,你以为,你还能活到现在吗?”
2
沈遐龄是什么人,大权在握的奸臣,人人得而诛之的逆贼。
帝京有一首流传多年的童谣:“关山月涟涟,沈家子,玉郎君,一朝变红颜;鸿雁来,啄皇孙,皇孙死,鸿雁王。”说的正是小字鸿雁的沈遐龄。
在她充作男儿养的时候,曾是名满天下的少年郎。等她恢复女儿身之后,却是让人闻之色变的阎罗王。莫说王公贵族,就是天潢贵胄,落在她手里,被她弄得死无全尸的都数不胜数,据说沈遐龄三个字甚至有止孩童也哭的效果。
整个帝京,从文官到武将,没有人不恨她,从老牌世家到后起新贵,没有人不厌恶她。就算是后宫里的娘娘,也是日日夜夜扎她的小人,恨不得食其肉,寝其皮。
要不是她给今上推荐了一大批所谓的世外高人,蛊惑得今上天天窝在上阳宫炼丹,梦想着羽化登仙,她们哪里会日日夜夜独守空房呢?年轻的娘娘没机会得一儿半女傍身,年老的娘娘也没机会为她们的子女说好话。
除了蛊惑君王修道成仙,远离后宫,疏懒朝政外,她还利用手中的权利杀忠臣,害皇子,诛宗室,滥杀无辜,残害忠良。据说就连老一代的忠义王,她的亲生父亲也被她囚禁在府里,卧病在床,奄奄一息,日日只能以残羹冷炙充饥。
当离鸾把这一切的传言告诉沈遐龄的时候,她却只是无所谓地笑了笑,仿佛传言的主角,与她毫无干系。
“您这般肆无忌惮,只怕到时候大事得成,也少不了非议。”离鸾想起种种喧嚣日上的传言,不禁有些忧心忡忡。她知道她们家大人是非常人,谋的也是非常事,可这种种不得已的行径,落在那些不知情的凡夫俗子眼中,却是残暴之举。
“在意那么多做什么?听说锦岚殿的柔妃怀孕了,她身边的菬红是我们的人,你亲自去确认一下。”
沈遐龄一边回答着离鸾的话,一边翻看着泸州来的奏章,她的时间不多了,外人看她是爵位上的忠义王,朝野上的摄政王风风光光,大权在握,可是则各种艰辛却是如人饮水,冷暖自知。
世家当政,朝廷腐朽,那些看似仪表堂堂的王公贵族,实则却是藏污纳垢,狼狈为奸,不知搜刮了多少民脂民膏。就算有个别两袖清风的文官,也是冥顽不化的酸儒,整天喊着以和为贵,被他们间接由此害死的北疆士卒不可枚举。还有帝王,若不是她蛊惑皇帝沉溺于修仙练丹,天下不知有多少人要因为他的沉溺酒色,大兴土木弄得家破人亡。
而眼下,泸州,靖州,畹城等各个地方,不是干旱,就是洪涝,官员们日日快马加鞭送来的奏章,都是要银子的,国库空无一物,银子从哪里来?都得她沈遐龄去筹措。
“如果是真有,那就落了吧,连同柔妃一起上路。”斩草不除根,春风吹又生,更何况,皇帝现在天天窝在上阳宫炼丹,足不出户,那柔妃,那里会有什么身孕?世事反常即为妖,朝政繁忙,她也懒得去查奸夫是谁,索性母子一起处理了。
离鸾领命退了下去,沈遐龄继续伏案批阅着各地的奏章,不知不觉就到了日暮,匆匆用过厨房送来的燕窝粥后,沈遐龄才起身去了祠堂。
祠堂里跪的正是沈芳龄,她同父异母的妹妹,三皇子顾毓心中的可人。
“三岁能诗,五岁能文,十二岁夺得文武状元,十五岁奔赴北疆上马击狂胡,到如今不过二十多岁就大权在握,我原以为姐姐是多了不起的人物,却没想到也会为了风花雪月为难我这个闺阁女儿,可见姐姐再怎么成绩斐然,骨子里也是个争风吃醋的小女子。”
沈芳龄一双杏眼,面带嘲讽地望着她。经过几月的折腾,原本娇生惯养的金枝玉叶早已被弄得形骨锁立,一身白衣,乌发如墨,不仅不觉得狼狈倒更添了几分弱柳拂风的姿态。
“怎么,姐姐无言以对了?就算阿母被你弄去了浣衣,就算我被你罚了日日跪祠堂,可顾毓心里依然只有我。姐姐,你风光一世,骄傲一世,可在儿女情长的战场山终究还是输给我的,谁让你一开始就是一个替身呢?”
说完,竟掩面得意地笑了起来,沈芳龄的话,再次刺痛了沈遐龄的心,扬手,一个耳光扇到沈芳龄的脸上,“我说过,你的东西,我不稀罕。”
她若一开始就知道顾毓对她的爱是出于那样的目的,别说动情,就是当即杀了他也是毫不犹豫的。
“我回府的时候,三殿下正跪在门口,哀求阿父同意你们的婚事。阿父虽是我朝的唯一异姓王,却一直远离朝中是非,想来也是不会同意你们的婚事的,我也就如此告知了他,所以你也息了心思吧。”
沈遐龄波澜不惊地说着,拿起一炷香点燃,插入了供奉祖宗牌位的香炉里,“我们沈家世代为国尽忠,如今也轮到你了,全国上下各处受灾,国库入不敷出,前些日子犬戎来朝,说愿以万金为聘娶我朝公主作为王妃。我已经允了他们的请求,封你为颂德公主,不日出嫁。”
沈芳龄如遭雷击,不可置信地看着沈遐龄,尖叫响彻整个幽暗的祠堂。
“你怎么敢,你怎么能?沈遐龄,我们是血脉相关的姐妹啊!你竟然要送我去和亲!”
3
沈芳龄自从那日被她告知要和亲外,就日日躲在房间里寻死觅活。可沈遐龄却早早就撤去她房间里的各种瓷器摆设,簪子剪刀等一切可利用的饰物,就连她的衣服也换成了韧性很好葛布,怎么撕都撕不破的那种。
还有二十四个丫鬟,六班倒一天十二个时辰寸步不离地看着她。接着沈芳龄又开始闹绝食,却被她直接吩咐嬷嬷,掰开嘴巴塞进去。
而顾毓,据说听到沈芳龄要被送去犬戎和亲之后,就日日跑去上阳宫跪着求皇帝。可惜这段时间皇帝正忙着闭关修炼呢,如何有时间见他?如果他的母亲,旧年那个呼风唤雨不可一世的贵妃,没有因为难产而一尸两命,皇帝大概还能想起顾毓,只可以没有如果。
沈遐龄并没有太多的心思关注顾毓和沈芳龄二人,她忙得马不停蹄,从江南的三百万两银子送来后,她立即拿了一百万,亲自督办着买了粮草和过冬的衣物,派了亲信押往塞北疆。又拿了一百五十万交与孟致斋购买器械,筹备京郊大营和南境千戎卫的粮草,剩下的五十万,则用于皇帝不久后的千秋岁。
这大概是皇帝的最后一个清秋岁了,虽然曾由于他的任人唯亲,还得北疆无数战士战死沙场。虽然曾由于他的爱子情深,还得自己声名狼藉,可是身为人臣,这最后一个千秋岁,她一定会为皇帝办得风风光光。
千秋岁上除了要宴请文武百官外,还要为犬戎族亲自赐婚,这也是一桩大事,不容有丝毫有失。沈遐龄想着,嘴角不由自主露出一丝心满意足的微笑。刚刚进入书房的孟致斋,看见的就是这样一副景象。面色苍白,一身白狐裘的女子,坐在太师椅上,脸上挂着狡黠的微笑,恍然一只修炼成人的雪猫。
“想什么呢,这么高兴,说出来让我也乐一乐。”
“离鸾,冲一盏老君眉来。”老君眉,是镇国候孟致斋最喜欢的茶,沈遐龄从小就知道。
“没什么,只是想起一些不相干的人罢了。致斋,银子我可是交给你了,你务必要多花些心思,兵器和战马可是军队的第二条命,没了他们,就没有充足的战力。”他们经营多年,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如今东风降至,决不能在最后关头有丝毫闪失。
对外说,那三百万两银子是孟致斋借给沈遐龄的,实则却是沈遐龄托人从江南搜刮来的。无论是扬州的盐商,还是杭州的布商,那都是富得流油的家伙,更别提那些中饱私囊官员了,随便抄抄,就是数不清的雪花银。
只是这些银子,都还有要事要办,决不能入国库,所以只能挂入孟致斋的名下,镇国候府兵强马壮,又世代经商,再合适不过了。
“放心,我都已经安排好了,不会有什么问题的。”孟致斋信誓旦旦,痴痴望着湘妃帘外的芭蕉出神,静默良久才缓缓开口,“遐龄,你后悔吗?你现在后悔,还来得及。”
现在后悔,他还可以力挽狂澜,等迈出了第一步,就真的开弓没有回头箭了。虽然他知道这样的希望很渺茫,可是他终究还是兴怀奢望地开口了。
沈遐龄果然如意料之中的摇摇头,她们谋划着这么多年,走了这么多年,不能因为一时的迟疑就功亏一篑。黎民百姓太苦,戍边战士太苦,他们没有太多时间了。
“那顾毓呢,你就真的舍得吗?”除了沈遐龄,三皇子顾毓,也是他们筹谋里最重要的一环。
尽管沈遐龄一直口口声声说自己已经放下,可孟致斋却不信。沈遐龄不会知道,那一日,在她从镇国候府离开的时候,他担心她的安危,于是悄悄尾随了一路,雨中发生的一切,他看得清清楚楚。
“致斋,我为他流过血,中过毒,赔上过性命,所以我已经不欠他顾毓什么了。”
没有亏欠,也就没有顾忌,至于舍得与否,在大是大非面前已经不重要了。
4
时至今日,纵使故事的主角早已分道扬镳,可“京都三杰”依然人们茶余饭后,津津乐道的话题。
顾毓,字如皎,今上第三子,母亲曾是圣宠一时的惠贵妃,风头直逼中宫,风神如玉,潇洒俊逸。昔年每每驾车出游的时候,必有掷果盈车的盛景。
沈遐龄,字鸿雁,十三岁之前都是充作男儿教养的,忠义王府长子,自小聪敏过人,文武双全,不过十二岁就高中文武状元。
孟致斋,字波若,镇国候府世子,镇国候府名为皇商,实则掌天下盐铁经营,富可敌国。孟致斋传承了祖上的经商天赋,周岁抓算盘,十岁就将店铺开遍了大半个江南。
孟沈两家是世交,沈遐龄的生母就是孟致斋同族的姑姑。若不是沈父偏宠侧室钟姨娘,在沈遐龄的生母去世的半个月,就扶正了钟姨娘做王妃,孟沈两家的情谊或许现在还持续着。
钟姨娘是沈遐龄祖母的远方侄女,从小就被沈遐龄的祖母养在膝下,和沈父是青梅竹马的情意。可由于未婚苟合,最终只能沦为妾室。在母亲孟氏难产去世,钟姨娘翻身作主后,七岁的沈遐龄在忠义王府的日子并不好过。
厨房看碟下菜,时不时克扣沈遐龄的饭菜,下人奴大欺主,伺候时总是敷衍了事,沈遐龄常常吃的是残羹,喝的是冷水。可既便如此,钟姨娘时不时找各种借口,罚沈遐龄去跪祠堂,钟姨娘所处的继妹沈芳龄更是对沈遐龄各种刁难,恨不得她早死,好给同胞的弟弟腾位置。
那时孟沈两家早已闹翻,互不往来,表兄兼好兄弟的孟致斋虽然知道沈遐龄的遭遇,可除了能偷偷托人将月例银子捎给她之外,也无能为力。真正救她于水火之中的,是三皇子顾毓。
“我记得,那是元丰二十五年的千秋岁,上阳宫的梧桐叶刚刚落下,那是我第一次进宫廷,”沈遐龄望着窗外的芭蕉,陷入了深深的回忆,“祖母和钟氏本来时打算对外宣称我生病的,不愿意带我进宫的。她们想让沈芳龄姐弟去露脸,可我却抢先一步用母亲遗留的玉簪,找看门的婆子换了二两巴豆粉,掺到沈芳龄姐弟的燕窝粥里。”
“是啊,你从小就是个足智多谋的,行事也果断狠辣。”孟致斋轻轻饮了一口老君眉感慨道。朝廷规定,每一年的千秋岁五品以上的官员都需要携嫡出子女入宫贺寿。沈芳龄姐弟被沈遐龄害得腹泻不止,修养在床,于是忠义王不得不带沈遐龄入宫。
然后沈遐龄在入宫的前两天就开始水米不进,把自己弄得越发憔悴苍白,等到在千秋岁上她假装昏倒的时候,所有人都被她给骗了过去。御医说她是饿晕的,足足给她喂了三碗小米粥。
等到醒来后,她更是故意装出一副饿虎扑食的样子,迫不及待地抓起桌上的菜肴就往嘴里塞,足足一副饿极了的模样。虽然席间的文武百官早就听说过,忠义王府继室苛待元配子嗣的传闻,可见到沈遐龄那般狼吞虎咽的模样,却都大惊失色,于是各种脑补,更有甚者,直接跪下来要求帝王无比严惩忠义王夫妇。
帝王果然无比震怒,当场询问了沈遐龄,沈遐龄虽然表现得哆哆嗦嗦,却添油加醋地把自己在府中遭到的种种苛待说了出来。帝王大怒,当即削去了钟氏的诰命,贬了忠义王为忠义候。
可沈遐龄要的远远不是如此,她要是是彻底离开忠义王府。
“我当时就给皇帝跪了下来,一遍遍磕头,求皇帝收留我。可无论是皇帝还是大臣,都没有一个愿意表态。皇帝可以为了后宅惩罚忠义王,却不能和他撕破脸,大臣们更是不愿意惹他。是顾毓,是他挺身而出,收留了我。”
他说:“君父,儿臣身边正缺一个伴读,忠义王长子很合儿臣的眼缘。”
平静如水的眼神里除了深深的关切,没有任何居高临下的同情或悲悯,他就那样静静地站在她的面前,一诺千金,掷地有声。
5
就在沈遐龄成为顾毓伴读的第三天,孟致斋也被镇国候黑着一张脸将送进宫做了顾毓的伴读。那一日的孟致斋格外奇怪,不知为何竟跛了脚,还站在镇国候身畔一个劲冲沈遐龄傻笑。
沈遐龄和孟致斋先是在顾毓身边做了四年的伴读,待顾毓开府分王之后,又入府做了他的幕僚。三人名为君臣,实则却是形影不离的好兄弟。顾毓长她们五岁,却与他们同寝同食,无话不谈,一起激扬文字,指点江山,一起对酒当歌,策马沙场。
那是他们生命力最欢愉的时光。
然欢乐苦短,良辰难得,三年后,惠贵妃难产而死,顾毓失去了庇护,之后又因为不肯接受皇帝的赐婚被一张圣旨放逐北疆。
孟致斋被镇国候强留帝京,而沈遐龄则义无反顾地和顾毓去了北疆。
北疆是废太子吴王顾融的地盘,顾毓刚到北疆就遭到了各种刁难,若不是有沈遐龄护着,早已不知死了多少次。也就是这时候,顾毓真正产生了夺嫡的心思。
沈遐龄记得,那一晚的月色极好,他们并肩坐在黑河畔,有阵阵凛冽的风从关山吹来,顾毓紧紧握住她的手,说:“鸿雁,你知道我为什么要推却君父的赐婚吗?因为我不想娶一个自己不爱的人,我宁愿随着心仪的人一起到北疆风餐露宿,粗茶淡饭,我也不愿意在违心地娶一个世家贵女。”
沈遐龄一愣,随后就被顾毓拥入怀中,“什么伦理纲常,什么大逆不道,只要有你,我什么都不在乎,”顾毓眼里流露出一丝丝疯狂的神色,“鸿雁,我会把整个天下都捧到你的面前。”
沈遐龄始终不曾对顾毓说明过自己的性别,不过也曾问起他为什么会对自己情有独钟。顾毓却只是温柔地凝望着她的脸庞,如痴如醉地呢喃。
他说:“鸿雁,你我之间早有因果,注定要相爱,注定要在一起。”
然后,拉起她的手,轻轻拂过他额上的一块伤疤。那块伤疤,早在沈遐龄入宫之前就已存在,只是究竟因何落下,顾毓却从不曾说起。
夺嫡之路看似容易,可军权、财权还有人脉,帝宠以及势力却缺一不可。于是沈遐龄先是利用了顾融好色的特点,设计了他和北疆主帅威武将军最宠爱的小妾暗通取款,离间了二人,然后又让顾毓投其所好,娶了威武将军壮硕痴呆的独生女为侧室,将二人绑在了同一战线上。
接着沈遐龄又收买了马夫,在顾融的战马上做了手脚,使顾融在战争中摔断了腿,储君不可有残疾,于是顾融从太子降为了吴王。然后又将此事嫁祸为威武将军,而威武将军巡查归来的路线,又被沈遐龄透露给敌军,最终与埋伏的敌军同归于尽。
在顾融养伤期间,又让顾毓则一心一意扮演着好弟弟的角色,各种安慰照顾好他,甚至割肉疗亲,吴王果然大为感动,将势力都给了顾毓。
北疆军权尽在手中,然后沈遐龄又说服了孟致斋支持顾毓,于是富甲天下的镇国候府也归于顾毓麾下。接着沈遐龄又用孟致斋提供的银子为顾毓联络官员,巩固人脉,训练私兵,构筑势力,还从天南海北选来四名倾国倾城的美人,各种训练后安插进宫,一来替顾毓说好话,二来也替顾毓监视皇帝。
北疆的军权虽然在顾毓的手里,可是士兵却并不臣服于顾毓,于是沈遐龄亲自出马,将他们一一收复。在夺嫡的路上,作为顾毓最大的依仗,沈遐龄记不起自己遭遇到多少次暗杀,多少次下毒。她为了护住顾毓,一向是身先士卒,直到在一场战争中,她为了给顾毓挡敌军的流箭,种了寒毒。
流箭射中的是左胸,也就是在这一次,沈遐龄女儿身的事实彻底暴露了。她原本以为顾毓会恼怒她隐瞒了事实,却没想到顾毓却如同魔怔一般,抱着她哭哭笑笑了一整夜。
沈遐龄中的寒毒,需要千年雪参作为药引,那时候他们手里刚刚有一株,可却是为帝王准备的寿礼。千年雪参难得,只要能献上这件寿礼,顾毓回京必定是板上钉钉的事情,所以沈遐龄最终选择了忍下寒毒。
回京的前一夜,她寒毒发作,浑身冰凉,顾毓将她拥在怀里了一整夜,泪如雨下,一遍遍念叨着:“鸿雁,等回到京城,我就去求父皇赐婚,娶你为妻,一生一世唯一的妻。”
6
他从皇帝那里求到了赐婚的旨意,金银珠宝,十里红妆到忠义王府下聘。
只可惜这聘礼却不是给她沈遐龄的,而是给她那楚楚可怜的继妹,沈芳龄。据说他与沈芳龄是一见钟情,再见倾心,生死相许。
她不敢相信,找了孟致斋去调查此事,果然牵扯出了一段尘封的往事。原来顾毓在十一岁的时候,曾于上元节偷偷溜出宫,不幸遭到了人贩子的拐卖,他虽然侥幸逃路,却在逃跑的过程中撞伤了脑袋,他额上的那块伤疤,也就是在那时候留下的。
顾毓流血过多,昏迷在巷子里,是一个路过的小女孩将他送到了医馆里包扎伤口,那个小女孩直到顾毓苏醒过来,才放心的离开,还将身上所有的银子都留给顾毓,让他安心养病,顾毓没来的及问小女孩的名字,却从此记住了她。
顾毓多方打听,可却再也没有见过那个小女孩,只是从此挑人伺候的时候,总喜欢挑选和女孩有些许相似的人,谓之合眼缘。而顾毓,之所以肯留下她作伴读,乃至后来不顾一切要和她在一起,也不过是因为她那张和沈芳龄七分相似大的容颜。
是的,救下顾毓的那个小女孩,正是年幼的沈芳龄。
她被气得寒毒发作,但整个忠义王府却喜气洋洋,春风得意的钟姨娘更是日日花枝招展到她面前各种炫耀,炫耀沈芳龄和顾毓的恋情,炫耀沈芳龄是如何有福气,顺带感慨一句沈遐龄母亲和她是如何福薄。
祖母更是是非不分,夺走了母亲留下的各种嫁妆,要给沈芳龄作为陪嫁,撑场面。甚至就连顾毓也派人来,苦口婆心劝她识大体,先将嫁妆让给沈芳龄做陪嫁,事后自然会照价给补偿给她银子。
可笑,当真可笑,拿着她赚的银子,要买她的嫁妆,还要她感恩戴德,否则就是不识大体。她如何能甘心?于是用贴身佩带的玉佩收买了送饭的下丫鬟,先用药草稳住了病情,然后忍辱负重,掩而不发,在他们慢慢放松警惕的时候,利用砒霜毒死了那个曾害的她母亲难产而死,害得她走投无路的祖母。
祖母死,是大丧啊,沈芳龄可得守卅年的大孝呢。三年,足够做很多事情了,她懂得政治,又有资源,搅动风云轻而易举,更何况朝廷早已腐朽,帝王早已日日沉溺酒色。
她成功了,成为了呼风唤雨的摄政王,成为了人人畏惧且憎恶的奸臣,大权在握,天下在手,再没人能伤她半分。
“遐龄,你真的确定,顾毓会在千秋岁上动手吗?”孟致斋仍有些忧心忡忡。千秋岁的日子越临近,他的心就越焦虑,而沈遐龄却是越发沉默,似乎一切胸有成竹,胜券在握。
“我确定。”
世间大概在没有人比她更了解顾毓了,沈芳龄被她许配给犬戎国,千秋岁上就要正式赐婚,若是顾毓不在千秋岁动手,那么就会彻底失去她的心中所爱了。他那样的痴情人,怎么舍得?
“致斋,别担忧了,如今早已万事俱备了,你还没听过我唱歌吧,我给你唱一首歌吧。”沈遐龄依旧是一贯的风轻云淡,不待孟致斋开口,就朱唇轻启,缓缓地唱了起来,“数声鶗鴂,又报芳菲歇。惜春更把残红折。雨轻风色暴,梅子青时节。永丰柳,无人尽日花飞雪。莫把幺弦拨,怨极弦能说。天不老,情难绝。心似双丝网,中有千千结。夜过也,东窗未白凝残月。”
她唱的是张先的《千秋岁》,声音是前所未有的苍凉和悲怆,仿佛北疆粗狂的风。歌罢,窗外竟真的落起了雪,飘飘洒洒,恰似漫天白纸钱。
望着前方那个瘦弱而决绝的背影,孟致斋忽然感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悲痛,仿佛心中最重要的一部分,正被人缓缓地挖去。
7
银月皎皎,丝竹袅袅,美酒佳肴,文武百官列宴席间,觥筹交错,谈笑风生,帝王高坐与九龙玉案上,心满意足地听着臣下的恭维,一派君臣同乐的情景。
沈遐龄捂着暖炉,坐在离帝王最近的一张白玉案上,面带些许嘲讽的神色,冷眼旁观打量着场上其乐融融的局面,仿佛在看一场乏味的戏。犬戎使者在刚刚给文臣武将敬酒的过程中触了不少冷眼,于是跑到了沈遐龄面前求助。
“摄政王,万金的聘礼我们早已送到您府上,只是不知赐婚的圣旨合适才可以拿到?我们犬戎素来对天朝文化仰慕已久,我族太子更是心心念念想娶天朝的公主为妻,一片赤诚,还望您能多多相助。”
“我既然允诺要嫁公主于犬戎,就绝不会食言,今晚乃是圣上千秋,千载难逢的机会,你还不赶紧出面,求圣上赐婚?”
犬戎使者面色大喜,果然出宴向帝王行了一礼后,絮絮叨叨提出了下降公主的请求。帝王被犬戎使者的一番话奉承得飘飘然,正要一口应下,可想到膝下并没有适龄的公主,于是只能为难地将目光投向沈遐龄。
“沈爱卿可有何良策?”
“忠义王府二小姐沈芳龄容颜淑丽,久有才名,乃是帝京难得的贵女,今上与忠义王曾以兄弟相称,如此二小姐沈芳龄也算是今上的侄女。依臣之见圣上可封其为颂德公主,下降犬戎,彰我天朝睦邻友好之意。”
席间顾毓顷刻之间面色惨白,死死握住手中的青铜酒樽,堪堪走向帝王。顾毓的脚步越来越近,眼中的愤怒也越来越浓,而沈遐龄也越发笑得风轻云淡。
“君父文成武德,威加四海,儿臣恭祝君父圣寿安乐。”说完,举起酒樽,一饮而尽。皇帝赞许地点点头,接过近侍斟的酒,送入口中,不想刚刚喝下,就一阵剧痛,七窍流血,匍匐在案上。
“你,你真逆子,竟敢弑君弑父……”皇帝不可置信地望着下方胜券在握的顾毓。他想叫人救驾,可是场上的文武百官早已被顾毓的军队重重包围,明晃晃的宝剑架在脖子上。
“父皇放心去吧,儿臣会替您守好着江山社稷的,您修仙炼道多年,也早该驾鹤西去,位列仙班了。”
“三殿下,您这是谋朝篡位,大逆不道,列位大臣,你们食君之禄,难道就眼睁睁看着真等逆贼兴风作浪吗?”沈遐龄望着案上毫无生机的帝王,愤怒地拍案而起,目光如炬,死死地望着顾毓。
顾毓被沈遐龄看得惊慌失措,踉踉跄跄往后退,幸被侍卫扶住,“我……我没有弑君,这一切都是你逼我的,是你逼得我走投无路,是你逼得我出此下策,这一切都是你的错,你才是始作俑者……”
“殿下,您现在可是今上了。”身后的侍卫低声耳语,沈遐龄一眼扫过去,原来那侍卫竟然是沈芳龄假扮的。
顾毓一愣,恍然大悟,顷刻之间变得神采飞扬,当即下令:“摄政王沈遐龄狼子野心,谋害先帝,从即日起废除王爵,押入诏狱……”
“只等罪证确凿,秋后问斩。”沈芳龄打断顾毓的话,恶狠狠望着风轻云淡的沈遐龄,笑靥如花。
8
飞鸟各投林,墙倒众人推,沈遐龄一夜之间从高高在上的摄政王成为了阶下囚,朝中的文武百官也立刻罗织了关于她的各种罪名,大到架空朝政,蛊惑圣上,小到她们家的车夫曾不小心曾碾死了一只鸡,桩桩件件,有的没的,都不约而同往她的头上扣。
“看看,姐姐,这些折子可都是参你的,三皇子,不,如今该唤圣上了,可是怒不可恕呢!本宫可真没想到,姐姐竟然做下如此多天怒人怨的事情。”沈芳龄把厚厚的一垛罗织着罪名的奏章扔到沈遐龄的面前。
“本宫?”
沈芳龄高高扬起头,仿佛一只骄傲的孔雀,“是啊,姐姐身陷囹圄,自然是有所不知的,就在昨日,今上已经下旨封我为后了,只等择日到太庙祭祀先祖了。”
沈芳龄捏着秋香色绣牡丹的云锦丝帕,笑得猖狂,敌人倒台,爱人上位,她不仅可以免除远嫁和亲的命运,还要马上成为母仪天下的王后,此等幸事,如何能不让她喜笑颜开呢?
牢狱中的沈遐龄虽然面容狼狈,却还是一贯风轻云淡的模样,面带讥讽之色望着沈芳龄,仿佛在打量一个跳梁小丑,“是吗?凤冠那般沉重,妹妹可别被压了头脑袋才好。”
说完,懒洋洋地闭上了眼,靠在墙角打盹。顾毓谋反登基,她一点都不在乎,顾毓要是不谋反,她才怕呢。
只有顾毓谋朝篡位了,孟致斋才能名正言顺地率领着北疆,京郊大营等各路的军队进京,才能占据天下大义和历史制高点,夺了这江山社稷,还黎民百姓一片海清河晏的太平盛世。
无论朝政如何腐朽,君王如何昏庸,臣子起兵终究是名不正言不顺,即使为王后如何兢兢业业,励精图治也摆脱不了一个乱臣贼子的骂名。她沈遐龄聪明一世,要做就做得尽善尽美,如何能留下这样的瑕疵呢?
自十五岁从北疆归来后,她就对这朝廷心如死灰,这个王朝早已由内而外病入膏肓,救不了,医不了,所以只能推翻从头再来。她为北疆,为天下士卒奔波劳碌,不仅仅是因为感同身受,更是要他们对自己感恩戴德。
如此,在他们得知自己被下狱后,才会不约而同地加入到起义的大军中。还有犬戎,他们千金聘得的王妃被人夺走,这可是举国上下的耻辱,想来未尝也不会助起义军一臂之力。
至于和孟芳龄和顾毓的恩恩怨怨,她也的确在意,毕竟她再如何叱咤风云,可归根结底也依然是一个将计就计的小女子。
“有姐姐天下难得贤良人在前面顶着,妹妹自然会一帆风顺。”沈芳龄冷冷哼了一声,拂袖而去。
狭小的窗户轻轻落下几缕金色的余晖,斜斜地洒在阴暗的牢房里,带来一丝丝久违的温暖,仿佛要让人羽化飞仙。沈遐龄舒适地闭上眼,朦朦胧胧之间听到了阵阵子远方传来的马蹄……
快了,很快了。
9
沈遐龄从来没有想过,顾毓在最后关头竟然会跑到诏狱来求她。
那样的顾毓是她从未见过的狼狈,衣冠不整,胡子邋遢,满脸泛着血丝,一进门就哆哆嗦嗦地跪下,“遐龄,从前是我被对不住你,现在我们握手言和好不好?你愿意做皇后,我就给你做皇后,我们一生一世一双人,做一对神仙眷侣好不好?只要你愿意出去劝降孟致斋,我什么都答应你。”
“沈芳龄呢,你的红颜知己,你的可心人呢?她怎么不陪你来了,难不成是大难来临各自飞了?”
沈遐龄懒洋洋瞟了顾毓一眼,满脸讥讽的神色。顾毓被她火辣辣的目光看得有些尴尬,随后左右开弓,抽起自己耳光来。
“从前是我瞎了眼,是我被沈芳龄那个贱人迷了心智,现在我真的后悔了,孟致斋如果真的不肯归降,我也可以与他划地而治。不,就是要我归降让位给他也可以。遐龄,你们自小交好,他一定听你话的,君子大人不记小人过,我求求你,你出去和他求求情,让他饶我一命好不好?”
沈遐龄不置可否,如同看好戏一般地打量着顾毓,“沈芳龄呢?”
“她,她,”顾毓哆哆嗦嗦,面如筛糠,“她被叛军给杀死了。”
“你们不是要同生共死吗?既然她已经死了,你还活着做什么?而且如你这般背信弃义的小人,还有何颜面苟活于世?”
沈遐龄说完,冷冷地转过身,接着就听到一声惨叫,回头顾毓早已浑身鲜血躺倒在地,而一身银甲的孟致斋正站在身后,寒光凛凛的宝剑上有滴滴鲜血滑落。
“遐龄,我来接你回家。”孟致斋缓缓向她伸出手,声音温柔得仿佛阳春三月拂面而过的清风。
沈遐龄却只是缓缓蹲下身,轻轻地合上了顾毓怒目圆睁的双眼。死不瞑目,他有什么好死不瞑目的呢?今天的这条路,是他自己选的。
那年北疆,白雪纷纷如葬礼,是他亲口许诺,要把整个天下捧到她的面前。她信之念之,于是为他出谋划策,为他出生入死,把自己的毕生都交付在他的手中。她以为她会和他共结连理,会和他白头偕老。
可他竟然从始至终只是把她当作沈芳龄的替身,甚至最后为了沈芳龄将她抛掷脑后,不顾丝毫曾共患难的情谊。
如此,她就把她昔日交付一切都拿回来吧,连本带利地拿回来。
今日的结局,不过是因果轮回罢了。
“致斋,带我回北疆吧,我想再去看一场黑河的雪,看一眼关山的月……”
还未说完,沈遐龄就一口鲜血喷涌在地,猝不及防地向后倒去。
10
沈遐龄是在一个春意融融的日子回到北疆的,那时候关山的雪刚刚融化,黑畔的红柳刚刚绽出嫩黄色的新芽。
她的墓就建在关山脚下,直直地对着北疆的大营,那是她曾念念不忘的地方,曾让她刻骨铭心,满心欢喜。永龄朝年轻的新帝将她的骨灰罐亲手放入了棺椁,久久伫立在汉白玉墓碑前,无语凝噎。
墓碑上写的是“追封武穆将军暨永龄帝元后孟氏遐龄之墓。”
她是天下人的将军,也是他孟致斋今生今世唯一的妻,没有人知道,他有多爱她,他也从不曾对她说起过。
或许是从第一次得知与他吵吵闹闹十多年的哥们是个女儿的时候,或许是第一次见她穿女装一身英姿飒爽的时候,亦或者是他违背个人意愿答应她的祈求辅佐顾毓的时候,亦或者是他劝他远离顾毓莫沉溺于风花雪月的时候,也许更早,他就对她动了心。
只是那时候,她心有所属,他爱不到,而后来,她中了寒毒,依然托着残躯为天下战战兢兢的时候,他更是爱不到。
早春的风夹杂着些许寒意,自关山吹来,这个春天,静谧得寻常。
,免责声明:本文仅代表文章作者的个人观点,与本站无关。其原创性、真实性以及文中陈述文字和内容未经本站证实,对本文以及其中全部或者部分内容文字的真实性、完整性和原创性本站不作任何保证或承诺,请读者仅作参考,并自行核实相关内容。文章投诉邮箱:anhduc.ph@yahoo.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