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你到了结婚的年纪(时间之舞61岁开始独舞)
每一个小女孩都曾幻想过自己长大后的生活,要嫁什么样的人、生几个孩子、要不要养一条狗,在薇拉11岁的时候,她的梦想是:
她要嫁一个在大家庭里长大的男人,他的大家庭和和美美的。他跟全家人都能友好相处——像薇拉爸爸那样友善随和,他们全家人都喜欢薇拉,视她如家人。她想要六个孩子,八个也行,一半男孩,一半女孩,跟许多堂亲、表亲一起长大。
等到61岁的时候,再回忆11岁时的自己,又会是怎样的心情?
美国普利策奖得主安·泰勒(Ann Tyler)在《时间之舞》(Clock Dance)这本小说里描写了一位女人从11岁到61岁的人生历程。小说截取了1967年、1977年、1997年和2017年四个年份,对应薇拉11岁、21岁、41岁和61岁的四段经历。作者安·泰勒非常巧妙地将薇拉的一生浓缩到一个故事里,她用了三分之一篇幅带读者概览了薇拉的11岁、21岁和41岁,然后用剩下的三分之二篇幅描写61岁的薇拉的“冒险之旅”。

作者Ann Tyler
11岁的薇拉正在面对母亲的“突然失踪”,这显然不是第一次,也不会是最后一次,在母亲失踪的两天里,薇拉经历了诸多的情绪变化,面对妹妹、面对父亲、面对同学,她的性格在这一个过程中初现端倪。
21岁的薇拉正在上大学,结交了一位帅气的学长,正趁着男友毕业之际带他回家见父母,在回家的机场被求婚,她在学业与婚姻之间犹豫,父母强烈反对婚姻,反而让她下定了决心。
41岁的薇拉正被迫陪丈夫参加丈夫商业合作伙伴的泳池派对,在高速路上两人因小儿子的问题发生争执,丈夫在情绪愤怒的状态下超车而发生车祸,当场死亡,薇拉经历丧夫之痛。
前三段人生,我们只能窥见一小段生活片段,在这些片段足够具有代表性,让我们得以想象一个性格隐忍、牺牲自我的女性形象。
这个形象到了61岁时更甚。
61岁的薇拉再婚了,两个儿子都已成人,并离开家乡过自己的生活。突然一个陌生的电话打破了她的平静也许带些沉闷的生活,她的大儿子的前女友的邻居打电话请她帮忙去照顾孩子。事件的发生很具有戏剧性,她的大儿子肖恩曾经与单亲妈妈丹尼丝交往过,后来分手;丹尼丝在街上偶然中枪,腿部中弹进了医院,导致她9岁的女儿谢莉儿无人照看,好心的邻居在帮忙照看了一天之后”无法忍受“,于是误打误撞在电话本上找到了“肖恩妈妈”薇拉的电话,请她飞来照顾孩子。
这个正常人不会搭理的电话,却让薇拉几乎瞬间下定了决心,她要赴这场陌生人的约。
她的第二任丈夫彼得不放心薇拉一个人出行,执意同行;但抵达之后便开始催促薇拉返程。
薇拉与谢莉儿一见如故,薇拉似乎在谢莉儿身上见到了年少时的自己,“总是很谨慎,好像老练的成年人寄寓在了小姑娘的身体中 ”。薇拉陪着谢莉儿做饭、遛狗、看电视剧,在遛狗途中认识了这条街上的很多人,他们中有中年单身职场女性、有丧妻的医生、有同性恋、有相依为命的兄弟,似乎每个人都有着自己的故事,他们在丹尼丝家里进进出出,就像一个大家庭一样。
薇拉在照顾谢莉儿和丹尼丝的过程中逐渐唤醒了内心的某种东西,她开始不断推迟回家的时间,从丹尼丝出院、到拆石膏、再到她能独立驾车,不耐烦的彼得早已一个人飞回家,而薇拉依然在丹尼丝家里扮演一个照顾者的角色,她甚至还帮忙调节邻居家的关系,大家都把她当成了这条街上的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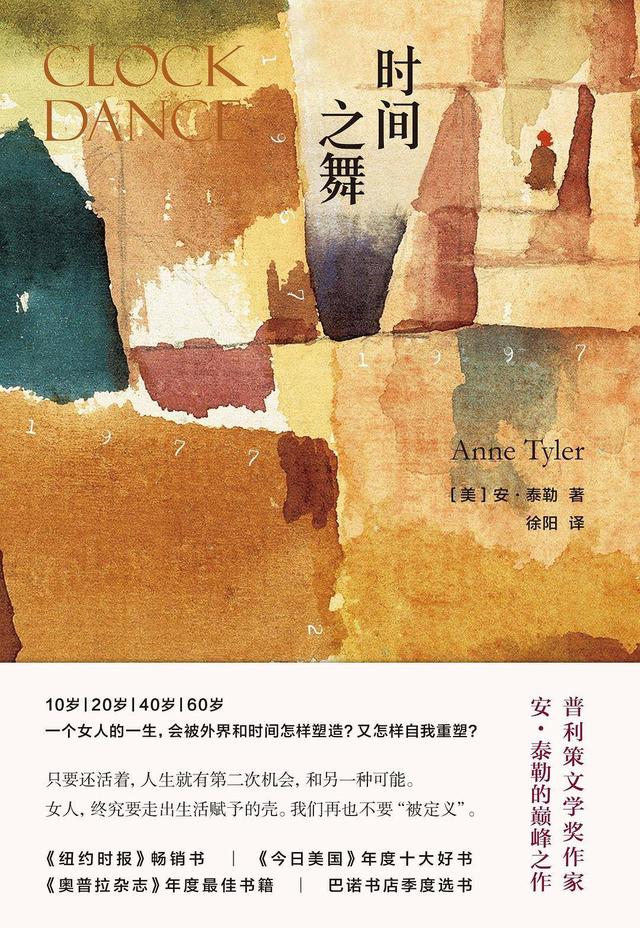
初初看时,也许会有读者觉得作者写得过于平淡和细碎,有点像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加拿大女作家艾丽丝·门罗笔下的女性,但心理活动没有那么细腻;又有点像瑞典作家弗雷德里克·巴克曼笔下那个倔强的叫欧维的老头和叫布里特-玛丽的63岁老太太,但故事跨度更长、表达的主题更偏向家庭而非个体。
实际上,安·泰勒最擅长的便是家庭与婚姻这个主题,她曾说,婚姻“就像灾难片里的地震,人们猛地聚在一起,暴露出真实的个性。家庭生活更是如此,几乎不可逃避,所以给小说家提供了非常好的仿真菜肴。”因而,在她笔下,总是能呈现出平凡生活中值得落笔和着眼之处。
在《时间之舞》的腰封上,编辑选择的推荐语是“一个女人的一生,会被外界和时间怎样塑造?又怎样自我重塑?”但我的第一感受更认同《人物》杂志的评价:“这个震撼人生的故事颂扬了自我发现的乐趣,揭示了家庭的真义:家庭需要我们自己去定义。”
01 家庭
美国著名的家庭治疗师奥古斯都·纳皮尔和卡尔·惠特克曾在《热锅上的家庭》一书中分析原生家庭的影响,有毒的家庭必然会带来诸多负面影响,“即使我们对自己的成长经验很满意,但总会多多少少对自己或原生家庭有不满意的地方。无意之间我们会期盼与足以带给自己新的人格特质、经验与关系的人结合。在建立自己的家庭时,我们希望能解决某些存在于自己原生家庭中的问题。借着选择配偶,我们希望完成心理上的完整。”
薇拉的原生家庭幸福吗?从她小时候的愿望可以看出,在原生家庭中,她对随和友善的父亲很满意,但对于无法预测的妈妈则敬而远之,她甚至曾经向自己保证,绝不要成为像妈妈那样的人。
从小说中的部分描写可以推测,薇拉的妈妈很可能罹患双相情感障碍,在她病发的时候,她会表现出很多不理智甚至伤害孩子的行为:
妈妈会冲他(爸爸)大吼、跺脚,或给薇拉一记耳光(多么耻辱的心痛经历,被打耳光——在旁人看来还是挺吓人的),她还会抓着伊莱恩拼命摇晃,当她像破布娃娃一样,然后妈妈用双手扯自己的头发,松开后,脑袋两侧都乱蓬蓬的。还没等你反应过来,她就已经离开颤震的房子,扬长而去。
而爸爸的表现呢?爸爸会说“没事,她只是需要一点儿思考时间。”至少他看起来毫不担心。“她只是累了。”爸爸会这么说。
爸爸真的是个完美父亲吗?
家庭是一个复杂的动力系统,在每个家庭中,成员之间的结构、层级和互动关系都有着固定而隐秘的运行规则。
在薇拉的家庭中,父亲对于母亲的病情实际上表现出的是一种漠不关心,他在扮演着“圣人”的角色,他表现得随和友善,但是对自己的妻子却没有尽到足够的照料义务,只是给予妻子“思考时间”,却没有爱与关怀。
薇拉11岁时母亲的这次出走算是时间较长的,但父亲并没有费力去找寻;薇拉和妹妹伊莱恩放学后回家打算照着菜谱制作巧克力布丁给父母一个惊喜,但因为没有做足步骤失败了,父亲的反应是教导她们正确的方法,而丝毫没有肯定她们的心意和努力。
为此,薇拉非常生气,但只是生闷气,她没有把自己的真实想法说出来,就像她在接下来50年间一样,她只是自己默默地想、生气、抉择,却从来不会将自己的需求诉诸于人。
在这个家庭系统里的另一个成员——薇拉的妹妹伊莱恩——则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她在青春期非常叛逆,将自己打扮成小混混一样。这实际上是伊莱恩寻求父母关注的一种方式。求而不得的伊莱恩在接下来的50年间过得非常淡漠,与家人几乎失去了联系,即使是与自己曾经亲密无间的姐姐,也无话可说。

11岁的薇拉生气的原因,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父亲没有给予她足够的认同感。
正如纳皮尔教授提到的,我们在建立新的家庭的时候,总是希望能够解决自己原生家庭中的某些问题,因为人总是试图对自己的人生拥有掌控感,既然原生家庭无法选择,那么自己的婚姻就必须能够如意。
21岁的薇拉面对德里克的求婚表现得非常犹豫不决,对薇拉来说,放弃学业是一个艰难的抉择,而另一个艰难的抉择是判断德里克是不是自己理想的丈夫人选。
在回家的飞机上,薇拉坐在三个座位的中间,德里克坐在窗边,旅程中薇拉突然感到旁边的陌生人用一支枪抵住了自己的肋骨,她吓到一动不敢动。德里克似乎察觉到异样,又或者只是偶然,提出了跟薇拉调换座位,将薇拉从困境中解救了出来,在那一刻,薇拉觉得德里克是自己的英雄。
但是事后,德里克却非常怀疑薇拉是否真的经历此事,他怀疑一切只是薇拉杜撰出来的或幻想出来的,甚至为此与薇拉的父母发生了激烈的争执。就在双方发生争执的时候,薇拉下定了决定,她要嫁给德里克,并毅然离开了家。
第一次看到这个情节设置的时候,我自己是无法接受的,完全不能理解薇拉的决定。
但转念一想,这也许才符合薇拉这个人物的内在需求:认同感。
诚然,德里克怀疑薇拉的经历是在否认她,但在两人初相识的时候,在薇拉还是只丑小鸭的时候,在父母都担心她会永远嫁不出去的时候,德里克看到了她灵魂里的光芒,牵起了她的手,这种认可对于薇拉而言是极其宝贵的。她曾经努力想要在家庭中获得这种认同感,但始终求而不得,所以当父母与德里克发生冲突的时候,她非常畏惧又一次失去别人的认同感。
德里克刚到她家的时候,有一段餐桌上的描写非常形象地传递了薇拉的内在需求:
薇拉静静地给饼干抹黄油,突然感到自己非常重要。这三个人聚在一起坐在这儿,全都是因为她。她前所未有地成了自己世界的绝对中心,慢慢地享受着甜蜜的饼干时光,眉眼低垂,慢慢地将黄油在饼干上细细抹匀,一直抹到边缘,这个动作令她感到悠闲自得。
但同时,我们也不得不承认,我们在建立新的家庭的时候,一方面寄希望于新的家庭动力系统能够解决旧的问题,另一方面我们的潜意识又希望新的家庭动力系统能够表现出我们所熟悉的特征,因为熟悉感才能带来安全感。
薇拉的两任丈夫表现出出奇一致的特征,两个人都有些好胜心强、自我中心、脾气暴躁,按照肖恩的话说是“难伺候的人”。从她的两段婚姻来看,的确她在重复着自己熟悉的婚姻互动模式。但与她的原生家庭似乎完全不同,她的父亲是个过于温和友善的丈夫了。
但再深入分析会发现,本质是一样的,薇拉在扮演着曾经父亲的角色——和蔼友善耐心细致地伺候那个难伺候的爱人。薇拉在试图用自己的方式控制原生家庭中的“失控”,那些母亲离家而去的日子她无力挽回,但至少,在自己的婚姻中,她在努力维持一种完美。
薇拉的深层动机被后来认识的本医生一语道破:
“我太太以前总是说,最糟糕的事情就是嫁给甘地。”本说。
“为什么?”
“想想吧:甘地是圣人。和他比起来,其他人看起来都很粗鲁,大嗓门,都以自我为中心。”
“我觉得我妈也许就是嫁了甘地。”最后她说道。
……
“要么嫁给这种人,要么自己就是这种人,以前我是这么想的。”
很显然,薇拉自己成为了“圣人”。

但,没有人生来就是圣人,俗世生活中的“圣人”无非是牺牲了自己的所好来成全他人罢了,但这种极高的道德感既让别人产生逃避的冲动,也让自我长期被压抑。
要解放自我,就需要一个契机。这个契机就是薇拉在61岁时接到的这个电话。
美国密歇根大学文学教授托马斯·福特斯在《如何阅读一本文学书》里归纳到,大多数关于某人去某地完成某事且出发原因非己所愿的故事,都是“追寻小说”,其真正原因永远是找寻自我。
在薇拉接到这通电话后,她本可以置之不理,却选择了踏上旅途,大概是因为听到了命运的召唤。
之所以出发去某地更容易找寻自我,是因为在陌生的环境中我们惯常用来作为保护盾的熟悉感会消失,面对不确定性,我们可以选择缩回到狭小的自我中,也可以选择打破自我的外壳,接触更多的不确定性;无论哪一种,都会让我们对自我有重新的审视与思考。
当薇拉离开亚利桑那州来到巴尔的摩,她的探索之旅开始了,但她的自我追寻之旅真正开始,应该是在彼得离开之后。彼得无法忍受住在陌生人家里、照顾与自己毫无血缘关系的孩子,无法忍受远离自己熟悉的人际圈子和生活,于是丢下薇拉一个人飞回了家。但彼得在场的时候,薇拉仍然是小心翼翼的薇拉,她需要时刻留意彼得的情绪和心情,为彼得的无礼向他人道歉。
有时,薇拉感觉自己生命中有一半时间是在为某些男人的错误道歉。应该说,是她生命中的一大半时间。先是德里克,然后是彼得,他们总是迎头往前冲,留薇拉在身后尾随,收拾残局,道歉解释。
但当彼得离开之后,这种桎梏就消失了。薇拉可以慢慢展露出自己的真性情,去成为别人需要的人,尝试自己开车,每天在固定的时间遛狗并与街道上的邻居们打招呼,参与到自己喜爱的游戏中。
在这个过程中,薇拉发掘出自己身上更多的可能性。原来自己没有那么路痴,开车技术也还可以,最关键的是,有人发自内心的需要自己、认可自己。
彼得离开之后的每次电话,都是在喋喋不休地抱怨,谈论的内容都是自己身边发生的事情,从来不过问薇拉过得怎样。这种极度自我中心的男人怎么可能关注到敏感细腻的薇拉的内心需求?
但在丹尼丝和谢莉儿身边则不同,她们真心实意地需要她、挽留她、接纳她,同时也关注她的需求;她们对她懂得五门语言发自内心地崇拜和赞赏;她们依赖她时有一种亲人般的羁绊。
在薇拉决定回家的时候,彼得不管不顾、拒绝到机场接她,但薇拉丝毫不介意,这位丈夫的喜怒哀乐已经无法影响到她,也不会让她再惴惴不安地想办法弥补彼此之间的不悦了,这标志着薇拉的自我已经开始逐步强大,她的自我在剥离那些与自己无关的部分——尤其是从小一直与自己如影随行的原生家庭与婚姻。
而作者给了读者们一个更棒的结局:在薇拉落地后,在机场的人潮里,她决定回到巴尔的摩,回到那条街道上,做一些更需要自己的事情,比如利用自己曾经钟爱并已引以为傲的语言能力,帮助更多来美国的移民。
至于彼得嘛,再也不是薇拉自我的一部分了!

什么是时间之舞?
在谢莉儿这些9岁的小孩子们看来,时间之舞是大家站成一排,将手臂当成指针,跟随乐曲中的滴答声转动手臂。
而在薇拉看来,她会让“一名女子在舞台上从左向右一路旋转下去,观众只能看到一团飞旋的模糊色彩,然后她便消失在侧幕中,呼呼!就这样。然后消失。”
时间之舞的寓意每个人会有不同的理解,于我而言有三重寓意:
- 第一重寓意着快速闪过的一生,从11岁到61岁的薇拉都在飞快旋转着掠过舞台,并没有在别人的生命中留下太多的痕迹;
- 第二重寓意是对于本人而言,这支舞蹈非常简单,简单到甚至没有一个驻足停留的宝贵时刻便结束了;
- 第三重寓意在于独舞,不同于三个小女孩的配合,薇拉的生命中并没有遇到真正与她“嵌合”成时针与分针的人,她与家人之间更多是表面上的关联,她的父母、妹妹、丈夫与两个儿子都不曾深入她的内心世界,表面看上去的美满,本质上永远是一个人的独舞。
但这支独舞在舞者消失进侧幕时并没有结束,薇拉在61岁的时候,又重新旋转回了舞台,这一次,她可以一个人成为自己世界的绝对中心。

免责声明:本文仅代表文章作者的个人观点,与本站无关。其原创性、真实性以及文中陈述文字和内容未经本站证实,对本文以及其中全部或者部分内容文字的真实性、完整性和原创性本站不作任何保证或承诺,请读者仅作参考,并自行核实相关内容。文章投诉邮箱:anhduc.ph@yahoo.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