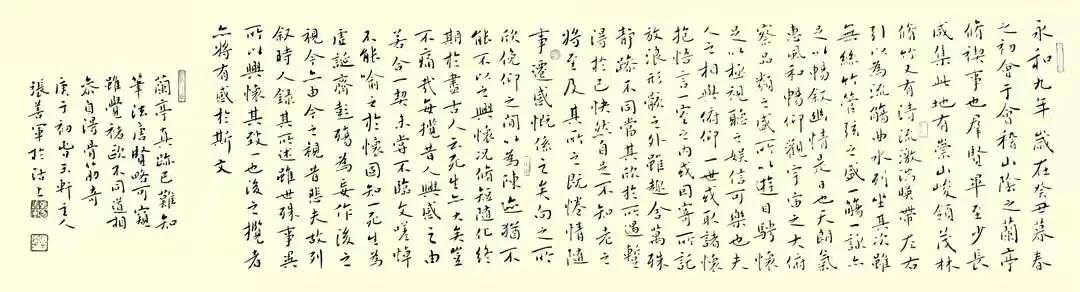永不熄灭的那盏灯(那些永不熄灭的灯盏)
文:张克习 图:来自网络
岁月匆匆,转眼间外孙已经到了上学的年龄了。为了给他营造好的学习环境,家里为他布置了书房,买了许多时尚的学习用品。
为了他晚上看书方便,还购买了落地台灯。这是一台LED灯,一有米八高,铝合金方管支架,通体浅灰色,亮度可调,光线柔和,一看就属于高大上的东西。看着这台花费几千的灯,我感慨万千呐……

曾几何时,一盏如豆的油灯,尽管它弱不禁风,火苗飘忽不定,浑身沾满了油腻,但要经过我苦苦追求才能拥有和点亮。在艰苦的岁月里,这盏丑陋、寒酸的油灯却和灶台、饭桌构成了我家的生活中心。
一到夜晚,害怕黑夜的我总是渴望家里尽快地点起油灯。但是为了省下油钱,大人们不到关键时刻,无论如何是不会轻易点亮油灯的。
那个时期,我既敬畏又向往灯光。在缺油少盐的日子里,我对灯光的向往不亚于佛教徒对佛龛的神往。那时候我家只有一盏油灯,哪里需要就把灯端到哪里去。
“高灯矮亮”是大人们常挂在嘴边的话,所以打小我就知道要把灯放在高处,这样灯光照亮的范围会大些。灯光不仅能够驱散令我生畏的黑暗、带来光明,而且能给我带来快乐,所以天一黑我总希望家里的灯光早点亮起。
有几次我置“点灯熬油”这一朴素的道理于不顾,私自把家里唯一的一盏油灯及早地点亮了,因此遭到大人的责怪。年龄稍大一点,我也知道了节省、学会凭着白天的记忆,在黑暗中摸索做事、找东西。
据听说早期的油灯用的是食用油,那时候人都吃不上油,何来点灯用油!我记忆中的油灯用的是煤油,那时人们称煤油为洋油。
煤油灯火头明亮,烟气小,很受乡村人的欢迎。那时母亲常告诫我,过日子三件事——拾柴捞火、称盐、打油,我想买煤油点灯,应该包含在打油这件事里吧。
记得我家第一盏煤油灯如墨水瓶子那样大小,是个玻璃瓶,一个中间带孔、做工粗糙的铁皮盖松弛地盖在瓶口,一根比筷子略微粗的铁皮管,含着一段棉捻子插在瓶盖中心的小孔内就算作灯芯了。

灯芯的上端高出瓶盖一公分不到,下端拖着个尾巴浸润在瓶内的煤油里,那棉捻的形态逶迤、臃肿,犹如浸泡在高度酒里的贵重的营养品。
过一段时间灯不大明亮了,就要用大号的针拨一拨灯捻,这样一是拨去灯捻结焦的部分,二是借机把捻头往上挑高少许。
一个偶然的原因,致使我家这盏煤油灯从高处跌落下来,摔坏了个粉碎,一时家里每个人的心头像是缺少了什么,总是担心怎么熬过夜晚。
情急之下我跑到公社医院,到换药室后面的小巷口里悄悄地捡了一个稍大点的圆口药瓶,飞奔赶回家,用铁钉在瓶盖上冲了个圆不圆方不方的小窟窿,然后把那个摔坏的油灯的灯芯勉强地安在上面,这样一盏油灯就算做好了。
晚上点上我做的油灯,一家人都喜出望外,都感觉这盏灯比原先的大气多了,是那盏灯的升级版。虽然还是原来的灯芯,但我感觉灯光较往日明亮多了。
那时候我比较向往我家能拥有一盏马灯,因为马灯造型讲究,制作精良,可以手提着随意走动,特别是不怕刮风下雨,灯的亮度可以随意调整。
可马灯无法自制,只有花钱到专门卖灯的商店去买啊!一提到要花钱,我内心对马灯的憧憬一下子消失殆尽。
并且那时马灯只有生产队和极少人家才有,一想到这,我内心也就释怀了。
还有一个偶然的时间,我看到生产队会计办公桌上亮着一个台灯,引起了我的兴趣。那灯的上部有个腰鼓形的玻璃罩,下部像哑铃。整个灯看上去玲珑剔透。或许为了使灯光更迷人和温馨,那玻璃灯罩外还套了一个白纸卷成的灯罩呢。
可是像马灯、带玻璃罩的台灯这样看上去高大上的灯,只有生产队才有,并且那盏台灯只有会计一个人才配用啊!一想到这,拥有这样灯的奢望也只好埋在心底,成为永远的秘密。

我家唯一的那盏煤油灯,虽然弱不禁风,但却时常要在锅屋、堂屋以及猪圈之间端来端去。在移动的过程中,灯被熄灭是最令家人沮丧的事。因为要重新把灯点亮,浪费火柴不说了,关键是黑灯瞎火的一时半会地拿不到火柴啊。
每当刮风下雨要移动灯的时候,我就主动站出来。因为我那时穿的棉袄破旧且肥大。我大大咧咧地把棉袄大襟解开,把那盏油灯围拢在胸前,我侧着身子,像护卫神明一样小心翼翼地把油灯从一处移到另一处。
怀里的煤油灯散发出的烟气和煤油味,丝毫没有引起我的不快。相反,怀里灯火的温暖却在寒冷的夜晚给了我特别的慰藉。
在物资匮乏的年代,买不到点灯的煤油是常有的事。记得有一年冬天,由于买不到煤油我家已经多个晚上没有灯照亮了。无奈之下,我家想出了一个应急的土办法——
把秋天收的蓖麻子的外壳剥掉,再把包裹蓖麻子仁那个黑色薄壳剥掉,然后用竹扫帚上的竹杪,将蓖麻子仁像串糖葫芦那样串成串,用火柴点燃蓖麻仁串代替油灯来照明。
在用土办法应对夜晚照明的同时,我和邻居的小伙伴们也四处打听哪里有煤油卖,一旦有了消息,我们就结伴前往。
记得那是一个冬天的下午,西北风刮得特别的猛,树梢发出一阵紧似一阵的鸣响;乡间的路面被吹得像赤膊莽汉的脊梁;路边枯草个个都一丝不挂,肤色苍黄,强打精神迎寒而立;枯叶、尘土连同各色鸡毛在墙角处,在沟渠的转弯处聚会,它们弹冠相庆,人来疯似的打旋、上下翻飞。
我和小伙伴顺子听说,离我们村五六里路远的一个代销点有煤油卖,于是我们就顶着寒风前去打煤油。我家打了两毛钱的,有小半瓶,顺子家打了五分钱的,好像没过瓶底没有多少。当时我还暗自嘲笑顺子家寒酸呢。
在回家的路上,我俩被寒风催逼得不得不一路小跑,尽管是这样,身体冻得还是受不了。于是我们两个就跑到一个深沟下去避风。背靠着沟坎我们歇息了片刻,待身体的寒气散去一些,又整了整衣袖,准备一气跑到家。
为了保住这半瓶期盼已久才买到的煤油,我把油瓶子揣在怀里,左手伸到怀里把着瓶子,以防煤油咣当出来,右手臂从棉袄外面搂住自己的前胸,手掌塞在腋下,像企鹅一样,被西北风追赶着,左摇右晃地往家的方向奔……

夜幕降临,我家多日没有点亮的煤油灯又重新亮了起来。一家人围坐在饭桌旁,昏黄的灯光混合着饭的热香气,氤氲着,弥漫着幸福的味道。
一向傍黑就打盹的奶奶,此刻昏花的眼睛竟然也水灵起来了,那双看惯秋月的眼不停地忽闪着,像欣赏婴孩的脸蛋一样品味、把玩着跃动的光焰……
时代的步伐,跨入一九七八年,那是全面改革开放的前夜。中国即将告别物资短缺的时代。那时煤油已经敞开供应,农村也告别了一家一户一灯独明的年月,我家也用上了高大上的台灯了,并且我自己也可以独享一盏煤油灯,晚上看书不管多晚母亲也不会责怪我点灯熬油了。
这一年,我带着对高中学习生活的向往,走进了公社驻地的中学。这时只有公社机关和学校率先通了电,晚上有了电灯照明。这时教育已经走上了正轨,初、高中学生开始住校上晚自习了。
夜幕降临,教室里的电灯齐刷刷地亮起,感觉教室里的一切都焕然一新。可是,那时候的供电不稳定,经常停电。学校为了应对停电已经准备了神器——汽灯。汽灯亮度比日光灯要高得多,但是很遗憾,汽灯会形成灯下黑,并且还发出“呲……呲……”的气化声。
在汽灯也坏了的那一刻,只听一股欢呼声如巨浪般在教室里应声掀起,把遗憾、沮丧的声音彻底淹没。虽然同在一个教室里上课,在灯光一亮一灭间,映出了每个人的学习心态。
要是和外孙这台富含高科技的LED灯相比,我家那盏煤油灯连同我曾经向往的台灯、马灯、汽灯……绝对是丑小鸭。但是奢华的LED灯,它是冷光源,没有温度,它照亮的只是我的眼前。
而我家那盏煤油灯,虽然光焰不怎么明亮坚毅,甚至是弱不禁风,但是它曾经伴我穿过黑夜,走过泥泞,经历寒雨风雪。我呵护过它,它温暖过我,它照亮了我求生存求发展的路,它是我心里永远不灭的灯。

今天记取这些灯的往事,无意抖落苦难,旨在珍惜当下,汲取前行的力量!
,免责声明:本文仅代表文章作者的个人观点,与本站无关。其原创性、真实性以及文中陈述文字和内容未经本站证实,对本文以及其中全部或者部分内容文字的真实性、完整性和原创性本站不作任何保证或承诺,请读者仅作参考,并自行核实相关内容。文章投诉邮箱:anhduc.ph@yahoo.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