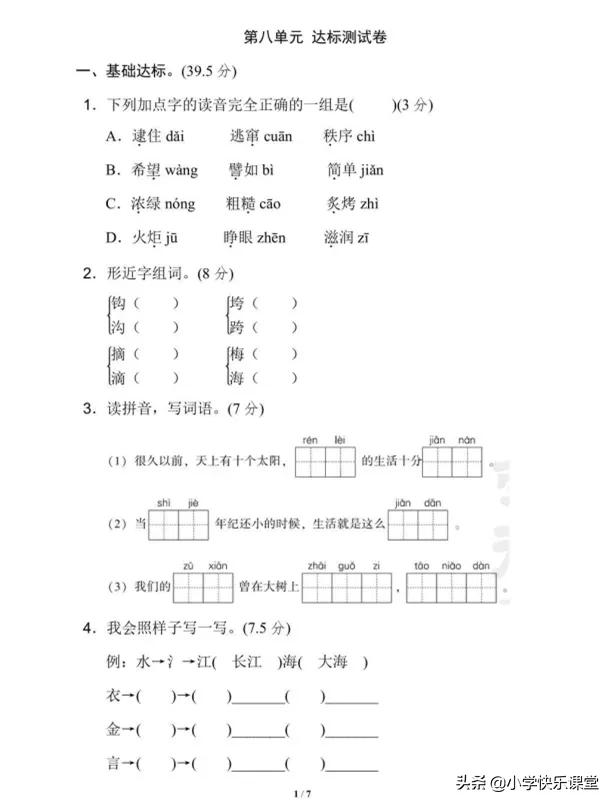少数民族地区留守儿童受教育现状(适龄儿童未上幼儿园)
本文刊载于《三联生活周刊》2020年第5-6期,原文标题《山村幼儿园:大山里的教育公平实验》,严禁私自转载,侵权必究
中国还有约20%适龄儿童没有上幼儿园,他们多集中在贫困山区。山村幼儿园尝试解决学前教育“最后一公里”的问题,将幼儿园带入这些乡村。
记者/黄子懿

留守、贫困、孤独等,这些都是山村孩子们成长面临的“毒性压力”,会影响其成长发育(秦斌 摄)
抢救式干预
5岁的小诗雯努力地在石板上走着。所谓“走”,是用双手提着两个特制的“平衡木”,脚踩其上,步伐随着手提动作而动。特制“平衡木”是一罐用过的紫色奶粉罐,顶部用不到1米一根绳子系着,首尾连接。小诗雯要弯下腰,双手提绳,双脚一步步往前挪着小步。
这是一场幼儿园锻炼儿童平衡能力的游戏。小诗雯要往前挪动约10米,然后快速通过一段由砖头垫着的独木桥,再跳过6个汽车轮胎。但小诗雯在第一环节就卡住了,她手提着奶罐“平衡木”时,每步只能挪动10~20厘米,比其他小朋友缓慢许多。但她似乎想尽力做好这个动作,在平地上小步往返练习,不去参加其他环节。
突然,她摔倒了。铁质的奶粉罐在地上碰撞出清脆的声音,衣服沾上了尘灰。在不远处的观望的老师肖燕赶紧过来扶她起来,拍了拍她身上灰尘。“没事吧,诗雯?”“没事。”“要不你先休息一下?”“不休息了。”小诗雯说罢,又开始了自己的平衡练习,铁罐发出撞击石板的声音,在冬日的大山沟壑里回响。
小诗雯是青海省海东市乐都区刘家寺村的一个5岁女孩。当平衡练习后,我走进她家,才明白她的那一份坚持与倔强何来。小诗雯一家是村里的建档立卡贫困户、低保户。家里三厢房,两厢是近些年危房改造翻修而来,老房布满了木质架子。放学后的下午,小诗雯唯一的玩伴,是家中一只不到半岁的小橘猫。妈妈从家里消失了——她蜷坐在村口一张桌子上,靠墙晒着太阳,看着女儿回家也不为所动。坐在一旁的几个男性,刻意与她留出距离。
“她妈脑子不太清楚。”50岁的大伯说,诗雯母亲有精神病,父亲常外出跑运输,爷爷早逝、奶奶残疾,诗雯的放学接送、伙食多靠他负责。大伯至今单身,不会说普通话,而诗雯母亲几乎没有照顾能力,这导致诗雯性格内向。5年来,她和大一岁的姐姐相互照顾。冬天,姐姐帮她穿上几层的厚衣服,她则要自己洗袜子。“没办法,穷人的孩子要早当家。”

在山村幼儿园里,孩子们能找到彼此的玩伴(秦斌 摄)
现年72岁的卢迈是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的副理事长,从事基金会工作20多年来,他见过无数个类似的孩子。贫困、留守、父辈疾病、长期被忽视……成人世界的疤痕,在这些年幼的孩子们身上,已有了外露的痕迹。无论在哪儿,每当卢迈上门造访这些山区幼儿的家里,都会见到各类认生的孩子。有的躲在爷爷奶奶身后,怯生生地看着他;有的钻进床底和内屋,怎么叫也不出来;还有的孩子,会被直接吓哭,仿佛见到了外界“怪物”。
低质量的看护与环境,用学术词语来说,是孩子成长的一种“毒性压力”(toxic stress)。如果看护环境长期得不到改善,“毒性压力”将损害大脑中负责情绪控制和社交能力的神经元连接。来自脑科学、经济学等多学科的实证研究表明,人类大脑的语言、社交、情感功能发育高峰均在4岁以前完成,3~5岁是成长教育的关键窗口期。农村孩子一旦错过窗口期,贫困极有可能代际传递下去,让这些孩子20年后成为新的贫困人口。
大山不像城里,难有幼教机构。乐都依附在河湟谷地狭长地带,南北两岸皆是祁连山区,属于中国11个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之一。刘家寺村就坐落在南部山上。12月的冬日,山区被成片的泥黄色覆盖着,没有一丝亮色,只有干枯的植被与裸露的黄土,将低矮平房包围,彰显着人力在这土地上的渺小。
上世纪90年代,曾有当地人集体“卖血”被媒体曝光,而如今,贫困表现在娶媳妇难。小诗雯的妈妈,是父亲第四个带回家的女人。大伯说,诗雯爸爸今年47岁,10年前从浙江带了一个媳妇回来,对方后来跑了;过了几年,他又找了一个西藏女友,来这住后不久,女友“待不惯”,又走了;诗雯爸爸没有办法,选择近亲结婚,娶了舅舅的女儿,却在生育时因难产妻儿双亡。最后,他找到了诗雯妈妈,后者曾远嫁甘肃,“可能是在那边受了什么刺激”,逃回家后就神志不清。
希望工程发起人、南都公益基金会理事长徐永光曾呼吁,这些乡村孩童急需一场“抢救式干预”。在卢迈看来,贫困山区是中国学前教育目前的最大短板。据其估算,中国0岁到6岁孩子中,约有48%分布在农村,尤其是在贫困地区的村庄,这些孩子共约有1680万~2000万。当前,中国幼儿园的毛入学率已超80%。“但剩下最关键的那20%左右的孩子被遗落下来了。”卢迈说。偏偏是这部分孩子,面临着最大的“毒性压力”。

山村幼儿园设施简陋,通常利用闲置村的小教室、党员活动室等开展活动,设施多是就近取材(秦斌 摄)
卢迈说话轻言细语。他早过退休之年,可依然极为忙碌,日程排得满当。这是一个个人命运与历史进程紧紧绑在一起的老人:他是归侨子女、老三届、北大荒知青,80年代进入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师从“农村改革之父”杜润生,自此与农村政策打交道。1997年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成立后,卢迈开始与农村孩子结缘。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旗下的非营利机构,每年最重要的活动之一,是筹办中国发展高层论坛,论坛要邀请中外知名嘉宾,卢迈要上台与诺贝尔奖获得者、全球政商领袖对话。另一边,他又频繁出现在各地偏远乡村。“甘肃庆阳校车事件”“贵州毕节4兄妹自杀事件”后,他都带着同事去了现场,了解事因。亲历这些适龄儿童的悲剧后,卢迈异常痛心:要是这些乡村有就近的幼儿园,悲剧是否就可以避免了?
卢迈和同事决定送幼儿园进村。2009年,基金会启动了“山村幼儿园”计划(又称“一村一园”计划),在一些贫困山区建幼儿园,只要一个村子里有10个适龄儿童,就去开一个幼儿园。第一个试点就在青海乐都,当时的乐都还是一个县,县城仅有两所幼儿园,全县学前幼儿园毛入学率为46%,超过一半的孩子被遗落下来。基线测试显示,在语言认知上,农村孩子大约只有城区孩子40%~60%的水平,记忆能力只有约20%,“因为没人教过他们记东西”;在跑、跳等大幅度动作上,城里孩子也比农村孩子表现更优异,放得开。农村孩子唯一能比肩城里孩子的,是用筷子夹东西等精细动作。很多农村孩子还不会讲普通话——当地只有收费的学前班会教,学前班用的小学课桌,很多孩子坐上去,脚都够不到地。
幼儿园成了一个急需品。但办一个幼儿园何其容易。当时有人问:怎么办起来?能不能找到钱、招到人?办起来后,教育质量能否保证?一个老师在村里能坚持多久?卢迈说,这些都是问题,起步困难很大。
山村幼儿园采用了一种最节省成本的方式,借用被闲置的村小教室、党员活动室等,与地方政府合作,政府出面招聘幼教志愿者,通常要求各类师范类的大专与中专的毕业生。“农村有一批接受过教育的知识青年,在城市打工做着简单劳动力,他们也并不适应,愿意做点教育专业相关的工作。”卢迈说。
刘家寺村的幼儿园,是乐都第一批山村幼儿园,有10年历史,整个乐都现今有96所山村幼儿园。12月冬日的这一天,小诗雯就在这里练习平衡木。
“你在家里有什么玩具吗?”当我这样问小诗雯时。她立马跑到一间厢房,用双手拖出一个有她身高一半高的旧纸箱,里面装着约半箱有污垢的塑料积木。大伯说,这些都是幼儿园送给她的旧玩具,她平日回家后,就喜欢拿着这些积木拼凑。在被黄土包裹的村子,山村幼儿园为小诗雯生活增添了一抹难得的亮色。
山村里的亮色
走进这些山村幼儿园,最初很容易有种误入之感。校舍是小学的,一些幼儿园隐匿在小学教室背后深处,一些则与小学共用。刘家寺村的小学是一栋一层平房,有5~6间房,一间是小学教室,只收一年级学生,剩下的全归幼儿园,内部走廊贴满了孩子们的画与手工作品。
这样的幼儿园,硬件成本一年只有几千元。设施是简陋的,外墙是黄土的,厕所是没有隔离的蹲坑,粪便在下面垒了1~2米高。除了奶罐做的“平衡木”外,还有被胶带缠好的7个八宝粥罐子做成的“垫脚石”,把小学课桌锯断一截腿而来的小桌子。走廊尽头,是两处供孩子们玩耍的小沙盘,里面还有水迹。“我们这里没有纯沙,都是土沙。”一位老师说,这些沙子多是家长从山上弄来的。
这一天是周三,幼儿园亲子活动日。14个孩子中,超过一半是双留守儿童,家里只有老人。中午刚过,爷爷奶奶们就带着孩子前来,拿着扫帚和抹布。孩子们练习平衡木时,爷爷们进行大扫除,奶奶们搬个凳子,在一旁挨个清洗擦拭玩具。这些玩具,与小诗雯家的一模一样。一个孩子淘气,在独木桥上使劲儿跳,把桥踩断了。一个家长就跑过去研究怎么修复,他把木头翻过来,找3个钉子钉上,下面垒上砖头加固。独木桥又能用了。
“家长现在都非常配合,很珍惜。”34岁的老师肖燕在此已工作了10年,多数时间是她一个人负责。她说,最初家长都很不配合,“今天农忙了就把孩子送来,明天闲下来就不送了”,有些带走孩子时都不会请假。很多时候,她见某个孩子没来,打电话过去问,家长就说不想来。那时候孩子们身体营养也很差,农忙时节,有些家长要早上7点就要出门,早饭就随便拿点水和馍馍给孩子吃,中午继续,导致孩子每到下午就打不起精神。
老师的日子也不好过。第一批启动81个试点,但只招到46个老师。老师们要骑着自行车,上午和下午奔波在不同村子“走教”,晚上就回到乡里的中心学校住宿,周末回家。卢迈说,云南寻甸的起步阶段更加艰难,很多幼儿园没有校舍,一度在树荫底下上课。乐都与寻甸,一北一南,是这个项目最早启动的试点。
基金会的儿童发展中心副主任曹艳记得,最初他们进村时会给家长开咨询会,家长们担心的最多的问题是:以后会收费吗?要是收费了怎么办?但卢迈承诺永久免费。在乐都,当地农民都给他算了一笔账,若是要去县城,租房带孩子上幼儿园,一年的花费约1.2万元,其中包括2000元学费、4000元房租、6000元生活费。
“这都是私人的投资。”卢迈说。按照乐都当地人口算,山村幼儿园用大概2000万元的投入,节省了这些家长约3亿元的支出。“公共产品投资有很大的规模收益,溢出效益长远。如果这么算,这钱绝对是应该投的,是国家和社会的责任。”
既然是公共产品,政府的角色在哪里体现呢?山村幼儿园采用社会力量与政府合作办学的模式,基金会负责前期踩点调研、师资培训、早期主要的资金支持,地方政府则负责教师的招聘与幼儿园的管理,一般三年之后会接管幼儿园的运营。乐都虽是贫困地区,却是一个教育大区,明清时期就以出秀才闻名,当地政府很重视教育。2009年,时任海东地区地委书记与卢迈在美国哈佛大学访学时相遇,谈及农村学前教育的残酷现状,两人一拍即合,遂将试点选在乐都。

贵州铜仁市松桃苗族自治县一处苗寨内,山村幼儿园的孩子正在荡秋千(秦斌 摄)
现今乐都有178个幼教志愿者老师,都是乐都政府出面招聘,包括肖燕。10年前,肖燕还是一个民办幼儿园老师,学前教育专业毕业。她看到县(区)教育局招人,就果断去报名,当时报名已截止,工作人员看她专业对口,给了补报机会。“教育局招人,会觉得靠谱一点,虽然没有编制。”肖燕说,当时她觉得城里民办幼儿园存在一些乱象,即幼儿园“小学化”,主教孩子算数和认字,“都是为了家长高兴”,而幼儿园的功能被弱化了。
在早年的其他试点,一些地方政府也秉承着类似观念。曹艳说,那时候项目刚在全国铺开,他们在调研时发现,有些地方政府会悄悄把招聘给山村幼儿园的青年教师安排去到当地小学,留给幼儿园孩子的是代课老师或一些素质不高的小学老师。“就是那种他们不好辞退的,就安排给我们。”曹艳觉得很无奈,“我们不太赞同小学老师来做幼教,二者要求完全不一样。”
在山村幼儿园,孩子们以玩乐游戏为主,建立与同伴的联结和对外界的初步认知、锻炼表达和人际互动的能力。教室配有电子琴、电视和电脑。肖燕说,电脑是最近一年才配的,以前电视也没信号。“比如说要给孩子们讲动物吧,光看图片他们没感觉的,一定要动态的。”幼儿园教材是当地政府参考公办幼儿园教材,结合本地风土人情编制。
“上没上幼儿园,孩子们差别很大的。”卢迈说,幼儿园办起来后他去走访,多数孩子们一遇见外人就会问好,热情洋溢,普通话标准。肖燕说,很多孩子刚进幼儿园的时候会哭闹,有跟着她屁股后面半年不愿离开的,还有看见生人就会吓得哭的。“因为在家里爷奶会说,老师是很凶的,还会讲‘吃人婆’的故事。”
小诗雯的改变很大。肖燕说,小诗雯刚来时,“闷闷的,不说话”,状况持续一学期。后来活动参与得多了,她慢慢开朗起来,如今陌生人问她什么,她都能回答。大伯说,她回家能自己画画了,有时候还想看看姐姐的小学课本,这让他和诗雯父亲很欣慰,“当时给她取这名字,就是想让她好好读书,能有点出息”。
在乐都,基金会追踪了10年来受益的8500多名孩子进入义务教育阶段后的学业表现。研究发现,近70%的山村幼儿园孩子在进入义务教育阶段后成绩分数在平均分以上,这一比例仅次于县城公办幼儿园的74%,而其他幼儿园(乡镇幼儿园、民办幼儿园)为47%,而没有接受学前教育的不到20%。多个试点地区的数据显示,读过“山村幼儿园”的孩子,语言、认知和社会性显著高于未入园儿童。
肖燕说,山村幼儿园受限于小规模,但有时反而效果更好,放得开。她的孩子在县城上的幼儿园,一个班50~60个孩子,玩玩具要排队,山里的孩子拖着一根木棍就能跑,城里的孩子则更局促一些。她曾把孩子带来几次,看见这里的游戏,孩子怯生生地不敢上,“平衡木就不敢玩”。据基金会邀请中科院心理所、哈佛大学教育学院等机构所做的最新评估显示,乐都1378名上过山村幼儿园的八年级孩子们,除了在瑞文智力测试成绩中稍落后于县城公立幼儿园的孩子外,在抗逆力(resilience)、亲社会行为上表现都更好。
要做到这一切,所需投入却并不多。乐都教育局副局长张永鹤告诉我,现在若要新建一个幼儿园,投入至少百万元起,而在村里改造一个幼儿园,经费很低,花费不过几万元。乐都96所山村幼儿园,大多采用的是一个老师配十余个孩子的搭配,小规模,成本节省。一个幼儿园的管理维系,一年约需3万元,最大的成本(80%)在教师的工资。
2012年之前,资金主要由基金会向社会筹集。2012年,乐都教育局接手管理,公共财政进入,保障项目运营。10年来,乐都有超过2.5万名孩子受益于山村幼儿园项目,学前幼儿园毛入学率已由10年前的不足50%,提高到如今的98.6%。
从乐都起,山村幼儿园也扩展至全国11个省30个县,共有3800个幼儿园(班)在各个贫困地区生根发芽,累积惠及超过20万名孩子。贵州松桃、新疆阿勒泰、云南怒江等地区,都有山村幼儿园的身影。
2018年,“山村幼儿园”计划获得了世界教育创新峰会(WISE)的教育创新奖。该奖项有“教育界的诺贝尔奖”之称,山村幼儿园成了有史以来第一个获奖的中国项目。WISE表示,该计划获奖是因为“服务了最需要的人”,而其创新在于“在规模和能力上,充分利用并实现了政府议程”。

青海乐都,幼教志愿者带着孩子们玩老鹰捉小鸡的游戏(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供图)
公平的起点
然而,在山村幼儿园之外,中国还有大量的农村没有幼儿园。全国共59万个行政村,有40万个没有幼儿园——这个数据来源于农业部的统计。
卢迈奉行“社会实验”加“政策倡导”的方式做公益。早年,他在杜润生手下做农村政策工作时,先后参与过流通体制改革、城市蔬菜价格改革、贫困地区和边境开放等调研工作。亲历国家政策的制定过程,让他意识到,要解决中国的问题,一个很重要的方式就是帮助政府形成政策,“政策可以影响千万人”。
“阳光校餐”计划是基金会成功影响决策,从社会实验上升为国家政策的一个成功案例。2008年起,卢迈团队对贫困地区学生营养状况进行研究,并着手推动营养改善,如提高补助、课间加餐等。三年后,项目上升为国家政策。2011年年底,我国启动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多年来累计投入上千亿元。受益于该计划的8~12岁学生,平均身高均有增长,其中11岁男、女生平均身高分别增长了5.7厘米、5.6厘米。
“没想到,山村幼儿园等了10年。”卢迈说,最早启动时,他以为项目能在3~5年内同样上升为国家政策。他在多个场合呼吁,全国推广的成本并不高,10万贫困村办园的成本不过30亿元。他建议将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比重,从目前的4.1%提高到5%,惠及更多贫困地区。
不过卢迈说,他能理解政府的考量,即担心风险与可持续,“政府立了项,就是不能随便撤掉的”。在云南怒江和江西吉安,都有政府领导给他承诺:只要幼儿园建好了,老师找到了,顺利运营2~3年后,地方政府将以政府购买社会服务的方式接收。2009年项目启动时,与乐都一同启动的云南寻甸县就暂时失败了。“模式也是一样的,但那个试点就非常不顺。”曹艳说,这与政府配合程度、当地群众基础有关系,当时大政策就是依靠民办幼儿园来解决问题。
即使是成功的试点,也存在一定师资流失的问题。一个幼儿园,80%的成本会花在老师身上,但在乐都的老师,哪怕工作10年,如今平均每月工资也只有2400余元,超一半依靠中央财政转移支付。“一些老师考上事业编制就走了。”乐都教育局副局张永鹤说,以前还有3个男老师,现在只剩一个坚持着。
在山村幼儿园,老师们都被叫作“幼教志愿者”,或许也是其处境的一个反映。张永鹤说,乐都所有幼儿园有8000多个孩子,但在编老师只有24人,“几十年没变过,这个全国都一样的”。他说,不希望编制增加,但最好待遇上能同工同酬。为留住这些老师,教育局在2012年接手后,给志愿者们上了三险。目前,城区幼儿园的老师,平均工资要比山村幼儿园老师高300~400元/月。张永鹤说,希望能将老师工资提高到3000元/月,但遥遥无期。
这也是一些学者的困扰。华东师范大学学前教育系教授周念丽曾对项目进行评估。她忧心的是,这只是一种扶助形态,资源仰赖外部输血,只有靠政府或者社会力量加大力度,才能可持续,而项目本身缺乏自我造血功能。采访中,我了解到,“乐都模式”虽然取得成绩,但周边其他地区在去年之前都没有效仿打算。
目前的山村幼儿园,依赖着有爱心的农村回乡志愿者们的奉献。肖燕对我坦承,自己曾动摇过,考过两次事业编制,最近一次在三年前,笔试过了,但是面试被刷了下来。“那之后我就安心了,自己也适合这个。”每天7点多,她就要从家里出门,搭同事的车或转乘公交来到刘家寺村,下午放学再回到城区家中。她的小孩,也多靠在家的父母带着。
与此同时,幼儿园本身的数量也在减少。一方面是自然的城市化进程,另一方面是扶贫工作力度加大。在政府帮扶下,大山深处的一些居民异地搬迁到城里。2011年最多的时候,乐都有超过170所山村幼儿园,如今已降至96所。原有的老师或进程中被遗落的孩子,会被就近安置到其他项目点里。
“山村幼儿园不是一个永久的解决方案,中国最好的解决方式还是城市化,让大家在城市中都能享受到好的公共服务。”卢迈觉得,消失的山村幼儿园完成了自身的历史使命,“毕竟城市里人气聚集起来时,教育水平各方面都会好一些。”但他强调,要让这些进城农民市民化,尤其是外出打工的人,在城市里也能享受到公共服务,“不能让这一代人在城市、农村两边都接不上”。

乐都属于国家连片特殊困难地区。冬天大雪覆盖黄土,远看去一片苍茫之感(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供图)
项目越做越久,卢迈对于儿童早教的认知也在变化。2011年,一场乐都的考察活动中,世界银行专家和巴西政府官员表示,儿童的干预时间越早越好。卢迈和团队梳理了国内外学术圈的最新研究,发现3~6岁之间的干预还不够,最佳干预时间在人诞生后的0~1000天内。为此,2015年,基金会启动了“慧育中国”项目,探索6~36个月农村幼儿的干预。项目借鉴国际上儿童早教模式,在当地招募育婴辅导员,每周入户一次,提供60分钟左右的育婴辅导。
基金会去年还做了另外一项研究,将中国和OECD等同等发展水平的国家的终端需求结构作比较。研究发现,过去中国的基建投资成本比其他国家高一倍,但是在包括教育等社会福利支出上,政府支出少了将近40%。“人力资本方面的支出,这是欠账的,这块要补上。”主持这项研究的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理事长刘世锦说,“不要让20年以后又出现新的贫困人口”。
“对人力资本的投资是一本万利的,越早期越重要。”卢迈说。他至今记得甘肃华池县一个叫皓皓的男孩,今年3岁多。去家访时,皓皓正被家里老人拿一个砖头拴在炕上,两平方米的炕就是他所有的活动范围。交流后卢迈得知,皓皓父母离异,父亲和爷爷有家暴倾向,不负责,奶奶则有精神病,皓皓只有靠90岁的太奶奶带着。基线测试显示皓皓属异常,成长有高风险。
这种情况下,育婴辅导员开始入户干预,教太奶奶如何与孩子互动游戏,如何锻炼其表达。辅导员去得频了,90岁太奶奶渐渐学会了。辅导员还会定期给皓皓在外打工的妈妈通电话,告知孩子的近况。最近一次中期检测显示,皓皓智力水平超过了他的年龄段。“他现在是超常儿童。”卢迈说。(文中诗雯为化名)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理事长卢迈
随着人们对大脑发育的认知越来越深化,卢迈认为,对农村儿童早期发展,越早进行干预越好。与世界上很多国家相比,中国在这方面具有独特的社会和制度优势。
乡村孩童的风险因子
三联生活周刊:从你过往的调研经验看,乡村的孩子到底面临哪些风险?贫困对他们的影响具体表现在哪儿?
卢迈:中国社会转型中,如果是在村一级底层,我们看到非常多的风险情况。第一就是留守,这是中国的特殊情况。第二个普遍情况是单亲,父母不一定办手续离异,但结婚时可能手续就不全,最后导致的事实是孩子和爷爷奶奶过,这样的孩子比例挺高。我的同事在青海乐都一个示范型山村幼儿园看到,一个班里有一半的孩子是单亲家庭,全国统计中单亲比例也是9%以上。第三就是冷漠,爷爷奶奶不知怎么带,就自然放养,缺少情感交流,村里玩伴数量也在减少。在一些深度贫困县,酗酒、吸毒这些社会问题都已侵入基层,深入村民家中。哈佛大学有一项研究,一个人有9个这样的风险因子,如果达成一定数量,就几乎会重蹈父辈的覆辙。
三联生活周刊:脱贫有很多种方式,但你一直强调从儿童入手。为什么?社会效益体现在哪?
卢迈:这是很多理论都证明了的,是脑科学、心理学、社会学、经济学等学科研究证明过的。人力资本投资很重要,投资早期最重要。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詹姆斯·赫克曼(James Heckman)教授就认为,为弱势儿童早期创造有利的学习生活条件的“预分配”策略,比后期的弥补和“再分配”策略更符合成本效益。能力会产生能力,越早投入干预,产生的能力越能延续。
我们国家做了很大努力,对教育是高度重视。在云南怒江,政府把挨着找那些不识字、辍学了的成年人,想尽办法通过各种方式找回来,真的是一个都不能少,让他们补习上识字班。还有现在的中专职业教育都免学费,有1500万学生。但除了少部分中职生,尤其是大城市里的中职生考试成绩不错外,绝大部分学生的平均成绩,按百分数算只有40分。如果等到这些人都成年了再去让他补习识字,等到上中职了给他们免学费,甚至给生活补助让他结业上高中,不如把这个过程前移。
早期的人力资本投入不仅体现在是智力发育上,更关系到关系低收入人口怎么能够沿着社会的阶梯往上盘升、向上流动,也关系到这些群体一生的福祉,包括他的生活习惯和身体健康。文化程度高的人,对自己会比较爱惜,文化程度低的人、收入低的人,有时反而会觉得无所谓。
中国做儿童早期发展有独特优势
三联生活周刊:当初你做儿童早期发展干预时,有国际经验可以借鉴吗?
卢迈:美国在上世纪60年代启动了开端计划(Head Start),是美国联邦政府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早期儿童发展项目,背景就是美国上世纪60~70年代,社会收入差距在扩大。这个计划主要关注3~4岁的儿童发展,为穷人家的孩子提供学前教育补助。现在福特基金会的会长,就是第一批开端计划的受益者。
它的个案很多,但整体评估显示,这个项目不成功。小范围做是很成功的,到全国推开时就不行了。一个重要原因是,虽然孩子们在幼儿园接受教育,但到小学后,社区、校园的环境变化对他们的成长会有影响。比如一个孩子上完幼儿园,回到一个低收入社区,暴力、毒品问题频发,会影响孩子成长。所以光早期投入还不够,一定要持续营造一个良好的环境。成长中知识信息的获取,会在他大脑功能构建的过程中根植进去,潜移默化地变成一种行为方式和认知水平。但这种能力,是会随着环境的变化而退化的。
三联生活周刊:你会担心中国的孩子重蹈这样的覆辙吗?
卢迈:我们一直在跟踪山村幼儿园出来的孩子的表现。从效果来看,学习成绩是稳定的,大部分人符合增强能力的趋势。越学,越愿意学,不像以前,没有接受过学前教育,连普通话都听不懂,上学完全是懵懂的。
所以这10年试点证明一条,初期学前教育的影响是可持续的。这得益于中国整体的社会环境和学校环境稳定,当然我们也看到有些小学,尤其是村小,也有教学水平不高、影响孩子学习成绩的现象,但整体上还是稳定的。
相较于许多其他国家,中国开展儿童早期发展工作有很明显优势,例如宏观经济稳定、政府执行力强等等。我们现在是中高等收入国家,还没有达到高水平,贫困地方连中等收入都没有,但整体上中国社会环境相对稳定,教学秩序良好,政府有很明确的教育均等化要求和定期培训检查,这对孩子成长提供了有利条件。学前教育的短板如果补上,它的效果是可持续的。
城乡孩子的差距在扩大
三联生活周刊:2015年,基金会会启动了“慧育中国”计划,针对贫困地区0~3岁儿童做入户的育婴辅导。从山村幼儿园到慧育中国,你对儿童早期发展的认识经历了什么变化?
卢迈:关于大脑发育的研究国际上早就有了,但上个世纪90年代才进入中国。2011年,我们请了一些国际专家到青海乐都去,其中包括巴西社会部现在的部长、世界银行的专家。他们在看项目的时候,给我们介绍了关于早期大脑发育的过程和早期干预的重要性,那个图往那一放,我们才看到人大脑的1000亿个神经元,知道了对于大脑发育而言,是越早干预越重要。
上世纪70年代时,大家都相信自然成长,认为大脑发育也好、对外界的理解认知也好,是一个自然过程。但随着对大脑认知越来越深刻,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我们慢慢转成了精心培养的模式。富人家庭会拿出很多的时间和金钱培养孩子,从小教孩子各种技能。所以现在的孩子比我们这几代聪明得多,他们的逻辑推理、语言表达能力是很强的。但是有谁落下了没有?就是那些乡村里被遗落在角落的孩子。现在城乡孩子的差距,可能比我们10年前测试时还要大。
三联生活周刊:这些孩子,对于中国未来的人力资本发展有何重要性?
卢迈:他们的状况,可能决定着我们整个社会的发展。比如,现在我们迈向老龄化社会了,这决定了以后所有劳动者们都要提高自己的劳动生产率,这对他们的技能提出了更高要求,以后每一个劳动者可能要多养一个人。但如果劳动力里还有20%~30%的人只是简单劳力,情感发育等方面还有问题,这对中国未来的人力资本影响很大的。
美国后来想了很多补救措施,包括90年代开展了早期开端计划等,都有点晚了。当然解决这些问题,只靠早期干预是不够的。城市化政策、户口政策等都需要改革,解决流动人口的教育问题是大事。但只要是村里还有孩子,不管占比是30%、20%、10%,对于中国来讲都是一个很大的事情。
更多精彩报道详见本期新刊《爱的物证:为什么偏偏是这一件,如此重要?》,点击下方商品卡即可购买
,
免责声明:本文仅代表文章作者的个人观点,与本站无关。其原创性、真实性以及文中陈述文字和内容未经本站证实,对本文以及其中全部或者部分内容文字的真实性、完整性和原创性本站不作任何保证或承诺,请读者仅作参考,并自行核实相关内容。文章投诉邮箱:anhduc.ph@yahoo.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