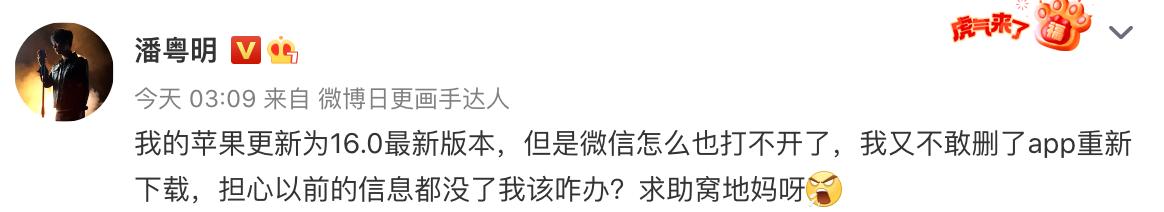现代汉语历史发展过程(现代汉语向其他语言借用了哪些词汇)
在国风国潮大行其道的今天,我们也应该意识到一点,那就是传统是层层叠加,不断累积的,对于今天的我们是传统的东西,其实在古代有鲜明的异族色彩。
诚如沈括在《梦溪笔谈》中所言:

北齐徐显秀墓的壁画
中国衣冠,自北齐以来,乃全用胡服。窄袖绯绿,短衣,长靿靴,有蹀躞带,皆胡服也。窄袖利于驰射,短衣长靿,皆便于涉草······本朝加顺折,茂人文也。

而这一过程的默默见证者,就是语言中层层叠加的外来词汇,今天,我们就从上古汉语开始,来聊一聊汉语中不同时代的外来语借词,以及它们的影响。
先秦两汉:汉语稚嫩期的外来借词

1980年周原出土的西周雕像 周天子的胡人巫师
其实早在先秦时代,很多蛮夷戎狄的部族名称,算是有典籍记载的第一批外来词汇,比如大夏,敦薨,猃狁,荤粥,绵诸,绲戎,翟,豲,义渠,大荔,乌氏,朐衍,林胡,楼烦等等。

古代中原文化的世界观是天下
而伴随着张骞通西域和汉匈战争,中国人的天下观里,第一次整体出现了西域的概念,在先秦时代断断续续的局部交流之后,东土再次和中亚乃至地中海文明建立了直接联系,与之同步的,是汉语迎来了第一大波来自草原和西域世界的外来词,这一波借词除了部族名称和国名,主要是特殊的物产名称:

比如来自匈奴语的单于,左右贤王,左右谷蠡王,殴脱,当户、且渠等词汇,还有来自波斯语的狮子(sēr),苜蓿(muksuk),琉璃(vaidurya),葡萄(budawa),还有民乐“琵琶”(burbat)“唢呐”(surna)“箜篌”(cauk),都是波斯语的借词。此外,作为西域文化的东传中介,吐火罗人也为汉语词汇的丰富性做出了贡献,比如“蜜”来自于吐火罗语的(mit),而mit其实又和原始印欧语的médhu大有关系,这个词又在斯拉夫语,梵语,希腊语那里结出了发音有别但是词源相同的果子。当然在日后的南北朝时代,有一半吐火罗血统的鸠摩罗什和其他西域僧人,将为汉语言的词汇和概念丰富性做出更大的贡献。

进入希腊化世界的汉使
而汉代很多两个字的西域城邦国名,往往有着印欧语系的来源,相关的资料敬请移步往期好文:追根溯源:这些古老的新疆地名,来自前伊斯兰时代的印欧人先民


虽然秦汉时代有过秦政的短暂荼毒,但是当时依旧充满了昂扬进取的精神,只是此时的帝国广度在不断增加,但是思想深度似乎却跟不上疆土扩张的速度。经过了汉末三国的混战和短暂的西晋,南北朝时期,有很多来自梵语的外来词进入汉语世界。由于原生文明的儒道经典,对于哲学性的三个问题“我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缺乏解释力,以及对于南北乱世中人受苦受难的原因,还有人死后的世界无能为力,五胡十六国和南北混战的乱世变局,已经远远超出了孔孟老庄的认识范围。说到底,和古希腊和古印度相比,早期文明的哲人们在思辨力和体系构建能力上存在短板。儒道留出的思想空白,就被来自西域的佛教所填补,因此佛教和西域文化对汉语言的输入在所难免。

玄奘的西游记
在当时,中原,草原和西域以或者友好和平,或者血腥暴力,或者铤而走险的方式,进行着文化交流,其中有法显这种以高龄西行获得各方礼赞的案例,也有鸠摩罗什被姚秦大军劫掠到长安的情况,还有玄奘偷渡出境,但是学成归来获得顶礼膜拜的曲折经历,还有更多的人没有在史书中留下姓名。

比如《世说新语》记载,王导出任扬州刺史的时候,有一次宴请宾客,宴会上有几个来华的西域僧人在角落里,没有和众人交流很融洽,为了活跃气氛,王导走过去,用有佛教含义的动作---弹着手指,说出了梵语里表示褒奖的话语:“兰闍,兰闍!”,西域僧人们看到自己被尊重,都很开心,主宾俱欢。这就是当时外来语进入汉语的鲜活例子。

在无数求法僧和传教僧的努力下,佛教艺术,佛教文学,还有跟着佛教进入中国的古代音韵学如春风细雨般丰富着传统文化面貌。当年的翻译遗产,依旧在滋养着今天的汉语使用者。
南北朝到隋唐的佛经翻译,扩宽了汉语词汇承载的内容,也为中国人引入了一些全新的概念:比如在谈到世界结构的时候,先秦两汉之人的第一反应,可能是“天下”或者“天地”,在描述过去时代或者当下的时候,可能会用“世”: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而佛经给汉语带来了“世界”(lokadhātu)的概念,此词汇包含了时间和空间的概念,这是一个更加立体而丰富的词汇,直到今天我们仍在使用它。

流传甚广的玄奘译本心经
佛经翻译扩宽了汉语词汇的本来意思,给它们增加了字面含义和语境含义:比如在《论语》或《老子》中,“色”的意思主要是颜色,美色或者脸色:”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就是例子;而在鸠摩罗什和玄奘等人翻译《心经》时,“色”和“空无,虚空”这一抽象概念相互对立、相互转化,意思是泛指世界上所有物质性的存在,这让”色“增加了哲学性和世界观性质的含义。

云冈石窟
当然,还有的词汇发生了语义脱落,在汉人使用的过程中,有些词汇被赋予了全新的意思,比如一尘不染现在是指干净,但是在佛教中,尘指的是指的是色、声、香、味,触、法,如果能够摒弃一切杂念,佛语就叫作“一尘不染”;其实迷信一词,最早也是来自佛教,是作为善男信女的反面出现的,意思是不能正确理解“诸行无常、诸法无我”义理的人和充满贪心、怨恨心及痴迷心的人。到了后来其来源于佛教的本意脱落,才有了妄信超自然力的含义。

汉画像砖上的荆轲刺秦王
汉文化中,还有一个受到佛教影响的观念是报应。先秦两汉时代,士人和贵族为了自己的荣誉,为了邦国的荣誉,绝不容忍别人和外邦的侮辱,有仇必报;就算祖辈遭受不公待遇,子孙不要想太多,只用继承祖辈的仇恨,为了祖先去和敌人的后代厮杀是值得赞扬的义举。先秦之人有仇必报,宁折不弯,不长久隐忍的性格和后世差异巨大,比如汉武帝在对匈奴的宣战诏书中咬牙切齿的表示:“齐襄复九世之仇,《春秋》大之”,意思是自己要像齐襄公攻灭陷害过自己祖先的纪国那样,为高祖遭遇的白登之围对匈奴人报仇。

而报应和业力等观念,则以相反的方向开导人:这一世的苦难或者喜乐,都是有前业的,这就为现世的苦难提供了圆滑开脱的意味。现代人常用的“前因后果”一词,出现在南北朝时代,就是当时佛教观念影响的痕迹,直到今天一个没有明确宗教信仰的人都会将"报应"挂在嘴边,足见观念的影响之大。
除此之外,现代汉语中经常使用的极乐、微妙、智慧、因缘、境界、喜乐等描述心理状态或者心境的词汇,都和魏晋隋唐时代佛教的传播有关,没有这些词汇画龙点睛般的点缀,后世的各种心灵鸡汤只怕是另一番滋味了;

佛教的极乐世界
除了过去,现在,未来三个表达时间概念的词汇,现代汉语中表达短时间的几个词:刹那,须臾,弹指,一瞬同样来自佛教,这背后对应的古印度发达的数学成就,没有这些表示极短时间的词汇,汉语文学的很多动作性描述或者心理活动的描写,只怕也会失色不少:
“百二十刹那成一怛刹那。六十怛刹那成一腊缚,此有七千二百刹那。三十腊缚成一牟呼栗多,此有二百一十六千刹那。三十牟呼栗多成一昼夜。”

在处理佛经的时候,为了防止出现一词多译的情况,翻译者会统一规定好专有名词的译名,比如菩提、舍利、罗刹、罗汉、夜叉、沙门、比丘、释迦、佛陀等等。这样的翻译实践,也被后世翻译在处理其他文化的经典时所采用。

玄奘和鸠摩罗什的开场译经,对于后来的翻译实践有很大启发
为了考虑受众的文化喜好,翻译在处理外来语时,会谨慎地采用汉语谐音,尽量用有美好寓意的字词,比如早期汉语对佛的翻译是浮屠,鸠摩罗什认为“屠”让人想到屠杀,和佛教的宗旨也不符合,所以他选用了“佛徒”二字。沙门,旧经为“丧门”,鸠摩罗什因为丧字不吉利,所以改为“桑门”,后世汉语中的英吉利,法兰西,德意志,美利坚等外国名的翻译选用汉语中寓意美好的字词,就基于同样的原理。
也是在集体翻译佛经的过程中,汉语语法也潜移默化地受到影响。比如当时的不少贵族名字携带僧,甚至直接用梵语里的神或者精怪为名,类似于现代中国人起英文名:

北朝时人多以神将为名者,魏北地王世子名钟葵,元义本名夜叉,其四弟罗,本名罗刹。
六朝时期的佛典中,开始使用“把”“着”“了”“过”等句式,文言文中表判断句式的“者”“也”使用频率大大降低,为了利于向大众传播,译师都会采取贴近平民的句式,而摒弃复杂冗长的句式。同时,汉译佛经也存在大量倒装句、提问句和解释句,这些句式变化也给当时汉语带来了冲击。
五代到蒙元:北方外族传入的外来词汇

在汉人政权和辽金蒙元对峙的时候,一些北方的外来语还在源源不断地传入汉语。辽金时代北方汉人出现了“杂居番界,皆削顶垂发,以从其(契丹)俗。唯中衫稍异,以别番汉耳”的胡化特征,其语言出现的番化特征,也流传到了今天。

随着蒙古入侵的狂飙,一些来自蒙古语的制度和概念开始进入汉语,比如札萨克,怯薛,巴特尔,达鲁花赤,海子等等。在日常用语中,表示停车地点的“站”,最早来自蒙古语jam,意思是道路,后来指的是停车驻马的地方。此外,另一个现代汉语词汇“胡同”,疑似的起源是水井(因为民居依水而建)或者城镇(hot,浩特)。
伴随着清朝入关和定都北京,满语传入普通话的口语词汇也有不少,比如马虎,邋遢,麻利,背肐拉子,砢磣,大剌剌,搅裹,埋汰,啰嗦、妞妞,忽悠,旮旯等等,都和满语大有关系。

在发音上,今天北方方言里,特别是北京话的一个鲜明特征是“儿化音”,这一识别度很高的方言特征,伴随着官方文宣的强力推广,和相声小品等语言类节目传遍南北,其实这是北方汉语番化特征的遗留。汉语中的儿字后缀在南北朝和隋唐时代已经出现,比如“我是虏家儿,不解汉儿歌”,比如“蹀座吹长笛,愁杀行客儿”,只是当时的发音未必是后来的“er”,在唐代可能是“ie”;在辽金时代,儿化词缀得到了属于阿尔泰语系的契丹语和女真语的推波助澜,根据后世学者的复原,当时的北方,儿化词缀的音值已经是“er”,比如“ger”为“狗儿”,“dargan”为“牒尔葛”,“sigur”为“师古儿”等等。

体现金章宗时期北方汉语风貌的《西厢记诸宫调》
《董解元西厢记》中“马儿登程,坐车儿归舍;马儿往西行,坐车儿往东拽”的言语,已经和现在的儿化后缀用法有一定相似性了。
晚清民国:文化冲击背后的外来词系统性输入

到了明清乃至民国时期,随着新航路开辟,沿海通商还有鸦片战争,外来词先是以洋泾浜英语的形式,最后以更加系统的方式涌入汉语,并以非常强势的态度冲击汉语言的词汇库。除了直接来自于印欧语系的沙发,咖啡,加农炮,白兰地,三明治,布丁之外,还有表达制度和理念的德莫克拉西(democracy),赛因斯,伯理玺天德(president),奥林匹克,乌托邦等词汇,还有的词汇是描述科技概念的,从已经显得古早味的软件,镭射,菜单,快餐,白领,纳米,低碳,转基因,到相对较近的人工智能,抗氧化,虚拟现实,网际等等,都是从外语借来的外来词。
伴随着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和甲午战争的胜利,相当一部分的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方面的术语是从日语引入的,或者说是古汉语先借出给日语,然后以借形回流的方式传回汉语,就连使用者们都意识不到它们的外来语词源:

来自日语的现代汉语借形词
而且在这些外来语的影响下,现代汉语的词法和语法也在悄然间更加丰富,比如上古汉语和中古汉语中个别词汇有词缀的作用,比如老---老弟,老哥,老虎等等,但汉语整体缺乏词缀这种附加成分。

有的外来词进入汉语之后词缀化,带入了印欧语系的词法,成为了其他词汇的前缀或者后缀,并派生出了大量衍生词。比如bar-吧,在进入汉语后结合现代的语言环境和社会环境,派生出了 “吧娘、吧女、吧台、餐吧、茶吧、迪 吧、电脑酒吧、街吧、酒吧、泡吧、书吧、陶吧、玩吧、玩吧人、 网吧” 等词汇。类似的词缀化借词还有秀(show),啤(beer),模(model),车模,女模,嫩模,野模,都算是印欧语系借词演化成汉语词缀之后的派生词,而这些派生词又在当代的互联网语境中,被玩出了意味深长的引申义。
此外,还有的英语前缀和后缀直接带着自己的用法进入了现代汉语,丰富了现代汉语的表述:比如“化--生活化、法制化、内卷化”,“性:开放性、准确性、民族性”,“度:硬度、浓度、湿度、烈度 ”等等,这些已经不是词汇的借用,而是明显的语法借用了。

很多装X黑话已经给语言的基本属性--交流制造了困难

最后在前几年引发过争议,但是现在已经见怪不怪的字母词汇化,已经成为了当代内卷青年们的互联网生活的一部分:从历史已经比较悠久,被压在简汉互联网堆积层底层的Call机,CBD,RMB,OUT,HOLD住,WTO,G8,到最近的ARPU值,feed流,okr,kpi,push,follow,都是如此。
鲜为人知的外来语痕迹

其实在现代,外来语依旧不显山不露水的潜伏在汉语中。而且以改头换面的方式继续存在着。

牛街礼拜寺
首先是一些方言中存在各种时期累加积累的外来语。在现代汉语中,”猫腻”一词广为人知,意思是不太光明正大的勾当,其词源“猫儿腻”来自于老北京方言,猫在便溺后,会主动用沙土掩埋,这是长期野外生活形成的生存技巧,以防天敌循迹而来。但 “猫儿腻”原出波斯语,最早写作“马儿密”,本指“隐情”、“阴谋”,后来逐渐汉化,与之有类似来源的还有”鼠媚“,类似的高度本土化的外来语词汇,在北京牛街的回民群体中依旧沿用;

作为元朝著名的高加索外族部队,阿速军曾在中国留下了独特的地名痕迹,比如北京的地名阿苏台就是阿速军曾经的驻扎地,虽然这些阿兰人还有其他高加索军人的后代向全国各地流散,但是阿苏台这个地名像化石一样留在了当地;

而在开对外开放风气之先的广东,多士(toast),的士(taxi),士的(stick),士多(store),车厘子(cherries),士多啤梨(strawberry)都是粤语对英语词的音译;
今天湖北方言中的“造业“(ye发二声),其语境意义一般是“可怜”,但是这里的业的字面意思,其实已经如前文所提,来源于佛教,是业力(karma)的简称,所以造业的原意应该是遭受业报;
在西安,某些来自蒙语或者维语,阿拉伯语的词汇用法已经融入了当地汉语,比如西安回民称汉民为“探家”,这一词汇的词源其实在新疆:在《马可·波罗行纪》第53章中注道:“和阗即于阗,回人呼汉人为赫探,……和阗赫探之对音也”。

除了方言,还有一些鲜为人知,已经头顶光环的词汇,也是外来语。晚清和民国时代,中国南海的岛礁纷纷被西方人命名。为了在文化层面,政治层面彰显主权,1947年,南京国民政府对西方人命名的岛礁名称做了二次处理,对西方人的命名做了以音译为主,但是在用字上兼顾意译的翻译方式,必要时直接意译或者采用近似的汉语词汇翻译:著名的曾母暗沙,其英文为James Shoal;女神庙石(Flora Temple Reef)译为福禄寺礁;火十字礁(Fiery Cross Reef)译为永暑礁;傍俾滩(Bombay Shoal)改译为蓬勃暗沙;沙比礁(Subi Reef)改译为渚碧礁;符勒多儿礁(Vuladdore Reef)改译为玉琢礁;南恶礁(Mischief Reef)改译为美济礁。
这些翻译兼顾了外来语发音和汉字的字面意思,这也是近现代汉语处理外来词的主要规律。
语言借用的规律

英语中的外来词比例
语言学家萨丕尔曾说:“语言像文化一样,很少是自给自足的。”只要人们发现或者创造了新事物,那么他们就一定会想使用语言来描述或者指代这种事物,他们可能会采用其他民族的语言,这样外来语就进入了本民族的语言。“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对于个体和民族都是如此,受制于各自的自然环境,气候带和各种资源,大家很容易培育,驯化或者发明具有地域特色的动植物物种或者物品,并按照最简单朴素的原则为生活的地域命名,随着族群间的交流,其他民族首创的外来语也许会被其他民族采纳,如果两个族群地理位置过近,那么政治强势或者经济发达,或者文化先进的族群也许会对另一个民族进行语言置换,这样的过程,都会出现大量外来语进入一种语言的情况。随着秦军南征百越,还有之后历朝汉人对岭南的开发,百越的词汇在粤语中有大量的底层残留;东北地区来源于各少数民族语言的地名被转记为汉字,也是外来语在汉语中的底层残留。


洋泾浜英语其实比互联网黑话中的英语借词更符合交流本质
所以外来语在各个语言中都存在,世界上的各种活语言,都吸收了大量的外来词汇,绝对纯净的语言,就像“纯种汉人”,“纯种突厥人”那样经不起推敲。更何况,语言除了语汇,还有语音和语法两个维度,三个维度的互动才决定了一种语言的最终形态,所以仅因为采用外来词,就称之为“语言污染”实在是神经过敏。

马氏文通
更何况,语言间在语法和发音层面的相互影响,对民族习惯的影响更加潜移默化。比如西北某些地区的汉语方言呈现出“三声调”,而不是四声调的特征,三声调汉语方言点的分布,和阿尔泰语系语言的分布关系密切,这一特征基本上可以确定来自于阿尔泰语系诸语言的影响;而汉语言的第一部系统性的语法著作,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汉语语法著作《马氏文通》,就是仿照拉丁语语法对汉语语法进行的规律总结,这其实是近现代,印欧语系语法对汉语强势影响的一个缩影。

张骞和班超等人没有记错古代西域地名的读音。他们带回的地名,体现的是那些汉字的上古读法,只能证明上古汉语和现代汉语读音差异巨大
此外,从前述汉语外来词的发音来看,历史时期进入汉语的外来词汇反应的,是当时那些汉字的古代读音,和现代汉语的发音不一定能完全对上。这也证明了一点:上古、中古、近代和现代汉语的发音前后变化巨大,语言每时每刻都在发生着微妙的变化。可以说某地方言可以保留某一历史时期的某些词汇用法,韵母或者特殊声调,但硬要说某种方言就是中古汉语或上古汉语,那就是贻笑大方。
,免责声明:本文仅代表文章作者的个人观点,与本站无关。其原创性、真实性以及文中陈述文字和内容未经本站证实,对本文以及其中全部或者部分内容文字的真实性、完整性和原创性本站不作任何保证或承诺,请读者仅作参考,并自行核实相关内容。文章投诉邮箱:anhduc.ph@yahoo.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