迎来秋冬大雪(夜雨北走大雪入梦来)

大雪入梦来
北走
冬天,我总做一个梦,梦里下着大雪,白茫茫的大雪。
那真是鹅毛大雪,天庭敞开大门,慷慨地向大地源源不断地倾倒白色的精灵。她们前赴后继,先到达的瞬间消失。经过无数奋不顾身的铺垫,先是草垛上、屋面上、道路两旁枯草上慢慢呈现白色,然后铺向所有可以歇脚的地方,白色逐渐隐藏了大地所有的秘密。田野里的小麦、油菜躲藏在积雪下酣然沉睡。大雪甚至覆盖了田埂上的沟渠,我不小心一脚踩入,跌入干枯的沟渠,在梦里忍不住自己笑起来,索性在雪地里躺一会再爬起来。
小村旁是条河,雪一朵追一朵,无数朵降落水面,悄无声息地成为了水,她们称之为雪的生命如此短暂。船泊河岸,雪落船头、船尾、船舱,便有了一船积雪。麻雀落在船上找食,留下几许凌乱的脚印。满载积雪的船在我梦中静默无语。
梦中,雪压枯枝,突然断了,枯枝断裂的声音和积雪落地的声音轻微却清晰。竹子上一大团积雪掉落地面,噗嗤声里我看见了飞扬的细碎雪尘相随,跟着有受惊的飞鸟扑棱着翅膀飞向另一处枝头。明瓦窗盖了层厚厚的白雪,如同盖在了自己的被子之上。我甚至闻到了年的味道,飘雪里裹挟着种种香味。人们在大雪中置办年货,街上人人喜气洋洋,肩背手提,相互打着招呼。纷纷扬扬的雪花中,人们迎接着一个新年。
悄无声息的大雪用自己的身躯占领了整个原野村庄,无边无际的白。母亲已铲出家到河滩头的一条小道。我穿上套鞋,戴上父亲泛黄宽大的雷锋帽,跑出门,故意往雪厚的地方踩,感受着积雪的蓬松柔软,踩到底,咯吱一声,拔出来,又往前轻轻踩下去,回头看身后一个个脚窟窿,有种莫名的兴奋。村子里的小伙伴们都出来了,长着冻疮,肿得像发酵馒头的小手,丝毫没有影响将雪球捏结实。你来我往,雪球在空中飞舞,砸在身上,飞散开来。光滑平整的雪被,很快凌乱不堪,无数落雪创造的这件艺术品,就这样轻易被破坏掉了。兴奋中,土根将两条进进出出忙碌不堪的黄浓鼻涕,擤在了雪白的积雪上,这种对白雪的亵渎行为让我颇气恼,将更多的雪球对着他砸过去。在家门口,我和哥哥堆了一座雪桥,桥孔、台阶俱全,我在上面走过来走过去。这座属于冬天的雪桥一直在梦里,从来没有融化掉。
梦见去镇上上学,大雪连着下了几天,每天去上学时,总有许多人在街上铲积雪,为行路者挖出一条道路来。学校门前那条叫做人民路的两侧,雪堆得比我人还高。教室是老旧的平房,有天桥跨过人民路,对面是三层楼的教学楼。我坐第一排,看着操场上厚厚的积雪泛着冰冷的雪光,看着天桥栏杆上拱起的积雪,竟恍惚起来,梦里做着梦,觉得这分明是座通往童话世界的桥,老师讲课的声音遥远得似乎越过千山万水而来。雪化的时候,屋面滴下的雪水结成了冰凌,它们整齐地挂在街上两侧屋檐下,长短不一,闪着寒光,尖角如剑指大地。我行走在南方小镇的冰天雪地中,走啊,走啊,走不到尽头。
梦见下大雪,跟着母亲搭邻居家的船,去收购站卖削好的荸荠。船在吴淞江里慢悠悠前行,数不清的雪花从灰色苍茫的天空源源不断地飘落下来,落在江面,消失得无声无息。落在我眼睫毛上,眨巴几下,没了,冰冷的空寂和莫名的欢欣交织袭来。船到收购站,船头积了一层雪。收购站排着长长的队伍,人们的脚边是红的、白的、黑的各种颜色的桶,桶里都是满满的晶莹雪白的荸荠,雪落桶里,分不清哪个更白。大雪纷飞里队伍慢慢往前挪动,后面的人不时引颈张望。终于轮到了,过秤,结算,拿钱。我们家二分地荸荠卖了七十多元,母亲低头笑眯眯地数了好几遍,说,你们明年的学费有了。
梦见姐姐出嫁那天,大雪。姐姐姐夫都是老师,镇上还没有房子,各自住教师宿舍。结婚完全是水乡传统婚礼,用船,从一个村庄,吹拉弹唱迎娶到另一个村庄。大雪中,船只突突的马达声和欢快的奏乐声飘散在孤寂清冷的江面,少年的我,心中有种雪白的忧伤,亲爱的姐姐成了别人的妻子。
梦见十多年前的一个凌晨,妻为谋生出门坐车,我在北窗目送她出小区。下了一夜大雪,目之所及,白雪皑皑。寒气逼人,透过玻璃窗直达全身,我不禁打了个寒战。万籁俱寂,昏黄的路灯洒在积雪之上,泛着温暖的冰冷。积雪里,妻为生活奔波的脚印从来没有这么清晰过,这些雪白干净的脚印在她身后延伸,直到消失在拐角处。
梦里串连着一场又一场大雪。梦醒来,已不知道哪个是梦境,哪个是真实,一切过往都成为了梦境。江南已无大雪,在冬夜的梦里却一场接一场地下,我独自一人站在白茫茫的大地上,看着一块巨大的白色幕布,放映着过往的一场又一场大雪。
(作者简介:陈宏宇,笔名北走,苏州市作协会员,广电技术高级技师,发表散文随笔120余篇及少量诗歌。)
编辑:罗雨欣
责编:陈泰湧
审核:冯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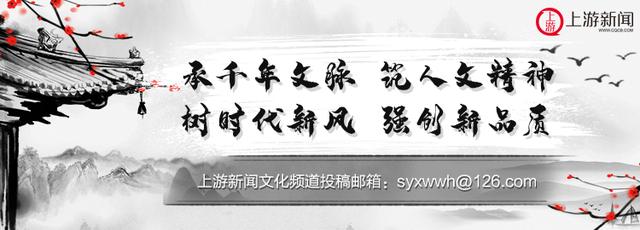
免责声明:本文仅代表文章作者的个人观点,与本站无关。其原创性、真实性以及文中陈述文字和内容未经本站证实,对本文以及其中全部或者部分内容文字的真实性、完整性和原创性本站不作任何保证或承诺,请读者仅作参考,并自行核实相关内容。文章投诉邮箱:anhduc.ph@yahoo.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