尧在位期间第一次派去治水的人(帝尧发祥于山西长子县)
帝尧向来称为“陶唐氏”,无论怎样解释,都不能回避这样一个问题,即何以在“唐”的前面加“陶”字?整个平阳地区无陶地之名目。古人大多数认为尧先居住于陶,后封于唐,故曰陶唐。那么,这个陶在什么地方呢?
关于尧的出生地、发祥地、兴旺地、死后的葬地,古籍所载涉及的地方计有今山东、河南、河北三省不下十数处。怎样来确定某处的传说更具有可靠性呢?我以为从古人“鸟飞反故乡,狐死必首丘”的习惯看(这种习惯是从农业民族对旧土的留恋而来),尧之葬地与其生地必不相离。《竹书纪年》卷上言:“(尧)八十九年作游宫於陶,九十年帝游居于陶……一百年帝陟于陶。”足见尧对陶这个地方深厚的情感,皇甫谧曰“帝崩曰陟”,就是说尧最后是死在陶这个地方。这就启发我们,在讨论具体问题之前,我们必须有这样的逻辑认识:关于尧生于丹陵居于陶、兴于唐、死后葬于谷(穀)林,这些说法,必须作统一的综合考察,不能单一地拿某地的一种传说作为尧或丹朱的“封地”。比如,尧的诞生地与其发祥地相去必不甚远,他的发祥地与其兴旺地亦应有一定的联系—我们应该考虑到古代一个部族迁移的艰难性,尤其是农业部落的转移,多年垦殖的土地绝不会轻易地放弃这就是中国古人“安土重迁”的根本原因,何况在远古农业初兴之时。而考察尧的封地,也应该把关键的地名联系起来丹、丹陵(或丹岭)、丹水(或丹渊),这些条件缺一不可。尧让丹朱“出就丹”,最大的可能就是把他安置在自己的发祥地。生地、葬地、元子(或长子)之封地,这三者统一起来,才能确认某地是尧的发样地和葬地。在山东、河南、河北无论什么地方都不能把三者统一起来,只有山西的长子县才是具备这三点一致的地方。
首先,长子处于丹陵这个尧的诞生地的范围之内。
其次,这里有陶水。
《欽定大清一统志》卷一百三载:“陶水,源出长治县南六十里雄山,西北流至长子县界,人漳水,一謂之尧水。”《水经注》:“淘水,南出南陶,北流至长子城东,西转经其城北,東注於漳水。”《魏书·地形志》:“长子县羊头山下穀关,有泉北流至陶鄉,名陶水,合羊头山水,北流入浊漳。”
《大清一统志》所引《水经注》和《魏书地形志》的两条材料所传达的信息非常重要:一是长子有水名陶水,清代雍正年间所修《山西通志》卷十九于“陶水“下注云:“当即尧水。”《魏书》的作者魏收与《水经注》的作者郦道元属同时代人,且《水经注》说得十分详细,则“陶乡”肯定在长子城南。但河流的走向古今往往有比较大的变化,有些小的河流甚至完全干涸。所以,以河流而论,北魏时的地形与今之地形相去甚远,即清代雍正年间所修《山西通志》也与今之地形有较大的差异。如《通志》卷十九《山川三》所叙述的陶清河的流经情况,与现在的情形就极为不同:“淘清河自壶关南界入县境,经高河誧,由西南二十里杨暴村流至西北暴河头入漳水。”杨暴村今属长治市,而陶清河入浊漳河则今在长子东南李末村附近,杨暴村远在南李末村北至少三公里。用这个比率看,《水经注》之所谓陶,《魏书·地形志》之所谓陶乡,就应该是今长子县东末村乡之陶唐村,大约在今长子城东北三公里处。这种情形也并不奇怪,随着自然地貌的改变,还有长子、长治两县县治的变迁,这些说法已经很难用现在的长子县县城的具体位置来描述古代村镇的位置了。
发源于潜山(今之尧庙山)的尧水和这条陶水,已经在现在的长子县地图上找不到了,但旧迹犹存。1998年新修的县志上,还能找到尧水及其发源的潜山(尧庙山)的记载,而陶水则渺无踪迹。今修县志也无只字提及。当然,《山西通志》作者说陶水当即尧水,与发源于长治雄山的陶水无关—那条河大约也已经干涸。而这个陶唐村在新修的县志上解释村名的来历时说:“相传古时此地生产陶器,汤王曾在此巡游避暑数日,故名陶汤,后改为陶唐。”这个传说有极重的后代阐释意味,且陶和汤是不能联系在一起的。尧在前,汤在后,古人说“新鬼大,故鬼小”,传说不断地添加新的朝代和新的“圣王”的故事,是可以理解的。但这个传说中所谓“生产陶器”是真,这个生产陶器的始祖就是炎帝神农氏。以长子、高平、长治三县交界处的羊头山为中心的关于炎帝神农氏的传说,说明这一带是中华农业文明的发祥地,也应该是陶器最初的发明地。那么,尧这位“神农氏之后”,当然要继承炎帝的事业——继续发展农业和陶器业,并且也因此兴旺起来,是合情合理的。
二是陶水发源于潜山,这个潜山上有尧庙。这个尧庙始建于何时,已不可考。但它肯定是非常古老的,不但古老,而且是天下数不胜数的尧庙中最重要的尧庙——《魏书·地形志》曰:“乐阳有尧庙令,长子有乐阳城。”这个乐阳,可能即今长子县西十多公里的岳阳村。但岳阳并无尧庙,应为《魏书》作者误记。《山西通志》卷一百五十六又载:“帝尧庙在西南十五里潛山上,金季毁于兵。元至元暨至正间增葺,明成化四年、万历六年暨国朝康熙七年,胥重葺。岁四月二十八日,有司致祭。”就是说,天下所有的尧庙都没有像长子潜山上的尧庙那样,国家(中央政府而非地方政府)专门设立“尧庙令”,以管理尧庙。这难道是偶然的吗?这个尧庙为什么这般重要呢?而且重要到超过了平阳(今临汾市)的尧庙?如果没有特殊的意义,这是不可想象的。所谓特殊的意义,就是这里不但属于尧的出生地丹陵地区,也是尧的发祥地,并且是他生命最终的归宿—尧的葬地。

新修县志说“潜山”是“俗称”,恰恰相反,尧庙山”才是俗称,而“潜山”应该是当初的正名。为什么叫潜山?《山海经·北次二经》云:“西望大泽,后稷所潜也。”什么叫“潜”?郭璞注臼:“后稷生而灵知,及其终,化形遁此泽而为之神,亦犹傅说骑箕尾也。”“终”、“化形”、“为神”、“骑箕尾”,都是古代对死亡的委婉说法。所以“潜”就是藏,也就是葬,潜山上之所以有尧庙,就是指示着尧的葬身之处,也昭示着尧已“化形”而为神。《路史》卷三十六云:“成阳有尧冢、灵台,而此碑(《灵台碑》)云‘尧母葬兹,欲人莫知,名曰灵台。’”这种解释太神秘了。上古之时人死而堙葬,理由极简单,就是不想让人看见尸体而已,以巫术的解释也不过是让灵魂归于地下。但“不欲人知之”,却使后人无法知道尧的确切葬地了—也许当初具有神秘的意义,长子人虽知之而不敢言之也。遂至长子的这个本来应该著名的小村子也就被后人逐渐遗忘。然而这里的神秘和那至高无上的地位,却仍然留在人们非同寻常对待它的态度中,留在那非同寻的祭祀之礼中。
然而,为什么“不欲人知”呢?这让我们想起明人陈耀文撰《天中记》卷十三几句话:“故尧城在濮洲鄄城县東北十五里。《竹書》云‘昔尧末德衰,为舜所囚也’。”
明人王世贞于《弇州四部稿》卷一百五十九也说到这个问题:“太白诗有云:‘尧幽囚,舜野死。按《续述征记》云:‘小城阳城在阳城西南半里许,俗云囚尧城。’……《竹书》云:‘昔尧末德衰,为舜所囚也。’……又《述异记》朝歌有狱台,相传为禹囚舜之宫。《韩非子》云:‘舜逼尧,禹逼舜。’盖自昔有此种议论矣。”
两人所记也是传说,按历史发展逻辑讲也不是完全不可能,同时也给后代以武力方式更替朝代找到更为原始也更为权威的理由。“德衰”——他老了,精力和能力都自然衰退,但还是坐在领导的位置上,代替者很可能采取强硬的手段把他拉下来,要使众多的部落小首领服从新一任首领,也可以编造出他的前任是把帝位禅让给他的。为了不让这个老首长乱说乱动,只能把他囚禁起来,或者干脆让他“永远消失”。这种事情当然“欲人莫知”了。就是真的禅让了,老首领既然是禅让,就要考虑到对新首领的影响,也该自觉地消除影响,自动地潜藏”起来。到什么地方去呢?当然到最安全的地方,那就是自己的发祥地。从这个角度讲,长子的潜山为尧晚年的潜藏之地,也还是成立的。所以,“不欲人知”,并不是尧本人或尧的后代“不欲人知”,而是后来的掌权者“不欲人知”——尽快地消除前任首领在人们心目中的影响,以便尽快树立新领导的威信。
当然,其结果就是关于帝尧的陵墓在什么地方,就给后代留下了诸多猜测和想象的余地。所以,古籍所载帝尧的葬地也很多,光山东就有三处。各地的说法也都有其理由,也都有不能完全肯定的遗憾。如《山东通志》卷三十五载明·王道《濮州帝尧陵祠碑》文云:“帝尧陵见于山东郡邑者凡三,而史牒事证的然可据者,惟濮之竹林寺为最著。盖《史记》注既以为尧葬济阴成阳矣,吕不韦又云尧葬谷(穀)林,皇甫谧谓谷(穀)林即成阳也。《汉·地志》:济阴郡成阳县有尧塚,雷泽在其西北。杜佑《通典》:濮阳雷泽县即汉成阳。而郭缘生《述征記》云:尧塚在雷泽东南。其说皆与《史記》合,则尧陵当在濮境无疑。”可是这说法并非司马迁《史记》正文所言,而是裴骃《集解》引诸书所言,而诸书所言各异。如刘向言“尧葬济阴”,《吕氏春秋》言“尧葬谷(穀)林”,并没说谷(穀)林在什么地方。皇甫谧说“谷(穀)林即城阳。尧都平阳,于诗为唐国。”也没说城阳在什么地方。仔细体会皇甫谧的意思,他所说的城阳应该在平阳一带。而杜佑则认为是濮阳雷泽县。那么,王道凭什么理由就认定“竹林寺本穀林遗址,其為尧陵也益无疑”呢?
事有凑巧,就在长子县潜山西不远处有一村子名为“城阳”或为“成阳”。今不知其村名之来历。焉知尧所葬之成阳或城阳非长子之城阳村也?前引《今本竹书纪年》所载帝尧对陶这个地方的眷恋,已说明长子绝不是一般的地方,定是他的起家之处。王国维《疏证》又引《史记·货殖传》:“昔尧作游(于)成阳。”如淳注曰:“作,起也。成阳,在定陶。”既然是“作于”成阳,那就不可能是山东济阴之成阳了—任何一部古籍都不曾说帝尧从山东兴起,而且这里也没有与丹有关的任何地名。更为重要的是,司马迁的这个记载把陶和成阳自然而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了:这两个地名也可以说本来是一个地方,就是长子的潜山左右,一在潜山之西(城阳),在潜山之东(陶乡),相距不过数里而已。
这座在长子县南,值得我们特别关注的潜山(尧庙山),其北有村曰“西尧”,其东有村日“尧神沟”。既有西尧,当有东尧或尧村,而今从《长子县志》新绘制的地图上看不见尧村的踪迹。尧、陶古音同,所以陶水也叫尧水,平陶改为平遥。那么,我们还可以作这样的推测:《魏书·地形志》所载陶水即尧水所经之陶乡即尧乡,应该就在西尧之东,其村人后来不知什么原因全部迁移到了今长子东面的陶唐村,而原地遂消失,只有西尧仍存。
我们再往上联系炎帝神农氏尝百谷(穀)、始造陶器两件关键的历史记载,作一下综合思考:沁源县古称谷(穀)远县,长治有百谷(穀)山,这一带到处都有与炎帝神农氏尝百谷(穀)的传说。高平县与长子县交界处的羊头山恰是神农氏的发祥之地已经为古今学术界确认,而百谷(穀)之成为食物,是离不开器皿的所以,农业生产与制造陶器就必然是相伴相随的。既然农业生产的发祥地在晋东南,那么,晋东南的高平、长子、长治这一带,起码是最初生产陶器的地方之一,则陶乡(尧乡)作为地名也就绝非偶然。帝尧的先进技术也应该在于制造陶器和农业生产,这就应该是尧能够兴旺发达并吸引众多部落归附的理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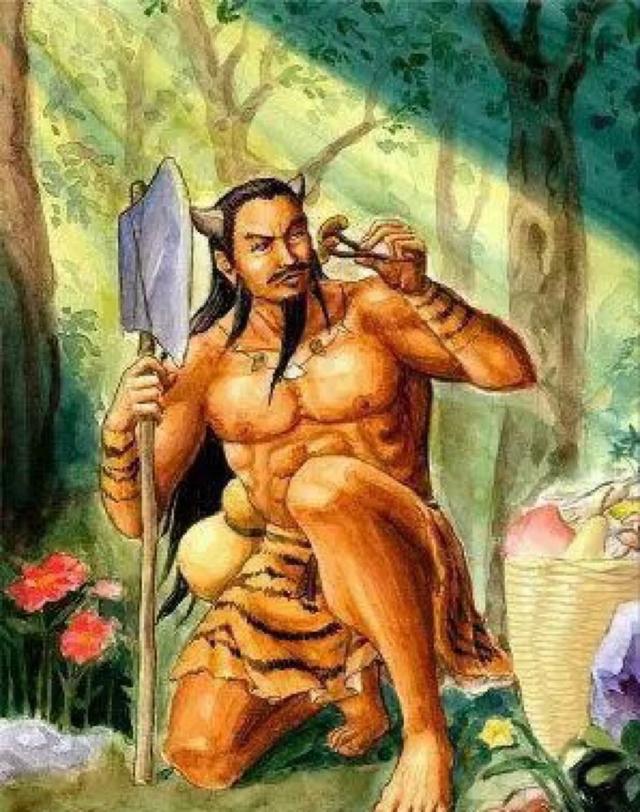
还有一点也值得我们注意:沿潜山即磨盘山西麓,有一条河名曰苏里河,有村庄名曰苏村。今新修县志不知村名所由来。按《路史》卷七云:“赫苏氏是为赫胥。九洛泰定,爰脫曬(按:原误为灑)于潛山。”这位赫苏氏把辞掉帝位看得像脱掉(扔掉)双破鞋一般,这传说也加入了后代隐士一类人的高洁出世之想象,显然是后代对禅让制的一种阐释。其中说到的潜山,就是长子县南的潜山。原注:“胥,蘇也。传谓赫然之德,为人胥附而号之也。又以为即炎帝,妄矣。”这个“又以为”,作者以为其“妄”,我倒以为并不“妄”。因为把潜山与炎帝直接联系起来的地方就是长子的潜山——这里离炎帝之发祥地羊头山近在咫尺。这样,我们就可以理解苏村、苏里河的由来了——原本这是赫苏氏“脱镅”的地方。这位脫于潛山”的部族首领(帝王),作出了“九洛泰(大)定”的伟大成绩,那也是因为发明了人类赖以稳定生活的农业生产,而具备这样功德的人,遍数中国上古帝王,非炎帝莫属。先进的生产经验是需要代代继承和积累的,说尧是炎帝的后代,从继承炎帝的生产和生活方式的角度讲,完全正确。
接着的问题就是所谓“尧葬于谷(穀)林”。谷林在什么地方?《路史》卷三十六广征博引,以为是山东济阴之成阳。但所引先秦著作已有巨大分歧,《墨子》、《吕氏春秋》、《山海经》所言各不同。尧是继承了炎帝以农业为主的生产和生活方式的一代领袖,这才是晋东南地区长久地流传着神农氏故事的原因。前文说过,这里以谷(穀)命名的地方也特别多。羊头山的南坡为高平县,其北坡为长子县,《山西通志》卷十九引《魏书·地形志》:“羊头山下神农泉北有穀关,即神农得嘉穀处,山下有穀泉。”引章怀注:“羊頭山在上党郡穀远县。”这个穀远县即今长子县西北的沁源县,这是晋东南的另一座羊头山。又引《金志》:“(长子县)有羊頭山,發鳩山,堯水。”也就是在这座羊头山的北坡有神农氏得嘉古(穀)处的谷(穀)关。长治县有百穀山,在县东北十三里,昔神农尝百穀于此;有百穀泉,在百穀山神农庙前(《山西通志》卷十九),山下有百穀寺(《山西通志》卷一百六十九);泽州府(今晋城市)高平县有穀速山,在县东北二十里(《山西通志》卷二十三),又长子县今有谷村乡,疑当作“穀村”……·那么,所谓“谷(穀)林”,就不是一个具体的地点,而是一个众多的以谷(穀)命名的地区(林,众多之义)。这个地区除了以晋东南羊头山为中心的长子高平、长治、陵川一带以外,别无他求。
由此我们可以解释尧为什么称为陶唐氏,也能绘出尧的发展路线:尧开始居住在长子的陶乡,并以制陶和农业生产而闻名遐迩,远近部落纷纷归附。然后沿着漳水向西,越过发鸠之山,到了翼城,改号曰唐,再发展壮大,占据了整个平阳地区。然后沿着汾河北上,占据了太原地区。同时向南占据了整个“河”地区。遂成为空前的一代众多部落的伟大领袖。
说到这里,还要引一段《山西通志》卷十九记载的又一传说:“(长子县)庆云山,在县东南五十里,递高一里半,南至高平界一里,连紫云山。相传尧時五色庆云見此。”可以推想,当初尧在长子陶乡之时,真是一派风调雨顺农业兴旺的景象。
至此,我们可以回到本题:长子既然与尧有这么重要的关系,则帝尧把他的大儿子封在长子这个地方,也就完全是情理中事。
万物简史作者 李蹊
,免责声明:本文仅代表文章作者的个人观点,与本站无关。其原创性、真实性以及文中陈述文字和内容未经本站证实,对本文以及其中全部或者部分内容文字的真实性、完整性和原创性本站不作任何保证或承诺,请读者仅作参考,并自行核实相关内容。文章投诉邮箱:anhduc.ph@yahoo.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