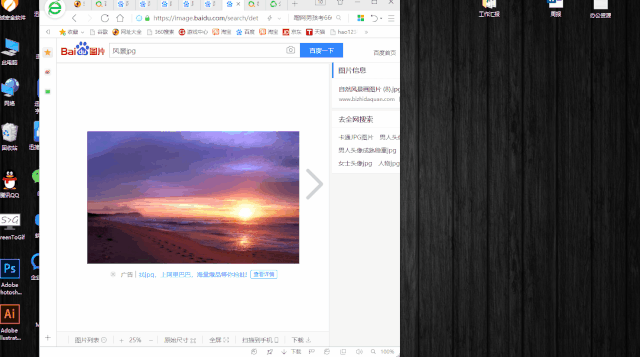原来15年前我们就在谋划去月球(纪录片月球时代白日梦)
布莱特·摩根(Brett Morgen)长达140分钟的纪录片《月球时代白日梦》(Moonage Daydream)传递了这样一个信息:我们都是大卫·鲍伊(David Bowie)的粉丝。鲍伊死后,这位导演拿到进入鲍伊所有素材的权限,在浩如烟海的现场影像、画作、电影、影像实验、幕后花絮及采访中漫游。摩根以穷尽预算的方式工作,先用五年时间浏览素材,其中就有粉丝们心心念念的“独角兽”:1978年Stage Tour的Earls Court场,内容主要来自鲍伊1970年代后期的柏林专辑《Heroes》《Low》。“五台摄像机,两晚,35毫米胶片,24声道音频,或许是大卫·鲍伊最棒的现场影像。”这次巡演被视作失落的圣杯,资料从未进入过公众视野。其它的著名现场还有伦敦Hammersmith Odeon的《Spiders from Mars》巡演最后一场,1974年《Soul Tour》的水牛城和华盛顿场。
因为有这些珍贵之物的存在,布莱特·摩根尽可能看得仔细,惟恐遗漏。因为团队在前期超支太多,后期时摩根只能解散剪辑团队,自己成了唯一的剪辑师。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他每天从上午八点工作至午夜,独自一人坐在黑暗的剪辑室,还差点死掉。大卫·鲍伊死后一年,布莱特·摩根心脏病发作,心电图拉直三分钟,当时他53岁。
因为这次不同寻常的经历,当他康复后回到那个房间,觉得自己接收到大卫·鲍伊的精神启示。布莱特·摩根从眼花缭乱的“大卫·鲍伊冒险记”中得到鼓舞,日夜沉浸其中,令他自己也想从病床上飞升,过从心所至的生活。
他从立项开始就不准备拍一部传统的、按时间顺序发展的传记片。闯过鬼门关后,他更加确定影片的方向。他要使电影如同一面完全遵从直觉,不惜混乱的镜子,让观众在漫游中看见灵性的大卫·鲍伊和他们自己。

这部电影被摩根定义为“主题公园”“大卫·鲍伊的短句集”,运用IMAX为观众提供身临其境的体验。大卫·鲍伊本人将担任旁白、演员、心理治疗师和哲学家的角色,向观众传递生命稍纵即逝的真相,并许以新生的承诺。“我想让不同时期的大卫·鲍伊之间产生对话。“前一分钟他还在1983年,下一分钟就来到十年前,坐在摄像机前接受英国脱口秀主持人罗素·哈提(Russell Harty)的采访。“成名前你在想什么,有没有想过,哦上帝,总有一天我会走到镁光灯下?”“我从来没有向上帝求告过什么。一切主动权在我。”
成片致敬了大卫·鲍伊眼花缭乱的一生。除了从资料库里挖出来的素材,摩根还添加了动画、特殊音效和鲍伊本人最爱的电影片段(包括《大都会》《诺斯费拉图》)。
他必须绞尽脑汁,使观众“感受到大卫·鲍伊”。鲍伊在药物渗透下创作《Station to Station》,摩根苦于找不到相应的注脚来重现当时情境。如何用电影语言表达这种无声的状态?他心生一计,决定不在素材库里寻找,而是使用了肯尼斯·安格尔(Kenneth Anger)创造的声音碎片来制造通感。
大卫·鲍伊所到之处会触发一种奇特的现象。七十年代的演出现场展示了这种奇迹:现场的年轻人们好像个个都变成了他。他们共享相似的面孔和神情,专注、出神、漂亮、目光远至宇宙星空。鲍伊视自己为一块黑幕,反映着观众的渴望与恐惧。他在电影里说:“艺术家是人类想象的一小块碎片。我们是原始的假先知。我们是神。”他的目的是潜入人们的意识中,改变他们对自身的认知。为此,他不惜“伪装出一些实际上我没有的情感实质。”

鲍伊曾花很长时间对镜研究、练习表情。脸和声音、身体一样,是他重要的表达媒介,因此大卫·鲍伊永远经得起近镜头的考验。摩根了解这一点,大量的特写镜头被剪入影片,包括《Life on Mars》MV中那套著名的冰蓝色西装。鲍伊涂同色眼影,红发,几近透明。那支MV的导演米克·洛克(Mick Rock)说:“这件西装鲍伊一生只穿过这一次。”他的特殊能力即在于,能够让这几分钟的亮相融入全世界的幻想中。
随着工作的进行,黑暗和色彩开始对布莱特·摩根产生影响——他获得了一些神秘的体验。搞创作的人很容易发现一些细微的巧合,抓住它们,并视之为游戏和启示。摩根正在观看《The Hearts Filthy Lesson》音乐录影带,画面中的鲍伊在舞台上画画、跳舞。摩根有边工作边听音乐的习惯,这时恰巧播放至菲利普·格拉斯(Phillip Glass)的交响乐段。屏幕上,大卫·鲍伊仿佛也听见了音乐,动作随之发生变化。这段菲利普·格拉斯的音乐后来被剪进了成片。摩根不得不迷信地认为:“是大卫·鲍伊自己选择了这段音乐,我甚至感觉不到是自己剪进去的。“
他被动或主动地为电影增添神秘色彩,以契合大卫·鲍伊其人。纪录片《又贱又快又失控》(Fast, Cheap & Out of Control, 1997)是摩根在剪辑时的灵魂导师。他欣赏这部影片的跳脱与诗意,以及在数段不同的混乱人生中让秩序凸显的功力。那部电影中包裹着半透明的梦境般的物质,呈半流质状态,拥有自发成型的潜力。
落到实处,为了追求这种质感,摩根在每晚夜色浓重,眠梦于世界游荡时起床工作。他把这段时间视为魔术时光。正是在这段黑夜里,他为影片找到了恰当的结尾——《Memory of a Free Festival》《Station to Station》的混剪。

电影的声音团队主要由《波西米亚狂想曲》(Bohemian Rhapsody)的奥斯卡得主小组组成。他们按照摩根的要求,让声音从四面八方传出。他想让观众用各种感官感觉到,而不仅仅是听见大卫·鲍伊。
这样做的灵感来自摩根发现的一段采访素材。那天关麦以后,大卫·鲍伊开始即兴吐槽法西斯主义。他喋喋不休,情绪高涨。一时间,工作室里到处都充满情绪的标点。声音引发画面的想象,那段片子摩根剪得很顺,他毫不犹豫地决定该使用什么画面。
2018年工作走到窄径时,摩根决定追随传主的一段旅途,飞到新墨西哥州的阿尔布开克后搭乘火车返回洛杉矶。这样做的依据是:摩根认为,鲍伊最好的音乐写于1970年代早期穿越美国西南部的火车上。
《Moonage Daydream》罕有涉及大卫·鲍伊的私生活。它展示公共层面可见的鲍伊,抖落变色龙的百变外表。鲍伊和妻子伊曼(Iman)共同生活之前的私生活是个谜,那就让它继续成谜。他愿意淡化“生活”的一面,对婚前生活仅以“作为艺术家,在伦敦、洛杉矶、柏林存在着”概括。似乎大卫·鲍伊真的是一个外星人,而生活是一个洞。他不得不常常旅行,用“艺术”来填满它,好让他尽量融入地球人之间而显得不那么特殊。
布莱特·摩根顺应其意,没有去做“揭露真实大卫·鲍伊”的尝试。他尊重鲍伊的自我描述:“我是收集者,收集不同的人性。”试图接近大卫·鲍伊的前作有:《David Bowie: Five Years 》(2013)、《The Last Five Years》(2017)、《Finding Fame 》(2019)。更早的还有1975年的《Bowie in Cracked Actor 》和《 Ricochet》(1984) 。
1983年的《Let's Dance》把大卫·鲍伊推上全球流行巨星的位置前夕,他在采访中表明了心志:“我不想做太浓烈的东西。现在,我只想给人带去快乐。”对那时的大卫·鲍伊来说,做阿拉丁灯神和Ziggy差不多,都是经过设计后问世的角色。他即将进入主流的视野,接受另一项挑战,从Live House跃入十万人体育馆。

摩根和鲍伊2007年见过一面,不善。鲍伊直言不喜欢摩根当年的新作《芝加哥10》(Chicago 10),摩根也很坦率地告诉他:“你1983年以后的东西我都不太能欣赏。”大卫·鲍伊用卡通和电视里的人物才会说的“Touché”表达心情,二人算是不欢而散。
十五年后,布莱特·摩根可以欣赏1983年以后的大卫·鲍伊了。他爱上了《Outside》(1995),《Earthling》(1997)和《Heathen》(2002)。“向人们介绍鲍伊中晚期的作品成了这部电影的使命之一。”但当他想把这些作品放进影片中,摩根仍然失败了。不是节奏不对,就是氛围不符。最终他放弃努力,转了一圈后又回到开场曲《Hallo Spaceboy》和那个同名现场。
“万物都是垃圾。垃圾皆很美丽。”跟着《月球时代白日梦》进入人类性格之旅,由大卫·鲍伊领路。你会发现,他用百变的形象保持自我,寻找身心灵的平衡。那么多的脸孔,存在于无数光辉片段中的大卫·鲍伊,仅此一人。
,免责声明:本文仅代表文章作者的个人观点,与本站无关。其原创性、真实性以及文中陈述文字和内容未经本站证实,对本文以及其中全部或者部分内容文字的真实性、完整性和原创性本站不作任何保证或承诺,请读者仅作参考,并自行核实相关内容。文章投诉邮箱:anhduc.ph@yahoo.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