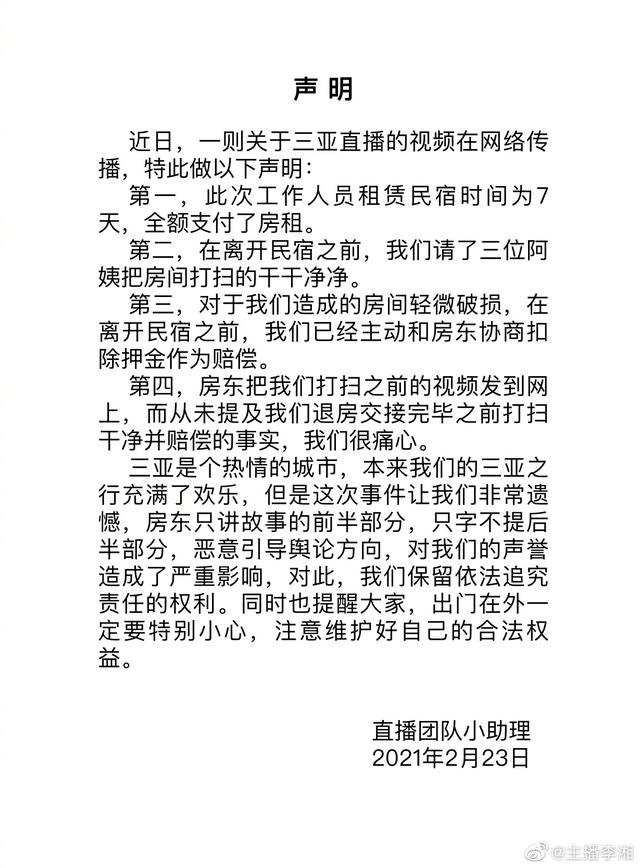人生第一命(领生活之命)
来源:人民网-人民日报海外版
null


乔 叶 郭红松绘




从“泡村”和“跑村”而来
我的长篇新作《宝水》(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讲的是太行山深处一个叫宝水的村子,如何从传统乡村转变为以文旅为特色的新型乡村,入选了中国作协“新时代文学攀登计划”首批名单。有人问我为什么会想到创作一部反映新时代新山乡、美丽乡村、乡村振兴的作品。前些天开研讨会时,评论家李国平说:《宝水》的诞生是领生活之命、文学之命、寻找文学新资源之命。这样的理解非常精准。我创作这部作品的个人自觉与时代文学命题的邂逅,如同山间溪流汇入江河,某种意义上造就了作品的际遇。对于这种际遇,我从来不追逐。但既已邂逅,也不回避。
《宝水》从动念到写成用了七八年时间,事实上可能更久。之所以用这么长时间,可能还是因为我太笨。写一部与老家和乡村有关的小说,对我而言非常难。
难处很多,难以备述,难的类型也有多种。写作前的资料准备和驻村体察,写作时的感性沉浸和理性审视,初稿完成后的大局调整和细部精修……还有在前辈的乡村叙事传统中如何确立自己的坐标,这都是难点。可以说,纵也是难,横也是难,朝里是难,朝外也是难。还真不好比出一个最大的。或者说,每一个都是最大的。因为克服不了这一个,可能就没办法往下进行。比如说,对这个题材的总体认识就很难。为什么说写当下的乡村难?因为这个当下的点正在跃动弹跳,难以捕捉。也因为很少有现成的创作经验可资参考。
但说难其实没多大意义,一旦选定了,就只有面对这难。对这些难点,除了耐心去面对,我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比如“泡村”,即在老家选两三个村子长期体察。比如“跑村”,即尽可能地去看更多的乡村样本。
趁着采风的机会,全国各地的村子我跑了不少,一二十个肯定是有的,没细数过。其实走马观花的见闻都进不到这个小说里,但我觉得确实也有必要。因为能够养一股底气。看得越多越有底气,这会让我踏实,让我能确认宝水不是众多乡村中唯一的个例,而是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乡村。即便和那些发展相对迟滞一些的乡村比,它作为一个发展得比较快的新乡村,也是有意义的。
回归隐秘的精神原乡
《宝水》这个新长篇,对我而言,其实是个回归之作。
上世纪90年代初,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乡村孩子,师范毕业后被分配回了豫北老家乡下教书,4年后被调到县城工作。几年后又被调到郑州,直至两年前来到北京。迄今为止,乡村生活在我的生命长度中所占的时间份额约是1/3,都浓缩在20岁之前。随着离老家越来越远,我对家乡的认识和理解也有一个漫长的发酵过程。
在河南文学谱系中,乡土写作传统有很强大的力量。或许是有点叛逆,我年轻时特别不喜欢乡土,极想逃避乡土文学这个概念。不认命,总是试图与之保持距离,甚至反抗。约10年前,有评论家曾说,不少前辈作家都有或是曾有过自己的写作“根据地”,也可称为地缘上的“原乡”,将之视作精神上的源脉或感情上的情结,甚或演变为创作中的一贯风格和手法,比如莫言的高密、贾平凹的商州、苏童的枫杨树。他们通常有一个或数个精神原点,或是相对固定的写作地域。这位评论家进而问我:在你的作品中并没有看到某种一以贯之的精神情结或地域元素,你内心有没有一个潜在的写作生发地,或是说隐秘的精神原乡?
没有,在这方面我没有什么明确意识。我当时很决绝地这样回答。还分析了原因说,这应该跟生活背景和成长环境的差别有关。许多前辈的乡土记忆完整坚实,成了他们的一种习惯性资源。他们建立的文学世界不可避免会受到这种记忆的影响。相比之下,我们这代人的漂泊性和无根性更强一些,一般没有长期的固定的乡村生活经验,写作资源相对来说零碎一些,当然也可能会更多元一些。
但其实,怎么可能没有呢?只是彼时不自知。不过没关系,时间会让你知。这么多年过去,悄然回首,我发现自己的小说写作有了两个方向的回归。一是越来越具有乡土性。作为一个河南籍作家,虽然已在北京工作和生活,但地域视野的多维度似乎让我的乡土性更鲜明了。二是越来越女性化。之前我还不时有男性叙事视角或中性叙事视角,如今几乎全是女性视角。身为女作家,进行女性化写作似乎是一种再自然不过的原点选择,可对我而言却是一种返程。
回头盘点一下,《最慢的是活着》可以算作比较明晰的回归标志,接下来的几个长篇,《拆楼记》《认罪书》《藏珠记》都有乡土背景,且也都是女性视角。还有些中短篇小说亦如是,如《旦角》《雪梨花落泪简史》《玛丽嘉年华》《给母亲洗澡》《叶小灵病史》等,其中《叶小灵病史》和《宝水》有一个参差对照的关系。叶小灵的“城市梦”发生在城乡之间鸿沟巨大的上世纪末,讲述的是一个理想主义者的理想“被实现”后,精神突然落空因而无处安放的故事。新世纪以来,城市化进程迅猛,想不被城市化都很困难,有意思的也许该是“乡村梦”。
感知新与旧的相依相偎
“作为作家,我们应该认识到,我们所面对的,是变革中的、内涵丰富且外延广袤的新时代的乡村世界。无论从人员的流动、经济结构的转型去分析,还是从观念意识的变化、生活风尚的更新来观察,一种新的乡村,在我们过去的历史和想象中从未有过的乡村,正在这个时代形成和崛起。”中国作协主席铁凝在全国新时代乡村题材创作会议上的讲话中说。这深合我心。《宝水》写了村庄的一年,是个横切面。横切面意味着必然什么都有。历史的、政治的、经济的、社会学的、人类学的、植物学的,等等,乡村的复杂性必然携带着这些。在驻村采访过程中,我确实能鲜明地感受到新时代背景下乡村的多元力量:乡建工作者、支教大学生、村里的第一书记等,这些力量通过各种方式作用到农村,使得乡村之变成为一种非常鲜活的状态,这种鲜活使得我无法简单地褒贬或明快地判断,这一切在不断突破我固有的写作经验。我越来越深刻地意识到,在书房里架空想象是多么荒唐。
新固然是新的,但看到有媒体在采访时用“呈现了一个全新的中国乡村”来评价《宝水》,我只有敬谢不敏。小说里有新时代乡村的新风尚和新特质,但这新也建立在旧的基础上。在江南采风时我就发现一桩很有意思的事:那些富裕乡村的宗祠都修得一家比一家好。宗祠的存在就是典型的旧,却能和新完美融合,而新旧的彼此映衬也让我觉得格外意味深长。我认为,写乡村一定要写到旧的部分,那才是乡村之所以为乡村的根本所在。正如中国之所以被称为乡土中国,那一定是因为乡土性如根一样深扎在这片大地上。
新时代的乡村固然有新,但旧也在,且新和旧是相依相偎、相辅相成的。新有新的可喜,也有焦虑和浮躁;旧有旧的陈腐,也有绵长和厚重。我不崇拜新,也不崇拜旧。我在其中不会二元对立式地去站队。如果一定要站队,我只站其中精华的、美好的部分,无论新旧。
于是就不给自己预设,只是去跑村和泡村,只是去沉浸式地倾听、记录、整理和选择,然后保持诚实的写作态度,遵从内心感受去表达。在这个过程中,脚力、眼力、脑力、笔力,缺一不可。我个人的体悟还应该加上一点听力——像特工一样潜伏在村里,“窃听”人们藏在深处的微妙心事,这样才有可能和他们同频共振,同悲共喜。如此一来,时代这个原本很宏阔的词,竟然让我慢慢觉得具体可亲。甚至可以说,它就在宝水这个既虚且实的小小村落里,正如滴水藏海。
(作者系北京作协副主席,鲁迅文学奖获得者)
,免责声明:本文仅代表文章作者的个人观点,与本站无关。其原创性、真实性以及文中陈述文字和内容未经本站证实,对本文以及其中全部或者部分内容文字的真实性、完整性和原创性本站不作任何保证或承诺,请读者仅作参考,并自行核实相关内容。文章投诉邮箱:anhduc.ph@yahoo.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