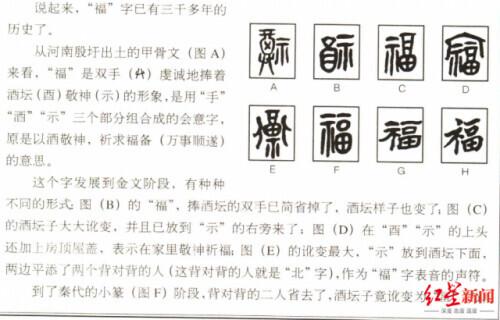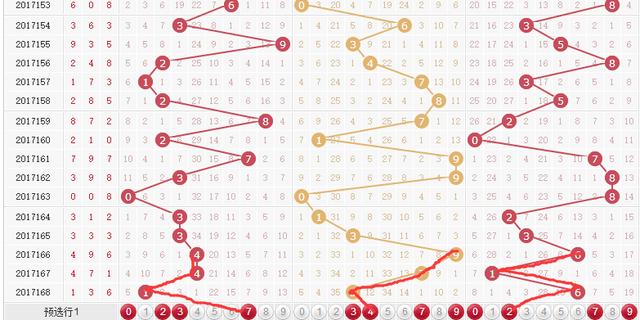李帅比赛完整(李帅董云峰)

“logic”自明清之际传入中国,就陷入了音译与意译的困境。据研究中国现代逻辑史的学者统计,从20世纪20年代至新中国成立前的近30年间,我国学者所著的逻辑学著作达80余种。其中,80%的著作名为“论理学”,其余的20%则多冠以“理则学”“名理学”名称,只有极少数几部书名带有“逻辑”字样。新中国成立后,学界开始形成普遍共识,只采用“逻辑”作为“logic”的约定译名。
“logic”译名流变
“logic”在历史上有诸多译法,如名理、名理探、辩学、名学等。这里,我们介绍其中影响力较大的几种译名。
一曰名学。我国近代启蒙思想家、翻译家严复自幼接受传统儒家教育,他在翻译“logic”一词时采取了最保守的译法,希望将其与中国传统的哲学流派对接起来。中国古代逻辑学发端于名实之争,先秦名辩思潮促进了中国古代逻辑思想的发展。所以,严复倾向于将“logic”译为名学。严复大力提倡归纳逻辑,把“黜伪而崇真”的科学方法视作西学的命脉。同时,严复还肯定中国古代存在着丰富的逻辑思想,认为“夫名学为术,吾国秦前,必已有之”。他在译介西方逻辑相关语词时,只要他认为基本相符的,就采用中国逻辑思想中已有的术语。严复之后,一般用“名学”指代中国古代逻辑学,如胡适1922年哥伦比亚大学博士论文英文标题即为 “ASdualyoftheDe-velopmentofLogicalMethodinAn-cientChina”(《中国古代逻辑史的发展》),他在英文标题下面赫然列着几个繁体汉字:先秦名学史。
二曰理则学。理则学译名最早由孙中山提出。他曾指出,“然则逻辑究为何物?当译以何名而后妥?作者于此,盖欲有所商榷也。凡稍涉猎乎逻辑者,莫不知此为诸学诸事之规则,为思想行为之门径也。人类由之而不知其道者众矣,而中国则至今尚未有其名。吾以为当译之为‘理则’者也”。孙中山的影响力和号召力自不待言,其后理则学译法开始通行起来。1932年,陈大齐著 《理则学大意》,这是中国第一部以“理则学”命名的著作。
三曰论理学。梁启超等人使用“论理”或“论理学”指称“logic”,直接采用“逻辑”日文译名的汉字字形而成。日文中的“论理”或“论理学”最初是英文推理之学(scienceofreasoning)的外来翻译词,较为偏重强调逻辑命题的分析。梁启超在《墨子之论理学》中明确提到影响此时译名转变的外在因素:“‘logic’之原语,前明李之藻译为名理。近侯官严氏译为名学。此实用九流‘名家’之旧名。惟与原语意,似有所未尽,今从东译通行语,作论理学,其本学中之术语。吾中国将来之学界,必与日本学界有密切之关系。故今勿宁多采之。免使与方来之译本生参差也”。1902年,留日学生田吴炤翻译的日本学者十时弥的 《论理学纲要》一书,是第一部用“论理学”来表示逻辑学的著作。1930年,王章焕编写的《论理学大全》以本论和附录形式将西方传统逻辑、中国古代名辩学和印度因明学集中在一部著作中加以论述,开风气之先。
四曰逻辑学。严复在1903年译自密尔的《穆勒名学》一书中,第一次使用“逻辑”作为“logic”的英译。但是,在《穆勒名学》的第一个注解中,严复写到:“逻辑最初译本为固陋所及见者,有明季之《名理探》,乃李之藻所译,今日税务司译有 《辩学启蒙》,皆不是本学之深之相副。必求甚近,姑以名学译之”。可见,严复虽然第一次间接指出了我们现在所通用的“逻辑”称谓,但他似乎不太满意这种译法,只将其作为一般的口语性表达,而非学理概念。章士钊1917年写就的《逻辑指要》是中国第一部以“逻辑”命名的著作。奥图尔(G.Barry.OToole)著,英千里译的《逻辑学》是中国第一部以“逻辑学”命名的著作。
“logic”:意译与音译
“logic”一词之音译、意译的对垒从其于明清之际传入中国便已开始。耶稣会士艾儒略 (GiulioAleni)在《西学凡》中将逻辑刻画为“辨 是非之法”。由于缺乏中文对 等名词,他便采用音译法,把 “logic”译为“落日加”或“络日 伽”,并对于这个译名下了一 个粗略的定义,即 “明辩之 道”。传教士艾约瑟(Joseph Edkins)也碰到翻译“logic”一 词的困难,在《亚里士多德传》 一书中,他将“logic”意译词“辨 驳之理”和音译词“罗吉格”并 列使用。此后的译著者大都试 图从汉语文化中选用“logic”的 对等词,同时也新出现了一些 音译词,主要有 “录集克”“路 际”“牢记伽”“牢辑科”“落及” 等。这些不同时期出现的音译 译名反映了 “logic”在汉语文 化中译介之困难。
章士钊不满“logic”杂多 且变动的意译,第一次正式明 确提出用音译代替意译。在 《论翻译名义》一文中,章氏以 “逻辑”一词为例阐述自己的 观点。他认为,意译词无法精 确表达原词所蕴含的观点, “名学”一词至多只能表示出 亚里士多德或传统的逻辑,却 不能指称培根以来现代逻辑 概念。“辩学”和“论理学”衍生 自“推理”这一概念,存有同样的缺陷,所以也只能表达“提 达(即演绎)逻辑之一部”。
章士钊提倡所谓意义中立的音译词,在学界引起广泛反 响。读者们或要求他提出更多 因意译词产生误解的例证,或 要求提示如何从古经典中找出 “逻辑”这个复合词的原始意涵。也有论者对章士钊的论点提出了质疑,如张礼轩认为,音译方式应保留在对人名地名或是全新事物的翻译上,其余还是使用意译词较佳。首先,意译词可以为阅读者提供直接,即便是模糊地理解字词意义的可能。其次,唯有意译词才能维持中文译名和外文原词语意之间的关系。最后,如果严格遵守章士钊的规则,所有无法找到意义完全相符的中文词汇都使用音译词,则中国语言中“无意义”的词汇和单字必会急剧增加。
由于中西文化客观上存在较大差别,从“logic”开始引入中国时,中西双方的译著者都遇到了翻译上的困难。在很长一段时期里,西方逻辑学著作的译著者虽然大多采用意译的方法译介西方逻辑学,但一般都不能准确传达西方逻辑思想的真实意蕴。在这样的情形下,采用音译法以确定一个没有争议的学科译名是学术共同体首先要解决的问题。
“逻辑”作为“logic”的最终接受样态
诚如著名中国逻辑史专家崔清田所言,伴随着“logic”汉译的论争,其汉译译名的变化体现了西方理论语词在中国历史文化语境下所产生的极具创生性的流变。纵观“logic”的中国之旅,这一西方理论术语在汉语文化中的传播与接受过程,实际上也是它与中国文化思想不断接触、反复碰撞与交融,不断衍生出新的含义,并实现它与中国文化融合的过程。就翻译而言,所谓“logic”在汉语中的对等词实际上是不存在的,意译的方式行不通。
“logic”最终以“逻辑”之名确定下来,一方面表明该词作为一个文化信息极为厚重的理论术语跨越语言和文化障碍而被异质文化所准确理解和接受的困难。另一方面也体现着“logic”在中国走出它一开始所陷入的意译与音译的困境,实现音译回归的曲折历程。意译法争议较大,所译名称繁多,诸派难以达成共识,但是前辈学者探索较真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特别是他们希望通过译名勾连出东西方文化的某些相通之处。逻辑先行者们至少在某种程度上表现出强烈的文化自信,试图充分挖掘传统文化的新内涵,没有一味地厚彼薄己。音译法的优势体现在凝聚学术共同体之力量上,最大程度上消除分歧,“逻辑”译名的确立有效促成了这种共识的形成。该译名将形式逻辑以及非形式逻辑都囊括在内,各派逻辑门类的学者,都能够在“逻辑”的名义下自由通行。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现代归纳逻辑的新发展、理论前沿与应用研究”(15ZDB018)阶段性成果)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李帅 董云峰
(作者单位:南开大学哲学院;天津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免责声明:本文仅代表文章作者的个人观点,与本站无关。其原创性、真实性以及文中陈述文字和内容未经本站证实,对本文以及其中全部或者部分内容文字的真实性、完整性和原创性本站不作任何保证或承诺,请读者仅作参考,并自行核实相关内容。文章投诉邮箱:anhduc.ph@yahoo.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