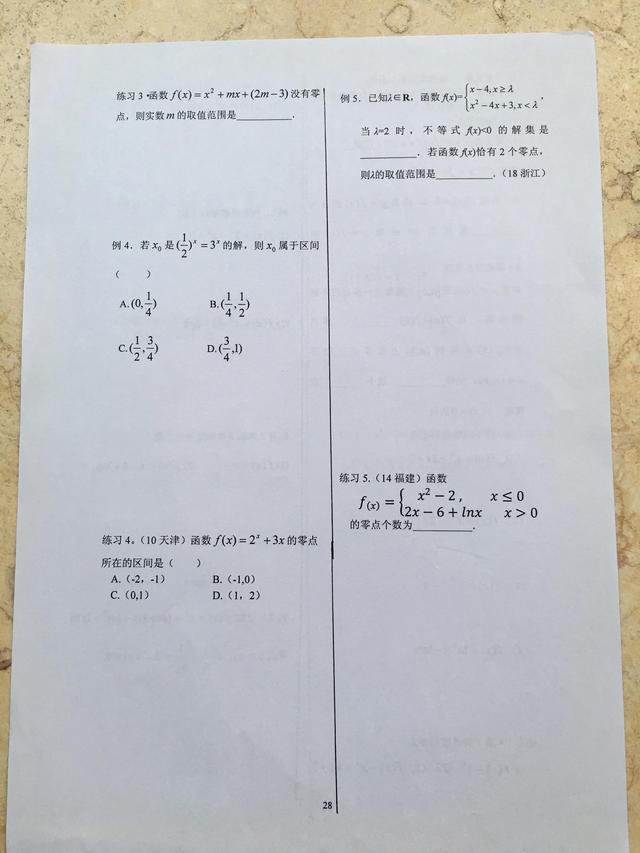古代希腊罗马哲学的成就(共和晚期希腊哲学对罗马法之技术和内容的影响)
本文来源:中国社会科学2003年05期
转自:叙拉古之惑
内容提要:本文旨在研究共和晚期古希腊哲学对罗马法的影响。作者研究了古希腊与罗马的文化联系,考察了对罗马法律文化发生影响的古希腊人和作品;确认西塞罗的Topica一书是把古希腊的普通逻辑学转化为罗马的法律逻辑学的关键作品,并阐述了古希腊逻辑学对提高罗马法的科学水平的革命性意义;分析了古希腊的历史—社会哲学对罗马法内容的影响,着重探讨了社会契约论从古希腊到罗马的传播。本文认为现代大陆法系的法律体系不仅包括罗马和日耳曼因素,而且还包括古希腊因素。

一、古希腊与罗马的学术接触
如果我们知道现在被称之为意大利的许多地方曾经是古希腊人的地盘,我们会认为古希腊哲学不是作为外来之物输入意大利,而是就在那里生长。在现在的意大利南方,从那波里(希腊文为Neapolis,意为“新城”,是古希腊移民建立的城市)以南下至西西里岛的地方都是古希腊人的殖民地。它们是古希腊文化圈的一部分。古希腊哲学的一些流派不是在希腊半岛成熟后再移植到这里,而是直接在这里生长,故南意大利学派是古希腊哲学的重要部分。
而且,古希腊文化的中心是不断转移的。从哲学来看,最早发达的地方是古希腊殖民地而非古希腊本土,例如,往往在古希腊哲学史上最先提到的米利都学派就属于小亚细亚,其次提到的毕达哥拉斯学派就属于南意大利。因而南意大利是“返销”母国哲学的生产基地。直到公元前6世纪末5世纪初,古希腊的经济、政治和文化中心才逐步从殖民地区转向希腊本土,雅典才成为当时哲学活动的中心(注:汪子嵩等:《希腊哲学史》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页。),这种“返销”现象才告结束。但后来随着希腊本土的衰落,学术中心又发生外移。在希腊化时期,罗马建成了比亚历山大帝国更大的帝国,古希腊哲学的中心便转移到了罗马,它本身成了古希腊文化圈的中心。
所以,从地缘学术的角度看,意大利半岛始终参与了古希腊哲学的发展。尽管如此,罗马人仍然是古希腊人的学生。
西塞罗的《布鲁图》一书追溯了演讲术在罗马的发展史,基本上可视为一部罗马的学术史,其中揭示了一些受古希腊各派哲学影响的罗马人。(注:Cicerone,Bruto,a cura di Enrica Malcovati.Oscar Mondadori,Milano,1996.)
在罗马的法学家中,最直接受古希腊哲学影响的有如下几个人:
昆图斯·穆丘斯·谢沃拉(Q.Mucius Scevola),在公元前95年任执政官,并于公元前82年被谋杀。他和他父亲都是西塞罗的法学老师,也都是古希腊哲学的信徒,西庇阿集团的成员。这个集团的目的就是讨论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哲学。它是罗马历史上的两个哲学集团之一。值得注意的是,几乎当时所有有名的法学家都是这个集团的成员(注:Fritz Schulz,Storia della giurisprudenza romana.Sansoni Firenze,1968,p.120.)。
塞尔维尤斯·苏尔毕丘斯·路福斯(Servius Sulpicius Rufus),出身贵族,担任过多种公职,于公元51年担任执政官。他师从阿波罗纽斯·摩隆(Appollonius Molon)研究辩证法和修辞学,开始了他作为演说家的生涯,并达到了第一流的程度。后来他与谢沃拉相遇,决定致力于法学。他根据古希腊哲学创立了“法律的辩证法”,并第一个创立了以其名命名的学派(注:Manuel Jesus Carcia Garrido,Diritto privato romano.CEDAM,Padova,1996,p.11.)。
特雷巴求斯(Gaius Trebatius Testa)是西赛罗、奥古斯都的同时代人和后者的元首参议会的成员,为补充遗嘱制度的确立发表过决定性的意见,著有《论圣物》和《论市民法》。他曾访问西赛罗在图斯库卢姆的别墅,在西赛罗的图书馆里看到亚里士多德的Topika(注:中译本名为《论题篇》,被收入《工具论》,载苗力田主编《亚里士多德全集》第1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北京外国语学院《意汉词典》组编的《意汉词典》将这个书名所用的Topica一词译为“切题”(商务印书馆,1985年,第827页);谢大任主编的《拉汉词典》将之译为“论题方法,有关求得论证的学说”(商务印书馆,1988年,第544页);黑格尔的《哲学史讲演录》的中译者将之译为“正位篇”或论“场所”。泰勒的《柏拉图——生平及其著作》一书的译者将之译为“辨谬篇”。韦卓民将之译为“部目”(《纯粹理性批判》,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113页)。亨利希·肖尔兹的《简明逻辑史》(张家龙、吴可译,商务印书馆,1977年,第29页)的译者将之译为“论辩篇”。Topica一词同时有修辞学和逻辑学两方面的意义,语言词典的译者强调前者;哲学—逻辑著作的译者强调后者。就我个人而言,最给我启发的译法还是“切题”,通过它,我感到自己一下子抓住了这个词的含义。但如果我自己翻译这个词,我宁愿把它译成“理路”。)一书,便询问西塞罗对它的看法。西赛罗说:“此书中包含了亚里士多德创立的寻找论题的理论,它帮助人们在不犯错误的情况下以合理的条理取得对论题的占有”。他建议特雷巴求斯自己直接阅读此书或在一个专门的修辞学家的指导下搞懂其中包含的学说,特雷巴求斯依此行。后来,由于感受到不论是修辞学家还是哲学家都难以解释清楚亚里士多德的Topika,在去希腊的船上,西塞罗遂决定自己写一部同名著作(注:Cicero,Topica,1—5.In http://patriot.net/~lillard/cp/cic.topica.html;also see Anche si vedi I Topici,a cura di G.Galeazzo Tissoni,Arnoldo Mondadori Editore,1973,pp.198ss.),其《论题篇》(Topica)由此成文。这是罗马法史上的第一篇法律逻辑学论文,对当时和后来的法学研究产生了重大影响。特雷巴求斯当然是第一个受影响者。
真正系统把古希腊哲学“搬运”到罗马并将之罗马化的人当推西塞罗(公元前106—前43年,公元前63年任执政官)。西塞罗是罗马文化的大师。根据普鲁塔克为他写的传记的记载,他最早的哲学课业就是由学园派(即柏拉图学派)的哲学家费龙(Filon)讲授的(注:不过,王焕生先生认为西塞罗的第一个哲学老师是伊壁鸠鲁派的哲学家费德鲁斯。);与此同时,他师从谢沃拉父子学习法学(注:La vida de Ciceron por Plutarco,in Nicolas Estevanez edi.,Obras Escogidas,Casa Editorial Canier Hermanos,Tomo Primero,Paris,s/a,p.3.也参见王焕生《古罗马文艺批评史纲》(译林出版社,1998年)第141页。)。成年后,他于公元前87年第一次听因米特达拉悌战争被放逐到罗马的罗德岛哲学家摩隆讲学。后来,他的家里就长住了一位斯多亚派的古希腊哲学家狄奥多托,后者死在西塞罗家里。公元前79年,西塞罗因得罪苏拉避居雅典,在那里听过非学园派的哲学家安条科(Antioco)的课程。苏拉一死(公元前78年),西塞罗即回罗马,途中走了1年,经罗德岛,又去了小亚细亚,在那里听了耶诺克勒斯(Jenocles)、狄奥尼修斯(Dionisius)和梅尼普斯(Menipus)的修辞学课程。他在罗德岛再遇费都鲁斯,与哲学家阿波罗纽斯(Apollonius)和波赛唐纽斯交往,后者属于斯多亚学派。阿波罗纽斯不懂拉丁语,请求西塞罗用希腊语讲话,西塞罗就用希腊语发表演讲,在别人的一片赞誉声中讲完。阿波罗纽斯沉默不语,西塞罗细问何故?阿波罗纽斯说:“我在为希腊的命运悲伤,因为我看到希腊人最后的优势——知识和雄辩——也已经到了罗马”(注:La vida de Ciceron por Plutarco,in Nicolas Estevanez edi.op.cit.,p.5.)。这一故事表明,在西塞罗的时代,古希腊的学术在罗马已经本土化,且有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之势。而且我们还必须知道,西塞罗在因错误处理卡提林那案件而受处分时(公元前58年),也因被放逐的原因到希腊深造哲学。西塞罗兼受各种古希腊哲学学派的影响,尤其受伊壁鸠鲁和斯多亚两个学派的影响。对前一个学派,他有始受终弃之举,因为他认为这种哲学体系不适合于一个演说家,这构成他后来转向斯多亚哲学的原因(注:伊壁鸠鲁哲学主张唯物主义,它与罗马人强烈的宗教精神相矛盾,这或许也导致了它后来在罗马的式微。参见全增嘏主编《西方哲学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226页。)。
经过这样的修炼,西塞罗博采各家,成了罗马的古希腊哲学权威。他在给朋友阿提库斯的信中说,自己不过是一个搬运工,希腊有什么,他就把什么搬到罗马来(注:R.H.巴洛:《罗马人》,黄韬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69页。)。例如,柏拉图有《理想国》,他就有《论共和国》(这两本书的中文名字不同,但西文形式一致);柏拉图有《论法律》,西塞罗也有同名著作。甚至他的被认为最有罗马特色的著作《论义务》,据说也是模仿巴内修的同名著作写的。当然,在下文的分析中我们会发现,如果把西塞罗的著作与古希腊的同名著作仔细比较,我们会感到西塞罗做了许多创新。
古希腊哲学对罗马法的影响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共和早期(公元前450年)的十二表法就大量地引进了古希腊法。那么,本文为什么不研究这一时期的古希腊哲学对罗马法的影响,甚至或者为什么不研究更晚时期,而只研究共和晚期?
我认为,公元前1世纪时期的共和晚期,是影响罗马法深远的古希腊哲学流派斯多亚派(注:斯多亚学派是比较晚起的一个学派,它主张一种以宿命论为中心的伦理学,强调理性和顺应自然的生活,主张泛爱主义,因为所有的人都是神的儿女,因此应彼此相爱。这种观点极大地改善了罗马奴隶的地位。这种哲学传入罗马的具体过程很有戏剧色彩:公元前156—前155年,斯多亚派的哲学家第奥根尼与柏拉图学园派的卡尔内亚德、逍遥派的克里托劳代表雅典出使罗马要求减轻赔款。他们在罗马发表演说,深得罗马青年人的钦佩,使罗马人接触到古希腊哲学。罗马人对此如醉如痴,发生了所谓“征服者的被征服”。为了防止过分崇外的情绪,老迦图禁止这些希腊使者作过长的逗留,把他们送回了希腊。此后,正式把斯多亚哲学传入罗马的是巴内修和他的门徒波赛唐纽斯(Poseidonius,公元前135—前51年)。因此,对罗马产生了较大影响的是中期斯多亚派。罗马人学成毕业以后,就有了自己的哲学家塞内卡和马可·奥勒留。他们属于晚期斯多亚派或罗马斯多亚派。(参见全增嘏主编《西方哲学史》第242页))和伊壁鸠鲁派的成熟期。经过一定的时间差之后,它们就传入罗马了。斯多亚哲学的引入期,正好也是罗马法学的开创期(习称为前古典时期,从公元前367年起至公元前27年奥古斯都建立元首制止)。当时,古希腊哲学对罗马法的基本走向发生了深刻的影响,决定了罗马法基本的技术风格和价值取向。在以后的古典时期,古希腊哲学衰落,斯多亚派转化为以罗马为本座的新斯多亚派,谈不上是一种从外部影响罗马法的因素,而且罗马法已经按既定的轨道发展。
古希腊哲学对罗马法的影响,分为技术和内容两个方面。用现代的术语来说,前者是形式逻辑的影响;后者是普通意义上的哲学的影响。
二、古希腊逻辑学对罗马法之技术的影响
法律技术是组织法律材料的工具。初级的法律技术包括下定义的技术。这是一个寻找事物的属(共性)和种(差异)的过程。定义正是产生在这两个要素的统一中。高级的技术包括进行法律推理的方法:一方面,以归纳的方法获得规则;另一方面,对得到的规则以演绎法适用于比规则由来更广泛的情境。这些法律技术为我们现代人日常运用,然而它们并非理所当然,而是人类经过艰难的探索得来的。罗马法史反映了人类的这一进步过程。
最初的罗马法十分原始,其基本的发展轨迹是先有立法,后有法学;法律先秘密,后公开;先宗教,后世俗。其原始的状况表现为决疑法(Casiatico),即逐案解决问题,缺乏一般规则(注:Manuel Jesus Carcia Garrido,op.cit.,pp.13,15.)。古希腊的辩证法引入罗马之后,罗马人的法律经验在其帮助下上升为理性,使罗马法学脱离质朴的状态进入理论阶段,罗马人学会了从具体案件的解决过程中推出一般的结论。
路福斯根据古希腊哲学创立了“法律的辩证法”,这是后来的罗马法学家频繁运用的研究方法。那么,什么是辩证法?对罗马人产生影响的古希腊辩证法是苏格拉底、柏拉图甚至更早的爱利亚学派的芝诺开创的。“辩证法”一词由Dia和lektikos构成,意思是“通过说话”。柏拉图在其语言哲学专著《克拉底鲁篇》中说:“凡是知道如何提出和回答问题的人便可以称为辩证法家”(注:汪子嵩等:《希腊哲学史》第2卷,第424页。)。他进一步说,辩证法就是对“种”(拉丁文用diviso,distinto,differentia表示)的研究,这种研究通过区分和综合两个途径进行。对种的研究旨在发现管辖种本身的原则并解释个别的情况(注:Fritz Schulz,op.cit.,p.119.)。
这样的辩证法与我们理解的“关于永恒发展的科学”意义上的辩证法不同。现代的逻辑学辞书认为它是亚里士多德学派用来指称今人所称的逻辑学的概念(注:参见《逻辑学辞典》编辑委员会编《逻辑学辞典》(吉林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222页。)。而按西塞罗的说法,辩证法是关于判断的学问,它与关于寻找(Inventio)的论题术一起,构成关于论述的科学(注:Cicero,Topica,pp.6,54.)。
辩证法的输入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它把罗马法学带入了古希腊的职业科学之门,并转化为真正意义的科学。通过辩证法,罗马法学变得完全合乎逻辑,取得了统一性和可认知性,达到了其完全的发展并变得精致。它不仅可用来整理已发生的现实现象,而且也是发现在实务中尚未发生的问题的工具。因此,其意义如同普罗米修斯之火(注:Fritz Schulz,op.cit.,p.130.)。
古希腊辩证法输入罗马的途径是我们感兴趣的问题。我们知道,西塞罗的法学老师昆图斯·穆丘斯·谢沃拉就是一个受古希腊逻辑学影响的人,他在市民法研究中运用了辩证法和区分种和属的系统分类法(注:Manuel Jesus Carcia Garrido,op.cit.,p.10.),并在此基础上对法学进行了概括化的研究,写作了《定义集》1卷(此书的名字用的就是希腊文,它表明了其灵感来源,也表明作者或许懂希腊语)。其中创立了许多范畴。彭波尼说他是通过区分种的方法研究市民法的第一人(注:D.1,2,2,41.)。但谢沃拉是怎样受到古希腊逻辑学的影响的?我们仅知道他是专门研究古希腊哲学的西庇阿集团的成员。此外,基本上也是西塞罗的同时代人的苏尔毕丘斯·路福斯受古希腊逻辑学影响的过程要清楚一些,因为我们已知道他有留学希腊的经历。而最终使我们找到古希腊逻辑学流入罗马的最翔实途径的是西塞罗的《论题篇》一书。
西塞罗的《论题篇》是作者为了向特雷巴求斯诠释亚里士多德的同名著作而写的。亚里士多德的《论题篇》是其逻辑学著作《工具论》中的第五篇,其贡献在于开创了一种语义逻辑,为后来亚里士多德建立三段论的形式化的逻辑理论奠定了基础。
《论题篇》的希腊文名称是Topika,它是从Topos派生出来的词,后者的意思是“场所”、“地方”、“书中的一个段落”等(注:K.Feyerabend,Pocket Greek Dictionary,Classical Greek-English.Langenscheidt KG,Berlin and Munich,w/y,p.381.在现代意大利文中,Topo仍然是表示“地方”的一个词根。)。本文前注已说明,关于这一书名的译法五花八门,不一而足。这种现象出于对Topos一词的把握不准。我自认为这个词的意思是:“节骨眼”、“关节”、“把手”、“经络”。中国有一句话,叫做“老虎吃天,无从下口”,讲的是老虎如果找不到一个端口,就不能把偌大的天吃下去。我们研究问题的时候,面临的是类似的情况,如果找不到一定的“节骨眼”(如庖丁解牛中的关节)、“把手”,我们就无从或难以剖析一个事物。事物自有其经络,犹如动物之有关节。逻辑学者的任务就是为普通人指出认识事物的哲学“经络”,以求得认识的快捷和准确。这些“经络”就是做文章的地方或产生论题的地方(注:例如,对墓前演说或传记等文学形式,西塞罗就总结出这样的写作套路:分精神、身体和身外之物三方面来写。前者要写美德;中者要写健康、美丽、力量、速度等;后者要写荣誉、金钱、婚姻关系、祖先、朋友、祖国、权力等。见Cicero on the genres of rhetoric,tras.by John F.Tinkler,in www.towson.edu/~tinkler/reader/cicero.html。事实上,我们中国人在类似的作品中,是按时间的顺序(出生、成年、老年、死亡)来设计Topos的。有时也以德、智、体3个方面来设计Topos。)。打个比方,犯罪构成的4个方面便是理解犯罪的重要经络。
不错,论题或Topika是寻找被考察之事物关节点的技巧,与之有关的学问也研究各关节点之间的协调问题,所以,亚里士多德说,“通过论题,我们就能从普遍接受所提出的任何问题来进行推理;并且,当我们提出论证时,不至于说出自相矛盾的话”(注:苗力田主编《亚里士多德全集》第1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353页。)。这样,论题就从一个认识问题上升到了逻辑问题。尽管如此,“论题”术之所以吸引罗马人,首先是因为它对培养演说家和养成谈话能力很有帮助。在当时的民主政治条件下,演说术对公众人物极为重要。亚里士多德的《论题篇》就是从演讲、说话的角度研究这门科学的。
西塞罗的《论题篇》是否对亚里士多德的同名著作的模仿?只要把这两部《论题篇》的内容比较一下就可迅速做出回答。从形式来看,两书的结构十分不同。从内容上看,西塞罗的《论题篇》与亚里士多德的同名著作相去甚远。下文试举三例说明之:
例一,亚里士多德在《论题篇》中认为有3种定义:实质定义、名称定义和发生定义(注:幺大中、罗炎:《亚里士多德》,辽海出版社,1998年,第135页。)。但西塞罗在其《论题篇》中提到的定义主要有两种:关于事物本身是什么的定义和关于对事物理解的定义(注:Cicero,Topica,pp.26—28.)。可以看出,西塞罗的定义理论对亚里士多德的相应理论做了发挥或发展。
例二,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中的关系范畴只有“同”、“异”、“相似”、“相反”、“先于”、“后于”等6个(注:参见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吴寿彭译,商务印书馆,1959年)第38页。),而西塞罗在其《论题篇》中提出的同样范畴有13个,即同源词、种、形式、相似、区别、对反、附加、前项、后项、矛盾、原因、结果、比较。西塞罗找到的关节点多于亚里士多德的。事实上,亚里士多德的上述6个关节点的抽象程度更高;而西塞罗的关节点的抽象程度较低。因此,如果说西塞罗受了亚里士多德的影响,西塞罗也出于务实的精神选择了这种影响的范围,从而把抽象的哲学论述转化为具体的法律问题研讨。
例三,最重要的是,亚里士多德的《论题篇》是完全的逻辑学著作,如果说一部书的论点是“骨”,论据是“肉”,这本书的“骨”和“肉”都是逻辑学;而西塞罗的《论题篇》的“骨”诚然是逻辑学,但其“肉”则是完全的法学,因为西塞罗考虑到特雷巴求斯是一个市民法学者,这样安排以照顾这位特殊读者的要求。例如,对于“相似”,亚里士多德是这样说的:“健康的东西和健康之间的关系,与强壮的东西与强壮之间的关系是相似的”(注:苗力田主编《亚里士多德全集》第1卷,第367页。),他完全用的是逻辑学的例子;而西塞罗是这样说的:“如果其用益权被遗赠的房屋崩坏或变得有缺陷,在崩坏之情形,继承人无交付该房屋的义务;在变得有缺陷之情形,继承人无修理义务,完全如同如果一个其用益权被遗赠的奴隶死亡,继承人无义务交付该奴隶一样。”(注:Cicero,Topica,p.15.)在这里,他比较了两种被遗赠物在设立遗赠后状况恶化不导致继承人义务增加的情形,并赋予同样的法律效果,实际上是把已经为后一种情况设定的规则扩及于前一种情况。于是,一个逻辑学上的“相似”的关系范畴,经过西塞罗的处理,变成了一个法律规则的类推适用过程。通过这样的方式,西塞罗完成了古希腊哲学的法律化、罗马化。可以说,西塞罗是法学史上的第一个法律逻辑学者。
上述的比较并非试图抹杀亚里士多德逻辑学对西塞罗的影响。其实导致两部《论题篇》内容差异的最重要原因是,西塞罗不仅研究了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而且作为斯多亚学派的学者,他还研究了自己学派的逻辑学。该学派的创始人芝诺甚至被认为是第一个使用逻辑学这一名称的人(注:E.策勒尔:《古希腊哲学史纲》,翁绍军译,山东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227页。)。正如西塞罗在《论题篇》中所说的:“在我看来,无论对于寻找还是对于判断,亚里士多德都是两者的权威。但斯多亚派专门研究判断”(注:I Topici,op.cit.,p.200.)。因此,我完全有理由相信,西塞罗的《论题篇》是一部综述性的著作,其内容可能更多地倾向于斯多亚派的逻辑学说(注:西塞罗在逻辑学上的贡献之一是创造了古希腊逻辑术语的拉丁文译法;二是向罗马社会介绍了斯多亚学派的逻辑学。参见马玉珂主编《西方逻辑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5年)第105、137页。)。然而不管是模仿亚里士多德还是师从斯多亚派,都难以否认西塞罗法律逻辑学的灵感来自一衣带水的近邻希腊这一事实。
就这样,古希腊的辩证法或逻辑学主要通过西塞罗进入罗马法。当然,在西塞罗之后,阿普里乌斯(公元125—180年)、盖伦(公元130—200年)、波菲利(公元234—305年)、亚历山大(生于公元2世纪末)等学者也成了古希腊逻辑学输往罗马的使者(注:参见马玉珂主编《西方逻辑史》第137—149页。)。他们活动的时期,正好是罗马法学史上的古典时期(公元27—285年),也就是罗马法学达到了成熟的黄金时期。我们看到,罗马法学的繁荣与逻辑学的繁荣是交相辉映的,由于后者的工具意义,我们难以否认它对前者的影响。
那么,古希腊逻辑学对罗马法影响的具体情况如何?我认为有以下方面:
首先,依靠古希腊哲学提供的概念工具,罗马法建成了煌煌的蜂窝式法律概念体系的大厦,成为分析各种生活现象的便利工具。
形式逻辑的首要问题是定义问题。定义要以属概念加种差的方式做出。构成同一属的各种必须彼此不相交,由此把杂多的感性世界组织为一个井井有条的概念世界。最早运用这种概念组织技术的罗马法学家是昆图斯·穆丘斯·谢沃拉。他对法学进行了结构性的研究。在其著作中,市民法被划分为4个主要分支:继承法、人法、物法、债法,其中每一分支又再进行划分:继承分为遗嘱继承和无遗嘱继承;人法分为婚姻、监护、自由人身份、家父权等,其中的监护又分为5种;物法分为占有和非占有,其中占有又分为多种;债法分为契约和侵权行为,其中契约又分为物权契约、买卖契约、租赁契约及合伙契约,侵权行为又分为殴打、盗窃和损坏财产(注:伯尔曼:《法律与革命》,贺卫方等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年,第163页。)。这一概念体系已基本包罗现代民法中所有的主要概念。
推而广之,从宏观的角度看,罗马人首先把法分为圣法和世俗法。世俗法又分为公法和私法。私法又分为人法、物法和诉讼法。在人法中,人分为自权人和他权人;在物法中,物权分为自物权与他物权;债依据发生根据分为4种;履行根据标的不同分为给、做、供3种;继承分为遗嘱继承和无遗嘱继承,等等。这样合理设计的法律概念大厦几乎可以容纳一切已发生或未发生的生活现象,由于其合理性,至今为我们沿用。当它发展到能容纳一个法律部门的所有材料的程度时,一部法典的龙骨就产生了。因此,民法典的骨架在很大程度上是古希腊逻辑学的赠予。民法能被誉为逻辑严密、理论成熟,在很大程度上要感谢这一概念体系。
其次,依靠“相似”的关节点,罗马法中发展起了法律的类推适用或扩张适用的技术。如果发生了现有的概念体系不能容纳的法律现象,罗马人即用“准”的制度解决问题,例如用“准私犯”的概念解决对一些特殊侵权行为的法律调整。“准”的拉丁文形式是“Quasi”,意思是“好像”、“差不多”,这实际上是运用“相似”的关节点对法律作类推适用。对既有的诉权不能涵盖的类似生活关系,裁判官创立“扩用诉权”(Actio utile)解决之,它是对旧有规范的扩张适用。从新与旧生活关系的可比性来看,它又是法律的类推适用。
再次,依靠“原因”的关节点,罗马法中发展起了因果关系理论,为责任制度的合理建立奠定了基石。对此,西塞罗举了这样的例子:如果拆除共有墙的人提出了潜在损害担保,他不应赔偿拱门的缺陷造成的损失,因为不是拆除人的行为造成了损害,而是拱门的缺陷导致它不能承受拆除(注:Cicero,Topica,p.22.)。这个事例贯穿着非出于行为人原因的损失不能由他承担的原则。依靠同一关节点,罗马法还发展了法律行为的原因理论。根据注释法学家的研究,罗马人把亚里士多德的终极原因用来表示订立契约的目的,用驱动原因表示促使当事人订立契约的动机(注:参见伯尔曼《法律与革命》第298页。)。
实际上,罗马法学家往往综合运用各种关节点来分析法律问题。例如,公元2世纪的法学家魏努勒尤斯·萨杜尔尼奴斯在《论对平民的刑罚》一书中,就把犯罪分为四类:因为行动的犯罪、因为言论的犯罪、因为文字的犯罪和因为会商(即帮助他人犯罪的行为)的犯罪。这种分类已对所有的犯罪进行了种的追寻,形成了把握纷繁复杂的犯罪现象的4个Topos。对于这四类犯罪,萨杜尔尼奴斯又以7个Topos缕析之:动机、身份、地点、时间、性质、数量和结果(注:关于萨杜尔尼奴斯对这11个Topos的运用,参见桑德罗·斯奇巴尼选编《民法大全选译·债·私犯之债(Ⅱ)和犯罪》(徐国栋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205—207页。)。我们看到,一个受过训练的法学者,通过运用这两个层次的11个Topos,马上就可透彻地解剖一个犯罪现象。不难看出这些与西塞罗的13个逻辑Topos间的前者是后者的法律化(注:在完成此文后1年多的学术工作中,我更加感到寻找合适的Topos对合理组织法律材料的重要。下面试举两例说明。其一来自我对十二表法的研究。我们知道,现在人们使用的这个法典的复原版本遵循的是部门法的Topos,即把12个表的内容大致分为诉讼法、民法(含亲属法、继承法、物权法、侵权行为法)、公法和宗教法4个部门。我的研究(参见拙著《民法的名称问题与民法观念史》,未刊稿)证明,部门法是18世纪下半叶发现的Topos;意大利的十二表法专家O.Diliberto教授的研究证明,古代美索不达米亚的立法者遵循一种相关性的Topos,例如,以土地为核心,把凡涉及土地的规范都归拢在一起,不论它们属于民、刑或诉讼(参见Una Nuova edizione cinese delle XⅡ Tavole:qualche riflessione sullo stato dei nostri studi,Manoscritto inedito)。看来,学术的进步,有时候表现为更好的Topos的发现。其二来自我起草合同法分则的经验。这实际上是个Topos问题。对于某种具体合同的运作,我国立法者遵循的是定义、合同的主要条款、甲方、乙方的义务、违约责任的Topos。对于某种具体的合同来说,这样的安排当然没有什么问题,但若同时规定许多具体合同,它们彼此间就会有大量的重复,尤其是关于合同的主要条款和违约责任的规定。也许是为了避免这种局面,《埃塞俄比亚民法典》的起草者勒内·达维德在这一领域遵循了“某种合同最可能发生争议的问题”的Topos,例如,关于住宿合同,该法典主要规定了租房一天者的使用期间、租期的延展、房间的预订、旅客的权利、客店主的留置权和保管责任等Topos。如此,一种合同的Topos就可能不同于另一种合同,每种合同都将各有特色,不与其他合同重复。这意味着勒内·达维德找到了一个组织关于某种合同的诸材料的更好的Topos。)。
第四,古希腊逻辑学影响了罗马法学家的著作类型。如前所述,定义是古希腊逻辑学的重要内容,它也成了罗马法学家著作的一种重要类型。我们已知道,谢沃拉是罗马法史上第一位写作《定义集》类型著作的法学家。在谢沃拉之后,罗马法学史上还有帕比尼安写过《定义集》2卷;埃流斯·加鲁斯写过类似的著作《论与市民法相关的词语的意思》(注:参见桑德罗·斯奇巴尼选编《民法大全选译·法律行为》(徐国栋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附录三、附录四。)。
逻辑学在法律中之运用,除了定义,还有规则之寻找,它是在古希腊逻辑学的帮助下对过去的罗马法学决疑法弊端的克服。这一工作是通过从属和种中发现原则来完成的。共和时期的法学由于致力于这种规则的寻求,也被称为“规则法学”(注:Fritz Schulz,op.cit.,p.127.)。这些规则往往是简短的法谚。罗马法学家们留下了14部《规则集》,其中内拉蒂的《规则集》达15卷(注:参见斯奇巴尼选编《民法大全选译·法律行为》附录三、附录四。)。它们原来都是教学补充读物,供学生加强对学习材料的理解使用,在历史发展中很快成为立法的内容。
最后,古希腊逻辑学为罗马法学提供了一套法律推理方法。西塞罗向罗马介绍了斯多亚学派的逻辑,其中包括5个非证明的推论形式,从它们可以派生出无数推理形式。他列出的可以派生出的第六式是这样的:
不能是这又是那,而是这,所以,这不是那(注:参见马玉珂主编《西方逻辑史》第138页。)。
按照我的理解,这个第六式涉及的是不矛盾律。我们看到,罗马法学家已有意识地运用此式分析法律问题。例如彭波尼说:“我们的法律不能容忍同一个平民既有遗嘱而死,又无遗嘱而死,因为依事理之性质,‘有遗嘱’和‘无遗嘱’相互冲突。”(D.50,17,7)(注:本文凡引以D.打头的优士丁尼《学说汇纂》的片断,都是我根据The Digest of Justinian,edited by Mommsen and Alan Watson,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Philadelphia,1985年拉—英对照版翻译的。下文不再另行注明这一事实。)。
三、古希腊哲学对罗马法之内容的影响
此处所说的“内容”,指法律的基本观念和制度。在我看来,古希腊哲学对罗马法的内容影响最大的方面是社会契约论和以自然为中心词的系列概念(注:本文关于古希腊哲学对罗马法中“自然概念”、“自然状态”和“自然法”以及其他观念的影响论述,因为篇幅的缘故被整体删去。笔记将于另文论述。实际上,在以“自然”为中心词的希腊—罗马的哲学—法律术语体系中,我感到了惊人的混杂。尽管西塞罗有“罗马法的灵魂”的称号,他说明的自然状态却不同于优士丁尼《法学阶梯》中可被还原的相应状态。这反映了各种希腊思潮逐鹿罗马,罗马人各有所取的状况。对高级法意义上的自然法与退化论的联系的发现,却是我研究中的意外收获。)。
社会契约论是关于国家与法之发生学的理论,是一种导源于古希腊的源远流长的观点。古希腊以赫拉克利特为代表的协议论者开启了契约论的方向,因为他们把国家、法律、社会和正义的起源看作人为的。智者如普罗泰哥拉、高尔吉亚、普罗迪科、伊壁鸠鲁就认为,国家、社会、法律和道德都是由理性的人为了自己的利益通过社会契约按照自然法确立的,这些伟大的古希腊人勾勒出了最早的关于国家与社会起源的契约论解释(注:Roman A.Tokarczyk,The Paradigm of Social Contract,in Eugenio Bulygin etc.,edited,Changing Structures in Modern Legal System and the Legal State Ideology,Duncker & Humblot,Berlin,1998,p.326.)。
古希腊哲学中的社会契约论思想经历了如下的发展过程:
(1)普罗泰哥拉和其他智者。普罗泰哥拉是最早留下用契约论解释国家与法产生之言论的古希腊哲学家。传说他写过《论城邦》和《论人类的原始状态》等著作。如果此传说属实,他当是研究人类从原始状态过渡到城邦状态之问题的专家。他认为,城邦国家的产生是处于自然状态下的人们为了实现自保的要求而相互约定俗成的结果。(注:参见汪子嵩等《希腊哲学史》第2卷第178—180、183页。)这种对人类进化史的寓言式描述概括了后来的社会契约论的“自然状态”和“自保”两个要素,从此有了社会契约论的学说史。但据有些中国学者的看法,它还不是社会契约论本身,因为它假定的社会契约仍是神的而不是人的产品,它认为建立城邦秩序的原则是神授的而不是人们自己互相约定的,而且法律也是神授的(注:参见汪子嵩等《希腊哲学史》第2卷第178—180、183页。)。因而,可以把普罗泰哥拉的理论理解为从神授说到契约论的中道。
除了普罗泰哥拉外,还有一些智者也表达了完全的或类似于社会契约论的观点。如吕哥弗隆就认为国家组织是人们相互联盟的契约的结果,为了保障个人的权利,人们才缔结了建立国家共同体的契约。普罗迪科(约生于公元前470年)认为,国家共同体及其公共设施是人类有目的的联合努力的结果。克里底亚则认为,有一个时期,人曾像动物一样生活于无秩序状态,并且为暴力所统治。后来为了消除暴力,人们制定了法律(注:涅尔谢相茨:《古希腊政治学说》,蔡拓译,商务印书馆,1991年,第102—110页。)。这样的法律只能理解为终结自然状态的社会契约。上述智者或者直接或者间接地提出了社会契约论。
(2)柏拉图(公元前427—前347年)。柏拉图在其《普罗泰哥拉》中转述了普罗泰哥拉关于国家起源的意见,同时也对这一问题提出了类似的观点,但有所发展。关于国家的起源,他认为,根据古老的传说,洪水和瘟疫曾将绝大部分土地和人口毁灭,只有少数人留在山顶上继续生活下来。他们住在洪水隔绝的山顶上,不能相互交往,他们的生活很简单,没有贫富的区别,因此没有争吵和斗争,也没有法律,只按照前人的习惯生活,但他们有一种被称作首领制(Dynasty)的政治制度。洪水消退,人们从山上来到山下从事农业,为了保卫自己防御野兽而建造城墙。居住区扩大,矛盾也增多了,“人们在彼此交往中尝到过不正义的甜头,又尝到过遭受不正义的苦头。两种味道都尝到了以后,那些不能专尝甜头不吃苦头的人觉得大家最好成立契约:既不要得不正义之惠,也不要吃不正义之亏。打这时候起,他们中间才开始订法律立契约”。此外,为了执行法律,同一氏族的人在一起选出他们认为最好的人作为仲裁者,这就是氏族首领(注:参见汪子嵩等《希腊哲学史》第2卷第1111页。)。显然,柏拉图在公共权力的产生问题上持社会契约论的观点。他认为人主要是根据分工的原则为解决衣食住用而结成一体的(注:参见汪子嵩等《希腊哲学史》第2卷第183页。柏拉图:《理想国》,郭斌和、张竹明译,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46页。)。这就是人文主义的社会契约论了。这样的社会契约不是神的干预,而是人自己活动的结果。
(3)伊壁鸠鲁(公元前341—前270年)。伊壁鸠鲁写过《论自然》37卷。他从个人自由出发的观点提出了一种国家起源说,认为国家起源于人们自愿订立的“共同协定”,其目的在于相互保证不损害他人,也不受他人损害,以达到个人的幸福。这是一种比较明确的社会契约论表达,因此马克思认为他最早提出了社会契约论(注:参见全增嘏主编前引书第232页。)。
我们看到,在古希腊哲学史中,经过上述作家的加工,社会契约论思想由神的视角转向人的视角,由含糊而明确。这种理论的成熟程度已经便于它被移植到罗马了。两个人在其传输中起了重要作用。
(1)卢克莱修(Titus Lucretius Carus,约公元前99—前55年)。斯人是把古希腊的社会契约论传播到罗马的主要中介。他是罗马杰出的唯物主义哲学家、无神论者,伊壁鸠鲁主义在罗马的主要代表,著有阐述伊壁鸠鲁哲学的长诗《物性论》。在这部长诗中,他把自己表现为一个不折不扣的社会契约论者。他认为人类有过一段像野兽一样到处漫游的生活,此时“他们也不能够注意共同福利,他们也不懂得采用任何共同的习惯或法律”;后来有了火、衣服、住处和家庭,文明得到了提高。于是,“邻居们开始结成朋友,大家全都愿意不再损害别人也不受人损害”,这就订立了一个默示的社会契约。于是首领们开始建立城市、筑建城砦、设立官职、制定法典。大家厌倦了暴力,因此自愿接受法律和最严格的典规(注:卢克莱修:《物性论》,方书春译,商务印书馆,1981年,第330—332页。)。伊壁鸠鲁学派的社会契约论就这样以卢克莱修为渠道进入了罗马思想界。
(2)西塞罗。作为罗马法之灵魂的西塞罗也基本上是个契约论者。前文已述,他的古希腊文化素养是综合性的,至少兼包伊壁鸠鲁学派和斯多亚学派。早年他受过伊壁鸠鲁学派的熏陶,这可能使他倾向于社会契约论。
西塞罗在《论法律》中借西庇阿之口说,“人类不好单一和孤独的天性”使他们通过订立社会契约联合成为城邦或市民社会(注:西塞罗:《论共和国·论法律》,王焕生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39页。),而此前人类生活在彼此孤立的自然状态中。他描述了当时人类散居、恶斗的凄惨情形(注:Cicero,De la Invencion,in Nicolas Estevanez edi.Obras Escogidas,Casa Editorial Canier Hermanos,Tomo Primero,Paris,s/a,p.208.)。在西塞罗看来,这种不幸状况的结束要归因于英雄人物而不是神。他说:“这时出现了一个人,他无疑是伟大人物,他懂得人的精神的力量和伟大,他催生其萌芽,引导它、完善它。他把四散在旷野和隐藏在密林的人们聚集在同一个地方,然后一步步地以全部的功利兴趣和诚实影响他们。起初,人们因缺少习俗而对抗,但随后他们由于智慧的语言和雄辩术而变得更驯服。于是这些人改变了粗糙和野蛮的状况而转为温和、具有社会性”。(注:Cicero,De la Invencion,op.cit.,p.209.)照西塞罗这样的说法,城邦倒是由于演说术而建立的了。此术真奇妙,散沙作麻石。事实上,上面的文学性描述也许是对某种历史真实的折射。梅因认为,“古代意大利大半是由强盗部落所组成的,社会的不安定使得人们集居在有力量保护自己并可以不受外界攻击的任何社会领土内,纵使这种保护要以付重税、以政治上权利的被剥夺、以忍受社会耻辱为代价,也在所不惜(注:梅因:《古代法》,沈景一译,商务印书馆,1959年,第27页。)。”此乃剀切之论。
显然,建立城邦后,人类就抛弃了彼此孤立的状态而进入相互合作的状态,由此必须建立公共权力和法律。西塞罗在《论义务》中描述了这种结果:“至于说到城市,如果人们不聚合到一起,无论是建设,无论是密集的居住,都是不可能的;由此制定了法律,形成了习俗,而后公平地分配权利,形成一定的生活规则。”(注:西塞罗:《论义务》,王焕生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67页。)至此,从自然状态到市民社会的过渡完成,社会契约是两者间的中间环节。
这种历史解释的大思路很快被转化为法学语言。优士丁尼《法学阶梯》2,1,11写道:“而显然,自然法更为古老,它是与人类本身同时,自然传授的事务。事实上,市民法则在城邦开始被建立、长官开始被创立、法律开始被写成文字时,才开始存在。”(注:优士丁尼:《法学阶梯》,徐国栋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15页。)这一片断明确地揭示了没有建立城邦、创立长官、把法律写成文字时期的状态与出现了上述三者之状态的对立。显然,借助于古希腊思想的背景,我们可把前者称为自然状态(注:梅因:《古代法》,第41页。),后者称为市民社会,两者的过渡通过订立社会契约完成。
这个重要、影响深远的法哲学预设体现在罗马法的具体制度中。优士丁尼在其《法学阶梯》中如是说:“但元首所决定之事也有法律的效力,因为人民已以颁布的关于其谕令权的王法(Lex regiae)(注:该法的全称为“关于谕令权的库里亚法”,是王政时期罗马人民向国王让渡统治权的法律。帝政时期重新启用。这是罗马法史上一个具有浓烈的社会契约论色彩的法律。)把自己的一切谕令权和权力授予给他个人。”(注:I.1,2,6.In Enzo Nardi,Istituzioni di diritto romano(testi 2),Giuffrè,Milano,1986,p.11.)这是关于王权民授的说明,是社会契约论式的,不同于中国的君权神授论。阿奎那提到,“在《法典》里,罗马皇帝狄奥多西和瓦伦蒂尼写信给地方长官沃鲁西亚鲁斯说:‘如果君主自己承受法律的拘束,这是与一个统治者的尊严相称的说法;因为甚至我们的权威都以法律的权威为依据。事实上,权力服从法律的支配,乃是政治管理上最重要的事情’”。(C.1,14,4)(注:阿奎那:《阿奎那政治著作选》,马清槐译,商务印书馆,1963年,第123页。引用时根据拉丁原文对译文有改动。)这些记载表明了罗马君主认为自己的权力来源于法律之授权的社会契约论意识。
社会契约论以人的合作天性为基础,晚期斯多亚哲学为此提供了证明:人与人之间是有极大的共性的,“一个人和整个人类之间的亲缘关系是多么紧密,因为这是一种共有,不是一点点血或种子的共有,而是理智的共有。”基于此等共性,人们彼此接近,“我们是被造出来相互合作的。”(注:马可·奥勒留:《沉思录》,何怀宏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第105—116页。)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晚期斯多亚哲学为了强调人的合作的意义,把这种合作说成是人的自然,这就遗忘了合作状态前的自然状态,造成了这种“自然”与自然状态中的那种彼此隔绝状态的“自然”的矛盾。
四、结论
通过以上研究,我们可以重新认识现代大陆法系民法理念的债权人。如果说,我们过去相信现代大陆法系民法在很大程度上出于罗马人的创造和德国人的加工,现在则要承认它同样承受着古希腊哲学的恩惠。
必须说,是罗马人的务实精神和古希腊的思想工具合伙创造了深远影响现代民法的罗马法,两者的结合为“拎起”人类无比庞杂的生活关系设计了非常适用的“把手”。在宏伟的大陆法系中,古希腊、罗马和日耳曼思想各占有一定的份额。尤其是使现代民法显得成熟和优越的、可容纳几乎任何生活现象而处变不惊的蜂窝状概念范畴体系,完全是古希腊逻辑学与罗马人的法律头脑的合作产品。如果我们对一些初生的法律部门的理论混乱状况感到不满,如果我们感到民法的蜂窝式概念范畴体系为其他法律部门——包括国际法——所广泛移植,我们就会感到这一体系的来之不易和它一旦形成所带来的广泛恩惠,并由此为它感到骄傲。事实上,把握民法调整的生活关系的“把手”就是用以建构民法典之各编的宏范畴,它们相互间的关系就是民法的体系。从共和晚期的罗马法到法学阶梯体系、到潘得克吞体系、再到正在进行的第三次法典编纂运动中产生的新潘得克吞体系,它们的变迁是设定“把手”的位置的变迁,但万变不离其宗,这些类型的民法典体系的基本框架在昆图斯·穆丘斯·谢沃拉的手里就奠定了。
希腊哲学还是社会契约论的来源,这是一种主权在民的理论,它在希腊的发展经历了从神文主义到人文主义的过程。可以说,没有这种理论,就没有现代的西方政治文明。罗马人敏感地抓住了古希腊人关于社会契约论的乍现灵光,承担了古希腊社会契约论思想传导到中世纪和现代的中介。
正是在谢沃拉、西塞罗生活的共和晚期,古希腊哲学犹如西斯廷小教堂天顶画《创世纪》中的那个上帝,罗马法犹如那个被造好的亚当,前者的手指轻轻触及后者,被触者就从一堆泥土变成鲜活的生命,并生生不息地繁衍下去,进而影响着诸多的后世来者。
,免责声明:本文仅代表文章作者的个人观点,与本站无关。其原创性、真实性以及文中陈述文字和内容未经本站证实,对本文以及其中全部或者部分内容文字的真实性、完整性和原创性本站不作任何保证或承诺,请读者仅作参考,并自行核实相关内容。文章投诉邮箱:anhduc.ph@yahoo.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