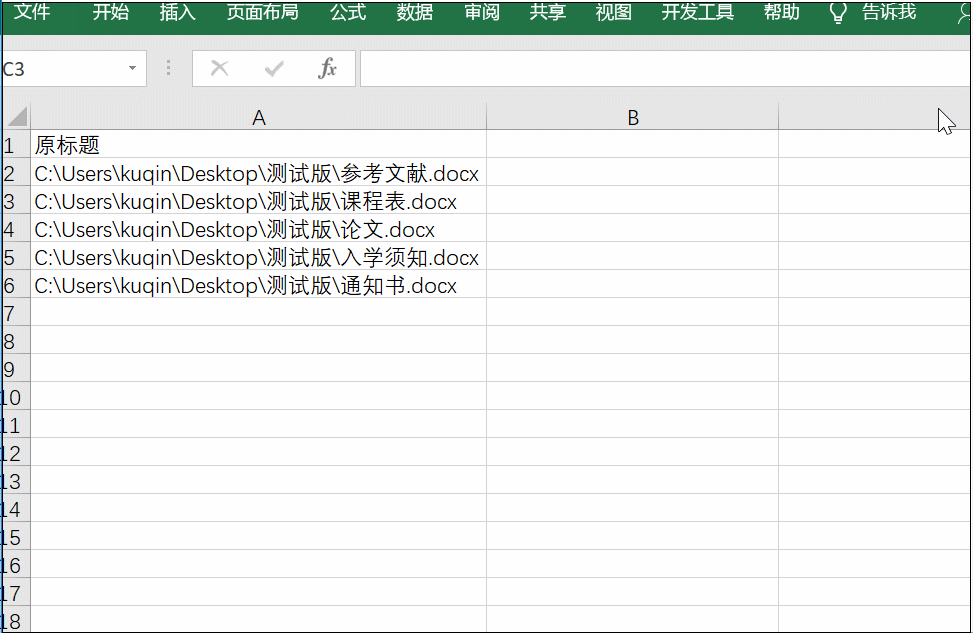肖复兴是怎么成名的?肖复兴卞毓方林少华简平苏沧桑这样和你说
今天,是2022年的第一天,为读者们奉上朝花周刊专栏作者所写的新年寄语——深情回眸,欣然憧憬,你好,2022!
新年寄语
新的一年又要到了,对于即将到来的新的日子,有了新的期许。
最希望的是:已经蔓延两年的疫情尽早地过去,让我们的生活重回正轨。我们国家这两年在抗疫中锻炼的意志和积累的经验,会让我们燃起新的希望和力量。对于个人,写作自然还是本分,希望能够余勇再鼓,宿墨出新,不负读者,不负岁月。达夫曾有诗句“一样春风仍浩荡,两般情思总缠绵”,以此祝福自己,更祝福大家!——肖复兴

美文赏读
天坛的门多,花甲门是我的独爱,因为那里安静,门前有一片古柏,夏季密荫匝地,尤其凉爽。我常坐在门前的椅子上,对着那些有几百年历史的古柏画画。那些树干纵横枝叶沧桑的古柏,让我想起美国诗人罗伯特·弗罗斯特一首题为《劈柴垛》的诗,其中有这样一句:“身前身后能见到的,都是一排排整齐的又细又高的树。”
弗罗斯特站在劈好的劈柴垛前,见到的不是柴垛,而是“一排排整齐的又细又高的树”。这些曾经“整齐的又细又高的树”,变成了眼前的劈柴垛。
一百多年前,八国联军入侵北京的时候,他们把兵营安扎在天坛,砍伐了眼前的柏树当柴烧。那可不是“一排排整齐的又细又高的树”,而是拥有几百年树龄的粗壮的柏树呀。
弗罗斯特在这首诗的最后一句写道:“树躺着,烘暖着沼泽,狭窄的山谷无烟的燃烧。”
天坛里,那些柏树也曾经燃烧,不是无烟,而是翻滚着浓烟。(摘自肖复兴复兴走笔专栏之《天坛的门》)

新年寄语
“朝花”是迎向太阳的生长,她绽放在千家万户的案头,霞肆锦绣,五彩缤纷。愿我的笔尖也能分得她的一缕芗泽,以不辜负时代和读者的期望。
说到读者,想起一件往事:夏日,一位中原的老先生千里迢迢进京找我,我以为有什么要事,原来是老先生被我某篇文中的几句话击中心扉,觉得正是冲着他说的,特地上门来道一声谢谢。啊!其实,真正要感谢的是他,而不是我——他使我意识到手中这支笔的分量。——卞毓方

美文赏读
诗三百,秦风仅占其十。秦风十首,我独钟《蒹葭》和《无衣》。若问另外八首,自然各有千秋,限于篇幅,不一一赘述。若非要说几句?嗯,好吧,且容我别出机杼,从其余的篇什里拎出一个“我”。
“我”是什么?在商代,“我”是一柄锯齿状的巨型兵器,斩伐、威权的象征。到了《诗经》的时代,“我”却摇身一变,成了第一人称的“施身自谓”。以《秦风》为例:言念君子,温其如玉;在其板屋,乱我心曲。(《小戎》)未见君子,忧心钦钦。如何如何?忘我实多!(《晨风》)彼苍者天,歼我良人。如可赎兮,人百其身。(《黄鸟》)
瞧,在这里,我就是自己,自己就是我。可见,“我”的出身是多么炳炳烺烺、铿铿锵锵!
这是名副其实的夺胎换骨,点铁成金;是文字领域、意识形态世界的一场革命。(摘自卞毓方岁月游虹专栏之《秦之怀古》)

新年寄语
何其幸也!新的一年,2022年即将到来,套用年轻人的幽默:“爱你爱爱”。爱你,爱了又爱。“爱”的一年。仁者爱人,爱人、爱你、爱学习、爱工作、爱家乡、爱祖国。无须说,爱是人类最美好的情感。也是拯救这个世界的唯一“疫苗”、处方!
何其幸也!2021年,我以夕阳晚景,邂逅沪上“朝花”。朝花,清晨开的花。世界上还有比朝暾初上的清晨噙着晶莹露珠开的花更美的花吗?博尔赫斯曾言:“花开给自己看,却让许多眼睛找到了风景。”相信“朝花”正是这样的花。祝她在充满爱的2022年越开越美,越开越多,开满上海的大街小巷!——林少华

美文赏读
那么,当下的我们的孤独呢?问题首先是:我们是不是不再孤独了呢?应该说,我、我们仍然孤独。但孤独和孤独不同。我们的孤独,大部分已不再是屈原、陈子昂等古人问天问地、忧国忧民或怀才不遇、报国无门的孤独,也不同于鲁迅、陈寅恪“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孤独——这样的孤独不妨称之为大孤独。甚至,也不同于莫言那种特殊社会环境或个人语境中的不大不小的孤独。相比之下,我们的孤独,尤其大多数城里人的孤独似可称之为小孤独。它或许来自汹涌澎湃的科技浪潮对个体存在感的稀释,或许来自各种监控摄像镜头对个人品性的质疑,或许来自物质主义、消费主义对诗意栖居的消解,或许来自城镇化的快速推进对赖以寄托乡愁的田园风光的损毁,或许来自西方文化对民族文化血脉和精神家园的冲击,或许来自碾平崇高的喧哗众声对理想之光的冷嘲热讽,甚至来自身边亲人对手机饿虎扑食般的全神贯注、如醉如痴……这样的孤独,似乎虚无缥缈又总是挥之不去,似乎无关紧要又时而刻骨铭心,似乎不无矫情又那样实实在在。说极端些,这样的小孤独正在钝化以至剥离我们对一声鸟鸣、一缕夕晖的感动,正在扭曲乃至排斥我们拥有感动或被感动的权利和能力。
所以,当务之急,我们是不是应该修复这样的感动和感动的能力?用一声鸟鸣、一缕夕晖、一朵牵牛花、一棵狗尾草、一片落叶,或者一本书、一首诗……(摘自林少华林林总总专栏之《孤独和孤独不同》)

新年寄语
岁月如水一般长流,但未必流着流着就会消逝,只不过注入了更为深邃的海洋,注入了更为辽远的时空。所以,2021年这一年我以“似是故人来”专栏来怀念那些故去的作家朋友,仿佛再一次与他们见面,与他们交流。我相信他们及他们的作品将永存于世,永存我们心中。新的一年又要到了,祝亲爱的读者们在沾满生动露水的“朝花”中倾听流水潺潺。——简 平

美文赏读
有一次,我和流沙河在茶馆喝茶。我想请他为刚刚组建的《大波》剧组主创人员讲讲李劼人和他的经典文学作品,但他没有答应。说实话,其实,我见了他之后,已经打消了原先的念头,原因是他受了风寒,喉咙嘶哑,都快发不出声音了。他俯在我的耳边轻轻地、一再地说:“真的很抱歉,请你谅解!”我说,今天你不舒服,就不应该再来这里了。可他对我摆了摆手,接着又用手指了指胸口,我明白了,他的意思是,来这里,他心里很高兴,也很快乐。他微笑着看着我,那笑意荡漾在他刻满了岁月印痕的脸上,那么坦诚,那么明亮。我曾读过他写的一篇文章,说在他看来,茶属“轻度毒药”,古人云“毒药苦口利于病”,是后人将“毒药”改作“良药”的,而味苦的茶可发汗,所以能治感冒。果真,即使受了风寒,流沙河也要乐颠颠地去茶馆喝茶。
那个星期二的上午,成都弥漫着轻烟似的薄雾。我再次和流沙河相约到均隆街上的那家茶馆喝茶聊天。那天,我来早了,便站在府南河边,望着缓缓流淌的河水。我心想,流沙河为什么喜欢这个河边的茶馆呢?是不是因为这河水里承载过他的理想,他的浪漫,他的激情,同时也承载过他的失望,他的痛苦,他的坎坷?我不由得默念起他《草木篇》中《白杨》的句子来:“她,一柄绿光闪闪的长剑,孤伶伶地立在平原,高指蓝天。也许,一场暴风会把她连根拔去。但,纵然死了吧,她的腰也不肯向谁弯一弯!”流沙河不就是这样的一棵白杨吗,任凭风吹雨打,都像白杨那般昂首挺立。(摘自简平似是故人来专栏之《“茶客”流沙河》)

新年寄语
2021年,有很多值得感恩的事,其中与写作有关的,出版新书《纸上》是一件,成为《解放日报》朝花周刊专栏作家是另一件。如果说《纸上》是老来得子,“月空来信”(专栏名)则是老来得女,其中的每一个字,都浸润着我知天命之年有别于过往的所思所想所念,与读者朋友们分享中国南方故乡海岛的云卷云舒、潮起潮落时,共同感受月空之下、时间之上的生命之歌、万物之美时,我觉得很幸福。
感恩从不放弃品位的“朝花”,感恩与读者朋友们在此相遇。新的一年,愿山河无恙,你我仍有一份安安静静的好时光在此相遇、相知。——苏沧桑

美文赏读
入春的第一拨雨水,唤醒了结香树,唤醒了停泊已久的渔船,唤醒了岛上无数个干涸的梦境,唤醒了大地之下深深浅浅的盘根错节,仰起身奋力拱破通往春天的一道道重门。辛丑年雨水时节,父母和三个儿女又一次离别前,按照四十七年前五口之家的黑白合影,照了一张同样的合影。父亲又辗转难眠,写下了以下几句话:“四十七年弹指一挥间,天地茫茫不觉我已老,一生无作为,唯有儿女成人可欣慰,愿苍天保佑一家大小永安康。”
黄昏,人迹寥寥的街头,一位因疫情留在岛上过年的年轻男子满身酒气,拉着一位交警的手,用西北话哭喊着:我好想回家过年啊啊啊,太远啦……同样年轻的交警内心拒绝让一个大男人拉他的手,但他忍住了,好言安慰他。有谁知道呢,今年也是他第一次没有回老家过年。他想,等下了班,给远方的父母打个电话吧。
如同一棵树,总是梦见离自己而去的种子和落叶,每一个故园的梦里,彻夜回响着游子的脚步声。新雨后,圆月初升,海岛轻轻吞咽着漫天清晖。母亲慢慢缘楼梯上楼,点亮女儿房间的灯,点亮儿子房间的灯,点亮所有的灯,就像他们小的时候,就像他们从未离开。(摘自苏沧桑月空来信专栏之《一棵树梦见离自己而去的种子》)
栏目主编:黄玮 文字编辑:黄玮 题图来源:本文图片均来自新华社
来源:作者:肖复兴 卞毓方 林少华等
,免责声明:本文仅代表文章作者的个人观点,与本站无关。其原创性、真实性以及文中陈述文字和内容未经本站证实,对本文以及其中全部或者部分内容文字的真实性、完整性和原创性本站不作任何保证或承诺,请读者仅作参考,并自行核实相关内容。文章投诉邮箱:anhduc.ph@yahoo.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