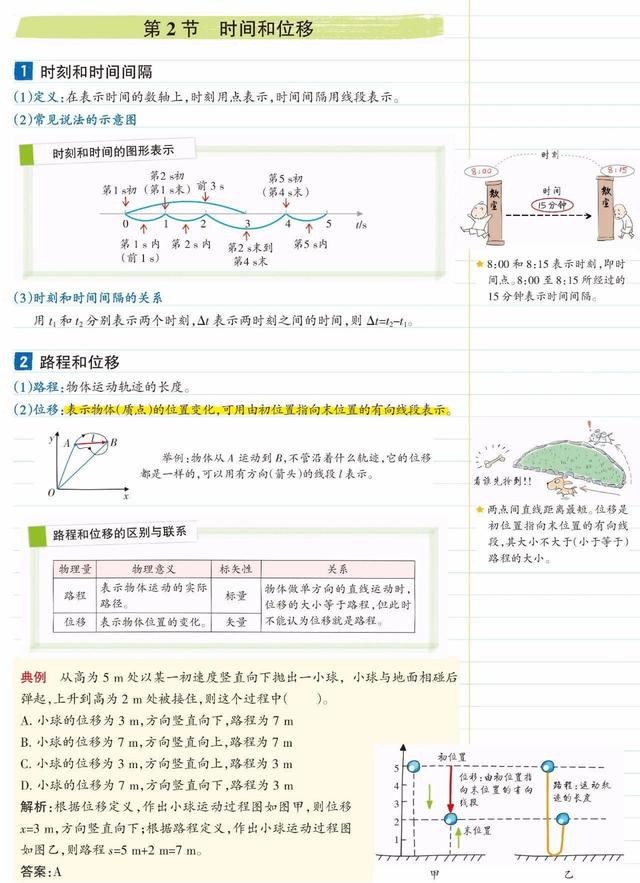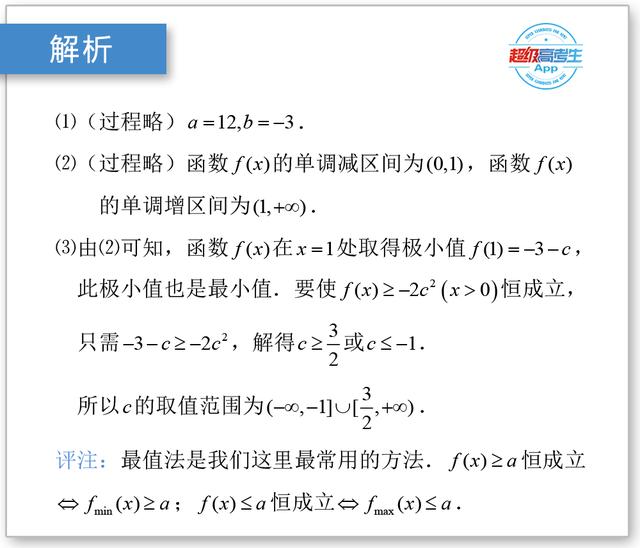漂泊后归乡句子 记忆和语词指引归乡路
现代散文的题材选择多与日常生活有关,对客观真实的追求某些时候也限制了自身的审美表达为了获得更大的想象和表现空间,写作者不断在内容和视点上拉开与现实的距离这样,记忆及其联想成为最常见的书写对象毫无疑问,言说者自己的经历是最牢固和最有温度的记忆,而与身在的日常距离最远的就是童年生活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关于故乡的写作在散文中最常见——书写个体生命最远端的、也就最具有想象可能性的个人回忆,不仅是写作的情感需要,也是文体发展的内在需求,下面我们就来说一说关于漂泊后归乡句子 记忆和语词指引归乡路?我们一起去了解并探讨一下这个问题吧!

漂泊后归乡句子 记忆和语词指引归乡路
现代散文的题材选择多与日常生活有关,对客观真实的追求某些时候也限制了自身的审美表达。为了获得更大的想象和表现空间,写作者不断在内容和视点上拉开与现实的距离。这样,记忆及其联想成为最常见的书写对象。毫无疑问,言说者自己的经历是最牢固和最有温度的记忆,而与身在的日常距离最远的就是童年生活。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关于故乡的写作在散文中最常见——书写个体生命最远端的、也就最具有想象可能性的个人回忆,不仅是写作的情感需要,也是文体发展的内在需求。
但是,无论是昔日泛政治化了的整齐划一的社会活动,还是今日网络时代同质化的信息接受,差异化的审美在散文中变得越来越稀缺,类同的题材和表达成为写作中的顽疾。在多少有些沉闷的散文现场,马陈兵的《潮汕往事·潮汕浪话》给我带来了阅读冲击。这部靠个人记忆、地方知识和乡愁情节交织成的散文文本,用浪漫主义的手法表达了对故乡磅礴幽远的眷恋之情。作者以充满深情的回忆打捞记忆,对故乡乃至整体上的乡土生活展开思想史意义上的文化审视,用一个史学家的个人情感、立场和传统的文史方法在纸上赋予“乡愁”以具体的形象。其情感内蕴由故乡山水、生活现场深抵乡村文化的精神内核,凸显了散文的文化价值及其规范的可塑性。
作者在开篇的自序中说:“任何一个严肃的写作者都首先必须对生命的诞生与成长有所交代。”潮汕乡下的故人、故事、方言和民间传说、风土人情构成了这部散文集的主要内容,串联起这些内容的则是作者的回忆,而追忆与倾诉的位置在当下——内容和叙说的姿态可看作是作者对故乡的“交代”。童年、少年时的快乐一次次被父母不断徙居的生活所打断,生活的艰辛、成长中的苦闷心志乃至强说之愁,时过境迁后已经被时间磨去了刺痛生命的锐利尖角;曾经鲜活而又激越的人生现场被打磨出情感的包浆,变成内心深处可供养育和安放乡愁的温润港湾。
这一过程的实现,既仰赖时间的自然流逝,更凭借作者回望故土时的沉吟、审视与反思。区别于惯常的抒情,马陈兵对故乡的情感既热烈又冷静,且多有理性的观照。他记得幼年时赤足走进经天窗投影下来的菱形月亮,多年以后回想这个情形也并不被感动裹挟,而是发出“那个小男孩和现在的我是不是同一个人呢?”的疑问,由此掀开记忆的帘幕,进入历史的世界中。从阿婆口中讲出的乌佬仔、白贼公的故事,到潮汕地区带水挟溪的地名;由来往密切、淳朴勤奋的加强叔,到曾勾起自己懵懂性别感的乡下女孩甜丸与甜粿,作者从传说、风物和人物身上一路寻觅和清醒地勾勒自己成长的印迹,那也便是走出故乡的履痕。
当然,这种对记忆的追述是在与当下的对比中进行的。在作者看来,“那时的天、地、夜晚和白天,真与今日大异”。从被禁止的风俗变化,到环境污染中“风水观念”的作用,“异”表现在相当多的方面。而作者的反思意识虽然来自后天现代观念的启蒙,但种子在童年即种下了。作者将土尾、成田、盐汀这些地方看作故乡,因是跟随父母的工作迁移而至,总是与当地人不同的,所以他观察和体味乡土的视角是有第三方意味的:“我在潮汕乡村出生、长大,但父母的出身、教育、职业和信仰,使我从未真正进入传统的乡村社会。”作者的身份意识相当清醒。
散文集的上篇《潮汕往事》钩沉记忆时尽管不乏交错的情节和恣肆的感情表达,但大体上还是一个线性结构,家庭和父母的影响是其中最重要的线索。及至下篇《潮汕浪话》,体例完全变化。作者自言是“作为向《马桥词典》致敬之作”而写的,“借若干潮汕方言词与风物互相生发,演绎地方人文历史”,但“演绎”“选材的原则与范围却也严格限定在我早年的成长经验与听闻”,这就使得上下编的文风及其内在的情感得以一致起来:它们都萌发于作者的人生和审美经验——这种经验又带有相当程度的公共性,因为“作为现存最古老的汉语方言之一”,“几乎不同时间层次的中原古汉语及吴语、楚语等方面的语词,都汇集到潮汕方言之中”,而“当代生活尤其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浪潮又为其注入了新的元素和活力”。创意的产生,恐怕与作者史学家的身份是分不开的。尽管马陈兵并不专治语言史,但对方言所蕴含的文化内涵是相当敏感的,以至于秉持着“潮汕话是潮汕文化的主要代表和载体”的观点。
借助方言,我们得以窥见隐含在语词背后“出意表,得天机”般丰饶纷繁的潮汕文化景观。“潮汕浪话”中的“浪话”就是作者要讲清楚的第一个语词,我们不曾想到,被作者用“僻”“福”和“浮”来界说的日常俗语,竟然关联着一部潮汕地区的开化史。接下来的“浮氏物语”中的“物”字是当作表示行为的动词使用,而这一词性的变化过程彰显的却是潮汕人“敢为天下先”的精神气派。同样是“浮”字,搭配为“浮景”就成了“有行情、得好事、发了财、大快活”的含义,作者用研究历史的兴趣和功力阐释这一说法,从汉武帝刘彻和李夫人,过杨太真、白居易后,追踪到带着五百童男童女浮海而去的徐福身上,进而抵达改革开放设立特区的时代,一句在当地司空见惯的话带出来的是波诡云谲的历史变迁和时代风云。“吟唱灵魂”抓住“吟唱”这个字眼,写出了一篇韵味悠长的怀人散文,黄宗泽老校长的清吟浩歌不仅是他生命的“积习和独唱”,亦是一代传统知识分子贫贱不移志的骨气与襟怀……这些绵延久远且代有更新的“浪话”是潮汕文化的载体,更是指引作者打开记忆之门,重返故乡的标记物。
虽然自认与故乡隔了一层,但散文集《潮汕往事·潮汕浪话》仍然充盈着作者浓重的思乡情。马陈兵之所以会对故乡念念不忘,以至于郁积出“形而上”的“愁怨”来,断不只是因为标志故乡的那个地名,而是因为那里的自然养育了他的肉身,那里的文化涵育了他的精神世界。毫不夸张地说,是故乡给予了一个人最初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从此游子背负着故乡的山水,用故乡赋予的道德行走世界。而故乡,则成为他们无论身在何处都无法放下的灵魂牵挂。(桫 椤)
来源: 中国作家网
,免责声明:本文仅代表文章作者的个人观点,与本站无关。其原创性、真实性以及文中陈述文字和内容未经本站证实,对本文以及其中全部或者部分内容文字的真实性、完整性和原创性本站不作任何保证或承诺,请读者仅作参考,并自行核实相关内容。文章投诉邮箱:anhduc.ph@yahoo.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