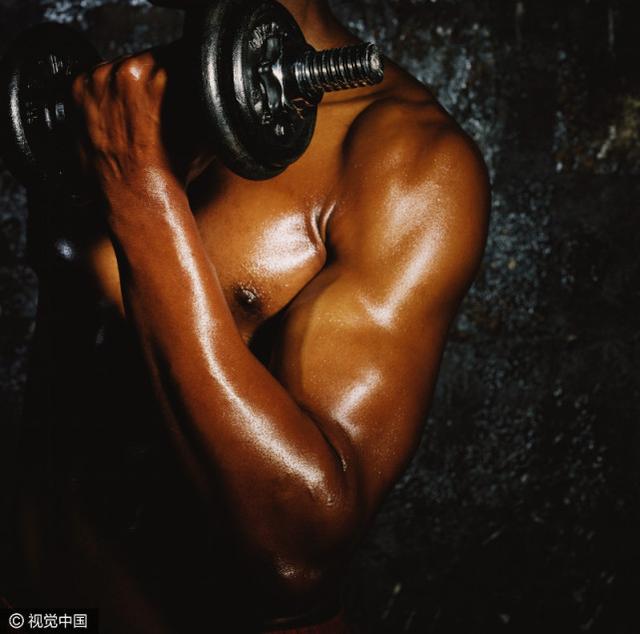城市 马尔康(河滩小城马尔康)

马尔康,藏语意为“火苗旺盛的地方”,引申为“兴旺发达之地”,也有“酥油灯点亮的地方”这一美称。
在二十世纪的三、四十年代,马尔康最早为一寺庙,在寺庙前宽广平坦的河滩上,没有高楼,也没有景致,只有一排白杨林,但南来北往的商贾依然选择了这里,沿河滩搭铺,靠白杨林支帐,开始了物品交易,特别是夏天,这里完全是一个多民族的贸易市场,各路商人云集于此,进行药材、茶叶、马匹、食盐、皮货等交换。久而久之,这里也就形成了一个季节性的市场。人们把这个繁荣一时的季节性街市也叫“马尔康”。解放后,这里建成了永久性建筑,并渐渐成为颇具规模的城市集镇,这时,人们仍然叫它马尔康。
这个诞生不足百年的城市,梭磨河在这里被装饰过了,两岸绿树成荫,台阶井然,鹅卵石被整齐到了河床里,城外带有一野性的梭麿河入城后也长成了整洁、干净、时尚的模样。河道沿着山脚弯曲着,伸展着,也恣意的流淌着。沿着河,整齐的楼房层次错落在曾经的河滩上,沿着滨河大道,长长的城区沿着山脚、沿着河,也转了个弯,据说从山顶上俯瞰,城市象一条即将腾飞的龙,我没有爬到山顶,只爬到了山腰,城市真的象一条活动着的龙,那些色彩艳丽的藏式建筑就是它身上的鳞片,身上的装饰。

下午6点多时进入马尔康,打听了两家宾馆,要么价格有点儿高,要么满客,后来听说是因为公务员考试,好多家大小酒店才会住满了,没办法,车子一直往西,在快要出城的时候,才找到一家,并且第一次听到所谓标准间为套间的说法,还以为是里外两间呢,却原来只是个标准间而已,所谓的套,大概是指房间里套了个卫生间吧。
就是这样的套间,也只有两间,其他的没有卫生间,两张床,一个床头柜,一个电视,两个插线板而已,于是,一行十几个人,分性别排着队在那两个房间里洗漱,先是和两个小姑娘一个房间,半夜里实在经受她们的折腾,跑到那个套间里沙发上睡了一夜。
对于马尔康,除了大脑这个存储卡上一点零星的记忆外,因为是临时走到了这里,事先没有关于它的资料准备,虽然回来后狠狠补了一些,也是难以弥补在那里几乎空白着背景这座城市的感受,城市还是这个城市,街道还是这个街道,但是有了资料背景的去感受,会觉得你是在和一个有生命的城市在交往。
这里,就遗失了许多该有的记忆,比如卓克基官寨,比如昌列寺,比如它的历史。

在距离马尔康还有60多公里的鹧鸪山隧道时,就看到官寨景区的旅游标牌,也心心念着它,只是不知道有多远才能到,也跟同行的人说要去,只是,知道它的领队不愿去,不知道的同行人没有附和着去的,而我自己,半路撑不住眯了会,醒来后以为已经过了,结果,它却只在城外不足7公里的地方,很遗憾,就这样错失它了,下一次,如果有缘,一定要在那个小说里已经熟悉的走廊里走一走,在主人幽暗的卧房里站一站,看一看这间让那个美丽的女子害怕的屋子,只是,也不知是什么时候了。
因为《尘埃落定》,知道官寨是小说里官寨原型,却没想到小说里,关于那个河滩里因商品交换而兴起的小城也是根据马尔康的历史而来的,小说里,有太多马尔康踪迹了,连小说里的空气,也是马尔康的。
作者在这里出生,在这里成长,在这里工作,在这里写出了以这个城市为原型的小说,那么,对于喜爱这部小说的读者,在这个城市里,肯定能够遇着太多热爱着并且熟悉的城市的细节,就像你热爱并且熟悉的女子,你会在她的言谈举止间,就感觉哪怕是鬓角的一朵小花儿呢,也会觉得亲切的很。
马尔康,这个年轻的城市,年轻的现在正是浑身活力的城市,白色、黄色的外墙,红色、蓝色或者白色的屋顶、屋面,鲜艳红的藏式窗檐、屋檐装饰带,沿河弯曲有致,沿坡层次错落着,蓝天下,河水哗哗的流着,一如野外沟底坡前的洁净和欢畅,街道上齐整的楼房,没有巨高,也极少看到低矮棚户,一切都是那么整洁,一切都是那么带着淡淡的似乎庭院里月季花儿一样的,既清秀,亦不浮泛,梳齐了刘海的少女模样儿,还有大街小巷里走过的身着民族服饰的普通人,衣服虽不是非常高档和洁净,色彩与装饰也是鲜艳的很,走在这样的小城,走在这一群人中,走在河水边,由不得,不对它喜爱起来。
对于喜爱这个小城的人来说,也是乐于在小说里感受并且回味,并且骄傲,并且内心喜滋滋的细品,致细微处会会心的一笑的吧。

下车的时候,感觉到了身体的不适,心脏弱,后脑勺有点儿痛,大脑也有点混沌,根据经验,应该是轻微高反了,只是当时并不太清楚马尔康海拔有多少,功课没有做到,后来查了下也是3000多了,心想,也许与劳累有关系吧,还有点儿担心如果不是高反造成的,那么这一次的这么多天的旅途,身体真的不能够承担了吗?近一年,一直担心再过几年,会因为身体,想走也走不了了,那是最担心的事了,所以一直鼓励自己,在现在身体没有异样儿的时候,能走多远走多远,能走多少走多少,难道担心的,这么快就来到了?
带着一丝担心,也带着随遇而安,以身体为主的原则,别人在忙着讨价还价和面对异乡异景表达着惊喜之情的时候,我歪在大堂一角一个铺上,靠着床角的被子,把呼吸放缓,把眼睛微闭,把心思慢慢清空,床铺一侧墙上的唐卡上,佛,静静的跏跌而坐。
同行的人,经过协商,经过讨论,经过选择,终于安排差不多,半个小时也过去了,这半个小时,我也把身体调得好一点儿了,脸色应该也恢复一点了。
这一行人,天南地北的聚到一起,年龄、习惯等等,相互之间都不熟悉,又是第一天晚上,难免有点儿乱,住房啊,车辆啊,慢慢地,也就磨合好了,也都不容易的。
楼下院子里有篮板,几个年轻人不知疲倦地下去活动了,还是年轻好啊,我在那个所谓的套间里简单洗漱,并且告诉他们有点儿不舒服,不出去吃东西了,再到安排的那个房间,躺了会,把前面的几天,用简单的文字补记了下,相机里的照片不理想的就删了。
时间已经晚上八点多了,天色依然亮得很,感觉身体基本无碍了,把从成都出来时穿得稍短的裤子换成长的,又加了件衣服,下楼来转一转。

酒店在梭磨河边,三层的楼房,沿河几间藏式色彩艳丽的毡包一样儿的吃饭包间,中间一座木桥架在梭磨河上,木桥两河沿被护栏拦了,河水哗哗的,溅在了岸边,溅在那些鹅卵石上,片片水花儿恣意的落下,又升起,夕阳淡淡的金色似有若无的映射过来,水花儿也有了暖暖的感觉。
酒店建筑不算多,院落却是真的很大,在楼前大片水泥场地与沿河建筑之间,是修整成图案的绿化和喝茶休闲的地方,几个吊椅分散在几个被植物们环绕的角落,因地就形,植物图案间摆着一个桌四个椅,或者两个桌八个椅的,最阔的那一片,好几张桌子拼在一起,四周摆满了椅子,真象是大会议室被整个搬到了园林里,并且桌椅一律仿藤制,褐色的,框架是铁艺的。
天色渐渐暗了,风也凉了,河边坐着,是有点儿冷了,在吊椅上坐了会,自己把自己再晃了会,看着天边云彩渐红又渐灰,再暗淡的渐渐消隐于初夜的天空。
这个酒店,像马尔康所有的建筑一样,建在河的一侧,也坐落于一侧的山脚,面对着的是另一座河那边的山坡,抬头是浓绿,转头还是浓绿,因为转角,前望,后望,还是不一样儿的峰与坡,不同的,东边远远的雪山顶从峰丛后可以看得到,南边坡上经幡鲜艳艳的,经幡柱高高的,西边群峰缝隙里还有许多许多的分散的建筑,而背后的坡上那个不知名的寺庙,看起来好像并不是很高,很想就上去看一看,只是不知道路有多远,天色也渐晚,也在叫着去吃晚饭了,只得作罢,看着晚霞里的寺庙在半山坡上渐渐的消隐,想着要早点儿睡,早晨再去转转吧。
晚饭在住的酒店吃了,不太能吃得下,还有就是看着那么多的筷子在一个盘子里搅动,就觉得有点可怕,虽然采取了菜上来先来上一大筷,然后就不再弄了,可是,吃不饱,前几天还能坚持这样,后来饿得难受,又没有补充零食的习惯,有时候也会顾不得了,硬着头皮吃吧。
第二天,早早醒了,轻轻的洗漱,轻轻的背着相机就出门了,连手机放在茶几上都忘了拿。

太阳还未出来,一个人在半山腰上静静凝望山下这一个弯曲有致的小城,马尔康中学在目力可及处时,揣测,哪一片坡,是作者彷徨时会躺在那里看蓝天白云的坡?
现在,我就站在那个坡的对面,浓绿苍翠郁郁葱葱的满山满坡的树林,河水欢腾着穿城而过,依河的曲度,顺着滩的高度,高底错落的建筑,一直绵绵延延的,直到目力所穷处,精致的竟如精巧火柴盒一样的玩具样了。
几乎没有风,几朵白云软软绵和的,厚厚薄薄的,闲闲地缠在山腰,落在山顶,有几朵,懒懒散散地在蓝天山峦间发呆。
日从高耸山峰尽头雪山顶上露出红红小小圆圆脑袋儿,云朵儿一片一片地慢慢晶亮了,一层一层地叠着,一根绳儿串起来,就是最华贵的串片儿项链了;刚才还有点儿灰灰的天和绿,瞬时清纯了,天蓝的像是刚刚洗过,浓绿深沉一点儿,也忍不住展开了脸儿;阳光从淡淡,很快明亮的欢快起来,云下深深的绿与云的飘忽不定的影子,云之外,那样明亮亮的色彩与高原特有的清透的空气里的所有,是那样的明快,是那样的闪着最动人的色彩。
大山,连绵的山,高耸的山,将这个美丽小城环绕的大山,以及山顶的雄鹰,在魂牵梦绕的缠缠绵绵的云丝、云带、云朵下,阳光跳跃在浓绿上,阳光以云作模,在山上,城上,河上,作出了各样儿的绚烂的光的图画,并且巨大,巨大到天地间,这一幅画,人间仅有,世间绝无。
远远望去,山顶上的那隐约可见的民居,在早晨的阳光里被照亮了,似乎一个可以发光的玩具,近处那些色彩艳丽的建筑,通通儿圣洁起来,这山腰的寺,经幡在阳光里似乎要燃烧起来了。
光在走,云是它的脚,脚步落在哪里,哪里便灿烂的一片光明,或一条亘长延绵的光带,或一个大大的跌落进了山凹的光盘,或直接走到了河边,于是,河水开始闪烁,绿树更加鲜亮,楼房更加的靓丽了。
沿着酒店对面一个藏家乐前的水泥路,缓缓而上,两个之字转弯后,水泥路没了,盘旋而上的是一条完全掩在树荫里的黄土小路,小路曲折弯弯,有几处坡还挺陡,走走停停,从挂满经幡的枝下经过,从手提布袋的藏民身边走过,那布袋里露出松柏枝,走着,也听着自己渐渐深重的呼吸,高原上爬坡,很容易会这样。

桑烟屡屡,白色塔体显得沉旧了,可是,黑色煨桑的口内,火光红红,未燃起的青葱的翠柏袅袅的,淡淡的柏香在空气里弥漫。
半坡上,一大片平地,一座经堂,经堂西边是两层的僧舍,楼前一辆面包车,白墙红顶,经堂顶下渗落的雨水将白色墙的上方浸染上了淡黄的斑驳,大门上方悬挂着白色底、黑线纹的花卉和山羊的图案,虽然旧了,可是,正是因为岁月风霜在这里留下的痕迹,倒觉得这样的地方,比近年来在那些大兴土木,光洁鲜亮的修复了的经堂,感觉佛离自己更近一点。
漆面剥落,吉祥结已然不再蓬松,硕大的门环扣也许已经锈迹重重,可是,这样的地方,不知道为什么,却总比那些鲜亮的地方更能让自己安静,那些地方,太喧闹了,商业的痕迹越来越难以掩饰。
偏爱这样坡上凹间的网上也搜罗不到名字的寺庙,这里,才是居民们日常信仰表露的地方,这里有最真诚的心愿,有最虔诚的信仰,也有最真实的安宁。
朝佛,煨桑烟,几乎是藏民一大早起来的必修课,只是我来得太早了,经堂前只有一位中年妇女在磕着长头,经堂门紧紧地关着,两边两个矮矮破旧的厚实的木门,门扣,扣着,仔细分辩,才发现,这里的经筒就在这两个小门里,一边进,绕上一圈,另一个门出,经筒所在的地方是经堂房屋外围切出来的一个廊道。
走过不少的寺庙了,经筒、经廊,会有很多种的格局,也有很多种的材质,木的,铜的,铁皮的居多;有绕着整个寺庙的超长的廊,象拉卜愣寺,也有只是绕着经堂的,这样格局的居多;有居于经堂屋檐内的,也有居于外的,等等。
轻轻扭开门口,经廊内很暗,只有面东墙上有一个小小窗户透进来的光,窗台上,许多青稞面和酥油做的捏成了长长,底坐圆圆,尖上有一个小小酥油帽子的礼佛的祭品,在很多地方看到过这样的祭品,但是表达的是什么,不太清楚。

经筒已经很陈旧很陈旧了,底轴凹槽里的油和槽都是黑的了,经筒各个棱面上的菩萨被转经筒的手摩挲的线条已经模糊了,当初应该是艳丽的色彩,也只有淡淡的了,不少经筒的板面,也有不同程度的损毁了,几个木质经筒间,会有一个铜质的,面上锃亮,只是经文已经看不清了。
经廊地面还是原来的被圈进来的土地,现在,因为踩踏,早已凹凸不平,有的凸起的地方,像那个铜的经筒,泛着亮光。
走过窗,里面更暗,靠北的那一面,几乎没光了,暗黑里,一个一个经筒,凭感觉的转过,空气里酥油的味道,在沉沉的暗里飘散着,这些古老的转经筒啊,每一次触摸过你们,仿佛穿过了时间,许久许久的以前,什么样的手触摸过你们?什么的心情在你们这里留下?你给那些人带来安宁,而今,你们依然一如当初的沉静,静静的在时间隧道里,等待着来这里的一批一批人,给他们安宁,给他们安慰。
心灵的事,真的与物质无关,金碧辉煌里,同一个佛,于我,很多时候却不能带给我象在这些安静地方静静等我的,或者过于老旧,或者过于冷清的小小寺庙里给我的多,像香格里拉时,那一个小小经堂里,深深的追问自己,这么辛苦,这么遥远,你在这里,到底想找些什么,能找到些什么?那一次深深的追问,找了这么些时间,现在,还没有答案,可是,问题,在那里了。
青海湖畔的那个洁净的一尘不染,小沙弥也不懂得汉语,我问一句,他们总是微笑,供奉的莲花生大师并不像那些大寺庙,高高的坐在需仰视处,而是如果你站着,平视着他,就好了,虽然面容一如既往地怒目相向,可是,你会觉得,那两撇胡子,有着人间的味道,有着严厉里的那一绺关切。
莲花生大师在佛典里是个永远年轻的美男子,不知道为什么后来所有供奉的塑像都是怒目而视的。
记得当时真的很感于佛的亲民平民的高度,酥油灯在他的脚下,三两盏,如豆,在光线暗淡的经堂里温暖并且指引着。
这个安静村子一头的寺庙,不够鲜艳的经幡在粗高木头上,因为几乎无风,软软柔顺地下搭着,走过几级台阶,是一个小小的院子,院子里再几级台阶,是一排僧舍,玻璃封闭的走廊里,一扇扇门关着,一个小沙弥站在正中间一间贯通房间门口,询问去后面经堂的路,回说正是这一间前后通着的房间,拾阶而上,房间左右两边整面墙都是线条美丽的壁画,再是又几级台阶,这才在小小经堂门口脱了鞋,进了那一个干净的不能再干净的经堂。

从经堂出来,沿着一侧的小门出去,寺后坡上五彩的经幡紧紧覆着坡面,高原上连绵起伏的坡,起伏回环,线条柔和,气质优雅,大方而且典雅。
早晨的阳光打在坡上,寺顶金色经筒上,还有那个好安静好安静的村子,村子前成群的羊,村子尽头那一堵快要倒塌土墙脚磕长头的那个藏族女子。
时间已经隔了这么久,脚步已经走了那么远,这个寺庙里,却想起了那一个,心底深处,将它们,并列了。
转了一圈,走到另一扇门,伸手拉,却发现,这一扇门不知被谁从外面扣上了,使劲敲了几下,原先那位在经堂前磕头的女子打开门,歉意的微笑着,说了句谢谢,估计她没听懂,因为,她一直微笑着。
经堂后,茂盛草丛间,一条菱形石板铺成的小路忽隐忽现,一路攀升上去,因为,坡上,经堂正后面,还有一座似乎更加神秘的殿堂,殿东那个白塔里的柏烟在浓绿深重里袅袅的,几乎不沾尘间烟气。
小道边,有一块一高低错落的不大的田块,种着玉米,刚一尺来高,几页青葱,几缕生命的张力,成排成行的,甚是好看。
推开一扇低矮的铁栏门,继续上坡,一大丛开着密密白花的植物,呈硕大圆形状从墙上垂下来,一伸手都可以够得到了。
围墙外,依然一扇低矮的铁栅栏门,虚掩着,推开,一个小小院子里,一个小小的殿,门开着,棕色木板地面,光洁见人,反射着门外斜照过去的一缕光,门廊头上一块金色匾,原想现场记得来着,可是一时记不下,小相机拍了吧,还糊了,现在也没搞清楚是什么名字。
经堂里供奉着的佛像,我也说不清是谁,殿东墙角,一面红色框面大鼓几乎将一位年纪很大的喇嘛完全淹没了,敲着鼓,念着经,听不懂的经文用藏语念出来,不管什么时候,都会有一种浑然天成的神秘与感觉。
殿里依然壁画、唐卡、经幡从屋顶,一直要垂到地面,地板光可鉴人,老年喇嘛诵经声,唉,一切,都那么自然,只是,被告知,这个殿,一般是不可以进的,是护法殿,赶紧退出,老喇嘛停止了鼓声经声,在我身后的小小塔里煨上了一束清新的柏叶,估计是因为我扰乱了护法殿的安宁了吧。
真的有点抱歉了。
看看表,快到集合的时间了,沿着来时路,下山,穿过马路,司机师傅们正在进行出发前的准备,上楼收拾好自己的东西,背着大包下来,站在院子里,绿树掩印里的寺庙,在已经升高的阳光里闪烁着金光,那是屋顶金色山羊和法轮的亮光。
一行人,去城里吃早饭,是一个菜场附近的小吃街,点了一碗面,吃完,在菜场里逛了逛,菜场里那些新鲜的野菜,也有内地过去的那些水果,头上戴着艳丽花儿的女摊主有一搭无一搭的招呼着,橙子6元一斤,买了四个,在路上吃,补充维C。
一路往西,开始了这一天的行程。
,免责声明:本文仅代表文章作者的个人观点,与本站无关。其原创性、真实性以及文中陈述文字和内容未经本站证实,对本文以及其中全部或者部分内容文字的真实性、完整性和原创性本站不作任何保证或承诺,请读者仅作参考,并自行核实相关内容。文章投诉邮箱:anhduc.ph@yahoo.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