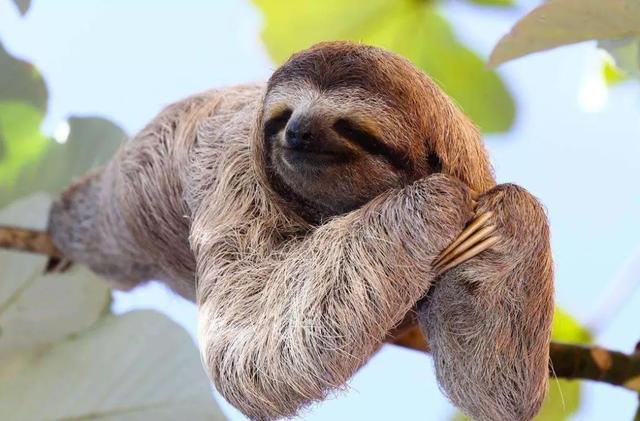鹪鹩之群(鹪鹩一居)
一直以来,我都有一个愿望,那就是拥有一个院子,养一院子的花,种一园子的菜,过上那种“晨起侍花,闲时煮茶,阳光下打盹,细雨中漫步”的日子。
2020年,因为各种机缘巧合,我的愿望实现了。
故事是这样的:小时候在黄河边上的一个小城里一起玩儿大的三个小姑娘,长大后天各一方。其中一个闺蜜的姥爷家在河北官厅的村里有个荒废多年的大院子;另一个闺蜜嫁的夫家也在官厅,多年前因为下岗带着孩子回到了婆家,就在姥爷家隔壁村儿;还有一个是我,大学毕业后留在了北京。
官厅地处河北的怀来县,其实离北京不远,只有110公里,因位于官厅水库的西岸得名。官厅水库是咱们国家第一座山谷水库,1954年建成,后来很多参与官厅水库建设的人都去了三门峡,支援三门峡水电站的建设。闺蜜们的父辈们都是因为去 了三门峡,孩子们也都成了黄河儿女,在三门峡结了缘。

2019年,闺蜜来北京玩的时候,我们带她回了一趟姥姥家,那是她有生以来第一次回姥姥家。闺蜜的姥爷姓寇。我还记得小时候,老师一让填那种登记表格,闺蜜总会急火火地回头问一句“寇*美的寇字咋写”,一开始我很纳闷,什么是“寇*美”?后来才知道这是她母亲的名字。
寇字是挺难写的,这个姓也很少见,除了寇准,我都不知道谁还姓寇。后来到了这个村里一看,哈哈,这回可真是掉进了姓寇的窝里了,镇子上竟是“寇家杂货”、“寇氏早点铺”啥的,再一打听,就连村长也姓寇。
嫁到隔壁村的闺蜜带我们去看姥爷家的院子,她是隔壁村的,一开始也不很确定到底是哪个院子,带着我们在村里鬼鬼祟祟地溜达了好几圈,几经侦查,最终锁定了一个破败大院。因为院子已经荒了许多年,年久失修,很多地方的院墙都豁开了,用树枝、石头挡着,但是整个院子散发着一种残破之美。院子很大,方方正正的,里面种满了树,粗粗一数,得有四五十棵。各种果树,黄杏、苹果、梨树,还有枣树,枣树也不像鲁迅家的,“一株是枣树,另一株也是枣树”,至少得有七八棵呢,在院子的东南角还有一大丛香椿树。

这院子大概得有30多年没人住了,因为荒废太久,院子里除了树就是一地的荒草,老屋里也竟是蜘蛛网。好多人第一次来看的时候,都说“这简直就是聊斋里的院子呀”。可我第一眼就喜欢上了这座老院子,院子敞亮、平整,还有那三间老屋,虽说年久失修,黑黢黢的,有点破旧,但是细一看就是好材料盖的房子,屋里面的大梁油亮油亮的,还有那种木头窗棂,古香古色的味道,这要好好修缮一番,那得多美。
铁三角一通合计,找到了院子的主人—三舅家的表姐,还有现在院子的看护—大舅家的表哥,再找到村长,经过一番小斗争,最终成功。这是怎样的曲折缘分呀,原本是一起长大的少年,居然在中年之后,在人生逆旅的途中再次搭上同一辆车,把在黄河边的缘分北移1000公里,成功地又接续上了。嫁到当地的闺蜜一拍胸脯,保证以后管好院子。
又找来几个朋友来参观,大家一拍即合,商量着建个共享小院。于是,大戏开始,大家启动各种规划,有推荐设计师的,有管基建的,有提供旧家具的,还有给打听政策的。可是尽管2020年疫情已经开始,但让大家始料不及的是这疫情一闹就是三年,而且,官厅还被画在了北京的圈外。
接下来,小院只能成为我们微信群中热议的话题,我们也只能是从前方发来的报道、从照片和视频中见证小院的修建过程。修缮老屋时,看到房顶雕梁画栋的椽,老屋门楣上的漆画,盖新房时,听到动工时劈里啪啦的炮仗,上梁时敲锣打鼓的仪式。一切都是那么新奇,真想去现场看看呀,可是严格的禁止出京政策让我们只能是望院兴叹,无可奈何。

2021年是小院的建设年,6月份动工,9月份建成。建成之后,疫情就更加严重了,在这之后,大家就再也没去过。
去年,我们还在小院采摘了不少黄杏儿,在秋天收获了一些萝卜白菜,还有一堆酸酸甜甜的小苹果。今年一次也没去过,新建成的小院就默默地静立在了那里,隔着这一百多公里,距离产生了美,我们看着照片中阳光下的小院,想象着月光里的另一番景象,恍恍惚惚的。疫情下的两点一线,让外出成了不可能的奢望,可我们在心里又燃起建设小院的希望,只要还有希望,我们的人生就还有光芒。
为了修建小院,大家热烈讨论,在群里发着各种小院建设的视频和田园生活的鸡汤,提着各种建设规划。有人提议用石子铺路,还得铺出花来;要建凉亭,得是能晒着后背的;挖个鱼池,那水系得是流动的;还有人一再强调一定要有个工具间的,最差也得有一面工具墙,墙上整整齐齐地挂着各种工具,假装像007的武器库;烤全羊的炉子,一直因为是坑烤还是炉烤争吵不休,还没能确定;还有人甚至提出了环保节能,如何实现一个自循环的生态环境问题,对了,还得挖个地窖,用来存放苹果和美酒。
一时间,不知多少身怀绝技的能工巧匠,设计师、工程师、园艺师和厨师都应运而生,这大把的人才都埋没了呀,看来把我们变成“五谷不分、四体不勤”的“夫子”的真的是环境,如果给大家一点阳光,所有人都会瞬间灿烂起来。不过当有人提议要给围墙勾缝,当弄明白勾缝就是端着灰泥把所有的砖缝涂抹整齐之后,面对那么长那么高的墙,没人吱声了,都默默地放弃了,不是这工程太宏伟,只是我们这小胳膊太细呀。
前几年,以前单位的一位领导退休后,在顺义租了个小院子,邀我们去参观。那领导在单位是管工程的,那是绝对的能工巧匠。他的小院面积不大,墙角有两棵树,还有一小丛竹子。院子里一半的面积挖了个大大的鱼池子,池子上面有个木质的台子做凉亭,池子里种着荷花,养着金鱼。老领导还有一个专门的工作室,装备了刨子、电锯等各式工具,因为他还有一个特殊的爱好,制作一种叫做麻梨疙瘩儿的工艺品。
老领导还饶有兴味地为我们讲解了麻梨疙瘩儿的整个制作过程。麻梨疙瘩儿是一种灌木,他会在每年的夏天,到山里去找这种植物,最好是长在崎岖不平、有石头的地方,这样地方的麻梨疙瘩儿的根系会更加扭曲,造型就更奇特。他们会给树根系上一个醒目的红绳子,然后到了十一月份,在土地还没有完全冻上之前,再去把它挖出来。为什么要系上绳子,不是怕它跑掉,只是为了做个标记,不然叶子都掉光之后就认不得了。
麻梨疙瘩儿其实也是一种根雕艺术。首先,挖回来的树根要放进一个地窖里,在阴凉地儿放两三年,否则会在后期制作中爆裂,然后再取出来,去粗打磨,再根据想象去做细处理。看着他手工做的那些把件,木头的东西愣是摸上去玉石般光滑,我震惊了,头一次那么真切地体会到了创造之美。
为了不让小院梦因距离和疫情失去温度,我组织大家给小院征名,于是大家又热闹了起来。群里有一朋友是大学教授,有学问,他首先发言,给小院起名“倚群居”可否?这是有感于苏轼的一句话“群居不倚,独立不惧”,看看,他找了个更有学问的依据。
这句话出自苏轼《苏轼文集》,意思是在群体中而不依靠谁,独自一人时也没有恐惧害怕,这可是人生在世的最高境界呀。可是叫“倚群居”不是明显与苏轼的意思相悖吗,要叫那也得叫“不倚居”还差不多。
又一个朋友举手了,给小院儿命名为“乐水小憩”,因为离小院官厅水库很近,可听上去好像是个游乐场似的,这是不是又有点太俗套了呢?
我想起了庄子《逍遥游》里的一句话“鹪鹩巢于深林,不过一枝,鼹鼠饮河,不过满腹”。我想给小院儿命名为“鹪鹩一居”,鹪鹩是一种很普通的鸟,个头不大,看上去有点像麻雀,没什么特别的。我想给小院起这个名字,是觉得庄子的这句话表达了我的心境,我为能有这样一个小院而感到满足。
其实这些年来,我一直在北京附近的郊区寻找,想找一个这样的院子,但是一直都没有遇到合适的,这个院子虽然有点远,但是真的很合我心。也有人说干嘛不直接买个别墅,其实别墅不是我想要的,我只是喜欢一个能自己养花种菜的院子,在一方天地自由呼吸,并不想是要做一个不停打扫各式房间的仆人。
当然,最重要的是我认为自己并没有达到住别墅的高度,无论是在经济方面还是心理方面。有朋友家去年搬进了别墅,上下五层,还有个小院子。住的是宽敞,房间很多。厨房也特棒,现代化的厨具一应俱全,大窗户外面是一棵春天里盛开的樱花,欣赏着窗外美景,洗个碗都是一种享受。
可是吧,这别墅住着我心虚呀,每次上下楼,站在电梯门口我都犹豫,是爬呢还是爬呀,这电梯启动一次那得费多少电呀;上上下下的光卫生间就五六个,这得准备多少消耗品:有时候我都离开好几天了,还会突然不踏实地想着,楼上哪个哪个房间的灯是不是没关。
维持一个庞大的别墅运行那真得不少钱呢,这焦虑我还是不背了,退而求其次,平日里住在市里,上班工作,逛公园喝咖啡,享受城市的便捷服务,周末假日再到小院放松一下,不会负担很重,又能适当调剂,自由切换,这才是当下完美的选择。
也有人会说“鹪鹩一居”太高深了吧,光“鹪鹩”这俩字我就又不认识又不会写,那就赶紧学习一下啊,正好长学问,要是再由此而起意,顺便看看《逍遥游》,那你就更赚了。时间扑面而来,又无声逝去,我们终将只是希望自己健康地活着,平静地过着,开心地笑着,适当地忙着,体味生活,充实内心,有所为有所不为,做想做的事,说想说的话,做自在的自己。
我把给小院起名的由来、经过告诉老同学,拜托她帮我写一篇文言文的小传。这位同学是上学期间年级的学霸、才女,诗词歌赋样样精通,甚是了得,而且她也是在黄河边和我们一起长大的小伙伴呀。
前两天,特别雾霾的一天,我在车里收到她的微信,窗外混沌一片,看着这些文字,简直就是雾霾和不能出京双重压力下的灵感呀,心里更生出对小院的无限向往。这篇文章写得非常好,贴切道出了我们建这个小院的初衷和愿望。
鹪鹩一居小传
鹪鹩巢于深林,不过一枝;
偃鼠饮于河渚,不过满腹。
吾等囚困于帝都蜗居,往来于喧嚣市井,时闻高音喇叭之刺耳,熟视钢筋水泥之无情,呼吸浑浊阴霾之空气,隐忍单调沉闷之人生。虽四季衣鲜,三餐丰足,然身心俱疲,神思委顿。唯愿能与三五挚友,抛凡弃俗,返朴归真,把酒一盏,欢言几番,方感大自在耳。
于是遍寻郊野,偶得此方小院,京北盘踞,官厅湖畔,果树满院,老屋数间,与友共建,归于田园。启有土之逍遥,享片刻之空闲,不胜美哉!
有言曰:山不在高,云过天晴;舍不在奢,禅定性明。地种五谷,园摘蔬青;圃植花草,案烹香茗;随缘接朋客,小食表寸情。结庐南山乃吾意,采菊东篱必潜心。
快哉!乐哉!人生无憾耳。

这回小院的梦圆满了吧,有这么一篇像是名志的文章,小院建设的规格和基调一下子高大上了许多。其实,我估计大多的时候我们还是会亲切地叫她“小院”,“鹪鹩一居”姑且算是个大名吧。
在小院建设过程中,我发现“逃离城市,回归田园”并不是个别人的想法,不然李子柒怎么会成为网红?可以说几乎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自己的小院,或者说是梦想中的人生向往,尽管向往之后紧跟着是现实不易的叹息。
我们都是从小在城市长大,其实并没有太多乡土生活的印记,但是农耕文化的影响还是在潜移默化中植入了不少人的内心深处。对于中国人来说,土地是特别的存在,它一言不发,包容万物,可以是失意者隐居乡野的后盾,也可以是成功者喂马劈柴的理想,更可以是普通人在接受平凡之后享受平凡的选择。
我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是工薪阶层,也是国家改革开放高速发展四十年的亲历者和见证者。在现代化的发展大潮中,我们滚滚向前,从踌躇满志的青年,走过了自己的中年,人生如蝶,不断蜕变。当世间繁华都归于平淡,当年的热情和冲动,在不得不为五斗米折腰的职场摸爬滚打中,也早已烟消云散。转眼间,我们就到了好像还没认真年轻过,就要去做人生向晚之规划了。
然而,再过几年,到了退休的年纪,回首职场人生,我们能从中品出多少成就感和自豪感?这是个细思极恐的问题,好像一下子迷失了,突然有一种找不到人生意义的感觉。
相比我们的父辈,他们虽然也是打工族,但是他们经历了一个火热的建设年代,大多数人一辈子都是在一个工厂、一个单位度过整个的职场人生,几十年的积淀会让他们对工作单位无限依恋,相比他们曾经的激情岁月,我们这一代人似乎平淡了许多。
然而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特有的经历,都有自己要寻找的价值意义以及需要解决的问题。我们这一代人步入职场的时候,迎来了国家改革开放、人才流动的洪流,当然这是幸运的。这使得很多人不再被束缚,有的人在职业生涯中跳过很多次槽,也有的人直接被冠以自由职业者的称号,当然也有人一直待在一个单位,但不管怎样,我们都很难拥有以前人对工作单位的那种情怀了,无论你现在有多高的职位,一旦离开就很难再从事业的角度去刷存在感了。有时候我想,要不是能领到退休工资,好像都没法证明这人以前工作过似的。
对于这个问题,其实无论什么国家,什么时代,什么主义,大家要面对的困惑都是一样的。一部日本老电影《早春》,早就在七十年前前瞻性地为我们描绘了打工族的众生相,揭示了工薪族命运的真相。现代化的社会体系由每一个人组成,但人们也在无知无觉间被各种规纪裹挟,无法逃开身处阶层所带来的枷锁束缚。人们朝九晚五,忙忙碌碌,以为自己正掌握着人生的主动权呢,但当某天回头看时,却猛然发现,一旦离开这里,我们根本无处可去。导演小津安二郎曾说,他拍的这部电影就是要拍出上班族的悲哀,“当领取退休金的时候,寂寞开始了”。看来,要排解这种寂寞,一定得未雨绸缪地早做打算呀。
十月的北京是绚烂多彩的,“数树深红出浅黄”,今年的秋风也似乎比往年温柔,金黄的银杏叶子依然像个穿着漂亮舞裙的小姑娘似的,旋转着婆娑起舞,让这红与黄的童话世界显得更加情深意重。我们也如愿没有辜负这万山红遍、层林浸染的金秋时节,实现了十月的“每周一爬”。先是喇叭沟门,然后是药王谷和药王谷一山之隔的一座无名山谷,最后是顺义的舞彩浅山,真的是遍看壬寅金秋的每一片红叶。
在舞彩浅山的栈道上,因为疫情和防火的控制,游人很少。那天是个阴天,满山的红叶没有了阳光的加持,不再反射出金红的光,但也仍然是秋画阑珊,呈现出另一种真实、本色的美,黄就是黄,红就是红,和那些依然绿着的叶子,在这片山谷里冷静地抵御着外界的喧嚣和灿烂。
大家在这画境中游走,在时间里潜行,看着那一片一片金黄的叶子不紧不慢的凋零,咀嚼着伸手采摘的小黑枣丝丝的甜涩滋味,与季节同悲喜,与岁月共言欢。也许是这醉人的秋色激发了同行四位不老男神内心的温柔,他们即兴为大家“现演”了一首歌,以最恰当的方式向这秋日山林致敬,看着他们几个认真又不乏激情的表演,再加上那临时组合的男生乱唱,我们都忍俊不止,但是细想那歌词“如果再回到从前,一切重演,我们是否会明白生活重点”,还是让大家心生感慨。我想起头条上一位关注的大咖最近发出的人生思考,如果给你15年的时间让你重新来过,你最想做什么,你会怎么度过这15年?
我不知道他们会怎么回答,但我知道自己的答案,我会建一个小院,种树养花,煮茶做饭,吃上自己种的菜,为自己打造一个亲近自然,放松心灵的空间。我希望能在这个空间穿越回到童年,无忧无虑,脚踏大地,仰望星空,在清醒之后重新体味人生。
前两天,闺蜜夫妇已经为小院做了入冬前的收拾和规整。今年收了一编织袋的核桃,一篮子金丝小枣,因为没有打过药,三棵梨树上的梨子掉了一地,一堆芥菜被闺蜜腌进了大缸,希望能成为冬天的馈赠。还有一筐红红的姑鸟,我都不知道是啥味道,只能在微信群里发个朋友圈MARK一下。

看着她发来的照片,我们在群里互相拍了拍肩膀,是真的,小院就在那里。
收获的热闹过后,小院该是一地落叶衰草的萧瑟了。不,等等,你看视频里,在墙角的杂草丛中,千里光迎着寒意开放了,那小小的黄花星星点点,灿烂盛开,生机勃勃的样子。尽管无法闻到那淡淡的菊花香味,但用心感受,仍能被那种朴素平凡的美感动。

不是花中偏爱菊,
此花开尽更无花。
这花开过之后,小院真的是要归于寂静了。
,免责声明:本文仅代表文章作者的个人观点,与本站无关。其原创性、真实性以及文中陈述文字和内容未经本站证实,对本文以及其中全部或者部分内容文字的真实性、完整性和原创性本站不作任何保证或承诺,请读者仅作参考,并自行核实相关内容。文章投诉邮箱:anhduc.ph@yahoo.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