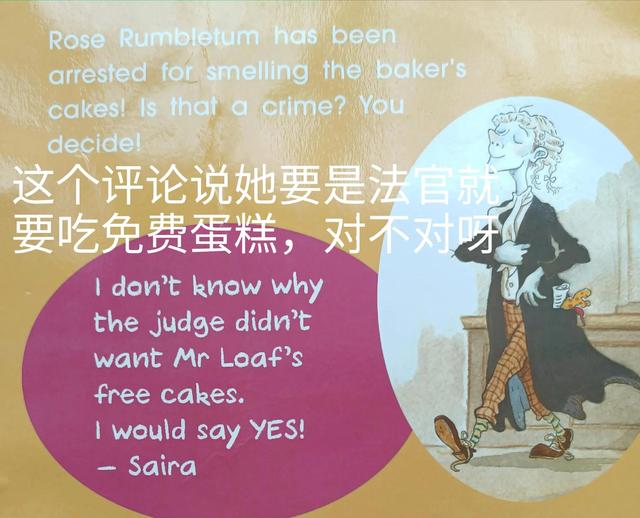为什么喜欢朋克(你永远不可能低下高昂的头)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文 | 云村研究所
如果你第一次到武汉,第一个落脚点通常会是武昌火车站或者汉口火车站。
在长江边闷热的天气里排半天队打上车,在一路满城挖的场景里,你会听到司机师傅嘴里喷涌而出的一些方言,你可能听不太懂,但你明白,那不会是什么好话。
听着肆意狂飙的脏话,坐着肆意狂飙的出租车,看着肆意狂飙的公交车,所有这一切躁动的场景和声音,都在和你印证一件事情:朋克之都到了。
从武昌火车站出来,我们沿着主干道武珞路继续往东狂飙,一路上会经过一些武汉的重要地标:首义广场、武汉大学、街道口商圈、卓刀泉……然后就到了武汉光谷。
环绕光谷的大圆盘延伸出去有五条大路,选中一条叫鲁磨路的向北走5、600米后,在经过一片高大商业体与老旧社区交织的城中村后,我们在曹家湾下车。
VOX到了。
01
讲述武汉音乐的方式有很多,从这家叫做VOX的livehouse开始,除了在很长时间里,它是武汉的音乐中心外,也因为VOX创始人朱宁曾经所在的一支乐队,是武汉音乐风格的奠基者。
朱宁不是武汉人。
1994年,还在四川攀枝花工厂里上班的小伙子朱宁迷上了打鼓,在一年后扔掉了工作,北上去北京迷笛音乐学校学习打鼓。在那儿,他认识了另一个从武汉来的小伙子吴维。
武汉人吴维是这支乐队的灵魂人物,也是这座城市日后最重要的音乐人之一。他从小在老汉口的巷子里长大,每日行走在其中,自然浸润了武汉人的江湖气质。
十几岁时,吴维就开始在街上混。19岁那年,也就是1994年,有一天,吴维在武汉最繁华的江汉路上游荡时,看到了北京迷笛的招生信息。当时他自称对音乐完全没有兴趣,只是想借此离开这座让他感到压抑的城市。
在北京短期的培训后,吴维带着朱宁回了武汉,在那里,他们找到了另一位迷笛的同学韩立峰,在1996年组建了一支乐队,叫“生命之饼”。这支名字从《圣经》而来的乐队,将会在未来奠定武汉流行音乐的本色和主要风格。
1996年12月,生命之饼在武汉的一个小酒吧迎来了他们的第一次演出。朱宁记得,上台前他整个人都懵了,脑子一片空白,吴维对他说,不管了,上去打就完了。后来的朱宁只记得当时的自己一阵乱打乱来。
这种胡来让本来就躁动的观众更加躁动,朱宁后来回忆说,观众们“像疯了一样”。
这似乎就是朋克音乐的力量。作为“更叛逆的摇滚”,在音乐上,这种音乐类型追求使用最为简单的三和弦,同时配以快速激进的鼓点和简洁的旋律,快感和爽感齐头并进,根本不给人安坐的可能。
这些特质在生命之饼身上体现得很明显,他们的音乐节奏极快,吴维的声线也充满了发泄式的嘶喊,哪怕是在没有干扰的环境下,你可能还是听不清他在唱些什么,但也能从中感受到他想传达的不羁和反抗。
反抗好像是武汉这个城市的基因。如同百年前在这座城市打响的革命第一枪一样,生命之饼的出现让朋克音乐在武汉的影响力迅速壮大。
02
当我们要解释这种必然时,也不能忽略在那之前,武汉受到国内90年代大的音乐环境的影响,也出现了一些摇滚和民谣的乐队。然而,可能是与武汉人骨子里那种反抗和不羁的精神态度过于契合,最终为这座城市在音乐领域打上标签的,还是朋克。
一个从武汉走出的英语不是那么OK的企业家,有一段论述在这里同样适用。他说:“我花了几十年才明白,企业要顺势而为,不可与趋势为敌。”做企业如此,做投资如此,可能做音乐也如此。
总之,武汉和朋克就此齐心携手,珠联璧合了。
这种趋势一旦起来就顺其自然了。1998年,武汉当时的四支朋克乐队“妈妈”、“死逗乐”、“愤怒的狗眼”和“生命之饼”带着自己灌录的小样开始巡演。
当时已经影响全国的石家庄杂志《通俗歌曲》在介绍这些乐队时,顺便就提出了武汉是中国的“朋克之都”的说法。
这个说法既是横空出世,也是盖棺定论。从此乐迷圈就认定,也不用另请他城了,就由武汉来做朋克之都吧。
你别说,这种武断还挺准确。
历史上的武汉被深深打上了码头文化和工业文化的烙印。曾经的汉口江滩在民国时期,是各大国外银行的汇集地,这也让大武汉有了仅次于大上海的名头。
建国后,武汉又成了华中地区的工业重镇,从武钢到武柴、武重,都是规模庞大的重型国企。
到了80、90年代,经济快速成长与体制改革带来的阵痛交织在一起时,也没有吓到“不服周”的武汉人。
他们靠着从长江码头和汉正街市场上沉淀下来的拼命干和不服输,走出时代巨变带来的困境。十几年后,颜丙燕在电影《万箭穿心》里完美还原了这种感觉。
如果命运想要压倒一个武汉人,那个武汉人想的一定是,去他的,和他干,然后把命运压在身下。
这话说起来好像有点搞颜色,但这种不服和反抗,自然也就氤氲成了朋克之都的底色。
03
在这波朋克浪潮里,哪怕是连达达乐队这样为数不多的异色,也有过一段朋克岁月。
与巷子里混出来的吴维不同,武汉人彭坦从小长于市政教育机构汇集的武昌水果湖地区,那里的氛围是迥异于汉口老巷子的静谧。1996年,还在上学的彭坦与发小魏飞一起组建了达达乐队。
那时,年轻气盛的彭坦似乎也觉得自己是一个有朋克精神的人,他当时的作品都比较尖锐躁动。不过,1999年,当吉他手吴涛加入达达后,乐队成员终于固定下来,他们的音乐也开始变得丰富柔软和旋律化。
2000年,几个男孩离开武汉去往北京,成为了中国内地第一支也是当时唯一一支签约全球五大唱片公司的摇滚乐队。这一年,彭坦22岁。
一年后,在推出了市场反应强烈的《天使》后,达达一举成名;两年后,在推出了市场反应不佳的《黄金时代》后,达达宣告解散。
那十几年间,彭坦与名模春晓的婚姻成了他们在公众间唯一的话题。直到2019年乐队重组,这时人们才发现,彭坦那清新沉静的声音里唱出的南方还是那么令人神往。
就在达达北上的时候,2001年,原国家计委批复,在武汉东湖高新区建立首个国家光电子产业基地,即“武汉·中国光谷”。武汉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朋克们也到了结婚生子、养家糊口的时候。
2002年,朱宁从生命之饼退出,在武昌火车站附近的开了我们开头提到的叫VOX的Livehouse。经历了初期的关店搬迁之后,在鲁磨路上一扎就是十五年,直到去年才搬到了几百米外的光谷步行街。
虽然这片区域在当时还远称不上繁华,但这里很快还是成为了武汉音乐演出的中心。每到夜色降临,街边都会支起一排排红色帐篷的烧烤摊子,连带着周边的老五烧烤和潮汕砂锅粥等餐饮店,都在等待着听完live的乐迷前来打卡。
04
那几年,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以及互联网的迅速普及,年轻人们也开始更快地接触到各种来自国外的流行音乐风格。
2004年冬天,在武汉念书的丁茂和朋友们组建了一支乐队,取名“花伦”,开始在武汉本地活跃起来。
那个阶段,花伦接触到了美国天空大爆炸和日本MONO等乐队的作品,这些被称为“后摇”的音乐风格给年轻的花伦乐队带来了冲击和震撼。在丁茂看来,这种“门槛更低”也“更新鲜”音乐形式更适合他们,并且——最重要的——这种音乐可以不需要主唱。
2007年,他们发行了首张专辑《Silver Daydream》,整张专辑全部以器乐纯音乐的形式呈现,给人非常强的沉浸感。这几年,他们又参与到了不少影视作品的配乐中,比如电影《大象席地而坐》和纪录片《武汉武汉》,都是非常动人动心的作品。
一个怎么都忍不住想和大家分享的八卦是:花伦乐队的丁茂,是早期网易云音乐著名的“空虚小编”编辑之一。
意外不意外?惊喜不惊喜?
我们从八卦回来。另一支在当时成立,并在日后逐渐成为武汉音乐代名词的乐队是AV大久保——一个名字听起来不太正经,但音乐令人过耳不忘的乐队。
乐队灵魂人物陆炎和前辈吴维一样,受涅槃乐队影响踏入了音乐的圈子。2006年,陆炎在武汉组建了AV大久保乐队。他们的首张专辑《大时代》,灵感源于他们自己在武汉的生活,其中有不少歌使用了武汉方言。
当狂躁的鼓点配上歇斯底里的人声,它所带来躁动和反叛一如他们的前辈。就像《我的一张大字报》里唱到的:“你说,世界是属于我们的,用血肉浇铸的大厦啊,我们难道不是最坚固的螺丝钉吗?”
不过,虽然他们身上受朋克音乐影响的痕迹很重,但你恐怕很难将他们归在某一个类型下。陆炎自己也说,他们这一代音乐人坐上了互联网的快车,风格更多元,没那么固化了。
这种融合性与武汉“九省通衢”的特点异曲同工,再加上一波又一波从全国各地涌入的大学生,在更年轻一代的音乐人身上体现的更明显。
05
武汉有着超过百万的大学生群体,磅礴的荷尔蒙气息像从农田里拔地而起的光谷一样无法阻挡。
这个城市里流传着各种年轻人的故事,躁动的、平庸的、亢奋的、无聊的、激荡的、生猛的、香艳的以及让人感叹惋惜或者一飞冲天的。从高校中走出的各种风格的乐队,也在武汉燥热潮湿的环境里,渐生渐长。
2011年,从华中科技大学毕业的85后徐波在武汉成立了Chinese Football乐队,玩笑似的乐队名中,有对美国乐队American Football的致敬,也有一种对中国足球悲情形象的解构。他们的音乐风格虽有后摇的影子,但更偏向相对小众的EMO音乐。
2015年,几个在武汉上大学的外地年轻人成立了海皮威尔乐队,风格同样多元。既能听到强烈的NewWave律动感,也有层次丰富的电子音乐元素,还有后朋克的黑暗。
当然还有从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校园里走出的民谣组合房东的猫, 虽然已经收获诸多主流综艺节目的邀请,但依然保持着非主流的独立清冷和恬淡气质。
这些年轻人从不同的地区汇集到武汉,和他们的前辈吃着一样的豆皮、鸭脖、蛋酒、热干面,却创作着与他们的前辈们并不一样的音乐。
在这个过程中,所谓的“朋克之都”似乎早已成了一个名不副实的习惯性称谓。就像海皮威尔的年轻人们都搞不懂为何武汉是“朋克之都”。
但对于老武汉乐迷来说,只要吴维还在,只要生命之饼还在,只要VOX还在,武汉朋克就不会消亡。
06
两年多前,武汉遭遇了一种新型传染病毒的袭击,忽然被打懵了。这座千万人口的大都市一度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危机和停滞。
然而,就像他们闷声不响的表面下不服周的个性一样,回过神的武汉人,依然谁挡也不服,爆裂地反抗着企图让他们屈服的一切,憋着一口气扛过了那段岁月,被人热泪盈眶地称为“英雄之城”。
武汉当然当得起“英雄之城”四个字。毕竟,多少年来,他们咬牙扛过了生活和时代变化带来的苦和难,生生不息至今;一百多年前他们就率先用第一声枪响,表达了对旧世界的诀别;24年前他们又一步不退,数次顶住了洪水的侵袭。英雄总是无言也无悔,服是不可能服的,直接干就是了。
从这个角度来说,吴维的那首《大武汉》,也显得比其他歌名里带“武汉”二字的歌曲,更符合这座城市的气质。
“她会得到自由 她会变得美丽
这里不会永远象一个监狱
打破黑暗就不会再有哭泣
一颗种子已经埋在心里
这是一个朋克城市 武汉”
它有血有肉,率性自然;它醉酒狂欢,愤世不羁;它直抒胸臆,爆裂狂躁。很多人叫它大武汉,不仅是因为地方大,这里的人脾气也大、嗓门也大。
但最终,这些都化为了一种气魄上的大,让每个武汉人都能拍着胸脯说出这句:“武汉,蛮扎实!”
,
免责声明:本文仅代表文章作者的个人观点,与本站无关。其原创性、真实性以及文中陈述文字和内容未经本站证实,对本文以及其中全部或者部分内容文字的真实性、完整性和原创性本站不作任何保证或承诺,请读者仅作参考,并自行核实相关内容。文章投诉邮箱:anhduc.ph@yahoo.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