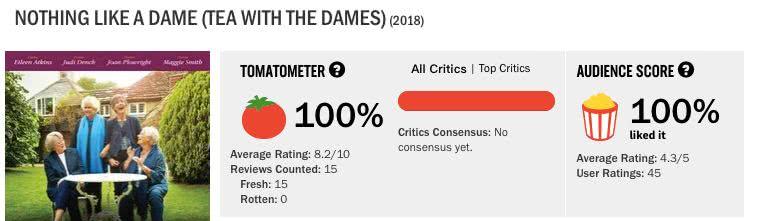嫁娶不须啼番外 嫁娶不须啼作者
《嫁娶不须啼》
作者:怀愫

简介:
新帝登位,旧太子党被绞革清算
裴家替裴观迎娶阿宝
人人都笑探花郎娶了个不识字的马伕女
婚后二人相敬如“冰”
一朝重生,裴观才发现
他娶是有所图,她嫁也是有所图
她前世早亡更是疑点重重
遂替林家出谋划策,请医问药,求她长命
阿宝自从阿爹升官,全家进京就好事不断
京城贵女所求不得的探花郎对她有求必应,百般关切
还几次替她避开祸事,又再三求娶
阿宝终于点头应嫁
可自从嫁给裴观,她便每夜入梦
这些梦,有时灵验,有时又完全不同
待她梦见裴观纳妾生子
而她一生无子,二十出头便病入膏肓
病榻前还有各路夫人以探病之名,行推销女儿之实
气得阿宝抽出马鞭:这探花郎谁爱要谁要去!
精彩节选:
连日阴雨压春,雨一收,桃堆锦杏翻霞,满院春意盖都盖不住。
阿宝甜睡正酣,绣房的门“呯”一声被推开。
陶英红扫一眼床上,扭头瞪戥子一眼:“都这个时辰了,怎么还不叫姑娘起来?”
戥子缩缩脖子:“我叫了,叫不起。”姑娘可骑在马上都能打瞌睡的主,她哪儿有法子把人拉起来啊。
阿宝分明听见红姨的声音,但她裹着被子在床上骨碌,就是不肯起。
连着赶了一个多月的路才到京城,这又是车又是船,骨头架子都颠散了。
陶英红只好自己上,跟戥子一块儿,把阿宝从被子里拖出来,按到妆镜前。
“今儿你爹要回来的,看你这猴子样子,还不赶紧收拾收拾!”
阿宝弹开眼睛,爹!她好久都没见过爹啦!
自穆王起兵南伐,爹跟着大军开拔离开崇州,都过去四年多了。
丫鬟捧盆上前,一人一边,先把她那层层密密的头发分成一络络,再拿梳子沾水,将头发梳顺,最后上篦子。
阿宝的头发浓密,还打着卷儿,要给她梳着京城里时兴的发式,可真不易。
陶英红看见她这头发就发愁。
原是放养惯了,如今眼看身份不同,就要订亲的姑娘家,这从头到脚,没一处乖顺。
都是叫打仗给耽误了!
今日怎么也得治治她这头发。
“哎哟!”阿宝一下被扯疼,捂住脑袋叫出声。
梳头的小丫鬟“咚”地跪在地上:“姑娘恕罪。”说着自己就掌起嘴来,左边一下打实了,右手刚挥出,便被阿宝一把逮住手腕。
阿宝瞪圆了眼,戥子张大了嘴,主仆俩的表情一模一样。
那丫鬟细白的脸上浮起三道红指印。
连陶英红都吓了一跳。
这一批人,都是才买来的。
现在买个人,便宜得很。
穆王打进京城,登上帝位,办完大事,再办小事。
大事便是将死忠于小皇帝的大臣们,绞的绞,关的关。
官眷下狱,奴仆发卖。
阿宝的爹叫林大有,原先就是个替穆王养军马的芝麻小官。穆王起兵,林大有一路跟随左右,积功升迁。
如今朝中大事刚定,林大有的新官职还没下来,田宅财宝已是攒了不少。
这宅子原是香料商的,被林大有买下。他又只有阿宝一个女儿,宅中最精致的绣楼当然归她。
阿宝昨日刚进京,兴奋得夜里都睡不着觉,还想爬墙头看看隔壁住了谁,被陶英红揪住耳朵狠狠打了两下:“你如今可不一样!不许上墙头!”
眼瞅着就要十四,光长个子,还皮得跟猴子似的,这以后可怎么说婆家?
阿宝一点儿也没觉着自己进了京城就不一样,看丫鬟跪下,她惊了片刻,“扑哧”笑出声来:“干什么呢你?”
戥子就从没跪过她。
有个机灵些的,把那丫鬟拉起来带到廊下去。
陶英红才刚当了半天家,也不知如何应对,只能绷住脸:“赶紧给姑娘梳头。”
看剩下的丫头都不敢使劲,干脆自己拿过篦子,梳到一半扯都扯不动,她一使力气,这祖宗还敢嚎。
气得撒开手,由篦子卡在阿宝头发上,没好气地道:“上刨花水。”
阿宝跳起来,捂住脑袋跟陶英红撒娇:“不要!红姨,你就饶了我罢,刨花水有味儿。”
刨花水服帖是服帖,太阳底下晒久了就一股臭树叶子味儿,她最不喜欢这些。
丫头们都是从犯官宅中卖出来的,就连她们平日都不用刨花水,如今听说要给“姑娘”用刨花水,都站住脚跟,不知怎么动弹。
还是戥子问:“是不是该抹点头油?”
“那就用头油,按住她,给我梳!”陶英红往榻上一坐,小丫头赶紧把引枕递到她手边,又跪着给她捶腿。
陶英红哪享过这种福,刚想叫她别跪,又怕这会儿软和了,以后不好治家,一时僵住。
只好在心里默念:进京了,封官儿了,不一样了。
几个丫头七手八脚要按住阿宝,阿宝一旋身,轻巧巧跳到绣墩子上,好险要给众人来个金鸡独立。
丫头们原来都是文官府上的奴婢,哪见过姑娘家这般生猛,当场愣在原地。
陶英红咳嗽一声,戥子适时递上软竹条,她接过去抖一下,竹梢在半空中“哔啪”一声脆响。
哪有如来佛治不了的孙悟空。
阿宝立刻老实,坐到绣墩上,让丫头给她通头发。
不光是阿宝老实了,屋里的丫头婆子更连大气儿都不敢喘。
她们见过兵丁打进城来,是个什么光景的。
春日花香再浓,也还未掩住城中的硝烟味。
来了两日,大家大概齐摸明白了,这家是武官,爷们儿都在营里忙,宅中只有姨夫人和大姑娘。
男人嘛,不管是贩夫,还是走卒,总少不了要讨老婆的。
往后怎么说不论,如今且只管讨好姨夫人。
“姨夫人,要不然,奴婢调个花露给姑娘用吧?”其中一个丫鬟猜测着阿宝的喜好,怯生生进言,“花露香得淡些,也不油。”
陶英红点点头。
她便调好花露奉上,因是春日,桃李正浓,用的香就要淡雅。
调上来还怕阿宝不喜欢:“城中别家也惯用花露的。”
阿宝放到鼻前一嗅就笑了,花露还真比刨花水强得多,终于肯让人收拾她的“狮子头”。
丫鬟见她喜欢,又细声细气说道:“姑娘若想养头发,也很容易,以后洗头先用蔷薇油搓,再用花露泡,日子久了,头发就软了。”
陶英红点点头:“你叫什么?”
“燕草。”
“以后你就在姑娘屋里,专管她这头发。”
几个丫鬟一看,争相进言,有会搭衣裳的,也有会梳妆的。
阿宝年纪虽小,身量不低,京中正实兴大袖,可她活泼好动,还是给她穿了件窄身小袖。
青碧色小袖配上芽白的裙,看着倒有几分大姑娘的样子了。
小丫头还取出一件同色的薄斗蓬,上青下白,绣着几只粉蝶儿,正该是她这年纪用的。
阿宝不畏寒,摇手:“我不披这个。”
陶英红左看右瞧,越看越笑:“可算有个人样子了,能见你爹了。”
阿宝换上新衫,还问呢:“爹使人新给我裁的?”
“是外头现买的成衣,一屋一箱子,给咱们穿的,也就这件合适点。”好在还知道人来了得吃饭穿衣,先给预备下了。
陶英红说完这句,刚要起身,眉头一皱,口中轻“咝”,伸手按住额角。
阿宝一看就知她又害头风了,赶紧挨过去:“红姨,你又头疼啦?”
连着一个多月的车马劳顿,陶英红一直强撑着,还以为进京就享福了,谁想进京才是真的头痛。
宅子有了,下人也有了,可该怎么料理,她没一点头绪。
昨日进京,林大有让腾字营的兵丁在城门口接,给了她一个匣子一串钥匙,人影都没见着。
这里房子又大,人又多,昨儿夜里乌压压一片人出来请安,还吃喝拉撒都要她拿主意,她怎么能不头疼。
阿宝扶住她,两指相叠,指尖微微用力,替陶英红揉着额头:“那红姨歇歇罢,家里事儿我来管。”
害头风一点办法也没有,只能靠静养,不能多劳动。
陶英红又疼又忍不住要笑:“你来?家里这许多事儿,你能来得了?”连她都发怵,阿宝才多大,她能知道什么。
阿宝看陶英红笑完又把眉头皱得死紧,知道她这会儿疼得厉害,放眼一看,家里都是新来的。
除了她,就是林伯和戥子,林伯老了,戥子还小,只有她能顶上。
遂挺起胸膛打包票:“我能行,不就是管家嘛,我原来也管过呀。”
陶英红揉着额头,又嗞一口气儿,这哪儿能一样呢?
在崇州时,林大有官衔小,林家就住在王府后街的四方小院里。浅浅的几间屋子,用着一个老仆,两个婆子,两个丫鬟。
陶英红一害头风,家里就由阿宝管。说是管家,不过就是买米买面切点肉,再抓两帖药罢了。
一整个四合院,都还没这绣楼的前院大。
“这有什么难的。”阿宝一点不慌,夸下海口。
陶英红听她这话就额角直跳,又实没精神再跟她缠,想着让她见识见识也好:“那让林伯领着你,先把人数出来,再把饭安排了,等我好些再说。”
小丫鬟送上巾帕热敷,扶陶英红躺下。
阿宝带上戥子,大步迈出绣楼。
几个丫鬟还等着姑娘给起新名字呢,不知该不该跟。只有燕草,阿宝一动,她即刻跟上,余下几个就跟在她身后。
阿宝刚走出垂花门,扭头一瞧,身后跟着一串丫头。她觉得好笑,哈哈乐了两声,又赶紧忍住:今天她管家,得绷住喽!
林伯听说陶英红害头风,为难起来:“这怎么好……”
抓药都摸不着门。
阿宝一摆手问:“家里有多少人?”
看林伯也答不出来,打开匣子,拿出一叠身契:嚯,这么多?
阿宝伸手想挠挠脸的,又收回来,坐得极端正,轻点下颔:“把人全叫出来罢。”
先择了几个力壮的,将堂屋里那张梨花长案抬出来,在堂前一摆,铺上笔墨纸砚。
宅中下人按男女排成两行,阿宝粗粗一扫,约摸得有三四十人。戥子站在阿宝身后直咋舌,以后家里要用这么多人啊?
再给林伯设座,让他拿一张身契,念一个名字。
阿宝清清喉咙。
戥子立时送上茶盏。
她接过去,似模似样吹上几口:“报到姓名的,依次列队上前,各自再报姓名、年纪、籍贯、有何长处,原先在哪家效力,各自领多少月钱……”
有敢扯谎的,就都弃用。
说着又扭头对戥子道:“你去寻个木梃来。”
木梃是崇州征兵时,用来给兵丁量身的木杆子。
戥子原就越听这调子越耳熟,这要是再挂上幡,不就是营中征兵呢嘛?她眨巴着眼睛,征兵是得量身不错,可这会儿要木梃有什么用?
看戥子脑子没转弯,她脚尖轻跺一记:“那不还得裁衣裳嘛!”
进了哪个营,就得穿哪个营的军服啊。
这三四十人中,大多是被主家牵连发卖的奴仆。见到新主家刚进京来,连买药都摸不着门,出来管事的,又还是个十三四岁面嫩的姑娘家,难免动了些偷懒糊弄的心思。
眼见阿宝大刀阔斧来这么一手,又听见她对林伯说:“咱们用不了这许多人,选些好的,余下的还回去,岂能给人白吃饷。”
两排人立时站直了,哪还敢有半分轻忽之心。
宅中很快就理出头绪来,林伯让常在城中跑腿的小厮,出门去找还开着的药铺,买了药来。
厨房煎上一碗,戥子赶紧给送到后院去。
陶英红端着药碗:“姑娘在前头干什么了?”没大闹天宫吧?
戥子想了想,说是在管家罢,又实在不像。
最后她说:“姑娘在征兵呢。”
陶英红喝了药昏昏欲睡,直睡到晌午才醒,一醒便有人送上饭食。
因她害头风,厨房送上的吃食很是清淡,清粥配几碟小菜。她自己没吃,先问阿宝:“姑娘呢,她吃什么?”
燕草回话:“姨夫人放心,姑娘在前头摆了膳。说是用了午膳,要开库房造册。”
把阿宝说得很忙活,其实阿宝跟戥子两个,正在前面商量着要吃羊肉。
二人说什么早韭嫩晚菘肥,正该是吃韭菜的时候,让厨房给做韭菜春饼,再烤点羊肉串起来吃。
还特意嘱咐别叫陶英红知道。
上午理清人事,从四十来人中选出二十个,余下的退给人牙子。又以五人为一伍,说是日后方便管理。
不过一个时辰,这二十来人的住的屋子,拿的月钱,春日里要裁衣裳,就都有个大概了。
这些丫头婆子们,也是官家富户中出来的,也都见过别家太太姑娘如何管事,如何主持中馈。
可哪一个能像林家姑娘这样,三两下就把宅院收拾出个大概章程。
这会她说要吃韭菜羊肉,没人敢说不。
厨房为了讨她喜欢,还特意又做了韭菜酥盒一起送上。
阿宝立即献宝,拎着食盒到后院来,进门就往陶英红身边一挨,掀开盒盖:“红姨,你快闻~香吧~”
面饼子里揉上猪油,再裹上韭菜鸡蛋馅,上锅一烘就起酥了,食盖一掀,满屋都是香味,正好给陶英红配粥吃。
陶英红嘴里淡得很,送上来的小菜又不咸又不辣,没一点滋味,瞧见韭菜酥盒才胃口大开,连吃两碗。
身边的丫头们赶紧记在心中,如今的主家,没有那病了便要清肠素几顿的规矩。
阿宝手里拿着册子,交给陶英红:“留下这些人足够用了。”
册子分成两本,一本男一本女,每页上还写着串字,陶英红问:“这是什么?”
“各人的标号啊。”军中兵丁军械粮草,就连军马的马蹄子上就有记认,病了伤了,立时就能查册子。
阿宝依样画葫芦,以后有什么事儿,查起来方便。
一桩桩念给陶英红听:“从哪家出来的,以前的月钱是怎么领的,也都记下来了。”
月钱发多少,衣服裁几套,都由陶英红来定。
陶英红看看册子,又看看阿宝,真是不经事不知她这么能干:“你……你这是怎么想到的?”
她怎么一点都不怵呢?
“就这么想到的呀,营里几千几万的兵,照着法子都能管束,咱家里才多少人啊。”
陶英红笑看她,早上还觉着她孩子气,这会儿再看,又觉着这一路从崇州到京城,到底经过见过,懂事多了。
阿宝算不上是美人相貌。
她的眉毛、眼睛、鼻子、嘴,长得全不是标准美人的样式。
眉深浓,尾带峰,黑白分明一双凤目,鼻头微微有肉。
是讨喜的,但也一打眼就知是个极精神,极有主意的人。
陶英红感慨吾家有女初长成,刚想伸手摸摸她,一眼扫见她碧色衣袖上沾着几点油花,再一闻:“你偷吃羊肉啦?”
阿宝缩头不及,脑门还是被戳了一下。
“偷吃都不晓得擦嘴,这才刚上身的衣裳就脏了……”要念叨她两句罢,看看手里的册子,又笑又叹,到底还是小孩心性。
“可不是我自己贪嘴啊,是给爹和阿兄预备的。”她也就偷吃了那么二三四五串而已。
“不是不给你吃,是你吃完就上火,嘴里又要生疮疡。”到时候捂着腮帮子叫疼,受罪的不还是她自个儿。
“那倒不怕,已经叫厨房在煮菊花脑了。”燕草适时开口,看她们不明白,笑说,“京城人到了春日爱吃七头一脑,其中菊花脑煮汤最败火,寻常吃了燥的火性大的,喝一碗就好了。”
俨然已是阿宝房里的大丫头。
这回进京,阿宝身边只有戥子一个,她跟戥子又从来是一个鼻孔出气的,倒是该给她把人配齐。
陶英红之前还生怕阿宝弹压不住这些京城官家富户中出来的丫头们。
这会儿也放心了,都交给她管。
“不着急别的,你娘的牌位先摆出来。”
“早摆上啦。”收拾出屋子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把她娘亲的牌位摆出来。
香炉、供果、点心都是新置办的,让她娘也尝尝京城的点心果子。
家里的规矩,新鲜点心都要在牌位前摆一摆,才能分到孩子们嘴里。
“姨父的牌位我也摆上啦。”
陶家上一代就替王府养军马,陶老爹只生了两个女儿。也不说招赘,挑年轻壮实的后生当女婿。
把他一肚子马经教给女婿。
先是阿宝的娘走了,跟着陶英红的丈夫也没了,两家人本就一个四合院里住着,剩下的互相照应,搭伙过日子。
陶英红头疼才好些,立时去给姐姐亡夫上香。
阿宝跪在蒲团上,仰脸看看牌位,她都已经不记得她娘长什么样子了。
“赶紧跟你娘说说话!”
阿宝跪正了,双手合十,苦思一番:“娘啊,我又长高了几寸……今儿吃了羊肉……我的鞭子也越使越好了!”
陶老爹一手好鞭法,不仅教了两个女儿,还教给了外孙女。
陶英红在灵牌前跟姐姐说阿宝长大了,再寻一门好亲事,就算对得起姐姐的嘱托。
对着亡夫的牌位,她红了眼圈,上回见儿子还是四年前,也不知道他在外头吃没吃苦:“有姐夫看着他,我也放心。”
絮絮说了许多,才一抹眼泪:“过几日打听个灵验的寺庙,给你娘你姨父点盏灯。”
上完香才跟阿宝一道开库房。
一只只箱笼打开,阿宝跟戥子齐齐咽了口唾沫。
戥子张大眼,刚要赞叹,看了眼燕草,怕被燕草看笑话。见燕草只管低头盯着鞋尖,这才凑到阿宝耳边才小声轻叹:“好多金子啊。”
发大财了!
阿宝长这么大,还从未见过这么多金银绸缎。
有些是穆王分功行赏,有些是豪绅富户送的礼。
比如卖林家宅子的香料商,宅子折价卖,家具全都白送,库中来不及运走的香料,也都送给林家。
只求让林大有能派两个腾字营的兵,送他们出城门。
光这些箱子里的东西就记到掌灯时分。
阿宝先还劲头十足,见着什么好的都要仔细看看,七八只箱子翻下来,她没兴致了,只想满院子溜达。
但陶英红格外用心,看到合适的就单列出来,存起来给阿宝当嫁妆。
还没忙活完,林大有回来了。
阿宝跑出去迎接,她拎着裙角跑得飞快,除了戥子,没人跟得上她的脚程。燕草跑两步便喘,扶住垂花门的柱子,三个丫头互相望一望,谁也不敢在背后议论半句。
“爹!”阿宝跑到门边,脆生生喊。
四年多不见,爹的胡子还是这么毛炸炸的。
“哎!”
林大有方才差点不敢认门。
门前灯笼也挂起来了,下马有小厮来牵,进门又有热茶热巾。下人各司其职,见了他,都躬身叫老爷。
林大有进了京城就一直扎在营中,宅子下人都有了,可还没当过老爷。
韩征紧跟其后,瞧见阿宝“嚯”一声,伸手比划:“小丫头都长这么高了?”
阿宝差点认不出他,人晒得黝黑黝黑的,站在灯下都不显得白,绕着他看一圈儿:“你这会儿比滇马高几个头了?”
“呸!”韩征伸手就要揪她小辫子,再一看,她如今不梳小辫了。
韩征一伸手,阿宝就知道他想干嘛,吐着舌头往后跳,一把挽住她爹的胳膊:“爹,今天有韭菜酥盒,还有烤羊肉呢。”
厨房知道老爷回来了,特意备了下酒的凉菜,大姑娘吩咐的,猪头肉和炸花生不能少。
林大有坐下大嚼,长叹一声:“这才是过日子。”
阿宝还跟她小时候一样,挨在桌边陪阿爹吃肉,自己挑半肥不瘦的,把太肥的全往她爹盘子里拨。
林大有挟着就吃了。
韩征先到后院去看陶英红。
母子见面,陶英红眼圈一红:“快给你爹上柱香。”
韩征上香拜倒,结结实实磕三个头。
陶英红这才拉他起来细看,瘦了黑了,也精神了:“娘给你做的鞋子,你收着没?”
当兵的最费鞋,陶英红只要有空就做鞋子给儿子。崇州小院收着一箱鞋子,偶尔也有机会往前线捎带,可这种东西,能不能到都看运气。
韩征自然没收到过,可他舍不得娘伤心,点头:“收着了,就是后来我脚大了,穿不了。”
陶英红是照着亡夫的脚寸做的,低头看看儿子的脚,已经他爹宽了:“你比你爹生得高。”
“我看阿宝也高了,高了这许多。”他拿手比划一下。
“那可不,她长得可快着呢。”不见的时候不想着,一见到儿子,陶英红就想到两个孩子的亲事。
何必到外头去寻呢?
“你姨父呢?在前头吃酒?”说着就带儿子到前面。
一家人隔了四年,终于又坐在一起吃饭。
“咱们腾字营,头一个打进宫城,好家伙,你是没瞧见皇宫有多气派!”韩征一面吃肉一面跟小妹妹炫耀。
“那你见没见到妃子?”崇州人人都知小皇帝要杀穆王爷,王爷起兵南伐的时候,连三岁小儿都能背檄文。
据说小皇帝穷奢极欲,最好女色,一年便要一采选。
“那倒没有,都在大殿里关着,我听人说,个个都长得跟天仙似的。”他们将皇城团团围住,还是没能活捉小皇帝。
小皇帝一把火烧了崇英殿,直烧了三天三夜,只捡出几具烧焦的人骨。
为了这,到现在腾字营的封赏还没定下来呢。
阿宝哪听过这些,她微张着嘴,不住问:“还有呢还有呢?”
陶英红看两个孩子凑在一块说个不停,微微笑了。
这要是能亲上作亲,该多好。
林大有也在看女儿,离家的时候,她才有马腿高,几年不见都比马笼头高了。
他嚼块猪头肉,又大喝一口酒,放下酒盏,对陶英红笑道:“已经有好几家,来跟我说亲事了。”
裴家堂前有两株百年玉兰,花开时玉盏万朵,如月中堆雪。
京城无人不知裴家这两株阆苑羽衣仙,每岁花时,裴府总会摘下玉盏分送亲友。
今岁玉兰又到盛时,无人摘折,玉瓣锈地。
裴观大病初愈,脸色微白,披着件石青斗蓬大踏步走在前面。
小厮提灯追着他照路,书僮松烟抱着手炉赶上,一行人在夜中疾走,谁也不敢出声。
城破之前,公子骤然病倒,病势汹汹,梦中还不住说着听不懂的糊话,把老夫人急得昏死过去。
下人们先是怕主家获罪,要被拉出去发卖。
等到城中日渐安稳,公子的病还不好,就又都在暗暗猜测,难道裴家预备要发两次丧?那可真是倒了横梁又倒金柱。
裴观一脚踏在满地玉兰瓣上,行过“克嗣徽音”的匾额,疾步走进祖父书房内。
书房后室烧着两个碳盆,裴如棠躺在摇椅上,腿上盖一条羊毛褥,怀中抱着手炉,还觉得春寒侵骨。
见孙子来了,对他微微颔首。
裴观刚要躬给祖父行礼,裴如棠沉声道:“你过来。”
裴如棠缠绵病榻多时,早已身似朽木,面如枯叶。
低头闷咳几声,喉中痰意难尽。
裴观赶紧奉上清茶,又捧起水盂送到祖父口边接痰。
裴如棠摇头不用,伸手拉开枕边格扇,取出一张纸笺。
嗡声道:“你与宁家的亲事不成了,这些是我替你选中的,你自己择一个。”
一张雪浪笺上,三五个名字。
裴观还记得祖孙俩的这场谈话,也记得最后祖父为他选定了林家女。但他当时并不能全然明白祖父的苦心。
等到明白过来,也已经走了许多弯路。
裴如棠见孙子默然,喉间一响,吐出口浊气:“咱们家眼下有两条路可走,你可知是哪两条?”
裴观抬眉:“第一条是辞官还乡。”退居田园,或可保得几日太平。
“第二条是忍辱蛰伏。”伺机而动。
裴如棠阖上眼:“你选一个罢。”
这是祖父临终之前给他的试炼,但他当年没能通过,祖父必是心灰丧气,很快就撒手离世。
裴观伸手接过,捏着那张纸笺,粗扫一遍,林氏的名字藏在其中。
其实他不必非选林氏,祖父将差不多的人选都算在内了,这些人后来是升是贬,官居几品,他自有本帐。
但再看一次,林氏也依旧是最佳选择。
“我选林家。”
但见裴如棠精神一振,他睁开眼,看着孙子缓缓颔首:“你明白了。”
他这个孙子,自来极看重读书人身份,先头的宁氏又是打小看好的人选,门第品貌才情,样样都是天作之合。
而这张纸上的人,旁的暂且不论,只论门第,没一个堪与裴家相配。可如今孙辈中最拔尖的人材,也只能在这里头挑。
原还怕他书生意气,压着他娶,不如让他心甘情愿的娶。
“孙儿明白了。”
裴观口中的明白,不是一时的明白,而是到他中年,才明白祖父临终之前,在棋盘上留了个活子。
但他当年心高气傲,处处被人耻笑探花郎娶了马夫的女儿,与林氏并不相偕,白费祖父一番苦心。
裴如棠握住孙子的手:“我去之后,族中这些人该打发回老家的就回老家,该容让的容让。”握着他的手使一使劲:“不要手软,不要拘泥。”
裴观微诧,这一句,上辈子祖父并不曾对他说过。
也确如祖父所言,他虽留下遗命,但依旧生出许多祸端。
“早知今日,便不该让你应试。”
旧皇帝跟前的探花郎有什么用?连主考官都下狱了,座师无人,同窗四散,独木难支。
“要是你爹还活着……”裴如棠徒然一叹。
裴观反握住祖父的手。
裴观大病一场,重回年少,一睁眼就回到裴家风雨飘摇的时候,他正有太多的遗憾要弥补。
“祖父有什么事都交待给我来办,且安心养病罢。”
亲手喂完药,扶祖父睡下,他才从书房中出来。
外面不知何时又下起雨来,又打得玉兰枝颤花摇,僮儿打起伞:“公子,您就拿着手炉子罢,身子要紧。”
裴观接过手炉,他掌心烫得很,不止掌心烫,浑身上下一股热劲难散。
方才来时,疾步而行,回去的路却走得极慢。
雨丝扑面,他并不伸手拭去,一任急雨顺着眉梢往下。
年十六点探花,二十六才谋职外放,三十六岁死在任上。
他从没有心绞症,怎么那夜一杯茶后,心如刀剜,倒下时,四周竟无一人。
裴观沉眉敛目,转过月洞门去。
三十六岁死,他的悼词中该用“宝剑光沉”“风催椿萎”。
再睁开眼,回到未出仕时。
雨越下越大,书僮不敢催促,他打小就侍候公子,平日也敢玩笑两句。可这回公子病好之后,脾气都变了,眉目冷冽,不苟言笑。
老夫人和夫人都说公子这是经过事,更有大家风范了。
只有贴身侍候的人最能知道其中变化,喝的茶,吃的菜,素日里穿的衣裳,就连熏的香都不同了。
简直就像,就像换了一个人。
裴三夫人正在房中等儿子,裴观一进门,她站起来:“怎么还淋了雨?”赶紧让小丫鬟送上巾帕,“快,快喝盏姜茶,祛祛寒气。”
裴观只觉得心头有火在烧,他压根不觉得冷。
是谁下手?太子的人?
他接过碗去一饮而尽,裴三夫人还怕儿子辣了嗓子,把蜜饯果子推过去:“外头,是不是已经安定了?”
该削的削了,该退的也退了。
老爷子眼看穆王壮大,上表辞官,闭门谢客,又替两个儿子谋外任当闲差,大撒银钱,这才勉强保全家族。
比起别家,裴家已是大幸。
“娘不必担心,外头差不多安定了。”余波难平,新帝在未来十数年都还在算旧党的帐,安定?哪有这么容易安定。
但裴观不想吓到亲娘,何况前头的事,自有男人顶着。
妇人本就该在后宅安享太平。
“那你祖父叫你去是说什么?他身子如何?好些了么?”家中人人噤若寒蝉,大爷二爷被贬官外仼,老四原就领着闲差,五爷没出仕。
一家子人都怕裴老爷此时撒手。
“祖父叫我去,是论婚事的。”
裴三夫人神色一黯,她极喜欢宁氏,可宁父获罪下狱,也不知是要杀头还是要流放。
建安坊这一路过去,隔几家便能见到贴着抄家的白条。
裴家堪堪自保,再无余力救人。
“说哪一家?”若有了人选,还得她来操办。
“太仆寺少卿林家。”还未任命,但他这位岳父确实是官任太仆寺少卿,后来又被调去行太仆寺,专管军马。
“林家?”短短半年,裴三夫人鬓边已添银丝,她想了许久也没起这家人来,“哪个林家?”
“是此番新进京来的,林家。”
裴三夫人明白了,是新贵。
如今清贵不贵,新贵才贵。
太仆寺少卿,四品官。自己的儿子少年探花,前途无量,前头的宁家是什么底蕴,这个林家……原先怕是根本无官无职。
裴三夫人为儿子抱屈,但怕触动儿子的伤心事,硬生生忍住,咬牙道:“进了咱家的门,娘自会好好教导她,让她能担得起裴家妇。”
裴观一点也没犹豫,点头应是:“那是自然,交给母亲,我很放心。”
他已然记不得林氏的相貌了,只记得林氏不擅文墨,但她治家有方,母亲就曾夸过她好几回。
可惜早早病故,也没能留下一儿半女。
林氏病故的时候,母亲很是伤心。
裴三夫人见儿子神色如常,还当他为了让她安心,在极力抑制。
“子慕,忧伤肺,思伤脾,你身子才刚好,万不可再过于忧心了。”裴三夫人口中虽劝,自己心中也不好受。
真是太可惜了。
裴观点点头:“儿子明白。”他根本不知母亲在说宁氏,只一心回想这几年发生的事。
迎娶林氏之后,他就出仕了。可因为裴家在先帝时就拥嫡皇子上位,一直不受新帝信任,得不到重用,在冷衙门里苦耗光阴。
好不容易投效齐王,才某职外放。
太子和齐王争了十数年,十二皇子异军突起。
裴观心中掐指,十二皇子这会儿应当开始学说话了。
正想得出神,胸中一阵滞闷,垂头咳嗽两声。
“子慕,万般都是命,你若实在放不下,咱们使人疏通疏通……”裴三夫人急起来。
“母亲在说什么?”裴观不解。
“当然是在说尔清了。”说到宁尔清的名字时,裴三夫人放缓了声调,唯恐触及儿子心事。
裴观恍然,他已经很久没想到过这个名字。
娶了林氏之后,许多年中他都时不时会想起宁尔清,但林氏病故之后,他就再没想起过了。
“你?你方才没想尔清吗?”
“是该疏通,我来想法子,母亲不必担心。”
裴三夫人一时无言,儿子应当是极喜欢宁氏的呀?
两家虽未定亲,但也只差走个行式了。要不是因为守父孝,宁氏已经进门,可若宁氏真进了门,裴家有这门姻亲,只怕又要再脱一层皮。
裴三夫人心中,虽则叹息宁家的命运,但也还暗自庆幸。
幸好,幸好没定亲,要不然裴家又要背负个背信弃义的恶名。
“陈妈妈,夜深了,扶母亲回去歇息。”裴观起身躬送,“明日我再给祖母母亲请安。”
宅中人惶惶多日,慢慢又都按着原来的轨迹过日子。
裴三夫人走在廊下,陈妈妈扶着她胳膊,她走几步又回头望一眼儿子,就见儿子还立在门边,低头不知思索什么。
“他,他原先并不喜欢宁氏么?”她还以为给儿子挑了个称心合意的妻子呢。
陈妈妈是裴三夫人的陪嫁丫鬟,打小看着裴观长大的,一样心头纳罕:“观哥儿定是怕你伤心,明日把松烟叫来问问。”
裴观见母亲转过廊角,这才回房:“松烟,磨墨。”
松烟也不敢问怎么这么晚还要读书作文章,铺好纸磨好墨,立在一边侍候。
“出去,把门关上。”
“是。”松烟头都不敢抬,退出去紧紧掩上门。
裴观抽出一支狼豪细笔,将他能想起来的,都细细写在纸上。
灯罩中蜡烛换了又换,到天色既白方才停笔,拿起来粗扫一遍,又提起笔来,在林氏的姓名旁边,写下一行小字。
“年二十三,北堂春去。”
,免责声明:本文仅代表文章作者的个人观点,与本站无关。其原创性、真实性以及文中陈述文字和内容未经本站证实,对本文以及其中全部或者部分内容文字的真实性、完整性和原创性本站不作任何保证或承诺,请读者仅作参考,并自行核实相关内容。文章投诉邮箱:anhduc.ph@yahoo.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