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春新视界女儿和被撕得粉碎的爸爸(青春新视界女儿和被撕得粉碎的爸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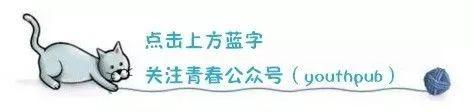


作者简介

慢三,1982年出生,现居苏州。曾干过电视台记者,节目策划,影视编剧,如今专职写作。已出版小说集《这么大雨你还要去买裤子吗》《尴尬时代》,长篇小说《影子里的恋人》《暖气》《尾气》等。女儿和被撕得粉碎的爸爸
慢 三
就这样,持续上了三四节课后,我逐渐对每一个孩子都有了一些初步的了解。他们中有的内向沉默,有的开朗活泼,有的话多得不得了,有的则缺乏专注度,一直被课堂之外的事物吸引注意力,但本质上都是品质很好的孩子。在课堂上,我使出浑身解数,尽力让自己表现得好玩一点,搞笑一点,放缓自己说话的速度,适当开一些他们能听懂的玩笑,偶尔为了纪律也摆出一副威严的态度。总之,我能感觉到孩子们逐渐对我产生了信任感,这点从他们看我的眼神中就能一览无遗。而我也在自我反思,活了这么多年,我从未有过这样的轻松、愉悦以及自省的时刻。这间二十平方米不到的教室如同一处避风港,让我每周都有机会从生活的烦扰中逃离,来此避难,获得短暂的心安。这完全出乎我最初的预料。一种为人师者的自满开始在我内心中悄然滋长。
然后就到了那节课。
出于某种试图去疗愈对方的目的,我出了一道名为“信”的作文题目,要求大家给自己最想念的人写一封信,可以是现实中的人,也可以是虚构的卡通形象,总之对象是开放的,但尽量写出真情实感。我的教室和传统意义上的有所不同,除了靠墙有一排书柜和一台用来讲课的液晶电视外,仅屋中间有一张长约三米、宽一米二左右的大木桌,八个孩子围桌而坐、埋头写作的样子就像在食堂吃饭。我叮嘱他们认真写,然后拉开教室门走了出去,到楼下室外去抽根烟。当第一口烟进入肺部时,我突然想起了我的女儿蓓蓓。自从在这边开课以后,因为周末被占据,我已经差不多有一个多月没有见到她了。她长高一点了吗?吃饭还是那么挑食只爱意大利面?数学的除法余数问题有没有搞懂?想着想着,我不觉伤感起来。这份伤感源自我的失败人生。我二十岁出头就认识了前妻,她是我的初恋,我们在一起生活了将近二十年,知根知底,而随着生活的品质始终无法突破,感情也在女儿出生之后急转直下,焦虑、争吵、互相伤害愈演愈烈,直至离婚。事后,冷静下来的我们也谈论过,如果没有生孩子,我们会不会好一点?会不会像以前一样,相互理解,相互扶持,过二人世界,哪怕生活贫苦一点也无所谓?讨论的结果是,也不会的。击垮我们的并不是我们可爱的女儿,不是不断增加的生活成本,而是多年来一直没有起色的人生。还有就是我们已不再年轻。我们步入了中年。中年要面临的危机并不是感情,而是全方位坍塌的天空。我们顶不住了。或许金钱会给我们一点力量支持,但赚到足够的金钱对于我这样的人来说,实在太难太难了。
图摄@大宝乐
基于这样的认识,我们虽然痛苦,但离婚时还算平和,并且,这种平和持续到了婚后。离婚两年以来,我们偶尔还会一起带孩子出去玩,吃顿饭,像一家人一样。但我们(包括蓓蓓)心里都非常清楚,这三个灵魂永远不会再组合成家庭了。没有为什么。
我拿出手机,给前妻拨了个电话。今天是星期六,天气这么好,她应该带女儿在外面玩。我只是想听听女儿的声音。电话响了很久。在等待的过程中,我看见一辆保时捷卡宴停在路边,没有熄火。车身是翠绿的颜色,非常好看,很正,一看就是那种好车才能喷制出来的漆色。车窗开着,一位年轻、漂亮、戴墨镜的短发女人正坐在驾驶座上,低头在玩手机。
“喂?”前妻的声音从听筒里传来,我从中听到了疲惫。
“Hi,最近怎么样?”
她没有回答我,似乎在忙什么。
“在吗?”
“啊?你说什么?”她心不在焉,“不好意思,我现在在外面。”
“我知道你在外面。蓓蓓在吗?”
“她在和同学玩。今天约了同学一起,在公园野餐。”
“哦。我能和她说两句话吗?”
“你等一下。”
我听见她在喊蓓蓓的名字,等了几秒钟。
“她不愿意过来,正玩得开心呢。”
“你跟她说是爸爸……”
“喝饮料吗?”
我愣了一下。是一个男人的声音。
“不喝,谢谢。”她回到电话里,“要不你晚点打来吧,这会儿……”
“知道了。”
我迅速挂断了电话。一辆交通协警的电瓶车停在了那辆保时捷旁边,协警对着那短发女人比画着说些什么。那女人一边解释,一边指了指我的方向。我猛吸了一口香烟,把它扔在地上,转身朝楼里走去。
图摄@大宝乐
孩子们大多数都已经写好了。从一开始害怕动笔,到现在每节课都能写出点东西,短短一个月,他们的进步可不小。我一一把他们的文章收上来,然后告诉他们可以看会儿书,等待家长来接。当我最后准备收一个叫毛羽的小女孩的文章时,她说自己还没写完,要等一会儿。我让她别着急,慢慢写。
然后我在椅子上坐下,开始看他们写的信。因为都是二三年级的孩子,刚学会写字,所以大家的文章不仅短小,而且很多字都是用拼音表示,错字错句也非常频繁。对此,我不打算去纠正他们。我的想法是,在这个阶段,自由表达比写正确字句要重要得多(也许是任何阶段?)。让我欣慰的是,每个孩子都写得不一样。有一个小男孩,他给奥特曼写了一封信。他问奥特曼,你每天都打怪兽会觉得无聊吗?如果有一大群怪兽围着你,而你打不过该怎么办呢?一个小女孩写给自己曾经的老师:老师,你为什么转到实验小学去了?是不是因为我们这个班太吵太闹了?还有一个小男孩让我捧腹大笑,他给胡萝卜写了封信,告诉它能不能每次看到自己妈妈的时候都躲起来,不要被妈妈买走,因为这样他妈妈就不会给他吃胡萝卜了。他实在太讨厌吃胡萝卜了。
看着这些孩子的信,我再次想到了蓓蓓。有很长一段时间,我都会靠在床头,给她讲绘本故事,而她也是这么天真,这么情感充沛,想象力丰富且问题不断。有一次,我骑电瓶车带她,她跟我说,自己的头发被风吹得飘了起来,就像有仙女在天空中给她梳头发。多么美好的比喻啊!还有一次,我让她吃南瓜,她不喜欢吃,就说自己不要吃南(男)瓜,要吃女瓜,因为她是女孩子啊。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但是现在不可能再有了,而且,她还会有新的爸爸——想到这,我就很难过。一切都是我的错,要是我努力一点,勤奋一点,多赚点钱,让家人的生活变得更好一点,也许现在会是另外一种局面。如果我……
“老师!”
我一惊,抬起头来,看见毛羽正举着手中的稿纸,朝我挥舞着。
“老师,我写完了。”
我点点头,站起身,朝她走过去。她把稿纸递给了我,我下意识地扫了一眼。
“有写名字吗?”
“噢,忘了。”
她又从我手中夺回了稿纸,然后在文章的结尾飞快地写上了自己的名字。
“老师,下课了吗?”
我看了下时间。
“下了,不过你家长好像还没来。”
“我妈妈给我发消息了,她在路边等我,让我下去。”
她举起了手腕,那上面有一只粉色的电话手表。
“好吧,那你小心一点。要不要我陪你下去?”
“不用了。谢谢。”
说完,她起身把椅子推进桌子下面,然后说了声“老师再见”就出了门。随后,那些其他孩子的家长们也纷纷到了。他们把孩子们带走,去某个快餐店简单填饱肚子,然后匆匆赶赴下一个培训班。
我把教室简单收拾了一下,关上灯,跟老板打了声招呼,也离开了。在面馆吃了面,我拿着电脑去了一家常去的星巴克,点了一杯热气腾腾的美式咖啡,开始继续写我的科幻悬疑小说。不知道为什么,我在家里一个字都写不出来,只能在咖啡馆里写。当我一个人的时候,我会不由自主地变得非常消极,只想睡觉、看书、看电影,其他什么都不想做,完全失去了自控力。我也不知道自己这是怎么了。我偶尔会觉得自己已经差不多完蛋了,可有时候又乐观地认为还能坚持下去。我会在门窗紧闭的黑暗中莫名其妙地哭起来,觉得好累,活着没什么意思,但一想到自杀,又害怕得要命。
所以我尽量让自己待在人群中,光线越好、越嘈杂的地方我越自在,或者说越安全。我的科幻悬疑小说就这样一点点缓慢朝前推进着。它讲的是在经历了宇宙浩劫之后,地球上最后一个人类一边要想办法生存下去或者繁殖(无性繁殖技术),一边还要竭尽全力保留艺术的故事。故事的主人公小卡认为艺术是人活下去的意义所在,否则还不如灭绝算了。我正写到,他捡到了一个手机,手机曾经的主人在里面存了大量的电影原声音乐,但遗憾的是,他才听了两首曲子手机就没电了。他没找到充电器。于是,他弄了一根电线,开始研究怎么做一个充电器。终于他做好了(过程略),然后接上汽车的蓄电池,开始给手机充电。在这个过程中,他饿了,用过期的罐头和发霉的面包给自己做了个三明治,吃完之后,手机自动开机了。他点开屏幕,找音乐库,刚要放歌,手机突然响了,把他吓了一大跳。有个电话打进来了!他犹豫了半天,颤颤巍巍按下了接听键。喂。电话那头传来了一个小女孩的声音……
写到这儿,我停了下来,看了一眼坐在我斜对面那桌三个正在说话的人。两女一男,其中并肩而坐的一对中年男女显然是夫妻,而坐他们对面的那个女孩,应该是保险推销员。她正在给面前的客户推销一种得了重病就会有大额赔偿的重疾险。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这些推销保险的都喜欢来星巴克谈生意,我已经见过不下十次了,但幸运的是,从没有人来向我推销过。也许我长着一张买不起保险的脸?谁知道呢。我合上了笔记本电脑。不写了。不是我有意控制我的写作冲动,而是我也不知道接下来的情节会怎么发展。我写的是悬疑,所以必须要弄点悬念,而且这狗屁悬念最好能把我自己也唬住,这样我才有信心保证读者也猜不出来故事往后的发展。
(精彩继续)
*全文刊发于《青春》2021年第12期
~~转载请私信后台
创作谈
向上滑动阅览
关于这篇小说本身其实没太多可说的。它采用第一人称叙述,现实细节处处可见,看起来像是真实发生过的事情,但纯属虚构。我的确年近四十,也在周末时间给一些孩子上写作课,生活常常被不如意笼罩,却并没有遭遇文中主人公那般的悲惨境遇(家庭破碎)和尴尬人生(父爱泛滥)。把真实生活戏剧化是我经常喜欢在写小说时干的勾当,虚虚实实,半真半假,用结实的砖头去垒一所虚无缥缈的房子,既贴近人物,又时刻抽离出来保持审视,从而获得写作的乐趣。
值得一说的是我这几年的写作状态。从三四年前开始,出于谋生的考虑,我开始转型专攻类型小说。在这几年里,我几乎停止了创作短篇,而是埋首写一些一惊一乍的悬疑犯罪长篇。我的写作逐渐变成了一种对类型技艺的训练和打磨。写作成了工作,成了糊口的工具,我则是那挥舞工具的匠人。这样说绝非是在往自己脸上贴金(不乏写作者以匠人为荣),当然也不存在抱怨。我的态度是苦乐自知,全盘接受,只要继续在写,这辈子就是赚了。要是有幸能写一辈子,那就赚大发了。只不过,偶尔在高强度的写作放松之余,尤其是那些自我面对的深夜,要命的虚无感总是如期而至。
于是从今年开始,我又鼓起勇气,挤出时间写起了短篇小说。
当我在写悬疑长篇时我是在工作,而当我写短篇的时候我才是在写作。这话虽然矫情,但事实就是如此。随着年纪的增长,我愈发感觉到了什么叫力不从心——写了这个,你就没精力写那个。但我还是希望自己今后在“工作”之余,多写一点短篇。无论如何,它(指短篇小说写作)是我文学梦的开始,也是我在这艰难人世留给自己的一小块精神自留地,偶尔去耕种一番,收获些许干净而无害的蔬果,自给自足,人就能平静哪怕一小会儿。《青春》2022年已经开始征订
可点击下方海报进行征订
《青春》杂志电子版上线了,欢迎阅读。2021年12月刊电子版订阅,请查看下方阅读原文。
纸刊订阅,可点击下方图片或进公众号菜单栏查看“青春微店”
文 | 慢三
责编 | 菡萏
版 | 钰玲
监制 | 游于艺
特别鸣谢摄影作者
大宝乐
~YOUTH~
“在看”的永远18岁哦~
,
免责声明:本文仅代表文章作者的个人观点,与本站无关。其原创性、真实性以及文中陈述文字和内容未经本站证实,对本文以及其中全部或者部分内容文字的真实性、完整性和原创性本站不作任何保证或承诺,请读者仅作参考,并自行核实相关内容。文章投诉邮箱:anhduc.ph@yahoo.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