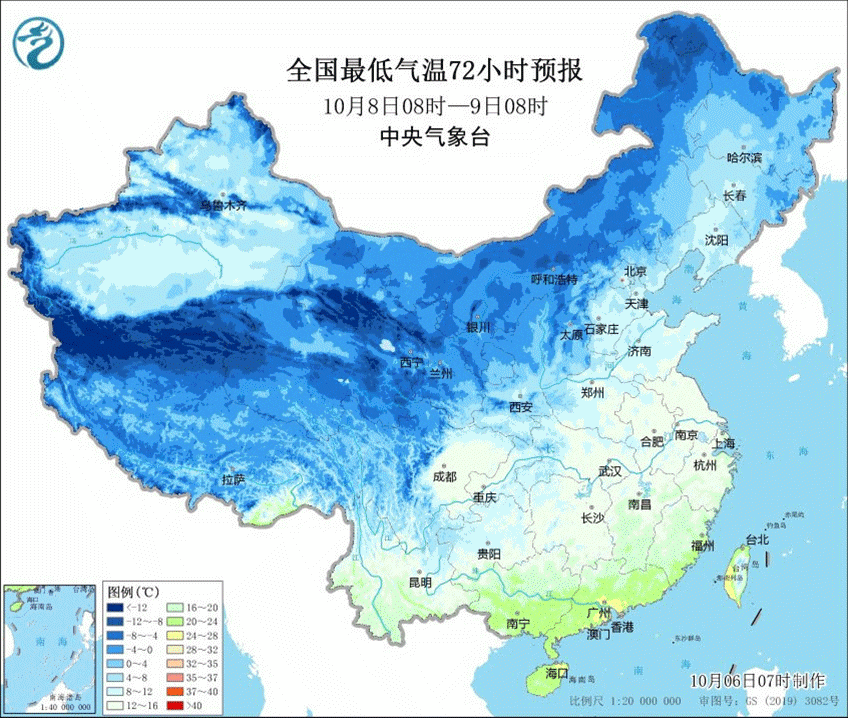52岁俞兆祥街头演唱会(布鞋文俞兆祥)

几十年来,我一直保持着下班回家后换布鞋的习惯。仿佛,一穿上布鞋,忙碌的工作就可以画上句号了;一穿上布鞋,就完成了自身角色的切割——由一个正襟危坐的上班族向一个悠闲的家庭成员的转换;一穿上布鞋,也就真正体悟和享受到了家的温馨。
然而,这种穿上母亲做的“千层底”布鞋后妥帖、舒适的感觉,随着母亲遗留给我的最后一双布鞋没法再穿以后,一去不复返了。
母亲亲手做的布鞋不能再穿了,我还是把它清洗干净,晾干,珍藏起来。我觉得它似乎还储存着母亲的体温,37℃;也似乎还保持着母爱的温度,37℃;更觉得它似乎还保留着我所有美好记忆的热度,同样是37℃。
没有布鞋穿的日子,于我而言,就像断了线的风筝,就像没有家的孩子,六神无主。我迫切需要一双布鞋,来接续我多年形成的习惯,无法想象下班回家后,还穿着一双乌黑发亮的皮鞋在客厅里晃来晃去。
曾经,百般无奈的我走进超市,花二十块钱买了一双方口布鞋。
这样的布鞋,我凑合着穿了几年。尽管与母亲做的布鞋无法相提并论,可是,我想它毕竟也贴着布鞋标签呀,或多或少能够让我找回过往日子里穿布鞋的感觉,对吧?然而,穿久了才发现,我买的布鞋根本算不上真正的布鞋。
尽管它看起来与母亲做的布鞋没有两样:浅方口,灯芯绒的鞋面,鞋底与鞋帮接缝处有一条白色的绲边……可是,它的鞋底不是棉布的“千层底”,更不是母亲一针一线纳出来的“千层底”呀。
记得一到冬天,母亲就开始打袼褙。找一块干净的门板,铺上几张旧报纸,用面粉熬糨糊,然后蒙一层旧棉布,刷一遍糨糊,再蒙一层旧棉布,再刷一遍糨糊,循环往复。在太阳底下晒。袼褙晒干,揭下,剪鞋底,剪鞋面。母亲的笸箩里除了针头线脑,还有一本厚厚的书。书里夹着大大小小的鞋样。有鞋底的,有鞋面的,一一对应。所以,她一再交代我不要把她书里夹的鞋样弄混了。不过,即使弄混了,母亲很快就能整理妥当,不会张冠李戴,出现差错。
做布鞋,有一道最辛苦、耗时的工序——纳鞋底。纳鞋底前,要浸麻绩线。我家的自留地里种了一种叫作苎麻的植物。一入夏,苎麻成熟,割下苎麻的树皮,浸泡一整夜后,用苎麻刮刀刮去青褐色的表皮,留下苎麻纤维,然后用石灰水沤。沤几天后,晒干,就成了细细的苎麻丝。有了苎麻丝就可以绩线。绩线时,选一颗头颅大小的平滑的麻石,将苎麻丝浸水后,在麻石上一搓,再往回一收,苎麻丝就绩成了苎麻线,也就是鞋底线。绩好线后,还要煮线。煮好线后,晒干,鞋底线就跟熟石灰一样白了。绩出来的鞋底线白不白,也是一个家庭主妇能不能干的考量指标之一。
垫好了鞋底,绩好了线,母亲就可以纳鞋底了。白天没有空闲,晚上做完家务活后,就着一盏昏黄的煤油灯,母亲的夜工——纳鞋底开始了。纳鞋底的工具有针锥、鞋底针(超大型号的针)等。母亲纳的鞋底针脚密集、齐整和均匀,看着就让人赏心悦目。实际上,可别小看纳鞋底,俗话说“穿针容易引线难”,每收一回线,母亲都要咬紧牙关使劲拽、使劲扯。线收得紧,鞋底就耐穿。纳鞋底的夜晚,我从来不知道母亲什么时候去歇息的。十一点,十二点,还是后半夜一点?有好几次,疲倦至极的母亲,不小心用针锥刺伤了自己的手指。
布鞋做好了,还有最后一道工序:楦鞋。母亲有一口藤条编织、刷了紫红油漆的笸箩,是专门用来存放鞋楦的。鞋楦用槭树制成,因使用频率高,纹理密致的鞋楦表面光滑、油亮,有一种温润感。笸箩里的鞋楦有大有小,还有一把精致的木槌,用来“加塞”。有一次,母亲刚把我的新布鞋做好,我就要急不可耐地穿上脚。母亲喝止我:“鞋子还没有楦呢!”我不听,径直穿走了。不久,就觉得不合脚、不好穿,好像穿了小了一码的鞋子,一双脚卡得生疼。回家后,母亲用鞋楦把鞋子楦了一个晚上。第二天,再穿上脚时,那双鞋子就舒适了。
参加工作后,我用半个月的薪水——24块钱,买了一双皮鞋,那是当年时兴的产自上海的“三接头”皮鞋。可是,没多久,脚后跟被磨出了血,我似乎有了削足适履的痛苦,没办法,只好重新穿上母亲做的“千层底”布鞋。
脱下皮鞋,穿上布鞋,我不知道这算不算得上是一种回归。
如今,在超市里买不到我想要的布鞋。是不是请村里的大娘做一双“千层底”布鞋呢?想想,还是打消了这种念头。我不想麻烦老人家,何况,她做的,毕竟与我母亲做的还是有所不同。再说了,我们村里连苎麻都没有了,会绩线的人也老态龙钟了,正宗的鞋底线都没有,做出来的“千层底”布鞋,还是地道的有着宜人温度的“千层底”布鞋吗?
,免责声明:本文仅代表文章作者的个人观点,与本站无关。其原创性、真实性以及文中陈述文字和内容未经本站证实,对本文以及其中全部或者部分内容文字的真实性、完整性和原创性本站不作任何保证或承诺,请读者仅作参考,并自行核实相关内容。文章投诉邮箱:anhduc.ph@yahoo.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