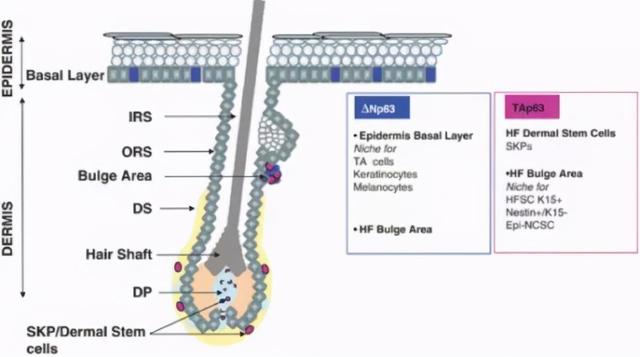穿梭千年小说(穿越千年说版权)
版权,也就是我们平时说的“著作权”,是体现作者对作品权属的重要标志,其中最突出的事项有两项,其一是在作品上的署名;其二就是在作品正式出版物上的版权记录。这两个事项之所以突出,因为它是作者通过它们来主张自己与作品相关的其他权利的依据。版权记录,正式的称呼应该叫版权页或者版权记录页,顾名思义,它就是有关版权或者著作权的记录,是出版物的版权标志,也是出版物的版本记录。现在标准的出版物版权页一般位于书名页的背面、封三或书末。在版权页中,按规定应记录书名、著译者、出版者、印刷者、发行者、版次、印次、开本、印张、印数、字数、出版年月、版权期、书号、定价等及其他有关说明事项。著作权是作者创作作品时随作品的产生而自然产生的作者的权利,版权页则是正式出版物对作者著作权亦是版权的规范性确认。打一个不甚贴切的比喻,版权页对于作品或作者的著作权而言,犹如合同签订时除了有双方当事人签字之外,又找了一些担保人,由这些担保人和双方当事人一起确认合同的真实性一样,而它另外的一层意思,实际上是把一些双方合同正文中不便出现的内容即除了署名以外需要表达的意思表达清楚,犹如签订合同时不便在合同正文中出现的事项,通过附件加以体现一样。因此我们说作品上的署名和版权记录,才构成了完整的作品或者作者的著作权或者版权。
当然,版权或者著作权既是作者的权利的体现,当然也是作者责任的承诺,文责自负,应该是它应有的含义。
当下,在自己的著述上署名,不仅天经地义,而且还有法律为之保证。在现实生活中,这种谁创作谁署名的观念,早已深入人心。其实,这种我们现在认为天经地义且得到法律保障的作品署名以及版权记录,作为现代版权或者著作权的重要内容之一,它能变成我们现代文化生活当中的天经地义,事实上是经过了一个漫长的过程。
一
有学者研究指出,在秦汉以前的古人著述都是不署名的,我们现在看到的许多古籍上的署名,其实都是后来的整理者们补署上去的。有两个例子。一是战国时人韩非写的书辗转传到了秦国,秦王赢政看到《孤愤》、《五蠹》之后大为感慨:“嗟乎!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这话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天啊,我如果能和这个在一起,死了也就没有什么遗憾了。当时秦王嬴政的丞相李斯告诉他,说这是韩国一个叫韩非的人写的。这是秦以前著述不署名的一个例子。另外一个例子,是说有一个叫杨得意的蜀地人,本人是为汉武帝养狗的侍从官,汉武帝读了《子虚赋》大为喜欢,说:“朕独不得与此人同时哉!”(我为啥偏偏不能跟这个人生在同一个时代呢!)杨得意告诉汉武帝说,这是我的同乡司马相如说是他写的。汉武帝大为惊讶,就把司马相如召来问,司马相如告诉汉武帝说,有这回事。这个例子是汉武帝时期著述不署名的一个例子。由以上两个例子,我们可以知道,汉武帝以前,古人在自己的著述上不署名应该是通例或者是习惯,而在自己的著述上自觉署名的事,应该至少是到汉武帝以后的事了。至于秦汉以前古人著述不署名的原因,现代学者余嘉锡援引《毛诗稽古编》的作者、清人陈啓源论有关《诗经》当中的诗歌有名或者无名、署名或不署名(注意:这里所说的有名或者无名、署名或者不署名,应该是指当时的作品有的有名称,有的则只有内容没有名称;有的是创作者自己给作品起了名字,有的则是作者只作了内容,并没有给作品取名称等)情况时的一段话说:“盖古世质朴,人情动于中,始发为诗歌,以自明其义。非若后世能文之士,欲暴其才,有所作辄以名氏也。及传播人口,采风者因而得之,但欲识作诗之意,不必问其何人作也。国史得诗,则述其意而为之叙,固无由尽得作者之主名矣。师儒传授,相与讲明其意,或与叙间有附益,然终不敢妄求以实之。阙所不知,当如是耳。”这段话的大意是说,古人著述不署名是因为古人质朴,无名利羁绊,有感而发,把自己发自内心的对生活的感受变成诗歌,以用以表达自己对生活的真实感受,他们不会像后来那些能文善写的人一样,打算彰显自己的才华,只要写了作品就一定要署上自己的姓名。古人的创作因为是对生活的至情至性的心声的自然流露,所以很容易被人们口耳相传,采风的人由此得到了这些在民间广为流传的诗歌,而采风的人收集这些诗歌时也只是从作品的抒情达意的情况出发来作为取舍的标准,并不会在意是谁作的。而掌管国家档案管理的官员们,则也只是根据诗歌本身内容的优劣来判断后加以收录、记载,也不会一定要知道作者是谁。以后讲授这些作品的大师宿儒,也只是讲解诗歌本身,即便是知道前人的介绍或叙录有增益或附会的东西,最后也不会妄加推断穿凿求证。不知道的仍旧让它“阙如”(即原样保留),应该是这样的。余嘉锡完全同意陈啓源的看法,并给予了极高的评价:“陈氏之言,可谓通达。不惟可以解诗,即凡古书之不题撰人者(即不在作品上署名)者,皆可以其说推之,学者可无事穿凿也。”他的意思就是说,该说的,陈啓源的说法已经很客观了,他的观点不仅可以解释《诗经》中的作品有名或无名、署名(有作品名称)或不署名(没有作品名称)的情况,而且可以以此来看待古书上署名或者不署名的原因了,学者们可以接受(相信)陈氏之说,不必再去怀疑了。这个评价应该是很高的了,它也告诉我们,秦汉以前的著述不题撰人即不署作者之名应该是符合实际情况的。
由以上秦王赢政读韩非书而不知道作者是谁,汉武帝读司马相如的赋而不知道作者是司马相如,以及陈啓源、余嘉锡对周秦以前古人著述不署名情况的研究,我们可以知道,秦汉以前,人们或因自谦或因习惯,作品上不署名应该是普遍现象。而更有可能的情况,也许是当时的人们对署不署名处在一个蒙沌状态,署与不署都是很自然的事。
二
中国人从什么时候开始自己在自己的作品上署名,其实是个很模糊的事情,如果我们能够找到中国人开始在自己的作品上署名的确切的时间的实证,应该是一件令人愉快的事。
在印刷术出现以前,知识或者信息的传播,用人工抄写应该是一种最常见最容易保存也最方便实用的方式。从现有的秦汉简牍及长沙马王堆帛书等实证资料的情况来看,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手写或者说抄书的复制方式,应该和现代印刷业一样,是作品复制、传播的主要方式。
敦煌莫高窟藏经洞的文献中,有大量的唐人写经,它是敦煌遗书中的一个大类。唐人写经,按历史实际看,一部经或者一个经卷,事实上就相当于我们现如今的一部书或一本书。坦白地说,作为敦煌遗书或文献中的一个大类,有关敦煌写经及与写经有关的问题的研究,已经无空白可言,即如写经题记这样的写经的附属品的研究也如写经本身的研究一样,也已经无空白可言。但是,对敦煌写经,不同的人,其关注点不同,有人关注内容,如写经本身的内容,是莲华经还是般若经等;有人关注写经的风格或书法,即写经是何人所写什么书体等;有人关注题记及相关的问题。而这些与写经相关问题的研究,则因人们关注点的不同,以及研究者们关注后用力的不同,因而其研究进展,应该永远是一个进行时。
写经题记,如上文所说,应该是写经的一个附属品,但这个附属品的价值,却在很早就引起很多人的关注,而且对这些写经题记的关注似乎不亚于对写经本身的关注,人们对个别写经题记的关注,甚至于超过了对写经本身的关注。其中的原因,我觉得是由题记本身的价值引起的。因为写经的主体,经及写经所用的材料、书体,很大程度上说是类同者或同质化的东西,如莲花经,般若波罗蜜多经等等,内容是一样的,如果说有区别,那也只是不同的写经手写了相同的经,或者同一个写经手写了多部不同的经而已;而写经的风格,如果一定要说有什么不同,也只是不同的写经手用同样的书体写同一部经,或者不同的写经手用同样的书体写了不同的经;而写经所用的材料,大致说来,同一时期所产生的写经,尤其是那些标明官方组织的写经,其用材基本上一致。而题记,虽然从形式上说,都是题记,但仔细观察,不同的写经上的题记的内容是不同的,而同样是写在同一内容的经卷上的题记,也因为写经的人或时间不同而不同,有些写经题记有时还会保留下一些与写经不相关的事情,给我们留下了了解写经以外的其他事情的线索。也因此,写经题记,以自身事实上的价值,为自己争得了该有的地位而引起了该有的关注。
从出版物的角度来看,敦煌莫高窟藏经洞的文献中的唐人写经及写经题记的存在,让我们有了了解唐人文化传播的实物资料。首先,它告诉我们,有唐一代,佛经的“出版”相当繁荣,不仅有官办的,更多的是民办的。唐代的佛经,如果我们把它当成当时的出版物来看,其复制、流播的方式主要是手写(抄),也就是主要是写经。同时,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大量的写经的存在也告诉我们,因为佛教的兴盛,佛经的需求量大增,由此产生了一种专门的职业——写经,而在印刷术没有出现的古代,“写”相当于现在的复制或印刷,是文字产品流布的主要形式。另外,写经的存在也告诉我们,因为要写经,自然也就产生了一种职业,由此也产生了一种专门人才——写经手,由这些职业人在职业抄写经书的过程中又逐渐形成了一种标准的或者说被市场认可的专门的写经书体——写经体。写经手和写经体的出现,说明了两个问题,从书籍出版的角度看,一是唐代书业的复制方式主要以手写为主,而在唐代已经开始出现的雕版印刷的方式并不是主要方式;二是写经已经职业化了,而且有了一套职业化的流程,而这套流程,在官方主持的写经过程中更为严格和细致,形成了完整的记录,而这些记录,与我们现代出版业的版权记录已经很接近了。
三
上世纪九十年代末,机缘巧合,我有机会在敦煌研究院敦煌遗书研究专家施萍亭先生指导下系统地查阅了敦煌研究院、敦煌市博物馆及酒泉、张掖等地博物馆、文化馆藏的所有唐人写经,由此也了解了敦煌研究院及河西各地市现存的所有敦煌唐人写经及题记的情况。因为是做出版的,当年所以有机会系统地查阅敦煌写经,本也是为出版甘肃省内收藏的敦煌文献做准备的,也因此,在系统查阅敦煌研究院和河西各地市博物馆、文化馆馆藏敦煌文献的过程中,唐人写经题记,尤其是那些记录写经从翻译到校勘全过程的写经题记,让我时不时地在脑海里把它们和我们现代出版物的版权记录相联系,因此产生了把写经题记和现代纸质出版物版权记录做些分析对比的想法。此后的一段时间里,我将敦煌研究院保存的写经和当时已知的我能看到的英藏(主要是斯坦因当年从敦煌莫高窟王道士手中骗买的敦煌写经,这部分写经有自己的收藏编号)写经进行了比对。通过比对,发现两者之间有一些明显差异。一是外观即品相方面的,敦煌研究院和河西其他地市博物馆或文化馆馆藏的唐人写经,虽然数量不少,但其中残卷较多;英藏唐人写经,尽管数量上没有敦煌研究院和河西其他地市的馆藏加在一起的总量多,但几乎没有残卷。这说明,当年斯坦因在王道士手中盗买唐人写经时,实际上是进行过认真挑选的,而且特别注重品相和保存完好的写经。另外一个问题是两者之间题记的差别。敦煌研究院和河西其他地市的馆藏唐人写经当中,有题记的很少,不仅少,而且所能看到的题记的内容都比较简单,其中最简单的就几个字,如“某某人写了”。而英藏唐人写经的题记,不仅数量多,而且内容也很丰富。这也说明当年斯坦因在敦煌盗买这批唐人写经时,不但进行过认真挑选,而且特别注重挑选了带有题记的写经。通过对写经及写经题记的比对,特别是对写经题记的比对,我觉得这些写经题记的形式及内容都有进一步研究的地方。在我看来,写经题记,尤其是那些官方组织完成的写经,其写经的写经题记,首先应该是由写经者自撰的一份准确记录写经产生年代及过程的完整的工作记录,而且是明确每个人责任的工作记录。这种写经的参与者一起自撰工作记录的情况,是从何时开始出现的,其具体年份我们不好直接判断,但从许多写经题记格式基本相同,所记内容有一定的基本事项的情况看,它们所反映的应该是写经尤其是官方写经,应该是有统一或者相对规范的管理要求的。而我们知道,形成一种完整而规范的工作要求,事实上是需要一定的时间,是需要有一个过程的。按照常理推断,要养成一种工作习惯或形成一种制度,都须有个过程也需要一定的时间,而且这种习惯或者制度,基本规律都是初时阶段可能相对简单,其后随着时间的推移,工作经验的积累,逐渐形成了完整的制度,而有了制度之后,就等于有了工作规范,也就有工作遵循。一旦变成了工作规范或行业遵循,就有可能变成了强制性的工作要求,因而越到后面记录也就更加完整。通过对唐人写经题记的实物或资料的比较,大致也能支持我们的推断。这里我们看几个例子。先看一个现藏敦煌市博物馆的唐人写经《妙法莲花经卷第六》的写经题记的情况:

照片中所提示的《妙法莲花经卷第六》及题记,现收藏于敦煌市博物馆(编号为敦煌博物馆055号),写经题记的内容,除标明了写经年代(咸亨二年即公元671年)、用纸、初校、再校(二校)、三校以及四个详阅人员和监制者的身份、姓名,表明此经应该官方组织的写经,但没有标明此经为何人所译,这与后面两卷写经题记有所不同,是疏忽还是因为其他原因呢?
下面我们再看两个英藏唐人写经题记的情况:
S. 3712《金光明最胜王经卷第八》题记(编号前的S表示这个经卷是由斯坦因盗买后收藏于大英博物馆的唐人写经)
大周长安三年(703年)岁次癸卯十月已口朔四日丙戌,三藏法师义净奉制长安西明寺所译,并缀文正字。
S. 2423《佛说示所犯者法镜经》题记(编号前的S表示这个经卷是由斯坦因盗买后收藏于大英博物馆的唐人写经)
景龙二年(780年)岁次景(丙)午十二月廿三日三藏法师室利未多(唐言妙惠)于崇福寺翻译大兴善寺翻经大德沙门师利笔受缀文大慈恩寺翻经大中心德沙门道安等证义大首领安达摩译语至景云二年(711年)三月十三日奉行。太极元年(712年)四月 日正议大夫太子洗马昭文馆学士张齐贤等进奉敕大宗大夫昭文馆郑喜王详定奉敕秘书少监昭文馆学士韦利器详定奉敕正议大夫行太府寺卿昭文馆学士沈全期详定奉敕银青光禄大夫黄门侍郎昭文馆学士延悦详定奉敕银青光禄大夫黄门侍郎昭文馆学士尚柱李义详定奉敕工部侍郎昭文馆学士护军卢藏用详定奉敕左散骑常侍昭文馆学士权兼检校右羽林将军上柱国寿昌县开国伯贾膺福详定奉敕右散骑常侍权兼检校羽林将军上柱国高平县开国侯徐彦伯详定奉敕银青光禄大夫行中书侍郎昭文馆学士兼太子右庶子崔湜详定奉敕金紫光禄大夫行礼部尚书昭文馆学士上柱国晋国公薛稷详定
延和元年(712年)六月廿日大兴善寺翻经沙门师利检校写奉敕令昭文馆学士等详定入目录讫流行
上引 S.3712《金光明最胜王经卷第八》的题记的内容较为简单,只是表明了写经的时间以及由何人所译。这里我们有必要说一下经与译者及写经者之间的相互关系问题。佛经应该是当年释迦牟尼讲经说法时的要义,后经弟子整理而用梵文写成了经文,传入中土之后为了便于传播,则必须将梵文先行译成汉文,因此,把梵文译成汉文的译者,实际上就应该是汉文经卷的作者了。因此,写经题记标明了译者,实际上也就是表明了经由梵文变成汉文的翻译者实际上就是本卷经卷的作者,而写经实际上也就是写经手接受别人的委托,把作者的作品按要求进行复制的行为。而这个题记还告诉我们几个重要信息,本卷经书的译者也即作者,是奉敕翻译,也就是说是受上级指派进行翻译,是职务作品。另外,它告诉我们,该卷经是由法师义净独立翻译并缀文正字(词语修改)的,也即是说,该经的翻译、修改是义净独立完成的,是事实上的个人作品,义净应该是这卷经的作者,题记标明了翻译和修改者的名字,这说明这卷经的翻译者也即是作者,在写经上是可以署名的了。
S.2423《佛说示所犯者法镜经》题记内容较前一个更加丰富,除了记录了译者(亦即此汉文经卷的作者)及在何处译成之外,与此有关的笔受缀文、证义、译语、进呈、详定(多人)、检校写人等以及奉行、入目、流行的时间等,都一一详加记录,表明这是官方组织的写经,以及官方组织的写经由翻译、笔受缀文(修改词语)、译语(译文词语规范?)、奉行、进呈的过程以及其后多级多人详定、检校写到最终登记入目、流行的全过程,这个过程,现在看,有点像现在大型电视剧末尾版权记录的字幕的样子了,各相关人等都一起出现了。只不过所不同的是,唐人写经题记的末尾,少了那句我们惯常所见的“版权所有,翻录必究”的用语。另外,从参与写经过程的所有人等都标明了官衔,说明了这卷写经应该是职务作品。参阅其他唐代由官方组织的写经题记会看到,这是一种常见的题记形式,可见当时的官方写经,不仅有严格的程序,也有严格的规范,事实上已经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制度,也即是说,正式的官方写经,必须有翻译、审定、证义等一套完整的工作记录,方可入目(登记备案),然后流行(允许传播或者发行)。
通过以上三例唐人写经题记的情况以及我们上文提到的有些写经题记只是简单地说“某某人写了”的情况,我们可以知道,唐人写经题记不仅有年份的区别,事实上也存在详略不同的情况,也因此,它们告诉我们,其实写经题记实际上有一个从简单到丰富、粗放到详细的过程,而这个过程中保留在写经上的写经题记,实际上在告诉我们,唐代的写经,事实上是唐代的出版物,而那些由官方组织的写经,更应当是正式出版物,在正式的出版物上标明作者及与出版相关的诸多内容,则让我们穿越时空,看到了古人有意表明作品著作权或者版权的实际存在。
四
如果我们有意把上述所引的唐人写经题记,和我们现在的正式出版物的版权记录做些对比,我们不难发现,它和我们现在的出版物的版本或版权记录,实际上有异曲同工之妙。下面我用几张当下的出版物的版权页或者版权记录页的图片与大家分享:

上面这是上世纪五十年代由中华书局出版的历史名著《资治通鉴》的版权页或版权记录页的情况,相关的信息相对简单,可以说只是简单地记录了一些重要的事情,如作品名称、作者、出版者、印刷者(复制责任人)、发行、出版时间、印刷数量、印张、定价、书号(书号为统一书号)等。这里面值得注意的是《资治通鉴》点校者注明是“校点资治通鉴小组”,告诉我们这是集体校点的作品。

上面这是上世纪七十年代由中华书局出版的《新唐书》。相关信息与上世纪五十年代出版的《资治通鉴》的版权记录的没有什么大的变化,其中最值得关注的是此书在1987年第3次印刷时,已经开始使用国际标准书号了,而且书号的使用方式变成了“统一书号” “国际书号”的形式。

上面这是2019年由中华书局出版的《读史方舆纪要》的版权页或者版权记录页的情况,其中的信息,较上世纪八十年代要丰富许多,单从形式上看,就多出了许多的东西。除了原有的如作品名称、作者、出版者、印刷者(复制责任人)、发行、出版时间、印刷数量、印张、定价、书号等以外,新增了一套“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之外,还加上了点校者、丛书名、责任编辑、印刷版次、规格等内容。版权页的信息量较前显然有了大幅增加。
上述由同一家出版单位中华书局出版的三种图书的版权记录的变化告诉我们,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到当下,出版物的版权记录变化实际上是很大的,其过程是从简单到丰富的过程,而且应该是一个渐变的过程,这个过程也告诉我们一个基本事实,那就是,人们对著作权的认识,是一个渐进的过程,版权记录的规范、完善也是一个随你时代发展而渐进的过程。
下面我们再来分享一下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创刊的《读者》(创刊时的名字为《读者文摘》)的版权页或者版权记录页的变化情况:

上面这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初,《读者》(《读者文摘》)创刊后第二年的版权页或者版权记录页的情况,很明显,信息十分简单,只是简单地记录了编辑、出版、印刷、发行等单位及书号、定价等,而且当时的杂志使用的是统一书号而不是刊号。这也告诉我们一个情况,在新中国的出版史上,曾经有过书号可以出刊的情况。

上面这是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已从《读者文摘》更名为《读者》之后的《读者》的版权页或者版权记录页的情况,信息显然比初创时期丰富了不少。除了编辑、出版、印刷、发行等单位及书号、定价,创刊时曾使用的书号已经变成了正规的刊号等外,已经有了编者个人署名的记录。

上面这是2022年第13期《读者》杂志的版权页或者版权记录页的情况,信息明显较前两个时期丰富了很多。可以说,与杂志编辑、出版、发行、广告等有关联的信息应有尽有。
《读者》杂志不同年代的版权记录,明白地告诉我们,中国改革开放以来著作权意识在我们生活中发生变化的时间和过程,而这个过程也表明了一个基本事实,改革开放,改变的不仅是经济体制,更重要的是人们的思想观念,而人们对著作权的认识则是从模糊到到清晰、从粗放到精致的过程。
从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的几个不同时期的不同出版物的版权记录的样本,我们可以看出,即便是在现代著作权意识已经深入人心的当今,对国人而言,版权意识的增强,亦即版权记录的重视,其实也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是一个由粗放向精细的过程。
五
如果我们把唐人写经中那些官方组织的写经题记的内容,和我们现在的出版物的版权记录进行比较,我们不难发现,两者之间在格式上虽然不可能一一对应,二者之间虽然叫法上有些不同,但在一些关键节点上都存在一些对应关系,如作者、出版者、印张(用纸)、编辑(详定、详阅以及一校、再校、三校)、发行(流行)、书号(入目)等等,实际上存在着一定的可比性。而最为重要的是,不论是唐人的写经题记还是当下的出版物的版权记录页,虽然相距千年,但它们都应该体现的是不同时代条件下,政府对出版物进行管理的一个标志。也因此,我们说,对唐人写经题记和现代出版物版权记录信息的比较,会让我们看到,相距远了说(唐初至今)1600多年、近了说(唐末至今)差不多1200年的两个历史时期的人,当其面对性质相同的事情时,思维的大方向应该是一致的,人们对自己所从事的工作以及所需承担的责任等,不论时代远近,事实上都会有所界定,而这种界定,则会因时代的不同有所差异。我们知道,我们当下出版物的版权记录,自然是因为管理的规范性要求而制定的工资规范要求,而事实上也就是一份实实在在的工作记录。而古人不经意地留在写经上的题记,也许有官方的规范,也许是约定俗成的行业规矩,事实上也是那个时代的工作记录,而在有了版权意识的现代的我们看来,古人的这些工作记录事实上也暗含着自有版权的意义。当然,我们也不排除,古人所以要在写经上用题记的方式,把每个人在写经完成的过程所做的工作一一标明,只是在向佛祖表示各人所有的敬意的可能。但即便是在表达敬佛的本意,即这是我或者我们对佛祖的一点敬意,但不可否认的是也表达着这种敬意是我或者我们的,是属于我或我们的,而不是他人的,用现在的眼光看,也还是在无意间流露出来了一定的权属意识。由此,我们可以说,如果说我们现在出版物上的署名权、版权记录是明白无误地以法律规定的著作权意识的体现,那写经题记就是那个时代人们有意识的著作权的正式记录。如果说,现代著作权中最能体现作者著作权的事项是在作品上的署名的话,从时间上说,中国人在作品上署名的意识,早在唐代就有了。而从我们上文列举前人有关古人著作权的研究以及唐人写经题记的内容和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的当代出版物的版权记录的内容,我们也能体会到,国人的著作权意识,从无到有,从粗放到完善,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
唐人写经,在印刷术还没有出现之前,应该像现在的出版物一样,是那个时代事实上的出版物,是传播知识、文化的事实上的主要途径,因此在写经上的署名,也应该看作是在作品上事实上的署名。如果我们把官方组织的写经作为正式的出版物来看待,那写经上的署名,就是在正式出版物上的事实上的正式署名。若以上我们的推论成立,那我们就可以认为,至少在唐代,在作品上署名已经成了风气,而这种风气的形成,一定是需要时间即有一个过程的,由此我们也可以知道,至少在唐代,中国人已经有了在作品上署名的习惯。而事实上,如果唐代开始在自己的著述上署名已经成为风气,那我们有理由相信,在自己的作品上署名的开始时间还可以推至隋代以前,因为隋朝的大一统时间很短,我们有理由相信,作者在自己的作品上署名的情况,也许在隋以前就有了。
我们可以想象,我们经常讨论的各种制度或者跟制度相关的体制等许多重大问题,在其初始阶段也许就很简单,也许就是为了相互之间相互理解避免误会,于是乎开始形成一些相互都明白也相互愿意遵守的约定,并不会像后世正襟危坐而需要专业人士青灯黄卷历经千辛万苦才能理出头绪那么复杂,许多制度,也许就是在相互争吵得不可开交时突然觉得应该有个约定,而这种约定,若能在实践中得到很好地贯彻,就有了演化成制度的可能。著作权的出现,也许就是为了避免作品的归属不清以及为了取得创作者该有的报酬而进行的事先约定而已,只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和进步,创作者越来越多,也因为人心不古,为了相互区别,也为了防范无良者剽窃,故而逐步有了在作品上署名的约定或成例。这也许就是我们现在大家所熟悉的版权或著作权法所以会产生的由来。
,免责声明:本文仅代表文章作者的个人观点,与本站无关。其原创性、真实性以及文中陈述文字和内容未经本站证实,对本文以及其中全部或者部分内容文字的真实性、完整性和原创性本站不作任何保证或承诺,请读者仅作参考,并自行核实相关内容。文章投诉邮箱:anhduc.ph@yahoo.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