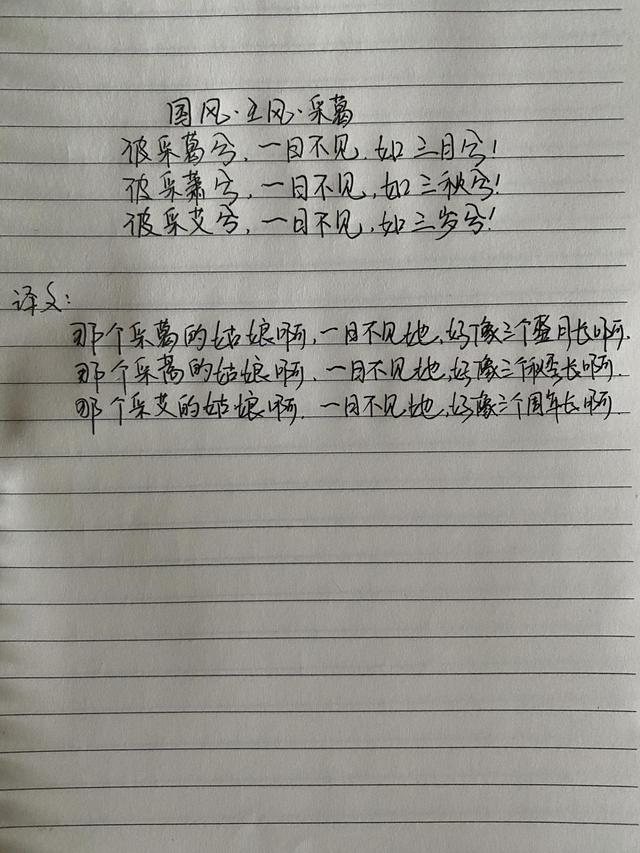秦腔随笔(秦腔杂谈四十年)
于当代新青年来说,多数人提起秦腔只知道是一种流传久远且风格鲜明的地方戏曲。倘若有人从长辈口中了解到这种艺术形式曾经在西北风光无二,并且还说得出几位名家,品得懂几段经典,那就算很有些文化修养了。

在陕西乃至西北五省,若从年龄段上来说,出生于上世纪六十年代及以前的人,几乎无人不爱秦腔,老幼皆是戏迷;而七〇后八〇后,相对前辈的喜好兴趣已出现迅速分化,至于九〇之后出生者恐怕确如前文所说。而就好之上瘾的人而言,偏爱秦腔分支眉户剧或碗碗腔的也不在少数,但总体上痴迷程度是一样的。之所以这么说,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戏台底下如日中天的热闹景象就可见一斑。
愚五六岁曾随祖母生活数年,有幸跟着她游历了周边村镇数不清的过年集会或农闲庙会,这过程无一例外的最后都要坐在戏台下看戏。起初只觉得戏服花花绿绿甚是惹眼,也根本听不懂那咿咿呀呀都唱的什么。可为啥能乖乖的坐着听戏,主要是戏台底下繁华且零嘴丰富。那年月人们日子苦焦,只有集会才能看到瓜子、花生、核桃、苹果,而戏台子底下往往还有甘蔗、糖人、糖葫芦、琼锅糖、镜糕、蓼花糖等等稀罕东西。奶奶说每次看戏不给我的碎爷庙孝顺点吃货就不得安然,于是看在零嘴的份上我自是态度较为积极。
平凹先生1983年写过一篇名为《秦腔》的散文,描述过戏台下孩子们爬上树杈占据了天空,大人或坐或站挤满地面,一众老汉老婆挤不进人群则拿着长烟锅靠墙占着两厢。而我所经历的场面则略微有些不同,因我幼时生活在平原地区,那里戏台子底下多是大片的开阔平地,天空也自是打开的天空,因而能聚集更多的人。而老幼戏迷多会早早拿着板凳坐在前排或中间,类似于现在剧场的VIP。其它的各色观众则靠后靠边一些就坐,然后才是站着围观的熙熙人群,如此传说起来都会用里三层外三层来形容盛况。淘气的半大孩子是舞台边的独特风景,要么就是认识乐队或台上的执事,偶有被特许蹲在两侧乐队跟前的。而大多没有关系自由流窜的,则调皮的趴在或蹲在戏台边上,那感觉就像栏杆上的一排猴子。经常开演时被驱赶的四散而去,开演后又一个一个踅摸着重回领地。
戏台上维持秩序的一般比较和善,多是拿着道具马鞭做个样子,而戏台下维持秩序的二杆子秦腔宪兵却很有些生冷。他们一众人手竖握着新砍的长竹竿站在边上,那竹竿足有丈余,稍头枝叶依然浓密,拄在那些人手里就像平地长出一样,而那些人轻松嬉笑的样子像似在竹下消闲。可一但人群有躁动,他们就会一边吆喝着一边挥舞竹竿朝人窝使劲的招呼。

我见识过戏台子底下人山人海乌乌泱泱的场面,尤其有名角现身的演出,高潮处戏台底下的掌声、喝彩声如山呼海啸。若有几个情绪激动或逞能现眼的怪怂趁机呼呼着想挪挤一下位置,那就必定会在局部人群中引起混乱。于是就看着那些长竹杆像拍苍蝇一般交替落在一群人的头顶,竹稍上茂盛的叶子在挥打中纷纷落下,不一会就连竹稍的细枝也几乎掉的净光。如此就有人头上起包,脸上落下血印,有人则抱头猫腰四处钻着躲避。这种方法虽有些粗暴,但效果很明显,原本看着不可收拾的混乱往往很快就能在骂骂咧咧中恢复平静。如此人们则继续津津有味的看戏,感觉就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过。而这时二杆子们一只手把竹竿怀里一抱,另一只手捏着纸烟抽的洋洋自得,那感觉颇似过年门上举着鞭锏的门神,或是得胜归来心满意足的将军。
戏窝子里的耳濡目染让我从小记住了不少唱词,可起先那种顺口溜式的记忆根本没有什么情感触动,倒是人称戏疯子的表姑之死让我伤感过。她感情多舛半生飘零,那些年跟随多个戏班子活跃于西北五省的各种戏台。我和奶奶跟会追戏时常会遇见,她每次见我都画着戏妆,有一次还挂着胡子扎着包头,以致她究竟长什么样子我都不太清楚。每次见面她都会热情的抱起我,有时还狂亲几下。我闻着她身上的油彩味,看着她神秘的脸谱感觉有些不真实。她唱戏时很投入,翻滚跌跃身法矫健。据说她饰演《闯宫抱斗》的梅伯方圆百里无人能敌,只可惜最后一次完成演出后居然直接死在了台上。祖母说这是她走火入魔所致,因为生命的最后几年她每次演出前都要抽上几口黑市买来的大烟膏,然后板带一扎精神抖数的上台,那次演出随着松香喷出连绵烟火,她按剧情倒在了道具炮烙之下就再没起来。所以那既是角色的完美谢幕,也是她人生的惨烈离场,而她不过才四十出头的年纪。后来我看过丁良生老师饰演的梅伯,那唱腔铿锵有力感情饱满,只可惜已无法对比谁更出色了!

因为这样一个插曲,秦腔于我多了一份情缘,之后再看似乎就上了心。先是觉得阎振俗先生和乔慷慨先生的丑角戏很是走心,他让我在《教学》中识得败家子的凄惨和没文化的荒唐。到后来又听懂了“不堪回首忆旧游,憔悴难对满眼秋”的刻骨柔情,也理解了汉苏武和李陵在异国荒野相遇时的悲切,如此也就慢慢从听热闹变成一个有些秦腔素养的戏迷。
如果说陕北民歌是黄土高原浪漫主义礼赞,那么秦腔就是秦人的命运交响曲。其配乐激越高昂,唱腔苍凉宽广,尤善抒发悲情与雄壮。而现代秦腔,经过历代艺术家的努力,其旋律更加流畅顺情,唱词愈发凝炼精彩,有时一句就直入骨髓。其中“呼喊一声绑帐外”不知震彻了多少人的神经,勾起了多少英雄往事。又如当年任哲中先生一句“李兰英秉忠烈人神共鉴”即能让全场落泪,他的独特嗓音和开创的鼻音拖腔极具感染力,让秦腔悲情戏的苍凉感别具震撼且又意境深邃。而贠宗翰先生的唱腔稳健浑厚,对于情感的拿捏牵动心弦感人肺腑。陈仁义先生的唱腔则更为硬倔有力,吐字清晰嘹亮,他的本戏《下河东》在哪个时代可是盛极一时。后起的刘茹慧先生唱腔也堪称一绝,她的代表曲目《辕门斩子》自不必说,其早年与陈仁义先生搭档演出的《苏武牧羊》就极为精彩,其唱腔慷慨亮润、字正气足,不但把降将李陵内心的悲愤、羞愧之情演绎的入木三分,而且还表达出一种不甘的昂扬。这折戏因人物背景复杂,一般演员要么只有悲愤,要么只表羞怯,因此就更显得刘先生的独特了!

都说任哲中先生的周仁是一代绝响,但李爱琴先生以其充沛的激情演绎了另一种具有代表性的风格。因此说李爱琴先生也是一代宗师,想来不会有多少人反对。任先生有个弟子叫胡屯胜,早年大有青出于蓝胜于蓝的势头,只可惜却英年早逝。而李爱琴先生栽培的秦腔天才杨升娟不但广为人知,加之这些年勤奋探索,唱腔日臻精进,已经成为秦腔女小生的扛鼎之才。她与西北金嗓子须生名家丁良生先生搭档的《苏武牧羊》也很有味道,只是个人觉得稍显柔弱了些,若再钢一点可能会更让人振奋。
提起生角那就必须说到李小锋先生先生,他嗓音高亢清润,演唱干净利落,扮相又儒雅俊逸,不管是《三滴血》、《花亭相会》、《白逼宫》还是《周仁回府》,李小锋不但收放自如,跌打动作还显示出深厚的舞台功底。自陈妙华先生之后还真是鲜见这样的嗓音和唱功,张保卫先生之后生角抒情也鲜见如此的力度。前一阵李小锋先生唱的所谓戏歌《人面桃花》火遍网络,虽然鄙人以为戏就是戏,何必非得与歌曲扯上关系,人们喜欢的是这旋律而不是具体什么属性。但李老师唱的确实好。另外他也经常与不同须生搭档演出《苏武牧羊》,他饰演的李陵这节双锤在当代似乎无人能出其右!
李小锋先生还与多位旦角搭档演过《花亭相会》,其中张宁老师的张梅英伶俐生动,张雅琴老师的张梅英有一种不可模仿的贵气,正如她出演《三对面》中的蓝屏公主一般有名媛风范。张蓓老师身材高挑,也曾和李小峰合作过《花亭相会》,其人扮相娇俏眉目传情,因此也堪称珠联璧合。看秦腔同一折戏不同组合的表演那是一种资深戏迷才能品味的享受,所以如听人说秦腔过来过去就那几本戏倒有啥看的,内行的人根本就不须理会,因为说这话的人是真不懂!

著名小生演员还有一位叫张涛,其人扮相英俊潇洒,嗓音脆帅饱满,道白吞吐自如,是典型的苏派文武小生。而武小生戏最具代表的当属《金沙滩》中的折子戏《五郎出家》,开场一句“众家兄弟落了马,倒把延昭活吓煞”对演员要求极高,一方面要高而不破,另一方面还必须是一种清脆含情的音质。显然张涛先生这两方都很完美,加上挥洒干练的台风成名就是必然的结果。
自上世纪九十年代始,有人说市场大潮冲击了秦腔,但鄙人并不这么认为。应该说秦腔只是冲击了剧团,而不是秦腔本身。当年秦腔的空前繁荣独领风骚只是特定时期的文化现象,而在各种艺术形式百花齐放及多媒体传播的时代,秦腔回归它该有的地位自是必然。秦腔有着深厚的文化土壤,因此也从未真的衰落过。
说到这就想起秦腔的剧目改编问题,前些年有人将经典剧目《双罗衫》改为《集云山》就极为失败。不但破坏了剧情的连贯性,也极大的削弱了情节的感染力。尤其删掉苏云之弟苏雨的戏份最为不当,原创这样的设计是一种悲情的叠加,如改掉就必须有新的渲染桥段,否则就一定会挨骂。当然不是说不可以进行这样的尝试,只是戏剧剧本改编对创作者要求甚高。往往不仅需要很高的文学造诣,还得深谙地方剧种唱腔特点,并对方言发音有充分的了解。有时文字看上去很美,但唱出来不合韵味,这样就很勉强演员了。显然秦腔现代戏《红灯记》就做的非常好,句句唱词精炼有力,可谓把秦腔的特点发挥到淋漓尽致,我想这不仅仅是一部剧的成功,而确应是秦腔编剧艺术的样板和方向。

因此就秦腔新剧目的创作而言,窃以为应主要立足经典文学作品改编。比如《祝福》来自鲁迅小说,《红灯记》来自电影《自有后来人》剧本。因为这样的创作是站在巨人肩膀上的二次升华,如此基础的故事性是经过检验的,创作的重点在于取舍和唱词的锤炼,相对来说就容易一些,也容易出精品及保留剧目。如果完全原创,费力劳神不说,大多演几场就废了舞美封了箱子,实在浪费太大也毫无意义。虽然现在有了多媒体的记录方式,可没人看还不是一样的白废功夫。
前文提说过秦腔当中的呼喊一声,那种粗犷高亢的腔调是秦腔独有的酣畅。张小亮先生的《斩单童》那是一绝,绝在嗓音洪亮悠长,绝在吐字特别清晰,绝在对隋唐英雄情义的深刻认识上。当然对张小亮先生的偏爱有很重的个人色彩,因为除他之外张兰秦、李买刚先生的戏也精彩非常。每每对比两位先生饰演的包公戏是很过瘾的享受,尤其钟爱折子戏《三对面》,其中大净的豪迈和旦角阴柔有冰火两重天的激烈冲撞,而这种强烈比照是秦腔独一无二的魅力。

旦角之中有一种老旦也很有特色,无论展示天波杨府佘太君的威仪还是普通民间老妪的悲情都极具感染力。《杨门女将》里佘太君唱出“众儿郎齐奋勇冲锋陷阵,令公他提金刀勇冠三军”时必是激情澎湃掌声雷动;《双罗衫》老妈妈一句“你说是这两副灵牌吗?这是我长子苏云次子苏雨”定叫台下热泪盈眶。知道的名角有梁玉、康亚婵、武红霞等,个人觉得梁玉老师的佘太君自如大气,唱腔有一种不怒自威的特别气场,因此听的较多。至于花旦、刀马旦等明角也大有人在,但在此就不一一细说了。
另外除了省市院团专业演员的诠释,周边县级剧团也有很多广受爱戴的名角,甚至业余的自乐班里也藏龙卧虎。比如秦腔明星商芳会、徐通通等,还有前一阵备受关注的落魄名角李苏迎。说起来商芳会的风格很有些李苏迎的影子,她二人唱腔都有些撕裂般的悲苦。而大学生徐通通少年老成,声线极有沧桑感,一些老生戏他也能掌握的火候精准。至于青年演员包东东那更是平地一声雷的节奏,其表演沉稳大方,嗓音条件优越,唱腔板眼节奏感非常好。稍加时日,一定会有丁良生后来者的成就。

当然提到名家就会想起秦腔的派别,因为之前戏曲的传承多是传帮带,而现在借助多媒体学习,在老师的指点下演员更容易涉猎百家博采众长。但任何艺术立足自身条件保持独有特点是出类拔萃的基础,亦步亦趋只是学习,开辟新风才是个性。因此在缅怀大师学习名家的同时,实际上一代一代的秦腔人始终在继往开来。因此鄙人并不同意一些人说新人不若老人唱的好,而是觉得任何时候新生代因文化程度的提高,教学方式的进步,表演在艺术性和感染力上都超越了前辈。尤其舞美和乐队条件的改善,秦腔也越来越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比如这几年西安的易俗社、三意社等演出就很是卖座,这也足以说明只要唱的好,且不以创新之名跑偏门,不弄一帮不懂装懂的人胡折腾,秦腔就必定会越来越光彩夺目。
不过也要看到,新生代演员技能普遍在提升,但情感上的投入度上却不尽人意。艺术这东西没有真炙的深情技巧再好感染力也是有限的,过去讲演员欺戏就是说的情感投入。因此也希望新生代选择了秦腔就要真的爱,且爱的深爱的重,如此何愁秦腔不兴旺发达。况且随着这些年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广大农村空心化持续加剧,以后十里八乡流动舞台的演出一定会衰落。秦腔将更多的成为大小城市里市场化、常态化的剧场演出,而秦腔作为区域性传统艺术,好似陈年烈酒,品者往往要到一定的年纪才能领悟其醇美。所以即便当下年轻人有些疏离,但之后依然会成为秦人日常生活中不可替代的文化体验,看戏也必将成为一种高尚的艺术享受。
最后希望从事秦腔专业院团能组织一批高水平的文化学者和剧作家,对秦腔的传统剧目剧本进行深度挖掘和斟字酌句的优化,最好形成一套比较权威的标准剧本以便参考。一方面是对文化的保护,同时也凸现当代秦腔的整体艺术追求。因为随着普通话推广日久,以后要改出方言化的秦腔恐怕会越来越难。
区区小文致敬钟爱的秦腔,文中罗列及排名不分先后,点评见解也仅一家之言,如有不当敬请海涵!

免责声明:本文仅代表文章作者的个人观点,与本站无关。其原创性、真实性以及文中陈述文字和内容未经本站证实,对本文以及其中全部或者部分内容文字的真实性、完整性和原创性本站不作任何保证或承诺,请读者仅作参考,并自行核实相关内容。文章投诉邮箱:anhduc.ph@yahoo.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