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景观与艺术美学(生态艺术学建构的理论路径)
【编者按】从20世纪60年代生态运动兴起以来,人们越来越清醒地认识到人类社会和文明形态的生态转型势在必然。与此相应的则是艺术的各种理论形态的生态转型,生态艺术、生态艺术批评与生态美学已经成为非常值得关注的新兴学术领域,但“生态艺术学”的建构至今尚未引起学术界的足够重视。有鉴于此,程相占以其生态美学研究为背景,初步梳理了从“美的艺术”到“生态的艺术”的理论脉络,尝试着为生态艺术学建构探寻一条理论路径;张嫣格则以塞尚“知觉的觉醒”为案例,尝试探讨现代艺术与自然的关系。
生态艺术学建构的理论路径:从“美的艺术”到“生态的艺术”
程相占
【内容提要】生态艺术学的核心是生态艺术观,其理论途径可以概括为从“美的艺术”到“生态的艺术”。巴特和康德的“美的艺术”概念在将艺术从手工艺中区分出来的同时,还将艺术与美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从而为“艺术的独立”和“艺术的自律”作出了历史性贡献。黑格尔更进一步,他不但将艺术等同于美,而且强调艺术美高于自然美,艺术由此获得了神圣的光环。米克将生态学作为解释实在的模式,在借鉴生态学和生物学知识的基础上,反思和批判了现代观念论哲学框架中的艺术观念,进而提出了有别于“美的艺术”的“生态的艺术”,即基于生态实在之真、与自然形式和过程一致的艺术,这就从根本上将人类及其艺术创造视为自然生态系统的一部分,初步化解了“艺术对自然”的二元对立,使得我们有可能从生态美学角度倡导一种生态艺术观,从而为构建生态艺术学清理出一条理论路径。

【关 键 词】生态艺术学;生态艺术观;美的艺术;生态的艺术;生态美学
知识社会学表明,任何类型的知识生产总会受到社会条件的制约,这尤其明显地反映在哲学与社会科学的知识生产中。正因为这样,我国学者在思考艺术学问题的时候,就不能忽视如下两种有别于西方世界的社会现实:一是自 2007年以来的生态文明建设总体国策,二是艺术学门类自 2011年以来的独立。将这两种社会现实结合起来进行思考,就是我国学者探讨艺术学问题的特定语境——我们能否创造具有中国特色的艺术学理论,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如何理解并把握这一特定时代语境,在学术探讨中将“问题意识”与“语境意识”有机地结合起来。
正是根据这种学术判断,笔者在思考艺术学问题的时候,首先想到的一个问题便是:生态艺术学建构如何可能?这固然是笔者长期研究生态美学的学术惯性使然,但更重要的是出于笔者的如下观察:在当前的各种论著中,“艺术”通常与“美”“审美”一道,并被列为美学、艺术哲学、艺术学等领域中光辉灿烂的关键词——当人们使用“艺术”这个术语的时候,与其说是在描述一种事实、界定一类事物(即作出事实判断),不如说是在表达一种肯定性评价、表达一种赞赏(即作出价值判断)。这就意味着,生态维度在当前的艺术学建设中基本上付之阙如,其典型表现在于尚未认真探讨并积极倡导一种与生态文明建设吻合的生态艺术观。
本文的核心要点是,就像“美”“审美”在生态美学中并不总是意味着肯定性表达或评价那样,“艺术”也未必总是好的、正面的、积极的、值得肯定的;恰恰相反,“艺术”也极其可能是坏的、负面的、消极的、应该否定的。现代“美的艺术”这个概念一步步将“美”这一光环赋予了艺术,甚至将“艺术”与“美”视为同义词;但米克通过反思西方理论史上“艺术对自然”的长期论争而提出了“生态的艺术”这一新型概念,初步打碎了笼罩在艺术上的光环。我们下面依次讨论。
一、 “美的艺术”与艺术的光环“美”
西方文明史的发端时期就已经产生了艺术,只不过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内,那种艺术通常指的是“手艺”(crafts)。到了文艺复兴时期,艺术家们谋求提高其社会地位,试图将“美的艺术”从手艺中分离出来。于是,“美”受到了更高的估价并在社会生活中发挥重要作用。“美”的那些制造者们,包括画家、雕刻家、建造师等也受到了更高的尊重,这些人自认为比手艺人优越,希望与手艺人区分开来 [1]。这就意味着,从根源上来说,现代意义上的“美的艺术”观念与“美”有着不解之缘,它通过用“美”来规定现代艺术的性质而使之区别于一般的手艺。但这里需要指出的一个表达细节是,在西方语言中,“美的艺术”(fine arts)中的“美的”与美丑意义上的“美”(beauty)并不总是直接在字面上相关,我们下面将会对此有所讨论。
系统地研究“美的艺术”的学者首推法国学者巴特(Charles Batteux,又译巴托),他出版于 1746年的著作《简化成一个原理的美的艺术》(Les Beaux Arts réduits à un même principe)通常被视为现代“美的艺术”观念的集中表达;他所提出的那个“单一原则”即“对于自然的模仿”,也成为后世“艺术—自然”关系论的重要资源。巴特根据功用将艺术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机械艺术,即具有实用价值的艺术;第二类是纯粹为人们提供愉悦的艺术,即“美的艺术”;第三类则是二者兼而有之的艺术。艺术分类的标准是运用自然的方式:机械艺术将自然看作一种产生实际效益的工具,如园艺、种植等;“美的艺术”则并不利用自然,只是通过摹仿自然来给人们带来快感,它包括音乐、诗歌、绘画、雕塑和舞蹈等 [2]。我们不难发现,巴特所言“美的艺术”具有两个特点:一、非实用;二、能够带来快感——这两点正好是康德所揭示的“美”的特性。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巴特所论的“美的艺术”的原文为“ beaux arts”,翻译成英语应该是“ beautiful arts”而不是“ fine arts”——“beautiful arts”这种翻译方式的优势在于,它非常容易通过转化词性而生成“艺术美”(artistic beauty),从而与“美”紧密地联系起来。这个表达方面的细节通常被人忽视,但在本文中却是至关紧要的 [3]。

巴特的著作出版五年后就被翻译成了德语在德国正式出版,德国甚至还出现了三个不同的译本,随即成为包括康德在内的德国美学家们的理论资源 [4]。康德在表达“美的艺术”的时候,使用的德语原文为 “sch.ne Kunst”;但当代美国学者盖伊的英译本却对之同时采用了两种翻译,即 fine arts与 beautiful arts,其间的考虑我们这里难以细究。从《判断力批判》的整体框架和思路来说,翻译为beautiful arts具有一定的优势,那就是更加容易将该书对于“美的艺术”的讨论与该书第一卷“美的分析”结合起来,其整体的理论思路在于:鉴赏力作为一种判断“美”的能力 [5],既可以用来判断自然之美(第 1—22节),又可以用来判断艺术之美(第 43—53节)。二者中间穿插的是第二卷“崇高的分析”(第23—29节),此后的第 30—42节回到了对于判断美的能力即鉴赏力的分析。
康德美学的核心是对于鉴赏力所做判断(即狭义的“审美判断”,国内学者通常称为“鉴赏判断”)的分析,“美的艺术”其实表达了一种由鉴赏力作出的审美判断,即“艺术是美的”,其思路为:当我们面对艺术的那些可以感知的特征、内容以及思想时,我们的两种认知能力(想象力与理解力)达到了和谐的自由游戏状态,此时,我们的鉴赏力就可以作出如下一种审美判断:这件艺术品是美的。
像巴特一样,康德也是在与“自然”相对的意义上来探讨“艺术”的特点的:艺术区别于自然、科学、手艺。康德认为,艺术是人类主体有目的、主动去制造的,区别于自然力量对事物的被动影响。在此基础上,康德将艺术区分为“感性的艺术”与“机械的艺术”两类,进而将“感性的艺术”区分为“快适的艺术”与“美的艺术”两类。这就意味着,“美的艺术”不同于自然、不同于机械的艺术、不同于快适的艺术,其特性被逐层揭示出来。康德认为,如果某种艺术的目的是使愉悦伴随作为纯然感受的表象,这种艺术就是“快适的艺术”;而如果某种艺术的目的是使愉悦伴随作为认知方式的表象,那这种艺术就是“美的艺术”。也就是说,“美的艺术”并不建立在主观的纯然感受性之上,而是同时建立在感官之感性与心灵之理性这两个方面之上。由此,以道德感为根基的人类“共通感”才能应用于“美的艺术”;也是在此基础上,关于“美的艺术”的愉悦才能在不同主体之间具有普遍有效性,超越了私人纯然主观的感官体验。这就意味着,“美的艺术”的愉悦并不是出自于纯然感受的享受的愉悦,而是反思的愉悦。因此,“美的艺术”就是一种以反思性的判断力为标准的艺术,而不是以感官感受为标准的艺术。我们这里还能联想到《判断力批判》“导言”最后表格中“艺术”的位置——它位于自然与自由之间,对应的心灵状态为愉悦或不悦的感受,相应的主体认知能力为反思性的判断力,先天原则为有目的性 [6]。也就是说,反思性判断力连通了(自然概念领域的)理解力与(道德范导领域的)理性能力,主体对于“美的艺术”的反思性愉悦因而能够沟通自然与自由之间鸿沟,起到一种典范的桥梁作用。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康德对于艺术与自然之关系的考察。他在《判断力批判》第 45节的标题中指出,美的艺术是一种同时“显得像自然的艺术”。美的艺术中的有目的性虽然是有意的,但却要显得不是刻意的,需要师法自然,且摒除刻板的、学院派的形式痕迹 [7]。康德在第 46节进而指出,“美的艺术”是“天才的艺术” [8],而天才就是给艺术提供规则的才能,即自然天赋。这就意味着,艺术家的天才其实最终是自然的能力,它来自自然、从属于自然,用康德的术语来讲就是天生的心灵的前配置。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康德所说的“天才的艺术”最终只能是“自然的艺术”。我们不难发现,康德对于“美的艺术”的论述走了一个圆圈之后回到了原处:始于不同于“自然”,终于等同于“自然”——这或许体现了康德惯用的“二律背反”思维方式。非常遗憾的是,康德之后的接受者们通常忽略了“天才”与“自然”的本源性关系,总是将“天才”与“想象力”联系在一起展开论述,目的是强调艺术家作为创造主体对于“自然”的超越,艺术创造被视为艺术家的主观“表现”,康德艺术理论的自然维度很大程度上被遮蔽了。
到了黑格尔那里,“美的艺术”获得了更高的位置,这具体体现为三个方面:第一,“美的艺术”被等同于“美”。黑格尔《美学》开门见山地强调指出,美学的对象是“广大的美的领域”,是“艺术”,是“美的艺术” [9]。这三个术语涵盖的范围表面上来看是层层递减的关系,但实际上却被黑格尔视为同义词。我们不难发现,《美学》这本书很多地方混用“美的艺术”“艺术”“艺术美”和“美”这四个术语,这固然包含讲稿的不严谨性这一因素,但根本原因应是黑格尔的哲学观。他曾经明确指出:“对于我们来说,美和艺术的概念是由哲学系统供给我们的一个假定。 ”[10]他所谓的“哲学系统”,其实是“绝对理念”按照“正反合”的方式不断螺旋上升的发展过程,是黑格尔哲学所要研究的全部内容。“绝对理念”发展的三个阶段从低到高依次为逻辑阶段、自然阶段和精神阶段,而在精神阶段,“绝对理念”从自在发展到自为也经历了从低到高的三个阶段,即主观精神、客观精神和绝对精神;绝对精神的目的是全面地自己认识自己、自己实现自己,它也有从低到高的三个发展阶段,即艺术、宗教和哲学。根据这一哲学体系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艺术”是“理念的感性显现”,尽管黑格尔没有明确这样讲。他明确讲的倒是“美”的定义,即“理念的感性显现” [11]。这就非常清楚地表明,“艺术”与“美”在黑格尔那里必然是相同的。
第二,在美学观中大大突出“美的艺术”。我们知道,美学观是一种美学体系的灵魂或中心,决定着美学体系的思路和理论要点。黑格尔深明此道,他的《美学》单刀直入,明确将美学视为“美的艺术的哲学”。他提出:“这门科学的正当名称却是‘艺术哲学’,或则更确切一点,‘美的艺术的哲学’。”[12]这就从美学观上颠倒了康德美学侧重自然审美、兼顾艺术理论的整体格局,使得“美的艺术”的地位在美学这个领域大幅度飙升。
第三,抬高艺术美而贬低自然美。按照黑格尔的哲学思路,理念显现在自然的感性形式中,就是自然美;理念显现在艺术的感性形式中,就是艺术美。黑格尔尽管声称将自然美排除在外,但他在具体论述中并没有完全忽视自然美。他说:“理念的最浅近的客观存在就是自然,第一种美就是自然美。”[13]自然美不能完满地体现理念,因而是低级的美;艺术美则是理念超越自然后的感性显现,能够比较完满地体现理念,因而是高级的美。自然是“外在的无心灵的”[14],自然的产品“未经心灵渗透” [15];而“艺术和艺术作品既然是由心灵产生的,也就具有心灵的性格” [16];所以“心灵和它的产品比自然和它的现象(产品)高多少,艺术美也就比自然美高多少” [17]。黑格尔提出,为了弥补自然美的缺陷,所以我们要求艺术美。正是通过以上论述,艺术被等同于美,被高高置于自然之上,“美的艺术”由此获得了耀眼的光环。我们今天提及“艺术”的时候,很大程度上讲的就是黑格尔这种意义上的“美的艺术”——没有人质疑这种艺术的合理性,直到“生态的艺术”这个概念的提出。

二、生态学作为理解实在的模式与“生态的艺术”
康德是在其“先验观念论”的整体框架中讨论美、审美和艺术问题的,他的后学包括黑格尔在内被统称为“德国观念论”。这种哲学固然对于美学进行了全面系统的论述,但其理论弊端也是严重的,那就是在拔高艺术的同时贬低自然,抬高了艺术家对于自身心灵世界的创造性“表现”而贬低了他们对于自然的“模仿”,其背后隐含的现代性观念是人类超于自然、高于自然。这种情况受到了很多反思与批判,其中,美国生态学者米克的批判最为值得重视,因为他于 1972年发表的《走向生态美学》一文初步打破了现代艺术的光环,有针对性地提出了有别于“美的艺术”的“生态的艺术”,从而带来了艺术观念的重大变革,其理论意义值得高度重视、高度评价。
米克的深刻之处在于,他清醒地看到了一条鸿沟横亘于人类主体的心灵世界与超越人类世界的整体世界之间。康德哲学中最著名的鸿沟是自然(现象界)与自由(物自体)之间的鸿沟,康德试图通过运用于艺术(审美)领域的反思判断力来沟通自然与自由。但由于康德哲学的总体框架是主体性的先验观念论哲学,基点是人类主体的心灵世界及其各种先验能力,超越人类心灵的那个更广袤的世界,经常处于“存而不论”的状态。米克回顾了西方美学史并尖锐地指出:
理论美学的历史一直以来就被“艺术对自然”(art versus nature)这一著名争论所主导,而这一争论始于柏拉图的如下主张:所有的艺术创造物都不是完美的,通常是欺骗性的,是实在的类似物(approximation of reality)。在这一视点中最极端的看法是,艺术在某种程度上是自然的不诚实的堕落,一种被激发的谎言:“艺术”(art)这个词本身就是“人工”(artificiality)这一词语主要的词源要素。遵循这一思路,审美理论在传统上一直都强调艺术创造物与自然创造物的分离,假定艺术是人类灵魂的“高级的”或“精神化”的产品,不应该混同于“低级的”或“动物性的”生物世界。思想保守的人经常视艺术为“不自然的”,而持观念论的人文主义者,则在艺术中看到了人类精神超越自然的形象。两种观点都扭曲了自然和艺术之间的关系。 [18]
米克这里所说的“持观念论的人文主义者”,无疑指的是康德、黑格尔等人。我们知道,哲学史上,与观念论对立的通常是实在论。米克尽管没有直接提到“实在论”,但他有一句话明确地表明了自己的哲学立场就是实在论,他这样提出:“生态学作为一种富有潜力的关于实在的新模式,它的出现为调和人文与科学研究成果提供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机遇。”[19]这就是说,在米克这里,生态学不仅仅是生物学的一个分支学科,而且是一种“关于实在的新模式”,即对于“实在”(reality)的揭示。

按照米克的相关论述,生态学所揭示的“实在”就是“生态系统”(ecosystem),更具体地说就是“生态圈”(ecosphere),而人类和人类的作品都是生态圈的要素。正是从生态系统和生态圈这样的生态学观念出发,米克多次强调“生态演替”(ecological succession)作为各种“自然过程”的重要性,它们“为人类思想和创造力提供了基本的形式” [20]。简言之,米克在反思以康德为代表的持观念论的西方人文主义哲学的缺陷之后,在充分借鉴进化论、生物学、生态学的观念和概念的基础上,将学术视野拓展到超越人类精神世界之外的、更为广阔的实在世界,从“生态系统”这一崭新的角度重新提出了判断善恶、美丑的标准,进而在重新考量艺术与自然之关系的基础上提出了“生态的艺术”这一崭新观念。我们分别论述如下:
第一,判断善恶的标准。米克指出,传统的善恶标准及其道德判断属于“人类中心伦理传统”(man-centered ethical tradition),其基本特点是根据人的利益来判断善恶。比如,在牧羊人看来,狼是“恶的”,因为狼会吃羊。但米克从生态系统的角度指出,捕食活动对于维护长久的环境稳定性具有重要性:如果这个牧羊人成功地消灭了狼群,那他实际上也已经削弱了生态系统的完整性( the integrity of the ecosystem),而他自己的生命归根结底就依存于这种完整性。也就是说,人类应该“回应他们自身所处环境的复杂性”,只有这样才能走出生存的困境——他警告说:“西方人不能再重蹈覆辙了。”[21]
第二,判断美丑的标准。米克清醒地认识到,人类的美丑观( conceptions of beauty and ugliness)在某种程度上必须以自我沉思为基础 [22]。这就是说,人类对于自己的理解决定着其美丑观。米克将人类视为生态系统之中的一个物种,从“美的生物学”的角度来解释美与丑之间的区别、美与丑的范畴划分及其根源。他明确提出,要整合当代生物学家和生态学家所提出的“自然”“自然过程”等诸多概念,以便审美理论“更成功地界定美” [23];主体对生态系统之美的感知,与对其生物完整性( biological integrity)的认知是密不可分的。
第三,“生态的艺术”。米克比较深入地考察了对于自然的审美观念与生态观念之间的诸种相似性,提出二者可以相互强化,从而“改变由那段很长的、由人类物种过分简单化的自然观而造成的毁灭性历史” [24]。这就特别清楚地表明,米克从生态学这个特定角度反思了现代自然观的严重后果,试图用生态的自然观来取代它。他之所以倡导“生态的艺术”,根本原因正在这里。米克根据生态系统观念,对于“人造物”“驯化”和“文明”三者进行了反思与批判,这都表明,他所说的“生态的艺术”就是有别于上述三者的艺术,其最终本源就是植根于自然的艺术。米克这样指出:
人类关于美的体验深植于自然形式和自然过程——它们的存在与人类的感知有关或无关,我们的审美价值观实际上恰好是对于自然的抽象构想,因为自然既存在于我们之内,又存在于我们周围。专属于人类的东西对我们而言通常都不是美的,只有当人类艺术与自然形式和自然过程一致时,我们才能在其中发现美。[25]
这就清楚地表明,米克所说的“生态的艺术”就是“与自然形式和自然过程一致”的艺术,这样的艺术就是“美”的载体。这就促使我们认识到,西方传统美学中“艺术对自然”这类二元对立命题隐含着错误的审美观,被“艺术对自然”这类二元对立命题所主导的审美理论将艺术视为人类灵魂的“高级产品”,把自然与艺术的关系简化、扭曲为对立的两极。为此,米克指出,审美理论应该正视审美活动中人类的生物属性、艺术的生态性欣赏,以及人类与自然之间的生态性审美关联。
正因为生态学是一种富有潜力的关于实在的新模式,审美的标准就应被设定为有助于生态系统达到其最大限度的复杂性与多样性,这区别于以往那种在人类中心伦理传统主导下的善恶美丑标准。另外,与此相关的问题是——如何进行生态审美,米克认为,审美主体应该借助生态学知识进行审美活动,只有借助当代生物学家和生态学家所提出的“自然”“自然过程”等概念,审美理论才能更成功地界定美。简言之,米克认为,生态学展示了人类与自然环境之间的相互渗透性,这一点在人类的艺术创造方面得到了充分的证实,合理的艺术审美应该让人们自觉去回应、欣赏其自身环境的复杂性。
自康德三大批判发表以来,真、善、美便并列为人类的三个最高价值。米克却以“生态之真”——生态学所揭示的实在——为基础,对于传统“善”与“美”二者所隐含的人类中心主义视野和偏见进行了反思和批判,从而暗示了“生态之善”与“生态之美”的存在。这是米克生态美学的内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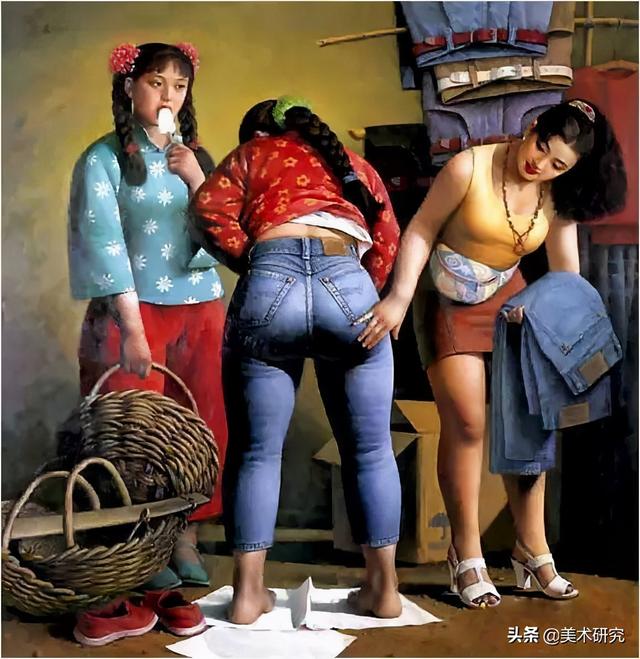
米克的生态美学在美学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可以概括为如下三点:一、在哲学思想的转变方面,米克生态美学的哲学基点是生态学所揭示的实在,以区别于传统哲学先验观念论中的实在。米克提出生态学是“一种富有潜力的关于实在的新模式”,这是他对于实在的一种新理解,这也是我们目前所发现的在西方哲学史与美学史上关于“生态学视野中的实在”的最早论述,最终启发笔者提出了“生态实在论”这一新型哲学立场[26];二、在生态美学与生态知识的关系上,米克特别主张审美理论应该借鉴一些生态学知识、生物学知识,由此才能更成功地界定“美”;三、从价值论的角度而言,米克反思并批判了西方现代美学的非生态性问题,由此克服现代美学中主客二分的审美方式、摒除观念论哲学与主体论美学中的“人类审美偏好”。在这样的意义上,正是米克的这篇文章将人类美学史从现代美学阶段推进至生态美学阶段,而米克也因此有理由被视为“生态美学之父”。对于本文而言,米克在生态美学的框架中所论述的“生态的艺术”具有很大的价值,尽管米克的探讨也是初步的——他只是提到了“生态的艺术”这个术语,尚未对之下定义,更没有对之进行详尽论述。
结 语
艺术观是统领艺术学的灵魂,生态艺术观则是生态艺术学的灵魂。建构生态艺术观的前提是追溯“美的艺术”的形成过程及其光环的根由。本文的梳理表明,塑造这种“艺术的光环”的主要是以巴特、康德和黑格尔为代表的现代西方美学,而米克的生态美学则为打破这种虚假的光环迈出了实质性的一步,初步提出并论证那种与“非生态的艺术”相对应的“生态的艺术”。

“生态的艺术”观念的兴起与生态美学有着密切关系,这一点对于我们建构生态艺术学具有很大的启示。自 1994年以来,特别是新世纪以来,我国的生态美学建构取得了长足的进展,我们也对西方生态美学进行了比较全面的梳理和研究。简言之,对于生态艺术学的理论建构而言,生态美学领域的成果足资借鉴。本文仅仅是一个初步的尝试。我们将会围绕“生态艺术美学建构”这个课题进行多方面的探讨,以期为我国的生态艺术学建构略尽绵薄之力。
【注 释】
[1]参见 Wladyslaw Tatarkiewicz. A History of Six Ideas: An Essay in Aesthetics[M]. Hingham: Kluwer Boston, Inc., 1980: 15.
[2]Charles Batteux. The Fine Arts Reduced to a Single Principle[M]. Translated with an introduction and notes by James O. Young. Oxford: OxfordUniversity Press, 2015: 3.
[3]笔者将撰写题为《“美的艺术”:beautiful arts与 fine arts之辩》的文章来详细讨论这个问题。
[4]参见 Paul Guyer. A History of Modern Aesthetics, Volume 1: The Eighteenth Century[M].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4: 253-254.
[5]康德在《判断力批判》的正文开篇之处就给鉴赏力做了这样一个定义,参见Immanuel Kant, Critique of the Power of Judgment. edited by PaulGuyer; translated by Paul Guyer, Eric Matthews, Cambridge, UK;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p.89.中译参考〔德〕康德 .判断力批判[M].邓晓芒译,杨祖陶校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2:37。
[6][7][8]Immanuel Kant. Critique of the Power of Judgment[M]. edited by Paul Guyer, translated by Paul Guyer, Eric Matthews. UK &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82,185,186.
[9][10][11][12][13][14][15][16][17]〔德〕黑格尔 .美学 .第一卷 [M].朱光潜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 1979:3,32,142,3,149,16,37,16,4.
[18][19][20][21][22][23][24][25] Joseph W. Meeker. Ecological Aesthetics[C]//The Comedy of Survival: Studies in Literary Ecology. New York: CharlesScribner’s Sons, 1974: 119-120,136,136,132,124,124-125,134,132.
[26]参见程相占 .生态美学的八种立场及其生态实在论整合 [J].社会科学辑刊.2019(1).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生态批评的理论问题及其中国化研究”(项目编号:19JJD750005)的阶段性成果。
程相占:山东大学文艺美学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副主任,山东大学文学院副院长
,免责声明:本文仅代表文章作者的个人观点,与本站无关。其原创性、真实性以及文中陈述文字和内容未经本站证实,对本文以及其中全部或者部分内容文字的真实性、完整性和原创性本站不作任何保证或承诺,请读者仅作参考,并自行核实相关内容。文章投诉邮箱:anhduc.ph@yahoo.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