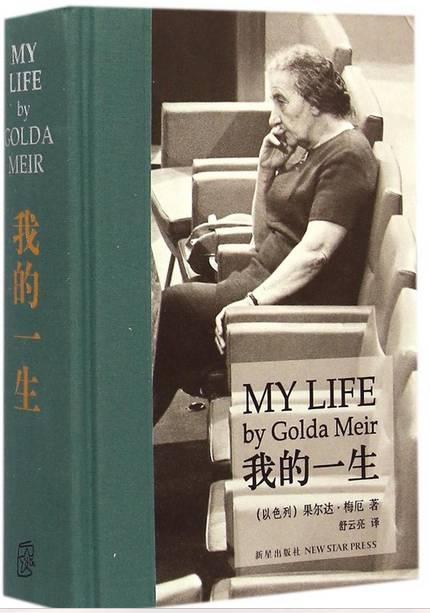老挝现在可以自己进国门吗(十九世纪末法国对老挝的)
大约在十九世纪末与二十世纪初,法国政府开始酝酿对老挝的“去暹罗化”政策,这项政策最初是通过经济手段隔绝老挝地区与暹罗的联系,不过,政策的主体却是在宗教与文化领域所开展的。从法国政府内部的一些资料显示:帮助老挝人重建民族化后的宗教与文化是应对当前危机的重要手段,而从后来法国殖民政府的实际举措来看,法国殖民者试图去除老挝社会与老挝人身上的暹罗文化,并在整个老挝地区重建一套新的的民族认同、文化体系与宗教。

但是,法国的“去暹罗化”绝对不是它所宣扬的“民族化”,这是因为,当暹罗对印支的威胁减弱后,法国的各种同化与压迫手段依然会接踵而至,因此,保证老暹在社会、文化与宗教领域的脱钩与维护法国的殖民利益才是其实质的想法。
一.经济政策经济利益是法国同暹罗竞争的核心利益。法国殖民者的目的很明确,他们既希望利用交通设施、移民与贸易等经济手段来保证“老暹脱钩”,有希望借此反击与消除暹罗在印支的经济与政治影响。1898年,法国殖民者放弃了为巩固“印支联邦”而架设的“西贡-河内线路”,转而采取了构建横跨安南山脉(越南与老挝境内主要山系)的公路线,这一通道形成了由北向南途径老挝内地并与沿海相连的交通网络,在公路线附近,法国殖民者修筑了大量岗哨,从而在纵向上切断老暹联系。

随后,法国在越南修筑的8号及9号公路线分别在1924年与1926年正式通车,这两条通过老挝的越南线路只是改善了越南境内的运输环境,却未能缩短交通距离,这是因为,两条公路在老挝境内均采取了通过道路、桥梁的方式切断老暹内河航运的做法。
在初步完善老挝境内的交通线后,法国殖民者又在老挝地区紧锣密鼓的进行着越南人移民计划,因为在法国人的眼中“只有越南人足够多,具有足够强的凝聚力和正确的人格,才能成功地参加战斗并粉碎那些团结的暹罗人”。在1912年前后,法国人首次向老挝派遣移民,之后逐年递增,在万象的越南人规模也从1912年前的4000人陆续增加到了1937年的12000人。这些越南移民在老挝担任公务员、工人与士兵,屯住在老挝的城镇、乡村和耕地,组建了许多配合法军占领的武装据点,在法国政府任意支配与雇佣下,他们被赋予了监视老挝人和抵制暹罗的重要任务。

不过,修筑交通与越南移民的举措并不能在经济上有效保障“老暹脱钩”,实际上,贸易活动才是暹罗与其他印支国家经济沟通的重要纽带,暹罗时常能通过贸易的手段来控制整个印支半岛,法国殖民者也逐渐发现“老挝与柬埔寨对我们的抗争源于暹罗对两地的经济控制力”。为抵制暹罗的经济影响,法国在老挝出台了两项反制举措,一项是在老暹边境严厉查禁法属印支人民的民间贸易行为,一项是将老挝变为它的商品倾销地,这两项反制举措均由法国总督统筹执行,旨在消除暹罗的经济影响、保障法国的经济利益。
但是,由于在暹罗的出口商品中,佛教用品占据了大多数的地位,而法国的商品难以找到市场,同样,印支人民狂热的宗教信仰与山地生活能力也不是法国人能有效阻挡的,因此,法国的贸易反制举措只能起到一些缓解作用,却不能解决根本问题。

宗教政策的举措是培养与扶持老挝本土的宗教信仰。1900年,法国殖民者将此前在越南设置的“法国印度支那古迹调查委员会”更名为“法国远东学院”,该学院被法国政府赋予了“调查老挝境内的佛经、抄本与古迹”的重任。自1909年起,法国殖民者根据德古的建议与远东学院所提交的《对老挝佛教古迹的调查报告》进而出台了一系列针对老挝的宗教政策,总结看来,主要分为以下三点内容:
一,在老挝全境设立各级佛教机构,法国在老挝设置的佛教机构主要分为四类。第一类为大型的佛教学院,其中以万象与琅勃拉邦等大城市的佛教学院、僧侣教师培训学院最为著名,培养本土的高级佛教僧侣、佛教知识分子为主要职能,同时还兼有编修本土佛经、抄本与画卷等工作,在招生对象上偏向于招收受过教育的老挝僧侣与贵族子弟。
第二类为佛教研究机构,包括设置于万象、琅勃拉邦、占帕塞克的佛教研究所与博物馆,这些研究机构主要从事对老挝佛教与暹罗佛教的调查与研究工作,例如,在1910年-1930年间,仅万象佛教研究院就给法国政府提交的调查报告与论文就高达900余份,其内容大多围绕于对“老挝人佛教信仰的特性”、“老挝人种族差异”等问题的探讨。

第三类为基层的佛教学校,基层佛教学校的设置在很大程度上源于法国殖民者对底层民众的担忧,原本,法国殖民者对底层民众采取了“愚民与奴化”的殖民策略,但碍于暹罗佛教对平民社会的巨大影响力,他们被迫设置了基层佛教学校来掌管对老挝底层民众的监视与教化,不过,所谓的佛教学校同佛教学院大为不同,佛教学校在管理上“重管制、轻教育”,聘用的教师多来自于越南,所执行的依然是法国殖民者对民众的“愚民化”策略,只是在少数课程上有强调本土佛教信仰的成分。
二,建设老挝本土的佛教古迹。该政策曾被法国谓之对老挝“佛教的复活”,法国学者罗兰·迈耶也强调“佛教的复兴不仅复活了这个古老的国度,还有力的抵挡了佛教曼谷对老挝人的影响力”。1915年,法国殖民者出资“修复”了位于万象的佛教圣地“塔銮寺”,在修复中,他们随意祛除了镌刻在塔銮建筑上的所有暹罗文字,将富有暹罗佛塔风格的“塔式层级”变为了“平竖角锥”的建筑特征,为笼络老挝人民,法国人还扩大了塔銮寺的建筑规模,用新编修的老挝文字对工程“立碑纪念”。

塔銮的修建作为标志性事件在老挝地区得到了推广,万象各地的佛教古迹都开展了“保护”、“修复”与“重建”的工作,法国殖民者为此制定了周密的计划,派遣了很多学者对老挝境内的佛教古迹、历史建筑进行了甄别,凡是带有暹罗文化与民族风格的古迹与建筑均遭到了破坏与清理,许多澜沧时代与分裂时期的历史建筑尤其是佛教古迹受到了修缮与推崇,不仅如此,为凸显万象佛教中心的地位,法国殖民者还煞费苦心的对万象的佛教古迹进行了大力度的宣传工作,许多出版的报纸、期刊与书籍都被印上了塔銮的宣传画与文字。
三,加强越南与柬埔寨对老挝的宗教渗透。在法国远东学院成立后,法国殖民者开始逐步向老挝派遣来自越南与柬埔寨的佛教法师、僧侣教师与佛教学者,这些佛教徒均在远东学院接受过不同程度的培训与教育,有些甚至有留学法国的西洋背景,他们大多活跃于老挝的大型寺院、研究机构、佛教学院乃至正规学校,少数人士被派遣到政府机构充当顾问,成为了法国对老挝“去暹罗化”的主要的执行群体。

文化政策是法国对老挝“去暹罗化”政策中最为重要且内容最为丰富的方面,法国试图重建一套新的文化体系来对老挝人进一步“去暹罗化”。1921年,法国政府起草了一项在老挝地区的总体行动计划用来对抗来自暹罗的挑战,其计划的原则是潜移默化的培养老挝地区的土著民对“老挝”与“老挝人”的时空认同,舰队司令德古在写给驻老官员罗杰斯的信中指出“那些很少费心去看关注外部世界的老挝人必须意识到,从现在开始他们属于伟大的老挝人”,之后,他还继续讲到了文化的“复兴”,这封信件释放出了法国对老挝地区在文化领域的“去暹罗化”。
随后,法国政府以法国驻万象公共教育主任查尔斯·罗切斯特、努伊·阿普海和卡泰·唐·萨所利特为首的一批驻老官员直接开展了重建老挝文化和身份认同的“复兴活动”,在运动的引领下,老挝人民被赋予了共同的民族身份,这种身份是以纯粹老挝人为民族特征,同化所有的老挝人民。

首先,法国殖民者着重于对老挝学校的教材、教学内容以及教学规模的“改革”。在教材方面,所有教材均刻意规避了暹罗与老挝的关联,法国殖民者于1918年和1921先后进行了两次教材改革,第一次是1918年首批老挝语教材的编修出版,学者宋金·皮埃尔·宁亲自曾参与了教材的编写,他本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这些教科书的重要性在于,它们是第一部将前代时期一系列国家及其国王作为20世纪老挝的前身予以呈现的常规民族史”。
第二次是在1921年,由法国殖民者发起、编撰和出版的第一批老挝基础历史教科书,相比于前者而言,这些教科书令人瞩目的地方是:这些书在开始的部分就探讨了老挝南部孟-高棉的少数民族及其与占婆古代文明的联系,从而巧妙的的弱化了老挝人来源于西部更广阔的傣族世界的事实。

在教学内容方面,法国殖民者按照西方课程的模式对教学课程进行改革,新编修的课程分为法语、历史、地理、几何等课程,新编修的老挝地图是以湄公河以东的老挝人聚居区,学生在学校所学的第一课就是潜在的民族标志,如老挝的概念与地图、老挝人的历史来源,虽然还以法语课作为学校的主科,但新编修的老挝语教材已经在许可下选用,另外,法国殖民者还在学校名义上推行所谓的“双语教学”,也就是允许老挝语与法语同时被作为老挝学校的教学语言,但严禁教师与学生讲暹罗语(包括暹罗境内的少数民族语言),为保证教育的“可靠性”,所聘用的教师仍以法国教师或精通法语的越南教师充任。
在二战结束后的四十年代末至五十年代初,此时的“暹罗威胁”早已不复存在,法国殖民者露出了它的本来面目,重演了他在殖民初期对老挝地区强推法语的举措,这是法国人的最后一次“语言改革”,此次语言改革再次遭遇到老挝精英阶层与老挝人民的强烈反抗,已成为强弩之末的法国殖民者最终放弃了它在老挝的法语政策。
,免责声明:本文仅代表文章作者的个人观点,与本站无关。其原创性、真实性以及文中陈述文字和内容未经本站证实,对本文以及其中全部或者部分内容文字的真实性、完整性和原创性本站不作任何保证或承诺,请读者仅作参考,并自行核实相关内容。文章投诉邮箱:anhduc.ph@yahoo.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