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幻新时代即将开启(扑面而来的科幻新风)

扑面而来的科幻新风
——评刘洋新作《火星孤儿》
文 | 徐彦利(河北科技大学)
《火星孤儿》是一部极富个人特征的小说,在佳作林立的国内科幻文学中或许不是最好的,但不可否认它清新自然的风格独树一帜,与普通硬科幻有很大区别,在一定程度上回避了科幻文学的形式化倾向,如新风扑面,某种意义上打破了科幻题材的拘囿。
科幻在许多人脑海中往往是凌空蹈虚的代名词,一个“幻”字已拉开了与现实的距离,将故事提至云端,书写那些不着边际的想象与不可实现的情节。纵观中外许多科幻名作很多可归入此类,如经典名作《弗兰肯斯坦》《莫洛博士岛》《时间机器》《万有引力之虹》《月球殖民地小说》《新法螺先生》等,故事基本不可能出现在现实社会中,只是想象的产物而已。
《火星孤儿》的核心主题星际救援、拯救地球等虽然也与现实有一定距离,但在叙述上却将科幻之“虚”与生活之“实”紧密联系在一起。我们可以看到,极富现实性的社会话题——高考是全篇的经线。在这条线上,赫然展现的是全封闭式高中,调动学生一切积极性,使主动与被动相结合的学习氛围,其间夹杂的高考知识、高考题型、高中管理、学霸、课堂、成绩等,无不充满活在当下的气氛。甚至每一章前面都特意加了一道真实的高考题目。除最后一道为2035年高考题是杜撰外,其余均确有其事,叙述环境给人一种身临其境、宛在身边的感觉。这一经线上还有隐形的辅线,即将现实合理化想象与夸张的结果,如用绩点来消费,建立在考试成绩基础上的学生贫富分化机制,临时饭卡充值需要回答试卷,查寝老师可以随意翻动学生的私人物品;饥饿感官教学法等。辅线使经线更加粗壮丰满,质感明确。
而纬线则是外星文明面临氦闪危机,急于逃离母星,向地球发出求救信号,人类为了破译这些暗藏玄机的信号制定出“263计划”。经纬两条线以近腾中学为纽结点并进行纵向、横向的并行推进,将不同维度的故事紧密编织在一起,密密匝匝,风雨不透。于是,在高考题材的包裹下,将社会性、民间性与科幻的想象性、虚无性糅合在一起,如云端之月与地上雪泥的交融,造成强劲的阅读张力。当作者凭借灵活自如的叙述能力将二者牢牢绑缚在一起时,读者会发现隼卯结合严丝合缝,没有令人不适的凹凸粗糙之感,超出许多人对科幻固有模式的认知。
普通科幻小说常常采用的时空模式在这里被颠覆了。一般而言,传统科幻小说中的时空观常带有某种特殊的假定性。暧昧不明的时间,常发生在远古或未来;遥不可及的空间,常设定在异国他乡、遥远边陲或宇宙深渊,这样,才使“幻”的出现合乎情理,摆脱日常的局限。而《火星孤儿》中的时间却是离当下不远的2035年,地点则是一所普通高中。那里对成绩的重视与现行社会毫无二致,在校生也与我们身边的高中生毫无差别。但与一般校园科幻不同的是,小说并未有意取悦低龄读者,未将中学生设为特定读者群,甚至也不从少年视角出发,设置过多未成年人情节或心理描写,相反,它是以成年人成熟的心智来审视与打量这个世界的,因此,《火星孤儿》不宜归入校园科幻系列。
在创作方法小说进行了有益的尝试,显示出将中西创作手法融于一体的倾向,在这里,我们既可以看到中国传统的现实主义,也能看到源自西方的批判现实主义、黑色幽默和拼贴结构,呈现出一种杂糅兼容的特征。
剔除小说的科幻元素之后作品的整体叙述手法无疑是现实主义的,其中的情节描述、人物形象塑造与性格刻画均与纯文学无异,而在关于教育体制的描述中,则又体现出批判现实主义的格调。提到批判现实主义读者多会想起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司汤达《红与黑》,萨克雷的《名利场》等,它们往往承载了对现实的不满与质疑,显示出严肃文学正襟危坐的气质,是一种强力干预现实的手段。
通常意义而言,科幻小说自带的批判色彩并不浓厚,这与其题材的特质相关,类似《猫城记》《一九八四》等高度影射现实的科幻作品并非常规类型。科幻的天马行空与虚构气质更多指向未来,与当下社会的平行性较差。试想,无论写作水平多高,写你隔壁的邻居怎么也不易成为科幻。而《火星孤儿》中,对教育体制的深入思考则带有某种批判色彩。那些只顾给学生灌输知识,训练答题技巧,只侧重应用、应试而忽略知识内涵,不探讨知识产生过程及背后原因的教授方式,对于学生的自我思索、自主观察有害无益。学生成了考试机器,不能将所学知识灵活运用于实践,充分暴露了应试教育的弊端。这些对现实积弊的诟病无疑超越了科幻范畴,成为对当下社会问题的探讨。当读者读到学校里没有法律,没有道德,不能联系家长,甚至不能退学,便能充分感受到现实中的人被偏执目标异化的过程,用作者的话而言,这部小说“既暗示了外星文明所困的位置也隐喻了人类的困境。”对现实表现了强烈的忧虑与质疑。
正是因为对现实的质疑,作品的时间设定、人物设定、情节设定均体现出热闹喧嚣的生活之流。与当下如此切近,人物似在身边。那些波澜起伏的情节,环环相扣的悬念,引领读者走入距离地球三万六千公里的近腾学校,它虽然遥远却又切近,虽然虚幻却又真实,与国内任何一所高中都无比相似。在故事情节的设置中,作者显示出较为从容的编排能力。从现实高中、备考、紧张氛围到地球大面积着火,电力中断,接着写满试题的奇怪石碑浮出,寻找能够解出石碑上古怪题目的人,于是选中近腾中学,想从学生中发掘解答人,近腾中校原来并不在地球,而是位于空间轨道上,能否解开石碑上的问题成为解决电力中断的关键,回答正确后石碑就会落地,一英里范围内的电器也会恢复正常……这些情节的设置步步为营,彼此交融渗透,不断将读者拉至情节深处,叩问最为关键与核心的节点。能否找到解答人,这些超越人类认知的问题到底是怎么回事?导体怎样变成了绝缘体?火灾与断电的真正原因是什么?石碑是恶意警告还是善意询问?诸多问题像洋葱一样层层包裹,需要更深阅读才能一步步解开,直开书的最后一页才能最终找到答案。
情节进展中,小说并未直奔引人入胜的科幻创意,而是张驰有度,舒缓得当,关注细节刻画,在紧张激烈中时时加入悠徐自然的格调,使叙述节奏快慢结合。如在描写太空站大气循环系统时,插入对云室四周辉煌景色的描述,在渲染学校苛刻的管理时,插入古河对书籍的品读和见解,在对高考知识的描写中,插入教师李翊君的教育理念,在描述阿木怪异性格时插入令人同情的成长经历及心理变化。有意降低了科幻的知识硬度,闲笔逸趣有效增加了小说的可读性。可以感知到作者利用科幻这一题材的同时又想挣脱科幻的束缚,将宏观的宇宙与微观的个人结合起来,既写宇宙之大也写苍蝇之微,将头绪纷纭的世界,不同层次的红尘众生统摄在视野中,一一加以放大并悉心观察。
作为科幻小说,作品中的科幻元素十分明显。如重力感应游戏,阿尔法波催眠音乐、电击项圈、眼睑中的纳米摄像机等轻科幻,也有二维宇宙、暗物质、电子河流等数理化生及航天学方面的重科幻。轻科幻与生活的相关度较高,不以严谨的科学知识为前提,更多带有设计感与创意性,并不做深入分析。重科幻则言出有据,引经据典,充分符合科学规律和原理,带有某种前沿性与可探讨性。前者满足了人们对高科技渗透日常生活的想象,后者则体现了作品的知识含量与理论深度及学术逻辑性。在这里,作者既表现出一个普通人对未来高科技社会的种种畅想,也表现出一位物理学家的严谨与知识储备。
幽默是一种叙述的智慧,也是一种诉诸于智商的情趣,幽默的语言往往使阅读变得愉悦与活泼,可延展阅读的内涵,如《围城》。用幽默的语言揭示了特定年代知识分子的坎坷与遭际,少了晦涩、沉重与枯燥,读来令人忍俊不禁。《火星孤儿》中亦体现出这种幽默的追求,虽然涉及到阴谋、灾难、荒谬,但语言却并不阴郁,而是明快、轻松,如介绍如何在课堂上看漫画书等,消解了科幻一本正经的严肃,易让人产生阅读快感。“睡意像军队一样坚定而有节奏地袭来”,“即使不用刻意去记那些公式和大段文字,只要它们从眼前经过,便深深地印在了脑子里,就像发霉的衣服上出现的黑斑,无论如何也洗不掉了。”这些充满新意的句子体现出作者试图冲破古板、僵化,从细节处观察与体会,丰富语言,凝词炼句使科幻小说充满趣味的努力。
黑色幽默与幽默不同,虽然它同样能让读者发笑,但笑声中却流露出某种无奈,更适合彰显社会的病态或荒诞。《火星孤儿》中的叙述语言常体现出幽默的一面,轻松、搞笑抑或滑稽,但情节则更多体现了黑色幽默的手法。
如对近腾中学本部的描写,这所以高考成绩闻名的学校到处充斥着非人的管理、不近人情的制度。下课时间只有九十秒,不够上个厕所,于是学生不敢喝水;阿木喝掉十几瓶蓝水后,神经变得不太正常,但成绩反而提高了,变成了一台只会做题的机器;紧迫答题训练课上,学生们在水中答题,答对了才可露出水面自由呼吸;为了检查学生的课外书而安装扫描仪,同学们一个个通过安检,类似登机检查;把学生关在小黑屋中的惩罚等。
这些描写质疑了现行教育体制中不尽人意之处,批评了为提高成绩而采取的极端作法,让人不禁想起约瑟夫·海勒的《第二十二条军规》,太空轨道上的近腾中学也让人联想到地中海里的皮亚诺扎岛。给学生套的电击项圈,可二十四小时监控学生作息,号称“生活辅助系统”,事实上却把人变成了项圈的奴隶,甚至宠物狗。与《第二十二条军规》中沙伊斯科普夫少尉的练兵奇想十分相似,沙伊斯科普夫少尉为了阅兵比赛上能使队列整齐划一,异想天开的想在学员的股骨上打进镍合金钉,再用三英英寸长的铜丝把钉子和手腕连接起来。二者都忽视了人应有的自由与权力,将人视为无生命之物随意处置。近腾中学里,一句“为了孩子”便可将孩子控制起来,使他们无法逃脱。皮亚诺扎岛上的飞行员们则因为那条无处不在又永远看不到的“第二十二条军规”而无法复员,无法摆脱战争。虽然二者的现实指涉有一定分歧,但《火星孤儿》对黑色幽默手法的运用却极为显著。它使人发笑的同时促人反省,引人深思。不得不说,脱去科幻色彩之后,小说对高考的一些思考切中肯綮,对当今社会过于重视成绩而忽略教育的根本目进行了批评。
此外,小说还体现较为明显的中国化倾向。长久以来,科幻似乎与西方有着某种不解之缘,无数奇异故事的发生地均在欧美,或非洲,或亚洲其他国家,真正以中国为空间背景的相对较少。近年来刘慈欣的《地火》《中国太阳》《乡村教师》,王晋康的《血祭》《蚁生》,何夕《六道众生》《天生我材》等很大程度上纠正了这种倾向,显示出“走中国科幻之路”的强烈意愿,使读者能在科幻小说中读到中国人物、中国思维、中国文化。《火星孤儿》中亦明显体现了这种中国作派,无论东吴、茂州、成都那些中国风的地名,还是关于社会现实的多层次描写,以及“中国是迅速崛起的超级大国”等论断,均显示出有意的中国化特征。将科幻情节放置在中国语境中,带有某种民族化情结地考察宇宙大背景下中国人的科技能力及处世方式,成为作者显在的追求。
《火星孤儿》是一部匠心独具的作品,它提示人们书写科幻的方式可以有很多,甚至可以从最寻常、最身边的人与事切入。这让人想起刘慈欣的一句话,“科幻文学的最大优势就是其丰富的故事资源,这种资源由科学技术的进步源源不断地提供着。这是任何其他文学体裁远远不能比拟的,科幻文学不能急着去走形式化这条艰难的道路。”(刘慈欣随笔《重建对科幻文学的信心》)科技发展无疑为科幻小说的创作提供了永动力,但即使科幻创意有彼此的交叉重复,每个文本依然可以拥有自己的独特之处,在题材的互文性下为文坛带来不一样的叙述,这取决于作家们非凡的创造力。正因为如此,科幻才能最终成为一个生生不息的文学增长点,而非类型化的桎锢。
当然,每部科幻小说都有自己的不足,即使一流科幻大师也未必写出十全十美的作品。《火星孤儿》前半部分现实过多,铺垫过多,科幻成分相对稀薄,甚至让人误以为是一部反思当代教育体制的作品,而后半部分则科幻成分堆积,科幻元素叠加到漫溢的地步,公式、定理、二维宇宙元素周期表等密集的科学分析与之前的现实主义描述有分离之感。另外,对于人物的刻画也相对较弱,学霸文仔、阴谋家索罗,做题机器阿木等,虽性格鲜明但多是通过叙述语言直接交待,而非通过情节进展、人物语言自然彰显,略显生硬。不过作为作者的第一部长篇科幻小说不可求全责备,作品已显示了许多不俗之处,完全可以期待后续之作愈加厚重、坚实,成为中国科幻文学重要的组成部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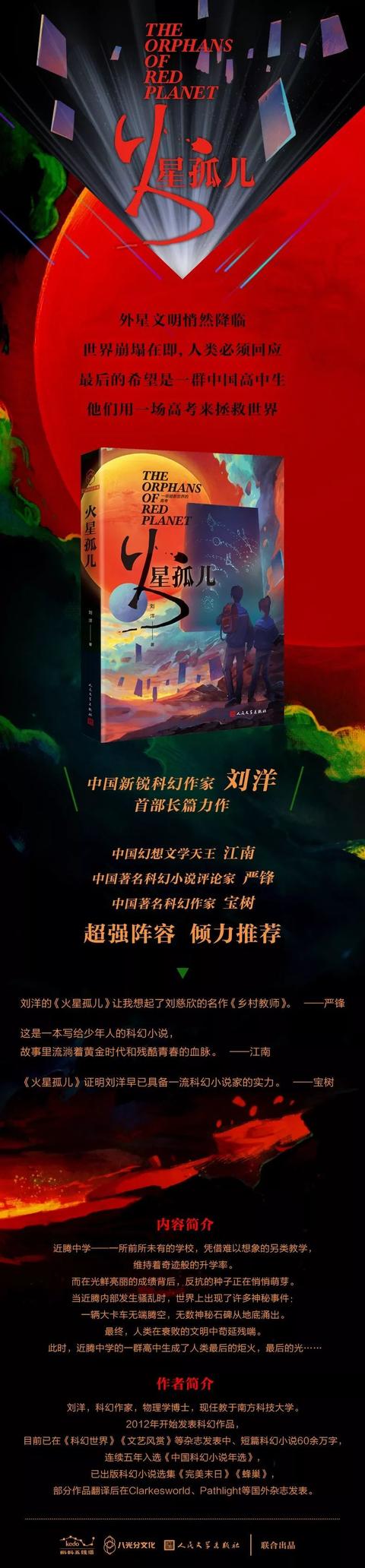
扫描上方二维码 即为购书链接
,免责声明:本文仅代表文章作者的个人观点,与本站无关。其原创性、真实性以及文中陈述文字和内容未经本站证实,对本文以及其中全部或者部分内容文字的真实性、完整性和原创性本站不作任何保证或承诺,请读者仅作参考,并自行核实相关内容。文章投诉邮箱:anhduc.ph@yahoo.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