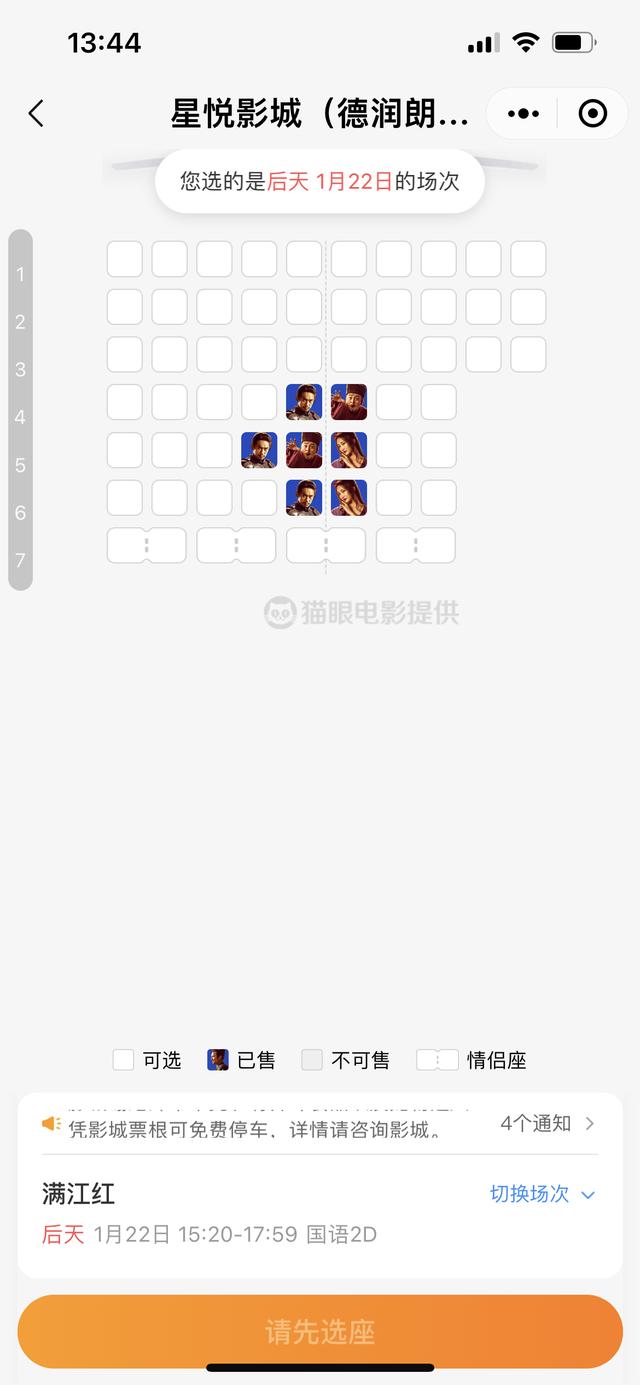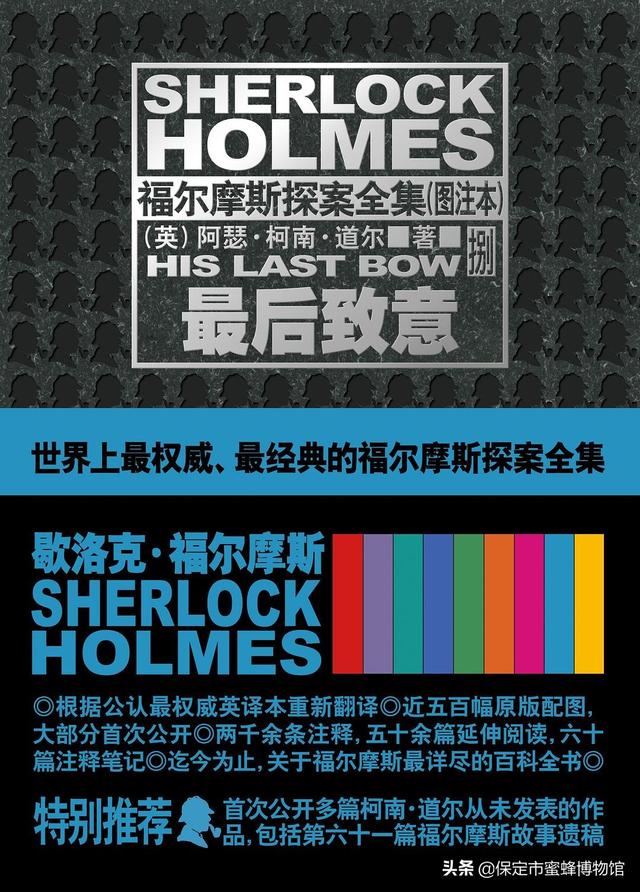一个大家庭的和谐取决于(大家庭的成功是一个悖论)

1978年的张晓刚、叶永青和刘涌(左起)

张晓刚《血缘——大家庭17号》,1998年

张晓刚,当代艺术家。1958年出生于云南省昆明市,1982年毕业于四川美术学院。
2月23日,“M 希克藏品:中国当代艺术四十年”在香港展出。作为中国当代艺术发展中举足轻重的人物,艺术家张晓刚出席了展览的开幕活动。
在三小时的睡眠后,他于次日中午回到昆明,为家乡的本土艺术活动站台。正是从这座中国西南边陲的城市出发,张晓刚成为中国当代艺术“西南现象”中的重要人物。
在成为天价艺术家之前:
不要成为“那两个人”
虽然上世纪80年代的昆明艺术家把贯穿这座城市的盘龙江,比作巴黎塞纳河,而80年代当地文艺青年的据点——张晓刚的宿舍则是他们心中的“左岸”。但至今,张晓刚依然认为那时的护城河颜色是深灰的,毫无光泽。
张晓刚自小性格内向,极不自信。跟随林聆先生(中国当代水彩画家、油画家)学画期间,他成为昆明美术圈的一个另类,被大家认为老套,他也常常怀疑自己;进入川美后,由于不擅长素描,学习过程几成折磨;毕业创作方案一开始得不到学校通过;毕业后被发回原籍云南等待分配,工作没有着落……
读书时期,张晓刚和他的同学叶永青常是被“嘲弄”的对象。由于两人都来自昆明,所以两人在学校有一个绰号“云南两怪”。他们的画作与“伤痕美术”、“乡土艺术”不同,偏向西方现代主义技法。他们的现代艺术价值观,在当时被认为是没有出路;甚至有保守的领导告诫学生,不要成为“那两个人”。
当时,有一位台湾收藏家来到他们班里面选画,很快就把叶永青和张晓刚的拿回来了。他们一听很开心,以为自己的画要被特意收藏了。万万没想到,收藏家的意思是,除了他们两个人的画,其他的都要。
事实上,张晓刚并非不勤奋。准备毕业创作期间,张晓刚一个人留在阿坝,像他的偶像凡·高一样画画。40多天一共画了300多张速写,十多张油画,拍了六筒胶卷。除了睡觉,就是画画。
在心绪最乱的时候,喜欢独行的张晓刚一个人跑到了四川大凉山。他喜欢大凉山高贵的灰色色调,欣赏那些沉默寡言与大山作伴、与天空对话的当地人。他甚至觉得,当地人那种通过酒精独自漫游山巅的半神半人状态,和自己的生活有几分相像。
张晓刚后来总结,自己几乎事事都慢人一拍,但最后一刻总是遇到贵人,所以“什么重要的事情都没有错过”。比如由于林聆教授的绘画模式来自严肃的欧洲传统,让张晓刚成为了第一个考上川美的云南人;时任《美术》杂志编辑的栗宪庭到川美组稿,肯定了张晓刚的创作,学院马上通知他去领创作材料;当他成为云南唯一一个未分配的大学生,昆明歌舞团团长毫不费美术劲地接收了他……
以《大家庭》作品取得非凡成功:
与幸福的家庭生活始终无缘
张晓刚作为中国当代艺术界的“带头大哥”,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保持着中国当代艺术拍卖的最高个人纪录。
2014年4月5日21点15分,香港苏富比举行的“现当代亚洲艺术晚间拍卖”会上,张晓刚的《血缘:大家庭3号》以5000万港元起拍,最终以8300万港元落槌,含佣金成交价为9420万港元——刷新了2011年他的另一作品《生生息息之爱》的7906万港元的拍卖纪录,并成为中国迄今为止最贵的家庭记忆文本。
张晓刚自1993年起创作的《大家庭》系列,画中的形象在中国当代艺术中极具标志性。他说,《大家庭》系列的灵感来自一批摄于新中国成立后的全家福照片——他以为这些照片早在“文革”时期被销毁,却在无意中重新发现。画中男女人物的面部细节几乎一模一样,暗示个性的缺乏,这引发了张晓刚创作的冲动。张晓刚通过这一组作品摆脱西方美学的影子,以个人历史叙述及集体回忆为主调,成功确立了清晰的艺术定位。
2003年开始,中国当代艺术以不断攀升的天价作品以及人气极高的艺术明星,吸引着国际艺坛的注意,而张晓刚是其中最具代标志性的人物。时隔多年,他这组创作于上世纪90年代的《大家庭》系列,仍然不断地在很有分量的展览上、拍卖场上频频露脸、制造着新闻标题。
叶永青曾说,张晓刚画了一辈子的《大家庭》系列,自己的家庭却一度千疮百孔。1982年,刚毕业的张晓刚被发回原籍云南等待分配。他和家人的关系一直很淡漠,甚至和父亲时有冲突。他例行每周回家一次,吃完饭就走,或者是借钱。
后来张晓刚说:“一个人的生活经历,肯定会在他的作品中变成一种反映,我一直渴望家庭生活,但是跟幸福的家庭生活始终没有亲近的缘分。因为我和父母的感情,始终是有隔阂的;兄弟之间的关系,说远不近;包括自己组建的家庭,最后也没有成功,也散伙了。但我却是画《大家庭》而成功的,这是一个悖论。”
访 谈
2月24日中午,在昆明翠湖畔的一家餐厅,羊城晚报记者见到风尘仆仆的张晓刚。他坐下不久,就和周围的老友寒暄,说着他在美国的女儿,整个人逐渐带劲起来。张晓刚的声音中透出自豪:最近女儿告诉父亲,她喜欢了一个怎样的男孩。
1
每一步都与国家开放有关
羊城晚报:在您艺术生涯起步之时,现实主义、写实主义艺术传统所占的比重还是比较大的。你也经历过比较痛苦的时刻,后来在大学三年级时才找到自己的一种方法,这个过程大致是怎么样的?
张晓刚:我们的每一步其实都跟国家的开放有关系,因为时代变迁以后、人的眼界打开了,并不一定都是自己的选择。1979年,国家开放了,对于我们而言最重要的是图书馆开放了,一些印象派、后印象派的画册就开始出现。我记得当时有一套日本出的普及版《西方二十世纪艺术》,这套书现在来看印刷质量是很差的,但是对于当时的我们而言就像是金子一样,每天都想着去看。
从那个时候我们开始接触到一些现代主义的东西,再后来是一些美术杂志的出现,例如中央美院的《世界美术》。这些杂志开始陆陆续续介绍西方现代艺术。可能因为年轻,对于前苏联的那套艺术模式我不是很适应,对古典的也不太了解,但对西方现代的东西非常有兴趣,这样就一步一步从后印象主义到表现主义开始学习。到了毕业的时候我已经基本确定了自己要当一个现代主义画家,其实那个时候也不大知道现代主义的意义是什么,但就有这么一个冲动去做。我的毕业创作也是现代主义创作,在当时也没有通过。毕业以后,才发现这是很艰辛的一条路,跟整个社会的主流价值都不一样。
羊城晚报:那么对于你来说,最大的艺术转折点会不会是1992年去威尼斯参展?
张晓刚:人的一生往往有几个转折点,于我的人生而言,第一个转折点是认识了林聆先生,他把我带上了这条路,教会了我很多,包括如何做人、对待艺术的态度等等。第二个转折点就是考上大学,如果没有去四川美院,我就不可能对艺术有什么系统认识。第三个转折点就是我开始喜欢上现代主义,选择了这条路一直走到今天,这是最适合我的一条路。我在昆明工作的那几年,从思想到情感、价值观都奠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那四年感觉又读了一次大学,自修了关于现代主义的知识。到了1992年参展,可能是我在艺术上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找到了这辈子基本的一个艺术方向。
2
“先锋”“前卫”的头衔有点勉强
羊城晚报:“中国当代艺术四十年”正在香港展出,你怎么看自己在中国当代艺术界的定位?
张晓刚:四十年走过以后,我几乎忘了自己是一个所谓的前卫艺术家,实际上我也一直没有这样觉得,我并不看重这个东西,因为从一开始,我只是决定要成为一个真实的艺术家。
当时要面对的主流文化是一种虚假的东西,但我想要把自己最真实最真诚的情感表达出来,这是一个底线。那时候我和老栗(栗宪庭)聊天时,就说我不愿意做什么前卫艺术家,前卫艺术圈给我的印象并不好,有很多东西我也看不惯。但是没有办法,你处于这样的浪潮里面。
羊城晚报:但人们都把你视为当代先锋艺术的代表人物。
张晓刚:后来所谓的“先锋艺术”、“前卫艺术”的头衔我觉得是社会强加给我们的。1992年的时候我去欧洲看前卫艺术,一点都看不懂,完全不懂它上下文的关系。而且四川美院培养出来的学生都拥有人文情结,国内的前卫艺术偏理性,是思辨以及反浪漫主义的。严格来讲,我们这一批“老现代主义者”应该是被前卫批判的对象。但因为大家都是社会边缘人物,所以就被带到现代主义的队伍里面了。
作品才是一个艺术家的关键,你的作品有没有自己的文化特色,自己的价值,在世界的美术史能不能留下自己的东西,这是我想要追求的。最重要的不是你处于哪个艺术潮流里面,你在江湖中的位置怎么样,这些都是虚的,最重要的是,艺术是个人的。
3
每天想成功学,会离成功越来越远
羊城晚报:大约在2005年前后,中国当代艺术进入到一个备受社会市场关注的时代,你是聚焦灯下非常重要的角色,也被很多人认为是很成功的艺术家。那么你认为艺术家成功的标准是什么?
张晓刚:这个社会学上成功的标准,是你的作品卖的钱很多,获得的荣誉、地位、机遇比别人多,那你就是一个成功的人。但是艺术家更加看重的应该是艺术上、文化上的成功,这种成功的意义就是你个人的奉献,个人在美术史上的价值。
社会学上的成功会给我带来很多方便,画卖得好那当然会很开心。但你最终还是要选择愿意或不愿意成为一个真正的艺术家,因为成功就是这么一晃而逝的,今天你在浪潮上,明天可能就会下来,这是一个自然规律。
对于我而言,艺术像一条河流,一直流淌不息,突然在某一段会成功,但是没有之前的积累,成功是不可能的。在生命结束之前,你还是要不停地以作品来前进。如果每天都在想着成功学的问题,你就偏离这个行当了。
羊城晚报:从一些回忆录里可以发现,您非常勤奋,之前也有传闻您因为画画心脏不舒服而进了医院,这是真的吗?
张晓刚:是真的。前几年我就发现心脏不舒服,但是没有注意,后来到医院做了个小手术,医生告诫不能喝那么多酒,还要注意锻炼,我用了一年多两年的时间将身体调养了回来。
羊城晚报:其实对于你来说,现在是不是已经不需要这么拼命了?
张晓刚:我并没有觉得我拼命,艺术家有两种:一种喜欢在外面活动,另一种喜欢待在工作室。我属于后者。让我每天在外面跟别人接触,一天两天可以兴奋一下,但是到了第三天就受不了了。工作室是我每天必须要待的,在里面我才能感受到自己的存在。艺术家的自信、存在感,所有的感觉以及思考的东西都应该在工作室。
4
只有画画才能让我最踏实
羊城晚报:你的艺术因为《大家庭》而被大众所熟悉,那么您的大家庭是怎么样的?
张晓刚:我是靠《大家庭》获得大家的承认,但是我的家庭并不是那么的一帆风顺,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件很无奈的事情。我的父母以前一直在学校很忙,到了我自己成立的第一个家庭,也并没有一直走下去,后来又组建了另一个家庭。一路走过来,我也觉得挺好的,可能也是上天的意思,人生总得经历一些波折。
我的《大家庭》其实也有受现实的一点影响,这就像艺术家在写日记一样,记录心路历程。生活中所有发生的事情在我心中都是一种体验,直接或间接地抒发出来,成为我的艺术。《大家庭》是对我个人家庭的一种反映,也是我对社会的理解。
羊城晚报:你曾经在深圳也有打工的经历,那么您对广东的印象是怎么样的?
张晓刚:1984年在深圳大学有一个艺术中心,那会儿人年轻,非常好奇,觉得深圳是一个最开放的地方,我就去那里工作了两三个月,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累得要死,还没能赚到多少钱。回来以后,我就坚定了要做艺术的决心,我做不了打工的人。也有人投资约我拍电影,我想都不敢想,也许未来哪天想通了我会去,但至少现在只有画画才能让我最踏实,也是最让我能够投入的工作。
图片说明
1978年的张晓刚、叶永青和刘涌(左起)
1977年高考恢复后,艺术生从西南各地奔向四川美术学院。十年浩劫后的“川美”,聚集了各年龄层的人才,其中77届有“四大金刚”何多苓、高小华、程丛林、罗中立。
翌年,叶永青从昆明考入川美。他和张晓刚、周春芽同一寝室,隔壁是程丛林,对面住着罗中立。如今,这群当年的青年学生已经成为中国艺术界中不可忽视的人物,他们所引领的“西南艺术现象”也在中国当代艺术历程中留下了浓重的一笔。
图片说明
张晓刚《血缘——大家庭17号》,1998年
1994年张晓刚的《血缘:大家庭》出现在“第二十二届圣保罗双年展”上,这一系列被诗人欧阳江河誉为美术史上第一次明确出现“中国人的脸,中国人的家庭,中国人的历史”的作品,为张晓刚本人以及中国当代艺术步入国际艺林获得了无数荣誉。
关于作品的源起,张晓刚1995年在《自述》一文中阐释:“构成近期作品的因素,除了历史和现实所赋予我们的复杂心理外,直接的灵感来源出自私人家藏的旧照片,以及中国大街上随处可见的‘炭精素描画像’。我无法说清楚那些经过精心修饰后的旧照片究竟触动了自己心灵深处的哪一根神经,它们使我浮想联翩,爱不释手。也许正因为处在今天的时代中这些旧照片已不仅仅给人某种怀旧心理的满足感,也许它们所呈现出的某种单纯直接而又充满了某种虚幻的视觉语言方式,验证了我对高深莫测的样式主义以及虚夸的浪漫主义的厌弃心理?同时,旧照片和“炭精像”一类的图式语言,体现出我非常熟悉而又曾经不屑一顾的东西,其中也包含著中国普通人长期以来所特有的某种审美追求,比如模糊个性而强调共性,含蓄,中性而又充满诗意的审美特性等等。”
,免责声明:本文仅代表文章作者的个人观点,与本站无关。其原创性、真实性以及文中陈述文字和内容未经本站证实,对本文以及其中全部或者部分内容文字的真实性、完整性和原创性本站不作任何保证或承诺,请读者仅作参考,并自行核实相关内容。文章投诉邮箱:anhduc.ph@yahoo.com